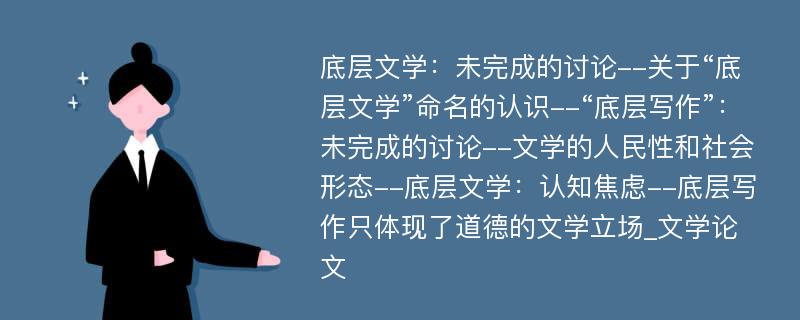
底层文学:未完成的讨论——关于“底层文学”命名的知识问题——“底层写作”:没有完成的讨论——文学的人民性与社会形态——底层文学:认知的焦虑——底层写作仅仅体现了道德化的文学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底层论文,文学论文,人民性论文,社会形态论文,未完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道德同情和社会批判为特征的“底层文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典型的“问题文学”,对“底层文学”的讨论乃至争论,不仅彰显了中国严重失衡的社会关系,而且也透视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某些缺失。文学绝不是社会生活的简单附属,亦不会躺在艺术的象牙塔敝帚自珍,在强大的社会现实而前,文学既要有自我的独立,又要有敢于对社会发言的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讲,近几年引发广泛讨论的底层文学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因此,我们特邀在文学批评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对底层文学进行讨论。
——主持人 叶祝弟
关于“底层文学”命名的知识问题
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当下的文学状况,已经名符其实沦为全球化背景下消费主义盛宴的一部分,它在一个极其肤浅的层面上全面参与并且复制了一场有关盗墓、玄幻、动漫、股票、基金、商界阴谋、企管手腕等等甜蜜蜜、晕乎乎的娱乐秀。若要为这台娱乐节目寻找正当性的话,除去现代性紧张以及后现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诸因素之外,由思想的苦闷乃至思想的寂灭转生为怪力乱神的想象力,庶几成为可理解的原因。应该看到,国人吁求了百余年的个性等权利主张终于水落石出之后,这类标举“审美自治”的写作至少在形式上有其合法性,尽管它们一向都是置身于社会历史之外和敝帚自珍的。
然而这只是真相的一部分。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真相是,“底层文学”的横空出世,它并不构成对上述消费主义写作的直接抗击,但它却是一次抗议性命名。“底层文学”算得上是近年来惟一一个具有社会公共性意义的文学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意义更多的属于历史而不是文学。之所以如此概括,乃是考虑到它的鲜明的社会问题指向,就此而言,“底层文学”之所以自己无法成长为某些学者所期待的审美风尚,这需要在历史变迁大格局中加以体会和理解。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与辨识,非常致命地考核着讨论者自身的知识能力。因此,对我个人来说,“底层文学”到底讲述了什么,远不如我们如何讲述“底层文学”来得更加迫切和真实。
作为一种携带重要社会信息的文学实践,“底层文学”在概念的命名方式上承继着20世纪以来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而这个传统又与它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历史吁求密不可分。这样一种因袭传统的命名法,所诉诸的乃是一个在观念上清晰透彻、可以理解的社会结构及其自身利益强调:从“底层”到“中层”再到“高层”的区分。换句话说,“底层文学”不是一个中性的知识概念,就命名的所指而言,它既不是“十七年文学”,也不是“知青文学”、“女性文学”或者“80后文学”,它尤其不是一种对自身文学品质的描述,譬如“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相反,由于诉诸传统的原因,它具有未经反思的笼统的道德优先性以及悲天悯人的批判精神。
事实上,“底层文学”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这个批判的力量来自于过去的历史结构和历史理解。文学与社会历史变迁以及巨大的时代思想运动直接关联并且结为天然盟友,这在今天已成人人皆知的常识,其实是在19世纪作为观念史和思想史的条件下形成的,它以某种二元论的紧张方式影响和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而“底层文学”的生成尽管与历史深刻关联,但上述条件在今天远不是构成“底层文学”的全部的、根本性要素。这一点决定了我们今天对它的描述,不可能完全因袭历史成规。
笔者曾经指出:“底层文学”的命名从一开始就是未经深察和缺乏反思的。在很大程度上,“底层”这个提法的使用方式,表征着一种思想方法上的惯性,寄寓着“用一个以意识形态名义建立起来的利益共同体来解决历史困境的努力”。当然,由于“历史终结论”的欺世横行和对全球化一统天下的万能崇拜,“底层”的提法也许更意味着一种历史描述的凄凉与无奈。如果按照诉诸传统的历史吁求来理解“底层文学”,我们不但无法在当下的历史结构中安顿“底层”这个庞大无名的群体,更为严峻的是,我们基本上也无法再像19世纪的先贤大师们那样,满怀信心地乐观地确定“底层”的思想涵义。我们迎面碰上的,是“底层”在可预见的未来中长期“妾身未明”。这个群体始终处于流转变异的过程中。而这些,正是我们讨论“底层文学”的知识前提。
对这个前提的轻率与漠视,导致了对“底层文学”讨论、评价上的歧见和困难,也就此暴露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知识品格方面的懒惰与缺失。如前所述,“底层文学”所呈现出来的意义更多地属于历史描述而非文学描述,故而它的人物、语言、风格、细节、氛围等审美范畴不被刻意上升为根本性的评价元素,就是有其自身充分合理性的。但如此一来,一个笼统的“底层文学”却难以归纳出基本的艺术边界,何种作品可以归纳为“底层文学”,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或者只凭印象而定、甚至不需要考虑的问题了。譬如,打工者、下岗者是“底层”,这是就其被剥夺的经济地位而言的;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也可以算“底层”,这是就其社会地位及其尊严感受等道德体验而言的。此二者能否在同一层面上构成历史理解当中的“底层”主体,并不是自明的。前者带有“题材决定论”的色彩,而后者,则带有道德判断的倾向。将两者混为一谈,是当下关于“底层文学”评论中常见的问题。
以道德同情和社会批判为特征的“底层文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典型的“问题文学”。由于社会历史变革的缘故,以往据以分析社会结构的阶级和意识形态理论几近销声匿迹,“底层”的说法因此成了一个权宜之计。但这个提法的批判性,不屈不挠地质证着在地位、资源、权利与义务等等方面严重失衡的社会关系。关于这些方面,当代社会学家有详尽的分析和论述。这种状况所导致的文学后果之一就是:“底层文学”真正地具有了强烈而尖锐的社会阶层指向。
正是这种看似粗糙、观念化的写作,在前述文学娱乐的歌舞升平中,为人的文学和时代的文学保留了最后一点尊严,也为当下和未来的历史理解提供了一个伟大的注脚。而它内在的历史要求就是:当我们希望认真面对并且有效地讨论这些现象和问题时,我们需要不同于以往的理解力和知识能力。
“底层写作”:没有完成的讨论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关于“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的讨论,从2004年至今一直是文学批评集中关注的话题。但是,关于这一文学现象的“认知焦虑”仍然没有结束。因此这是一个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文学现象。对这个文学现象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文学界,这个现象本身就不是所谓“纯文学”的话题了。这是继1993年“人文精神讨论”之后,十几年里唯一能够进入公共论域的文学论争,因此意义重大。随着讨论的深入,问题的复杂性也逐步显露出来。比如,“底层”是社会学概念还是文学概念,是谁在写“底层”,“底层”的问题是否仅仅是“苦难”可以描述或涵概的,“底层写作”的文学性如何评价,如何看待这一文学现象中的情感和立场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一方面表明了文学批评的进步和独立,在非“组织”的情况下,文学界主动介入这一话题,显示了文学对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但另一方面,也有试图迅速将其知识化的倾向,这种“学院式”的批评似乎很“学术”,但历史已经表明,学院式的研究或批评首先要经过历史化的过程。急于将鲜活、生动的文学现象纳入学院制度或范畴,结果就是远离了现实对象去纠缠概念、源流等“学理”层面的问题。因此,有些看似很学术的批评,恰恰将讨论引向了歧途。
“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等概念显然是临时性的概念。这种现象在当代文学史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伤痕文学”、“朦胧诗”、“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一直到“私人写作”、“70后”、“80后”等,这些概念都是临时性的,它们并不是科学的概念,但这些概念是可以通约的,文学界都知道这些概念具体指的是什么。至于如何更合适地命名这些现象,可以留给文学史家是研究。与此相关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底层写作”文学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在“专业”范畴里的讨论,对这个文学现象普遍的指责是“粗鄙化”、“苦难焦虑”等。对“底层写作”文学性问题的讨论是一个真问题,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清楚,“文学性”究竟是怎样表达的。这个问题就像前几年讨论的“纯文学”一样,文学究竟怎样“纯”,或者什么样的文学才属于“纯”,大概没有人说清楚。
从历史看,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说话,曾经是无往不胜,“政治正确”也就意味着文学的合理性。但是,在今天的文学批评看来,任何一种文学现象不仅仅取决于它的情感立场,同时,也必须用文学的内在要求衡量它的艺术性,评价它提供了多少新的文学经验。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许多年以来,能够引发社会关注的文学现象,更多的恰恰是它的“非文学性”,即文学之外的事情。我们不能说这一现象多么合理,但它却从一个方面告知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中,一般读者对文学寄予了怎样的期待、他们是如何理解文学的。另一方面,急剧变化的中国现实,不仅激发了作家介入生活的情感要求,同时也点燃了他们的创作冲动和灵感。“底层写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是,就像在文学领域没有可能认同的“中国经验”一样,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底层文学”经验。在“整体性”已经破碎,多元性已经建构了新的文学格局的时候,妄论统一的“文学本色”,其目的是试图建立新的“整体性”,但要实现这样的意图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既不是今天文学的现实,也不是文学未来发展需要的路线图。
事实上,“底层文学”发展到今天,情况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像马秋芬、孙惠芬、温亚军、徐则臣、吴君、鲁敏等作家的小说,虽然书写的也是底层生活,但并没有沉湎于苦难叙事的泥淖中,而是有了更多的精神特质。比如马秋芬新近发表的《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并没有着意于描写进城务工者惨不忍睹的生存状况,没有永无尽期的苦难叙事。小说将朱大琴在城市遭遇的精神盘剥和尊严践踏,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在生存艰难的背后,朱大琴们还在承受着另外的鲜为人知的精神苦难。他们内心卑微的希望在城市规则里转瞬即逝。在这个事件中,城里人共享资源,相互利用,他们密切结成的社会关系网,以不同渠道和形式瓜分了公共资源。行业垄断和行业权力资本在“合理”、“合法”地兑换成金融资本。但这一切与朱大琴们没有任何关系。都市合谋榨取了朱大琴最后的资源,一切都顺理成章,朱大琴还要含着眼泪表达她的感激和理解。因此《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重新书写了底层生活,将这一题材的创作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底层”从生存苦难的写作中被“解放”出来,但他们的精神苦难更令人触目惊心。朱大琴所经历的城市生活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精神事件。当然这只是一个例证,这种“底层写作”显然也不在某些对“底层写作”持批评意见的学者的概括之中。但我能够理解,部分学者对这一文学现象出现的某些问题表现的担忧,但他们显然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
在“纯文学”的讨论中,李陀说:“上世纪80年代所谓‘纯文学’的特点是去政治化,而未来的‘纯文学’很可能是很政治化的,会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提出特别强烈的批评和反驳。”李陀可能将他的想法做了极端化的表达,但我同意他的看法。过去的“去政治化”,是因为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太多,文学没有独立的精神地位;今天文学的“政治化”,是因为作家有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它是文学获得独立的另一个表征。当然,任何试图全面的概括都会辞不达意,都可能走向片面。但我也同意陈福民的看法:“正是这种看似粗糙、观念化的写作,在前述文学娱乐的歌舞升平中,为人的文学和时代的文学保留了最后一点尊严,也为当下和未来的历史理解提供了一个伟大的注脚。而它内在的历史要求就是:当我们希望认真面对并且有效地讨论这些现象和问题时,我们需要不同于以往的理解力和知识能力。”(见本栏陈福民文)
我的总体看法是,“底层写作”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虽然在文学的范畴内展开,但它所能达到的深度,事实上还远不如社会学界。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之后,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出了一个广被认同的概念:“底层的沦陷”。他不是简单地同情、怜悯底层的生活,也不仅仅是着意于底层生存的苦难,在底层生存状态恶化的背景下,他更指出了一些底层群体用泯灭人性的方式寻找生存出路。道德底线被彻底撕裂。比较而言,我们的“底层写作”和批评实在是太轻飘了。因此对我们来说,“底层写作”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讨论。
文学的人民性与社会形态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
人民性是一个需要我们审慎对待的词,因为它始终是政治舞台上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它的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常常会把我们绕糊涂。但是,当我们讨论“底层文学”时,我们不能不涉及到人民性的概念。有人认为与其使用人民这个概念,不如用公民这个概念更准确些。公民,当然是一个有着严格界定的概念,它本身就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且也是一个法律概念。在法律层面上说,我们可来不得半点糊涂。但是,公民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只有在真正的民主政治体制的框架内,才会有真正的公民。公民是可以简约为具体的个人的,公民的主体性可以从每一个公民的个体行为中得以呈现。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公民替换掉人民这个伟大的字眼。我说人民是个伟大的字眼,就在于它永远是一个集合体,它无法简约为具体的个人;就在于抽象的人民是一系列政治理念的落脚点;就在于许多政治实践和社会活动需要从“人民”这里得到合法性支持。今天,社会主义的旗帜上赫然写着人民两个大字,资本主义的纲领里面也把“人民”两个字填写得重重的。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从人民性的角度来讨论文学。
孟繁华提出的“新人民性的文学”显然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孟繁华在解释他的“新人民性的文学”时说:“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存在的问题。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是‘新人民性文学’的最高正义。在实现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要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的陷落’。因此,‘新人民性文学’是一个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潮有关的概念。”我在分析底层文学作品时曾认为一些作家接续起“五四”启蒙思想传统,沿着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思路,揭露当代社会的种种恶习,我将此称为“新国民性批判”。也许我的想法与孟繁华的“新人民性”有某种不谋而合之处。但我想强调一点的是,无论是新人民性也好,还是新国民性批判也好,其实都包含着人民性与社会形态的关系。不同的社会形态决定了人民性的不同的具体内涵。
该怎么描述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形态,不同的学派会有不同的描述。我比较赞同社会学家刘平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并不是以市场经济全面取代计划经济,而是这两种经济体制并行交织的“新二元社会”,是体制内社会与体制外社会的并存与互动。而我更愿意将这种新二元社会的特征理解为集权体制与市场体制的矛盾统一。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也就决定了当代底层文学中的人民性内涵。我以为打工文学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社会形态的本质。打工文学是与中国的“新二元社会”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二元社会体现为集权体制与市场体制的矛盾统一,这种矛盾并没有取代传统的城乡矛盾,但它将城乡冲突凝固化,给城乡冲突的转化设置了重重障碍。这一特征典型地体现在农民工身上。他们即使深深地陷入到城市困境之中,也无法摆脱城乡冲突带给他们的影响,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乡村立场,决定了乡村精神成为他们的基本思想资源。
我想在这里将打工诗歌与一位下岗工人的诗歌稍加比较,来说明打工文学的精神特性。河南安阳有一位下岗工人王学忠,十几岁就进了工厂当工人,1996年他所在的工厂倒闭,他的妻子是纺织工人,也下岗了。王学忠从小喜欢诗歌,下岗了仍写诗歌,据说写了3000多首,被称之为“工人诗人”。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工人”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工人,工人阶级曾被认为是最具有革命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的、胸怀最为宽广的先进阶级。我想,在王学忠的诗中我们是能够读到工人阶级的内涵的。他在诗中这样写下岗工人:“将他们组织起来/让沸腾的血成为力/让燃烧的火变成钢/便是一支能够移山填海的力量!”“他们才是真正的金子哟/一生任劳任怨/无论用在哪里都闪闪发亮!”(《然而,我不属于下岗工人》)。而在这样的诗句中:“捋起袖子抡锤/下岗,蹬着三轮贩梨/小康不小康没啥/只是眼睁睁瞅着/那大把的银子滚入贪官着急”,我们感到的是一个工人在绝境中仍不失宽广胸怀,作为工人,他们总会想到他们是一个整体,所以王学忠说:“落架的凤凰不如鸡/那是懦夫的见识/今天的工人兄弟/跌倒了再爬起/揩干血迹照样顶天立地” (《工人兄弟》)。王学忠的诗歌中不乏人民性,但他的人民性是与过去的社会形态即计划经济大一统的社会形态相谐调的人民性。显然,这样的人民性意象在打工诗歌中并不多见。但是,我们也会感到,王学忠诗中的理想主要还是复制了过去的理想,这多少在用过去理想的虚幻性来缓解今天生活的残酷性。
相对而言,打工文学中的诗歌就很少出现类似于王学忠笔下的激昂的理想的调子。打工诗歌中的形象基本上也是个人形象,很少像王学忠那样,吟唱的是工人群体的形象。但只要想想,今天的农民工是在集权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夹缝中生存,是缺乏组织的散沙,要求他们的文学出现激昂、理想和群体等因素就显得不切实际了。然而也正是这种特点,决定了打工文学与现实和大地贴得更紧,触及到中国当代社会最致命的伤痛。就像郑小琼的诗所写的:“再一次说到打工这个词 泪水流下/它不再是居住在干净的 诗意的大地/在这个词中生活 你必须承受失业求救/奔波,驱逐,失眠 还有打着虚假幌子/进行掠夺的治安队员 查房了 查房了/三更的尖叫 和一些耻辱的疼痛”(《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我愿意将这样的意象理解为孟繁华所说的“新人民性”。文学是一个时代的镜子,那么,如果当代文学缺乏了打工文学,我们就会感到对这个时代的反映有所欠缺。也许这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经历,打工文学真实记录了这段经历,它使以后的历史建构者不敢随意地将这段历史乔装打扮。
底层文学:认知的焦虑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底层文学”一直是文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这种关切其实和人们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切紧密契合。作家们发挥文学想象对于“现实”独特的观照和表现能力,关切在30年的中国社会急剧发展中的那些仍然面对许多困境和挑战的人们,显然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底层文学”正是在中国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一个“新新中国”正在喷薄而出的时刻出现,其意义和价值应该得到更多的阐释和理解。其实,“底层文学”也面临着许多值得深入反思的问题。有关“底层文学”的探讨才刚刚开始。
一般来说,对于底层文学的理论探讨是从两个向度上展开的。一个方向是延续192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写实”传统和1930年代以来“革命文学”对于劳动者受压迫及反抗和中华民族苦难的主题进行阐释,将当下的文学现状放入历史谱系之中加以陈述。另一个方向是以一种直观性的表述,提供对于“底层”的同情和悲悯,将底层的生活现状写出来表达一种感情的认同。这两种表述,前者较为理论化,而后者则比较感性和直观;前者涉及到某种文学史的连续性的考察,后者则直接凸显底层问题对于当下社会的情感意义。从文学写作来看,也存在着这样两种“底层文学”。一种是以曹征路等人为代表的具有强烈概念性的批判文学,是一种以理念引导的底层文学。另一种如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贾平凹的《高兴》等为代表的写作,作者从自己感性体验出发,描述“民工”等群体的生活处境,具有较强的感性色彩。
笔者所参与的讨论则是对于“底层文学”问题的再思考。这种再思考其实是对于当下出现的两种表述的“盲点”的探讨。这既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中的“底层想象”和今天的文学中的这一问题的表现的差异性进行思考,而且也需要对于当下的现实中的“底层”问题和“底层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只有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得以清晰,我们对于当下“底层文学”的认识才可能不再停留在表面上,也才能提供新的思考的可能性。
这里首先要讨论的是,有关当下“底层文学”和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写实”传统之间的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学来说,“底层”劳动者的命运一直不仅仅是某个个体的命运,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阶层或群体的命运,而是中国和中华民族命运的象征。每一个个体并不是以自身的命运,而是作为民族的形象的展开。由于中国在19世纪后期以来的民族的失败和屈辱的历史,中国人的个体的贫困其实是民族的贫困和危机的“寓言”。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性”文学在表现底层劳动者的时候所采取的表述的意义。
我们可以举出中国现代文学开端时期的两篇关于“人力车夫”的作品来稍加分析,一篇是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另一篇是胡适的诗作《人力车夫》。这两篇关于人力车夫的作品的情境相似,都是一个作为中产阶层的知识分子的“我”和一位车夫之间的相遇,但显示了截然不同的取向。《一件小事》所体现的是劳动者的品质,车夫面对一个事实并不清晰的撞人事件和一个似乎并不真诚的老太太所采取的承担责任的态度,使得他作为底层人物的道德的崇高性得以确立。车夫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整个民族的勇气和力量的象征。但胡适的《人力车夫》则与此不同,作者给我们展开的是一场世俗的对话,给我们的是一个“具体”的情境中的车夫的生活状态。他写一个车夫才16岁,“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而车夫的表述非常具体:“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都不管,你老又是谁?”而客人只好说:“拉到内务部西”。在胡适这里,贫困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存在,并没有超验的意义。所以,它是具体的和世俗的。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性”文学想象对于贫困的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由于中国的贫苦和危机以及中国人的深切的民族悲情,使得我们必然会将贫苦的个体升华为“民族寓言”。贫苦就有了天然的道德的合法性。因此,胡适的《人力车夫》将贫苦处境世俗化地表现就没有成为中国“现代性”文学传统,而且遭到了否定性批判。
就这样,贫穷和苦难的超验和抽象的价值变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基本形态。于是,老舍的《骆驼祥子》将祥子渴望发财的失败的命运写成“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直到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当代文学将发家致富表现为一种错误的道路和选择,都体现了贫苦不仅仅是个人或者群体的具体状态,而是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苦难和贫苦的象征。贫苦在此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一种巨大的“深度”。这种“深度”和西方文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的现实主义潮流中对于底层的表现有极大的不同。对巴尔扎克、狄更斯和德莱塞来说,贫苦不是他们的国家的命运,而仅仅是个人的命运,所以在那些经典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作品中,个人向上奋斗的梦想还始终存在,对于底层的悲悯同情与对于他们改变现实命运的想象始终存在于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之中。可以说,中国文学对于贫困的现实主义式的表现和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有相当不同。这种形态上的差异正是历史形态的差异的结果。
但今天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所创造的“新新中国”已经完全超越了20世纪中国“现代性”对于贫穷的想象方式。中国的“和平崛起”使得国家告别贫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可以说,今天的中国获得了整个20世纪历史难以想象的丰裕和繁荣。虽然贫苦问题仍然是中国当下值得关切的问题,但它显然已经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的处境脱钩。贫穷的个人或者群体的处境变成了一种具体的个体或者特殊群体的命运,它不再能够产生像过去所产生的“民族寓言”的“深度”。贫苦和中国命运的历史的联系在今天已经过去。所以,当下的有关“底层”的文学,除了渲染个体的困难的遭遇之外,难以产生强烈的冲击。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的普遍贫困的状态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存在,正是为了改变这样的命运,中国走上了通过改革开放,向全球化和市场化转型来发展自身的道路。无论从国内或者国际的统计来看,这些年来中国人告别贫苦的速度非常快。而贫困本身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一面有正在改变中的贫困和暂时的困难,另一面也有结构性的问题等等,这些都异常复杂地附着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之中,引发复杂的思考和探究。因此,“底层文学”在表现上就存在着和现实的经验之间的复杂的关系。文学想象所表现的一些情境和现实之间的裂痕其实是难以弥合的。如何在表现底层的弱势和困境的同时,以“中国梦”的光芒照亮底层的生活,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挑战。
在这里,我以为两种不同的当下的“底层文学”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走向,值得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框架加以阐释。一方面,那种以理念先行的关于底层的写作,其实仍然停留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表现框架之中,有相当浓厚的“概念化”的特质,难以适应当下社会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我以为那种感性地表现底层人民生活,对于他们的生命的感受加以表现的写作,乃是对于中国“现代性”文学所缺少的有关个体生命的生活的“现实主义”的展开。对于这种展开所表现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情境,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切和思考。其中包含的那些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经验和想象,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总之,“底层文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世纪文学”的重要现象,其中所表现出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认知的焦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底层写作仅仅体现了道德化的文学立场
洪治纲,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向来不缺少“底层生活”。从《诗经》开始到明清小说,才子佳人虽也占了不少,但街头巷尾的平民生活亦不见得缺席。“五四”之后,直到今天,乡土文学更是中国文学的一支主脉。因此,当人们提出“底层写作”的口号时,笔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摸不清方向:莫言不是在写底层么?余华不是在写底层么?苏童不是在写底层么?迟子建、贾平凹、王安忆、阎连科、范小青、池莉……细数一下,目前文坛上一些有分量的作家,大多数人的作品都涉及底层生活,可是,为什么只是一部分新生的作家的作品被冠以“底层写作”?
翻阅了一些相关的评论文章,我才渐渐有所明白:所谓“底层写作”,主要是对当前一些特殊生存群体的书写——包括城市里的农民工、下岗工人或乡村基层中的农民。用孟繁华先生的话说,“他们或者是普通的农民、工人,或者是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淘金梦幻者。他们有的对现代生活连起码的想象都没有,有的出于对城市现代生活的追求,在城乡交界处奋力挣扎。”但是,如果我们遵从这样的说法,那么像迟子建的《起舞》、《花牤子的春天》、《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苏童的《冬露》、《垂杨柳》,王安忆的《民工刘建华》、《骄傲的皮匠》等等,同样也是“底层写作”的代表性作品。
概念的追踪也许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底层写作”从其命名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彰显某种关怀弱者的道德立场,并不是对当前的写作思潮进行理论上的缜密归纳或探讨。我之所以这样认为,理由是:“底层写作”着力表现的这一特殊的生存群体,在本质上是属于现代社会的弱势群体,是被“文明社会”遮蔽了的生存群体。这是中国社会向现代性过渡中出现的一个特殊阶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阶层也许并不会消失。作家们对这个阶层给予文学上的自觉关注,从客观上看,无疑体现了他们积极参与当下生活的姿态,也体现了他们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精神抚慰的道德意愿。多元的价值观念造就了多元的生活形态,作家的精神资源自然也因此变得繁复驳杂,而有一批作家倾心于表现底层民众的生活,其主体背后所隐含的道德情怀不容置疑。
事实也是如此。细读那些“底层写作”的代表性作品,我们会发现,在作家们的主体精神里,非常明确地凸现出某种道德化的情感立场——同情大于体恤,怨愤大于省察,经验大于想象,简单的道德认同替代了丰富的生命思考。也就是说,“底层写作”看起来是在为底层平民的生存困境而呐喊、呼告,但由于大多数作家并没有写出底层生活的丰富性,往往依助于公众经验或大众传媒上的大量信息,极力推衍底层民众的悲苦辛酸,很有些“铁肩担道义”的伦理架势。
针对这一问题,我曾写过一篇《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的文章,试图指出这类写作所呈现出来的严重的模式化、粗俗化和平面化的审美倾向。在此文中,我曾以大量的作品实例为证,说明了很多作家写到“男底层”便是杀人放火、暴力仇富,写到“女底层”常常是卖身求荣、任人耍弄,不仅人物命运模式化,故事情节粗俗化,而且人物性格也是扁平的,不见温暖,不见尊严,一律大苦大悲,凄迷绝望,鲜有十分丰饶的精神质感。如果将这些写作倾向视为一种“新人民性”的追求,我以为,这显然是对底层平民生存状态理念化、片面化的图解,至少,它失去了“新人民”所拥有的丰富的精神内涵。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想完全否定“底层写作”的价值。作为多元文学格局中的一元,它在及时捕捉生活现实、揭示社会问题方面,自有它的特殊作用。但这种作用的社会学意义远远大于审美意义,道德价值远远高于艺术价值。如果深而究之,它依然隐含了创作主体的非文学性冲动,即,试图通过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悲苦命运的展示,以引起“社会疗救者的注意”,让这一群体获得真正意义的公民平等权,促动社会在文明的意义上走向公平和公正。而创作主体的这种非文学冲动,实质上也折射了他们正在不自觉地充当社会核心价值代言人的角色。因此,如果强调这种写作是一种“新人民性”的写作,那么,它显然不是审美意义上的民间化追求,而是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化追求。
作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对社会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对普通民众的生存困境,当然要给予积极的关注。只是这种关注不应该是社会学的,而应该是文学的;不应该是对现实困境的表象式书写,而应该深入到人物的精神内部,从艺术的丰富性上激活他们的生命质感。换言之,作家们在书写底层民众的生活时,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创作主体的道德安抚,而是要让这些底层民众的生命站立起来,使他们成为一个丰饶的、具有鲜活生命质感的艺术形象。而现在的“底层写作”之所以不能让人满意,就是因为大量的作品都是沉迷于苦难的书写,甚至是人性恶的书写,却没有认真地沉入人性内部,让人物站立起来,只是让作家自身的道德观念四处张扬。
坦白地说,这是一种游离了文学本色的写作,因为它不是对人的精神生活发难,而只是对人的生存处境进行极端化的演绎;它不是对人的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讨,而只是盘旋于现实生活的表象之中悲鸣不已。这种写作是一种下坠式的写作。在那里,我们看不到思想漫游的亮光,看不到灵魂飞升的姿态,看不到人类应有的伟岸、高洁与不朽。曹文轩先生曾尖锐地指出,当下的中国正充斥着“憎恨学派”、“怨毒文学”:“中国当下的文学浸泡在一片怨毒之中。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学普遍感到格调不高的原因之所在。”虽然曹文轩并没有指出这种现象具体体现在哪些创作实践中,但是,依我对那些“底层写作”代表性作品的阅读和理解,无论是“憎恨情绪”还是“怨毒意味”,它们都体现得非常突出。
我以为,这正是过度彰显道德化写作立场所造成的一种文学困境。说得严重一点,它是一种极端化的非健康性写作。因为一个显在的事实是,文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为了人类自身梦想的需要——通过这种梦想,解除内心深处的现实焦虑;借助这种梦想,寻找苦难生命的拯救勇气;怀抱这种梦想,踏上充满希望的未来之途。也许,这并不是文学的惟一使命,但它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内在品性,是文学拥有恒久魅力的重要基石。如果没有灵光四射的激情,没有圣洁高迈的理想,没有凌空飞翔的诗意,没有笑傲苦难的信念,写作只是依靠那些所谓的社会经验和生活常识,不断地复制现实生存的秩序,那么,这种写作将永远无法打开人们内心深处的隐秘空间,无法展示人类的某种可能性生活,也永远无法让人们在梦想中获得生存的智慧和力量,更无法激励人们重返精神的高贵与圣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