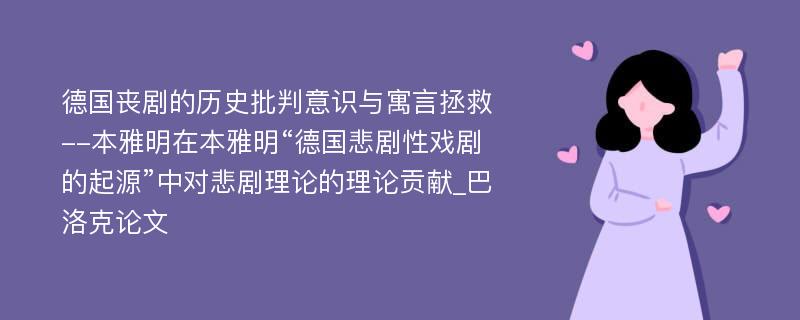
历史批判意识与德国悲悼剧的寓言式拯救——本雅明《德国悲悼剧的起源》对悲剧理论的理论建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理论论文,建树论文,寓言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3)05-0099-05
本雅明的悲剧理论集中在《德国悲悼剧的起源》(2001年出版的中文译本将书名定为《德国悲剧的起源》)一书中,该书谈到了德国悲悼剧的特点,悲悼剧与古典悲剧的关系以及寓言的表现方式等。作者在阐释每一个问题时都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虽然这些观点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不明显,很多具体观点亦未能展开,只是一组理论碎片,但仍可从这些碎片中窥见本雅明的思想深度。
一、17世纪的德国悲悼剧
17世纪德国的社会状况让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德国人感到绝望。当三十年(1618—1648)的战乱结束时,德国已经遍体鳞伤,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地方诸侯的权力得到加强。德国诸侯仿效法国建立专制王权制度,生活极其奢侈。但专制在法国至少促进了民族国家的统一,而在德国却完全走形。“德意志的专制主义却带上了诸侯小邦的专制主义的性质。在德意志的这种诸侯小邦专制主义加深了国家的政治分崩离析状态,妨害了一个民族市场的形成,推迟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在17和18世纪的欧洲战争中,难得有一次没有德国人反对德国人的战争,而且在两方面都总是为着外国的利益而斗争。”[1](P97)这就是德国巴洛克文学的时代背景。
有学者把这一时期德国的巴洛克文学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贵族沙龙中所崇奉的纯粹玩弄文字游戏的文学;另一种是“比较严肃、悲惨的,它和17世纪德国历史的阴暗事件的联系也比较深刻;这一方面所表现的已不是轻薄的贵族们所追求的色情,也不是感情游戏和玩弄词句,而是真正的悲剧、失望和三十年战争的血腥战火在人的心灵上所遗留下来的阴暗的折光”[2](P48—49)。德国悲悼剧显然应该属于第二种类型的巴洛克文学。德国巴洛克戏剧种类很多,有“教学剧、耶稣会剧、流动戏班子、雅剧,即西里西亚的悲剧和喜剧以及歌唱剧和歌剧等”[3](P269)。由于雅剧的倡导者与早期实践者奥皮茨,还有“从事这种雅剧创作的其他作家如早期的格吕菲乌斯和晚期的罗恩斯台因都是西里西亚人,所以在文学史上也称他们写的雅剧为西里西亚悲剧和喜剧”[3](P276)。本雅明所说的德国悲悼剧应指西里西亚悲剧。
为了进行德国悲悼剧的研究,本雅明摘录了许多资料,这从《德国悲悼剧的起源》一书的结构就可以看出,该书的英译本正文不过209页,却后缀了16页的注释。实际上,本雅明并未从文学史的角度去研究德国悲悼剧,也没有分析悲悼剧作家的创作经历、代表作品,而是直接阐述他对德国悲悼剧的研究感悟。不管这本书最后给我们留下了多少不成形的碎片,这种避轻就重的写作方式至少说明本雅明的研究态度是相当严谨的。
他觉得德国悲悼剧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由暴君、受难者和阴谋策划者组成的人物形象结构,宫廷则是悲悼剧的主要背景。当然,本雅明在一些作品的分类上与有的国内研究者意见不同,比如格吕菲乌斯的《卡尔德尼奥与采琳德》,这部作品不是历史剧,而是讲“一对恋人的故事”,国内研究者就把它当作悲剧作品[3](P280),而本雅明在《德国悲悼剧的起源》中却从未提及。
本雅明认为,德国悲悼剧的主要人物一般都有王族成员,故事在他们之间发生,或者围绕他们展开,君主形象往往在两个极端摇摆:“要么被判断为非常好,要么就非常坏。”“关于暴君的戏剧表现‘非常坏’的国王,因而产生恐惧;关于受难者的戏剧表现‘非常好’的国王,因而产生怜悯……在巴洛克戏剧中,暴君和受难者不过是君主的两面,是君主本质的必然极端的化身。”[4](P40)表现暴君的悲悼剧一般会尽力凸显其行使权力时的高傲姿态,忽略其道德缺陷。但是,本雅明觉得这些君主最突出的地方,“与其说是在素朴措辞中显见的君权,毋宁说是无时无刻不在转化的情感骤雨的纯粹任意性……他们的行动不是由思想而是由变化不定的身体冲动决定的”[4](P41)。这一评价明显包含着对暴君的挖苦之意。
本雅明批判暴君的批判意识只是表现在那些零碎的语言之中,其中包含着他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如在评价疯狂的希律时说:“当这位统治者沉溺于最狂暴的权力展示时,历史和阻止历史沉浮的更高的权力都在他身上显示出来。”[4](P41)话语中似乎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历史充满罪恶,但希律毕竟发疯了,这似乎也是上帝的最终判决。他对凯撒也有一句评价:“当恺撒沉溺于穷凶极欲的权力之中时,有一件事可以说是有利于他的:即在被神圣赋予的无限的等级尊严与卑贱的人性状况之间存在着一种失衡,恺撒正是这种失衡的牺牲品。”[4](P41)这似乎是在说:居于高位者往往具有最丑陋的人性。对暴君的毁灭,本雅明有如下反思:“暴君的毁灭产生的不衰魅力一方面根源于他作为凡人的无能和堕落,另一方面根源于时代对他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的信任……如果暴君不仅仅以他作为个体的名义,而且作为统治者以人类和历史的名义毁灭,那么,他的毁灭就具有审判的性质,这种审判也暗示了主题。”[4](P42)这些评价都是碎片式的,并未系统展开,但从中可以感到他对历史的批判以及从宗教体验角度对人类罪恶的反思。
本雅明在讨论暴君时,常有一些不断跳跃的观点,诸如“君主是忧郁之人的典范”[4](P113),暴君的忧郁还可以“被看作懒惰”,“暴君的垮台就是由心灵的懒惰引起的”[4](P124),等等。他的这种表述最终想要表达何意,我们似乎不得而知。
德国悲悼剧除了喜欢凸显君权的威仪,还喜欢同情受难的君主和因帮助君主而遭遇不幸的人。本雅明对受难者的论述虽然不多,但颇为深刻。在他看来,德国悲悼剧中“完美的受难者和理想的君主形象”都没有从“内在性”的层面上表现出来,与宗教观念毫无关系。这里的“内在性”,当指宗教救赎的精神体验,但悲悼剧中的受难者没有达到这种精神境界[4](P43)。
在德国悲悼剧中,除了暴君和受难者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阴谋策划者,他是悲悼剧情节的组织者。这个角色一般由廷臣担当。“廷臣幻灭的灼见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深切悲伤的来源,正如对别人来说则是潜在的危险一样,因为他可以随时利用这种灼见。如此看来,这个人物形象便呈现出最邪恶的方面。理解廷臣的生活就等于完全认识到在所有事物中为什么只有宫廷才为悲悼剧提供背景。”[4](P63)廷臣只忠诚于权杖与王冠,而缺乏对人的忠诚。他们拥有智慧和行动的意志,在表面上可能“被打扮成安详而有尊严的样子”,一旦行动起来可能又显得特别“厚颜无耻”[4](P46),这让他们显得更加恐怖。
总之,本雅明认为德国悲悼剧描写的内容大都阴森可怖,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他说:“巴罗克戏剧所了解的历史活动只有阴谋家的堕落。在僵化地反映基督受难态度的与君主作对的无数反叛者中,没有表达革命信念的迹象。不满是古典主义动机。只有君主反映道德尊严,而甚至君主所反映的也完全是非历史的斯多噶派的道德尊严。巴罗克戏剧的主要人物普遍表示的正是这种态度,而非基督教主人公的救赎信念。”[4](P56)在德国悲悼剧中,“对历史的召唤的惟一响应就是受难者的身体痛苦”[4](P58),传统美学已经无法欣赏巴洛克悲悼剧,必须寻找另外的切入点才有可能揭示其中可能存在的意义。
二、古典悲剧与德国悲悼剧
在讨论德国悲悼剧的过程中,本雅明有时会把悲悼剧当作“现代悲剧”的代名词,他认为:“悲悼剧的最佳典范不是严格循规蹈矩的剧作,而是对喜剧进行过轻松调整的那些剧作。由于这个原因,与17世纪德国作家相比,卡尔德龙和莎士比亚创作出了更重要的悲悼剧。德国作家从未越过雷池一步。”[4](P96)在《德国悲悼剧的起源》一书中,本雅明多次把卡尔德隆和莎士比亚的作品称为“悲悼剧”。
本雅明提到,悲剧理论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误解,即研究者或者“把古希腊悲剧的因素……看作悲悼剧的本质因素”,或者把古希腊悲剧“看作早期的悲悼剧形式,与后来的悲悼剧密切相关”[4](P72)。而本雅明则认为,悲悼剧与古希腊悲剧之间的差异远远多于它们的相似之处。悲悼剧与悲剧的主人公都出身于贵族之家,他们最后或者被毁灭,或者遭遇了不幸,两者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古希腊悲剧理论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效果是引起观众的恐惧与怜悯,以使这种情感得以净化。17世纪德国悲悼剧的理论家则把道德说教视为悲剧的主要功能,他们认为:“恐惧和怜悯并不是对情节的有机整体的参与,而只是对最著名人物的命运的参与。恐惧是由恶棍的死唤起的,怜悯则是由虔诚的英雄的死唤起的。”[4](P34)这完全是对亚里士多德悲剧观点的曲解。
在《诗学》中,古希腊悲剧的主人公在道德品质上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没有英雄与恶棍之分。古希腊悲剧以神话与英雄传奇为表现对象,而悲悼剧则以历史生活为表现对象。德国悲悼剧的主要内容是“证实王族的美德,描写王族的罪恶”[4](P35),揭穿政治活动的实质,“君主,即历史的主要代言人,几乎成了悲悼剧的化身”[4](P35)。当然,神话与英雄传奇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历史,但其中的事实非常模糊,虚构的成分较多,因而给悲剧创作留下了极大的精神生产空间,而现代历史观念则更加注重客观性。悲悼剧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固然不必完全符合历史真实,但这种创造必须局限于现代历史观念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只要想想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对待鬼魂的态度就知道悲悼剧在进行艺术虚构时应注意的规则了,而古希腊悲剧则完全没有这种顾虑。本雅明认为,古希腊悲剧的内容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悲剧所努力要表达的是预言的声音,或被这种声音拯救的苦难和死亡”,而悲悼剧“与其说是唤起悲悼的戏剧,毋宁说是使悲悼之情得到满足的戏剧:为可悲悼之人所写的戏剧”[4](P89)。所以,“哑剧”可以出现在德国悲悼剧中,但出现在古希腊悲剧中则是不可想象的。
不同时代的戏剧观众在接受心理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古希腊观众通过观看悲剧来感受自己的命运,舞台上表演的事也正是宇宙内发生的事,所以他们是悲剧艺术的参与者。“悲悼剧必须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理解;他知道舞台是一个属于内心情感世界,与宇宙毫无关系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各种环境不容分说地展现在他眼前。”[4](P90)两个时代的命运观念也不一样。在古希腊悲剧中,造成痛苦命运的原因是不明确的,只能通过神话加以解释,悲剧主人公虽然有时也指责命运的不公,但他最终只能选择承受命运。而在悲悼剧中,主人公自己的弱点和外在于不幸者的邪恶应该共同承担导致不幸后果的责任,悲悼剧对痛苦的表现其实是对制造不幸的所有责任者的集中审判,主人公不愿独自承担命运的惩罚[4](P104)。
本雅明描述古典悲剧与德国悲悼剧差异的思想碎片比较多,但这些观点都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其理论价值也是有限的。
在现代悲剧与古希腊悲剧之间,很多理论家都倾向于厚古薄今,如尼采、卢卡奇等。叔本华的与众不同在于“视悲剧为悲悼剧”,因而,“在费希特之后的德国大哲学家中,几乎找不出另一个对古希腊悲剧如此缺乏同情心的人”[4](P82)。叔本华曾把造成悲剧结局的原因分为三种:恶毒、盲目的命运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第三种写法是最可取的,因为这种方法“不是把不幸当作一个例外指给我们看,不是当作由于罕有的情况或狠毒异常的人物带来的东西,而是当作一种轻易而自发的,从人的行为和性格中产生的东西,几乎是当作(人的)本质上要产生的东西”[5](P352—353)。这样的悲剧完全是由人们的意志造成的,最贴近人们的生活,因而也最可怕。叔本华特别提到,如果从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奥菲莉亚的关系来看,《哈姆雷特》就属于第三种类型的悲剧。本雅明有时似乎准备赞同尼采、卢卡奇的观点,批判叔本华的观点,但他那种碎片式写作方式又使他很快跳过了这一问题。总体来看,他对古今悲剧的审美倾向是比较暧昧的。
三、德国悲悼剧与巴洛克寓言
德国巴洛克悲悼剧中经常直接描写一些比较血腥、残酷的场面,鲜血与尸体是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形象,而古希腊悲剧往往采用转述的方式把这些内容告诉作品的接受者。应该如何看待德国巴洛克悲悼剧的这种表现方式呢?本雅明认为,这些作品之所以值得阐释,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寓言的精神作为废墟、作为碎片而构思的”[4](P196),因此,“对极端的、寓言式的悲悼剧加以批评理解,只有从更高的神学领域开始才是可能的。只要采取美学方法,那么,悖论就是最后定论”[4](P179)。巴洛克悲悼剧不可能让人产生美感,只能对人有所启示,其意义只有在寓言观念的烛照下才有可能得到揭示。悲悼剧中的形象本身就不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它所提供的启示也具有含混性和多义性,这就使它与20世纪初期流行的“象征”美学观念决然不同。
有研究20世纪西方美学史的学者指出:“在1925年左右,象征这个概念开始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艺术是直觉表现或艺术是想象这种定义,或美是客观化的快感这种定义,让位于讨论艺术这样一种意义,即它体现了人们创造象征和符号的独特而神奇的力量。”[61](P735)这一时间段正是本雅明写作这篇教授资格论文的时期。不过,本雅明对当时流行的象征概念颇不以为然,觉得那是对象征概念的歪曲和滥用。他说:“把这种歪曲的象征概念引入美学是一种浪漫的和破坏性的放纵,导致了现代艺术批评的荒芜。美作为一种象征构造被认为与神性融合而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4](P131)他的这一观点只是点到为止,象征概念正确的用法并未作详细阐述。在《德国悲悼剧的起源》中,寓言与象征这两种表达方式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本雅明关注的是寓言。在本雅明的时代,寓言一般仍然被认为是“解释性形象与抽象意义之间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而“关于现代寓言式的看待事物方式的真实文献,即巴罗克时代的文学和视觉的寓意画册”,人们并不清楚[4](P133)。也就是说,“现代寓言”的观念其实是本雅明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有时将其称为“巴洛克寓言”。
本雅明以“毁灭”的表现为例辨析了巴洛克寓言的表现方式与象征表现方式的差异。“在象征中,毁灭被理想化了,美化了的自然面貌在救赎之光中被短暂地揭示出来。”[4](P136)而在巴洛克寓言的表达方式中,“观察者所面对的是历史弥留之际的面容,是僵死的原始的大地景象。关于历史的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不适时宜的、悲哀的、不成功的一切,都在那面容上或在骷髅头上表现出来……这是巴洛克寓言式地看待事物方法的核心,是把历史世俗地解释为耶稣在现世的受难……意义越是重要,就越是屈从于死亡,因为死亡划出了最深邃的物质自然与意义之间参差不齐的分界线。如果自然始终屈从于死亡的力量,那么,同样真实的是,它也始终是寓言式的”(参照英译本166页对引文有所调整,translated by John Osborne,published by Verso 2003)[4](P136—137)。巴洛克寓言在表现“毁灭”时没有进行任何崇高的升华、美化,而是把残酷的历史场面直接凸显出来,通过死亡把重要的意义凸显出来,这也正是世俗生活中人们理解耶稣受难的方式。
寓言式的书写碎片与“艺术象征、可塑性象征和有机总体的形象”是完全对立的[4](P145),与追求外在美的古典主义风格更是格格不入。本雅明以温克尔曼《罗马宫殿里的赫拉克勒斯雕像描写》为例阐述了寓言式书写的形态。温克尔曼的文章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一尊不完整的雕像,“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一个肢体一个肢体地描写”[4](P145),完全消解了对象的整体性。“在寓言的直观领域里,形象是个碎片,一个神秘符号。当神性的学问之光降在它身上时,它作为象征的美就发散掉了。总体性的虚假表象消失了。由于表象的消失,明喻也不复存在了,它所包含的宇宙也枯萎了。”[4](P145)
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方式,把“对事物瞬间性的理解”拯救出来,“永久保存它们”,“正是寓言最强烈的愿望之一”[4](P185)。但是关注对事物的瞬间理解并不是寓言式思维方式的唯一决定要素,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废墟”。他说:“寓言在思想领域里就如同物质领域里的废墟。这说明了巴洛克艺术何以崇拜废墟的原因。”“具有高度意指功能的碎片,那片残余,事实上,是巴罗克创造的最精美的材料。”[4](P146—147)废墟在文学中经常得到表现,德国悲悼剧中的罪恶的宫廷,波德莱尔笔下的丑陋与邪恶,卡夫卡笔下的人的生存状态,都是废墟的具体表现。罪恶也是废墟的一种表现形态,越是罪恶的东西,“它们的寓言阐释就越必要”,因为寓言“是它们惟一可想象到的救赎”[4](P186)。但在本雅明看来,有罪的不光是这些对象,用寓言的方式观照世界的主体本身也是有罪的,因为这些人都有善恶观念。上帝在创造了伊甸园和亚当之后,一切都是非常好的。“对邪恶的认识没有客体,世界上没有邪恶,邪恶随着对知识甚或对判断的欲望而产生于人自身。”[4](P194)蛇的诱惑让人类产生了最早的关于邪恶的知识,邪恶才在世界上蔓延开来。为了消除世上的邪恶,上帝决定毁灭他所创造的一切。为了给人留下一丝希望,才有诺亚方舟的传说。本雅明不断扩展罪恶的边界,以至于把关于善恶的知识也视为罪恶,寓言家因此也背负着罪恶之名,这就使得寓言的意义面临被消解的危险。但是,只要我们不把寓言看作说教的手段,而是将其视为不断自省的动力,那么救赎的希望就可以保留下来。德国悲悼剧作品中的尸体与残肢可以被视为上帝最终判决的隐喻,提醒世人上帝可以让毁灭人类的洪水随时而来,提醒世人反省自己的罪恶,其中也包括寓言家自己(不管是创作寓言的寓言家,还是接受寓言的寓言家),弥赛亚的模糊身影借此投射到生活中。
寓言的表达方式是“自然与历史的奇怪结合”[4](P137),本雅明没有解释他所说的“自然”和“历史”究竟是什么,但从上下文来看,“自然”大概指物质层面的现实,“历史”指主导性的社会观念。对于巴洛克寓言来说,“自然”是意义表达的主要手段,“而历史则必须永远是起从属作用的舞台道具”[4](P140)。在寓言的表达方式中,“任何人,任何物体,任何关系”完全可以意指其它的事物,“甚至基督生活的故事也支持从历史到自然的运动,这是寓言的基础;不管阻碍有多大,其世俗解释的倾向始终存在着”[4](P150—151)。这种狂欢式的、解构神圣的表达方式,或者从精神层面“突降”到物质层面的表现方式,都有寓言的意味,寓言的边界似乎被拓展得太宽了。
尽管本雅明对寓言的讨论仍然显得有些散乱,但他对“现代寓言”(巴洛克寓言)的阐释确实很独特,而且这一观念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主义艺术。虽然本雅明在其他著作中也讨论过这种寓言观念,但《德国悲悼剧的起源》对这一观念的论述是最充分的,因此,尽管这部著作存在种种缺陷,但它不会被历史轻易地遗弃。
1920年代前后,学术界开始重新评价一直遭受贬斥的巴洛克文学[3](P240)。本雅明力图找到一个立足点“客观”地欣赏巴洛克悲悼剧,寓言似乎就是这一立足点。在这一视角下,德国悲悼剧破碎的意义终于被拯救出来,这应当是这部著作的主要思想成果。反观本雅明的写作思路,似乎也带有寓言的特点。正如阿伦特所言:“本雅明关注着能够直接、实际证明的具体事物,关注着单个事件和‘意义’显明的偶发事件,而对那些不能马上设想出精确的想象外形的理论或‘理念’,缺乏同样的兴趣。”[7](P174)阿伦特的这一评价点出了本雅明那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这正是寓言的一个重要特点。作为一种文化批评方式,寓言大有可为,它通过细致而又具体的描绘使阅读者陷入朦胧、悠远的沉思,《单向街》、《巴黎,十九世纪的都城》、《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就是这种批评方法的范例。但是,作为一种理论表述的方式,故寓言总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故寓言式的思维方式并不适合理论建构。
标签:巴洛克论文; 巴洛克艺术论文; 历史论文; 本雅明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寓言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古希腊论文; 戏剧论文; 废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