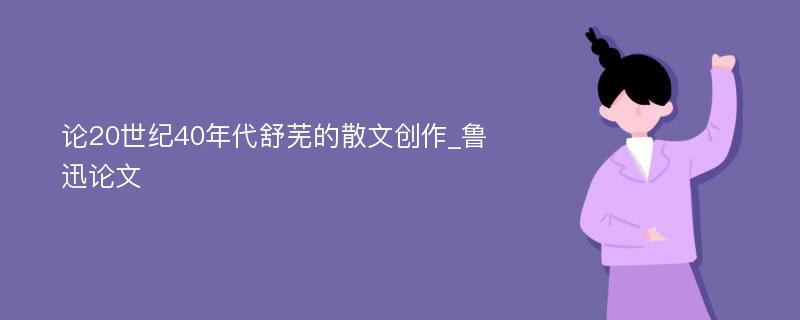
论舒芜1940年代的杂文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杂文论文,年代论文,论舒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04)04-0026-05
舒芜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关注舒芜《 论主观》一文的“公案”及其与“胡风集团案”的历史纠葛,忽略了他在1940年代的杂 文创作,从而遮蔽了舒芜杂文的历史色泽。滥觞于“五四”的现代杂文发展至1930年代 已蔚为大观,但在1940年代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影响而渐趋停滞与沉寂。 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一批赓续鲁迅风骨、高扬战斗精神的杂文家,舒芜就是其中颇有 实绩的一位。
一
舒芜出身于桐城出家,他的文化教育虽然以家学和理学起步,但他从小就受到五四启 蒙主义文化精神的熏陶,新文学各个流派的代表作家作品成为他的“精神摇篮”,鲁迅 和周作人的影响尤甚。新文学给予他的不仅是艺术的享受,更多的是思想的启迪。他在 上中学时逐渐形成了尊五四、尤尊鲁迅的思想基点。[1](P555-623)这为舒芜的杂文创 作规范了以五四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反封建、反法西斯的思想理路。
但是,舒芜杂文创作的发轫,很大程度上缘于胡风的激赏和“才子集团”的启发。194 1年《七月》停刊,胡风在香港筹办新的文学刊物,他非常需要具有鲁迅风骨的杂文、 文化评论等“突击性文体”。[2](p183-188)舒芜的出现让胡风倍加欣喜,胡风对舒芜 的写作先以“广义的启蒙运动”点拨,后又明示“个性解放”的要旨,并在《希望》上 连续“集束式”发表。在胡风的提携下,舒芜迅速成长为七月派重要的杂文家。
1940年代初,国统区的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才子集团”为反对蒋介石的“复古 ”逆流和响应延安整风运动,发起了一场批判封建思想文化、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启蒙 运动。他们把整风运动理解为“新启蒙”的观点和思路与胡风、舒芜颇为一致。因此, 于潮(乔冠华)的《论生活态度和现实主义》和《方生未死之间》、陈家康的《唯物论与 唯“唯物的思想”论》、项黎(胡绳)的《感性生活和理性生活》和《论艺术态度和生活 态度》等文章对舒芜启悟非常显著。舒芜与“才子集团”思想的同化和共鸣催生了他的 创作实践。
舒芜把鲁迅的杂文风骨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化合起来,形成自己对杂文的理解 。舒芜在《关于思想和思想的人》(本文所引用舒芜的文章见于:《舒芜集》第一、四 、五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认为“今天所谓‘杂文’,原来也可以说就只 是‘鲁迅体的论文’,……后来历史的发展,特别需要这种风格的,和这类风格同类的 论文,才使它变成一个独立的文学品种。”但是现在的杂文作者不能专以学鲁迅为能事 ,必须发展自己的精神个性和人格力量。他在《思想建设和思想斗争的途径》中指出: “杂文,不是普通的一种新文体,是从现实人生要求中随处发掘出一切新思想的锋利的 锄头。”随后他阐述了杂文的三要素:“新思想”(舒芜曾解释说“新思想”就是指马 克思主义,当时由于国统区的政治环境不能直接标明。实际上二者并不能等同,他的“ 新思想”既包含有马克思主义因子,又具有启蒙主义、自由民主主义质素,十分含混) 、“现实人生要求”、“生命的燃烧”,杂文必须在“生命的燃烧”中化合“新思想” 和“现实人生要求”,才有坚持到底的战斗性。他由此认为“杂文的意义,是无可估价 的。不仅中国的思想史,而且全人类的思想史,都由于杂文的出现,而进入了一个全新 的胜利的阶段。”舒芜以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强化了鲁迅式杂文的“匕首”、“投 枪”的战斗功能,认为鲁迅式杂文昭示着怀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斗争生活实现 与人民结合的途径(即从个性自我到人民大我)。
二
舒芜的杂文贯穿着反对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理念。他的杂文创作都是“从‘ 五四’出发,向前看,……追求彻底的个性解放;向后看,想继续‘狂人’的事业,在 历史的满纸‘仁义道德’下面,不断挖掘‘吃人’两个大字。”[3]他对封建礼教及各 种陈腐观念予以猛烈的抨击,对丑恶的社会现象给予无情的鞭挞,思想锐敏,大胆泼辣 ,文笔犀利,颇有鲁迅杂文的风骨。如《耶稣闻道记》构造两个杀人的强盗在杀耶稣时 还在宣讲《孝经》里的孝悌观念的戏剧情景,对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作绝妙的讽刺。同 时,舒芜还仿效鲁迅,围绕着个人的觉醒来思考和设计他的杂文。如《“嗜痂”与“制 痂”》接着《热风·随感录三十九》的一句话生发开来,展开对国民的劣根性批判。《 无捧无不捧》嘲讽了捧人者和受捧者的丑恶世相和奴性心态。
舒芜的杂文展示了为女性解放“助一呼之力”的人文情怀。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 文从人文主义的人性论的角度提出“人的解放”,尤其是妇女解放的观点,引起舒芜的 共鸣。他的杂文强烈抨击了现实社会仍然存在的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对女性生命自由、 价值、权利、尊严的忽视和戕害,呼吁女性解放。《吹毛求疵录》从报纸文章中看到了 文字背后的“封建社会的婚姻观、生育观、男女观、家族观乃至人格观”。其中一则妻 子不得承继财产的启事声明就赤裸裸表现出“女人是制造子孙的工具”,另外一则妇女 逃婚的消息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买卖婚姻的现象,在人们头脑里仍然存在着忠 孝节烈的观念。《谈妇言》批判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肯定了妇女接受文化教 育的权利。《“祖国”与“情郎”》对视女人的爱情为男人的附庸的行径予以批判。《 邓肯女士与中国》剖析了某些人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剥夺妇女的权利,阻碍男女平等。 《关于几个女人的是是非非》指斥了“祸水说”。《女作家》肯定女作家的文学价值的 同时,批判了某些人以女作家为名来哗众取宠。舒芜为妇女“立言”,其思想源于人道 主义和现代人学观念。他看到女性与男性在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社会性不平等, 主要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认同造成的,因此他致力于对社会进行现代性思想的启蒙 。从话语的背后解读社会文化意识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是舒芜进行文化批判和思想 启蒙的杂文轴心。舒芜同时充分认识到在中国扫除封建意识残余、树立现代人学观念的 艰难,一向处于社会卑微地位属于弱势群体的妇女要想真正获得自由和解放,还有相当 长的路要走。
舒芜的杂文体现了珍爱生命自由和意义的人学观念。在现实生活的文化个体与群体、 现象与精神的冲突中,去发现潜隐在其中的生命的自由、意义和价值,这是舒芜杂文的 鲜明特色。《关于<立像与胸像>的两件事》就是一种生命的感发,他为勃朗宁的诗《立 像与胸像》“那种热爱生命的爱情,和充溢着爱情的生命力所震动”,感叹“原来充满 着生命与爱情的一对年青人,就只留下一对既无生命又无爱情的冰冷的塑像,悲凉地对 立于终古苍茫之中了”,批判了“那些在现实生活里面怯懦软弱,只能在虚妄的‘希望 ’里面得到躲避之所的人们”,“只看到人生的无常,生命的漂浮,人生或生命的意义 的被玩忽”。他主张人应与生活热忱地搏斗、与现实抗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才能显现 。《吹毛求疵录》、《谈妇言》等杂文在广阔的历史和现实文化空间中表达出对妇女命 运的深切关怀,对忽视女性生命存在,剥夺她们生命自由的封建文化予以猛烈抨击。舒 芜杂文从五四“人学”立场出发,肯定世界上一切生命自由存在的合理性,憎恶无视他 人生命的做法,并呼吁人们学会理解生命的意义。他又从戴东原、王船山等人的理论中 受到启发,从爱情自主、婚姻自由、理想追求、人格独立等“人欲”层面体认了个体生 命的价值,描述了在现实人生的混沌状态下个体生命的风貌。但是,这只是体认了个体 生命的自由形态,没有提出如何优化个体生命的途径。舒芜指出社会性是人的生命本质 ,主张以“新思想”为武器,与生活搏斗,与人民结合,在“生命的燃烧”中获得人的 独立、价值、尊严。也就是说,舒芜强调的不是一般的个体生命,不是那些软弱的堕落 的个体生命,而是强调生命中“主动地认识并把握客观现实”的人格力量,以及能深刻 认识生活、坚强把握人生、创造自己生命价值的“主观精神”。
舒芜的杂文洋溢着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精神。1940年代,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和文化 上对革命力量进行打压,白色恐怖令人窒息。在此形势下,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和法西 斯主义的斗争也日益高涨。舒芜的杂文有坚实的现实向度,批判的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 当局,不畏权势,敢于斗争,对黑暗现实进行揭露、鞭挞和讽刺,有着鲁迅式的“硬骨 头”。《“真”与“雅”》讽刺国民党政府宁可弃北平也不舍文物,不要江山却要古董 的可耻行径。《国家育才之至意》、《尊师一法》针砭时事,把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暴露 无遗。《“国字”的奥妙》以日寇和明清的“文字狱”为喻,批判了国民党的文化高压 政策。《知识青年向学者们要求什么》提出了人民民主的问题,在文化领域里反对法西 斯主义,希望学者们向青年开启“民主精神和民主态度”的大门。在《一切都是人民问 题》中,舒芜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的德国是“反人民”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 “为人民”的国家;源于叔本华、尼采思想的“国家主义”实质是以“国家”为武器, 剥削人民,掠夺全世界,帮助法西斯们磨利武器用来砍人民的头。
舒芜的杂文表达了知识分子必须与人民结合的时代要求。鲁迅先生把“人各有己,朕 归于我”作为通向“人国”的途径,个性解放始终系于民族解放、国家民主和人民自由 。舒芜沿着鲁迅的精神路向,突出强调了知识分子自我批判、走向生活、与人民结合的 发展道路,杂文中弥漫着入世精神、忧患意识。在《知识青年向学者要求什么》中,舒 芜提出学者们要注意“出处进退”、“辞受取予”的问题,发扬东林学派关注天下事的 传统。以研究为服务,与青年共进步;以梁任公(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 战”的精神;廓清(国民党)笼罩在人民头上的迷雾;关注人间事,扎根于现实的泥土, 吸取人民的健康的土气汗气来健康自己的学术思想。在《教授的生活》中,舒芜批判了 教授的生活脱离人民的生活,没有替自己修出或找出一条路来,也不曾替学生修出或找 出一条路。他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出发,坚持把个性解放与人民解放结合 起来,批判胡适、陈独秀等人在获得“新思想”后,不与现实人生的要求化合,不与人 民结合,表现出革命的软弱性。在《一切都是人民问题》中他强调了人民本位观点,批 判了林语堂所谓的“忍耐力”,反对周作人、朱光潜等人所主张的冷静超脱的“静穆观 照态度”和高高在上的贵族式的“客观态度”,主张知识分子在血肉的现实生活中发扬 “主观战斗精神”,从社会、文化、思想的层面匡正反动的、非正常的思想观念,走向 革命的人生。
三
舒芜的杂文是在后期七月派的文化空间里与胡风、路翎等同人的文学交往中生成的。 胡风在主编《希望》时有意识地加强了杂文的份量和成色。七月派成员创办的《泥土》 、《呼吸》、《蚂蚁小集》等刊物的杂文也占有较大比重。这些刊物拥有舒芜、方然、 阿垅、路翎、耿庸、何剑熏、赵荒陵、魏仲奇等一批杂文作者,但从数量和篇幅看,舒 芜是主笔和带头人。如《希望》合计出版8期,共刊载杂文70篇,其中舒芜有41篇,约 占60%。1947年胡风主编《七月文丛》时,把舒芜发表的杂文编为《挂剑集》出版。舒 芜作为七月派杂文的中坚分子,不仅代表着七月派杂文的成就,也突显了七月派的文学 个性和文化精神。
七月派“盟主”胡风以鲁迅为宗,他的理论深得鲁迅的思想神韵。他说:“为祖国的 解放的斗争同时也是为祖国的进步的斗争”,“对外抗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内部发 展的过程”。[4](P628—629)在他的理论思想中,启蒙与救亡、解放与进步、自我与人 民理想化地融为一体。在鲁迅和胡风的深刻影响下,七月派诗人在创作中突破自我精神 世界的藩篱,从现实生活、民族传统、域外文化中汲取生命与艺术的营养,把个性解放 的追求寄寓于民族解放之中,使二者相融为一;七月派小说家始终把个性解放与民族解 放作为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坚韧地探索个人、民族和人类的命运。舒芜也毫不例外, 他的系列杂文以启蒙精神对政治、文化生活领域的封建意识和时弊给予猛烈抨击,大力 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和生命的价值意义,颇具鲁迅精神和风骨,显示了七月派文学“主 观战斗性”的品格。在创作中,舒芜先肯定“人欲”层面的自然属性是生命的基础,又 立足于社会性是人的生命本质,主张在突入生活和与人民结合中获得人的独立、价值、 尊严,其实质是把个体解放与人民进步化合,以主观精神、人格力量优化个体生命。显 然,舒芜的杂文创作演绎了胡风的文化精神和思想结构,也体现出七月派文学所独具的 审美现代性特征。
有着“鲁迅风”的舒芜杂文,不仅受到了胡风和同人的称赏,也受到了革命文艺界的 肯定。胡风在编辑《希望》时致信舒芜说,他的杂文可“布得疑阵”,使论敌“不敢轻 易来犯”,自己感到十分快慰。[5](P486)在《编后记》中,胡风把舒芜的杂文比作“ 让麻醉的神经受一点刺痛”的匕首,并认为“所得到的成绩却超过了预定的期待”。[5 ]同为杂文家的耿庸也认为舒芜的杂文颇具鲁迅风骨。[6](P600)革命文艺领导人虽然对 舒芜的哲学论文持否定态度,但对舒芜杂文却表示了嘉许,如叶以群在批判舒芜《论主 观》时,赞扬了舒芜的杂文。[1](P606)由此可见,舒芜杂文的批判性和进步性是相当 突出的。
四
虽然舒芜的杂文深受鲁迅和胡风的影响,但在创作风格上与他们迥然有别的。尽管舒 芜像鲁迅那样针砭时弊、匡时救世,但他淡化了直面论敌,指“黑”打“暴”,怒骂严 斥的战斗色彩,更多地向民族历史和文化心理挖掘,力图警醒人们愚昧麻木的心灵。如 《“嗜痂”与“制痂”》、《吹毛求疵录》、《谈妇言》、《关于几个女人的是是非非 》、《“国字”的奥妙》等杂文,揭露社会上流行的一些腐朽思想和病态现象,在历史 评述和现实叙写的交错中注重对“世道人心”的挖掘,在对历史文化的透视中表现出批 判的力量。舒芜的杂文少有鲁迅式的幽默和讽刺,往往是把愤世嫉俗的情感蕴藉在委婉 平实的叙述中。尽管舒芜的杂文充斥着胡风文学理论的关键词和类似语句,如“奴役” 、“征服”、“摄收”、“搏斗”、“突击”、“生命力”、“战斗要求”、“人格力 量”、“生命的燃烧”、“主观战斗”、“自我扩张”等,但还是少了份胡风式的澎湃 激情与凌厉气势,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不是诗人气质,而是一种学者风范。《舒芜杂文自 选集》里的“内容提要”曾对舒芜杂文的总体风格作了一个概括:“舒芜是位学者型的 杂文家,他的杂文旁征博引,以古鉴今;辨识深刻,沉郁蕴藉;深刻处可见锋芒,冷静 中饱孕情感。”这种特色在舒芜1940年代的杂文创作中已经体现出来了。
舒芜杂文创作风格的形成自然与他的家学渊源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受到周作人的影响 。出身桐城翰墨世家的舒芜,自幼就受到曾祖父方宗诚、外祖父马其昶、曾国藩等人的 思想和著述的陶冶,并从小就对理学产生了兴趣。尽管舒芜后来实现了从理学向五四新 文学的跨越,但家学渊源的影响无法抛却,舒芜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8](P4-19)舒芜 杂文因合时世、品议时政的“性情”很大程度上受教于桐城派“经世致用”的为文之道 。桐城派在务求文章“经世致用”的同时,还要求才气和学识。方东树、姚莹等就认为 才、学、识是文章的“三本”。舒芜从小大量阅读家里藏书,博闻广识,治学为文受到 家学的训练,因此他的杂文总是引证古今中外的材料,不发空疏的议论,知识丰富又捭 阖自如。在家学渊源的影响中,潜在无形又最为重要的是思维形式的熏陶,它直接作用 于舒芜杂文的思想和表达。舒芜从小对理学感兴趣,由此形成了长于客观思辨的学者式 思维,所以他的杂文富于冷静从容的理性色彩,行文总是从生活琐事和社会现象出发, 通过“格物致知”的方式以达现代文化启蒙的目的。
舒芜谈论新文学总是把周作人和鲁迅相提并论,一直认为周作人代表着新文学的另一 半。周作人对舒芜的思想和杂文影响很大,他杂文中的人学思想和女性意识就源自周作 人。此外,舒芜还十分欣赏周作人的小品文,认为周作人在1930年代的抄书散文是古今 未有之创体。[9]他的杂文自觉地借鉴吸收周作人小品文的写作手法。我们从《谈妇言 》一文就可窥见一斑。这篇杂文,品析历史,漫谈现实,娓娓言辞中寄寓着对妇女命运 的关注,让人体悟、感知她们的痛苦和不幸。早在1940年代,耿庸就敏锐捕捉到舒芜的 杂文有着“卖弄学识”的周作人气;胡风当时说舒芜的杂文“迂回婉转”,“能引人入 微”[7](P600),但他没有明晰此乃周作人小品文的雅致之风。当代学者王兆胜认为舒 芜晚年的书话散文受周作人影响,重“心灵感知”,但理性意识和启蒙意识较强,多了 些杂文气质。[10]其实把这段论述反过来,也非常切合舒芜的杂文特色:舒芜1940年代 的杂文受鲁迅思想的牵引,重“文化启蒙”,但由于周作人的影响,多了些小品气质。 如果说,1940年代的杂文家在继承和高扬鲁迅杂文的传统时存在着两脉流向:战士型和 学者型,那么舒芜无疑是后一风格的重要代表。
收稿日期:2004-04-20
标签:鲁迅论文; 杂文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七月派论文; 舒芜论文; 胡风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希望论文; 周作人论文; 鲁迅中学论文; 散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