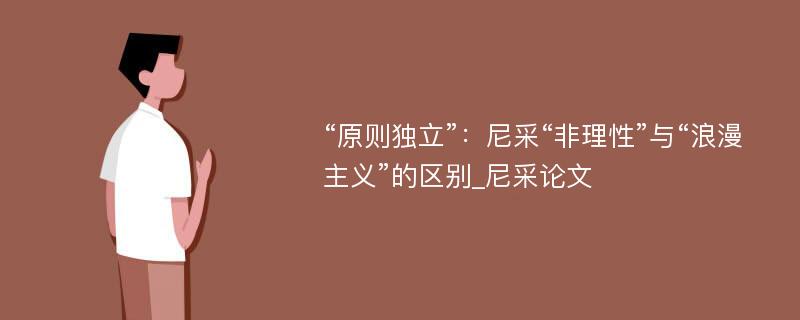
“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尼采“非理性”或“浪漫主义”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采论文,浪漫主义论文,Principium论文,Individuationi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思想家尼采是一位不断引起争议的人物。他提出的“酒神精神”一度被斥为“残忍的兽性”,他的名字也与纳粹相提并论。(注:[美]W.考夫曼编《存在主义》,陈鼓应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98页。)近来在国内学术界的“后现代”热之后又兴起一股尼采热,这一次是把他的“非理性主义”当作浪漫主义式的叛逆精神而大加赞美。无论斥为反动还是捧为革命,有两点大概是人们不假思索的共识:一是视尼采为“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的鼻祖”,以酒神精神反抗理性传统;二是认为他倡导浪漫主义哲学,要求个性自由。(注: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 134—135页、第224页、234页。 )至今国内各类西方现代哲学的教科书都给尼采贴上“非理性”的标签,似乎尼采哲学就是一种不要任何约束而放纵自我本性的哲学。
阐释尼采不能离开他的文本。如果细读一下尼采本人的作品我们就可以发现:一,尼采反复声称日神与酒神同属艺术范畴,从未把日神等同于理性或科学。《悲剧的诞生》(注:Friedrich,Nietzsche The Birth of Tragedy (1870-1),trans.Francis Golffing.Doubleday & Company,Inc:1956.中译参照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中与酒神精神相对立的是科学主义,而科学主义不等于科学;二,尼采本人对浪漫主义有严格的界定和批评,把它视为一种“自然主义的激情”与酒神精神相区别。以下就尼采的日神、酒神、理性、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从理论与历史表现两方面谈谈笔者的看法。
《悲剧的诞生》开篇即言:“艺术的持续发展是同日神和酒神的二元性密切相关的”,两者不断“撞击”并“和解”才产生艺术,缺一不可。就艺术理论而言,这一二元性思想贯穿尼采的作品,从未偏废。日神阿波罗是一切造型力量之神,把事物与自然母体分离,按“个性化原理”(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赋之以形式。但艺术家把原始的激情定型成艺术作品的过程不是在清醒的理性意识下完成的,而是在梦幻之中运用“更深刻的认识能力”达到的。这种“象征性”的认识能力构成了艺术的特征。
因此日神非但不是有害的,而且是完成艺术的关键力量。它与科学思维有严格的区分:科学运用逻辑推理,而艺术需要直观的象征能力。应当指出,把艺术与科学、象征思维与理性思维分离的观点并非始于尼采:17世纪意大利的维柯把艺术思维称作“诗性逻辑”(poetic logic),不同于科学逻辑(scientific logic);以后卡西尔明确表示“逻辑本身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它被划分为互相分离而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想象的逻辑和理性的科学思维的逻辑。”(注: Ernst Cassirer Essay on Man.中译参照甘阳译《人论》,译文出版社,1985 年, 第175页。)
日神力量是将某种原始、基本的东西用一种形式固定下来,这种东西就是酒神。这是一种“醉”的状态,当此状态的人放弃自我,“醉倒在大地上并与大地融为一体”。在尼采看来,人生“一切痛苦的根源和始因”就是个体的生命。酒神的作用在于冲破自我,把个人投入波澜壮阔的生命源流,重建人与自然的统一。
由此可见酒神精神的本质是消除主观自我达到客观。这不同于浪漫激情的主观抒发。尼采强烈反对主观的艺术:“主观艺术家不过是坏艺术家,在每个艺术种类和高度上,首先要求克服主观,摆脱‘自我’,……没有客观性,就没有最起码的真正的艺术创作。”他指责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以“炽热的情感取代酒神的兴奋”,这种虚张声势的修辞抒情“绝对不能进入艺术范围的思想和情感。”有人曾把酒神精神比作弗洛伊德学说的“本我”,(注:Keith M.May Nietzsche and the Spirit of Tragedy,Macmillan,1990年,p.2.)但本我是一种个体性的动物本能,而尼采的酒神却正是要打破个体。
自我解体是艺术家应走的第一步。但自弃不等于艺术。尼采明确指出“在酒神的希腊人同酒神的野恋人之间隔着一条鸿沟”。古巴比伦人也有酒神节,但其狂歌欢舞仅仅是“人向虎猿退化的陋习”而不是艺术。是什么使希腊人的自弃成为艺术?正是“那种奇妙的二元性”,是“巍巍然屹立的日神”阻止了酒神活动,并顺势塑造成稳定的艺术形式。然而任何形式必然是一种约束,野性的酒神必要寻找反抗的出路,于是两种相对力量此消彼长,最后在一个适当的时刻达到和解:这便是艺术史上的最高成就——古希腊悲剧——诞生的时刻。它既充满激情,又给予“形而上的慰籍”,是日神和酒神这对父母共同生育的孩子。
通过概念分析我们看到:酒神精神如同汹涌的欲望之河,时时冲破个人屏障,使人回归宇宙本源,获取新的动力;日神精神是坚实静穆的堤坝,它约束并规范流水,提醒人认清人生的界限,重建新的自我。经过日、酒神作用后的自我已不是原来经验现实中的理智的自我,而是既具个性、又与大地血脉相通的自我,是“本人形形色色的客观化”,是“根本上唯一真正存在的、永恒的、立足于万物之基础的自我”。在此意义上,尼采与康德相仿,康德以具有“先验共通感”的艺术来沟通主体与客体、个人与世界;尼采则将艺术喻为杂技表演者,优雅地走过架在无底深渊上的窄桥(注:尼采《人性,太人性了》,载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第208页。)。 他的艺术从“自我的束缚中逐渐摆脱出来,……直到最后仿佛可以完全解除:这个‘仿佛’乃是艺术中必然发展的最高结果”。“仿佛”在此是指:艺术作为一种存在必然采取一种固定的形式,而在最好的艺术中,形式如此自然地从内容中诞生出来与内容合成一体,艺术的两大力量结成如此紧密的神圣联盟:“酒神说着日神的语言,而日神最终说起酒神的语言来”,以至于旁人再也无法区分内容和形式,酒神和日神,艺术家和艺术品,“舞蹈者和他的舞蹈”。
从理论探讨可以得到日、酒神动态平衡直至融合的理想结论。然而理想在时间现实中的展开过程必然是不平衡的。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使理性得到高度张扬,自然科学取得惊人发展,人类的自我意识迅速膨胀。在一种“黄金时代”的乐观氛围中,一些人把科学理性超历史地提升,把它视作检验事物的惟一标准,以为执此科学主义的笏杖便能从此一劳永逸。尼采尖锐地指出这种“科学乐观主义”或称“逻辑公式主义”的弊端:抽象的符号、公式、规则日益脱离其生命之源,蜕变为“理论世界”的樊笼,人们如同希腊神话里干瘪的笼中侏儒西比尔,呼吸着其中的“汽油和柏油”的气息(见艾略特诗《荒原》),不再能感受自然与生命。
尼采反对的不是科学或理性本身,而是绝对化的科学主义。他本人从未把这种科学主义等同于日神精神,而是严格地把前者称为“反酒神精神”。然而作为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倾向,日、酒神的确不限于艺术领域。艺术与科学并非绝不相能,日神的艺术造型能力与科学的抽象能力有着共通之处。所谓抽象,顾名思义就是将固定的形式(“象”或“相”)加在流动的万物之上,它也是一种赋形作用,不同的是科学用推理得到概念规律的“相”,而艺术用象征得到譬喻性的图“象”。这也就是卡西区分的科学理性的逻辑和想象的逻辑。日神、艺术、科学、理性确有一脉相通之处。我们不妨理解为一种形而上的规范力量。事实上,整个文明就是一种规范,没有这种规范人类可能已在野蛮冲突中自行灭亡。人类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打破僵化的不合时宜的范式并创造新范式的进程。任何形式都不能夸大成绝对真理,否则只能是抛弃了酒神的极端日神的表现,是自我毁灭的“挑战者”和“泰坦尼克”。
尼采认为,这种惰性的理论世界观与古希腊的悲剧世界观进行着永恒的斗争,并且预言“只有当科学精神被引导到了它的极限,它所自命的普遍有效性被这极限证明业已破产,然后才能指望悲剧的再生。”那么向普遍的传统权威宣战的浪漫主义算不算“悲剧的再生”呢?作为对启蒙运动的继承与反动,浪漫主义要求摆脱一切传统,强调艺术家的主观自我表达。在《抒情歌谣集》(1880)中,华兹华斯给诗下的著名定义是“诗是内心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济慈也称“如果诗歌来得不像树长叶子那么自然,那还不如干脆不来。”可见浪漫主义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亦即尼采所谓的“自然主义的激情”。尼采岂能落时尚之彀,如前所述,他对“主观的艺术”和“自然主义的激情”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我指的不是自由。……在今天这样的年代,放任本能更是一种灾难。”(注: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5页。)个人必然是有限的, 如要视一切文化为洪水猛兽,盲目崇拜个人,放纵自我本能,其结局只能是“人与禽兽之异几稀矣”,这样的人其实是最不自由的。《权力意志》中也多次提及浪漫主义,把它与“消极”、“激情”、“自然性”等词划上等号。事实上,浪漫主义强调的主观性的确遭到不少批评。《浮士德》中以拜伦为原型塑造的欧福良在飞向高空的途中灭亡,“当时诗歌中的浪漫主义有过分充沛的精神,但缺乏自我克制,所以终于炸裂生存必须的形式。这是欧福良,也是拜伦。”(注:董问樵《〈浮士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7页。)其后的象征派诗人也都批评并力求摆脱浪漫派的主观性,寻求“个人才能”与“传统”的结合点、诗歌与现实间的“客观对应物”。当然浪漫主义留下的经典名作不能抹煞,但它们的成功恐怕不尽是其理论的结果。创造是艰难的,如果艺术像树叶般自然长出,它也会像树叶般迅速凋谢;不凋谢的是那千锤百炼、逼真又更胜于真的“最后一片树叶”。
正如“日神倾向”与“科学乐观主义”仅有一线之隔,“酒神倾向”与“自然主义的激情”亦相差无几。两者都包含激情,但什么样的激情是酒神式的自弃的激情,什么样的激情只是本能的放纵?事实上,酒神精神和浪漫主义在激情这种表达形式上是相似的。尼采自己也认为两者都属于悲观主义。但他同时又对两者的产生动机及目的作出区别:前者是“苦于生命的过剩的痛苦者,对现实给予的幸福表示感激”,后者则“对现实不满”,是“苦于生命的贫乏的痛苦者”,(注:尼采《权力意志》(1891),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 202页。)两者的根本差异是对生命现实的态度积极与否。尼采是具有强烈生命意识的哲学家,他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主张事物本身没有善恶,关键在于如何运用,是否激发活力,实现生命的“强力意志”:“我在每一个场合均问这里从事创造的是饥饿还是过剩,……着眼于创作的动机究竟是对凝固化、永久化的渴望,对存在的渴望,抑或是对破坏、变化、更新、未来、生成的渴望。”(注:尼采《快乐的科学》,载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第254页。)
尼采哲学的中心观点是唯生论,是对丰富多彩的生命的肯定与弘扬。理解了这点,我们便能挣脱所有概念的束缚:不要说日神和理性、理性和理性主义、酒神和浪漫仅有一步之差,甚至日神与酒神、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些对立的概念都往往在最短的直线距离上互相转变或并存。如古希腊悲剧正是日神和酒神的互相融合。而背离传统的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则同时具有“逻辑推理”和“自然主义激情”两种不健康的倾向:它既是“冷漠悖理的思考”,又是“炽热的情感”,主角失去了形而上的追求,沦为只追求感官享受的虚情的庸人。遗弃了酒神的欧里庇得斯必然也为日神所抛弃。现代的欧里庇得斯式悲剧同样是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杂交:在科学领域,理性作为反对神权的解放力量曾激发了生命创造力,但延及19世纪演变为超历史的绝对原则,科学变成了“非逻辑”,启蒙性的智力开发变成教条式的智力退化;在艺术领域,优秀的作品如歌德、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尊重并学习传统规范的结果,但“现代诗艺缺乏从自造的束缚中逐渐摆脱出来的幸运过程。……现代精神带着它的不安,它对规范和约束的憎恨,……先是借革命的狂热挣脱缰绳,然后当它对自己突然感到畏惧惊恐之时,又重新给自己套上缰绳,……不过是逻辑的缰绳,而非艺术规范的缰绳了。”(注:尼采《人性,太人性了》,载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第 208—209页。)激情的自以为是的创造只是重蹈前人的足迹, 最追求“自由”的人成为最受自然逻辑束缚的奴隶。这在劳伦斯和艾略特的笔下有典型的描写:《荒原》中以女打字员和她来历不明的情人为代表的现代人的性爱已堕落为没有“爱”的“性”;而劳伦斯认为现代的所谓色情小说根本未触及生命意义上的性爱,不仅不是酒神化,而且是极端日神化,反映了这个过于理性的“自腰部以下已经灭亡的时代的抽象精神”(注:D.H.Lawrence,the Critical Hertiage,ed.R.P.Draper,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0,p.298.)。 他的小说正想提醒人们什么是真正的酒神意义上的性。
综上所述,艺术理论中的日、酒神在思想史上代表两种基本倾向:一是与造型、规范、逻辑等相连的形而上作用,极端化为科学绝对主义;另一种是与激情、自由、浪漫等沟通的形而下作用,极端如“自然主义的激情”。人处天地之间,兼具通天的理性和根植于地的感性。两者相抗又并进,才有人类的健康发展。任一方的泛滥都会打破平衡,自绝于生活本身。两种极端取向在本质上又是相同的。理性与非理性在各自的极点上吻合。尼采曾形容科学主义者“惊恐地看到逻辑如何在这界限上绕着自己兜圈子,终于咬往自己的尾巴”,又把“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比作“一条咬往自己尾巴的蛔虫”。(注: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6页。)喻体的巧合并非偶然。人们只见用铁锤砸破一切传统的尼采,却不见潜心钻研古希腊文化的尼采;只见他扔掉梯子,不见他先踏实地攀登梯子;只见他疾呼酒神,不见他对日神的形而上渴求也一样强烈:他的“强力意志”、“超人”、“永恒轮回”等概念都表现人类克服自我、追求完美的不懈斗争。海德格尔称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的哲学家。事实上,无论以理性或非理性、形而上或形而下来概括尼采哲学似皆不得要领。概念本身没有善恶,惟一的“善”是丰满的生命。尼采式的“超人”坚守自己的信念,努力挣脱既定的常轨,以卓然独立的孤勇逆行。这样的生命真实而致密,于瞬间爆发出美丽和辉煌。或许理想越完美,越是痛感身之为人的种种无奈,才变得越绝望。尼采的作品标题:《看哪,这人》、《人性,太人性了》都明显不过地反映了这种矛盾思想的挣扎。是否是对人类的太透彻的认识导致了他的毁灭?这是永远发人深思的一个哲学事件:一个如此了解人类、如此热爱并渴望生活的人却以精神失常结束了生命。但他的哲学思想却激发了后人长久的思索,由此而言,尼采并没有死,或者说,他正像那被泰坦巨神撕成碎片后获得重生的酒神。
后现代文学批评早打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旗号。在此我无意以“不合时宜的人”或“尼采的最后一个弟子”自居,但想指出阐释必以文本为基础,认为尼采哲学是非理性的、浪漫主义的看法即可通过证伪排除。同时尼采哲学在今天仍不失其讽世意义。现代(或后现代?)社会似乎同样是一首奇异的交响曲:商品经济的基调上奏着“科学(或功利?)至上”的主旋律,“结构”、“符号”的科学商业音名渗透到艺术等各个声部;而同时进行的主题变奏曲则发自蝇王岛上的无知小儿,发自叫喊着打倒一切权威、解构一切文本的后现代主义者,发自意识流的喃喃自语,发自从世界各个幽闭角落现身于媒介之上的原始、仿原始部落,发自一个“黑暗的心脏”。这首交响曲是否和谐,又将如何发展,让我们引用但丁的一句话:在现世面前,我们都是盲人。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引用的一些评论家不乏对“非理性”和“浪漫”作全面论述者,但学术名词一经不严肃的媒介渲染,成为一种分不清是媚俗还是媚雅的时尚,便丧失了原意。尼采追求的绝不是在“非理性”旗号下自由放纵的个人,而是高度自律自醒的“超人”。他在日、酒神理论中重复多次的关键词语“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更是别具深意。查拉丁语“individuationis ”及衍变而来的英语“individual”主要有两义:一是分离的,个体的;二是不分离的,不可分割的(in-divisible)。中译本都译为“个体化原理”,Golffing的英译本则注为“不可分离的、终极的原则”(undivided or ultimateprinciple),似乎是各取一端。 尼采作为艺术家对语言多义性的灵巧把握令无数译者头痛;但这个古老的拉丁词根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人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他既是个体,又与自然溶为一体,不可分离。
标签:尼采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酒神精神论文; 艺术论文; 悲剧的诞生论文; 文化论文; 科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