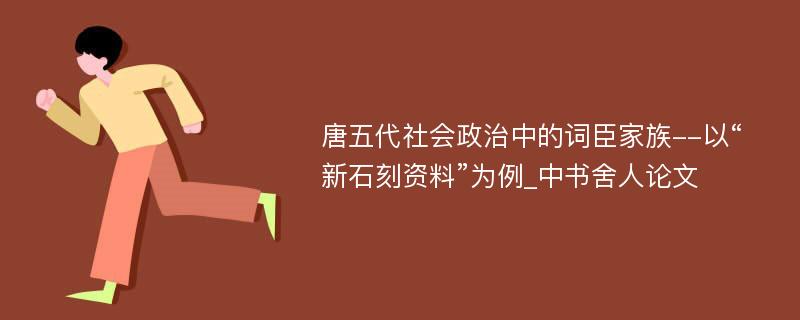
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石刻论文,为例论文,新出论文,唐五代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
在短短十几年内,石刻史料从一种边缘性史料成为中古特别是唐代研究最为丰富的信息来源之一。造成这场静悄悄的革命的是数以万计反映唐代各类人群生活景观的新出墓志。这使许多以往学界难以着手的研究课题成为可能。如此大规模出现的史料也促使传世文献中的历史讯息产生了新的意蕴,并迫使学者重新思考许多以往接受的历史观点。它使我们对唐代社会的了解能更加立体化并能窥视到更多构成其运作的肌理,使许多被历史湮没的环节得到呈现。墓志提供的细节之丰富是惊人的,对这些细节的解读也许是琐细的,其结果却能让我们对唐代社会的认识立体化。但研究者不应满足于从中找到历史的细节,墓志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也是古人用来表达其自我认知的重要空间。墓志的解读和研究工作无形中也打破了中古特别是唐代文史研究的界限,这组以新出墓志材料为中心的研究文章只是当下中古学界许多这类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荣新江陆扬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4-0005-12
唐代是将“文”的价值日益提升为社会和政治精英的核心素质的时代。这一提升对日后中国的社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为何文学在唐代会越来越受重视?这一看似容易解答的问题实则非常复杂,迄今为止中外学界虽对此现象的发展轨迹做了不少探讨,提出了不少看法,笔者感到这些解说仍不够充分和细腻。对这一现象的历史分析必须将心态史、文学史、政治史、制度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作多层次的观察,既要分析南北朝以来的各种传统和唐代政治文化现实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又要了解唐代的社会心态是如何影响这一过程的。其中一个关键的分析视角,便是所谓的词臣及其家族的发展。近年已经有一些学者对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等重要词臣做较为仔细的研究,但从整体上讨论词臣在政治中的影响及其意义却很少,同样缺乏的是将词臣家族和唐五代精英群体的变化相联系的研究。词臣即承担制诰或起草中央重要文书的大臣,尤其以知制诰、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为代表。虽然在唐以前词臣的职能就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重视,但只有在唐代,词臣才真正成为代表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化身,也是这一传统中最受尊敬和瞩目的成员,其地位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不少词臣成为唐代政坛最为显要的人物,这点在晚唐五代尤其突出。关于词臣生平和家族的材料,包括两《唐书》在内的传世史料中也有不少讯息。但能较完整地将重要词臣的生平轨迹、社会关系以及获取的某种文化与政治的定位勾勒出来的,近年发现的唐五代词臣墓志却是无可取代的好材料。从中可看到大量传统史料所不具有的细节,也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和制度的现实存在的词臣的发展轨迹上,揭示了许多曾被历史淹没的变化环节。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从唐五代墓志中择取较有代表性的六个案例,来探讨当时社会与政治文化中词臣身份的演变和结果。
唐五代词臣墓志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由于词臣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很高,他们的墓志对他们的生涯和家族情况往往介绍得比较详细;第二,他们的墓志也大都由同时代著名文臣所撰写,撰作者又对书写对象的成就和身份有很强的理解和认同,因此书写质量往往较高,其文字蕴含的意义比较丰富。这里首先涉及的是孙思邈之子、武周时期的中书舍人孙行的墓志,由时任鸾台给事中的著名文人徐彦伯撰写,其文的主要部分如下:
公讳行,字符一,太原中都人也。(中略)父思邈,曩在唐运,肃簪梁苑,身居魏阙之下,志逸沧海之隅。公清情雅韵,不因近习;爽心真骨,得之自然。年甫孩抱,已不好弄。迨于巾冠,尤难干犯。(中略)好读书,富词彩,亡箧能记,下笔不休。调露中,应岳牧举,对策甲科,敕授鄜州洛交县尉。寻丁父忧去职。服阕,补洛州渑池县尉。屡栖邦佐,未展厥庸,擢此下僚,登于近侍。敕授右拾遗,入侍青蒲,出居丹掖。邻密勿之地,处谏争之曹。鼎饪伫和,三公侧席。俄丁母艰去职,再居苫块,柴毁骨立,踰礼之酷,时论哀之。曾未半朞,有制权夺,仍复旧位。公载践阶戺,多怀謇谔。緑函青纸,亟奉清闲;枢论密词,□留稿本。寻降敕曰:“右拾遗孙行,履识清雅,学涉优长,久侍轩墀,载效忠谨,宜加宠授,擢掌丝言,可凤阁舍人内供奉。”寻而即真。乌雽!良玉藴石,孰掩其曜;美才具体,终不后时。公衔职帝謩,飞翔禁掖。提赤牙之翰,组织王丝;步文石之阶,抑扬朝寀。尝摄凤阁、鸾台、夏官三司侍郎,左台御史大夫,司礼卿。(中略)即授公朝散大夫,守太子中允。(中略)嗟乎!今年在巳,郑康成之有梦;本命暨辰,管公明之长往。以久视元年十一月七日,遘疾终于道化里之私第,春秋六十。即以其年腊月十六日迁窆于合宫县之北邙山,礼也。①
孙行生平颇显赫,《旧唐书·隐逸传》孙思邈传最后提及“子行,天授中为凤阁侍郎”。此外只有《元和姓纂》卷四华原孙氏条提到:“唐处士孙思邈;生行,中书舍人;子济,左司郎中,润州刺史”。②孙思邈虽长年具有处士身份,却也是当时名人,高宗时曾被征入朝,受到礼遇。《旧唐书·隐逸传·孙思邈传》:
显庆中,复召见,拜谏议大夫,固辞。上元元年,称疾还山,高宗赐良马,假鄱阳公主邑司以居之。③
孙行墓志提到他进入仕途首先是通过制举的成功:“调露中,应岳牧举,对策甲科,敕授鄜州洛交县尉”。岳牧举发生在调露二年(680),距孙思邈“称疾还山”的上元元年(674)并不很久。和孙行同时登科的还有员半千、殷楷等。④以孙行久视元年(700)去世时六十岁计算,他应岳牧举人时已近四十。这一行为很可能是武后时期通过制举等手段大力选拔草泽的结果。孙行在对策甲科后先担任鄜州洛交县尉。志文提到任此职不久就“丁父忧去职”。据《旧唐书·隐逸传》载,孙思邈死于永淳元年(682),与墓志纪录吻合。孙行丁忧后又补洛州渑池县尉,然后成右拾遗。墓志中特别加入了一份朝廷的除授制书,其中有“擢掌丝言,可凤阁舍人内供奉”等语,据志文“寻而即真”的字句,这应是先以凤阁舍人内供奉身份知制诰,随后才真除凤阁舍人。独独在墓志中加入授予知制诰的制书,说明孙行及其家人对这一授命的看重。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存有一篇孙行撰写的制书《西州氾德达可轻车都尉制》,署名正是“给事郎守凤阁舍人内供奉臣孙行”,纪录时间是“延载元年九月廿九日”。⑤这样孙行任凤阁舍人内供奉的时间大致可确定为694年前后。而担任凤阁侍郎当在此之后,因此《旧唐书》的记载有误。孙行此后任职大概以左台御史大夫和司礼卿为巅峰,只是不清楚他究竟在行政上扮演了何种角色。孙行处在一个政治变化剧烈而政坛人员起落频繁的年代,同时也是唐廷开始真正重视文词的政治效用的时代,凤阁舍人这一职位的文词要求显然比以往突出得多,这或许也是墓志的作者特别要强调的原因,但同时这一职位在制度和人事中的升降又受高宗武后时期特殊政治气候左右,进退颇不正常。孙行登科后十四年内便已跻身政坛高层,具有超擢的性质,不能不说是特殊境况造成。而他以闲散的正五品下的太子中允终结其政坛生涯,较左台御史大夫与司礼卿等职位都有所下降,墓志虽以身体状况为由,我们也不能排除和政情有关。不过从墓志看他仕途平稳,未遭明显的贬抑的经历,这在武后时代的高级官僚中不多见。
假若孙行成为词臣的例子有其特殊性,那么高宗武后时期对词臣的重视则是一持久之现象,对社会精英的心理造成冲击并产生深远影响。新出墓志中有两篇能凸显这一趋势,这就是徐坚为其父徐齐聃所作的《徐齐聃墓志》和岑羲所撰之《韦承庆墓志》。⑥《徐齐聃墓志》写于上元三年(676)。文中所涉及徐氏家族从南朝到唐代的情形近已有刘子凡做了精细考察。⑦刘子凡指出,徐氏家族能从“南方次等氏族”一跃而成唐代重要的文学官僚家族,固有凭借与唐帝室的特殊关系之处,更多却是依靠徐齐聃和徐坚父子的文化修养,体现出南来士人在唐初获取成功的特殊方式。这一判断无疑准确。保存在张九龄文集里的《徐坚神道碑》和新出《徐峤墓志》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这一过程。
徐坚在《徐齐聃墓志》里开宗明义地将“文”的意义提到无与伦比的高度:
孤子令坚闻:太上立德,隋武子死而可归;其次立言,臧文仲没而不朽。故以激清澜于百代,垂令范于千龄。是知树德不孤,有邻攸在。至如苞两贤而独映,兼二美而孤轩,芳徽与日月俱悬,茂轨共江河并逝者,窃谓先君为体之。
这里说“立言”能“没而不朽”和墓志末了铭文中的“可大者德,不朽唯言。懔然生气,千祀如存”前后呼应。张九龄在《张说墓志》的铭文中同样提到的“言而有立,古无不死”。这些地方的“立言”都非泛泛所指,而是有很具体的内容。墓志称赞徐齐聃的天纵文才:
先君禀辰象之祯辉,体山河之秀气。黄中内湛,止水外凝。体鉴清华,等玉山之引明月;瓌姿挺映,如珠树之引春风。粤在弄章(璋),而神情照射;岁伊怀橘,而风彩嶷然。甫年小学,窥览不疲。镂金群玉之书,五行俱下;兰叶芝英之字,一见无忘。文藻温华,新声绝唱。年十余,太宗闻而召赋诗。受诏辄成,特蒙赏叹,因赐金装刀子一具。黄香之日下无双,多惭声实;葛瞻之聪明可爱,有愧风猷。年十四,为弘文馆学生,齿迹环林,连踪国胄,博通经史,具览群书。谈丛发而珠玉开,文锋举而琳琅坠。俄而才华藉甚,郁号文宗。
这段文字着力渲染徐齐聃的词学能力。现代读者不应简单视之为溢美之词而加以忽略。正是通过此类书写,一种强大的舆论渐渐形成,将文才视为与生俱来的素质,且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体鉴清华”式的德性外露,润色王言又是这种素质最重要的体现,这就是“立言”的实质。徐坚毫不犹豫地为其父冠上“文宗”之名,这一地位恰要通过下面这样从龙朔二年(662)开始的长达九年的制诰经历才能为世所认可:⑧
敕西台舍人内供奉,寻除西台舍人。职典青筒,荣参紫闼。枢机周密,契温树之无言;朝序倾风,等高山之斯仰。纶诰之美,海内推雄。议者以有国已来,罕有此例。
这里徐齐聃从充西台舍人内供奉到真除西台舍人的经历和孙行相同,但他的影响力远在孙行之上。徐坚笔下,徐齐聃的纶诰之美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岑羲在《韦承庆墓志》里表达出与《徐齐聃墓志》非常类似的立场。韦承庆这位活跃于高宗武后时代的政坛人物,《旧唐书·韦承庆传》称其“辞藻之美,擅于一时”。⑨虽然他在后世的声名不如和他同时代的李峤、崔融,但在当时也是“大手笔”的代表。韦承庆属京兆韦氏小逍遥公房,其实他的曾祖和祖父官位止于县令,到了他父亲韦思谦才骤然进入权力的核心,终成武后朝的宰相,使韦承庆的家世背景符合唐前期“当代冠冕”的标准。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臣,韦承庆在事业上的成功固然有其门第因素,更多恐怕还是获益于他的家庭背景和本人的才能。韦承庆事迹唐代史料中有较详细的记载,这份墓志固然可以补充不少讯息,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唐代书写中较早对词臣意义作出清晰定位的文字,这种定位在中唐以后的文字里成为一种评价词臣的固定模式。墓志起始就说:
夫天降贤才,必偶昭明之后,俗登仁寿,式资恭懿之臣。观稷契之升朝,则知惟尧之德;鉴闳散之膺辅,允叶隆周之祚。其有德冠前烈,道光终古。发挥词诰,润色于皇猷;模楷彝伦,范围于士则。则我韦府君见之矣。
这个开端点出韦承庆是以词臣身份服务于朝廷,就像张九龄在《张说墓志》里说“始公之从事,实以懿文”一样⑩。“发挥词诰,润色于皇猷”的贡献使他能“德冠前烈,道光古今”。作者在提到韦承庆担任凤阁舍人内供奉服阕兼掌天官选事的经历时说:
自体国分官,以为人极;开物成务,式代天工。庶政攸归,丝纶之寄为重;九流是总,衡石之地尤先。公入掌王言,语晋与长舆比德;出参铨管,在魏与平叔齐声。非夫重望,孰谐佥属。
所谓“庶政攸归,丝纶之寄为重”,也就是说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维系必须通过出色的丝纶来完成,这种观点在唐以前就有,但此时却开始被无限放大,成为一种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墓志评价韦承庆制诰的能力说:
公冠冕词宗,弥纶学府。虽便繁百奏,吐洪河而不竭;密勿繁机,洞灵台而毕综。
称韦是“冠冕词宗”,的确是对他身份最为恰如其分的描述。而在同样以制诰著称的作者岑羲看来,出色的制诰不仅要学识渊博,更要有在政情变化的瞬息把握人心微妙并将之精确表达出来的能力。
韦承庆和徐齐聃的情况颇为类似,虽然家族的背景在其成功中扮演了相当的角色,但也都受益于唐代新的政治和文化的风气。正是开始重文的风气使其家族固有的传统获得更好发挥的机会。唐长孺曾就中古南朝文学的北传提出过敏锐的看法,指出北魏太和后,南朝的文风开始影响北朝,形成风气。这种情况在唐代早期“取得巨大成果,江左余风占领了北方文坛”。(11)韦承庆的例子正可印证这一看法。自北魏以来,一些北方高门开始转向重文并将之作为家族传统,其中京兆韦氏尤其突出,比如北魏后期的韦彧,就以草诏闻名。近年发现的《韦彧墓志》说他:“优册雅言,谟明盛辰。□(或为“飞”)章符檄之文,蔚万古以葳蕤;军国诏告之翰,□(或为“历”)千祀而昭晰”。对其制诰的评价之高与《韦承庆墓志》对韦承庆的评价无异。《徐齐聃墓志》和《韦承庆墓志》不约而同用“文宗”、“词宗”这类含义相同的名称来形容各自书写的对象,也非偶然。这里的“文宗”和“词宗”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造诣,而是替朝廷立言的文臣。也就是说,这类墓志和当时其他文人书写中不断出现的对文与统治关系的讨论一样,都渐渐将一种文学和治术结合在一起的价值观推举为文学的最高评鉴标准和精英最值得向往的成就。
与徐齐聃和韦承庆的墓志相比,新发现的《窦华墓志》在这方面的表彰就要逊色一些。(12)《窦华墓志》撰者是肃代之际以诰词著称的徐浩。对于窦华的记载正史里并不多,墓志提供了清晰完整的生平,恰好可以补充。墓志开头提到窦华“弱不好弄,幼而能文”。关于他的仕进经历,墓志有如下的叙述:
年廿四,秀才登科,解巾相州安阳尉,调岐州扶风、河南府河阳主簿,摄洛阳尉,即真,迁丞。俄转万年丞,摄大理寺丞,充和市、和籴判官并监司农出纳。丁家艰外除,正授大理丞摄殿中侍御史监左藏出纳。无何,正授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内忧去职,服阙,迁刑部员外郎充铸钱判官兼侍御史,别敕知台杂事,擢兵部郎中兼知如故,迁中书舍人加翰林、集贤院学士。
据两唐书的记载,窦华是作为杨国忠的亲信进入玄宗时期政坛的最高层。傅璇琮根据史料曾推测窦华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同时成为翰林院学士和集贤院学士是在天宝十一载杨国忠正式任宰相时期的事。(13)墓志虽然没有提到具体时间,但这个推测完全成立。其任官经历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两点,一是窦华在任中书舍人和翰林院学士之前长期服务于大理寺和御史台,主要工作都和财政管理有关,是个不折不扣的财政官。《新唐书》卷二○六《外戚·杨国忠传》载在鲜于仲通在云南败于南诏之后:
时国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为匿其败,更叙战功,使白衣领职。因自请兼领剑南,诏拜剑南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开幕府,引窦华、张渐、宋昱、郑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师。
墓志提供的窦华的任官经历恰好说明杨国忠开幕府引入窦华不仅因为两人在政坛上是联盟,也和窦华长年的职业经验有关。第二是窦华活动时期恰好是翰林学士院的形成期,也是词臣在唐代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开始上升并成为其新价值的代表性人物的关键时期。墓志说窦华“幼而能文”,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窦华在担任中书舍人和翰林院学士之前,有制诰的经历。这说明无论是在中书舍人还是翰林院学士的职位上,当时杨国忠引入的窦华、张渐、宋昱等人最主要可能还是从这些职位在行政体系上的重要性着眼,即中书舍人的参与决策与翰林院的接近内廷,而非这些人的丝纶之才多么出众。《窦华墓志》里徐浩对窦华的宦海生涯有如下的总结:
其効官也,使奏清白者一。特敕摄职者二,辟为判官者两,再知出纳三,典刑章,登南宫而外,掌宪简,拜西掖,而内刊秘籍。政方之用,台阁振其风霜;文翰之美,缃汨资其粉泽。至于发挥帝典,启沃皇猷,削藁诡词,人罕知者。
其中对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掌诰经历有所涉及,文字中有表彰窦华履行词臣职事的字句,但着墨不多,而“至于”云云虽表示窦华在这方面的贡献少为外界所知,实际也说明窦华并非以草诏文词名闻于世。窦华在中书舍人和翰林院学士的位置上和杨国忠本人的用人旨趣相关,从史料记载来看,杨国忠更多注重吏干型才能。同时在他推荐下成为中书舍人翰林院学士的张渐倒似乎在文才的表现方面有更多些的证据。(14)这里还可以比较一下稍早出土的苑论所撰的《苑咸墓志》。《苑咸墓志》作于元和六年(811),对象苑咸不仅是窦华的同僚,也是玄宗朝后期最知名的词臣之一。(15)苑咸的履历更符合唐后期词臣的生涯轨迹。但苑论在《苑咸墓志》中仍提说:
尝闻于宾客家相之言曰:公既龀,聪敏加于人。七岁诵诗书,日数千言,十五能文,十八应乡赋,耻以文字进,以经济为己任。
可见那一时期经济之才受到执政者的重视。开元到天宝时期以文词著称和以吏干知名的大臣都可以担任中书舍人,这和唐中期以后中书舍人以词臣为最重要的身份迥然不同,这区别同时体现在中书舍人职位升迁轨迹上。(16)窦华从长期担任于财政管理这类被视为“剧务”的位置上骤然转为被视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的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在8世纪末以后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另外窦华和张渐先后都以中书舍人的身份进入翰林院担任学士,这相较于肃代之后通常选择品阶较低的官员进入翰林学士院也有相当大的不同,也说明翰林学士院仍只比较临时性的机构。
上文讨论的《韦承庆墓志》和《徐齐聃墓志》体现的是一种从价值观和舆论的角度将朝廷典诰的制作与体国经野相联系、同时对词臣贡献加以定位的努力,接下来要讨论的《杨收墓志》和《卢文度墓志》则体现出当这种价值观在唐代后期开始深入人心并形成新的政治文化时,这种政治文化是如何成为一种强大的实际力量,使被认为能代表这种政治文化的人物及其家族在政坛和社会上获取了巨大的成功和声望。《杨收墓志》撰于咸通十四年(873)(17),而《卢文度墓志》作于后唐同光二年(924)二月。以时间论《杨收墓志》早了五十多年。但从本文论述重点考虑,这里先讨论《卢文度墓志》。
该墓志的撰者杨紫□身份是后唐的中书舍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志文正式的标题是《唐故罗林军□(当作“使”)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上柱国范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卢公权厝记并序》。志文中特别解释了当时无法将卢文度安葬回在长安万年县的家族墓地,只能临时安葬在河南。这种不能葬回家族墓地的情况非常普遍,但用“权厝记”而非寻常的“墓志铭并序”标题似有刻意标榜家族历史的意味。无独有偶,卢文度的同僚张文宝也是五代时期著名的词臣。卢价为他所作的墓志也以“权厝记并序”为题。(18)
这篇墓志涉及本文讨论重点的内容甚多,这里先引其序文的主要部分:
公讳文度,字子登,范阳涿人也。□乎氏族,则神农炎帝之祚胤也。暨十三代□□□派系□其□诸简籍,今莫得备述。然其祖祢间,遁时者则有神仙,济世者则有□□。知是于积功累行所钟者也。又分南北二祖,其实一宗焉。公乃北祖第四房□□。曾祖讳□,皇任河中朔方副元帅参谋、检校户部郎中,累赠□□□。烈祖讳简能,皇任驾部员外郎,累赠司徒。显考讳知猷,皇任检校司空、□□□□□,累赠太师。公即太师第二子也,幼则奇骨异表,壮乃博识强记,平生□□□□□者,览之如风□,出言成章,落笔如流,一时俊彦,莫之与京。一举擢进士上第,□□□宏词殊科。当时品流,无不开路者。释褐秘校,次任小著作,旋戴豸冠,□升□□。俄迁左□小谏。□□推以赴,已知勃□之势,不可得而□也。未几北飞,仍服银艾,转左史。充职期月,迁小□、知制诰,加以金组。俄为右司正郎。司言之称,喧于中外,紫微真秩,两加成命。寻乃首冠玉堂。猗欤!猗欤!天临笔砚之泽,于斯一□□□。陟民部戎曹二侍郎,依前视草。时以籍之重,论者佥其才可,乃拜春官,振滞□才,颇叶于公议。然有唐三百年,无卢氏主文闱者,公始辟之矣。俄转右辖。一入禁苑,十有五年,扬历三署,华显十资,所谓稽古之人也。洎右辖归南官,兼判二铨,加驭贵之阶,开上等而食邑。复为五兵侍郎,佐丞相□史笔,仍总选部东铨事。同光初,王师收复中原,六合混一。是时内则缺官,复诏入掌诰,密勿之地,平窥霄汉。无何,杯影疑蛇,床闻斗蚁,竟为二竖之所用。同光二年正月十六日薨于福善里私第,享寿五十有二。公之先代楸寄长安万年县小赵村,咦!是岁不利,乃权卜河南府河南县梓泽乡,厝于宣武里。呜呼!以公之轩冕内外,德行文学,无出其右也。公之龙章凤姿,清言雅道,无得而踰焉。夫如是,乃文儒之间气也。何天与其才,不与其寿,惜乎哉!外族清河崔氏,累追封晋国太夫人。公两娶清河崔氏,其继室者,封本邑县君,皆姻不失其亲也。无子,悲哉!痛哉!公令弟文纪,守尚书兵部侍郎,友于孝敬,虽古有美被田荆之行,不可同日而言。今则龟筮式从,牛眠荐吉,克以同光二年二月十一日衔痛护之灵,窆于□□之里,礼也。(19)
这篇墓志提供了一个从唐末到五代的清流家族成员的完整的生涯案例,意义非凡。卢文度在新旧《五代史》中皆无传,但他却是一个延续几乎两百年横贯整个中晚唐的成功文学官僚家族的终结人物。这个家族具有最典型的唐后期政治文化精英的特点。墓志虽一开始就强调卢文度作为著姓范阳卢北祖第四房后裔的煊赫背景,实际这一因素对卢文度家族在唐五代的成功帮助很有限。这一家族成为政治精英的真正肇端恰是“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也就是志文中提到的“皇任河中朔方副元帅参谋、检校户部郎中”的文度曾祖。笔者认为,中晚唐许多类似的文学官僚家族都有著姓背景,但实际在唐中期以前已被排除在政治权力的中心之外,连续多代都不再有任显宦的成员。但中唐以后,在朝廷乃至整个社会日益看重文学才能的氛围中,这些家族由于某一位成员被视作杰出文人,或一代中几位成员在进士科等文学考试中获取连续性成功,从而积累下深厚的文化和社会资本。即便这种资本未即刻转化为仕途上的成功,这些家族的下一代也能成为真正的获益者,其结果是不仅以下每代都有进士及第的成员,且相继以词臣身份连登台阁,进入政坛的最高层。这种现象也不断出现在非著姓家族上。个别凭借这种词臣地位确立的家族在玄宗甚至玄宗以前就已开始出现,比如从武后时代开始的崔融家族和从玄宗时期开始的孙逖家族,但此类家族的频繁形成是要到8世纪晚期也就是代、德朝以后。笔者称此类文学官僚家族为唐代的清流家族,其延续能力甚至能抗拒一时的政治挫折,因为他们的奕世衡贵被当时社会赋予了超越政治地位之外的更多的象征意义。这是一种新的精英群体,既非旧门阀,也不是宋以后的士大夫家族。从卢文度的曾祖卢纶开始,中经卢简能、卢知猷两代,到卢文度,其经历正是清流家族发展轨迹的最佳例证。
卢纶的生涯大都在幕府度过,史载卢纶晚年时德宗曾考虑让他掌诰,只因卢纶去世才未能实现。(20)尽管卢纶未能成显宦,他的文学声望变成一种无形资本,使其子辈在科举与仕途上大放异彩。卢纶的四子简辞、简能、弘正、简求先后登进士科,其中简辞、弘正、简求都备历清贯,最终做到了大镇节度使。而简能,也就是卢文度的祖父,或许是兄弟四人中最有潜力成为词臣并进入中枢的成员,只因被视为才俊,在郑注担任凤翔节度使期间被辟为幕僚,最后在甘露之变中不幸被杀,成为政坛事件的牺牲品。但卢简能的这一遭遇并不影响其子孙的前途。简能子知猷进士及第后仕途顺利,担任的职官中包括了中书舍人,词臣身份尤为突出。简求子弟中至少有嗣业、汝弼二人进士科第,汝弼在唐昭宗和后唐庄宗时均知制诰。《旧五代史·卢汝弼传》甚至称庄宗时“除补之命,皆出汝弼之手”。(21)嗣业子就是墓志中提到的卢文度的堂弟卢文纪,后者也在唐末进士及第,仕途贯穿五代各朝,后唐成为宰相,后周时以司空致仕。(22)
据墓志纪录,卢文度的家族籍贯已是京兆万年县人,这和新旧《五代史》中记载的卢文纪的籍贯一致。文度在唐末五代的任官经历大约如下:获得一举登第的荣耀后,又中博学宏词科。释褐任校书郎,著作佐郎,殿中侍御史,然后升左补阙,不久以左补阙入学士院充翰林学士,在院期间转起居郎,迁官(由于墓志字迹漶漫不能确定何职位)并加知制诰,再迁郎中、中书舍人,不久加承旨。此后又加户部和兵部侍郎衔,仍充翰林学士。接着以礼部侍郎身份知贡举。最后以尚书右丞的身份出院。文度出院的具体年份不清楚,但应是在后梁建立以后,近出后梁《牛存节墓志》有“诏命翰林学士卢文度撰碑辞以旌其墓”语,即指梁太祖授命卢文度撰写牛存节之神道碑。(23)此后卢文度转任吏部侍郎主铨选,复为兵部侍郎,佐宰相修史,仍总铨选。墓志称后唐光复后,他又再度成为翰林学士,并于同光二年九月去世。他不仅在科举上获得惊人的成功,且长期具有词臣的身份,整个生涯经历了词臣的最优选的任官途径。墓志提到他首次担任翰林学士时任期长达十五年,这在晚唐确实很罕见。尤其让墓志的撰写者感到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卢文度乃有唐以来第一位主持科举的范阳卢成员。这和比如多位清河崔成员曾主持科举的现象形成有趣的对照。卢文度知贡举应该在乾宁三年后,但具体年份不清楚,孟二冬在《登科记考补正》中认为,卢文度知贡举的时间是梁太祖初年,这是由误读《卢文度墓志》产生的论断,但以文度和文纪以及他们的叔父如弼进入五代后事业的成功推断,文度在梁初知贡举可能性完全存在。
有关卢文度的生平,这里还要补充一点。《文苑英华》卷四一九有钱珝《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卢说妻博陵郡君崔氏进封博陵郡夫人制》。又卷四五八有卢说《授李思敬马殷湖南节度使制》。此卢说两《唐书》无一字提及,据傅璇琮考证,《文苑英华》卷四五八的这篇卢说撰写的制文正确的标题应该是《授李思敬保大节度使、马殷湖南节度使制》,此制当撰于乾宁三年九月。据此卢说当为唐昭宗乾宁二、三年间入为翰林学士。上文已提到卢文度曾以兵部侍郎充翰林学士承旨。而墓志中又说:
公两娶清河崔氏,其继室者,封本邑县君,皆姻不失其亲也。
笔者认为这里提到的卢文度继室被封为本邑县君就是钱珝制文中提到的卢说妻“博陵郡君进封博陵郡夫人”一事。无论时间、卢说的职衔还是其夫人的姓氏地位都与卢文度吻合,由此可知卢文度的名字在《文苑英华》中被误作卢说。
墓志的结尾段落里,撰写者连叹“无子,悲哉!痛哉!”这一感叹似非一般意义上为一位有著姓背景的逝者的家庭的中断表示惋惜。撰写者当很清楚卢文度代表的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家族。以这一家族的常态来判断,当时人不难想象假若卢文度有后嗣,复制他的这种成功的机率很高。而无子这一自然律的限制恐怕是阻碍这种成功的最难意料的因素之一,甚至可说比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更无可挽回。当然子弟的素质也不能忽略,卢文纪纵然有子嗣,但其平生积累的巨万财富“为其子龟龄所费,不数年间,以致荡尽”。(24)
《杨收墓志》是对晚唐政坛重要人物和词臣杨收生平的一个独特的勾勒。墓志作者裴坦也是晚唐重臣,和杨收有类似的经历。杨收在两《唐书》中有传,在一些基本史实的层面上两《唐书》和墓志可以互证。已有学者据《杨收墓志》来对杨收和晚唐政坛人物和事件的关系做初步的分析。(25)本文的重点是讨论此志中传达出的唐后期词臣和政治文化的关系,但墓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对于书写对象有其特殊的描述路径。对于作者来说,要传达给心目中读者群体的整体意旨往往更为重要,这在《杨收墓志》这类作品里会体现得尤其明显,因此研究者不易作割裂式的分析。
以唐代墓志而言,《杨收墓志》可算是巨制,长达近两千八百字。墓志从一开始就将杨收的意义放在整个唐代的大脉络中加以定位,称其为房、魏、姚、宋一类能确保大唐事业的人物。和《卢文度墓志》一样,《杨收墓志》里也反复强调杨收作为弘农杨氏成员的著姓背景。甚至借用杨收兄弟之口来传递这一讯息。墓志特别说杨收是隋越国公杨素的八世孙。杨收标榜自己是隋代重臣杨素的八世孙几乎成为这一家族的历史记忆的重要部分。比如杨收侄女、杨发之女杨芸的墓志里就称是“隋越国公素之裔”。(26)但这一陈述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旧唐书·杨收传》说杨收“自言隋越公素之后”就是一种很不肯定的语气。(27)至少和同时期政治上极为成功同时也称为杨素之后的杨嗣复家族相比,这种族姓身份要不确定得多。杨收在当时被认为是孤进,他死前上书唐懿宗称“臣出自寒门,旁无势援,幸逢休运,累污清资”,谅非虚语。其祖辈三代皆地方基层官僚(28),正说明其弘农杨氏的背景就和范阳卢在卢文度家族成功的帮助一样,并不很重要。杨收和他的三个兄弟恰恰是他这一家族能够振兴的关键原因。杨收和他异母兄杨发、杨假以及同母弟杨严先后进士及第。杨收更是一举登第,和卢文度情况雷同。从此这四人的仕途都相当顺利,其中杨收和杨严更以翰林学士的身份成为懿宗朝词臣。对于奠定家族地位而言,杨收兄弟既扮演了卢纶式的开创性角色,又实现了卢简辞兄弟的成功。用裴坦的话说,就是“公昆弟四人,率用文华,声光友睦,次第取殊科,赫弈当代”。此种异军突起的实际缘由必然包含一些家族传统和社会网络的因素,比如两《唐书》杨收传和墓志都提到的杨收家族的学术传统和母亲教育的背景。但毕竟还是有突出的个人因素,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在攸关前途、竞争剧烈的晚唐,面对拥有强大得多的社会和政治资源的成员,杨收兄弟能连续取得如此的收获。裴坦着力渲染的就是这样一种个人的神话。他笔下的杨收几乎具备一种卡里斯马式的个人魅力。而这种魅力又是处处和以“文”为核心的新政治文化的趣味相合。
从两《唐书》杨收的传记看,杨收拥有的文学神童的形象恐怕当时确实为社会所接受。但到了裴坦笔下仍有进一步的渲染:
公未龀喜学,一览无遗,五行俱下,洎丱而贯通百家,傍精六艺。至于礼仪乐律、星筭卜卦,靡不究穷奥妙。宿儒老生,唇腐齿脱,洎星翁、乐师辈,皆见而心服,自以为不可阶。为儿时已有章句传咏于江南,为闻人矣。以伯仲未捷,誓不议乡赋,尚积廿年,涵泳霶渍于文学百家之说。洎伯氏仲氏各登高科后,公乃跃而喜曰:吾今而后知不免矣。亦犹谢文靖在江东之旨,时人莫可量也。将随计吏以乡先生,书至有司,阅公名且喜。未至京师,群公卿士交口称赞,荐章迭委,唯恐后时。至有北省谏官,始三日以补衮,举公自代,时未之有也。
“公未龀喜学,一览无遗,五行俱下”云云,和徐坚对徐齐聃的描述如出一辙,强调的是才学的与生俱来和在社会上造成的先声夺人的效应。
墓志中如下一段文字将杨收的这种神奇效应推到极致:
由是一上而登甲科。同升名者,皆闻公之声华而未面,牓下跂踵,迭足相押,于万众中争望见之。公幼不饮酒、不茹熏血,清入神骨,皎如冰硅,咸疑仙鹤云鸾降为人瑞,澹然无隅,洁而不染。始也,同门生或就而亲焉,则貌温言厉,煦然而和潜,皆动魄而敬慕之。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提到杨收“不茹熏血”的习性。这里可以比照《旧唐书·杨收传》的叙述:
收以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勖之曰:“俟尔登进士第,可肉食也。”
《旧唐书》文字突出的是杨收守礼孝母的品行,但这显然不是裴坦宣扬这一细节的意旨所在。在墓志里,这变成一种仿佛不习人间烟火的特点,使杨收成为宗教意义上的“清”的化身,这种“清”和他的文学才能也密不可分。同时这种“清”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裴坦形容众人眼里杨收如仙鹤云鸾般的外表和李商隐笔下的李德裕十分相似(29),也令人想起《金华子》中的一段对晚唐世冑子弟崔澹的描述:
崔涓弟澹,容止清秀,擢登第,累登朝列。崔魏公辟为从事,清瘦明白,犹若鹭鸶,古之所谓玉而冠者不妄也。
原本中晚唐的士人为了寻求仕途上的前程,往往要干谒当朝权要和节度使以获取后者的提携,具有孤进身份的杨收不大可能成为例外,然而读裴坦的叙述,读者感觉包括周墀、王彦威在内的当朝名臣,对于仍是一介布衣的杨收奉迎唯恐不及:
久而归宁江南东,诸侯挹公之名,皆虚上馆以俟之。故丞相汝南公时在华州,先遟于客馆,劳无苦外,延入州,引于内阁,独设二榻,问公匡济之术。公抑谦而谢,久而不已,后对榻高话达旦,汝南得之心服,如饵玉膏饱不能已。至于大梁,时太原王公尚书彦威在镇,素闻公学识深博,先未面,一见后,与之探讨,王公礼学经术该通,近古无比,著《曲台新礼》初成,尽以缃袠全示。公详焉,因述礼意,及曲台之本意,王公敬服,命袌简以谢。
这即便包含历史的真实性,也是裴坦对杨收形象的一种再造,目的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将杨收凝固为裴坦所认同的这个清流群体的象征,其存在居于尘世的众生之上。这是依靠“文”的价值观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努力。这种努力并非只留于文字,晚唐的现实让我们看到这种努力的实质性成果。已经担任了懿宗朝宰相的杨收于咸通八年被贬为端州司马,可以说在政治上处于完全失势的地位。咸通十年(869)更被流放驩州并就地赐死,“坐收流死者十一人”。(30)按常理这该是对杨收家族的致命打击,但这种打击显得很短暂。裴坦在咸通十四年作的《杨收墓志》中能对杨收作如此毫无忌讳的拔高,固然有朝廷昭雪的前提,(31)但也显示在晚唐特殊的文化下,杨收这样的人物在声望上拥有的相对独立性。距离杨死六年,杨严子杨涉就进士及第,这很可能是当时的清流精英在政治空气变化下对杨收家族的一种支持。杨涉后在唐哀帝时成为宰相。杨收子杨钜与杨严另一子杨注分别于广明元年(880)和中和二年(882)及第(32),并都在昭宗时期成为翰林学士。傅璇琮据现存杨钜所撰制文的规格,很有见地地指出杨钜在昭宗时期的学士院深受重视。(33)杨收另一子杨鏻也于乾宁三年(896)及第,五代时成为高官。杨涉子杨凝式的生涯更是贯穿整个五代。杨收的长兄杨发子杨乘“亦登进士第,有俊才,尤能为歌诗,历显职”。(34)可以说杨收兄弟的子弟完全复制了父辈的成功。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引用《旧唐书·杨收传》的评语“世非贵冑,门以艺升”,称杨收一门是“唐末五代间之世家”,可谓准确。而这里的“艺”最主要的就是文词的能力,具体的表现方式就是担任替朝廷立言的词臣,也就是墓志中说的“公于理道相业军国之机出于天资,人之所难,折若斤斧。内有刀尺,外无锋铓。落笔如神,率皆破的”。
上文涉及的几方新出墓志,它们的出土诚然是历史的偶然,但恰好透露出成为唐代政治文化新价值和秩序代言人的词臣的三个关键时期的联系和差异。这种联系和差异并不仅仅具有制度史或政治史的意义,墓志能比其他材料更为完整的展现当时社会对这些词臣的整体观感,即便这些观感包含了强烈的主观色彩,放在恰当的语境下可让我们看出文化意识是如何成为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过程。表面看来,徐坚家族上下三代的词臣身份和唐后期的杨收和卢文度家族数代为词臣的现象似乎很类似,实际却有本质的差别。徐氏家族的情况只是那个时代的特例,促成这一特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北朝以来社会往往根据精英群体事业上的不同特点对其家族做了身份上的定位,使得徐氏家族能在这种定位体系中获取独特的资本。同样的情况也落实在韦承庆身上。但徐氏家族或韦承庆式的成功尚未得到社会舆论和心态以及与之对应的政治结构的充分支持,因此这种成功不易大量复制。这和晚唐清流家族对词臣身份的垄断现象相去甚远。后者存在于一个“文”称为精英普遍追求的时代。然而徐氏父子和韦承庆的欣赏者开始将他们的工作看做统治天下的不可或缺的精致手段,通过墓志这类书写来确立舆论的方向,这种舆论的扩散虽也经历了类似窦华时代的曲折,却能在唐后期成为价值系统的主导。杨收和卢文度是这一意识形态的真正受益者。比照《杨收墓志》和《卢文度墓志》,我们会发现它们表达的旨趣极相似,两个家族的发展轨迹和原因也几乎一致。差别只是前者是后起之秀,体现唐后期代表清流家族能不断涌现的社会特征。杨收兄弟造就了一个新的清流家族,而卢文度则是这种典型的清流家族的受益者。虽然他们墓志的撰写者不断强调他们门第之美,实际他们成功的要素更多来自于其他的方面。孙拙是孙逖家族在唐末五代时期的传人,其墓志也在近年被发现,本文由于篇幅限制未能加以讨论。孙拙担任过后唐庄宗的知制诰和中书舍人。其墓志中就开宗明义强调其家族“世济文行,织于简编,余烈遗风,辉图耀谍”,墓志铭文里也说“时论允归,承家典诰”。(35)这才是这些家族得以不断延展巩固的真正秘诀。他们的墓志中对门第姓氏的强调只能说是一种身份再塑造的工作。这正是观感和现实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时常会造成现代研究者的困惑,但凭借着新材料和新方法,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景观。
注释:
①《大周故太子中允孙公志文并序》,拓片及录文见《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6—327页;又赵文成、赵君平编选:《新出唐墓志百种》,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②林宝:《元和姓纂》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69页。
③据《太平广记》引《谭宾录》,孙思邈显庆三年被征入朝,“寻授承务郎,直尚药局”。(见岑仲勉为《元和姓纂》卷四孙思邈条所作的校记。)“承务郎直尚药局”固然契合孙思邈的特长,但和《旧唐书·孙思邈传》的记载相差颇大,何况此时孙思邈已是高寿的隐逸之士。当然孙思邈传未必没有夸大的可能,但笔者认为《谭宾录》中提及的这一职授更可能是唐太宗时孙思邈第一次被召入宫时的情况。
④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83—84页。
⑤录文见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卷一九,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7页。
⑥《大唐故前西台舍人徐府君墓志铭并序》,拓片和录文见《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第196—199页;《大唐故黄门侍郎兼修国史赠礼部尚书上柱国扶阳县开国子韦府君墓志铭并序》,拓片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3册,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9页。
⑦刘子凡:《唐代徐氏家族及其文学家传》,《唐研究》第1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7—304页。
⑧关于徐齐聃担任西台舍人的年份,参看上引刘子凡文,第293—296页。
⑨《旧唐书》卷八八。
⑩张九龄:《故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并序》,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52页。
(11)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收入《山居存稿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2—241页。
(12)正议大夫守国子祭酒上柱国会稽县开国伯赐紫金鱼袋徐浩纂:《唐故朝议大夫中书舍人集贤翰林院学士窦府君墓志铭并序》。据陈尚君先生见告,此墓志的志石目前为私人所藏。笔者的录文根据的是尚君先生提供的拓片照片,在此表示感谢。
(13)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沈阳: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页。
(14)关于张渐的生平考辨,见傅璇琮:《唐代翰林学士传论》,第207—212页。
(15)《唐故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安陆郡太守苑公(咸)墓志铭并序》,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9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9—391页。依据《苑咸墓志》所作苑咸生平的研究可见胡可先:《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6)这方面研究可参看孙国栋:《唐代中书舍人迁官途径考释》,收入《唐宋史论丛》,1980年香港龙门书店初版,此处引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1—146页。
(17)《唐故特进门下侍郎兼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弘文馆学士太清太微宫使晋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冯翊杨公墓志铭并序》。该墓志的志石目前为私人所有,录文根据毛阳光:《晚唐宰相杨收及其妻韦东真墓志发微》,《唐史论丛》第14辑,2012年。
(18)《唐故中大夫守尚书吏部侍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公(文宝)权厝记并序》,拓片和录文见《洛阳新获墓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33、313—314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6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212页。
(19)《卢文度墓志》拓片见《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9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7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170页;又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127—130页。此处引用的录文在标点上略有不同。上述录文志主名均作卢文亮,陈尚君指出当为卢文度之误(《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二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注2,第3882页),甚是。
(20)《旧唐书》卷一六三《卢简辞传》载:“太府卿韦渠牟得幸于德宗,纶即渠牟之甥也,数称纶之才,德宗召之内殿,令和御制诗,超拜户部郎中。方欲委之掌诰,居无何,卒。”据《卢文度墓志》,卢纶以捡校户部郎中的职衔终于朔方节度使幕。如果德宗时朝拜户部郎中,那志文决无不提之理由。因此《旧唐书》的记载必然有误,但不能因此排除德宗有这种考虑的可能性。《新唐书》卷二○三《文艺传下·卢纶传》载:“是时,舅韦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见禁中,帝有所作,辄使赓和。异日问渠牟:‘卢纶、李益何在?’答曰:‘纶从浑瑊在河中。’驿召之,会卒。”这个记载应该比较可靠。关于卢纶生平的考订,可见史广超、涂显镜:《卢纶家世生平补考》,《贵阳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68—70页。
(21)《旧五代史》卷六○,又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5—1917页。
(22)卢文纪事迹可见《旧五代史》卷一二七《卢文纪传》,《新五代史》卷五五《卢文纪传》。又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二七,第3881页。
(23)《梁故太平军节度使郓曹齐棣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师牛(存节)公墓志》,拓片见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下,第654页。该墓志提到“太师之功业,焕乎简策,彰于碑颂,此不尽书”云云,也可以证明卢文度所撰为神道碑而非该墓志。
(24)《旧五代史》卷一二七《卢文纪传》。
(25)关于这一墓志牵涉的杨收与晚唐政治人物和事件的关系,可参考毛阳光:《晚唐宰相杨收及其妻韦东真墓志发微》,《唐史论丛》第14辑,2012年。但有关杨收生平最为全面的考辨,可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330—340页。虽然该著完成时《杨收墓志》尚未被发现,但傅璇琮的讨论仍有不少值得参考的意见。
(26)《唐故岭南节度使右常侍杨公女子书墓志》,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乾符0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1页。
(27)《旧唐书》卷一七七。这点已经由傅璇琮指出,见《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第330页。
(28)关于唐代孤进问题的研究,可参看王德权:《孤寒与子弟:制度与政治结构的探讨》,载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台北,2008年版,第41—84页。文中也讨论到杨收的情形,见该文第56页。
(29)李商隐:《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惟公字文饶”以下部分,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4册,第1665—1666页。
(30)《新唐书》卷一八四《杨收传》。
(31)据《新唐书·杨收传》,杨收死“后三年,诏追雪其辜,复官爵”。此事当发生在咸通十三年(872),即裴坦撰志的前一年。墓志中也说“果蒙皇泽,昭洗克复,官勋爵制,一以还之”。这也应当是杨收得以归葬的原因。
(32)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二三,第984、986页。
(33)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第540页。关于杨注的翰林学士经历,参看该著第606—608页。
(34)《旧唐书》卷一七七《杨发传》。
(35)王骞:《唐故朝散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柱国赐紫金鱼袋乐安孙公墓铭并序》,录文见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第176—1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