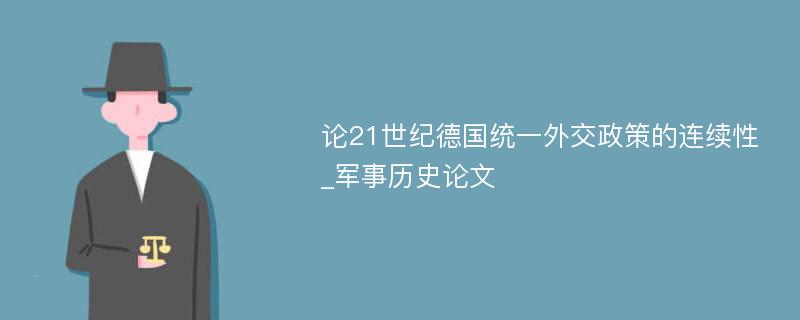
统一德国21世纪外交政策连续性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外交政策论文,德国论文,连续性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789 (1999)05-0069-78
“柏林共和国”(指1990年10月3日实现统一,并于1999 年将议会和政府从波恩迁往柏林的德国)在21世纪向何处去,是新世纪国际关系,特别是欧洲国际关系的一个热点问题。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柏林共和国将成为一个扩大了的“波恩共和国”(指统一以前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其二战以后与西方一体化的外交政策定势与取向维持不变;抑或会承袭“俾斯麦德国”(指1871年第一次实现统一的德国)的历史传统,重蹈一个正常民族国家的旧辙,即谋求与其地缘政治和实力地位相适应的特殊民族利益?一句话,是继续多边外交还是重行独立单干?
人们的耽心是由统一德国的强大实力引发的。有人认为:德国统一以后没有更加强大。因为在技术上同美国和日本相比,德国还有很大差距;在军事上,德国继续受到一体化组织约束;加上统一带来的内部问题成堆,因此所谓德国实力大增并不是现实存在,而主要是人们感觉中的问题(注:Eckhard Luebkemeier,InterdependenzundKonfliktmanagement.Deutsche Aussenpolitik am Beginn des 21.Jahrhunderts,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AbteilungAussenpolitikforschung,Bonn 1998,S.13.)。
事实上,统一以后的德国是变得强大了。德国不再是东西方对峙时期的前线国家,从而减少了其地位的脆弱性;它也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外界提供的军事保护;“2+4条约”的签订使对德国主权最后的限制也一劳永逸地消除了。
统一德国的领土和人口大大扩展和增加。1995年欧盟15国的总人口为371000000,其中德国人口为81000000,占22 %(法国和英国人口分别为58000000,各占约16%);在欧盟15国领土总面积中,德国占11%(法国占近17%,英国为7.5%)。在军事上,法国与英国是核大国, 德国不是。然而冷战结束以后,在“硬”实力资源的3大要素中, 军事力量的意义趋于下降,经济与技术实力的地位在上升,作为无核但却是经济大国的德国从中受益匪浅。在经济方面,早在1990年德国统一以前,联邦德国就是欧共体中最强大的国家。1995年,在欧盟12万亿马克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德国所占份额为28.6%,法国为18.4%,英国仅为13%。1995年,在世界出口总额中,德国占10.1%,法国是5.7%, 英国为4.8%。德国还是欧盟的最大出资国,在欧盟财政总预算中, 德国所占份额将近30%。在世界储备货币中,德国马克占15%,位于美元(57%)之后, 居于英镑和法郎之前(注:
EckhardLuebkemeier,Interdependenzund Konfliktmanagement. Deutsche Aussenpolitikam Beginn des 21.S.17—18.)。
德国统一已经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对比。失去平衡的力量对比结构使人们的历史疑虑与恐惧再次泛起。无论这些感知是否合理与现实,重新生活在统一国家之中的德国人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并对此作出回答。目前,这种尝试已不乏其人。譬如,有人认为:两大因素,即德国内政民主化和外交政策一体化及其可靠性促成了德国统一的实现,它们还将决定强大起来的统一德国在21世纪不会重蹈武力扩张、争霸世界的覆辙(注:Eckhard Luebkemeier,
InterdependenzundKonfliktmanagement.Deutsche Aussenpolitik am Beginn des 21.S.16,22.)。
历史学家重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以及掩藏在一系列历史事件表象下面的深层结构。二战以后,德国没有中断过对本国历史连续性的反思和探讨。1945年是德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但不是“零点”,德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注:Bernd Faulenbach,Ueberwindungdes "deutschen Sonderweges"?
- Zur politischen Kultur derDeutschen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 in: Aus Politik undZeitgeschichte,B51/98,S.13.)。然而,希特勒政权对内专制独裁、对外侵略扩张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德国必须走上民主与和平的道路,这是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此外,1945年德国的处境与1918年时根本不同,不仅军事上彻底战败,而且完全丧失了一个国家应有的政治主权,必须受制和听命于四大战胜国的安排。 德国分为东西两国, 自1949年以后分别进入“美国化”(=西方化)和“苏联化”的历史发展新时期。
由于德国统一是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按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完成的,因此,对民主化与一体化这两个过程的探讨主要限于统一以前的联邦德国。它的民主化是西方式的民主化,它的一体化是加入西方阵营的一体化。从德国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来考察,西方化(包括价值认同、政治制度取向、战略结盟关系等各方面)是对“德意志特殊道路”历史传统的背离,它在二战以后西德的发展获得了成功。德国重新统一没有根本动摇迄今为止实行的西方式代议民主制度,统一德国依旧是欧盟、北约等西方一体化组织的可靠成员。然而,这种定势与取向能在21世纪继续下去吗?近几年出现的有关德国“内部统一”、“正常化民族利益”等问题沸沸扬扬的争论说明:统一德国西方一体化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和理所当然的事情。
统一德国在21世纪的发展有很多未可知因素。分析西德1949年以后内政与外交40多年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脉络,对统一德国在21世纪外交政策的连续性问题,笔者以为可以作较为乐观的估计,原因有三:首先,在对外关系上继续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已成为统一德国的普遍共识;第二,经过40年的发展,西德社会已经演变成一个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立的市民社会。这是德国代议民主制度稳定性与可靠性的根本保证,也是统一德国西方一体化外交政策连续性的一个重要保证;第三,新联邦州(指统一以前的民主德国地区)居民中普遍存在的不满和对立情绪已经受到重视,德国正在加大力度克服和解决统一以后出现的新困难和新问题。
一
人们对统一德国未来走向的担心是由统一德国的强大实力引发的,德国统一毕竟从根本上打破了欧洲大陆几十年保持的力量均势。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然而,另一方面也应看到:1990年实现的德国统一既非是“旧日回归”又非是“全新开始”(注:Gottfried Niedhart,
Deutsche Aussenpolitik: Vom Teilstaat mit
begrenzterSouveraenitaet zum postmodernen Nationalstaat,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1-2/97,S.16.)。所谓非旧日回归,是指重新建立的主权独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已不再是1871年至1945年间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种“后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其根本特征是它已放弃或失去了自主行动的能力而要受国际机制和欧洲超国家机构的制约,是在一个国际网络中行动(注:Gottfried Niedhart, Deutsche Aussenpolitik: Vom Teilstaatmit
begrenzter
Souveraenitaet zum postmodernen Nationalstaat,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1-2/97,S.16.)。德国历史学教授尼德哈特认为:在欧洲大国圈子中,德国所体现的“后现代民族国家”形式最为发达。所谓非全新开始,是指历史地看,几十年的东西方冲突曾经历过冷战、缓和、再冷战、再缓和等各种不同阶段,西德的国际行动能力和空间也是逐渐增强和扩大的。统一德国并非突然地进入了一个自由真空境界而必须对自己的国际作用和利益进行全新解释,它依然是欧盟和北约等一系列国际和地区组织成员国。国际局势变化导致了德国统一,同时又向统一德国提出了新任务。承担新任务,迎接新挑战,不是重建主权独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结果,而是国际局势演变的结果。因此, 谈不上什么统一德国的全新利益或全新作用(注: Gottfried
Niedhart, Deutsche Aussenpolitik: Vom Teilstaat
mit begrenzter Souveraenitaet zum postmodernen Nationalstaat,S.22.)。
对德国统一的这种认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国际条件变化但德国外交政策依旧可以保持连续性的问题。另外,早在80年代就已产生的一种对国际关系结构的新看法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注: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New York 1986.)。据此, 国际体系分为两个世界,即:“贸易世界”和“领土世界”,以及相应的两种国家“贸易国家”和“权力国家”(注: Gunther
Hellmann:
Jenseits von "Normalisierung" und "Militarsierung": Zur Standortdebatte ueberdie neue deutsche Aussenpolitik",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1-2/97,S.26.)。西德由于它的经济潜力、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和它所处的敏感地位等因素,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贸易国家。它的行为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权力国家,它更重视多边而不是单边行动,它更易于在必要时将国家主权转让给一个超国家机构, 并在追求实现自身利益时放弃使用武力(注:Gunther Hellmann:
Jenseits von "Normalisierung"und"Militarsierung":Zur Standortdebatte ueberdie neue deutsche Aussenpolitik",S.26.)。
显然,“后现代化民族国家”、“贸易国家”这些概念已经昭示出国际关系中一种深层次的、且会持之以恒的结构上的变化。用它们解释二战以后西德的变化则意味着:它已经摒弃威廉主义或纳粹主义的“军事国家”道路,转而发展了一种奉行国际多边联系原则的“贸易国家”模式。这些看法是否有溢美之嫌,这里姑且不论。现实地看,在对外关系上,继续坚持西方一体化原则和多边主义政策,已是统一德国的普遍共识,这在90年代广泛展开的对德国新外交政策的辩论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除去大众媒体的公开讨论以外,以两种类型4 组人员构成的精英讨论最值得关注。两种类型是指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4 组人员为学者和政治咨询者(属第一类)以及执政党和反对党(属第二类)。他们在德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不同,关注的问题和提供答案的角度也不同。
理论工作者关心的是如何描述目前实施的外交政策,它与过去本国或其他国家的政策相比有哪些异同,如何解释这些异同,它们未来的发展前景等等根本性问题。他们创造概念,决定论证模式,对外交决策影响很大,然而却不直接(注: Gunther Hellmann: Jenseits
von "Normalisierung" und "Militarsierung": Zur Standortdebatte ueberdie neue deutsche Aussenpolitik",S.25.)。 政治咨询者之所以归于理论工作者,是因为他们并不亲自参与外交决策。他们关注的问题比学者更接近实际,譬如:制订外交政策的内、外条件,它们以何种方式(促进、阻碍)影响外交行动,在这种背景下应该和能够采取的外交步骤都有哪些,等等(注:Gunther Hellmann: Jenseits
von "Normalisierung" und "Militarsierung": Zur
Standortdebatte ueberdie neue deutsche Aussenpolitik",S.27.)。
执政党负责制订和实施外交政策,地位最突出。所以,他们必须注意满足两个要求:合法性和可行性。也就是说,他们今天发表的外交政策言论既要为明天的决策作准备,要对过去做法的延续或变更进行辩解,同时又要兼顾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条件。学者和政治咨询者可以对外交行动方案作出“二者必居其一”的明确选择,执政党却必须从本国所处环境的实际条件出发,协调各方利益,作出全方位多含义的“既要又要”决策。反对党尽管没有直接面临现实决策的压力,但也要为他们上台执政作准备。有鉴于此,他们一方面必须显示自己的高明之处以提高上台执政或参与执政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自己执掌权柄以后要作哪些事情,这是他们在批评政府时必须注意的。
上述4组人员在地位、角色,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角度、 对外交决策与实施的贡献等方面差异颇多,但他们对统一德国新外交政策取向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坚持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继续在现有一体化机构特别是欧盟与北约中发挥作用。
学者们大部积极评价西方一体化政策,认为西德外交政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历届联邦政府都义无反顾地背离了带来历史劫难的“德意志特殊道路”。他们提出的把国家分为两种国家(权力国家和贸易国家)以及德国已成为一个贸易国家的看法,如若被普遍接受,那么,德国今后外交政策的多边主义定势和走向就确定无疑了(注:
Gunther Hellmann:Jenseits von "Normalisierung" und "Militarsierung" :Zur Standortdebatte ueberdie neue deutsche Aussenpolitik",S.25—26.)。
在政治咨询者中,根据他们为外交政策提供的总体选择方案,又可分为务实多边主义者、一体化主义者、欧洲怀疑派、国际主义者和正常化民族主义者5个流派。第一流派认为:尽管国际、 欧洲和德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德国外交政策却没有随之改变的必要;多边主义仍然是德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原则(注:Gunther
Hellmann: Jenseitsvon "Normalisierung" und "Militarsierung":Zur Standortdebatteueberdie neue deutsche Aussenpolitik",S.27.)。第二和第三流派的代表也同样认为德国外交政策必须坚持多边主义原则,但在诸多国际机构中,他们更重视欧盟的发展,把欧盟的深化与扩大问题置于德国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一体化主义者主张优先深化,以利于欧盟平等、相互的监督网络发展和应付全球化挑战;欧洲怀疑派则强调冷战结束以后“国家的世界”重返欧洲的事实,认为欧盟深化不切实际,还是应以稳定中、 东欧国家局势为重, 致力于欧盟和北约的扩大(注:GuntherHellmann:Jenseits von "Normalisierung" und "Militarsierung":Zur Standortdebatte ueberdie neue deutsche Aussenpolitik", S.28.)。 国际主义者无论是在理论分析还是在实际政策建议中都完全摆脱了权力政治思维模式的影响。他们从全球化角度出发,反对再传统地谈论民族利益问题,指出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遏制战争和饥饿等重大问题已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解决;德国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与地区性和全球性组织交织在一起的贸易国家利益,它推行的已不是“国家外交政策”而是“世界内部政策”了(注:Gunther Hellmann:Jenseits von "Normalisierung" und
"Militarsierung":ZurStandortdebatte ueberdie neue deutsche Aussenpolitik",S.28.)。正常化民族主义者属于新右派,他们强调要更新“德意志自我意识”,反对美化“西方一体化”从而使由地缘政治法则决定的德国特殊利益淹没在欧洲多民族的集合体中,等等。然而,这些主张不是主流,即使是在右派阵营中,也有人指出欧盟一体化体系平衡的重要性(注:Gunther Hellmann: Jenseits von
"Normalisierung" und"Militarsierung":Zur Standortdebatte ueberdie neue deutscheAussenpolitik",S.29.)。
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科尔政府,还是施罗德政府,无论是基督教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和联盟90/绿党,在德国外交政策上具有广泛的一致性。这就是:继续立足于西方联盟,致力于欧盟一体化建设,维护同美国的传统结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同俄国和中、东欧国家的紧密合作关系。联盟90/绿党曾在1996年就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联邦国防军参加北约军事行动、美国在欧洲安全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注:Gunther
Hellmann:Jenseits von "Normalisierung" und "Militarsierung":Zur Standortdebatte ueberdie neue deutsche Aussenpolitik",S.32.)。对此,绿党领导人之一、 现任德国联邦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1996年6月8日在“法兰克福日报”上明确指出:欧洲安全没有美国存在是不能加以保障的(注:Frankfurter Rundschau,8.Juni 1996,S.14.)。1998年10月16日,他同新任联邦政府总理施罗德一样坚定表示:德国国防军参与北约行动是必要的。
对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欧洲国家既不能无视它在重建欧洲秩序中的主导作用,又不愿容忍它重新坐大欧洲。这种矛盾心理迫使德国外交政策必须继续注意在国际多边机制中自我约束,以避免历史导致的恐德症蔓延;同时又不放弃参与承担领导责任。关键问题在于:德国大国作用的发挥,不是独断专行而是多边主义的,是在“与伙伴国家联合在一起”的一体化机制框架之内(注:参见Gottfried Niedhart, Dautsche Aussenpolitik:Vom Teilstaat mit begrenzter Souveraenitaet zumpostmodernen Nationalstaat,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1-2/97,S.22.)。
二
1949年以后西德阿登纳政府奉行的西方一体化外交政策是对“德意志特殊道路”历史传统的背离。那么,此前的希特勒德国灾难是怎么来的?它与1871年首次实现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有何联系?换言之,什么是决定19世纪德国历史发展的因素?它们是否为后来纳粹主义发展开辟和扫清了道路?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把1933年希特勒上台视为德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呢?这些是深深触痛德国人心灵创伤的问题。
如何对待本国历史,是否敢于正视本国不光彩的历史,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民族自信心和对人类负责的态度。德国人没有回避他们的历史问题。1978年,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尼培戴(Thomas Nipperdey)在“历史杂志”上发表了题为“1933年与德国历史连续性”的论文(注:Thomas Nipperdey, 1933
und die Kontinuitaet der
deutschenGeschichte,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227(1978),S.87 und S.105.),公开提出了上述敏感问题。在世纪之交的90年代, 德国又在大规模地反思历史(注:参见Dirk Blasius,Von Bismarck zu Hitler- Kontinuitaet und Kontinuitaetsbegehren in der deutschenGeschichte,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ete,B51/98,S.5.):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在这两段历史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连续性。显然,重新生活在统一之中的20世纪末的德国人已经有足够的自信心面对自己历史中那沉重的篇章。事实上,目前还鲜为人知的是:早在惨烈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德国历史学家们就在思考这一问题了。
当然,1945年不是德国人反思历史的恰时佳境。对于主要经历是在俾斯麦帝国度过的那一代德国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把“第三帝国”与俾斯麦时代联系起来。西格弗里德A·凯勒(Siegfried A.Kaehler:1885-1963)就是不愿把纳粹历史包括在德国历史之中的当时流行思潮的典型代表(注:参见Dirk Blasius,Von Bismarck zu Hitler- Kontinuitaet und Kontinuitaetsbegehren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S.3—4.)。另一位历史学家盖尔哈德·里特(Gerhard Ritter:1888-1967)在1946年7月8日一封信中指出: “权力”不能等同于“暴力”,普鲁士德国的“实力政策”与纳粹德国的“暴力政策”不可同日而语(注:Dirk Blasius,Von Bismarck zu Hitler- Kontinuitaet und Kontinuitaetsbegehren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S.4.)。
然而,敢于正视1933年纳粹历史的亦有人在。譬如,早在俾斯麦帝国时期就已是德国历史学泰斗的弗里德里希·麦乃克( 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于1946 年出版了他撰写的《德国灾难——观察与回忆》一书。他在此书中认真探讨了导致第三帝国灾难的深层原因,大胆提出德国灾难(指一战和二战)是否一开始就已孕育在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之中这一敏感问题。在深刻总结了德国以往几百年的历史经验以后,他尖锐地提出“德国市民社会的蜕化过程”这一命题:德国市民社会的蜕化过程是德国历史连续性的核心问题;它不是在希特勒纳粹党上台之时发生的,而是早在此前百多年的历史中就已出现了;德国市民社会的蜕化为后来纳粹主义的产生准备了社会温床(注:转引 Dirk Blasius, Von Bismarck zu Hitler- Kontinuitaet und Kontinuitaetsbegehren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ete,B51/98,S.4-5."Entartung" (蜕化)是纳粹分子常用语汇。麦乃克教授故意用此说法,以引起世人对德国历史不幸发展趋势的注意。)。
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是反自由主义、反议会主义和反对民主改革的;德国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不幸的蜕变,由原来反对国家权威转而与国家权威结盟,由原来自由、普世的价值取向转而鼓吹德意志民族的伟大与独特,从而走向极端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相联系的还有反犹主义和军国主义(注:“在19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西方社会没有任何国家象德意志帝国那样,军国主义如此之深地渗入国家的集体精神之中、认同感之中、民族主义之中”,同上,第5页。)。总之, 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中,市民社会不可能得到发展。因为,普鲁士德国决不允许社会凌驾于国家权威之上(注: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详见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59—74页。); 军队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政治斗争的原则化和意识形态化阻碍了民主的政治文化及其本质妥协的生成;德国传统文化的内向性和非政治性也使调解冲突的机制和习惯的成形困难重重,
等等(注:参见BerndFaulenbach, Ueberwindung des"deutschen Sonderweges"?
- Zurpolitischen Kultur der Deutschen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51/98,S.14.)。 由此可见,把纳粹统治和俾斯麦帝国联在一起的历史连续性最突出地反映在政治文化领域。
当然,不能忽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历史上还有一个魏玛共和国,其宪法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是最民主和进步的宪法之一。然而魏玛共和国没能阻止希特勒的上台!德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失败的原因可以从国际和国内、政治与经济等各个方面及不同领域去探寻,这里只想借用联邦德国前国防部长佛尔克·吕尔(Volker Ruehe)的一句话:“魏玛共和国空有民主制,而没有足够的民主主义者”(注:转引自艾伦·沃森( Alan Watson ):《德国人——他们现在是谁? 》( The Germans Who Are Now?),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北京1997 年,第208页。), 以说明:魏玛共和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但1949年成立的:“波恩共和国”情况根本不同。
二战以后西德的西方式民主化改造获得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注:详见连玉如论文:“浅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治体制特点”,载于顾俊礼、刘立群主编:《世纪之交的德国、欧盟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200页。)。有研究表明:西德1949年重新建立的议会民主制度用了大约20年时间才得到本国公民较为牢靠的承认(注:参见Werner Weidenfeld/Karl-Rudolf Korte (Hrsg.),Handbuch zur deutschenEinheit, Bonn1993,S.373.),西德市民社会及其政治文化的发展也是在这时才得到了巩固(注:参见Bernd
Faulenbach,Ueberwindungdes
"deutschen Sonderweges"? -Zur politischen Kultur der Deutschen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51/98,S.15.),联邦德国由此获得了 “第二次新生”(注:Bernd Faulenbach,Ueberwindung des "deutschen
Sonderweges"? - Zur politischen Kultur der Deutschen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S.14.)。
诚然,在二战结束、东西方冷战开始的历史新时期,西德的西化或曰美国化的发展取向已呈历史必然性。然而,大势所趋并非就会自成其就。在50年代,西德距离一个市民社会的发展目标还很遥远:反西方、反民主的潮流仍然很有市场,崇拜国家权威的臣民意识仍然十分普遍,并影响着政党与社会团体的内部建设。然而,这一时期西德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以及各种各样的科学与文化交流已经开始;新的价值取向,特别是美国文化对西德年轻一代的诱惑力,西方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思想对德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冲击大大加强;利益多元主义与社会多样化的现实正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市民社会开始发展起来。
在60年代,西德政党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民主党从一个工人党转变为一个全民党,克服了50年代西德政党格局的“不对等局面”,形成了朝野两党旗鼓相当的二元制均衡状态(注:参见连玉如论文:“浅论德志联邦共和国政治体制特点”,第181—188页。)。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1968年有关“紧急状态法”的争论以及60年代后半期兴起的遍及全国的大学生运动,大大增强了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民主化”的呼声日益高涨。1969年上台执政的勃兰特政府顺应了这一潮流,宣布要施行更多民主。 西德的市民社会发展开始得到巩固(注: Bernd Faulenbach,Ueberwindung des "deutschen Sonderweges"?
- Zur politischen Kultur der Deutschen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S.15.)。
在70年代,一方面,东西方缓和潮流和勃兰特政府“新东方政策”的实施加强了西德与东方特别是与东德的交往,同民主德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从此成为西德政治文化的重要因素,并进而促进了联邦德国的自我肯定与承认;“临时国家”观念随之削弱,人们开始在首都波恩大兴土木。另一方面,西德的新社会运动,特别是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和平运动兴盛起来;各地区的公民倡议、公民参与等活动方兴未艾;绿党的崛起,并于1983年首次进入联邦议院,给德国政坛吹进一股新风。至此,西德的市民社会发展可以说已经获得巩固。此后,无论是规模宏大的和平运动中出现的“德国中立主义”潜流,还是80年代普遍展开的有关“德国同一性”的讨论,都没能动摇西德社会的西化取向及其与西方世界的紧密联系(注:Bernd Faulenbach, Ueberwindung des"deutschen Sonderweges"?- Zur politischen
Kultur
derDeutschen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S.16.)。1986年, 在著名的“历史学家争论”中,被公认为“今日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指出:“联邦共和国无条件地向西方政治文化开放”,应被视为战后西德足以使那代人引以为豪的“理智伟业”; 这是对德国思维传统的背离, 是一种进步(注:参见BerndFaulenbach,Ueberwindung des "deutschen Sonderweges"?
- Zurpolitischen Kultur der Deutschen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S.16.)。在西德皈依西方的一体化进程中,其价值规范内核超出了政治与战略的考虑(注:参见Werner Weidenfeld/Karl- Rudolf Korte (Hrsg.),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Bonn 1993,S.132.)。
德国统一使“美国化”的西德与“苏联化”的东德合二为一。然而,由于西德基本法适用范围向东德地区的扩大,西德各个领域的一整套体制在东德地区的植入,加上西德人口对东德人口的巨大优势等因素,所谓合二为一,实际上是开启了一个“西化”东德的新进程,并已带来一系列难以解决的新问题。
三
德国统一,对西德人来说,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变化,但对东德人则意味着失去原来熟悉的一切,从国家宪法到个人认同感等概莫能外。这一损失是无法用德意志的共同历史、语言、文化加以补偿的。另外,东德人追求德国重新统一的根本动力是在经济上立即获得改善。然而,这一愿望没有完全实现。统一以后的严峻现实,尤其是失业问题的加剧对东德人的打击是沉重的,加之东德人在感受到轻视、陌化以后开始感怀旧日时光,甚至意欲部分恢复原来的国家境况,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一种强调不同于西德的东德人认同意识更新并发展起来。
德国“内部统一”问题已经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注:参见Werner Weidenfeld/Karl-Rudolf Korte ( Hrsg.) ,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S.372—374; Lothar Probst,Ost- West-Differenzen und das republikanische Devizit der
deutschen Einheit,S.3.)。它会动摇德国迄今为止的西方一体化取向吗?从目前情况来看,对德国完成国际法与国家法意义上的统一以后是否要致力于实现内部统一的问题,各方面看法不同。譬如,来自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呼声就对把“内部统一”作为统一进程的一个目标提出了质疑:在一个实行多元化民主和联邦制结构、并把其主权转让给国际多边组织的国家与社会,有什么必要非得寻求精神一体化、政治文明同质化以及千人一面的集体认同感?!在统一德国中的东西德人之间出现分歧与不和,从根本上说是法制国家的正常现象,毋需大惊小怪;如果人们普遍接受了统一进程中机制化的稳固性、政治和社会分歧的必然性、利益多元主义的合法性、自由法制国家运行规则的有效性,那么,再鼓吹什么“内部统一”就是多余甚至是有害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错误地追求“统一”,而在于在宪法秩序框架中适当地促进利益多元化的发展(注:参见Werner Weidenfeld/Karl-Rudolf Korte (Hrsg.),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S.3.)。
当然,重视德国“内部统一”问题并对其探根寻源者大有人在。为什么东德人对民主机制及其代表的评价不佳或仅仅将其视为一种形式民主而加以拒绝?曾经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烙印不可能在德国统一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就完全消除,即使西德人也是花了几十年功夫才从内心深处认同并接受了民主制度及其运行规则(注:Pollack/Pickel,Die ostdeutsche Identitaet- Erbe desDDR-Sozialismus oder Produkt der Wiedervereinigung?
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ichte,B41-42/98,S.9.)。 那种把“责任”基本推给东德人的观点在1998年末德国政界与学术界盛行的诸多论述中已经受到有力批评。譬如两位中年社会学家就联名撰文指出:德国统一已近10年,目前东德人的政治态度,很难再主要归因于原东德体制的影响,而主要是统一以后的新经历使然。进而言之,统一给东德人带来的直接后果以及对这些后果的主观感受才是决定他们目前政治态度的根本原因(注:Pollack/Pickel,Die ostdeutsche Identitaet-Erbe des DDR-Sozialismus oder Produkt der Wiedervereinigung? S.47.)。
人们的争论并未止于对事物简单因果关系的分析。在迈向历史新纪无之际,围绕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及其断裂问题(注:参见Dirk Blasius,
VonBismarckzu Hitler-Kontinuitaet und Kontinuitaetsbegehren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ete,B51/98,S.3—10.),人们正在政治文化的深层领域辨析德国政治文化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发展问题(注:参见
Bernd
Faulenbach, Ueberwindung
des
"deutschen Sonderweges"? -Zur politischen Kultur der Deutschen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51 /98,S.11—12.)。在这方面, 人们既深入探讨有关“自由的”与“社会的”价值取向及其相互关系(注:参见 Carsten Zelle,Soziale und liberale Wertorientierungen: Versuch einersituativen Erklaerung der Unterschiede zwischen Ost-und
Westdeutschen,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41-42/98,S.24 ff.), 又在实际政策领域更加关注东德地区的发展及其利益。1998年9月27 日德国联邦议院大选以后成立的红绿新联合政府已把解决东德人特别重视的失业问题放在首要位置。与此同时,德国还对中、东欧地区发展以及全欧工程建设给予高度重视,指出:这一既包括西欧又包括东欧的全欧工程,在坚持市民社会理念(如坚持人的基本权利、分权、法制与社会国家原则)西方化取向的同时,还要鼓励和促进不同民族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注:参见Bernd Faulenbach,Ueberwindung des"deutschenSonderweges"? -Zur politischen Kultur der Deutschen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S.23.)。
总之,“波恩共和国”40年来的西方式民主化改造和对外关系中的西方一体化政策已经形成一种稳定结构。独立的市民社会的形成是德国代议制民主政体在21世纪继续稳定发展的社会基础;德国东、西两个部分的“内部统一”问题虽然严重,但已受到高度重视,并正在加大解决问题的力度;在对外关系上继续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已是统一德国朝野的普遍共识。有鉴于此,可以较为肯定地说:21世纪的“柏林共和国”将继续立足于西方联盟而不会重蹈“德意志特殊道路”的覆辙,“柏林共和国”在21世纪的大国作用不会游移不定、不可捉摸,而是有国际制约和可以预测的。
对1998年成立的德国红绿新联合政府外交政策的连续性,细心的外交政策观察家不会没有注意到:尽管德国新任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在1998年10月27日宣誓就职前后一再强调坚持德国原有外交政策的必要性,但与此同时他又在11月初德国联邦议院发表的外交政策讲话中提出人权和环保这两个外交政策新重点(注:参见1998年11月10日菲舍尔在德国第14届联邦议院第3次全体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难道菲舍尔要像美国前总统卡特那样大搞人权外交吗?
从菲舍尔就任德国外交部长不长时间的总体言行来看,他是一个坚持德国外交政策既定方针、政策的务实政治家。他重视和强调德国外交政策的可信性、多边性与自我约束,说明他已抓住了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根本问题。另外,他还表现出对欧洲历史的责任感,这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战后一代新人来说是很难得的。在具体外交政策实践中,菲舍尔注意坚持与盟国协调行动。譬如1999年3月, 在欧盟因其委员会引咎集体辞职而陷入危机时,德国与法国紧密合作、协调行动,使危机得以化解;德法合作还促使3月26 日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就2000年议程达成最后协议。
与曾任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达18年之久的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相比,现任德国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只能算是个小字辈。这不仅是指他的年龄,而主要是指他在外交政策上全无经验。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外交新手,上台伊始就要在国际政治大舞台上立即承担和扮演重要角色(如德国在1999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并要在6 月份主持召开八国集团年度首脑会议,等等),自然引人注目。当然,人们更为关注的还是统一德国21世纪外交政策发展的内容,它的连续性问题。
收稿日期:1999-0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