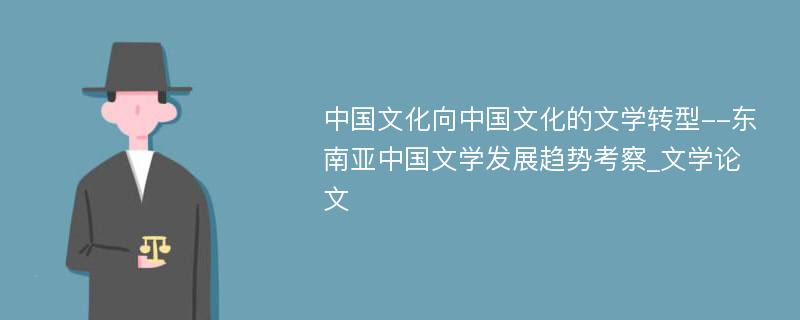
从华族文化到华人文化的文学转换——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趋势的一种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族论文,文化论文,东南亚论文,文学论文,发展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面向21世纪的世界华人文化”的背景上,东南亚华文文学正经历着从较为单一地固守中华文化传统,体现着较为纯然的汉族思维方式,较多地带有移民群体意识的华族文化到扎根于中华“本源文化”和居住国乡土,较多地融入了海外华人群体现代思维成果的华人文化的转换,从而在建立东南亚各国华人文化传统上显示出其独特的建构和凝聚力量。
我并不痴醉于某些外国学者所断言的“21世纪将是华人文化的世纪”的美好前景,但我认为,“面向21世纪的华人文化”肯定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华人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全球华人文化沟通交流、合作发展的前景等问题的探讨,会有益于华人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性作用的发挥。对于愈来愈带有全球性的华文文学来说,也只有在“面向21世纪的华人文化”的背景上才能更清楚地呈现出其独特的凝聚力量,同时,华文文学也会由此更好地把握自身的发展趋势。本文就拟在这样的研究视角上来展开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希望和危机所在的一点探讨。
在目前由中国大陆、中国台港澳地区、东南亚、欧美洲等地的华文文学组成的全球华文文学创作格局中,东南亚华文文学明显是个热点。这一地区的华文文学历史悠久,发展又不平衡,存在着许多时空上的差异现象。就现状而言,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作为居住国华人社会的文学,已成为或正在成为所在国国家文学的重要部分。泰国的华文文学,较多地融入泰国的当地社会。菲律宾的华文文学,在经历了70年代的沉寂和80年代末期的低潮后,正以文艺复兴表明着其再出发。但种种差异,反而有利于我们较为深入地将东南亚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其艰难的跋涉、蓬勃的生机和困惑的选择,都映现出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中华族文化如何演变为华人文化的诸多层面。
我这里提出华族文化和华人文化这两个有所不同的概念,正是基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的一种整体趋势。我所言的华族文化和华人文化虽都以中华文华为核心,但前者较为单一地固守中华文化传统,体现着较为纯然的汉族思维方式,较多地带有移民群体的文化色彩;而后者已比较明显地建立了居住国本土华人文化的传统和较多融入了海外华人群体现代思维的成果,是一种既扎根于中华“本源文化”又扎根于居住国乡土的华人文化。东南亚华文文学一开始便是在中国新文学影响下诞生的,并被视为中国新文学的支流,当初的报刊甚至有剪报制度(即从中国报纸杂志剪下文章刊载)。30年代后,建立居住国本土文学的课题开始被提出,而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几成绝响的艰难生存过程中日益深化着建立融合“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这样一种双重文学传统的认识。今天,文学作为最富有群体魅力和个性色彩的思维和语言形式,在建立东南亚各国华人文化的传统上显示出独特的建构力量。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勃兴首先联系着各国华人作家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集中表现为对中华文化在居住国命运的关注,而其具体内容正经历着从忧虑“传统的丢掉”到关注“传统的失落”的深化。东南亚不少华文作家的创作原先都强烈关注华语华教的兴衰,显然出自于“没有华文教育,便没有中华文化”的忧患意识。在马华文坛,甚至有着这样的共识:“文学是经国的大业……文学的力量足见左右教育的现状,这样,通过马华文学来提高华人对教育的重视,从而发展华文教育自是正确的途径”,“马华文学与华文教育息息相关,运用马华文学助长华文教育的发展是对症下药”[①]。因此,许多作家的创作笔涉华文教育式微的现状。新加坡张挥轰动一时的小说《45·45会议机密》便是在巧妙地动用三组富有讽喻性的数字中,通过某中学校长将英文会考成绩下降归罪于5名变流(即华文教育出身,后学英语者)的数理教员,并以成倍增加其工作量的办法迫使其自动申请转校的情节,写出了一代受华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希尔尼的小说《变迁》更是以刘氏三代的三则讣告在语言文种、格式上的变化,构成了一种令人悟到华文式微而引起家庭伦理变迁的震撼力。
东南亚华人作家笔下“传统的丢掉”主要是指由于居住国政治、教育等因素作为种种外力的压迫而导致华族传统的毁灭。那么,在政治压迫因素逐步化解、华语教育有所兴盛的情况下,中华文化传统是否就可以自然而然得到保存了呢?答案并非肯定。一些作家敏锐地捕捉到华族自身素质而导致的“传统的失落”。这里很值得介绍一下希尼尔、谢裕民这一对亲哥俩的微型小说创作。出生于50年代末的这两位青年作家,作为新加坡的“末代华校生”而情钟于中华传统文化,使人甚至会对一代海外华人有新的认识。他们各自在极短篇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和《世说新语》中,分别用60篇和53篇小说,构筑了一个源自新加坡乡土,而又浸润着中华文化情愫的小说世界,其中对“传统的失落”的开掘显得深刻。谢裕民《遗嘱》中的爸爸竟然视儿孙用汉语拼音将王拼成Wang为“篡改祖姓”的“大逆不道”,而将其“逐出家门”,其缘由就是因为“福建人姓王拼写成Ong是我们这里的特色,人家一听,就知道你是福建人,Heng的话是潮州人,Wong是广东人,Wee是海南人。你这样Wang、Wang叫的,是什么人?”近于荒诞的情节表达着作者的感慨:“怎样才算源头?”狭隘的地域、籍贯观念会使民族文化之源干涸枯竭。在希尔尼的《舅公呀呸》中,要毁灭华人传统的则是另一类华人。视《华人传统》画册为“不良读物”而予没收的那两位华人教员已彻底“洋化”,陷入了一种无传统的精神困境。在希尼尔、谢裕民的众多小说中举出以上两篇是具有代表性的,它们实际上揭示了导致“传统失落”的两个文化误区。东南亚华人的籍贯以福建、广东居多,华人社区维系华族文化血脉的活动也以借助宗亲、同乡会馆的力量为主,闽南、客家等文化影响深远。而海外华族要在异域他乡传承中华文化的薪火,似不宜将地域、籍贯文化凝固化,甚至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狭隘为地域籍贯文化。同时,在东南亚华人社会急速都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心安理得于被连根拔起的痛苦,心甘情愿于“西化”而失却中华思想文化的内核,会更可悲地陷入无根无源的精神困境。这两种由于华族自身素质而导致的“传统失落”在两位青年作家笔下得到揭示,确实反映出华人作家忧患意识的深化。
这种忧患意识的深化联系着华人作家创作中自我审视意识的确立和强化。过去,作为中国大陆的研究者,我曾觉得自己同海外华人作家审视海外华文文学危机的层面有所不同。海外华文文学的危机不仅在于华文华教的一度式微和商品消费社会中文学消费而产生的矛盾冲突,恐怕也在于作家自身素质的诸多方面。海外华人作家对文学的热情令人感动,华文作家云集的新加坡,仅英培安一个职业作家(他是执意在困苦中趟出一条新加坡华人社会职业作家的路子),也可窥见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华文作家卖文为生艰难但仍执着于文学追求的热情。但是,海外华文文学兴盛成熟的重要标志,在于各国华人社会的华文文学,形成了真正属于自己国家华人社会的特色,而不是以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文学为正宗。就东南亚华文文学而言,我的感觉是:真正属于东南亚各国华人社会的东西还不多,这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恐怕不能回避作家本身的素质问题。中国大陆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有近10年的历史,但我觉得双方之间似乎还未取得一种平等对话的地位,其中一个方面便是中国大陆研究界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上述问题而出于一种“等待”心理保持沉默。而现在,我们看到东南亚一些华文作家已经用文学的精神追求的目光审视自己,这种审视的结果,会使作家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更执着地将文学作为人生事业,作为内在精神追求来对待,从而写出更多真正意义上的属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作品,使其成为成熟的东南亚华人文化的重要基石。
季羡林先生在为著名的新加坡艺术家陈瑞献先生的文集作序时,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角度分析“陈瑞献现象”说:“新加坡,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东西文化的冲撞中,正处在两方面的前沿阵地上。换句话说,新加坡是东西文化交光互影最显著最剧烈的地方”,“陈瑞献正是在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激荡冲撞中产生出来的人物”。整个东南亚地区都相对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较为剧烈之处。而这中间,孕育蓬蓬生机,也潜伏失落危机。东南亚华文作家面向21世纪的自我审视正主要表现为对这一问题的日益清醒的把握,这也成为构建东南亚华文文学、华人文化自身传统的重要方面。
我们接触到海外华文文学时,总觉得其价值在于它在传统的汉学思维模式的文学以外,提供了一种在多元文化思维环境中产生的文学。东南亚一些国家由于其多元文化结构的相对均衡、稳定性,各种文化并存、交融显得相对宽容、开放,给一种根植于居住国土地,萌生于东西方文化互补中的华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东南亚华文文学正是凭借这种文化环境蓄积着自己的生命力。首先,作家们汲取东方文化的视野日益拓展,他们心目中的东方文化,不仅指中华母体文化,也开始包括印度文化的东方文明,包括居住国原住民族的文化。新加坡王润华诗作禅气所酿成的精妙艺术氛围,马来西亚诗人李敬德潜心研修佛教追求诗禅同宗的境界,他们各自的创作使人惊叹于东方佛教的生命力和震撼力。对原住民族文化的关注,有可能成为东南亚华文创作的又一股艺术源泉。大概由于泰国华人散居的环境和泰华作家“促进中泰文化的交流”的共识[②],泰华文学中独特的移民经验同泰国风土文化相融汇的色彩显得浓郁而迷人。在马来西亚,早就有不少精通马来文的华裔作家,1986年1月,成立了以推动华巫两族文学评介交流为宗旨的马来西亚翻译和创作协会,翻译出版了一些马来族作家的作品,《蕉风》等刊物也多次介绍马来语国家文学奖得主的创作。相当多的马华作家开掘起马来人的生活层面,其中包含有同马来族心灵沟通的渴求。梁放的小说将笔触直接探入伊班族人的心灵世界。洪泉的系列小说《传说》用交织写实和梦幻的笔触抒写马来人的生活,被人称为道地的马来西亚现代《聊斋》。雨川笔下呈现的则是甘榜乡镇马来人“移民大搬迁”的血肉历史。上述努力自然仅仅是开始,如果作家们能更深地理解、把握自己所处社会东方文化结构的丰富内涵,扬长避短,对于一种成熟的东南亚华人文化的出现显然是有利的,因为这种开放的东方文化观念中实际上蕴含着建立适合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文化的探索和努力。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黄孟文博士就曾说过:“在东方社会的结构中,也因地域的分隔而影响文学思潮。打个比方,中国的农村社会和新加坡的都市环境,所酝酿的文学气候肯定是两种人文科学条件的产物,我们也不能硬将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学作品格式搬过来,捧为我们的学习经典。”[③]注意到东方社会模式的不同,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本土化”,恐怕正是21世纪海外华人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而华文文学最先预示这种文化春天的萌动。
其次,以东方文化之活力济西方文化之穷,但又非简单化为中西对峙的二元模式,成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上的一种整体趋势。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曾是西方的殖民地,英文传统深广。五六十年代同中国大陆的隔绝,以台湾现代派文学为中介的西方艺术影响,都加深了欧美世界性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东南亚华文文学出现两种“背离”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创作趋势。一种是向传统回归,不仅向中华文化传统回归,也向“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某些层面回归,当然这种回归并非简单恢复一元的文化心态,而是着眼于提升新加坡华人文化的层次。王润华博士几年前曾分析新加坡华人的精神困境说:新加坡华人的失落感、彷徨感、恐惧感主要来自“自己是黄皮肤的华人,却没有中华思想文化的内涵,甚至不懂华文。新加坡华人受西文教育,却没有西方优秀文化的涵养,只学到个人主义自私的缺点”[④]的自省。为了摆脱精神困境,作家们开始探索在一个自由贸易,商品经济的社会中如何重建中华传统文化。老一辈作家的努力自不待说,使人感到充满希望的是一批几乎与新加坡同时诞生成长的青年作家也开始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谢裕民小说的前面都有一则哲理性短语,其中有的就蕴含有作者对中华伦理道德、思想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发掘。韦铜雀的小说集《人间秀气》用阴柔笔调写尽现代都市社会浮世男女的悲欢爱恨时,其伦理观、价值观也包含有对传统的认同。孙爱玲、董农政、艾禺等的小说题材、技法各异,但在描写海外华人在承受两种文化的错位而造成的身体、精神、语言等放逐之痛中,都有着希望重新强化中华“本源文化”的寻求。诚如吴作栋先生所言:“新加坡华人社会问题的关键,是最终会不会失去他们的文化认同和核心价值感”[⑤],这种文化共识正是作家们的创作心声。目前东南亚华文文坛上诗风的转换,创作使命感的重新提出,对华族移民历史兴趣的加浓,都可以视作回归传统的寻求。马来西亚著名作家小黑的《前夕》、《白水黑山》等小说集以一种爱国亲民的现实心境,来探寻、思考父辈们的人生选择,关注、同情普通百姓的历史命运,则令人感到“五·四”新文学精神的一种回归。
另一种趋势是在后现代的创作潮流中表现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叛离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如果把文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理解成企图超越现代主义的一种创作努力,那么东南亚许多华文作家的创作可以被包容进后现代的创作趋势中(自然这也联系着作者所处社会的电脑化、资讯化),同西方的后现代文学现象不同的是这种创作趋势中有着传统的影响。例如,近年来,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在东南亚文坛非常流行,陈政欣(马来西亚)的小说集《树和旅途》、张挥(新加坡)的小说集《十梦录》、梁文福(新加坡)的小说集《梁文福的21个梦》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尝试。而这些小说的共同特色是在居住国乡土的背景、氛围中,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而思想的内涵和表述方式都让人感到华族传统文化的色彩。作家们有时还尝试将现代都市大众传媒同小说文体结合在一起。如希尼尔的微型小说《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便是跟90年6月三头野象大闹德光岛的新闻报道同步创作的,在拟人式的手法中,不仅浓缩了整则新闻,并且传达出种种现实生命的、情感的讯息,表现出对现代化都市化进程的忧虑。语言文字的操作上,作家们也不象西方激进的后现代作家那样自由无度,在大胆的语言构建中表现出一种传统的艺术节制的驾驭力。
自然,上述创作趋势并未也不应冲淡、分化东南亚地区在中外文化最直接的互相渗透、影响中借鉴西方优秀文化的优势。在东南亚华文创作中,西方艺术因素仍被大量使用,但这已开始服务于建构“中西合璧”的华人文化了。此外,东南亚华文文学“双重传统”构建中还融入了各自国家作家们富有个性色彩的诸多创作因素,包括由于精通英文和其他语种而带来的对华文文学的渗透。这些都暂不展开论述了。
此外,文体的变革,文学新人的培养等,也都联系着东南亚华文文学建立“双重传统”的努力。笔者曾在《微型小说和海外华人社会》一文中论及过微型小说在海外华人社会兴盛的原因,而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在微型小说文体的创新上,广泛揉入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寓言小说和西方新小说等文体因素,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就培养文学新人而言,如果说当年鲁迅、茅盾等正是通过评介新人新作,奖掖青年作者推进了“五四”文学传统的建立,那么,今天,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界也正在着力于培养文学新人以促进本国华文文学“双重传统”的建立。亚细亚青年文学营的举办,各种青年文学奖的评选,青年文学刊物(如新加坡的《后来》的创办,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颇有创作潜力的华文青年作者。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新加坡著名诗人、学者王润华博士近年来屡屡给本国青年作者的作品集精心作序,有意识地从评介作品的具体实例中阐明新加坡华文文学“双重传统”的丰富内涵,引导青年作者探索形成本土华文文学传统的路子。
对于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华文文学,都面临着建立自身的“双重文学传统”的选择,它们之间的沟通交流互补,无疑也会丰富世界华人文化的格局。在这过程中,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要作出的努力也是艰巨的。“港台大陆的文学我们可以学,而金矿还要是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开”[⑥],有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坚持在东西交汇的文化环境中创新,东南亚华文文学将会从各自的乡土出发,走向世界。
注释:
①参阅1993年1.2月号马来西亚《蕉风》
②田流(新加坡):《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
③伍静:《再见孟毅的时候》,载新加坡1989年12月《文学半年刊》。
④王润华:《从浪子到鱼尾狮:新加坡文学中的华人困境意象》
⑤吴作栋:《1991年7月26日在新加坡报业俱乐部宴会上的讲话》
⑥马来西亚《蕉风》426期《脚踏实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