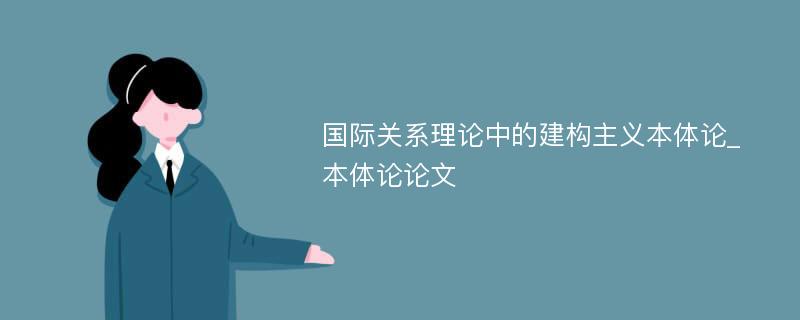
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的本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国际关系论文,理论论文,建构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异常迅速。从1963年国家决定在北大、人大、复旦三个部属高校设置国际政治系到今天,几乎每个重点高校都设有国际问题研究课程或系科。但是,从中国国际关系学一开始就缺乏自主的基础研究,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是由主流学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拿来主义所推动的。近年来,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建构主义”的文章比其发源地美国还要多。近乎全盘西化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成为一门显学,而中国外交研究则远远落在了后面。同时,这门显学采用的西方本体论、方法论和话语体系对自主的中国外交研究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从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起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的种种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由于各类理论,包括风行一时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对冷战的发展进程都做了错误的判断,国际关系理论学陷入深度危机。近年来,由温特等人所代表的建构主义独树一帜,给长期处于西化状态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打了一针强心剂,多数学者开始建构主义转向,对这个新理论推崇备至,为“西方纯理论先行”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找到了辩护的根据。不少人甚至提出,这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场“建构主义革命”,①并建议将这个理论运用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实践。
然而,指望一个理论流派拯救岌岌可危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只是一个幻想。由西方主导四个多世纪国际关系体系的根基本身已经开始动摇,时下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任何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有特殊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既然建构主义以“本体论革命”自居,我们对它的研究就不能停留在理论创新的技术层面,而不对建构主义的概念历史加以关注。我们绝不能重走20世纪80年代全盘西化的老路。建构主义的特点是寻找相互对立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间道路。用阿德勒的话讲是“占领中间地带”的一场运动。②任何概念都是有历史的,为什么建构主义采取占领中间地带的策略,为什么它迄今为止似乎能够占领中间地带,这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建构主义夺取中间地带的策略
建构主义并不是一场革命。任何调和不同学派的理论,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场改良而不是革命。建构主义据说打破了物质本体论,而以社会本体论取而代之,但它全然没有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形而上本体论的桎梏,不过为维护西方的普世价值找到了新的研究方法。
一般认为,以文化和认同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建构主义,是对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概念的现实主义和以制度、交易成本和信息为核心概念的新自由主义的有力补充。现实主义的研究主要基于政治学和历史学方法,新自由主义借鉴经济学方法,而社会建构主义主要运用的是社会学方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论战焦点主要是认识论,七十年代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的论战领域主要是方法论,八、九十年代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所谓新-新主义)的论战开始引向本体论。与新-新主义的物质本体论不同,建构主义提出了观念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它从社会学角度对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权力、利益、均势、国际无政府状态进行解读,提出了自己的“纯理论”(meta-theory)(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
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基于一套普世价值的存在,而支撑建构主义的普世价值仍然是西式民主优越论和天赋人权论,不过常常以民主和平论、国际体系论或共同体和平论的面貌出现。可以说,建构主义的西方中心论是深藏不露的,建构主义学者们的西方中心论立场早已确定,彼此心照不宣。例如,从表面上看,温特的实证主义倾向与后实证主义认识论并不相符,他对此作出了解释:
“由于我的理想主义的本体论立场,很多人以为我在认识论方面必定与后实证主义的立场相吻合,其实不然……我是相信科学的,这就使我在第三次辩论中处于中间位置,但这并不因为我想寻找一种中性的方法,而是因为理想主义的本体论并不表明要遵循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
显然,温特的理想主义的本体论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所以他明确拒斥对西方价值观发起根本挑战的后实证主义或解构主义,而采纳后现代的社会学方法去攻占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这两个长期尖锐对立的学派的中间地带。这个理论建设的策略之所以有凝聚力,原因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的价值观在本体意义上趋于一致。更重要的是建构主义学者们毫不讳言,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上,前者占主导地位。
在西方,本体论问题是普世价值问题。本体论(也称“是论”)问题就是探讨“这是什么”的终极问题,但在最后必然走进死胡同,即“上帝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不容置疑的。中国传统没有这种神学色彩本体论,所以推崇建构主义就必然要接受普世主义价值观。普世价值存在与否是个西式语境主导的伪命题,它根本无法被证明。这还不是问题的核心,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概念的历史渊源和实际作用。普世价值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狭隘的地方观念普遍应用,并号称是“永恒”的价值。在中国,所谓普世价值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外来语,它的原词是universal value。在欧洲中世纪,universalism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控制的概念,其含义是天主教政教合一的大一统世界,同“天主教”(Catholicism)是同义词,并常常互用。不难看出,在基督教新教改革以后,原本意义上的所谓普世价值即已不复存在,至少我们应当看到,普世价值是受到时间、地点限制的历史概念。
19世纪,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普世主义试图将宗教普世主义一网打尽,但历史证明,20世纪的东西方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发生的冷战仍然没有突破宗教普世主义的桎梏。冷战的双方都打出自诩为“真正”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并企图用各自的意识形态重新解释和打造世界。这个阶段的普世价值以拯救世界为己任,但带来的却是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军事对抗。冷战中苏式计划经济失败,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于是又出现了全然以西方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自由与民主的普世价值,而且据说人类历史已经不可能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所以有风靡一时的历史终结论。更有甚者,由于冷战的突然结束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很多人对西式民主是人类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个命题更加深信不疑。从本体论来看,建构主义同历史终结论相得益彰,是一种互补关系。
普世价值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天赋人权说”。西方有关中国人权的辩论总是用中国签署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作为中国已经接受普世价值的铁证。其实,中文从未将这个宣言翻译为“普世人权宣言”,而将universal译为“世界”恰恰反映了民族主权国家体系尚未消亡的事实。实际上,国际社会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应当被称为“共享价值”(commonly shared value),这是一个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过程的概念,而不是神学本体论意义的普世价值,或共同价值。
应当看到,诞生于1948年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正是当时的国际社会对惨绝人寰的纳粹集中营的即时反应。同样,奥林匹克运动固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作为人类的共享价值,不过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庆祝奥运是因为奥运精神同国际社会大多数人都赞同的和平与发展的共享价值相吻合。1936年,希特勒也特别重视柏林奥运,但他当时同世界大多数人有同一个梦想吗?因此,将奥运精神看成是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永恒的普世价值,更不能自圆其说。
毫无疑问,普世价值是西方人发明的东西,而且是基督教(包括其源头的犹太教教义)传统特有的表述方式。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文化,比如伊斯兰、犹太教或佛教,都没有致力将一种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文化的传教士精神。基督教传统不同,它以黑与白、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截然对立来解释世界。如果我们跟着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路走,不但违背了中华传统的中庸精神,而且在国际上坠入难以自拔的话语陷阱。
中国国内讨论普世价值总是存在误区,观点虽然迥异,语境却相同,至少在论辩方式上有非此即彼的西化倾向。两种观点在同一个话语陷阱之中挣扎。一种观点认为普世价值总是有的,无论从奥林匹克精神到汶川大地震中展现的人情,还是历代诗人们经久不衰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似乎都证明了普世价值的存在。另一种观点却截然相反,认为人世间绝无普世价值“那个东西”,它只是西人创造出来的政治观念,而与中国毫无干系,所以普世价值根本不值得讨论。笔者对这两种观点都不敢苟同。从概念历史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要关注任何普世价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要融入世界,我们就应当接受某些政治含义不强的普世价值,同时也可以摒弃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普世价值。这种貌似两全的思路是幼稚的,以为中国可以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而不必接受它的本体论。还有人把民主看成是一个普世的“好东西,”但在此基础上再谈“中国特色”就毫无意义。③还有一种思路认为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普世价值,比如赵汀阳认为中国和西方的两种普世价值不必融合,因为中国的天下观的胸怀更加宽广。④极力推崇建构主义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一度兴起“天下”热,以为找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基础理念。其实,既为普世,就不可能一分为二,更重要的是接受任何普世价值就必然要接受西方人的善恶二元论辩模式。这是一个用中华传统思路无法取胜的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论辩方式,比如“之辨”方式的摧毁,至今令人刻骨铭心。
普世价值绝不可一分为二,但却可以在国际关系实践中被灵活运用。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极力推崇一些的普世价值时往往采用双重标准。在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在鼓吹“自由、民主”的同时,也支撑一些反共、反苏的集权政府。美国领导人在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的同时,仍然非法拘禁在关塔那摩的塔利班战俘。
既然普世价值自诩为“永恒价值”,那么双重标准如何能够行得通?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多数核心的普世价值的评判标准都是由西方主导的,非西方世界处于劣势地位。冷战期间,任何可以被解释为推进自由民主的政策都是合理的,同样,九一一事件以后,任何可以推进反恐战争的举措都可以采用,先发制人也好,监听民众电话也好,同国家主权和基本人身自由并不发生冲突。在国际关系领域里也是如此。建构主义旨在推动全球“公共产品”,但公共产品的评判标准也是以西方为主导。
当然,对西方的普世价值不能采取不屑一顾的简单态度。在世界地位上升的历史时刻,中国应当为当代国际社会的共享价值作出积极的贡献。但是,中国只能从传统文化资源中阐发对现存的共享价值看法,既要警惕普世价值的陷阱,又要站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提出新的价值观。对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应当用自己的文化传统加以新的诠释和改造,创造新的共享价值。
建构主义受康德学派的“持久和平论”的影响很深。国际社会总是希望某些共享价值成为永恒价值,特别是有关持久和平的种种观点,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人类总是有着理想和美好的愿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也不断提出自己的一些理想,诸如大同世界、和平共处、和谐世界等。我们不必讳言永恒,但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将理想和受时间、文化和地点限制的国际关系现实混为一谈。
应当承认,普世价值观在中国还是很有市场的。无论是向传统回归,试图寻找儒家的本体论的海内外新儒家,还是继续坚持反传统的西化中学——其中包括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都在顽强地捍卫普世价值。近年在中国,建构主义开始占领一块核心阵地,中国学人从建构主义那里得到某些启示的同时,也在同这些西方学者一道固守永恒的普世价值的最后一道防线。
建构主义暗度陈仓
建构主义的成功在于创造了一个新的论辩平台,将西式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放在一个大的论辩框架(master frame)中进行讨论,所以对很多不同的学派都很有吸引力。用建构主义学者的话说,创造了“友好的论辩氛围”。但这不并是原创的思路,而是直接借鉴后现代主义对论辩方法本身的关注。建构主义并不放弃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因而能够避开后现代主义在话语权和概念历史方面发起的挑战,将各种不同的西方国际关系流派在纯理论基础上加以整合。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拒斥任何纯理论,所以建构主义还是在“现代”的框架中打转转。从这个意义上讲,建构主义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第四次辩论,暂时给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一线生机。然而,它并不是像某些人推崇的那样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集大成者,给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画上了一个功德圆满的句号。事实上,我们应当把它看作是一座拱形的桥梁,它画的只是一个半圆,在这个连接不同学派的半弧形的框架上能够允许不同的理论有发展空间(譬如国家利益论、国际体系论、体系转换论和共同体和平论等等),但它的基础仍然是不可动摇的本体论。
此外,建构主义还是将西方关系理论的核心理念向非西方国家推广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要把它上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首先需要让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界休战。因此,它夺取中间地带的策略是奏效的。从军事战略上讲,夺取中间地带是一着妙棋,中间开花最有可能完成对全部领土的征服。它的目标是捍卫民主与自由的西式本体论(即温特的理想主义的本体论),所以用后现代主义的论辩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实为暗度陈仓。
建构主义是在冷战结束,两极世界消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其推崇的权力政治因素衰亡,社会文化因素上升的理论可以说是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历史终结论的另一种,更加有力的表达方式。换句话说,建构主义是近年来用方法论捍卫本体论的一个典范。
建构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出现在中国国力东山再起的历史时刻。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再度参与已经开始改写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对这新一轮的普世价值辩论不能再掉以轻心。中国传统中从来没有本体论或称“是论”,也没有类似普世价值的概念。自诩为普世价值的理论总是要推销或强加给别人,而中国人没有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习惯。
建构主义最不喜欢的话题,正是后现代主义最关注的,特别是话语权政治和文化与种族的差异。因为建构主义在实践中的作用是将不同文化和种族纳入西方认可的“规范”,它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社会交往”(socializing)。这个从字面上看似乎是中性的概念,背后既隐含了对现存国际体制的游戏规则的辩护,也提供了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大一统的新方法。建构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交往的国际关系含义做过如下界定,“将行为者纳入既定的共同体的规范和游戏规则的过程”,毋庸置疑,行为者入围的前提必须是接受这些规范和游戏规则赖以生存的本体论。
当然,对外关系的政策运作和意识形态原则不能混为一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接受某些特定的、当下国际社会流行的共享价值,是每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使然。但这不能引导到原则上的让步甚或投降。此次在西方发生的金融危机对西方普世价值赖以生存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那种据说能够带来持久和平的市场普世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要求创建自己的国际关系学派的中国学者大多数出于对建构主义的崇敬心理,希望拿出一套对应的理论体系,但建设一个形而上理论体系的愿望本身就坠入了西式本体论的陷阱,因为中国文化的根基之深厚恰恰在于对本体论和理论体系的拒斥。在不少中国学者看来,赵汀阳的天下论似乎建立了一个连接建构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桥梁,但天下论不接受普世价值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便无法自圆其说。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建构主义在中国争夺中间地带,即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精英的努力也是颇有成效的。我们固然不能对所有的西方关系理论都一概加以排斥,但必须时时警惕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背景,不能再度陷入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的那种神学幻觉。⑥
为什么不少海外学者特别重视建构主义在中国的作用?长期用建构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外交的美国学者江忆恩说,“用中国问题专家熟悉的话说,现在是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在国际关系学中‘发挥使命’的好机会;或者,借用国际关系学类似的术语,到了中国外交政策学者成为‘思想创造者’的时候了。”⑦江忆恩的观点至少有两层含义值得关注:一是把西方主导的、以建构主义为集大成者的国际关系理论视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框架,长期游离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之外的中国外交研究被纳入这个框架的机会已经到来;二是认为中国外交研究学者必须接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才可能成为“思想创造者。”不难理解,这种思路在很多中国学者中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在不少人看来,“中国化”或“本土化”的提法本身就是因循守旧,只有建构主义才是一场真正的学理上的革命;接受和在中国推广建构主义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中国学者为国际关系理论发挥使命的绝好机会。
其实,把任何方法论和研究方法本身看成是真理是无意义的,我们必须把创建话语体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学科建设固然重要,但关键是学术评判标准,而评判标准的建立首先在于一定的学术语境。如果中国外交研究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建构主义的一个领地,其主导的话语系统必然成为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或本土化的最大障碍,中国外交的研究将会陷入“理不屈而词穷”的窘境。
当然,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必须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的政治话语体系十分混乱,尚有待认真地、艰苦地清理。特别需要我们时时警惕的是以下三方面,即以历史哲学为旗号打入中国的现代欧洲中心史观,这种史观在当代中国仍然保留一块核心阵地;以古希腊民主论为幌子的现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政治神学,对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体系曾带来摧毁性打击;还有近年来以全球化为掩护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即所谓“华盛顿共识”。
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大弊病是缺乏历史感。不少建构主义的推崇者也提出“适当采取历史谱系学的方法,”⑧但他们所说谱系学并不是后现代学者最关注的“关键词”的谱系学,即通行的基本概念的历史演化。只有对所有涉及国际关系领域的“关键词”进行概念历史的追踪,才能够达到釜底抽薪的解构效果,并建立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建构主义学者对现行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体系在本质上没有抵触,所以对关键词的历史演变不感兴趣,而是有选择地用某些史实来证明建构主义理论和方法论的历史正确性,对不符合理论建设要求的史实必然加以回避。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最惯常的研究手法,屡试不爽。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外交研究处于话语弱势反而被很多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是正常的,以为这不但提供了一个与西方“先进”理论进行接轨的机会,还有可能使中国学者成为江忆恩所说的那种“思想创造者”。经济实力与外交自主权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十分清楚的,不需要任何国际关系理论也一目了然。建构主义理论家们声称,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与国家外交自主权成反比。事实上,中国国力上升是外交自主权上升的基础,参与全球化、外交多边化正是信心上升的重要标志。
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实践严重脱离的状态已经引起很多顶尖学者的关注。哈佛大学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今年4月13日的《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并尖锐地指出,国际关系学者与外交实践毫无关系,在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进入政府之后,就再也没有顶尖学者担任政府要职。他指出,造成这个状态的原因不在政府,而在于学术界的“象牙塔的城墙越砌越高”,更糟糕的是国际关系理论成了学术水平的主要评判指标。奈引用了前国防部副部长纽萨姆的一段发人深省的话:“退缩到理论帷幕之后的学人们本来不会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但考虑到这些人是育人之人……他们对下一代人的影响就不能不令人担忧。同时,这个学科对公众和政府对国际问题与事件的感知将带来什么影响也令人堪忧”。
总而言之,在中国外交研究领域里是否会出现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学派?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在话语体系之争未见分晓之前是无意义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没有本土文化资源支撑的理论学派都是没有发展前景的。正如约瑟夫·奈所言,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越来越细,内容越来越多,实际意义却越来越少。对中国学人来讲,争取在全球治理领域里的话语权才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只有中国化才能帮助我们跳出在理论和外交实践中的“理不屈而词穷”的困境,并避免约瑟夫·奈所担心的国际关系理论误人子弟、误导政策的双重恶果。
注释:
①⑧见郭树勇《试论建构主义革命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若干意义》,《国际展望》2009年第1期。
②Adler,E.(1997),"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Constructionism in World Politic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3:319-363.
③对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英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批评,详见相蓝欣,英国《生存》杂志,2009年8月,伦敦(英文)。
④赵汀阳:《中国应比西方有更大胸怀》,《环球时报》2009年4月23日。
⑤详细分析参见William A.Callahan: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Oct,2008,pp.749-761;关于赵汀阳与笔者的公开争论,参见相蓝欣《戒言崛起,慎言和谐》,《新加坡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yl/y1060323_501.html.赵的回应参见赵汀阳《关于和谐世界的思考》,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06年第9期;相的反驳参见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三联书店,2007年,第38-40页。
⑥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参见拙作《传统与对外关系》,三联出版社,2007年。
⑦[美]江忆恩(Ian Johnston):《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
标签:本体论论文; 建构主义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