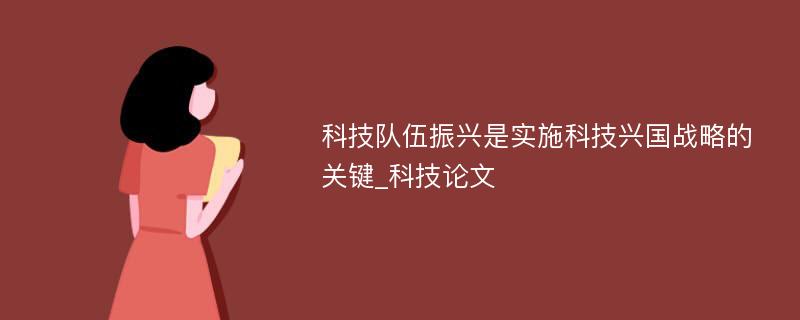
科技队伍年轻化是实施科技兴国战略的重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论文,队伍论文,重点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迈向21世纪,面对高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综合国力的竞争,我国必须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在实施科技兴国战略中,科技队伍年轻化是重点。本文拟对我国科技队伍年轻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做一探讨。
一、我国科技队伍年轻化存在的重要问题
建国以来,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已拥有一支规模较大的科技队伍。中老年科技人才,作出了很大贡献。年轻科技人才朝气蓬勃,茁壮成长,已成为生力军。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科技队伍,特别是年轻科技人才队伍方面,还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第一,我国科技队伍的年龄结构的调查,最明显、最突出的问题是年龄老化,处于科技创造最佳年龄区的人数太少,不符合大多数人处于最佳区的要求。据1987年对我国科技队伍的调查,25—44岁年龄段的总比例只占56.8%。更应该指出的是,其中成为专业技术队伍最为重要的中坚力量的两段即“30—34岁”、“35—39岁”正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以1987年为点,向后推算,到“文革”结束时即1976年概算10年,再向后推算“文革”开始时概算是20年,以这个时间差计算1987年30岁的人,“文革”期间在10岁—20岁之间,正是他们学习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黄金年龄,而1987年40岁的人在“文革”期间也是20岁—30岁的时期,他们或者刚刚进入高等学校,或者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却已经半途停辍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是被耽误的一代,科学素质较差,科技能力较低,是难以承担科技中坚骨干的重任的。而这两个年龄段相加,占专业技术队伍24.5%。如果把这两个年龄段减去,25—45岁最佳创造年龄区就只剩下32.3%,使专业技术队伍的最佳年龄区的人数显得更少,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科技人才低谷——断层。
由此可见,25—29岁年龄段正是低谷——断层所在。如果把30—39岁两个年龄段加入断层区,断层区就又延伸了许多。这个断层在1987年已经到来,到90年代断层最为严重。因为这时断层逐渐到达科技创造最佳年龄区的峰值——37岁,特别是1994年,正是前述1987年30岁左右人员到达峰值的时候。这个断层效应还要向前延续5年,到2000年左右,才能全部通过峰值,并逐渐走出这一区域。又据对1990年全国专业技术干部年龄结构的分析,90年代以后,我国专业技术干部最佳年龄区(30—45岁)已全部处于低谷——断层之中。
据张仲梁、鲍克主编的《中国科技界概观》一书比较了中国和美国80年代后期自然科技队伍的年龄分布,中国自然科技人员存在着明显的谷区,31—40岁年龄段处于低谷区,41—50岁年龄段处于高峰区。在1985年41—50岁年龄的自然科技人员占总数的32.95%,30岁以下占30.12%,1987年的年龄分布特征与1985年大体相当。但有一个明显变化,就是波峰相对降低,41—50岁年龄段的比例由32.95%降为29.69%。1986年,美国科学家、工程师年龄公布的峰值为31—39岁,正好对应我国自然科技人员年龄分布凹点,比我国自然科技人员的年龄峰值低10岁,而且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变化较缓慢。相比之下,我国自然科技人员的年龄分布大起大落,这一状况是在我国教育事业的曲折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科技队伍中高层次人员——研究与开发机构中的科学家、工程师的年龄结构,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队伍老化。45岁以下的人员仅占整个队伍的47.8%,还不到50%,一半以上的人已走出科技创造最佳年龄区,接近退休;二是大断裂层。30—44岁最佳年龄区(25—30岁无统计)三段相加也才仅有24.1%,还不及45—49岁一段人数多。科学家、工程师大多集中在45—54岁两段中,共占科学家、工程师总数的43%,他们是RSD机构中的基本骨干力量。30岁以下的比例也太大,且有很大一部分人过早结束业前学习生活,知识准备不足。统观整个RSD年龄结构的走势,明显的表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犹如两岸陡峭,夹着一个一泻千丈的深谷。一支20余万人的队伍,总数本来就不多,却又小的小、老的老,处在最佳年龄区的只有4—5万人,不到这支队伍的1/4,这是很不利于我国RSD事业的迅速腾飞的;三是年龄断层和职称断层现象依然存在。最佳年龄区的科学家、工程师职称结构,总计为56379人,其中高职100人,中职28007人,初职和未评职称的28272人。从高职看,出现了两个不到1%:一是高职人数占最佳年龄区总人数仅为0.2%;二是占本统计的全部高职人数仅为0.87%。中职也不多,占最佳年龄区总人数49.6%,占全部中职21%。初职和未评职称的却很多,占最佳年龄区50.2%,占全部初级和未被评职称的73.67%。中级职称大多是45岁以上,他们占中职78.8%。而高级职称更为45岁以上人垄断,占99%,其中55岁以上高达64%,60岁以上占33%。可见,年轻的科学家、工程师和高级、中级职称基本上无缘,这又是一种断层表现。当然,这是1985年职称的情况,现在已有较大改观,但年龄断层和职称断层依然存在。
据我们对美国科学家队伍的调查分析,其走势平稳,日趋年轻化。25岁以下数量很小,说明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人为了成为科学家还在学习。而25岁以上的各年龄段科学家比例呈下坡形,特别是55岁以上比例很低,说明每一代都多于上一代,新人辈出,吸收了大量的年轻人,美国科学家这种年龄结构无疑是理想模式,这是50—60年代美国科技发展特别迅速的决定性原因。美国科技队伍至今仍保持年轻化的态势,所以,其科技在当今世界上仍继续处于领先地位。
我国科技队伍年龄断层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有了一定的弥合和缓解。如“文革”后许多已过了“就学年龄”的人毅然入学深造;又如各种成人教育、在职培训也使一部分科技人员得到一定的提高,使他们真正挑起科技工作重担(当然,这其中又有滥发学历的问题,造成某种程度的虚假现象);又如提前启用年轻一代,大力提拔青年拔尖人员,给他们压担子,促其迅速成长,尽早“顶岗带班”;再如充分发挥中老年科技人员骨干力量和传帮带作用,适当延缓部分高级专家离退休时间,延长老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寿命,等等。但是,总体上的基本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
第二,我国科技队伍不仅年龄老化,而且不稳定,人心思走,特别是青年拔尖人才流失严重。1992年7—9月,据我们对全国108个单位调查:科技人员殷切希望调离本单位的占15.8%;比较希望调离本单位的占20.8%;经常想自动离职的占5.2%;有时想自动离职的占15.7%。另据河南省人才研究所1991年对1741名科技人员调查,在择业问题上希望“从事其它方面的科技、教育工作”的375人,占22.4%;表示“不再从事科技、教育工作”的361人,占21.5%。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科技人才曾出现三次流失浪潮。前两次不仅没有被扼止,而且1992年以来,又出现了第三次流失浪潮,情况比前两次更为严重。据统计,1978年8月到1991年底,我国向7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遣的17万留学人员,只有约5万名回国,占派出总数的29.4%。在回来的5万人中,获博士学位的1100人,获硕士学位的1200人,两部分加起来也不到回国人员总数的4.6%。
科研单位科技人才流失的比例很高。中国科学院10000名左右青年科研人员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流失率达39%;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流失率达27%。国内外闻名的物理研究所,由于人才严重流失,致使35—45岁的科技人才只占全所科技人员的15.7%。上海生化所是一所400余人的研究所,而出国在外的竟达100余人,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人才出现后继乏人的严重状况。
高等学校人才流失,特别是尖子人才的流失,也已到了惊人的地步。据上海高教局统计,全市51所高校,自1986年至1989年底,流失的老师人数为4266人(不包括人才交流),占高校教师总数的16%,其中74%流向国外。在流失的教师中,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80%,致使全市学校中30岁以上、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比例迅速下降,教师队伍年龄结构严重失衡。上海交通大学36岁至40岁的青年教师只有149人,仅占教师总数的6%。特别是1992年以来,尖子人才流失汹涌浪潮,对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形成更强烈的冲击波。80年代中前期,复旦大学曾以卓著的成果和优秀的师资蜚声海内外,显赫的声势直逼北大;如今在一片下海声中,昔日的辉煌正淡化为记忆中的光环。国际新闻专业教师几乎走尽,只好暂停招生。一项国际组织资助的前沿性高科技研究,由于从课题负责人到课题组成人员相继“跳槽”,被悄然搁置。据一项按国际惯例排名方式显示,复旦大学在全国高校名次表上已丧失了往日强劲升势,其主要原因就是优秀拔尖人才的严重流失冷落。地处辽宁渤海之滨的一所医学院,由于骨干人才接二连三出走,医学基础学已经基本没有学科带头人,原来实力最强的生理教研室,除了5名60岁开外的老教授外,只剩下几名35岁以下的硕士生和本科生。华中师范大学近几年,每年报考研究生外流的占教师总数的15%;公派出国的120名青年教师,逾期一年以上未归的达60%;流向特区的仅1991年就有13名教授、讲师。中国科技大学国外留学逾期不归的竟占90%以上。兰州大学,1992年起也受到人才流失的浪潮的冲击,优秀人才流向国外,流向东南沿海,流向东北、中原。仅1993年头三个月,又调离13位教授、副教授和高级实验师。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多年辛勤培育了16名硕士研究生,现已有12人去美国,年久未归,老教授感叹自己的辛勤劳动真成了“为她人做嫁衣裳”!
原来内聚力较强的高科技企业现在也面临严重人才流失。北京中关村是靠高科技人才和优惠政策起家的“中国硅谷”,已被许多家著名的外企高科技公司包围,每年要被外企公司挖走骨干人才200多名。产值达30亿、居中国民办科技排行榜前列的四通公司,原有8名博士生,如今只剩下一位,其余的全部被外国公司以月薪1000美元高薪挖走。有的企业甚至是“六个月一大震,三个月一小震”,人员更替竟以月计算,根本谈不上什么长远打算。
医院科技人才的流失,也十分严重。据上海市对华山、中山等8个著名医院的调查,1986年以来,出国未归的就有500多人,其中86%是临床骨干医师。更值得注意的是还将面临教授专家退休高峰。1992年统计,中国科学院系统的高级研究人员平均年龄超过53岁,到2000年退休的时间到了。全国高校18559名教授中,年龄在61岁以上者有6810人,56至60岁者有7734人,二者共占总数的78.4%;无独有偶,在85548名副教授中,年龄在51岁以上者也占78.4%。两个78.4%,几乎全部学部委员、首席专家、学科带头人都在其内,这难道不令人心悸吗?
面向21世纪,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需要更多更好的人才,可是扼制不住的人才流失,一次比一次严重。不仅关系到我国科技队伍的生死存亡,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前途和民族的兴衰。
第三,人才隐性失业、浪费惊人,青年科技人员无用武之地。
上海市人事局1986年对10048名科技人员抽样调查结果如下:(1)2/3的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据此测算,积压浪费人才约4—7.5万;(2)1/4的人任务不饱满。完全没有任务和任务不饱满的占26.3%;比全国高6.2个百分点。(3)用非所学、用非所长问题严重。专业不对口或不很对口的分别占17.6%和2.19%。认为前途较小和没有前途的分别占10.23%和5.08%。要求从事专业工作的占61.8%。(4)才职不符,高能低就现象普遍。据抽样调查,18.5%的高级知识分子实际在做中级职称的工作,中级的做初级的占16.16%,初级做一般工作的占14.56%。上述情况经过几年努力,虽有所改变,但仍不容乐观。
据河南省人才研究所调查,尚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科技人员由1986年的68.52%降至43.8%。但以下情况令人担忧:(1)197人“无事可做”,占11.4%。(2)604人感到“工作不太顺利,困难较多”,占36.9%。(3)102人感到“很不顺利,困难很多”,占5.9%。(4)331人在现职岗位上认为不可能取得成绩,占19.2%。(5)3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员占调查对象的39.3%,认为“工作量太少,常常无事可做”的占34.2%。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科技人员仍有50%左右的人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部分是青年科技人员。青年科技人员最感烦恼的是“任务不足,工资低,住房条件差,人际关系难处”。不少青年科技人员认为单位对他们不重视、不放手,任其自然,甚至压制排济,严重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和科研工作的开展。
第四,中青年科技人才负担太重,早衰早逝令人痛惜。
我国中年科技人才是科技工作的中坚骨干力量,可是他们肩负两副重担(一是科研教学;二是家庭),再加上内散、内耗等原因,常感疲惫,有的英才却已早衰、早逝。据河南省人才所调查,感到工作量过大,因而常疲劳者447人,占25.8%。在常觉疲劳的科技人员中,40—50岁左右的中年科技人才比例最高,竟达68.4%。这说明不少中年科技人才处在紧张的超负荷运转。特别令人焦虑的是,我国知识英才早衰、早逝的情况尚未根本好转。
10年前,当科技界两位中年专家蒋筑英、罗健夫因积劳成疾而溘然长逝时,在全国曾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可是,此后接二连三地传来令人心碎的恶耗:张广厚、钟家实、莫应丰、鲍昌、金乃千……一个一个都过早地辞世。据《光明日报》从1990年初至1992年3月5日所刊出具有副局以上职称的科技人才逝世的消息,计72组,452人,其中60岁以下竟达87人,占20%以上,有一些甚至是50岁以下。50岁左右,正是人才生命和才华的黄金时期,在事业上大有作为的丰收季节,但由于过早撒手辞世,致使多年积蕴的智慧、才华,未得到发挥,便毁于一旦。一些有识之士深刻指出:在全国人民平均寿命接近70岁的时候,而我国的一批科技英才却在未到60岁,甚至未到50岁便匆匆忙忙地在攀登的历程上划上了句号,真是令人痛心!
我们要大声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靠着热爱祖国,热爱事业,宠辱不惊,困不伤志,勤不惜身的精神脊梁支撑自己的一生。他们所要求的并不多,可是长期的超负荷运转,持久的收支不平衡,难处理的人际关系的内耗,该落实的政策旷日持久的拖拉,终究难以承受。人才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英才的散失,于国于民都是重大的损失!
二、解决我国科技队伍年轻化的对策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才队伍年轻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对于我国科技队伍年轻化问题应予高度重视。我们要有危机感、紧迫感,要充分认识实现科技队伍年轻化,优化人才结构,在我国已刻不容缓。
⒈从战略高度,认识年青优秀科技人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国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企业,聚集了一大批年轻科技人才。他们既是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他们正处充满创造力的黄金时代,是我国攻克尖端科技、赶上发达国家先进水平的希望所在。他们的境界充满了高尚的奉献精神。他们的付出对于国家和民族,带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党和政府、各级领导理应禅精竭虑地解决好青年科技人才的各种实际问题。
⒉解放思想,广开才路,不拘一格选用年青优秀人才。适应高新技术革命中,科技人员最佳年龄区峰值前移的发展趋势,当前特别要解放思想,打破旧观念、旧框框,改革用人体制和制度,不拘一格选用30岁左右的科技人才。我国已有一支年轻的科技人才队伍,但目前主要缺少科研、学术、技术和管理上的带头人,他们是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将帅之才。要花大力气培养、选拔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凡经过认真考核、批准为培养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计划的年轻科技人才,必须给予较强的启动经费,用于添置必要的仪器设备、本人住房等等。在工资待遇上,除按国家规定应发给的以外,还要给予特别津贴,并支持他们通过多种途径申请国家科研经费。
⒊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关键在于切实给他们压担子。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一靠追踪当代科学技术,不断进行理论学习,更新知识,更新观念;二靠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不断磨炼,不断提高,更快的成长。当前在培养选拔工作中,特别要解放思想,大胆启用年轻人才,给他们压担子,让英雄有用武之地,真正做到:海阔任鱼游,天高任鸟飞。
⒋继续对处于科技创造最佳年龄区的中青年科技人员组织强化性继续教育,进行重点培养,使他们的素质在短期内有比较大的提高。要将重点从过去的学历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全力提高中青年骨干队伍的素质,这是解决年龄断层的关键所在。
⒌尽力解决年轻科技人才的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在改革大潮涌动的今天,解决年轻科技人员的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无论从现实还是从长远角度考虑,都非常必要。由于种种原因,年轻科技人员的生活和工作的实际问题长期得不到改善。突出的是两大问题:一是住房问题,二是职称待遇问题。要采取强有力举措,花大量精力、人力和物力解决年轻科技人才的住房问题。住房是科技人员生活、工作的基本条件。有了住房,才能安居乐业。如不很好解决就很难留住他们。职称工作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关键是要破除种种旧思想、旧观念,冲破论资排辈的旧习,大胆破格晋升年轻优秀科技人才。
⒍要把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与建立淘汰机制结合起来,优化人才结构。过去常说:“脑体倒挂”,知识分子待遇太低是造成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人才断层、人才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大幅度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才可以解决。但是还要看到,由于少数中老年知识分子在新科技面前不思进取,逐渐落后,导致人才梯队中原有断层、人才外流呈上溯倾向;而少数青年知识分子非智力素质差,导致科技队伍断层下降,年青科技人才不稳。要改变这种状况,除提高待遇外,当务之急是建立淘汰机制,解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的冗员问题。冗员问题不解决,提高科技人员待遇的政策就难以落实。因此,必须首先予以切实解决。不很好解决生活待遇问题,不可能留住优秀年青人才。淘汰机制主要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的多余人员转移到其它领域中去;二是从动态的、发展的角度判断科技人员是否符合其岗位的要求,打破职称的终身制,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取得该职称所应获得的成果者,应暂缓对其在现在岗位上的聘任甚至取消其任职资格,让出岗位为年轻一代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⒎从长远利益出发,对有突出贡献的年青科技人才给予重奖。目前全国各地盛行重奖科技人员,但各地重奖对象几乎都是在应用科学、技术科学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给当地经济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科技人员。这些科技人员当然应得到重奖,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是商品,其创造者应得的高收入本应由企业支付,政府重奖这类科技人员实在是越俎代庖。世界各国政府对有贡献的知识分子的奖励,大部分都用于那些从事距离市场较远、没有高收入的基础科学方面的专家。作为从事应用科学研究的专家诺贝尔也同样认识到这一问题,诺贝尔奖金的设立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基础科学不仅是新技术、新发明的源泉,而且是关系国家长远利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用充足的资金保证基础性研究,稳定基础科研队伍,这是更高层次的改革。
⒏采取积极措施,吸引海外年青优秀学子回国。在培养选拔跨世纪优秀科技人才工程中,还必须拓宽视野,走向世界,采取优长政策,吸收流失在海外的优秀科技人才。国家和各省市培养跨世纪优秀科技人才计划,要扩展入选范围。凡是在海外作出了国际水平的工作,从事应用和科技开发工作的,已作出了新颖性、创造性和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工作的青年科技人才;凡愿意立足中国开创事业的,都可通过各种方式申报、入选。
⒐加强宏观调控,充分发挥人才市场在解决科技队伍年轻化方面的作用。要加强舆论导向,加强革命的理想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加强敬业精神职业道德教育,引导人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要利用经济杠杆,制定合理倾斜的分配政策,吸引人才向急需的部门和地区流动。要把那些人才严重匮乏、技术力量严重不足的单位,列为人才市场的服务重点。要通过制订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对人才流向进行调控,鼓励人才合理流动,限制不合理流向,使人才流动趋向合理有序,以利于培养、发现、选拔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标签:科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