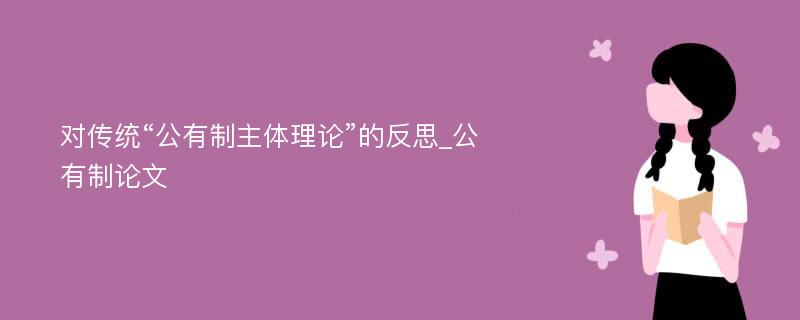
对传统“公有制主体论”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有制论文,主体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勿庸讳言,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碰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其中尤以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一些传统观念危害为大,它们给国有企业改革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至于长期以来形成了国有经济体制改革“走一步,瞧三瞧,摇三摇”的困难局面。这其中占居首位的传统观念则当属传统“公有制主体论”思想,它可以说是目前横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上的一块最大的拦路石。党的“十五大”报告突破了传统意识形态的羁绊,明确提出“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观点,为我们重新认识“公有制主体论”指明了方向。
传统“公有制主体论”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框框应用于各种经济成份的发展过程中,人为地、主观地规定各种经济成份发展的比例关系。其政策含义是:要求公有制经济成份必须始终在数量上占整个国民经济的绝对的比重,强行限制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发展速度。这一作法造成如下后果:(1)使改革者们在思想上套上一个沉重的枷锁, 担心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改革会削弱了所谓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因而宁可看着那些“死不了、活不起”的国有企业躺在国家银行的身上苟延残喘,也不愿对其进行有效地大刀阔斧地改革。(2)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心有余悸, 担心政策改变,不敢大胆发展,特别是一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担心继续发展会危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国家的限制和打击,因而不愿再继续投资,而宁愿要么让资金“闲置”,要么将资金“外逃”,流往海外,要么则是大肆挥霍掉,以规避所谓的政治风险。显而易见,传统“公有制主体论”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追根溯源,传统“公有制主体论”的思想渊源乃是来自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条式理解。事实上,对单一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最早起源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虽然使人类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更加科学化了,但在单一公有制这一点上,则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早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曾经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过小范围的社会主义试验,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当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些国家成功后,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在更大范围内付诸了实践。但实践的结果是,一些国家失败了,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另一些国家则在历尽了传统经济体制的低效率的长期困扰后,开始走上了改革的道路。当改革的希望之风吹进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之后,那种追求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经济体制模式的理论开始土崩瓦解。中国大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所有制问题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在传统派和改革派之间达成了一种折中性理论,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理论模式。其特点是综合了各方的不同立场:一方面容忍了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公有制占主体”这样一个尾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这一尾巴的消极作用变得日益明显。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往往动辄就拿“公有制占主体”这把“尺子”去“卡”某一地方的经济发展,去判定某一地方的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有些人则公然指责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有些人则居然认为现在非公有制经济已发展到顶了,不能再任其继续发展了,否则就会危及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从而危及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由此可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理论观点虽然在改革之初对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成为可能,但是在今天,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该理论观点则已开始成为阻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如上所述,这种观点是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身兼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者和微观经营者双重职能,同时政府不仅要办企业,而且还要办社会,因而俨然成为该社会的唯一经济主体。与这种统制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必然是公有制占主体的所有制模式(那种纯粹的单一形式的公有制则是这种模式的一种极端形式,只有在文革十年那种极端的年代里才能看到)。如果我们承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公有制占主体的所有制模式是由统制经济体制的性质决定的,那么今天在我们已经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的条件下,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坚持与传统计划经济相联系的传统“公有制主体论”呢?我们的看法是否定的。
首先,这种理论观点不仅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因此,一个社会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完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并非是人们的主观意志选择的结果。正如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迫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计划经济模式而选择市场经济模式一样,在所有制的问题上,我们的主观意愿和所有制偏好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让市场竞争的规律在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进行自然选择,优胜劣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站在市场竞争的赛场之外,一方面当好裁判员,制定和维护好竞赛的规则,另一方面为“游戏”者创造良好的外部竞赛条件,如公共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也不再直接经营企业,而是主要靠税收来维持运转,靠政权和宏观调控等对经济形成的控制力来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样,政府就没有必要硬性规定公有制经济的比例问题,因为不管什么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都须纳税,并且经济越发展,政府得到的税收就越高。这和计划经济的情况大不一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需要公有制企业提供收入来维持运转,所以强调公有制经济占主体是必然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不再存在这种必要性。并且,比较而言,政府投资于那些处于竞争领域内的没有活力的国有企业,不是收益低下,就是赔本,还不如兴办非公有制企业合算。应当看到,市场经济有它自己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按照优胜劣汰的逻辑,选出优秀的竞争力强的企业,淘汰掉落后的低效率的企业,而从不问你是姓“公”还是姓“私”,姓“社”还是姓“资”。一些国有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了,是规律使然。如果我们逆规律而动,勉强去维持那些本该被淘汰的企业,强行限制其他有活力的经济成份的发展,以便保持公有制经济的所谓主体地位,那么,最终被拖垮的是整个国民经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是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也就是说,不要把选择所有制模式的基点放到姓“社”姓“资”的经院式争论上,而应当是看哪种所有制模式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的机遇曾被我们多少次错过,如今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供空谈。
其次,从我国目前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来看,即使公有制经济不占主体,也不会否定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知道,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种特殊的社会主义阶段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有巨大的差别。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差别就是表现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上。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的高低是一个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进化的渐变过程,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高,因而大力发展生产力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位的目标,而不能把生产资料的公有程度作为第一位的目标。如果在这种特殊的历史阶段上,就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作为首要的追求目标,奢求公有制一定要占主体,把只能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上才能办到的事硬搬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来运作,则只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困境和非公有制经济的病态发展就是明证。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模式。既然是一个过程,就必然要有一个初级阶段。既然是初级阶段,就不一定具有高级阶段才能具有的一切特征。比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这段时期,虽然公有制经济不占主体,但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的国家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可以说,选择不以传统意识形态偏好为转移的多元混合的所有制模式,不仅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且也是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上层建筑相容的。那种认为不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等于是否定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
当前,在我国理论界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学风,那就是教条地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的设想,按照一种理论上的理想模式来雕塑现实,而全然不顾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无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总是企图让现实来适应他们的理想模式。在有些人看来,这种教条主义理解表面上看似乎是很马克思主义的,但实际上却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的。现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已经进行了近20年,但在理论界中,教条主义的阴影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观。几十年来,我们饱尝了教条主义和极左路线所造成的苦果。值得欣慰的是,党的十五大报告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高扬了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旗帜,在调整和完善我国所有制结构的问题上,充分运用了辩证否定的基本方法。这表现为:在肯定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又包含了对这一前提的扬弃。即明确提出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新理念,以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在“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差别”的思想。这些肯定中的否定都真正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时代精神。如果机械、僵化、形而上学地理解十五大报告,就会重新回到传统的“公有制主体论”的老路上去,从而与历史发展方向相违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