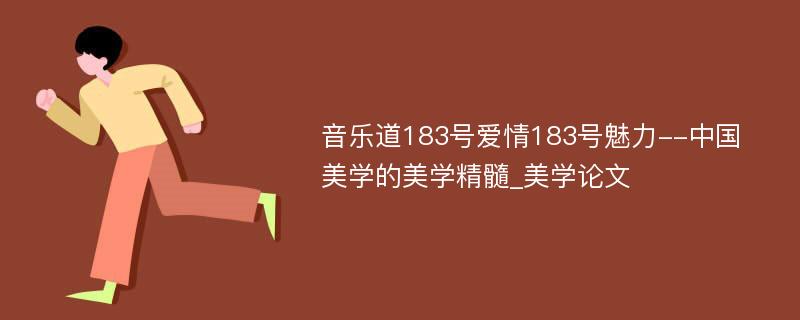
乐道#183;兴情#183;神韵——中华美学的审美本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韵论文,中华论文,美学论文,本质论文,兴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10-0117-09 一、审美本质的发现方法 西方美学把美当作与人无关的实体或实体的属性,所以运用逻辑演绎或经验归纳的方法来获取美的本质。与西方美学不同,中华美学认为美不是实体性的,而是人与世界感应的产物。因此,它不是通过逻辑演绎或者经验归纳的方法来获得美的本质,而是通过直观感悟来发现审美的意义,而这就是现象学美学的方法。从表面上看,中华美学是以直接论述的方式断定美的本质,而没有展示其发现的方法和过程,因此似乎有独断论的嫌疑。但实际上,它还是以现象学的方式来发现美的本质,也就是通过审美体验及其反思来使美的本质得以呈现。中华美学认为,美不能自美,必须经过审美体验而成为审美对象,这样,审美体验就成为发现美的方法。这个现象学的过程并没有直接作为一种理论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美学论述,特别是诗学论述,来复原这个过程。 现象学美学思想首先表现在道家的论述中,道家的美学思想也是通过现象学的方法而发现美,即通过“心斋”“坐忘”“观复”,发现了虚无的道,而其中间环节就是象,象作为道之显现,就是美。儒家美学思想在吸收了道家美学思想之后,也具有了现象学的方法论。孟子最早就指出,理解诗的方式是“以意逆志”。他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①这里所谓“以意逆志”,是指以读者的理解与作者的意图互相沟通、融会,达成解释学所谓的“视域融合”,最后了解作者的思想,从而得出诗的意义。这一论说有别于客体性的“我注六经”,也有别于主体性的“六经注我”,而是主体间性的“我”与作品的会通。但孟子的思想还只是解释学的,没有达到现象学的高度,因此还不能成为审美本质发现的基本方法。后来的美学家才把道家的象思维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以现象学的方式完成了审美本质发现的任务。在《文心雕龙》里,刘勰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考察,揭示了如何发现美的本质的途径。他首先指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这是要把现实观念悬搁,进入“纯粹意识”;进而指出,对文学作品要“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览”。②这里除了强调要广博地阅读以增加见识外,已经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当作把握美的本质途径。他提出了“圆照之象”,圆照是佛教用语,意为圆融观照,是一种区别于经验认识的、消融物我的纯粹直观;而象则是圆照的对象和产物,就是审美意象。它不同于外在的经验对象,已经达到了物我同一,作为现象呈现。于是,在这种圆照之象中,就把握了作品的审美意义。他又更为具体地展开了这个过程,指出了进入审美的情感体验:“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辞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③就是要通过对文辞的理解而达成美感(情),而在美感(情)体验中就有美的本质显现,即“虽幽必显”。这样,就通过具体的体验,把握了美的本质(理):“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他还具体地描述了美感体验作为美的本质发现的途径,认为审美鉴赏与美感是一致的:“深识奥鉴,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④除了道家之外,禅宗也为审美本质的发现提供了方法论。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直觉顿悟佛道。严羽以禅喻诗,通过审美直觉——妙悟,把握诗歌的本质。他指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⑤至此以后,审美直观就成为领会艺术和美的本质的现象学方法。 强调直观、妙悟的思想,直接来自道家和禅宗,而儒家美学思想强调审美体验的情感性。《文心雕龙》一方面接受了道家的虚静直观的思想,但更多的是接受了儒家的情感论,认为审美是情感体验,从而揭示艺术、美的伦理本性。刘勰提出“物以情观”“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他把审美归结为情感体验,认为情感意象克服了物我距离,揭示了艺术的本质。刘勰认为把握艺术的本质,要诉诸内在的美感,而不是外在的标准。他说:“夫惟深识奥鉴,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西方美学把审美当作感性认识、把现象学还原看作直观,从而建立了认识论的现象学美学;中华美学认为现象学还原是一种情感体验,审美意义的发现也是情感体验,从而建立了情感论的现象学美学。对于这种情感体验中的现象学的还原,刘勰称为“妙鉴”。他说:“书亦国华,玩绎方美。”⑥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要“玩绎”,即欣赏,而不是西方现象学或认识论的客观把握,在这种情感体验中,作品才体现出美。当然,审美体验仅仅是对审美意义把握的第一步,这只是非自觉意识而不是自觉意识。因此还要通过对审美体验的反思,达成自觉意识,来把握审美意义。 中华美学对美的本质的规定,是对审美体验反思的结果。反思得出美学的基本范畴,揭示了审美的本质。审美意象中包含着美的本质,在审美体验中领会了美的意义,这是中华美学的现象学方法。不同于西方美学把审美意象看作表象,通过对它的抽象来获得美的本质的认识论方法,中华美学认为,所谓美不是某物的属性,而是天、地、人之间流动的气的显现,是宇宙中的生命力的显现,万物都体现着这个大美。故中华美学认为,对具体对象的情感体验和观照,就可以获得美的本质。但美不是实体,而是审美,也就是说,中华美学不认为有一个客体性的美,而认为美不能自美,美既是对象,也是美感,美即审美,审美中才有美。因此,我们先考察审美,而审美本身也就是一种现象学的体验,在审美体验中获取美的意义(本质)。经过不同时代的众多美学家的协同努力,中华美学创造了一系列美学概念,构成了一个内在的逻辑,用以规定审美的本质。这些美学基本范畴包括乐道、兴情、神韵等。它们其中每一个都不能全面地揭示审美的本质,都必须由其他范畴来补充,以构成完整的审美意义。这些命题之间既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也有区别,如兴情说、神韵说可以从乐道说找到根据和渊源,同时兴情说、神韵说也突破了乐道说。其中乐道是审美的本体论规定,也规定了审美的伦理性质;兴情是审美的特性,也规定了审美的情感内涵;神韵是审美的超越性意义,揭示了审美超越伦理、情感的特征。中华美学运用这些范畴,层层深入,互相关联,对美的本质进行了规定。 二、乐道:审美的本质 运用现象学方法来还原美的本质,就要进入审美体验。在审美体验中,获得了什么呢?中华美学认为,获得了道,这个道不是通过单纯的认知把握的,而是通过一种情感体验——乐——把握的,所以,中华美学把审美的本质归结为乐道。儒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道德规范,并且自觉地认同天道,从而获得一种高尚的快乐,这就是乐道,所谓点之歌,颜之乐是也。孔子通过艺术而闻道,他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⑦这里的乐就是音乐表达的闻道之乐,它超越了感性之乐。道家在归返自然时达到怡然自得的逍遥状态,这也是乐道。庄子寓言多描述审美体验,物我两忘、同于大通,感到逍遥之乐——天乐,天乐即乐道。《庄子·天运》中虚拟了黄帝与臣子北门成的对话,谈论对“至乐”的看法。黄帝先描述了闻“至乐”的体验,然后总结说:“乐也者,始于惧,惧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以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⑧这就是说,通过审美体验而悟道,悟道也是一种“天乐”,所以审美即乐道。总之,乐道为(审)美,就是中华美学的本质论,它通向哲学本体论。 西方哲学天人分离,世界具有实体性,美也具有实体性。西方古代美学认为美是实体的属性,与主体无关,具有客观性。西方近代美学认为主体是实体,美具有主体性,是主体意识的对象化。因此,西方美学认为美是认识的对象,美学是感性学。而在中国,由于天人合一,道具有非实体性,它体现于万世万物,也体现于人心人性,道在天人之际,所以是变相的存在论。因此,作为道的显现的美也就具有了非实体性,美学也具有了存在论的性质。中华美学认为美不是实体也不是实体的属性,美即审美,是天人感应。乐道即审美,这一观点排除了实体性的美的观念,意味着主体介入才有美,美不能自美。柳宗元曰:“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⑨在中国语言中,美不仅是名词,也是形容词,还可以做动词,既可以是物的属性,也可以是美感,还可以是审美活动。这一语言现象体现了中华美学的存在论性质,即美不是与人无关的实体,而是人参与其中的审美活动,是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 中华美学认为,伦理是实践道,审美是乐道,二者都是道的体现。因此,美与善(伦理)相关,也由此规定了美的特性。行道为善,具有实际功利性;乐道为美,超越直接的实际功利性,但仍然具有实际功利的基础。因此,中华美学认为美与善相近,美的前提为善;美又超越善,为善锦上添花,因此“美善相乐”。但美与善毕竟不同,二者的区别在于,善偏于内容,美偏于形式;善偏于理性,美偏于感性;善偏于实用,美偏于情感。悟道、行道是出自实际需要,这是伦理范围的善,具有实用理性的品格。而乐道则超越了实际需要,把晤道、行道作为一种满足精神需要的手段,从而超越了实用功利。“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⑩这是说好德对常人来说,不具有必然性,非人之自然欲望,而好色(色可以理解为性欲对象,也可以理解为审美对象)则具有必然性,是人之自然需要。但圣人、君子则好德如好色,把道作为乐的对象。这就是他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1)乐道必须建立在行道的基础上,“子曰:……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12)孔子在这里直接提出了行道为礼(善),乐道为美。乐道,既是君子的最高理想,也是中华美学的基本理念。由于道不是彼岸之物,而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即“道不离伦常日用”(儒家)、“道在屎溺”(道家),因此乐道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以悟道、行道为乐。审美不是脱离日常生活,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富贵贫穷、顺境逆境,都信守天道,而且心甘情愿,以此为乐。这样的生活就是美的,如此的态度就是审美,这样的人就是完美的人。 儒家的道是伦理道德,美是道的形式。但是,道不仅是外在的规范,更是内在的追求和实践活动,因此不仅要得道,而且要行道,还要“悦道”(孔子)“乐道”(荀子)。如孔子说: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3)就是说学道之乐。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4)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5)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6) 孟子说“美善相乐”,也是因为乐道为美。荀子更直接地提出了乐道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17) 道家美学也以乐道为美,只不过这个道不是伦理之道,而是自然之道。庄子认为通过归返自然而达到的逍遥游,就是一种得道之乐,它不是世俗之乐,而是“天乐”“至乐”:“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18)乐道是更高的境界。道家的道是万事万物包括人的自然法则,行道即适性。审美即适性,是得道的逍遥状态。由于真人外无所求(无待),顺应自然,所以也是一种乐道(天乐)。魏晋玄学——道家思想的变体——也以乐道为美。嵇康一方面认为六经为核心的名教压抑人性,不合天道:“六经以抑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今若以虚堂为丙(病)舍,以讽颂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阙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19)另一方面,又认为放纵情欲“非道之正”,如果“惟五谷是见,声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务淫哇……谓之不善持生也。”于是他求取中道,以大和为至美:“以大和为乐,则荣华不足顾也;以恬淡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钦也……故以荣华为生具,谓济万世不足以喜耳,此皆无主于内,借外物以乐之;外物虽丰,哀已备矣。有生于中,以内乐外,虽无钟鼓,乐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轩冕也;有至乐者,非充屈也。”(20)道家的性不包括情,是无欲无情之自然天性。由于儒家哲学成为主流,而且与道家哲学趋于合流,道家的适性与儒家的合情融合。魏晋以后,性情合称,于是以情感体验为中心的乐道就成为中华美学的基本理念。 中华乐道美学把道与美等同,实际上主张德福一致。西方哲学一直有德福关系的争论,利他的道德与自己的幸福是否一致,这是一个悖论。儒家美学认为遵守集体理性的道德法则可以获得最大的快乐,最后就是乐道。而道家哲学以自然天性为道,所以为道就是为自己,就是最大的快乐。事实上,这个问题并没有真的解决,因为他人与自己以及自然与社会的矛盾仍然存在,所以德福并不能一致。由于道的天人合一性质,不具有彼岸性,仅仅具有此岸性,故道是伦理道德(实用理性),被现实性所规定;而道家的道,是自然天性,也属于此岸而非彼岸,从而桎梏了超越性。这就是说,在现实领域,德福不能一致,道与美也不能同一,这是中华美学的根本缺陷。 此外,乐道为美,也体现了情理一体的理念。乐为感性、为情,道为理性(虽然包含情,但理性主宰),二者有所区别,但乐道则消弭了这种区别,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但理与情毕竟有矛盾,二者不是一回事,不能消除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乐道为美的规定就潜藏着内在的矛盾。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中华美学理与情的统一破裂,一方面宋明理学以理抹杀情(“存天理,灭人欲”“文以害道”),另一方面宋以后主情说美学成为主流,从而使中华美学由道本体转向情本体。 出于对道的信念,中国人具有一种乐观主义精神,这是乐道的另一种含义。儒家代表的中华文化具有一种乐观性的世俗主义,这就是李泽厚先生所谓的“乐感文化”。李泽厚认为,欧洲文化是罪感文化,因为基督教认为人有原罪;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因为佛教认为人生的本质是苦;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因为它以不能履行本份为耻辱。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认为人生是乐观的,不必追求彼岸世界,此岸世界就可以悟道、行道、乐道。因此,在特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乐感文化。这是因为,中华文化具有实用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特征。实用理性不承认此岸与彼岸的区分,认为只有一个世界,此岸世界即可以成为完满的世界。因此,它对于社会人生抱有乐观主义,认为天道即人道,总会有光明的结局;即使一时困顿,但善恶必有报应。此外,中华文化是集体理性主导,由于个体没有独立于集体(家族、国家),所以没有个体生存的孤独感、无力感,也不会有死亡的畏惧。中国人依仗集体理性,相信生存的意义在家族、国家的存在,在无尽的历史延续中实现,因此具有乐观精神。孔子一生不得志,但仍然乐观,他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21)他自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22)孔子代表的中国人生观是乐观主义的。道家的人生观也摈斥了悲观主义。老子冷静睿智,洞悉一切,认为只要领会生存之道,就可以维护自然生命。庄子放荡不羁,更积极地争取生存的自由,他认为回归自然天性,就可以进入逍遥之境,立于不败之地。当然,这种“乐感文化”也有消极方面,它掩盖了现实的异化,把现实理想化,从而消除了超越性和批判精神。 乐道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是人生最高追求。钱穆先生说:“乐则人生本体,当为人生最高境界、最高艺术。”(23)以乐道来规定美的本质,不仅找到了美的本体论根据,也包含了审美的情感内涵,因此,必须进一步对乐道的情感内涵进行考察。 三、兴情:审美的特性 运用现象学方法,可以把审美体验还原为情感,道是情感体验的对象,这是中华美学对美的进一步规定。这一规定,既来自审美体验,也与乐道为美的命题有关。以乐道来界定审美,一方面把道确定为美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规定了审美的情感内涵。道体现为万事万物,那么,万事万物如何成为乐的对象呢?这就需要进一步加以规定,于是就有了兴情说,情感成为审美、艺术的心理内涵。中华美学与西方美学不同,不是基于认识论,不讲模仿现实、反映现实,而是基于价值论,讲表现情感。儒家重情,情理一体化,审美也是合理之情的表现。道家讲真,审美是归真,而这个真不是认识论的真,而是本性的真、价值论的真。虽然道家讲无情,但自然天性中又很难排除情。后来儒家的情与道家的性合一,形成兴情说。中华美学认为艺术的本质不是认识现实、再现现实,而是情感与世界的会通,是以情体道。在西方,直到康德才把审美划入情感领域,而中国古代美学更早地体认到了这一点。 但中华美学对美的情感性的确认,并不是从主体性出发的,而是与对道的体认相关。为什么能乐道?因为道是情理一体的,道有情,因此人和世界都有情。中华美学的情理一体思想源于道的本性,道既是理,又是情。道在人,也在自然,于是人与世界都有情。美作为道的形式,同时具有了理与情两种属性。情的原始意义是实际,既指主观的感情,还指客观的实情。如“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24),就是指客观实情。现代汉语中的“情况”一词还保留着这个意义。庄子讲圣人无情,又讲“万物复情”,这并没有矛盾,因为前后两个情意义不同,前者是主观之情,后者是客观之情。后来,情的意义就偏向主观,成为人的心意。但客观世界也非无情,由于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中国人认为世界也是有情的,它与人之情互相感应、彼此沟通,而审美和艺术就是这种情感的沟通方式。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就提出“道始于情”“礼作于情”,把情作为道的必要内涵。情感形于外,就成文,包括天地之文和人文。于是就有审美,就有艺术。中华美学的兴情论与西方美学的表现论不同,它不是主体性的,而是主体间性的。由于情感是感兴的产物,因此情感不是自我的专有物,而是我与世界互相感应的结果。主体的情感需要,与有情的对象世界之间就会发生感应、交流,这就是物感、感物、感兴,于是就有情感发生。《性自命出》还提出,“情生于性”“喜怒悲哀之气,性也。及见于外,则物取之也。”这里是说情感是人性与外物接触后生成的。所以中国艺术讲触物生情,情景交融,我有情,万物也有情,互相感发,引起共鸣,这就是物感说和感兴论的实质。《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25)陆机说“感物兴哀”(26)。刘勰说“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触兴致情”(《文心雕龙》)。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27)傅亮称“怅然有怀,感物兴思”。(28)萧统称“睹物兴情”(29)等。中华美学把我和物都作为有情感的主体,把审美看作两个主体之间的交流,因此具有主体间性的性质。这就是说,中华美学的情感论是主体间性的兴情论、同情论,而不是主体性的表情论、移情论。 兴情论不仅强调了审美的情感性,而且把兴作为一种真实生命体验的发生,从而具有本体论的性质。在先秦,兴是一种诗歌的写作手法,遂有“赋、比、兴”之说。同时,兴还是一种诗性的生活体验,可以使人超离世俗生活。所以孔子讲“诗可以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0)这个兴,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起情,当有更深的含义,否则孔子不会如此重视,多次提及。孔子认为有了兴,才通向礼,最后达到天人合一之乐,于是才有了真实的生存。兴源于气,感于物,归于道。中华美学以气来解释审美情感的发生,认为气充塞于天地人之间,使人和万物具有勃发的生命,产生了激昂的情感。钟嵘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气本于道,是原始生命力,也是人的真实生存之源。在气的充实之下,兴发生,这是一种在审美状态中的人生体验,是生命力的感发。总之,中华美学认为,兴是感物起情,但不是日常的情感发生,而是回归天人合一的生命意志。 中华美学的兴情论与中华艺术形态的特殊性有关。中华艺术主要形式为表现艺术,诗、乐、舞为其原始形式,后来也以抒情诗、抒情散文、风景画等为主,这与西方艺术的史诗传统以及后来的戏剧、小说等再现艺术为主要形式不同。但是,中华美学认为,再现艺术也是写情的,只不过这个情不是主体之情,而是“人情物理”。戏剧大师李渔说:“予谓传奇无冷热,只怕不合人情。如其悲欢离合,皆为人情所必至……”(31)“王道本乎人情……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32)这个“人情物理”是客观事理(物理)与主观情理(人情)的统一,仍然打上了情感论的烙印,这与西方美学强调艺术“再现现实”不同。金圣叹也以情论人物形象,说:“彼才子有必至之情”,“然而才子必至之情,则但可藏于才子心中”。(33) 对中华美学乐道论(道之美)和兴情论(情之美)的两重论述,西方评论家认为体现了玄学论和表现论的矛盾。美国学者刘若愚持此说。(34)但刘若愚把中华美学的情感论归结为表现论,是一种误读。中华美学的兴情论,不是主观的情感表现,而是人与世界之间的“感兴”。另一方面,从现代观点看,乐道与兴情有别,它们都建立在道气论的基础上,因此具有蒙昧性。而且,道偏于理性,而情为感性,二者不能完全同一。但是,用中华美学自己的逻辑来解释,并不存在这个矛盾,因为道在天人之际,道是情理一体,所以审美既是乐道,也是兴情。这也就是说,这种矛盾可以用道的两重性来解释。但道与情毕竟有别,道具有理性本质,道与情必然发生冲突。在传统社会早期,情理一体,没有分化,体现为言志说,美学思想与意识形态一致;而中后期,美学思想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产生了分离,于是理(道)与情之间也发生了分离,产生了扬情抑理和扬理抑情的不同趋向。但从总的趋势来说,中华美学的乐道说逐渐趋向于兴情说。 “诗言志”是最初的艺术本质观,兴情论是由言志说演化而来。这里的志,不是一般的思想情感,而是与道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感情,而且志还没有发生情与理的分化,二者融合在一起。由于诗歌等艺术天然地偏向于情感,因此言志说就倾向于表情说。《诗大序》把言志说作了偏向于情感论的解释:“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35)《乐记》认为音乐之美在于情感:“夫乐者,乐也,人情所不能免也。”(36)但此时的主情说还在理与情之间寻找平衡,没有发生冲突。为了避免情与理的冲突,于是儒家美学要以理节情,即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乐记》讲:“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礼者也。”(37)“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38)六朝时期,理性衰微,审美意识觉醒,情从志中分离,兴情说发生。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39)刘勰以道来规定文,认为文乃道的演化物,同时又认为情是文的本性,提出“情文”概念,从而使情与道相符而具有了本体论的地位。《文心雕龙》在大前提上是理性主义的明道论,而在具体展开时又是感性主义的主情论。刘勰在《原道》《征圣》《宗经》三篇中提出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论证,理性的道成为文的本质。但以后各章中既讲言志,又讲缘情,已经偏离了理性的道。这种矛盾体现了审美的情感性与伦理性的矛盾,从而就自觉不自觉地修正和超越了主流意识形态。刘勰也力图调和理与情的矛盾,他说:“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40)情为经,理为纬,“经正而后纬成”,已经向情感论倾斜。以后缘情说成为中国文论的主流,言志说逐渐淡出,而情逐渐取代理成为中华美学的基本范畴。 在传统社会后期,情与道(理)分离,脱离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具有了独立的意义,从而成为本体论的范畴,建立了情本体论。明中叶以后,作为陆王心学的支脉,李贽等把个性、人欲等提升到道的高度加以肯定,于是就产生了情本体的美学。冯梦龙在《情史序》中,认为情乃宇宙本体:“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牵。”(41)他最后提出“立情教”的主张,以“情教”代替“礼教”,意味着情取代理(道)成为本体,成为审美和艺术的依据。汤显祖提倡艺术的“至情”,他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诗之传者,神情合成,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曰传者,亦世所不许也。”(42)袁枚说:“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又必不可朽之诗。”(43)刘熙载把情作为义(理性)的根本,说:“余谓诗或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或寓情于景而情愈深。”(44)此时,以情论诗、文、画等艺术已成潮流。 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以道(理)抑情的倾向。儒家哲学认为,道为形而上者,情为形而下者。韩愈提出情有等级,“情之品有上中下三”,上品之情呵护道德规范,“动而处其中”;中品之情,有所偏差,但力求接近道德规范,“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品之情,放纵情感,不顾道德规范,“亡与甚,直情而行也”。(45)这实际上把审美限定于前两种理性化的感情中,而排斥了后一种纯粹的感情。邵雍就认为,审美有两种,一为“名教之乐”,是理性的审美,遵循道德规范;二为“人世之乐”,为情感审美。他肯定前者而贬低后者。这种思想后来就发展为对审美的排斥,如程颢就讲“作文害道”。但这些极端的理性主义思想并没有成为中华美学的主流。 中华美学把审美的本质限定于情感领域,以情来冲击理性,从而避免了极端理性主义。同时,兴情论有其缺陷,就是没有把现实情感与审美情感加以区别,从而掩蔽了审美的超越性。这个缺陷源于乐道说,道的实用理性化失去了其超越性。因此,乐道说与兴情论有其局限,不能充分说明审美的本质,于是就有神韵说来加以补正。 四、神韵:审美的隐超越性 神韵说来自审美体验,即认为审美的意义不能被充分阐释,具有某种神秘性、超验性。在审美体验中,审美对象包括艺术作品的意义不能完全被说明,还有理性所不能阐释的意义剩余,因此就把这种意义剩余命名为神韵。从本体论上说,存在非现实之物,具有超越性,因此审美指向存在,是一种超越性的活动,不能用现实生存来解释。因此,审美意义就具有超越性,包括超验性。但中华美学对于存在和审美的超越性的体认,还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一方面它把道规定为伦理法则,另一方面又认为道具有超验性,从而产生了矛盾。特别是道家认为道具有虚无性,它不可言说,无声无形,是超验之物。超验性仅为超越性的一个方面,并非其全部意义。超验性源于超越性,由于存在不在场,超越现实,具有虚无性,因此是超验之物。审美作为指向存在的自由生存方式和超越的体验方式,也具有超验性。中华美学用“神”来表达审美的超验性,以把握虚无的道。因此,“神”也指向审美。神在中国语境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外在的神灵,二是指内在的精神,后来又指艺术作品的精神内涵。这几种含义并存甚至相通,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性。儒家的道具有理性本质,它具体化为道德规范,可以理智地把握,一般不以道为神。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如“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把那些不可把握的神秘事物和演化为神秘不可知的超自然之物称呼为神,如“阴阳不测之谓神”(《易传·系辞上》),“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道家认为道先天地而生,是万物的自然本性,而鬼神也由道规定,道具有神性。如老子说道使鬼具有神灵:道先天地生,“神鬼神帝”;“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老子》第六十章)。神也指人的精神,与形(身体)相对。如庄子讲“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庄子·达生》。庄子称得道之人为“神人”,是指恢复了自然天性、摆脱了身体束缚的人。后来,由于中华哲学的天人合一性,外在的神灵与内在的精神通融为一体,进而与事物的本性相通,如讲艺术的“传神”和“神似”。 在中华美学语境中,神的概念也指称艺术的超验性特征。神在审美对象则指称其审美意义,在审美主体则指称其创造性、天才。神与形对称,或指审美主体的精神与身体,或指艺术品的内容和形式,所以讲形神兼备,讲艺术之“传神”、神似贵于形似。这种概念的含混,源于中华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中华哲学认为天人感应,故人与世界都具有某种神性。在美学中,神的概念揭示了审美的意义具有某种超理性、超验性,非形式所能规范,非理智所能穷尽。《易传》把神与妙联系起来,使其具有了审美的含义:“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易传·说卦》)在以后的美学论述中,提出了神思、神会、神韵等概念。神思指审美想象和创造力,如“神思方运,万途竞萌”(《文心雕龙·神思》)。神又指审美对象的精神意义,如“以形写神”“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顾恺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神会指主体精神与审美对象的切合、融会,“神会与物,因心而得”(王昌龄)。严羽把入神作为诗的极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矣。”(46)严羽以入神来对抗理性化的诗学观念,强调了诗的非理性。他进一步以“兴趣”解释了“入神”的涵义:“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矣。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言,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47)所谓入神,就是体现诗歌的非关书、非关理的不可言传的“兴趣”,所谓“兴趣”,即审美理想,它非现实观念,不可理性地把握,只能用神来表达。这里把入神阐释为超脱经验世界的表象,而入于审美的意象世界。严羽又以“妙悟”来阐释“诗而入神”:“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48)这里的妙悟指的是审美体验的超验性,妙与神至此会通,前者侧重审美的非经验性,后者侧重艺术的超理性。李贽从审美对象(竹子)的角度阐释了“神”,并且说审美对象的“神”对审美主体构成了亲和力即“物之爱人”。他说:“且天地之间,凡物皆有神,况以此君虚中直上,而独不神乎!传曰:‘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此君亦然。彼其一遇王子,则疏节奇气,自尔神王,平生挺直凌霜之操,尽成箫韶鸾凤之音,而务欲意味悦己者之容矣。彼又安能孑然独立,穷年瑟瑟,长抱知己之恨乎?由此观之……物之爱人,自古而然矣,而其谁能堪之?”(49)刘大櫆曰:“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50)这里把入神解释为艺术风格的根源。叶燮用神来指称天才:“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然必诗人为神明才慧而见。”(《原诗》)这里的“神明才慧”就是指天才,认为唯有天才能表现物之美。这是从主体方面揭示审美的超越性。神作为主体的心灵,转化为审美对象的内涵,于是就有形神之说,形为审美对象的形式,神成为审美对象的内容。作为审美内涵之神不仅沟通了审美的主体与对象,也揭示了审美的超现实性。王士禛提出“神韵”说,把神和韵结合为一。他说:“七言律句,神韵天然,古人亦不多见。……皆神到不可凑泊。”“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51)这里“神韵”更成为最高的审美标准。韵本来是艺术的审美内涵,可以意会而不可言说,而神韵更突出了韵的审美的超验性,因此,我们借用神韵来作为中华美学的普遍概念来界定美。总之,“神韵”揭示了审美意识的非经验性、神秘性,也揭示了审美意义的超现实性,从而突破了理性主义,接近了超越性的美学思想。 作为中华美学基本概念的“神”与西方美学讲的诗人“神灵凭附”(柏拉图)的迷狂性不同,也与近代的想象说或现代的无意识说(弗洛伊德)不同,它更贴近审美经验,是用来说明审美和艺术的超验性特征的,也隐含着对审美超越性的体认。 注释: ①《孟子·万章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9页。 ②③④⑥[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54、555、556、556页。 ⑤[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选自《中华美学文库·宋辽金卷下》,叶朗总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17页。 ⑦《论语·述而》,《论语·大学·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9页, ⑧《庄子·天运》,选自《中华美学文库·先秦下》,叶朗总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⑨[唐]柳宗元:《邕州马退山茅亭记》,选自《中华美学文库·隋唐五代卷下》,叶朗总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4页。 ⑩《论语·卫灵公》,《论语·大学·中庸》,第188页。 (11)《论语·雍也》,《论语·大学·中庸》,第69页。 (12)《礼记·仲尼燕居》,《礼记》,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355页。 (13)《论语·学而》,《论语·大学·中庸》,第7页。 (14)《论语·雍也》,《论语·大学·中庸》,第66页。 (15)(16)《论语·述而》,《论语·大学·中庸》,第80、81页。 (17)《荀子·乐论》,《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04页。 (18)《庄子·田子方》,《庄子译注》,杨柳桥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0页。 (19)[三国魏]嵇康:《难〈自然好学论〉》,选自《中华美学文库·魏晋南北朝卷上》,叶朗总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 (20)[三国魏]嵇康:《答向子期难养生论》,选自《中华美学文库·魏晋南北朝卷上》,第100页。 (21)《论语·子罕》,《论语·大学·中庸》,第109页。 (22)《论语·述而》,《论语·大学·中庸》,第81页。 (23)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2页。 (24)《左传·庄公十年》,《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14页。 (25)《礼记·乐记》,《礼记》,第254页。 (26)[西晋]陆机:《赠弟士龙诗序》,见《四部丛刊》本《陆士龙文集》卷三所附《兄平原赠》。 (27)[南朝梁]钟嵘:《诗品》,选自《中华美学文库·魏晋南北朝卷下》,叶朗总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6页。 (28)[南朝宋]傅亮:《感物赋序》,中华书局影印本《全宋文》卷二六。 (29)[南朝梁]萧统:《答晋安王书》,中华书局影印本《全梁文》卷二十。 (30)《论语·泰伯》,《论语·大学·中庸》,第92页。 (31)[清]李渔:《闲情偶寄·演习部》,选自《中华美学文库·清代卷上》,叶朗总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2页。 (32)[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上》,选自《中华美学文库·清代卷上》,叶朗总主编,第192页。 (33)[明]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琴心总评》,台北: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99年。 (34)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 (35)《毛诗序》,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1,郭绍虞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3页。 (36)(37)(38)《礼记·乐记》,《礼记》,第270、255、257页。 (39)[西晋]陆机:《文赋》,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1,郭绍虞主编,第170页。 (40)[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文心雕龙》,第368页。 (41)[明]龙子尤:《情史序》,《冯梦龙全集》7,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42)[明]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选自《中华美学文库·明代卷中》,叶朗总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 (43)[清]袁枚:《与程蕺园书》,《袁枚全集》2,《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27页。 (44)[清]刘熙载:《艺概·诗概》,选自《中华美学文库·近代卷上》,叶朗总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1页。 (45)[唐]韩愈:《原性》,选自《中华美学文库·隋唐五代卷下》,叶朗总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46)(47)(48)[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选自《中华美学文库·宋辽金卷下》,第416、418、417页。 (49)[明]李贽:《焚书卷三杂述》,《李温陵集》,明万历年间海虞顾大韶校刻本。 (50)[清]刘大櫆:《论文偶记》,选自《中华美学文库·清代卷中》,叶朗总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1页。 (51)[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选自《中华美学文库·清代卷中》,第125页。标签:美学论文; 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现象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感兴论文; 读书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乐记论文; 至乐论文; 天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