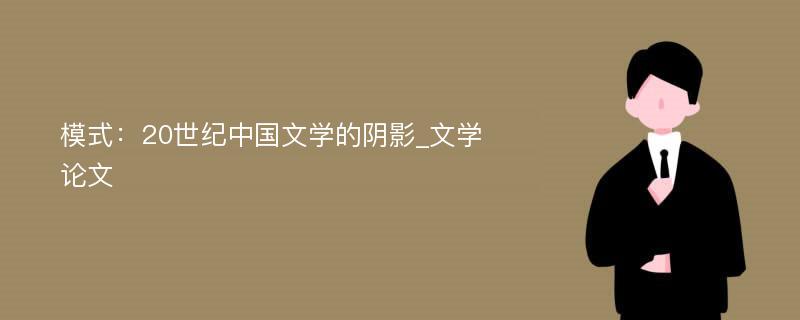
模式化: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阴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阴影论文,模式论文,世纪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01)01-0001-04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模式化却如影随形地与20世纪中国文学同步,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阴影。直到现在,模式化在中国文学领域里仍很严重。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模式化在不同时期有哪些表现?产生模式化的原因何在?如何清除中国文学中的模式化?探讨并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发展和提高21世纪的中国文学,无疑是有相当意义的。
一
1901年至1911辛亥革命的十年,是清王朝企图改革而遭受彻底失败的十年。在这十年间,印刷业大发展,舆论空间有所扩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然而,文学领域(主要是小说领域)里的模式化也同时产生。当时有这样四种模式:
一是揭露官场和社会丑恶的“现形记”模式。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一问世,读者欢迎,传阅者不绝。于是,类似作品蜂起,《新党现形记》、《学生现形记》、《医界现形记》、《商界现形记》、《后官场现形记》、《新官场现形记》、《绅董现形记》、《滑头现形记》、《家庭现形记》……不一而足。但它们仅得《官场现形记》的皮毛,思想浮浅,手法雷同,出版以后,很快就被读者遗忘。
二是表现中国未来的模式化。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上连载《新中国未来记》,反响很大。这一小说的成功,又出现了一批写中国未来的模式化小说:《未来教育史》、《乌托邦游记》、《新中国》、《新纪元》、《未来世界》,等等,全是模仿《新中国未来记》。
三是借古典名著中的人物写改革的模式。1907年,《新水浒》(“西冷冬青演义,谢亭亭长平论”)者出,写侯蒙保奏、宋江受降后,各位头领下山,各干个人营生,大搞改革。吴用办女学堂,雷横办警察,张顺办渔业公会,汤隆谋铁路事业,乐和出席音乐会演奏风琴,卢俊义将家产三分之一充作国民捐等。其后,《新三国志》、《新三国》、《新西游记》、《新金瓶梅》、《新镜花缘》等全都出笼,都是写这些名著中的人物搞改革,又是一个模式。
四是写社会怪现状的模式。自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出版并产生轰动效应后,写社会怪现状的小说又成了“一窝蜂”:《新旧社会之怪现状》、《警察怪现状》、《龙华会怪现状》、《官场怪现状》及类似作品,都是按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模式炮制的,但无一成功。
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成立,上述四大模式的小说顿时销声匿迹。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来前的七、八年时间内,鸳鸯蝴蝶的模式又盛行一时。所谓鸳鸯蝴蝶模式,乃是新的“才子加佳人”的模式。老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而鸳鸯蝴蝶的模式却是,“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1](P.434)比之旧的才子佳人小说,有一点进步,但作为一种模式,也倒了读者的胃口。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新文学取代了旧文学。但是,随着新文学的成功,20世纪二十年代却也出现了“问题小说”和“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冰心以写“问题小说”著名于世,她写了数十篇揭露社会阴暗面、探讨人生道路的“问题小说”,收在《去国》、《超人》、《往事》三个集子里。冰心“只问病源,不开药方”,并无模式。但后来追随冰心写“问题小说”的作者,却以冰心的“问题小说”作为模式,以“爱”和“美”作为人生的指归,并都有一个理想人物。当形成“问题小说”模式后,“问题小说”也就走下坡路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光慈写了《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和《丽莎的哀怨》等中、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大都宣扬个人的革命冒险活动,并带有多角性质的恋爱描写,形成了“革命加恋爱”的模式。这对“革命文学”很有影响,一些人向蒋光慈学习,写“革命加恋爱”的作品不少。
及至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中的口号标语型的模式作品更多。还在1930年,鲁迅即指出,“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并非无产文学。[1](P.376)很可惜,尽管鲁迅批评了这种口号标语型的模式作品,但在左联时期,这一倾向不但没有克服,反而有所发展。左联“以决议的方式规定作家必须写工人,写农民,写苏维埃等等,这种‘拉普’搬来的‘社会定货’式的分配任务的方式,不仅并未进一步拓宽小说表现的领域,其实比‘革命文学就是写革命的文学’的提法更狭隘,更机械。”[2](P.74)口号标语型的模式化作品更多了。
抗日战争时期,文学领域又出现了新的模式:“写将士的英勇,他的笔下就难看到过程底曲折和个性底矛盾,写汉奸就大概使他得到差不多的报应,写青年就准会来一套救亡理论……”。胡风称之为“公式化或概念化的倾向”。他“在公式化的作品里面,我们看得到过多的壮烈词句,一般结论,但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兴奋。”[3](P.79)
新中国成立,中国文学进入新阶段,但模式化依然存在。这一倾向其后不但未能克服,相反却恶性发展了。先是概念化、公式化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的模式;及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更把“三突出”、“主题先行”、“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模式规定为一切文艺创作的准则,把中国文学逼上了绝路。
新时期到来后,二十多年来,创作自由度前所未有地扩大,真正实现了题材多样化和“百花齐放”,但模式化倾向仍然存在。仅以八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而言,五大模式触目可见:
一种模式是,写改革开放中的两种主张、两种方法之间的斗争,几经曲折,最后正确主张、正确方法胜利。这实际上是以往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斗争的翻版。
一种模式是,写改革开放中某些聪明人得风气之先,率先“下海”,他们与掌权的官员互相利用,彼此勾结,多次取得贷款,“空手套白狼”,在房地产、股票、期货等市场上兴风作浪,大大地捞了一把,不几年就成了亿万富翁。但后来或由于算计的“一着不慎”,或由于“窝里斗”,或由于知情人的举报,或由于外国大商人的出其不意的一击,仍不免覆灭的命运。
一种模式是,写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成了新的冒险家的乐园。这些冒险家,或出卖批文,或哄骗集资,或卖官鬻职,或公款私用,顿时成了“大款”“大腕”。他们出入赌场,一掷万金,遗弃糟糠,金屋藏娇,在外国开账号,置家产,花钱如流水。即使作品最后写了这些人锒铛入狱的下场,但由于作品热衷于挑逗读者的感官刺激,却仍然使部分读者想入非非,其社会效果是很不好的。
一种模式是,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某些人大搞腐败,却出了一个廉洁无私的好干部。他和腐败分子斗争、较量多次,最后清廉干部获胜,贪官污吏受法律制裁,大快人心。但读者读了这样的反腐败的模式小说后还是产生困惑,何以现实生活中的腐败现象屡反不绝,变本加厉呢?
一种模式是,几个少男少女,莫名其妙地一见倾心,热烈爱恋,并形成多角关系,终因感情基础不牢而先后分崩离析,跌入爱情悲剧。这类长篇被称为“新言情小说”。
由是观之,“模式化”的确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顽症”。如果不痛下决心疗治,它在21世纪还将给中国文学造成损失。
二
要解决文学中的模式化问题,得先找出产生模式化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对“文艺是宣传”的误解。从晚清文学改良开始,不同时期的文艺领导人,都以为“文艺是宣传”,而宣传就免不了口号、标语、公式、概念,因此,他们对宣传了某种思想但模式化的作品,并不反对,谁要反对了,他们心里其实是不高兴的。所以,胡风说过,在现实主义阵营里反对公式主义、客观主义的斗争,“是使人烫手的”,会在一些人中间引起“不安和反感”。[4](P.301)“文艺是宣传”这一问题,鲁迅早就作过精辟的论述:“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1](P.298)但是,鲁迅的这一金玉良言,许多作家都忘记了,许多文艺领导人也忘记了。
第二,与对“文艺是宣传”的误解相联系,许多作家在创作时并没有把文学的特征置于创作注意力的中心,而是把某个主题、某种思想、某项政策、某些概念作为创作注意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必然会产生模式化。然而,文学是通过感性形象反映生活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可以而且必须发挥能动作用;作家在创作时必须凭借语言这一特殊的艺术物质材料,要在语言上下大力气;文学必然会对读者或观众、听众的思想感情发生影响。如果作家始终把这些文学的特征置于创作注意力的中心,他的创作就一定会有某种创造性,模式化作品也就不会产生。
模式化之所以产生,还因为长期以来,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人们总是以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强调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梁启超要求文艺直接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服务;章炳麟、孙中山要文艺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要文学为以反帝反封建为旨归的“新文化运动”服务;“左联”要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抗日战争时期要文艺为抗战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更明白提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这一情况,直到新时期到来后才有改变,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而只要求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新时期到来后,模式化作品虽然还有但已大大减少,就是因为已经改变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
模式化作品之所以在晚清和民国初期大量产生,之所以在新时期搞了市场经济后产生,还因为作家经不起市场的诱惑、金钱的吸引。晚清和民国初期,大城市里(特别是在上海)搞的是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而市场经济是把双面刃,一方面它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物欲也会淹没某些作家的艺术良心。当着某一作品获得成功后,市场一时需要类似的作品,于是文化经纪人、出版单位也就立即向作家“定货”,召唤作家对已获成功的作品如法炮制,模式化作品也因此大量出现。
最后,模式化作品之所以出现,还因为一部分作家生活底子很薄,只是关起门来在家里创作,艺术想象力日趋枯竭。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只能依葫芦画瓢,或则胡编乱造。但由于他生活底子薄,艺术想象力又趋枯竭,这种胡编乱造,只能是不自觉地根据某些模式七拼八凑,仍然受到模式的桎梏,编造出来的还是模式作品。
自然,模式化之所以产生,可能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但我认为,上述五种原因是主要的。
三
彻底克服模式化,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是,只要定下目标,根绝模式化,而且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又明确解决下述问题,那么,基本上克服模式化是可以在十到二十年时间里做到的。
一是要大力提倡文学创作的“原创性”。凡作家首次应用的素材、手法、塑造人物形象的范式、艺术形式,对习见的文学主题作出的新阐释,以及对“母题”的创造,都可称为“原创”。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之于历史演义小说,即为历史演义的“母题”作品。获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四部长篇,其中阿来的《尘埃落定》,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1、2)》,即为“母题”作品。而张平的《抉择》,虽非“母题”作品,但在对反腐败主题所作出的新阐释方面,却有原创性。王安忆的《长恨歌》写一个四十年代“上海小姐”的一生命运,这种写法并不“原创”,但王安忆认为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这一历史观却具“原始性”,它照亮了《长恨歌》。在文学史上留下篇页的作品都有或多或少的“原创性”。“原创性”越大,其文学价值也越高。鲁迅的《阿Q正传》即具有中国百年文学无人能够企及的最大的原创性。当中国所有的作家在创作时都刻骨缕心地追求“原创性”时,模式化自然也就绝迹了。
再就是在创作过程中一定要讲究艺术规律。在我看来,这样几个艺术规律是不同艺术部门的共有规律:即艺术创作要用形象思维的规律;艺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的规律;倾向性可以而且必须寓于形象之中,并在形象体系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规律;在艺术领域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的规律;既要继承艺术领域内一切有用的东西,又要革新、独创的规律。在以写人、叙事为主的小说、戏剧、电影、电视中,还得讲究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应该完美融合的规律。如果从事的是现实主义创作的话,那么还得讲究这一条艺术规律: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总之,当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自始至终地讲究和遵循艺术规律时,模式化作品自可大大减少。
三是要发扬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模式化之所以产生,从思维方式上来看,作家搞的是惯性思维,线性思维,模式思维,而不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曹禺在旧社会写的《雷雨》、《北京人》、《原野》、《日出》,因其具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而成为经典之作,但在全国解放后写的《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却因为缺少了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搞了模式思维、惯性思维、线性思维而为人诟病。曹禺创作的经验教训是值得人们记取的。作家而无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你就干脆不要当作家,不要搞创作,否则,写出来的作品只能堕于模式。
四是仍旧应该提倡到生活中去,不断加深生活的积累,加厚生活的底子。人类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经典说法仍然是创作真理。作家可以坐在家里创作,但不能老是“坐家”,不到生活中去。当作家与“坐家”划上等号,不再到生活中去,不再从现实生活中获得文艺创作的源泉时(即使是搞历史、神话、科幻题材的创作,作家也得通过熟悉、了解现实生活来加深对历史、神话的理解,汲取科学幻想的灵感),他怎么能摆脱模式的桎梏呢?
五是不要横加干涉。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所致的《祝词》中强调,“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5](P.213)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已经说了21年了,但文学领域里还不能说“横加干涉”的现象已经清除。“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创作方式仍然有人在使用,也因此,模式化的作品不断被挤压出来。作为领导,再也不要对文艺创作“横加干涉”了。
我们相信,中国文学进入21世纪后,优秀的、杰出的、传世的作品会越来越多,而模式化这一顽症终将会得到根治而在文学领域里逐步绝迹!
【收稿日期】2000-1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