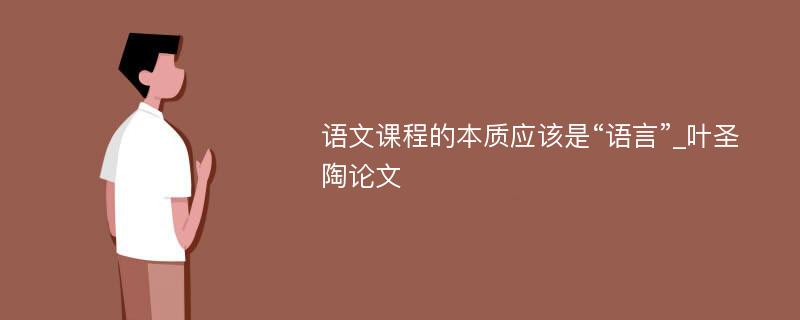
语文课程性质当是“言语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言语论文,语文课程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制订语文课程标准,首先要明确课程性质是什么。尽管要回答这一问题也许十分艰难,但这毫无疑问的是一个首当其冲的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终极性的命题,是一个核心概念,是一个标杆,是思维的逻辑起点,它制导着课程的整体建构。任何的含糊其词、折中迁就,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当我们作这一思考的时候,很可能不由自主地陷进“工具论”的泥沼。因为在语文界,“语文是一种工具”的认识已经深入人心,任何要否定它的企图都会遭到近乎本能的、非理性的顽强抵抗。这仿佛是一道不容逾越的“话语底线”。因为“工具论”据说是叶圣陶的定性。
其实早在叶圣陶之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就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对于语言,他也是“把它看做仅仅是思维的工具,是可以离思维而独立的东西”。(参见《陈元晖文集》中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第359页)
叶圣陶在1924年讲到“说话”是一种“独占重要”的“工具”(参见叶圣陶《说话训练》)。在1942年又明确说“国文是一种工具”(参见叶圣陶《认识国文教学》)。及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叶老较多的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诠释“工具性”。1953年他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语言的学说,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语言教育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让学生认识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学会正确地熟练地运用语言这个工具,让他们能够在参加各种斗争的时候,参加各种共同工作的时候,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正确地理解别人的语言,因而能正确地执行任务,做好工作。语言是形成思想的工具,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叶圣陶《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人民教育》,1955年第8期。)1962年他又明确地指出:“我们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叶圣陶《认真学习语文》)到了1978年,他更是从提高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高度作了新的表述:“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叶圣陶《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进语文教学》)可以看出,叶老的语文“工具论”实际上是语言“工具论”,这应该说是代表了当时我国学术界的认识水平的。然而,在今天看来,“语言”跟“语文”(叶圣陶认为“口头说的是‘语’,笔下写的是‘文”’——叶圣陶《语文是一门怎样的功课》)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语文”的属性应是“言语”,而非“语言”(二者的区别见下文)。只因为当时在认识上还没有这种区分,以致在表达上容易产生混淆,因而也造成了许多人的误解:以为“语言”跟“语文”的属性相同,以为“语文”跟“语文课程”属性相同,认为“语文”是一种工具,就等于说“语文课程”是一种工具,其实,叶老说的“国文科”,才是“语文课程”。
叶老曾明确指出:“语言是一种工具,工具是用来达到某个目的的。工具不是目的。”(叶圣陶《认真学习语文》)可见,他并没有把“工具论”作为语文本体论的全部。他的语文目的论是什么呢?是为生活、为实用、为应用的语言运用。他说:“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一种奢侈的要求,实在是现代公民必须具有的一种生活能力。”(叶圣陶《略谈学习国文》)“听、说、读、写四项缺一不可,学生都得学好。这是生活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也是参加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叶圣陶《听、说、读、写都重要》)他还多次强调“课内作文最好令作应需之文”“培养切实应用之作文能力”等。这种个人应生活之需的“语言”的具体运用和表现,实际上指的就是“言语”(参见下文)。叶老的语文本体论是以“语言”为手段,以“应需”的“言语”为旨归的。可见,叶老的“工具论”不等于他的语文本体论。
今天的语文界之所以据守着“工具论”的堡垒,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将其视为叶圣陶思想的精髓,殊不知“工具论”既不能代表叶圣陶语文本体论的完整内涵,也不是叶圣陶的专利,真可谓阴差阳错“工具论”!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语言(语文)是一种工具”这一认识的科学性早就受到广泛的质疑。语言是文化的地质层、语言就是思想、语言就是存在、语言召唤人、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等见解,“语言威能”“话语权力”“语言自己说话”等观念,在20世纪的哲学界、语言学界、写作学界日益被人们所发现与接受。语言业已成为哲学的本体,语言论哲学(语言逻各斯)已取代了理性论哲学的地位,语言不再被视为是任人呼来唤去的婢女,而成为人类精神家园的主宰。对这种发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哲学变革,“语言论”转向的创始者柏格曼这样说:“所有的语言论哲学家,都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这是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是日常语言哲学家与理想语言哲学家共同一致的关于方法的基本出发点。”(王一川《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35页)海德格尔认为本真的言说首先是聆听,聆听语言的言说。语言比我们强大,因此也更有分量。卡西尔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言语活动决定了我们所有其他的活动。我们的知觉、直观和概念都是和我们母语的语词和言语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要解除语词与事物间的这种联结,是极为艰难的。”(〔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70页)福柯认为具体的个人将不再被看成是话语及知识的组织者;相反,远远地先于我们个人身份而存在的话语作为一组正式的关系,将构成话语使用者的组织原则。非个人的、无作者的话语将成为知识的主要来源。(〔美〕大卫·宁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99页)沃尔夫也谈到人不仅生活在物质世界和社会活动的世界中,而且生活在自己语言的世界中。客观世界按照语言世界而建立。语言改变,客观世界也随之改变。准确些说,客观世界依然如故,而在人的思想中它已是另外一个世界。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和划分世界。我们获得祖国语言的同时,无意识地获得了一定的思维方式。如果牛顿不用英语思维,而用印第安语思维,在他的物理学中,世界构造的图景将是另一个样子。(王德春《现代语言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第215页)
如果说这些都还只是一种理论“猜想”的话,那么,在语言运用实践中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在《日瓦戈医生》这一作品中,讲到诗人日瓦戈有一段时间避居在瓦里基诺的旧宅中,夜里秉烛写作时的情形,对阐明“语言自己说话”的观点也不无启示:
在这样的时刻,决定艺术创作的诸种力量的关系仿佛倒转了。主导力量不再是艺术家所欲表达的心态,而是他欲借以表达心态的语言本身。语言,美和意义的乡土,自己开始思考、说话……就像巨大的河流靠自己的运动冲磨岩石带动机轮一样,语言之流在它流经之处按照自己的法则创造着韵律,创造着无数其他的联系……(参见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15页)
不论上述观点是否准确地揭示了语言的性质,但它对语言仅仅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的偏狭理解、对语言“工具性”认知所造成的强大冲击则是不言而喻的!诚如有人所言:“流行见解认为语言由人支配表达人的内在思想感情。这种见解至少要作大幅度的调整才能说明实情。特定词句受语言体系的制约更甚于受特定心态的制约。”“把语言当作表达工具这种观念是很成问题的。其实一般地把语言理解为工具的见解本身就很成问题。”海德格尔说:“把语言定义为交流信息促进理解的工具……只不过指点出了语言本质的一种效用。”(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15~316页)即使我们煞费苦心地为“工具”加上了“交际与思维”的定语,只要把语言仍然看做是外在于思想的纯粹的“媒介”物,也就无法填平语文“工具论”业已坍塌的地基。
撇开这一切都不论,要说语言(语文)是“工具”,哲学、思维学、逻辑学、数学等未尝就不是“工具”,这些学科又该作何定性呢?比较而言,这些学科的“工具性”似乎也都不弱,是否也都要作“工具”的定性呢?如果这些学科都是一种“工具”,语言(语文)是一种“工具”的定性又有什么意义呢?单凭这一点,语言(语文)“工具论”就可以休矣。
然而,“工具”告退,“人文”方滋。
将语文定性为“人文性”,就跟将其定性为“政治性”一样地经不起推敲。如果说当年将语文定性为“政治性”是“左倾”产物的话,而今的“人文性”定性,则是非理性、非逻辑的误判。
首先,“人文性”也不是语文的特殊属性。“人文性”是一切人文学科(甚至也包括自然科学学科)的共性。用一种普遍的属性为其中的某一具体学科定性,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至今还很难给“人文性”找到确切的定义,但其内涵容纳了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文明创造,这种认识想必不会有太多的非议。假如语文的特性是“人文性”,那么,“语文”就得能装下“人类的一切文明创造”的成果。由于“语文”本身就包含在这“一切”之中,只不过是“一切”之下,要用下位概念来包含上位概念,用普遍性来界定特殊性,这岂不是一种逻辑上的混乱吗?要装下这“一切”,得是“文化史”或“文明史”,“语文”撑死也没这么大的胃口。
一定有人会说,语文具有“人文性”,并非是语文等于“人文性”。是的,语文是具有“人文性”,但是,能否告诉我哪一门学科不具有“人文性”?既然“人文性”的外延囊括了所有的学科,说“语文”具有“人文性”,岂不是比说语文具有“工具性”更没有道理?一定还有人要说,别的学科虽然也有“人文性”,可是语文学科“人文性”含量最高。尽管这种争论没有什么价值,但为了遵循对话的“礼貌原则”,还是答曰:比语文更具“人文性”的除了“文化史”或“文明史”外,还有科学史、哲学史以至美学史等,在中学,历史与社会、思想政治、外语、科学、艺术等课程的“人文性”也都不弱,为什么这些学科的“人文性”可以一概略而不计,单单要给语文学科作“人文性”的定性呢?
其次,“人文性”主要体现在“文学教育”中的观点,又是一种逻辑的混乱。显然,“人文性”不等于“文学性”。文学的“人文性”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七侠五义》与《红楼梦》的“人文性”不可同日而语;非文学的经典文本也同样可能具有很强的“人文性”,传统文化中各个思想、学术流派的代表作,其“人文性”含量决不亚于优秀的文学文本。难道能说《论语》的人文价值就比《离骚》低吗?以增加教材中的文学作品的量来增强语文课程的“人文性”的做法,实在是于理无据的。当然,如果从加强阅读文本的趣味性来说,文学文本具有较强的语言魅力,可令学生从审美的愉悦中得到“人文性”熏陶,这又另当别论。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人文性”等于“文学教育”,更不能将此作为把语文课程性质确定为“人文性”的理由。
说语文有“人文性”,则可;将语文定性为“人文性”,则不可;将“人文性”等同于“文学性”,则是谬见。
那么,语文课程性质究竟是什么呢?所谓语文课程性质,指的自然不是语文课程的所有的属性,或语文课程和其他课程共有的属性,而是指语文课程的最基本的特征,指语文课程的特殊属牲,即语文区别于其他课程的“种差”。
——语文课程的“种差”就是“言语性”。
通俗地说,“言语”,指的是个人在特定语境中的具体的语言运用和表现。“语言”来自于“言语”,“言语”包含了“语言”。“言语性”,是指语文课程所独具的学习“个人在特定语境中的具体的语言运用和表现”的特殊属性。简而言之,语文课程的特性,即学习言语(包括学习语言,但终极目的是学习言语)。学习言语,包括学习个人的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实际运用和表现。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将语言与言语作这样的界定:
语言以许多储存于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记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有点像把同样的词典分发给每个人使用。所以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储存人的意志之外的。语言的这种存在方式可表以如下的公式:
1+1+1+……=1(集体模型)
言语在这同一集体中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其中包括:(a)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b)实现这些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行为。
所以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在这里只有许多特殊情况的总和,其公式如下:
(1+1'+1''+1'''……)(〔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6,第41~42页)
法国符号学家巴尔特进一步阐释说:“与作为制度和系统的语言(Langue)相比,言语(Parole,语言之言)基本上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和实现行为。构成言语的首先是‘说话者赖以运用语言规则表达其个人思想的组合’(也可把这种延伸的言语称为话语)……而且正是由于言语主要是一种组合,与其相对应的才是个人行为,而不是纯粹的创新。”(〔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99,第3页)由此可见,言语包含着语言,是语言的运用,是语言的个人组合,是表达个人思想的组合,是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这种组合具有无限多样性),是个人对语言的选择和实现行为。试问,语文课程剔除了人文学科的共性特征,其最本质、最纯粹的属性不就是学习个人在特定语境中的具体的语言运用和表现吗?不就是个人对语言的选择和实现行为吗?
“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就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实即学习“个人的语言组合”。“口头语言的说和听,书面语言的读和写”都是学习“个人的语言组合”,即是“言语”的学习。语文课程也只有在“言语性”上,才能达成与其他学科根本的区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叶圣陶说:“从国文科,咱们将得到什么知识,养成什么习惯呢?简括地说,只有两项,一项是阅读,又一项是写作。……这两项的知识和习惯,他种学科是不负授予和训练的责任的,这是国文科的专责。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认清楚: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从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就是学习国文的目标。”(叶圣陶《略谈学习国文》)叶老在这里所说的“国文科的专责”和“学习国文的目标”,才是真正针对语文课程性质而发的。
把语文课程性质确定为“言语性”,将使语文教学回归到本体。“言语”既是语文课程学习的内容构成,也是语文课程的目的指向。这种定性并不意味着对“人文性”的否定。只是说“言语性”体现了语文课程的特殊属性,而“人文性”则是一种共性特征。在语文教学中,应该用“言语性”去容纳、彰显“人文性”。良好的“言语性”势必内隐着丰富的“人文性”。
以“言语性”定位,就是表明在语文课程中应以学生“言语”能力的发展为本位。学生在对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学习和运用的过程中,势必也会自然地汲取积淀于“言语”中的历史、文化、思想、情感、思维方式等内涵,增进自身的人文修养和综合学养。在“言语性”上再并列其他的属性,只能有一个结果,这就是两败俱伤。
以“言语性”定位,语文课程就有了符合其本体特征的价值取向。“言语性”的内涵既单纯又丰富,在这个总的目标下,建造语文课程的整体构架,也就能较为容易地做到纲举目张,做到整体上的有机统一,系统自洽。
试问,语文课程不是学习个人的语言运用和表现,不是让每一个学生养成听、读、说、写的能力,语文课程的性质不是“言语性”,不是指向学生的“言语”上的自我实现,还能是什么呢?
注:除特别注明的以外,本文涉及的叶圣陶文章均见《叶圣陶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