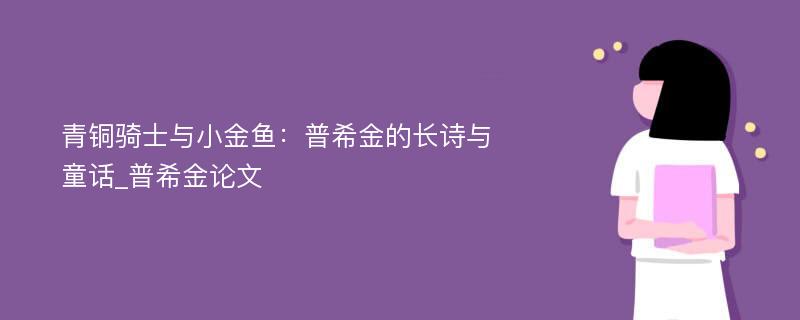
铜骑士与小金鱼——普希金两位一体的长诗与童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希金论文,长诗论文,两位论文,骑士论文,童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文化有一个特点,可以称之为意义的回溯性,或者说是逆向意义作用规律。这是指,每一部后来的作品都可以用前面的作品来解释并改变其意义。
于是乎,据博尔赫斯看来,卡夫卡拉近了在他之前完全不同,彼此陌生的作家的距离。例如,古希腊哲学家芝诺、一世纪中国作家韩愈、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与法国散文家莱昂·布洛瓦之间有何相同之处?从古希腊关于始终赶不上乌龟的阿喀琉斯的寓言来看,或者从古代中国关于独角兽的寓言来看①,他们在卡夫卡很久之前就是卡夫卡派。假如不是卡夫卡,所有这些作者和作品在逝去的文化中就会成为孤灯别盏,现在他们却变为共同传统链条上的一环。他们彼此不相似,可他们中的每一位又在某些方面同卡夫卡相似。“他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些卡夫卡因素。但如果没有卡夫卡,我们就发现不了他们的相似之处,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相似之处。……问题的实质在于,每一个作家自己在创造着自己的前辈。”[1](91)
本章深入考察意义回溯的一种情况,即生活时代靠后的一位作者使得另一位作者的两部作品突然具有了相似性。似乎,普希金作品的每一行,甚至是草稿,就其影响和借用而言,方方面面已被研究透彻,更不用说写于同一时期,1833年波尔金诺之秋的《铜骑士》与《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经典作品。不过,据我所知,还无人对这两部作品的构思、结构及形象体系进行过比较。的确,富有教益的童话与历史诗学思维的杰作之间又有何共通之处呢?
比较普希金的这两部作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竟成了我意想不到的媒介。或许,之所以先前无人比较这两部作品,是因为二者明显的交叉点恰恰位于普希金本人的创作之外,表现在他对其后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影响方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个奇异的场景,在他的作品中至少重复了三次。这就是彼得堡的幻象,这一建筑上美轮美奂的幻象似乎突然蒸发,正在与腾腾的雾气一道消失:留下的只有一片沼泽,曾几何时,这座童话般的城市就矗立于其上。在《脆弱的心》与《诗歌与散文中的彼得堡之梦》中这一情节类似,而在《少年》中(第1部,第8章,第1节)则又补充了一个细节:整个彼得堡都升入空中,只剩下彼得的纪念像,直挺挺陷入泥潭之中的“铜骑士”。
“在这片雾气笼罩之中,我的面前多次出现了令人惊奇却又挥之不去的幻象:要是这片雾气飞散开来,向上空飘移,这座湿滑的城市是否会随之似烟雾般消失,仅剩下先前芬兰湾的沼泽?而在沼泽中间,似乎是为了点缀,矗立着一尊骑在气喘吁吁、疲惫不堪的马上的青铜骑士像。”[2](113)
自然,这一以彼得堡为主题的幻像同普希金的《铜骑士》相似,后者是俄罗斯文学中所有彼得堡主题的原型。城市似乎暂时形将消失,卷入肆虐的涅瓦河水之下,沉入其不稳固的地基之中……不过,要使城市完全消失,原址依旧笼罩着“先前芬兰湾的沼泽”上的空旷荒芜,要使结尾回拢到开端,暴露出中间所有假象和“蓄意之处”,还缺乏某种最后的,决定性的发展。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幻象和幻想中的城市消失这一主题也与普希金的某部作品相关,但不是《铜骑士》……
此时我想起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乍一看,它似乎是一部无关宏旨的作品,仅仅是外部情节主线类似于《铜骑士》。之所以在破旧的小屋原址出现高楼,皇宫,就是为了日后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老太婆守着自己的破木盆坐在以前小屋的门槛上。紧接着,主题逐步展开,长诗与童话之间那种深奥的形象对应体系显露出来,似乎这是一部作品的两种写法。
2
无论长诗,抑或童话,故事情节都在海边展开,人的权力意志与大自然的自由本性,这对立双方势均力敌。开头描写了日常生存的贫穷与困苦,很快主人公自负的思想渗入进来:
“他们住一间破旧的小屋,
三十三年就那么度过——
老头儿出海撒网打鱼,
老太婆纺线在家里呆着。”[3](628)(《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在这里过去那大自然的
可怜的继子,芬兰的渔夫,
孤凄地在低湿的河岸上,
向着不可知的水中投入
他那多年的破旧的渔网,……”[4](645)
(《铜骑士》)
当然,长诗就其形象结构而言远比童话丰富,但起始环境的主题却吻合,这一环境以平时鲜用,具有修辞特色的词汇勾勒出来:“破旧的”和“渔网”。这就是两部作品开头中地处偏远、湮没无闻、原始存在的自然环境,它始终未变。
长诗形象体系中对立的一极:“年轻的城市,它是北国的精华与奇迹,从黑暗的森林、从沼泽地、华丽地傲然地高高耸起”(《铜骑士》),在童话中也一模一样,蔚蓝的大海边,在先前破旧的小屋原址上一座比一座华丽的住房拔地而起:先是座“宽敞的房子”,随后是幢“高楼”,最后则是座“皇宫”。(《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故事的整个视觉背景似乎在发生变化:“头上戴着一顶绸缎帽……镶宝石的戒指光彩闪烁,脚上穿的是一双红皮靴。”就连以前仅有黢黑小屋的空旷之地也具有了色彩:“浓绿色的花园”,“赛如玫瑰的少女的面庞”……(《铜骑士》)。此外,长诗与童话中均介绍了那时“皇室”生活的某种秩序,这种生活在曾经死气沉沉的岸边展示开来。
开端——豪华的建筑
“那是什么?是一座高楼。……
怎么?眼前是一座宫殿!”[3](632,634)(《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壮丽的宫殿、矗立的高楼
屹立着……”[4](465)(《铜骑士》)
随后——奢侈的盛宴
“给她斟上外国来的美酒,
她品尝印花的蜜糖饼干……”[3](634)(《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浮起泡沫的酒杯的嘶鸣
和彭式的淡青色的火焰。”[4](467)
(《铜骑士》)
最后是武装护卫
“四周的卫士个个威武,
肩膀上扛着闪光的利斧。”[3](634)(《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和那步兵与骑兵部队的
美好的整齐划一的穿戴……”[4](467)(《铜骑士》)
无论是长诗中的“战争首都”,还是童话中的“皇宫”都同样受到全副武装的队列,威武卫士的保护。甚至还召来了公职阶层保护帝位:“大臣与贵族”,“将军”,“高贵官人们”。长诗中可信地,而在童话中虚拟地勾画出米尔权力巩固,正迈上更高的台阶。
根据未进入童话定稿的异文,登上王位的老太婆坐得更高:坐到了巴比伦塔之上。
他的面前矗立着巴比伦塔。
在塔的最顶端
坐着他的老太婆。
童话中的巴比伦塔主题从何而来?正如所知,普希金1833年10月时创作的《铜骑士》,是对在此之前不久发表的亚·密茨凯维奇的长诗《先人祭》(1832)第三部的辩论性回应。在《奥列士凯维奇。1824年彼得堡洪水前一天》的片段中,彼得堡被同巴比伦相比较。巴比伦主题是否由此移植入童话?童话中提到巴比伦使其同《铜骑士》的比较显得更加可信。
谁活到清晨,他就是伟大奇迹的见证者,
那将是第二次,但却不是最后一次考验:
上帝要动摇亚述人王权的等级,
上帝要动摇巴比伦的根基,
上帝啊,可别让我们看到第三次啊!
住在彼得堡,研究圣经和喀巴拉的波兰艺术家奥列士凯维奇预言,彼得堡会同古代世界的首都一样被摧毁,随之而来的将是“第三次”考验:世界末日和最后的审判。在密茨凯维奇的这个片段中,彼得堡被别有寓意地称为“巴比伦”这类似于《启示录》中把当时异教世界的首都罗马称为“巴比伦”。②
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不是普希金与密茨凯维奇具体的分歧与一致,而是不断膨胀的权力主题居然延伸到在先前仅是“黑暗与沼泽”,“破旧的小屋”和“穷苦的芬兰人的安息所”之地建巴比伦或巴比伦塔。
3
从两部作品“权力”本身的角度来看,驯服陌生的自然力这一点至关重要。无论是长诗中的彼得,还是童话中的老太婆都达到了人间权力的极限,前者以“新首都”为象征,后者以“皇宫”为象征,不过要达到这一极限还需要主宰另一个力量,大海的力量。这就为两部作品具有决定性的情节发展奠定了基础。老太婆不满足自己世俗的王位,依靠小金鱼的支配力,她的小人得志是通过以下的宿愿完成的:“自由女王不合我的心,我要做海上的女霸主,我要在海洋上面生活,要让小金鱼听我调遣,要让小金鱼来服侍我!”[3](635)这也正是使真正的海上主宰无法忍受的胆大妄为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普希金借用了格林兄弟童话《渔夫和他的妻子》中的情节,这一点众所周知。在格林兄弟的童话中,未了,渔夫的妻子表达了统治月亮和太阳,成为世界主宰的愿望。③在普希金那里,生动的情节不是按直线平铺,而是按封闭的圆形轨道发展:老太婆从大海的主宰处获得权力,如今却想自己统治大海。这一情节为格林兄弟的童话中所无,它拉开了普希金童话与其德国源头的距离,却直接拉近了其与长诗的距离。要知道长诗中描写的彼得的主要事迹不是征服人间王国,而是征服人们陌生的大海,彼得欲借建彼得堡之势成为水国之王,“要我们在这海岸上站稳”。在序曲结尾处,作者总结了彼得荣耀的事业,宣告:“自然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愿它在你面前百依百顺;/让芬兰湾的海波忘掉了/自己往昔的奴役与仇恨,/而不要挑起无用的敌意/来搅扰彼得的永恒的梦!”[4](467-468)彼得向全民允诺在“新的波浪”上大排筵宴,实质上就是庆祝战胜大海。
两部作品“上升”曲线的高潮如下:“我要做海上的女霸主”,“要我们在这海岸上站稳”。紧接着,被征服的自然应当自愿服从,接受人的统治:“自然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愿它在你面前百依百顺……”,“要让小金鱼听我调遣……”
与此同时,还有一条“下行”线贯穿两部作品:回应不断增长的对权力的贪婪欲望——“被战胜的”自然的回击。它对人不断增加的愤怒,汹涌沸腾的脾性与将至的惩罚通过同样的强度逐渐传达出来。虽然童话中的描绘比长诗中显得更为清楚、细腻。
“……只见海上轻轻泛着波浪……
……蓝色的海水已变得浑浊……
……蓝色的大海已不再平静……
……蓝色的大海已经变得黑暗……
……海上起了黑色风暴:
暴风掀起了惊涛骇浪,
奔腾汹涌,怒吼呼啸。”(《渔夫与金鱼的故事》)
“涅瓦河用它那惊涛恶浪
……
正像一个病人在病床上
一刻不停地不安地翻转。
涅瓦河的河水被不断掀起,
像一锅开水般翻转沸腾,……
……翻起了像高山似的大浪,
而且越来越凶,不可一世,
在那里,风暴不停地怒吼,
房屋的碎片在到处漂流……”(《铜骑士》)
两部作品中不仅因暴怒而毁灭沿岸所有人建筑的海水画面吻合,而且这一画面中个别的,极富特色的细节也雷同:表达声音和颜色的动词与修饰语。为了强调两部作品的内在联系,我们将相应的片断排成两列:左边是童话,右边是长诗。
波涛涌动用有表现力的动词“掀起”表达:
《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铜骑士》
暴风掀起了惊涛骇浪,涅瓦河的河水被不断掀起
声响—“怒吼”
怒吼呼啸风暴不停地怒吼
风也在吹着,悲凄地怒吼
色调—“黑色”,“阴暗(忧郁)”
蓝色的大海已经变得黑暗 在阴暗的彼得的城上空
海上起了黑色风暴忧郁的巨浪
情感状态—“不平静”,“愤怒的状态”
蓝色的大海已不再平静一刻不停地不安地翻转
暴风掀起了惊涛骇浪雨在窗户上急骤地猛敲
在将童话语言转换成长诗语言时,两部作品内容的一致性突显出来。一部作品中装入了另一部的主要形象。童话中:“暴风掀起了惊涛骇浪,奔腾汹涌,怒吼呼啸。”长诗中:“围攻啊!冲击!汹涌的波涛……”童话是将长诗深邃的历史理论构思改写成民间创作形象最简单的语言的一种方式。
让我们比较一下两部作品的结尾。童话的结尾极其精炼,是向开头的简单回拢。“瞧:眼前还是那间小屋,老太婆在门槛上坐着,守着个木盆又旧又破。”[3](636)小金鱼,这一自由的大海的主宰,收回了赐予不知好歹的人间“女王”的一切。
其实,《铜骑士》也有一个环形结构:结尾与开头合拢。故事情节转到饱受洪灾之苦的城市,并最终向“长满鲜苔泥沼的岸”上先前的贫困生活回拢。
“……在那里—在巨浪旁边,
差不多就在那海湾跟前—
有一颗柳树,有一段短墙,
墙内有一所破旧的小房……”[4](475)
在半个世界的首都显现出原始的,赤裸裸的现实的特点,似乎所有的建筑,宫廷奢华的摆设也不过是被暴怒的涅瓦河冲走的幻象。洪灾虽然未从实体上摧毁城市,但却暴露了其形而上之虚幻,仅仅在洪灾过后,我们才发现这块土地在建成彼得堡之前的样子。长诗结尾暴露出最初的,彼得之前的,彼得堡之前的情况:沿岸到处都是一片荒芜的景象,似乎它是疯子叶甫盖尼梦中所见,或者仅是彼得本人头脑中的伟大思想。
“在海边
望得见一座小岛。有时候
渔夫捕鱼捕得为时太晚,
拖着渔网就在那里停泊,
准备他们的可怜的晚饭……
……荒岛。那里没有
长起一茎青草。洪水泛滥,
冲到那里,把破烂的茅屋
也给冲倒。在汪洋大水上
它的残迹好像黑色的灌木。
去年春天有人把这破烂
已用帆船运走。一片荒芜,
一切尽毁。而我们的疯人
人们发现,死在茅屋门口,
就在这里,人们为了上帝
掩埋掉他的僵冷的尸首。”[4](485-486)
长诗开头与结尾的遥相呼应虽然不像童话中那么明显,却也意义重大。序曲中彼得站在“碧浪无际的河岸上”,结尾处叶甫盖尼在“没有长起一茎青草”的“荒岛”上寻觅着自己的归宿。古时渔夫向不可知的水中投入自己的破旧的渔网,在长诗的结尾处渔夫则拖着自己的渔网来此停泊。长诗的开头“到处是黑黢黢的小房”,而在结尾:“破烂的小屋……,像黑色的灌木”。一批批大船来自世界各地,它们意欲停泊的富丽豪华的码头在哪里?意欲停靠的生机勃勃的岸边又在哪里?取代大船的是渔夫的小舟与过客的木船,如同开始时河面上只有“可怜的小舟孤零零地摇荡”。两部作品的序曲和尾声中“破旧的”一词使用频率最高:童话中是“破旧的小屋”,“破旧的渔网”;长诗中则是“破旧的小屋”,“破烂的茅屋”。
作为全文总结之“又破又旧的木盆”是破烂小屋的绝配:“一片荒芜,一切尽毁”。同老太婆一起留下的破木盆是人的生命在大自然进逼下无能为力的标志,是能力衰败的标志,衰败到已无力保护事物免受时间的冲刷,海岸免遭洪水的侵袭。木盆的形象绝对不是普希金童话中偶然的开端与终结。在普希金创作的来源,格林兄弟的童话《渔夫和他的妻子》中,没有木盆之说。破木盆与长诗中的主宰,大海的形象具有对比关系,似乎是沉船的类似物。此外,破漏的木盆底部似乎是长诗中整座巍峨的城市童话般的对应物,不过这座城市却有致命伤:建在沼泽之上,常受暴怒的大自然的侵扰。这泥沼岸边的人类文明的“方案”本身一开始就具有无法消除的缺陷,在这里,人类文明最终受到了惩罚。
两部作品的故事情节在门槛上戛然而止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疯人/人们发现,死在茅屋门口”(《铜骑士》)。“他的老太婆在门槛上坐着”(《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门槛是与岸(水与陆地的界限)相同的界限的象征,但已被用于房屋本身。普希金两部作品中的门槛与海岸标志着家园与陆地无力同周围的大海抗衡。长诗与童话的结尾是门槛,在门槛之上我们看到被大海索回之前所拥有的一切的人:老太婆(拿着破木盆)和叶甫盖尼(在海水淹没的小屋旁)。
这样一来,普希金在加工格林童话时,拉近了童话与长诗情节的距离,增强了与海、水及沿岸生命相关的形象的表现力,并以此强调了自己两部作品的主题。“在他的周围都是水,再没有别的东西!”无论是长诗还是童话,周围如史前般空旷的一片汪洋成为“奇迹的创造”出乎意料,却又不可避免的结果。
“这可是在梦中?
难道说我们的整个人生
只是一场空洞虚幻的梦,
只是上天对人间的戏弄?”[4](475)
这一“空洞的梦”在童话和长诗中表现为一连串利欲熏心的念头,从“新木盆”到“皇宫”:炫目的世界仿如幻影般展开-收拢。④
4
两部作品不仅形象体系接近,它们也是同时创作的,准确地说,是在1833年波尔金诺之秋先后写就。10月6日《铜骑士》草稿完成,31日誊清。童话末端标注的日期是10月14日:也就是说,它写于创作长诗的间歇。普希金大致完成长诗后,在最终定稿之前,似乎又创作了一个版本,虚拟童话版。在创作过程当中,长诗吸取着童话的元素,并间接将其表现出来。
二者在标题形象,即金属的象征名称方面亦彼此呼应:《铜骑士》是权力的体现;《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则是财富的体现。在普希金的形象体系中,金属同水对立,反映了人试图将自己坚强的意志凌驾于“自由自在的大自然”之上的意图。权力与财富,铜与金,这就是既使“奇迹的创造者”,又使“发脾气的老太婆”迷恋心醉之物。
不过,长诗与童话之间在情节建构方面却有根本差别,表现出这种情况下不同体裁作品中相异的宇宙观。长诗中沙皇对大海的支配权在开端已实现,且成为情节的起点;童话中老太婆—女王对大海的支配权则变成最终未实现的奢望,意味着故事即将结束。这不单纯是结构的差异。彼得的创造行动于情节开始之前已告结束,故其整个情节建构仿如自然本身的自发行为,这也正是悲剧作品的标志:城市遭到了命运本身,“上帝的惩罚”。“沙皇没有办法管辖/上帝的不可抗拒的力量”[4](474)(《铜骑士》)。童话则相反,以喜剧的方式处理这一主题,因为同大自然,同“生命的本体”较量的主要动机缘于发脾气的老太婆。如果说悲剧中厄运起作用,而人只有忍受命中注定之事,那么喜剧中起作用的就是个体,其奢望被以可笑的方式展示出来。
彼得作为悲剧主人公,伟大而又可怕,因为他“凭着自己的宿命的意志/要在海边建立城市”。彼得无法未卜先知,招致厄运对其创造物毁灭性的反击。“他在昏暗中是多么可怕!”普希金把彼得堡建城的全部历史浓缩于长诗的序曲中,将彼得的建树描绘为无可争议的既成事实,因此命运的无情捉弄就成为长诗随后两章的内容。童话中则相反,整个情节建构在主观性和客观存在不一致的游戏之上。老太婆有违常理,置大自然警告的符号于不顾,其行为举止中表现出来的首先是一种癫狂。“老太婆比以前闹得更凶”。这个“凶恶的”,“该死的”婆子经常“开骂”,“破口大骂,对丈夫很凶”。她试图摆脱命中注定的角色:像一个妇女和一般人那样驯顺,因此受到惩罚。但大海的惩罚本身在长诗中铺展为整个故事情节,而在童话中被压缩到尾声:厄运顷刻之间就击毁了人们苦心经营的雄伟建筑。
换句话讲,长诗中主体(沙皇彼得)的行为谱成了其两章中描写的命运(大海)波澜壮阔之举的简短序曲;童话中命运(也是大海)的行动谱成了主体(登上王位的老太婆)肆无忌惮之举的简短尾声。这就是悲剧作品与喜剧作品之间的区别:如果说前者给我们展示了客观存在的必然性,那么后者——主观世界的虚幻性。因此,对立的因素:长诗中人的意志和童话中命运的意志,相应地只是预告或结束故事情节,以序曲或尾声的形式构建世界的开始和结束的状态,在此背景之下主要情节就变得可以理解:悲剧性——大自然或喜剧性——老太婆。
运用1833年10月构思的双重性情节,普希金把同厄运斗争中人类自我肯定的两个版本推上舞台。专横致祸与刚愎自用之间是有差别的:前者非凡的意志只有用厄运本身的最高意志来摧垮,后者表现为四处炫耀,吹毛求疵与肆意妄为。这些范畴的相互关系正如多少世纪以来美学思想分析的那样。喜剧性展示了妄图支配世界命运的人类意志的愚蠢与虚幻,尽管这个世界只是狭隘的局部;悲剧性则揭示了命运的肆意妄为,它甚至有权摆布最高层,最强大的个人的意志。
这一差别也扩展到了两个其他人物的相互关系上:老头和叶甫盖尼。如果说老太婆是一个被贬低的专横君主的可笑变体,那么老头则是一个被贬低的“小人物”变体,其悲剧命运在叶甫盖尼身上得以展开。两个人都质朴善良,容易满足,他们的愿望不超过“破旧的小屋”(《渔夫与金鱼的故事》)和“简陋却安适的家”(《铜骑士》)。他们向往着“舒适”:家庭的田园生活,平淡乏味的日常生活;他们觉得觊觎权力与“荣耀”是荒谬的。其实,叶甫盖尼就幻想着老头过的那种简陋生活。
“……他们住一间破旧的小屋,
三十三年就那么度过——
老头儿出海撒网打鱼,
老太婆纺线在家里呆着。”[3](628)(《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想想办法总可以弄一个
虽然简陋但却安适的家,
在那里安置我的巴拉莎。
……我们就这样一道活下去,
手携手一直活到老死……”[4](471-472)
(《铜骑士》)
但是,两部作品的“小人物”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叶甫盖尼敢于威胁专制君主,老头却不敢反对结发之妻(“老头儿不敢说一句话,他没有胆量违抗女王”)。如果说老头不折不扣、盲目地执行老太婆的意愿,那么叶甫盖尼有一天则决心奋起反抗,从而使其成为真正悲剧作品中的人物。在他心中,与周围大自然平等的伟大意识瞬间觉醒,尽管大自然狂暴地对抗专制君主,毁灭着国家的要塞。叶甫盖尼的“心里燃烧着烈焰,血已经沸腾了……”,这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肆虐的涅瓦河的画面:“波浪依旧在忿怒地翻腾,好像是在下面烧着大火”。
总之,以前限定城市遭遇的自然现象的一系列修饰语也用在了叶甫盖尼身上:“两眼好像蒙上一层薄雾”,“他变得阴郁起来”——“风雨夜的黑暗”,“在阴暗的彼得的城上空”;“他为恶狠的力量所支配”——(涅瓦河)“已厌倦自己无礼的狂暴”;“他恨得浑身发抖,喃喃地说”——“波浪依旧在忿怒地翻腾”。
暴风雨的景象似乎钻入画框:涅瓦河通过叶甫盖尼继续着自己的抗击。就连主人公发疯也成为控制着他的涅瓦河与狂风的某种“凶恶的蛮劲”。“涅瓦河和狂风的可怕的/吼声老在他耳中轰响”——“他早已为心中/不安的巨响把耳朵震聋”。
的确,叶甫盖尼最终屈服了,已不敢在沙皇的塑像面前抬起他惊慌的眼睛。但在内心屈服之前,他发疯了:这就是他悲剧命运的主要特征。要知道抗击现实既可以通过意志上不接受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理智上不接受表现出来,后者仿如在外部世界现象面前关闭大门,拒绝接受其意义。经常在叶甫盖尼耳中响起的恶劣天气的吼声导致其头脑慌乱,使其在建于海平面之下,把自己的居民送入海底的荒谬的城市面前无法自持。
叶甫盖尼发疯,向从年代久远的山岩上跃下的铸像挑战,二者是符合常理的悲剧矛盾的标志:木偶正在摆脱操纵其命运的国家力量的控制。叶甫盖尼就其命运而言是一个小人物,但他却想用内心的反抗战胜自己的命运,于是他选择了疯癫。疯癫本身是一种反抗,它不可能被以后的任何意志屈从所弱化。叶甫盖尼的情感爆发是短暂的,但拒斥理智却使其永远离开喜剧的平面。正因为长诗中的专制君主是一个悲剧形象,故与其对抗的小人物也具有悲剧性。如同彼得堡的命运是不以彼得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现实也不受历史理性控制(“伟大的思想”),反之,小人物叶甫盖尼的理智也不受现实控制。它们之间的这种脱节从两方面被揭示出来,同样都具有悲剧性:在洪灾面前现实是不受彼得的理智控制的,叶甫盖尼发疯时理智同样不受现实控制。
童话中起作用的则是相反的规律:不是脱节,而是重复。老头一次次惶恐不安地向小金鱼转达老太婆命令,他的顺从是运用纯粹重叠手段的喜剧要素。喜剧人物自身没有个性,没有“自我”,行动如同木偶,完全靠借用或者是外部强加给他的手势和对白表现。老太婆重复着自己对小金鱼不断提高的要求,老头儿则亦步亦趋地重复她的要求。这只是要求与请求量的累积、增加、翻倍,缺乏质的进步,是喜剧的本质特征。肆意妄为是其内部动因,而机械性、呆板性和多次性是其外部表现。肆无忌惮的欲望求新求变,但它却不创造,不接受任何新事物,它是寓于多样性中空泛的单一性。这就是为什么说老头儿和老太婆是产生于对权力过度觊觎土壤上的一对喜剧人物,而彼得与叶甫盖尼这一对悲剧人物恰恰也产生于这片土壤上。如果说刚愎自用的老太婆是对悲剧君主的讽拟,那么意志薄弱的老头儿则是对悲剧中疯子,弱小的反抗者的喜剧性解释。
童话中的喜剧性也是把国家关系转移至家庭生活的结果,此处的国家关系已被弱化和颠覆。开始很难发现童话与长诗的相同之处,因为喜剧选择悲剧情节是通过极端的方式实现的,即将悲剧情节移入另一个体裁—主题层面。一家之“主”,丈夫成了女王、自己的妻子的奴仆,而妻子却瞧不起他,命人把他揪着脖颈拖出去,使其成为全民的笑柄(“人们纷纷耻笑老头儿说:这老糊涂,自作自受!”)。叶甫盖尼奋起抗击半个世界的主宰,老头儿却不敢对抗糟糠之妻。
通常在“权力”情节框架内,家庭因素同国家因素相悖且容易成为其牺牲品。这种情况出现在《铜骑士》中:叶甫盖尼想同巴拉莎过好日子的幻想就在国家意志与自然的冲突中被击得粉碎。这种情况也出现在《铜骑士》创作前一年,1832年,歌德发表的《浮士德》第二部中:按照“奇迹的创造者”浮士德和梅非斯特的意志,在先前大海的位置筑堤建设伟大的城市,直接导致生活在海边的一对质朴的夫妇菲力门和巴乌希斯的毁灭。歌德悲剧中的浮士德如同普希金长诗中的彼得,都是权力意志的化身。这种权力不只是人间的,而且是形而上的,它越过了自然力的界限:
“我心头迅速地反复筹谋:
把汹涌海浪从岸边赶走,
逼海水远远向深处回流,
使低湿地带的圈子缩小
那该是怎样珍美的享受!”[5](546)
菲力门和巴乌希斯是摧毁一切的意志的牺牲品:为了把“自由的人民”迁入“自由的土地”,居然必须毁掉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两口的栖身之处,同时毁掉他们本人;按照事物的逻辑,为了实现彼得的构想,同样需要毁灭另一对:叶甫盖尼和巴拉莎。
在普希金童话的开头,老头儿和老太婆是过着田园诗似生活的两口儿,是另一种类型的菲力门和巴乌希斯,他们在破旧的小屋共同生活了很久。但随后情况却发生了喜剧似的剧变:家庭未遇到国家的挤压,却由于“弱”势的贪权内部出现分裂。对老太婆而言,在实现自我肯定的场所首先需要的就是老伴儿的顺从。普希金的巴乌希斯自己变成了“浮士德”,而菲力门则成为其卑躬屈膝的仆从,“傻瓜和蠢货”,喜剧偷梁换柱取代了悲剧的牺牲品,其结果是一切“恢复原状”。
我们曾提及长诗与童话情节的环形结构。但如果说长诗的开头与结尾之间是一对年轻伴侣的毁灭,巴拉莎的死亡和叶甫盖尼的发疯,那么童话的开头与结尾之间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损失完全等同于收益,老两口又处于和开头一模一样的景况。“瞧:眼前还是那间小屋……”等等。此处起作用的又是纯粹重叠手法,从而弃绝了无论在英雄胜利层面,还是悲剧损失层面事物发生激变的可能性。田园诗实际上内部接近喜剧,但又不能简单归纳为喜剧。如果说由于完善和自给自足处在田园诗状态的世界波澜不兴,那么在喜剧中激变的舞台之外则揭示了情景的内部静止性,自我等同或者最终重合。长诗中叶甫盖尼同巴拉莎过田园生活的希望被不可逆转地毁灭了。⑤童话中老两口田园诗般的平静生活被打破又被恢复,就像总和为零的加减法。
长诗和童话用悲剧和喜剧的形式阐释着同一情节。让我们回忆一下,古希腊的讽刺剧是在悲剧之后才出现在舞台上,与其组成一个系列,以便减轻观众的紧张情绪,同时展示存在的另一方面:命运可怕的意志和人们愚蠢的觊觎并存。恐惧与笑在完整的审美情感中相互补充。于是乎,普希金在创作自己的悲剧长诗各章间隙,把喜剧置于想象的舞台之上:秉承了对生活进行全方位艺术解读的古代规则。《铜骑士》与《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不仅通过写作时间统一起来,它们还形成了古希腊意义上的统一的戏剧,使悲剧性和喜剧性互为补充。长诗与童话实际上是统一的作品,不仅“先后”写就,还那么完整,应该被理解为对宇宙中一个事件的两种解释。
有可能在创作《铜骑士》草稿时,普希金已对某一情节提纲了然于胸,且立时在打字机下排键上操演,以便随后将其悲剧体现推向新的高度。童话烘托出长诗,用民间笑话,“趣事”的手法修饰着同一的情节进程,以此使长诗充分展开自身的悲剧内容。试想莎士比亚的戏剧,粗鲁,低俗的幽默讽拟烘托着高雅的悲剧,并成为其组成部分。1833年波尔金诺之秋,普希金正向往着莎士比亚的纯艺术,有意识无意识地创造出某种类似的作品。
5
从这两部作品可以看出,一个主题完全占据了诗人的意识:他同时在祖国历史经验和流行于不同民族间的童话情节两个层面审视这一主题。权力与自然力。皇宫与空旷的沿岸。文明与自然。祖国历史中“蓄意的”,“有计划的”因素似乎要主宰自然之物,大自然的赐予,其特点及奥秘何在?大自然又如何回应这种将其置于命令和驱使之下的企图?
陀思妥耶夫斯基充分阐释了普希金两部作品的审美意向:悲剧和喜剧的意向就像两条平行线,最终在俄罗斯文学复杂扭曲的空间交叉。伟大的城市消失这一现象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故事》的想像中补写,并以其幻想的结尾让我们回到童话。童话中老太婆的王国果真土崩瓦解,只为她留下一个破木盆,仿如整个彼得堡只剩下奠基者的塑像。在普希金那里,一个情节分成悲喜剧两种写法的情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则表现为极其浓缩的一句话定义中的怪诞—幻想的复合形象:消失城市的悲剧与喜剧般陷入沼泽的城市奠基者的塑像,尽管奠基者最终也没有稳住根基。普希金构思的两半用不同体裁先后完成,以至于甚至在普希金本身的语境中都很难发现其共同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将这两半作为象征的两个部分合在一起。
于是,在悲剧与喜剧的结合中产生了怪诞:普希金的作品中缺乏的形象的新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半揶揄,半凄凉的话语特别强调了其艺术特性:“似乎是为了点缀”。这已是崭新的,无论是普希金的童话还是长诗都没有的“点缀”——悲喜剧荒诞美学:陷在芬兰湾沼泽地中的铜骑士。建构在荒谬基础上的形象,既可怕又可笑,它将存在的各种形式和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因此是怪诞的。
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个形象让我们看到普希金两部作品的共同之处,那么扩展至普希金创作的德国和波兰源头,逆向意义规律仍然有效:它们通过普希金获得了内在联系。创作的本质是隐喻性的。这不仅与具体的词语和形象相关,而且同整部作品相关。为什么在1833年的这个10月,普希金的创作偏偏会回应密茨凯维奇揭露专制的彼得堡的长诗《先人祭》第三部,会回应格林兄弟童话集中揭露女性吹毛求疵、刚愎自用的童话《渔夫和他的妻子》?很明显,无论德国的童话还是波兰的长诗,对普希金而言,都是一个构思的隐喻,一种意义的讽喻,这种意义通过不同形式(“童话的”,“长诗的”)体现于其创作中。
有普希金作为媒介,我们在《渔夫和他的妻子》这部童话中就能找到似乎颇有寓意地传达《先人祭》第三部中表示冲突的词句(个人意志与以北方首都专制堡垒为化身的陌生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她就像尊塑像,坐在他面前一动不动”。[6](49)格林兄弟童话中贪权的妻子预示着《铜骑士》中“高傲的铜像”。莫非就是这种“算法规则”能使普希金童话的内容转化为长诗中的形象并弄清楚,为什么两部如此不同层面,不同体裁的作品原型会在诗人的意识中碰撞,会在其一个时期的创作中交叉?要知道密茨凯维奇描写的沙皇的塑像是彼得的纪念像,他顺利完成了暴动的波兰人憎恨的专制权力的所有建构。密茨凯维奇将彼得堡这座要塞城市比作结冰的瀑布:有朝一日冰雪消融之时,瀑布会在自由的阳光下四处飞溅。格林兄弟笔下的老太婆登上王位之后,坐得更高,居然居于巴比伦塔之上,而密茨凯维奇笔下的画家奥列士凯维奇则预言彼得堡会像新巴比伦塔那样倒掉。也就是说,形象的这种隐秘模糊的内在联系在格林兄弟和密茨凯维奇那里已初现端倪——通过普希金的创作意志实现的可能性如同一块磁石,把汲取自遥远的文学源头的一部分共同的思路吸收过来。
于是,波兰诗人的作品同德国民间故事收集者的所得通过普希金间接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已成为一个概括性情节的隐喻,一个立刻确定两个故事的同一意义的隐喻:威严的君主—小人物;刚愎自用的婆娘和她备受折磨的丈夫。两个源头衍生出的超意义直接将历史与个人聚拢在一起,“世纪”与“前额”是关于人的两个真理。⑥人的意志加速并预先确定事件的进程,从而激起存在本身的不满,结果人一无所获,又退回到起点……
这就是能互为“转述”,且以民间创作形象确定故事的两个情节的主导思想。借助普希金而植根于俄罗斯文学中的彼得堡神话,也正是在普希金那里,即其起点处,才找到了与创造世界,划分自然现象的宇宙神话之间的联系(回想一下圣经中创世的日子)。为了使宇宙平衡,创世第二天必须将旱地与水分开;⑦奢望征服宇宙,在水上建城,使大海屈服于人的意志必然招致大自然的反击和敌视。宇宙的惩罚,“上天对人间的戏弄”就成为对历史反讽的基础。一方面将《铜骑士》与《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对比,另一方面,将其同《浮士德》第二部对比,可以使我们在强大首都辉煌虚幻的矛盾概念基础上发现彼得堡神话的宇宙因素。其实,彼得堡神话是对这些极端情况的调解,是解决雕像与幻像之间矛盾的一种尝试。
可以说,普希金同时关注密茨凯维奇的长诗和格林兄弟的童话与“海边城市”情节自身的特性紧密相连,同叙事—历史母题,民间创作—宇宙母题在情节中交汇紧密相连。两种不同语言的原型在普希金的创作意识中相连,成为其思想中十月(1833年)情节的象征。随后的历史将这一情节展开到了完全不同,但却已隐喻似地预料到的十月的终结(1917年),那时俄罗斯历史的整个彼得时代,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讲,“化作一团水气飘向深蓝色的天空”,“似烟雾般消散”,身后留下的是毁坏的宫殿和重又荒芜的岸边黑黢黢的小屋。为了再次服从“破旧的木盆”规则,流经自己的起点,历史逆转了时光。
“在碧浪无际的河岸上……”“要让小金鱼听我调遣……”1918年,瓦西里·罗赞诺夫为几位伟大的作者通过相互呼应创造的,具有互文性的作品下了结语。结语中以最简洁的方式归纳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母题,结尾和开端已经合拢于俄罗斯历史的情景中,合拢于1918年,崭新的,革命纪元的头一年这个点上:“上帝啊,俄罗斯变得空旷荒芜了……幻想着重塑未来与伟大历史的‘小金鱼’”。[7](367)
注释:
①博尔赫斯此处是指韩愈的《获麟解》中的记载,相应的原文为:麟之为灵昭昭也。咏于诗,书于春秋,……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然麟之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
②普希金知晓《先人祭》第三部(其中包括《彼得大帝纪念碑》和《奥列士凯维奇。1824年彼得堡洪水前一天》)之事见诸《亚·谢·普希金。铜骑士》一书。该书由伊兹马依洛夫编辑出版,古代文献系列,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78,137-139页。密茨凯维奇诗作《奥列士凯维奇》依此版本第141页逐字译出。
③格林文集中的波美拉尼亚童话是普希金童话的来源这一推测首先由西波夫斯基提出(见《普希金与他的同时代人》,圣彼得堡,1906,80-81页),随后,庞纪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出版了普希金童话的草稿,其中载有描写巴比伦塔一节。除了格林的童话,这一段在所有的民间创作版本中均未见载(庞纪,普希金的新篇章,莫斯科,世界出版社,1931年)。阿扎多夫斯基得出结论,一系列细节的吻合就能“确定普希金童话与格林的文本之间的直接从属关系”(见其《文学与民间创作》,列宁格勒,国家文学出版社,1938,74页)。另参见科列斯尼茨卡娅收入《普希金。研究的结果与问题》(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66,440-441页)一书中研究普希金童话的评论文章。
④普希金的两个主题:“空洞的梦”和“上天对人间的戏弄”的确反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得到呼应,而且是在《脆弱的心》和《诗歌与散文中的彼得堡之梦》中:“涅瓦河上的城市就像一种奇妙迷人的幻想,像一场梦境,形将消失,化作一团水气飘向深蓝色的天空”。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卷集,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72,第2卷,第48页;1979,第19卷,第69页。
⑤这种不可逆转的标志之一就是“一位穷苦的诗人”搬入叶甫盖尼的住处。“他的那一所幽僻的小屋/租期届满的时候,房主人/又租给一位穷苦的诗人。”叶甫盖尼幻想巴拉莎时自己就像诗人:“这时他痛心地叹了口气,便像诗人似地浮想联翩……”但叶甫盖尼“像一个诗人”,意思是他如同“在碧浪无际的海岸上”的彼得,试图体现自己的理想,因此在同彼得造成的现实发生冲突时死亡。一位像叶甫盖尼那样穷的真正的诗人来到他的住处,他那“幽僻的小屋”,不过诗人却把不能也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当成自己的志向。
⑥俄文中“人”(человек)一词由两部分组成:чело(前额)与век(世纪)。故有人戏称“人是世纪的前额”。此处为双关语,指代前文所述。
⑦此处应为作者误记:创世第三天上帝将旱地与水分开。——译者注。
标签:普希金论文;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论文; 大海论文; 彼得堡论文; 涅瓦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