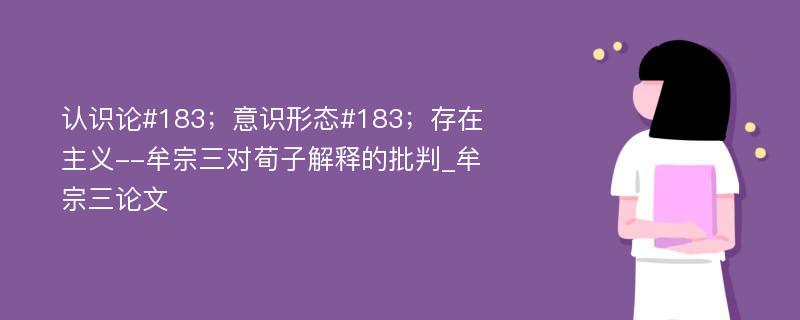
认识论#183;意识形态#183;存在论——牟宗三的荀子阐释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荀子论文,认识论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宗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17-662X(2013)10-0012-07
中西会通,使道德与知识之争显得分外惨烈。荀子的性伪之分,又让荀子处于旋涡的中心。荀子是知识论的,还是道德学的?是儒家正宗,还是别子?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等等问题纠结在一起,常常将人撕裂为二。“当代大儒牟宗三”即其例也:一方面,他每每乐道道德的理想主义比之于知识学的优越处,强调中国对于西方的拯救意义,则荀子被判定为不见道的别子;另一方面,他悲痛于道德缺乏客观性,除却自律而别无他道以约束之,以致常常幻化为任性,又判荀孟并列而为孔学之不可或缺的两极。①这里截判分明,似乎不具备任何寻找整体性的可能。
然而,如果说荀子的思想并不只是一种杂凑,那么就有必要重新思考道德与知识的分裂及分裂双方的本源统一性问题,或者说思考“道德教化之精神”的客观化及其限制问题。它影响到荀子的历史定位,更事关儒家文化的现代性,即儒学传统是否可以与时俱进而能针对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发言的问题。
一、遮蔽与解蔽
人们渴望进入真理的无蔽的状态。然而,被遮蔽的却往往是真理的本相。孔子的“必也正名”(《论语·子路》),孟子的“不得已”而“距杨墨”(《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因为真理已经被遮蔽了。被遮蔽并非只是一时的偶然现象,或者是某种能够轻易去除的东西。②一切美好的东西恰恰是最有可能成其为遮蔽的。③这是整个人类都要面对和思考的重要问题。例如那个在《沉思录》中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口号的英国人培根,就在《新工具》中留下了著名的“四假相说”,以示真理之本质性难以到达。④德国人康德更是敏感于“误谬之惑人影响”,直接断言“现代尤为批判之时代,一切事物皆须受批判”。⑤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康德的第一批判问世以后,人们常常在认识论的框架下看待遮蔽和解蔽问题。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真相。且不说“正名”、“绝四”就首先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也不论“距杨墨”第一关注的是“正人心”,只来看康德。在“现代尤为批判之时代,一切事物皆须受批判”这句话之后,康德紧接着道出了他的真实目的:“宗教由于其神圣,法律由于其尊严,似能避免批判。但宗教法律亦正以此引致疑难而不能得诚实之尊敬”;⑥即是说,只有通过自由而公开的检讨,才能唤醒人们心灵深处对于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的敬畏。这其实已经是一种信仰,而进入实践理性的领域了。
这并不是说“认识论”是一个“错误”的话题,而是说,要真正建立认识论,必须跃出认识,进入实践。康德将这称之为“界线”。⑦托拉西沿此思路写下了四卷本的《意识形态要素论》,其主要任务是建设一门基础性的“观念学”(ideology),即通过“从思想回溯到感觉”的方法,将政治、伦理、法律、经济、教育等各门科学的基本观念“还原”为感觉性存在,以摈弃宗教、形而上学及其他各种权威性的偏见。⑧而马克思则直接将自己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解蔽工作命名为“意识形态批判”。它声称,在意识中,正如在现实中一样,对历史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观念或精神,而是物质的关系(社会秩序、社会地位等),因此在阶级社会中那些采取了“普遍的形式”的观念,只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争取其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的伪装。面对这种普遍的伪装,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⑨争取自己现实利益的现实的斗争,成为历史实践中的正题。
是的,每个人而非个别人的感性的实现、人类力量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令人愉快的必然性,不需要比艺术作品更多的功能性理由。因而,“历史实践”必然与“审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兼具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整全之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比如道德或者认识,突出地成为问题的中心。那指导马克思实践的原则,就只能是废弃个人的财产,以便让身体被掠夺掉了的力量得到恢复,让感觉回到它们自身。⑩这已经进入存在论了。
海德格尔评论马克思的“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1)的“改变世界”时说:“没有黑格尔,马克思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难道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吗?……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预设为工具吗?”(12)如果说,康德试图将社会历史实践中各方面力量的争斗纳入和谐之中,因而他的美学带有某种神秘色彩(那心灵与世界之间的难以言传的默契,构成了所有特殊的认识活动的基础),那么,海德格尔的反问在表明他与马克思的实践美学的差异的同时,似乎也暗示着他把这种美学主张彻底地变成了作为基础之基础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存在论。(13)从此以后,“解蔽”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成为一个显赫的话题。
二、解蔽与认识论
对于荀子“解蔽”的梳解,更多的是“认识论的”,甚至对西方强势思想极具警惕性者如牟宗三,亦莫能外。牟宗三对当时荀子研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即所谓“民国以来,讲荀子者,惟对其《正名》篇尚感兴趣。至于其学术之大略与精神之大体端,则根本不能及”。但有意味的是,他一方面强调,荀子“毕竟非正面面对逻辑而以逻辑为主题也。此乃从其正面学术拖带而出者”,另一方面又言之凿凿,“荀子实具有逻辑之心灵”,“荀子之思路实与西方主智系统相接近”。就他本内圣之学以接榫西方之知性而解决外王问题的基本用心而言,他也和他的批评者一道,实际看重的只是荀子的“认识论”。(14)
荀子的“解蔽”的确与认识论关系颇大。《解蔽》曰:
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
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是以与治离走而是己不辍也,岂不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况于使者乎!
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荀子给出的“蔽”的原因有三:一是有“私”,认识沦落为济私之具,蔽生于认识之前;二是“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世界万物复杂难测,人们往往“顺”已知者来“类”所未知者,岂不知氤氲相推,本无一定之成法,故蔽塞生焉;三是道流迁化,蔽生于体“常”而不知“变”。“私”蔽与“常”蔽均可归之于“异”蔽,这些似乎都是人的自然倾向,是本己的和难以消除的。但荀子并没有走向相对主义。他同时强调,面对此种“心术之公患”、“蔽塞之祸”,“圣人”还是有能力达于“大理”与“道”,形成普遍客观的认识。《解蔽》曰:
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何谓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人何以知道?
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
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夫恶有蔽矣哉!
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
此段论说,为人所乐道,兹不解说。值得一提的是,学者至此,每每言荀子受稷下道家的影响。但是,孔子有绝四之无,《中庸》亦特别喜言诚本体的无,并引诗“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赞其曰“至矣”!孟子则将这种“无”和“智”联系了起来,强调“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下》)如果说,“圣人践仁到‘大而化之’之境固可说无,此无是以‘化’来显。‘无适无莫’是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无,‘天何言哉’是无,‘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是无,‘无为而治其舜也与’是无。然此种无皆是由德性生命之沛然与浑然而显”,(15)那么似乎可以认为,这里言说的是某种共法,为大家所普遍认同者,它可能特别张显于某家,但却不为某家所仅有。换言之,“无”能够通过不同的路径或通孔来接触到。正是“无”让“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成为可能。也唯因此“无”,所异者不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就此而言,荀子所讲的“心”中同样包含了“德性生命之沛然与浑然”之“衡”,否则他就不是儒者,而礼义法度等等之制作在人身上也就没有真正的根源。
但是,由于仅仅从限定了的认识论着眼,人们认为这种论述只是“性恶”论的某种失误和异端。牟宗三在梳解《不苟》“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段时言,“此段言诚,颇类《中庸》孟子。此为荀子书中最特别之一段。……荀子于此不能深切把握也。故大本不立矣。”(16)所谓“大本不立”,即荀子的心仅仅是认识心,与道德实践绝难关涉。牟宗三说:“孟子从道德的心讲。道德的心即实践的心、创造的心,也是动态的心,故能成就人文世界。而荀子则从辨心讲,辨心即认识的心,也是静态的心。”(17)又说:“明辨之心能明礼义,能为礼义,而礼义却不在人性中有根,却不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中表现,是则礼义纯是外在的,而由人之‘积习’以成,由人之天君(智心)以辨。……然礼义究竟是价值世界事。而价值之源不能不在道德的仁义之心。其成为礼文制度,固不离因事制宜,然其根源不决不在外而在内也。此则非荀子所能知其矣。落于自然主义,其归必至泯价值而驯至无礼义可言矣。其一转手而为李斯韩非,岂无故哉?然则性恶之说,岂可轻言乎?不可不慎也。”(18)
问题的本质在于,有“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吗?认识论必然是“价值世界”之外的事吗?圣人有“仁圣人”与“智圣人”两种吗?就强调德之于智的意义而言,牟宗三无疑是在解蔽。所不同的是,此解蔽目的不在批判,而在建设。换言之,如果说马克思的解蔽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永远指向未来,则牟宗三针对荀子的解蔽就是意识形态的,指向某种现成物。
三、解蔽与意识形态
说牟宗三的解蔽是意识形态的,是因为他坚持让个别直接成为普遍,其要义有三:首先,他要消除一切可能的客观化,将“天理流行”限定在纯粹个体性的感悟中——所谓王龙溪的“四无句”。圣王之所以为圣王者,以此;其次,他要反对并拒绝一切“物”和“气”,将真善美表达为某种非关“气”的神秘的“天命不已、纯亦不已”,即某种特殊的道德感;(19)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牟宗三让自己处于批判之外,断言“道德问题与证据无关,只能自己作证,不能问为什么。你一问为什么,你就不是人,而是禽兽”。(20)
《荀学大略》之四“荀子与法家:君德与君术”中,牟宗三认定,荀子之异于法家者,在于荀子重君德,有价值,而在法家思想中,无价值观念,仅为君术。他批评说:法家和新型法家“实是人类精神之大堕落”,其或以富国强兵、称霸天下动人主,或以穷人翻身为号召,“要者乃在其物化生命,不以人视人之唯物论,乃在其自身之运用与夫运用他人之一套权诈。……故上自运用者,下至被运用者,一是皆落于权诈之机器中,人类社会焉得不陷于阴森、黑暗、冷酷、物化之深潭?”(21)
此讲法似有历史运会。但它并非偶然,其根底在荀子客观化了的尽伦尽制。《解蔽》曰: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其物也杂博,其情之至也不贰。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老身长子而与愚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荀子也特别重视心的“自律”性,所谓“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但荀子并没有居停于此。他的问题是,如何“容”物,如何“浃万物之变”?不能保证“物”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则前者将转成为“愚”、“妄”。换言之,圣人必然是“及物”的,同时是仁的也是智的,是尽伦的也是尽制的,是普遍的也是特殊的。是故荀子在理论上让圣王一体,圣、王分立将造成“圣”的纯粹抽象化即愚和妄,“王”亦随之身死位易(《儒效》)。
但牟宗三恰恰要追求没有“物”的现实限制的纯洁超越之“圣”。为此,他特别将“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分开来看,认为后者仅仅为外部的形式规定,而前者才是内部的自觉实践。“是故徒以传经为儒,徒以‘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为儒,则是从孔子绕出去而从王者,是并未能了解儒家之本质。故儒之为儒必须从王者尽制之外部的礼乐人伦处规定者进而至于由圣者尽伦之‘成德之教’来规定,方能得其本质,尽其生命智慧方向之实。”(22)显然,王、礼被理解为仅仅只是“形式地规定”,是外在的物性压抑,而内圣心性之学成德之教才是“自觉地实践”,它已经自己给出了法则。牟宗三强调:“自由自主自律的意志连同它自给的普遍法则”是一体的,是一个名词,中间绝无异质;(23)“自由自律的意志之自我立法是性体之不容已”;(24)“依我看,意志底自律与意志底自由,康德虽然分两步讲,其实是同意语。由道德法则的先验性、普遍性、与必然性分析地逼至意志之自律,与由意志之自律批判地假定意志之自由为一设准,实无多大的差别”。(25)
如此说来,法则完全成为个体内部的东西,根本无需考虑他者。如果法则根本不用考虑“物”(包括他者、政治理念的技术化实现路径、政治活动的物质前提等),美将成为纯粹个体性的精神愉悦。如果美不顾及合规律性,而成为纯粹精神性的愉悦,难道它不是最大的意识形态吗?(26)
牟宗三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这绝不可能是偏见,而只能是最难理解的无上真理。因为,人直接地“与天合一”,直接来自于“天”。因为,《诗经·大雅·烝民》所说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周颂·维天之命》所讲的“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已经能保证“自律”不脱变为“任性”。人可有智的直觉,人虽有限而可无限,个人怎么可以不直接合于道体呢?儒家讲性善,说明道德,能够超越康德而又融化康德,根源即在此“常道性格”。
然而,“好是懿德”并不等于“懿德”,就如同“就禀赋而言的好树”并不是“事实上的好树”。在讨论到性善与性恶的争论时,康德认为,前者的“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但人本身还没有因此就已经是善的,而是在他把这种禀赋所包含的那些动机接纳或者不接纳入自己的准则之后,他才使自己成为善的或者恶的。”(27)换言之,尽管可以把“天生烝民”与“维天之命”认作是一种信仰和直接知识,但儒家却从来没有在这里停止过,而是强调说它所包含的内容,必须经过教化,经过发展,才能够达到自觉。就教育、发展和教养的过程而言,儒家是承认特殊性不即是普遍性的。
越是美好的东西,越是容易以普遍的形式表现自己,滑转为意识形态。余英时提醒人们注意“良知的傲慢”。他说:“新儒家虽然在现实上距君临天下的境界尚远,他们的君临天下心态却牢不可破。‘良知的傲慢’至少有一部分是从这种心态中派生出来的。”(28)这意味着,牟宗三的哲学很轻易就能够与他所反对的“意底牢结”殊途同归,在私底下结成死党。
四、解蔽与存在论
历史是共时的,也是历时的;所有人的心灵都具有不变的属性,也都具有可变的属性;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但天道毕竟又在循环。在这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之中,或许列维-斯特劳斯讲出了一个“先验唯物主义”和“唯美主义”联合共处的事实:首先,“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去构成人,而是去分解人。”所谓分解人,就是在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中,把人当作“蚂蚁”来研究,以便能够“把人类的事物分解为非人类的事物”;(29)其次,这当然并非全部,列维-斯特劳斯实际上走在一条通过“分解”来“构成”的道路上,他的任务主要是将主体从一切前在的结构(所谓科学知识领域、既定的社会秩序、权威等)中暂时分离出来,以解开结构与主体之间的棘手关系,最终突出了具有“真实的辩证性”和“整合性”的“野性的思维”,从而得以“顽固地拒绝使任何关于人的(甚至是关于有生命的)东西与自己疏离”。(30)
儒者当然不会首先把人当作蚂蚁。但儒者同样强调整合性、辩证性的思维。不同于“野性”的思维,这是一种“文明”的思维,是一种“成人之教”,即在理解一切前在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上,让人自我生成的问题。它要求真正的践履,要求实在性的东西,保证存在成其为存在。如果说,认识论对于人的分解不过是从人的存在中剥离出来的东西,是真善美分别说者,那么,作为存在论的“成人之教”对于人的构成就一定是被剥离东西的回归其自身,是真善美合一说者。这一回归,一定是行动(工夫)的回归,一定要通过社会生活,在不断的践履和转变中成其为一个善人。《解蔽》曰:
身尽其故则美。……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
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这里的“身尽其故则美”,与《孟子·离娄下》的“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一样,引起不断争论。(31)杨琼注曰:“故,事也。尽不贰之事则身美矣。”身如何能尽其不贰之事呢?荀子认为,虽然“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但抛弃物则不是正道,通过弃物也一定不能通达于美。这里,荀子区分了“以物物”与“兼物物”。在他看来,后者并不一定要排斥前者,壹于道的目的恰恰是要“赞稽物”(杨琼注:一于道,所以助考物也。助考,谓兼治也)。这样,荀子将自己与一切唯心主义的“物物论”区别了开来。(32)
然而,这种区别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可能压根就不是知识,如果以为已经将其作为确定性知识掌握在手中、可以为我所用的话,它可能就会失去,甚至成为其反面。这是十分凶险的事情,是“危微之几”。作为几微之知,此“知”常常只有示范性的意义。荀子认为,舜就是这种典范。王念孙认为,“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则曰:舜身行人事而处以专壹,且时加以戒惧之心,所谓危也。惟其危之,所以满侧皆获安荣,此人所知也。舜心见道而养以专壹,在于几微,其心安荣,则他人未知也。”(33)作为典范的舜的存在,给出了我们法则和统类。我们在舜这里所知道的,是法则和统类;我们在舜这里所不能知道的,是他何以能给出这种法则和统类;当我们知道时,我们也就具有了典范的意义,成为圣人了。
荀子是否变着法子为“庶人隐窜,莫敢视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正论》)的现实帝王唱赞歌?中国的帝王专制思想是否已经根深蒂固、深入骨髓而了难自知了?
谈到“天才”与“最高的典范”即“鉴赏的原型”时,康德认为,鉴赏只对“自律”提出要求,若有人将外在的东西当作自己判断的规定根据,就会导致“他律”,那就不是鉴赏而仅仅是工匠的模仿动作了。这似乎表明,如果坚持认为有某种可以作为典范的作品的存在,那就宣布鉴赏的来源是后天的,并反驳了“自律”说。然而康德还是强调,由于我们不能“从自身中通过概念的建构而凭最大的直觉产生出严格的证明来”,我们还得承认典范的存在,让“法则的强制性”不全源于我们的“自由本性”。这就是天才,一个值得尊敬和警惕的存在,一个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奇里斯玛”(charisma)。康德说,鉴赏力“最需要的是在文化进展中保持了最长的赞同的东西的那些榜样”。这是因为,在审美中,“自己最内心的”“普遍的同情感”必然要求“能够普遍传达的能力”。(34)换言之,我们既要相信我们的存在,同时也必须信仰别人的存在,审美的愉悦是“对一般人类都有效、而不只是对任何一种私人情感有效的愉快”。如此,向典范学习就不是什么外在的事情,这里没有强制性的权威和服从。它就是我们本性的要求,“仅仅只意味着:从那个创始人本人所曾汲取过的同一个源泉中汲取,并且只从他的先行者那里学到这件事上的行为方式”。这种学“构成了与人性相适合的社交性,通过这种社交性,人类就把自己和动物的局限性区别开来。”(35)
在这种“社交性”的“学”中,道德与知识、认识与存在合一了。强烈的历史感汇集于当下。而荀子在做的,恰恰就是向那些先在的典范学习。荀子说,夏桀殷纣是“昔人君之蔽者”(此蔽即康德所谓“独创的胡闹”)的典型,成汤文王是“昔人君之无蔽者”的典型,唐鞅奚齐是“昔人臣之蔽者”的典型,鲍叔宁戚隰朋召公吕望是“昔人臣之无蔽者”的典型,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是“昔宾孟之蔽者”的典型。孔子“仁知且不蔽”,学治天下之术而行先王之道,最为典范。在高扬了孔“圣人”之后,荀子才道出了他“虚壹而静”的解蔽观。这就回到了前文所讲的解蔽与认识论的问题。就此而言,荀子对“物”与“圣王”的强调并不是变着法子论证现实帝王的合法性,毋宁说,他恰恰以人类社会的存在为依据,批判着这种合法性。此种永恒轮回着的存在,除了人类的幸福(身尽其故)之外,不论证其他任何东西。
一个民族必须经由典范而学会善待平等、自由与敬重、服从、强制之间的巨大张力,以及虚灵精神与物性法则之间的永恒冲突,即保有、维护、协调它,而非企图消除它。如果仅仅出于对普遍性可能脱变为某种专制性强制的恐惧,一个民族就将法则交给我们自己的“智的直觉”,并在“从自身中通过概念的建构而凭最大的直觉产生出严格的证明来”之后,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避免特殊性的专制性强制的话,那这个民族在未来的时代里“就几乎不可能做到使自己获得这种一个概念,即幸运地把最高教养的合乎法则的强制性与感到这种教养的固有价值的自由本性的力量和正确性结合在这同一个民族中”。(36)这个民族将会越来越不接近自然,最终消失在纯粹的不可知的神秘之中。
注释:
①在疏解《荀子·正论》之“桀纣无天下,汤武不弑君”时,因“古人对君除责之以自律外,盖无他道”现象,牟宗三不无深情地说,“吾每感此而兴无涯之悲痛,遂发愿深思而求其故。必解消此中之暗礁,吾民族始能卓然自立,免去此历史之悲运”。他的对策是,“道德理性”必须在“国家形式”中出现,从而让上之君与下之民等俱能“维持其政治上之独立性与客观性”。这就要求关注中国的“客观精神”,重视和研究荀子。牟宗三说:“荀子之学一直无人讲,其精神一直无人解。此中国历史之大不幸。值得注意的是,在智的直觉概念成为中心后,这种悲痛和精神就不见了;相应地,荀子也就不再被关注。”参阅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第233-234页;牟宗三:《历史哲学》,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128页;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东方朔:《客观化及其限制——牟宗三先生〈荀学大略〉解义》,《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②“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意必固我是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习以为常。
③在《子罕》、《宪问》两处,孔子表达了他对知、仁、勇的敬意,但在《阳货》中,孔子还表达了他对这类神圣的字眼的忧心,此即所谓的“六言六蔽”:“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④[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页;培根:《崇学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69页。
⑤⑥[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页。
⑦康德认为,“既然界线本身是一个肯定的东西,它既属于它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又属于存在于既定和总和以外的天地,因此它也仍然是一个实在的肯定的认识。”([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3页。)换言之,要划定思维的界限,我们就必须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考虑到这个界限的内外两方面。这是康德的一个常识,牵扯到直观与思维、规定性判断力与反思性判断力等等的区分和融合,康德的认识论、马克思的实践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亦在此相遇了。
⑧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26页。
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页。
⑩[英]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6-199页。
(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12)[德]海德格尔:《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13)[英]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3页。
(14)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第139页。
(15)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15页。
(16)(18)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第197-198、266-267页。
(17)牟宗三:《人文讲习录》,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138页。
(19)牟宗三:《康德第三批判讲演录(九)、(八)》,载台北《鹅湖月刊》2001年第5、4期。“从儒家义理系统的展开严肃地讲,要发展到王龙溪的‘四无句’的境界才达致即真、即美、即善合一。‘天理流行’是一句话,到王龙溪‘四无句’的境界才真正见到了。”“美的领域套不进天命不已、纯亦不已里面去。”“美是属于气化。”此类论述绝非一时失语,在牟宗三前后期的著作中比比皆是,是牟宗三的“意识形态”。
(20)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23页。
(21)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第248-249页。牟宗三此处的“物化”显然同中国哲学所言称的“气”有特殊关系,反映了他对于“气”的敌意和消物入心的策略。有意思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及为写作《资本论》写下的手稿中,马克思大量使用的正是“物化”概念。在马克思看来。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它的结果是物主体化,人客体化,物成为人的主宰,人成为物的臣民。马克思同时指出,将这种物的依赖性关系看作是自然发生的,是一种同粗俗唯心主义一样的粗俗的唯物主义,从而使物神秘化。可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化的批判,只是要恢复“物化”的中性含义,目的是完成对物的盛赞,让物在更为普遍的美学意义上成其为物。
(22)(23)(24)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13、131、116页。
(25)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第77页。
(26)鲁迅说过煤炭大王照例是不懂得北京拾煤渣的老太太的苦楚的,贾府里的焦大,大致是不会爱林妹妹的这类话,这不新鲜。新鲜的是人们对此的态度。皮埃尔·布尔迪厄指出,审美无功利关系的纯粹性使人们忽视,只有少数人,才能够掌握编码艺术品的代码,而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天资更为聪颖,只是因为他们拥有的经济资本或由此转化而来的文化资本使他们可以接受较好的高等教育,可以摆脱生活的直接性和必要性。然而,同样是“以美学精神投身现实事业”,大讲生命美学、批判理论的潘知常,认为鲁迅“说得不对”,“我觉得鲁迅的作品里面存在着对于阶级性的误解”。马克思认为,有一个“意识形态阶层”,或许他道出了一个事实。这也是熊十力批评牟宗三“喜享用现成良知”、“仅以驰求知识为能事”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参阅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潘知常:《失败的鲁迅与鲁迅的失败》,http://www.guoxue.com/lwtj/content/panzhichang_sbdlxykdsb.htm,及其论爱与信仰的相关期刊文章;熊十力:《十力语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242-246、271-280页等。
(27)[德]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第43页。
(28)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年,第569页。
(29)(30)[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81、279页。
(31)可参阅田智忠、胡东东:《论“故者以利为本”——以孟子心性论为参照》,《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拙文:《“故者以利为本”——论〈孟子〉中的形上演绎》,《孔子研究》2009年第2期。
(32)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59-860页。若把“物物”解释与“命名物”,而规定为认识论的事情,那么命名物而又不陷于物的“兼物物”,就必然是存在论的事情。认识论的“物物”(名物)能够偏安一隅,为抽象的专家之学,所谓农、贾之属;存在论的“物物”(各物)则必然具体而全面,所谓官师是也。这样说来,荀子的“身尽其故则美”就是要点燃认识论与存在论、专家与官员、知识与意识形态等等之间的战争,成就双方之亲密的区分关系。再进一步,荀子也就“点燃”了健康的“心”与健康的“物”之间的“争论”,把有限之人的生存论境域端呈出来了。当然,这种理解又是海德格尔式的,参阅氏著:《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512页。另外,杨柳桥引《尔雅》言“身”为“亲”。这是用“身”来修饰“尽”,谓“亲究其故”。此说味短,且没有顾及“身尽其故则美”与“心枝则无知”中身与心的对照,故不取。
(33)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08年,第400页。
(34)(35)(36)[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4-125、204-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