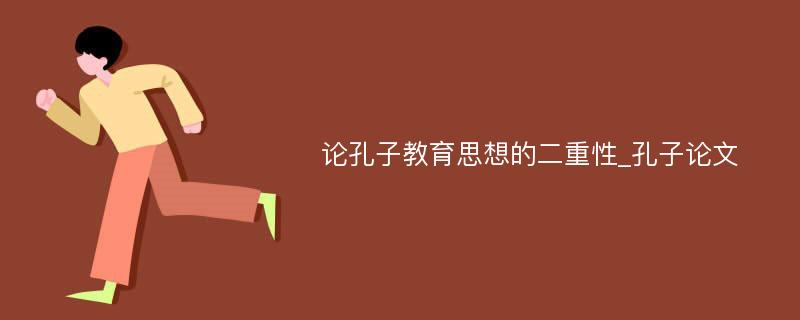
孔子教育思想二重性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创立的儒家思想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影响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是任何一种思想都无法比拟的。他开办私学,杏坛讲解,广招弟子,诲人不倦,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使他成为我国古代社会教育的一位前无古人的集大成者,一位承上启下的奠基者;他提出了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举贤才等一系列教育思想,在教育理论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在今天,我们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更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如何总结批判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这在当前的学术界仍有争论,本文就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问题的提出
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研究和评价历来是肯定多于否定,赞扬多于批评,但对其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各家仍有争论。冯天瑜在《孔子教育思想批判》中认为:“孔丘一生主要职业是从事教育工作,教育活动是他反革命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的政治观点是反动的,他的哲学体系是唯心的。从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和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派生出来的教育思想,必然是反动的。”[2]蔡尚思在《孔子思想体系》中认为:“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中,应把他的教育思想跟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史学思想、文艺思想等等区别开来,在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中,也要把他的教育经验、教育方法跟他的教育目的区别开来,因为前者多是正确的,后者多是反动的,二者千万不要混为一谈。”[3]匡亚明在《孔子评传》中认为:“孔子关于教育思想、教学态度、教学方法以及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规律等属于方法论方面的思想言论,是没有明显阶级含义的,是孔子思想中至今日尚闪耀着光辉的一部分,一般说来,可以作为箴言来借鉴学习。”[4]陈景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认为:“孔子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比较开明的奴隶主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新兴进步力量的倾向和要求,他的教育理论,特别是他的教学方法至今仍有不少积极的东西,值得我们批判继承。”[5]我们认为孔子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能随意地把它割裂开来,拔高或贬低其中的某一部分,也不能从机械的推理入手而无视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应当从全部的史料入手,从全部的思想出发,并联系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和以后思想的发展演变,来全面评价孔子的教育思想。也就是说,对孔子的评价既要有静态资料的考察,也要有动态发展的分析。鉴于此,我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具有二重性,既有积极肯定的一面,又有消极否定的一面。只不过是在教育思想的不同侧面,积极与消极之比重占的不同罢了。
二、孔子教育思想二重性产生的社会背景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正处于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这是一个旧制度已土崩瓦解,新制度尚未建立的社会动乱时期。从政治上来看,王室衰微,天子失官,大权旁落,诸侯称霸,出现了“天下无道”、“陪臣执国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从经济上来说,代表奴隶社会经济制度的井田制已遭到严重的破坏。随着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始出现了大批的私田,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鲁国颁布的初税亩便从法律上确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从文化教育看,由于战乱频繁,文化典籍从宫廷中流出,教育也从王宫中解放出来,出现了学术下移,学在四夷的局面。因此,无论从政治、经济上,还是从文化教育上来看,春秋时代都是一个新旧交替、矛盾迭起的时代,这种矛盾的社会,也必定会在孔子的思想中留下投影。
孔子出生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使他能更多地接近社会的下层,了解下层百姓的喜怒哀乐,他说他自己“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他当过吹鼓手,替人办过丧事,后来又做过管牛羊的“乘田”和记帐的“委吏”,因此,他要求改良无道的社会,减轻人民的负担,体现出他思想中积极进步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他出身于奴隶主贵族家庭,从小就受到奴隶主统治思想的熏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丘年少好礼”。[6]所以,他长大以后仍念念不忘西周,十分推崇周礼,要求恢复周礼,在旅途中尚能“与弟子习礼大树下”[7],反映出了孔子思想中消极保守的一面。从孔子的出身来看,孔子具有双重的社会身份,向上,东奔西走,替统治阶级出谋划策,以求重用来实施其政治主张;向下,同情民众,了解民众,要求施恩惠于民众。这种双重的社会身份是他教育思想二重性的原因之一。
孔子生长在鲁国,春秋末期的鲁国,奴隶制度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地崩溃。公元前594年鲁国的初税亩,确认了私田的合法地位,加速了奴隶社会的瓦解,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说,鲁国无疑是走在了前头。另一方面,孔子生长的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初期长期摄政,使鲁国成为唯一能用天子礼乐祭祀天地祖宗的诸侯国,因此,周代的礼乐在鲁国保存最为完善,直到春秋中叶吴季札使鲁“请观于周乘”[8],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和晏子也曾“入鲁问礼”[9],晋韩宣子使鲁,“观书于大史氏”,称赞“周礼尽在鲁矣”[10]。这些事实说明鲁国保存了大量周代的礼乐典章制度,孔子一生向往周礼尊崇周礼,这和鲁国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说,鲁国又是一个保守落后崇尚礼制的国家,这种经济发展的进步性与思想文化发展的落后性,不能不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得以反映。“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的政治、哲学和宗教”[11]。思想上的二重性只能到社会生活现实条件中去寻找原因,孔子教育思想中的二重性也是春秋时期的社会生活现实条件的矛盾性在观念上的反映,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二重性产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研究孔子思想的资料来看,现在研究孔子的资料多以《论语》为主,而《论语》的成书,并非出自孔子本人之手,而是后来孔子的弟子整理成籍的,孔子的思想可能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不同,这也是极有可能的,但孔子的弟子是照录如初,因此,从孔子的《论语》本身看,其内容也有抵牾之处,这也是必然的,这也是我们评价孔子教育思想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三、孔子教育思想二重性的具体表现
孔子教育思想的二重性主要表现在他提出的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
1.从教育目的来看,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能担当从政复礼任务的君子。面对当时礼崩乐坏,名分颠倒,犯上作乱,天下无道的混乱世情,孔子想通过教育的方法来培养能治国安邦的贤才,以达到他实行德政的政治目的。在政治上,孔子是一位奴隶主阶级的改良派,他“修成康之业,述周公之训”,既向往有朝一日能“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恢复周礼,又面对复杂的现实不得不在礼的外壳下注入仁的内容,他“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周游列国,到处宣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表现了他复兴“文武之政”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他也要求统治者实行德政,施恩惠给民众,这样才能达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社会。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如果“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免而无耻”,如果“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有耻且格”。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办教育就是为了“学而优则仕”、“举贤才”。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他还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君子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官从政以致其道弘其道。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要担心自己的才能,他要求弟子从自己做起“克己复礼”、“修己以安人”,然后才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从他办教育的结果看,他的弟子大多成为当时政界之要人,为实现孔子之政见而奔走呼号。宋人曾说:“仲尼之门,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闵子、曾子数人而已”,可见,他的教育目的是基本上实现了。只不过是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罢了。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从主观来讲,孔子提出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以天下为己任,恪守善道的君子,他想以学而优作为标准,来推举贤才,使之步入政界,以实现复礼之大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引导人们向后看的,是消极保守的。从客观效果来讲,孔子在教育目的上提出了“学而优则仕”、“举贤才”的主张,打破了自殷周以来形成的仕途贵族世袭制,顺应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参与政治分享权力的愿望,符合社会的发展,对以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政府官吏的选拔,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的教育目的是积极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的脱离,这是孔子始料不及的,这也是孔子教育思想之所以在封建社会流传已久的内在原因。
2.从教育的对象看:孔子是在他的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教育对象。孔子人性论上的二重性决定了他教育对象的二重性。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紧接着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说明在人性论问题上,他一方面承认人人生来都是差不多的,是相近的,其差异主要在于后天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上智与下愚的不移,相信有圣人、君子、小人之别,否认了前面的观点,这两者显然是矛盾的。正是他人性论上的矛盾性影响到了他教育对象的二重性。他一方面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主张不分种类、族类、德类,来者不拒,只要能“自行束 以上,吾未尝无侮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也说明了他教育对象之广泛,这对促进当时文化学术的下移,普及文化知识,开发启迪民智,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从他的言论看,他的教育也是有差别的,决不是什么全民的教育家,他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还承认有生知、学知、不知之别。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因此,从主观上来讲,他实行开放式教学,面向社会,广泛宣传他的一套治国平天下之术,培养能践行他思想的弟子,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为实现恢复郁郁乎文哉的西周而努力,他决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着想,实行全民的教育,他办教育的目的就决定了他的教育对象是有区别的。但从客观效果看,他开创私学广招弟子还是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推动了学术下移,百家争鸣;他主张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扩大了知识的传播,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又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要把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区分开,决不能因为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以及在他的学生中有一些出身较低的学生而忽略了他在教育对象方面具有的某些落后思想,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的脱节,这在历史人物身上常有发生。我们应从全部的思想及其实践出发来衡量孔子的教育对象,决不能“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只见其客观实践结果的积极性,而忽略了其主观思想中的某些落后思想。
3.从孔子的教育内容看,孔子的教育内容是文行忠信,具体的教材便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教育的内容实质上是用哪个阶级的思想意识来教育下一代的问题,孔子的教育内容基本上属于道德的范围。他在道德教育过程中主要讲仁与礼的问题。他说:“不学礼,无以立”,“上好礼,则民易使也”,“为国以礼”,礼的作用在“辩异”“正名”,分别贵贱等级,维护社会上下尊卑之秩序,从社会的外在的角度来要求人的道德行为能符合外在社会道德标准——礼的要求。如何使外在的要求转化成个人内在的自觉呢?他又提出了仁的道德范畴。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要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经常反求诸己,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平,使自己言行符合礼的规范。从当时的情况看,孔子的教育内容一方面体现着他的政治主张,他要求弟子学习六经,以达到知礼、行礼、复礼的目的。在进行道德教育时,过分强调自我束缚自我修养,不论是非,都要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忽略和压抑了个性的发展给中国汉民族心理带上了一些不利的文化特点。如因循守旧,谨小慎微,害怕冒险等。在他的教育内容中还忽略了其他知识的传授,轻视科技知识、生产劳动等内容,对以后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孔子的教育内容,尤其是道德教育内容是面对现实,侧重人事而非宗教的。他避而不谈鬼神,把当时具有的文化知识传授给了学生。这对传播文化,提高民族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以四书五经为主的教育内容占了统治地位。一方面相比于西欧中世纪的宗教教育内容来说,我国早期的教育内容无疑是丰富充实的。同时在他的教育内容中也提出了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如忠廉孝温恭俭让等,对调节人际关系,形成礼仪之邦的中国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孔子提出的教育内容随着儒学的独尊而定于一统,成了正统的教育内容,这也影响了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他的道德教育原则,被统治阶级用作统治思想以后,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人民死守善道安于被压迫、被剥削,甘心过着穷苦的生活,不到生死攸关,不敢“犯上作乱”,形成了我们民族自身的一些奴性。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孔子的教育内容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重的影响。
4.从教育方法看: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教育方法。他知人善教,诲人不倦,要求弟子在学习过程中要以学为基础,反对空想乱想,力求把学与思结合起来。他说:“学而不思则 ,思而不学则殆。”“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主张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要有虚心笃实的态度,他斥责了那种“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还反对一知半解道听途说。他说:“道听途说,德之弃也。”他还认为学习要不耻下问,每事必问,随时随地拜人为师,学人之所长。他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学习还要广交朋友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否则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学习以后,必须时时温习,才能把新知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融会贯通,运用自如。他因材施教,长善救失,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积极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这些教学方法至今仍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是他教育方法中可取之处。另一方面,在他的教育方法中也有一些消极的东西。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强调继承,忽略创造,他“共己以待,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消极等待他人来问,而不是积极主动地施教于人。他还重视传播和学习书本知识,而轻视生产劳动,轻视向社会学习。当时有人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当樊迟向他请教如何种庄稼,他痛斥樊迟为小人。这些方面是孔子教育方法上的消极面,总的来说,孔子的教育方法中积极的成份多于消极的成份,但二重性仍然体现在其中,只不过是积极与消极成份之比例发生了变化罢了。这是因为孔子不但是一位教育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位教育实践家。主观的理论与客观实践效果发生了分离。他的教育实践顺应了时代,某些教育方法也合乎教育规律,这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继承的。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最终归结为二派,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派是以孟子为代表的,主张内圣,一派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主张外王,这二派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推动着儒学的发展。这两派追根溯源皆可从孔子的思想中找到依据。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二重性的丝线。这种二重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孔子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孔子也不失为我国古代教育的奠基者,我们决不能因为孔子教育思想中有二重性而否定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因为历史人物的评价只能从历史的角度,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从纵横交错、动静结合的历史坐标系中确定其位置。
注释:
[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6页。
[2]冯天瑜《孔子的教育思想批判》。
[3]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
[4]匡亚明《孔子评传》。
[5]陈景磐《孔子的教育思想》。
[6]《史记·孔子世家》。《史记·鲁世家》。
[7]《史记·孔子世家》。《史记·鲁世家》。
[8]《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9]《史记·孔子世家》。《史记·鲁世家》。
[10]《左传》昭公二年。
[11]《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第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