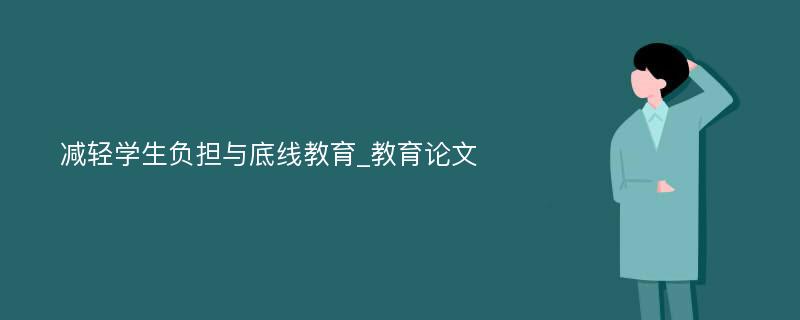
学生减负与底线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底线论文,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到“中小学生减负”,人们经常把中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学生负担的情况进行比较。相比之下,外国学生课量少、假期长、负担轻。由此,我们的减负也有了某种依据。其实,这后面往往隐藏着误解。
前不久读到一篇关于减负的报道,说是“现在学校没有功课也没有了考试,孩子回到家就是看电视。频频在电视机前逗留让孩子的眼睛也出现了问题。这样的减负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实在忧心忡忡……”
究竟有多少学校真的减负减到“没有功课也没有了考试”的程度?还不得而知。不过,这则报道反映了减负过程中的一种倾向,就是将“学生减负”简单地等同于一刀切的“底线教育”。
底线教育
所谓“底线教育”是指学校按规定所必须提供的最基本的教育服务。在美国,政府部门对公立中小学校有严格的法律要求和规定,具体到学科总数、授课时量、知识和技能要点等等。以宾夕法尼亚州为例,中小学生每学年在校时间约36星期,每天在校时间约7小时(包括中午吃饭时间)。只有在教学上基本满足这些底线要求,学生才可能有较多的假期、每天有较短的在校时间。但一所学校如果仅仅是按照法律规定提供基本的教学服务,那只是达到了法律规定的底线。达不到底线,学校就有麻烦,必须整改。然而,一个学生光是接受在校的底线教育,是难以完成学习任务的,也说不上高素质,甚至难以在美国社会上有出头之日。事实上,绝大多数美国学生,在接受底线教育的同时,通过种种途径,补充和完善了底线教育,并丰富了所受教育的内容和范围。这些“底线以外的教育”,又与学校、家庭、社会、政府等方方面面相关。
底线以外的教育
美国社会底线以外的教育,可以从校内和校外两方面去理解。
校内的底线以外教育。经费情况和管理水平越好的学校,底线以外的教育活动开展得越好。这些活动可以是课内的,也可以是课外的,而且多半体现了个性化的培养。其基本出发点就是要发掘学生的潜力,提高教育的有效性,促进素质教育。我认识一个旅美华人的孩子,上小学。由于他已经掌握数学课的内容,所以每当本班上数学课时,他就到一个跨班级、跨年级的特殊班去上课。特殊班所讲的数学内容海阔天空,未必要学生全部掌握,主要是激发学生的思维。美国的中学也有类似的安排。有条件的中学开设一些大学低年级的课程,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去学(所谓advanced placement),学分通常可以在将来入大学后转到大学去算学分。甚至,有少数高年级的中学生同时在高中和大学双重注册(dual registration),直接在大学里选修部分课程。至于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更是五花八门,有文化知识方面的,有艺术体育方面的,有实验操作方面的,有社会实践方面的……
校外的底线以外教育。首先是家庭。家庭在学生校外底线外教育中起着核心作用。家长,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都很关注孩子的教育,有时直接辅导孩子。但家长更多的只是在钱财和时间上的投入,如请家教、让孩子上各种文化学习班和技能班、文艺社团、运动俱乐部、夏令营活动、社会实践等活动。其次是社区。许多社区都有活动中心,有些有独立的场舍,有些则借用当地学校、教会或其它机构的设施,组织和支持学生的校外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公共图书馆系统。每一个社区都有当地的公共图书馆,备有书刊、音像资料、计算机等,为当地居民提供免费服务,还经常组织其它文化活动。这些图书馆的主要读者群之一就是当地的中小学生。据报道,欧美发达国家中,平均每一万人或数千人就有一座公共图书馆。此外,许多社区还有各种各样的免费的或低价的博物馆、画廊、演艺场所、运动设施、展览馆等,直接为学生校外底线外教育提供服务。
美国市场上已建立了成熟的商业性教育服务体系,以满足底线外教育的需求。在文化学习方面,有大量的人员从事业余辅导和家教,也有许多专职人员以此为业,甚至还有一些全国性教育服务公司连锁店等经营此类业务,最著名的有西尔文学习中心(Sylvan Learning Centers)、库门公司(Kumon)等。在非文化课学习方面,更是门类繁多,体操、武术、瑜珈、芭蕾、音乐、绘画、雕塑、陶艺等包罗万象。
网上的教育服务资源也很丰富,有专门辅导学生做作业的,有专门授课、答疑的,有提供咨询的,有供学生和家长聊天交换信息的。服务形式也很多样,有收费服务的,也有免费的;有人力服务的,也有人机互动的。
社会机构,包括公司企业、地方商会、各种基金会和民间组织、社区学院和周边的大学等,也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支持底线外教育,诸如提供场所、赞助赛事、组织活动、发放夏令营奖学金等等。
各级政府也直接介入底线外教育的活动,政府财政中对此还有专项预算。除了正常的文化教育项目以外,还有些特殊项目。比如,依据“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联邦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如果在“条件较差的学校”上学,就可以申请专设的课外辅导,由政府买单。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不少免费的或非赢利的服务,但大量的底线外教育的活动还是商业性的。然而,即使是商业性的服务,因为市场相当成熟,收费也不很高。
底线外的教育对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它首先是对学校在文化课底线教育方面的补充;而对所有学生来说,底线外的教育大大丰富了个性化教育和素质教育。
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有关法律和各级主管部门发布的红头文件及相关规定。如果学校真的按章办事,那么,学生的负担不至于太重。然而,各地的学校实际在做的都是在底线以外层层加码。这种加码的“底线外教育”,往往以牺牲学生的个性教育或素质教育为代价,培养学生应付各种考试的能力。其结果是普遍的学业负担过重,还伴随着高分低能、低素质的弊端。
中小学生减负是否就是“一刀切”地实施“底线教育”,完成最基本的文化课教学要求?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但在学生减负的同时,我们还应加强底线外的教育。据报道,有些学校已经行动起来,提高“教育有效性”。然而,对大多数学校来说,这样做的难度是很大的。举一个例子。有一位落户上海的海归博士,带回一对七岁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的女儿,经过激烈竞争后进入上海市的一所一流小学。入学一年多了,每周三次英语课,这一驾驭英语能力可能比老师还强的孩子还得坐在教室里,陪着其余同学学习“I love Shanghai.”这样的入门英语。
上海的一流学校尚且如此,其它学校的难度就更大了。那么,底线外教育的主要任务就要指望社会了?事实上,从本文开始的那篇报道看,随着学生减负,一些学校已经把底线外教育的任务推向了社会。然而,社会上的情况并不容乐观。
在大多数中国家庭,在知识能力和经济能力上,都难以为子女提供较好的底线外教育。中国人口整体上受教育程度较低。就学生家长群体而言,受教育程度还是不高的。加上新知识的不断出现,普通家长直接辅导子女的能力十分有限,常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以外的社会教育资源尤其重要。然而,中国的社会(指学校以外的)教育资源相当匮乏。即使在上海这样经济和文化都相对发达的城市,公共图书馆和其它免费或廉价的公共文化教育资源仍十分紧缺。同时,质量好的商业性文化教育服务既少又贵。普通收入的家庭难以从经济上长期地正常支持子女接受底线外的教育。
综上所述,随着学生减负,学生的学业负担减轻、在校时间减少,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重视和切实有效的解决,将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甚至隐含着某种危机。
中外有别
中外有别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不可能一一细说,只说一说在底线外教育中起着主要作用的家庭及家庭的经济结构。在这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有着重大差别。发达国家早已进入了中产社会,即社会中大多数家庭都处于中产或中产以上的经济地位,整个社会的家庭经济结构呈菱形,中间大两头小。正是这些有着较好经济实力的中产家庭,构成了开展社会上的底线外教育(尤其是商业性底线外教育)的基础。而在中国,尽管过去二十多年里取得了令世人瞠目的经济发展,但由于老底子太薄,至今真正富起来并堪称中产或中产以上的家庭只占人口的少数,大多数人都处于社会经济结构的下层。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开展社会性底线外教育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一方面,少数富人如鱼得水,利用学生减负赢得的时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子女获得较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占人口大多数的家庭因无力参与这样的游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接受全面教育的机会。最后,当政府正着手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时,伴随着学生减负,新的教育不平等又不断形成,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里所说的教育不平等又不断形成,并不体现在正常上学所需支付的学费、书费、生活费等方面,所以具有较大的隐蔽性,更容易被忽视。
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并由此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发展教育,因为教育是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最主要的渠道。但从上面分析的情况看,简单地推行学生减负而不辅以切实的底线外教育,必将导致新的教育不平等,进而维持和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最近已有报道指出,我国农村学生入重点大学的学生数比例正在下降,其背景当然与城乡经济差异以及教育不平等直接相关。如果以城市学生的家庭收入作分析,他们的家庭阶层情况很可能也会体现在大学生的比例之中。在一个倡导平等、公正的社会里,这种结构性的社会不平等必然会导致民怨,积怨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也说与世界接轨
一定的教育制度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产物。发达国家的学生负担轻,主要体现在底线教育方面。如果考虑到与底线教育相辅的底线外教育,许多发达国家的学生负担也是不轻的。就整个教育体系而言,底线教育和底线外教育两者不可或缺。发达国家的素质教育,是通过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作用,强化了底线外的教育得以实现的。
我们要改革教育,首先要改变观念。把教育局限于学校的观念早已过时了,教育是全社会的事。我们在学习外国的经验或者试图“接轨”时,如果只是从学校内的“减负”着手而忽略了其它,势必要“出轨”。所以,在我们致力于学生减负的同时,必须加强底线外的教育。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矛盾的焦点在于,缺乏经济实力的广大民众对底线外教育的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针对这个有着广泛社会意义的矛盾,发展底线外教育的公共事业尤为重要。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学校的资源,尤其是在减负过程中“解放”出来的人力物力资源,积极开展底线外教育;另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社会公益性的文化教育事业,诸如建立社区中心、公共图书馆以及其它有实效的公共文化设施。
要解决相关的资金问题,首先应由政府增加投入。中国的财政预算中文化教育经费比例偏低的情况,已成为中外专家们的老话题。同时,要调动地方和民间投入的积极性,而政府可以在财政税收政策和舆论导向上予以支持。
只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底线外教育的体系,学生减负才不至于成为“令人忧心忡忡”的事情,素质教育才具有现实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