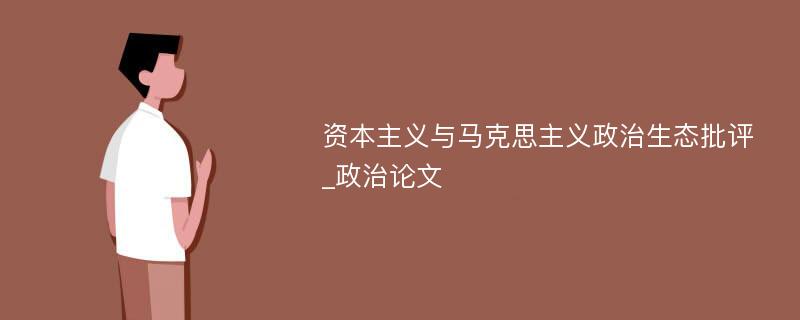
资本主义与对政治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司已经可以创造新的生命形式,而且很快就可以以地质工程学的方式“研究天空”。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所谓的“自然”还有自主性和能动性可言吗?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提供商品与服务的资本主义方式可以被说成是在“生产”某种从定义来看是被给予的而非被制造的东西?各种形式的“自然”是否可以及是否应该建立一种旨在改革或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呢?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积累的生物物理学维度如何能够被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因素呢?本文将通过回顾过去40年人们关于资本主义与我们习惯称之为“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便对这些分析性和规范性问题加以处理。 由于涉及的问题很宏大,而且相关研究著作很多,本文想集中考察已故地理学家内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著作。尽管史密斯只是众多研究资本主义与自然的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但是出于以下三条理由,他的几部相关著作却值得特别关注。第一,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他的这些著作就成为试图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作更广泛的“物质化”处理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和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地理学家重要的参照点。第二,即便那些没有关注史密斯这方面著作的人(他们大多是地理学学科之外的人),也可以让他们的贡献参照史密斯所坚持的一个观点而得到很好的解释,那个观点就是资本主义甚至按照它自己的形象创造了自然。当然,反过来说也适用:当参照其他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念,即自然可以反抗而且确实在反抗资本主义独特的请求来阅读史密斯的著作时,史密斯所坚持的这一观点可以得到多大程度的辩护?第三,尽管他后来试图修正并澄清他在《不平衡的发展》(Uneven Development)一书中提出的基本主张,但是这些主张仍然可以作不同的解释。一些批评家(包括几年前的我自己在内)在探明史密斯的“真实意图”时试图对此敷衍了事,因此却有可能忽视了他的思想的一些重要方面。我们可以将这些方面看做是“生产性歧义”。 总之,本文重点讨论史密斯关于资本主义与自然的论著,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关于这一主题(有时候被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基本命题与洞见。尽管我这样做的意图是要对这位在地理学界最富启发性的思想家表达敬意,但并不是要表达史密斯的贡献超过了研究自然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相反,我希望通过联系史密斯论证来解读他们的论证,以此阐明一些重要的观点以及一些长期存在的分析性和规范性分歧。鉴于相关文献已经很多,我在涉及史密斯自己的论著以外的论著时必然会有所选择。我对它们的解释源于20多年来浸淫于关于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与自然的争论,有时候我对史密斯的工作是有些同情的。 本文是以时间先后顺序来组织的。首先介绍史密斯的一个命题,即自然是被制造出来的。该命题于1980年末提出,并在他的《不平衡的发展》一书中得到充分阐述。同时我也会关注他写作的思想与政治背景。在这一篇幅很长的一节之后,将简要总结当时刚刚萌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学领域的其他一些论著,那些论著出版于史密斯的命题提出之后(大致是1987~2000年),他们往往忽视了史密斯的命题,参照史密斯来读这些论著,也对比它们来读史密斯的论著,并提出一些当时没有或很少有人提出的联系。然后将关注最近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它既包括了思想意义上的也包括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我要把史密斯最初的命题及随后对它的评论与更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学理论相联系,也要把它们与更广泛的政治与思想潮流相联系。自始至终,我所关心的问题都是对政治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要是离开了“自然”,是否还能发挥作用且又如何发挥作用。在此要对博学多识的读者表示歉意,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对所有的论著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考察。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个关于术语的问题、一个与本文所忽略的文献有关的问题以及一个有关“知识后果”的问题。史密斯从来没有自称为一个“政治生态主义者”,即便是在该术语自20世纪80年代初在地理学和人类学中流行起来以后,但是他关于自然的相关论著显然对这一术语给出了某种定义。毕竟史密斯一生主要致力于研究的文本就是马克思的中后期著作,而这些著作集中于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的社会定义、创造、分配、调节、效果与政治化,即“政治经济学”。阐明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隐而未宣的东西,就是要表明他的政治经济学始终有一个生态学维度,这正是史密斯和他的同道们所作出的努力。生物物理学领域为什么既使得作为资本的财富创造、增长和获取成为可能,又对它们构成了阻碍,无论从分析还是从政治的角度而言,这都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尽管史密斯很少提及该领域的论著,但不应该感到奇怪的是“政治生态学”的某些先锋人物比如皮尔斯·布莱基(Piers Blaikie),就受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论述的启发。 这里提到了布莱基影响深远的著作,似乎暗示着史密斯的论著与政治生态学领域之间应该存在着很强的联系,然而很奇怪这些联系却很少。史密斯对马克思所作的高度理论化的处理不同于布莱基、迈克尔·瓦茨(Michael Watts)及政治生态学其他先驱人物的具体而经验式的思考,因此尽管他的著作在政治生态学家当中得到了广泛的阅读,但是他们在研究中却很少使用他的著作。这里无法充分地审视自封的“政治生态学家”如何实施马克思的观点,也无法审视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研究自然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史密斯是如何阐发马克思的观点的。因此,在本文中提到“政治生态学”时并非指该术语所指的领域,而是指类似于史密斯著作的那些理论著作,它们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富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一个生物物理学的维度。 在处理“资本主义的自然”这个问题时,我们最终所支持的那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史密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给出的答案。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资本主义更为普遍,“正确地”获得这些答案让我们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振奋人心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与过去的几十年相比,大学更多地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但是对于产生对抗性的思想来说,大学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场所。要是没有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肯定会更加无足轻重,而且不会那么精致而复杂,尽管与上一代人相比,对它感兴趣的学者和学生都更少了。对史密斯来说(我希望对本文的读者来说也是如此),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会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道理,而这些道理是其他理论出于故意或别的原因而忽视的。正如我要表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一如既往地充满生气且尖锐而深刻,但是在政治上它似乎软弱无力,尽管20世纪90年代末以及十年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全世界范围内都表达了一种强有力的反资本主义情绪。 一、去自然化的自然:内尔·史密斯离经叛道的思考 1.一个独特的视角 30年前,西方资本主义为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全面而深刻的经济危机寻求解决之道。作为这场危机的一部分,左派政治组织在很多国家失去了以前的优势。有识之士早就发现,现存的“共产主义”远不符合任何值得信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理想。然而激进的梦想很难消亡:环境保护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在当时的许多西方国家都逐渐声势壮大起来。尽管从内部众说纷纭,但这些运动从根本上说是要挑衅主流的思想与惯例。大学为这些新左派们提供与他们的政治雄心相配的时间与场所,而他们的政治雄心是以强有力的哲学和理论为基础的。对那些试图理解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们也成了一个庇护所。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东欧国家一夜之间解体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大学以外就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词语,而且“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一个即将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上似乎已经占据支配地位。正是在这样一个冲突不断、狂躁不安的背景下,当时还年轻的地理学家内尔·史密斯于1984年出版了一本艰深的抽象理论著作——《不平衡的发展》。他在开篇解释说,该书是“通过考察和批判概念来更敏锐地审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 这本书的出版过程非常独特,我想强调其中的四条理由:第一,它对我们所谓的“自然”有诸多论述,尽管马克思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评论非常零散。事实上,该书属于最早的系统性尝试之列,即尝试着将生物物理学现象整合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并在此过程中将它们与空间、尺度及地理的不平等相联系。在史密斯之前,思考马克思的自然观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除去恩格斯外,还包括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塞巴斯蒂亚诺·提姆帕拉诺(Sebastiano Timparano)、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以及诺曼·盖拉斯(Norman Geras)。第二,用史密斯自己的话来,他的言论既“刺耳”又“不切实际”,因为他声称自然是被生产出来的而不是被给予的。他说,“这个观点公然蔑视一个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即自然与社会相区分。……我们习惯于把自然看做一种外在于社会的东西,它纯朴而且出现在人类之前,要不然就将自然看做一个庞大的宇宙,人不过是其中微小而无足轻重的一部分。但是在这里,我们的概念已经赶不上现实了。正是资本主义热情地蔑视承袭下来的自然与社会相区分的观念,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它有积累越来越多社会财富的持续动力……这样,资本主义就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形态。”第三,史密斯强调资本主义具有败坏道德的力量,这便让人们开始质疑20世纪80年代那种激进且更符合主流的思想背后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存在论假定。他坚持认为在社会话语、关系与惯例之外没有任何可以理解的自然,这便对大多数“环保主义者”的思想构成了挑战,也对以“人性”为基础的政策与政治构成了挑战,同时又对“自然科学”研究一个本质上“非社会的”世界、而社会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包括人文地理学家)研究其他东西这一观点构成了挑战。第四,史密斯拒绝将自然的社会特征限定于语言学框架或符号学的滤网内。 2.理解“生产” 在史密斯所谓的“生产”中,“新陈代谢”与“劳动”这两个术语占据中心地位。前者远不是一个类似于“互动”的词语,它假定所谓的“人与环境”或“社会与自然”是统一体而非二元体,主张“社会内在于自然之中”。在马克思和他看来,内化的驱动力来自于人的一种倾向,人总是倾向于把物质世界变成有用之物,从而改变他们自己的生理或心理“本性”。在《不平衡的发展》一书第二章一节标题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的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即所有的工作都不仅涉及一种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还涉及一种与他人的关系,而后一种关系制约着工作如何开展,也决定了“外在自然”中什么东西被认为是有用的,以及“人性”将因这些工作的结果而如何改变。这顿时让我们警觉,所有关于商品与服务的“生产”都不仅仅是个人从非人的世界夺取有用之物这样一个物理行动。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新陈代谢让我们警觉到流动(能量的流动、观念的流动和物质的流动),而劳动则让我们警觉到一些至关重要的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着这些流动的具体方式。 那么,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如何组织的呢?史密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见于其书第二章。与所有生产方式一样,资本主义也使得使用价值急剧增加。但是由于它不是一种自然经济,有用的东西被生产出来是为了交换。交换什么?史密斯追随马克思,认为是为了交换金钱。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来换取薪水,从而购买商品与服务,以便实现自身的再生产。资本家则要通过出售大量的商品来实现自身的再生产,并通过积累大量的金钱来确保商品生产的继续。总之,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关系使得“为了积累而积累”成为“一种由社会所强加的必然性”。这些关系使得扩大销量成为经济规范。 对史密斯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有某种特殊之处,这种特殊之处就在于雇佣劳动这种商品是财富之源,而财富是由资本家致力于积累的金钱所代表的。与主流经济学思想所持的商品并没有“内在价值”这一立场相反,价值不仅仅是由消费者的偏好所“赋予”的,利润也并不是产生于具体资本家的技能或效率。正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中所解释的,工人集体创造了并且无意识地异化了社会财富。在这里,新陈代谢是独特的,因为具体的劳动行为受到真实但却抽象的社会力量的严重影响。它之所以特殊还因为从一个层面来看,资本主义是单调乏味永不改变的,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却又是不断变化的。 因此似乎完全可以合理地说,资本主义“利用”、“依赖”而且经常“破坏”我们所谓的“自然”,但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生产了自然。毕竟史密斯自己也承认,我们往往认为自然是不能被生产的。史密斯始终坚持这种生产概念,而且是在严格意义上而不是在比喻的意义上的坚持。他还考虑过这样一个论点,即因为“自然”的某些部分不是由社会所生产的(比如熔岩、大脑或重力),所以必须小心翼翼地限定生产概念。不过他最终抛弃了这个论点,“这些比较极端的例子几乎不能证明‘自然的生产’这个命题是错的”。史密斯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他最后一篇重要论文中,他仍然认为“自然的生产急剧强化了,其维度也多元化了”。 3.为什么否认人化自然和非人的自然 史密斯写作《不平衡的发展》一书时,各种形式的“环保主义者”已经非常引人注目,为什么史密斯还要如此尖锐地批评“自然”具有自主的存在性和能动性或伦理道德上的可考虑性这种观点呢?这一问题引申出史密斯形成自己学术观点的背景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对自然—社会二元论的反动,这种二元论在史密斯所从事的地理学研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首先,史密斯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哈维无疑对他的思想具有重大影响。哈维1974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后来成为对新马尔萨斯主义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重要源头。哈维坚决反对世界“人口过多”这种观点,与强调经济增长的“自然限制”相反,哈维将生物物理世界如何影响社会这个问题进行了“去自然化”、“相对化”的解读。在他看来,人类的贫困和稀缺问题反映了物质财富比如食物的分配不公,因为社会财富的转移是不平等的,这样“增长的限制”就内在于资本主义当中。 第二,尽管哈维的注意力集中于“自然资源”,但他并没有集中关注“自然灾害”,比如飓风或海啸,这些威胁独立于任何社会条件。1976年4月的《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由三位地理学家共同撰写的论文,他们试图从社会而非自然的角度去理解自然灾害。他们注意到,与以前相比,更多的人受到极端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因此他们指出,是社会经济与政治因素而非其他因素使得一些人更加脆弱;避免居住于危险地区,或者投入更多的金钱以便用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未必是最好的办法;相反,解决贫困与社会边缘化问题就可以使得遭受最不利影响的人群更容易抵抗自然灾害。史密斯无疑注意到了这个论点。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史密斯会认为“利用了自然的权威观点几乎总是根源于关于社会的观点”。对史密斯来说,所谓脱离了社会的自然这个说法不仅使得资本主义的所有计划稳固下来并合法化,比如生物技术公司所出售的“基因疾病”的疗法,而且它也从概念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自我呈现的日常形式。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揭穿表象,并表明“自然问题”其实是社会如何界定、创造和分配它赖以存续的财富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去问自然阻碍了什么,或使我们能够做什么,而要去思考如何才能以更民主、更正义也更容易受到集体控制的方式来生产“自然”。 二、为“自然的生产”设定分析限制? 我们已经看到,史密斯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然始终是生产出来的。不过,在《不平衡的发展》和后来的论文中,细心的读者可以找到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比如“与重力不同,价值‘规律’并没有任何自然色彩”,而这个说法恰恰是构成了他的书试图加以挑战的那个部分。 究竟是史密斯本人观点前后不一呢,抑或是他表面上的摇摆不定反映了20世纪末资本主义的某些重要问题?毕竟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生物技术公司以极大的精确性在基因层面跨越物种之间的障碍已是司空见惯,同时一种新型全球化的资本积累体制既穷尽了自然的馈赠,又高估了环境吸纳废物的能力。或许资本主义生产了某些自然,但并没有生产其他自然,这就意味着史密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一种不同的“自然”概念,许多分析家都试图界定这一概念。虽然他们都没有特别关注史密斯的命题,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使用使得我们很容易在他们之间建立起联系。这里分两部分集中讨论七份文献。 1.资本主义对“自然”的不平衡的内化:生物物理学方面的障碍与机遇 前五份文献涉及对农业的分析,也关系到资本主义如何利用新的边远地区来满足对利润的追求。农村社会学家苏珊·曼(Susan Mann)和詹姆斯·迪金森(James Dickinson)主张农业的经济“例外主义”,即它向来抵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其生物物理基础有一定的关系。在投资和劳动(比如买拖拉机和播种)与投资回报之间有一条受自然决定的鸿沟(比如粮食作物生长所需要的时间),这使得农业对资本家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苏珊在其大作《农业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Agrarian Capit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论点。她认为自然的“障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农业仍然受租赁者、家庭和各种小农团体的支配。 不过,也有人表明这些障碍并非始终是障碍。大卫·古德曼(David Goodman)、贝尔纳多·索尔亚(Bernardo Sorj)与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从农业种植到生物技术:农业工业化发展理论》(“From Farming to Bio-technology:A Theory of Agro-Industrial Development”)一文中,主要解读资本家的公司是如何控制某些农业领域的。他们关注“侵占”与“替代”,认为前者是指先改变农民对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理解,然后生产农民,所需要的东西(比如联合收割机),后者是指用制造的产品(比如化肥)代替农场自产的东西(比如牛粪)。同年,马克思主义农村社会学家杰克·科洛本伯格(Jack Kloppenberg)在其专著《种子第一》(First the Seed)中阐释了这两个过程在美国的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农业科学和民选政府以某种方式间接建立的一系列向农民提供转基因种子的私人公司,实际上也是“自然的生产”,表明这些公司创造了一些新商品,这些新商品避开了农业积累以前所面临的生物学障碍。地理学家乔治·亨德森(George Henderson)在其研究加州规模农业增长的权威性专著中阐述了“金融资本”是如何通过贷款给那些面临积累障碍的农民来牟利的。 2.资本主义的生物物理环境 上述文献很少关注环保主义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表示的担忧,而且它们的分析也集中于自然的那些具有直接实用性的方面。但如何看待自然的其他方面,比如淡水、氧气、人的智力等,资本主义把这些东西看作免费的“馈赠”,或者看作排放生产的副产品的“污水池”。以“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之名著称的理论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解释资本主义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全面地恶化自身存在的生物物理基础;另一方面又要向马克思主义者和“左”倾的环保主义者解释为什么他们需要联合起来完成共同的政治事业。 其中有两位学者像史密斯一样,直接利用马克思的原著来批评资本主义与自然的关系。在《市场的未来》(The Future of Market)一书中,德国学者埃尔马·阿尔特瓦特(Elmar Altvater)致力于他认为被主流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严重忽视的一个维度……原材料和能源在生产、消费和分配过程中都经历了改变”,他认为资本主义劳动在这个改变中居于中心地位。在此基础上,阿尔特瓦特辨识出“生态学与经济学之间矛盾的五个维度”。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 Connor)也提出了类似的论证,他的很多论文都收录于1998年的著作《自然原因》(Natural Causes)当中。这些论文提出了“生产条件”、“生产不足”、“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矛盾”等概念,这些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很有影响力。“生产条件”是指资本主义所依赖但又并非由它来生产的所有东西;“生产不足”是指当资本主义把这些东西当作无限资源加以利用时,它们表现出来的稀缺性;“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矛盾”指的是在资本主义与自然打交道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生态辩证法”。奥康纳认为这个矛盾与马克思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一样重要,因此他建议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在反抗资本主义时,应该加入工会和共产主义组织。从这两位学者的视角来看,史密斯的命题无疑更多的像是比喻,因而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 3.一个假想的史密斯式的回应 史密斯会如何回应之前所提到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呢?在20世纪90年代他的两篇重要论文中都没有提及。只是鉴于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都不再是先锋,他可能会赞成阶级政治应该与自然政治联姻的观点,也肯定会认为这些学者把意识形态思维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史密斯在《不平衡的发展》一书第一章就基于这些理由批评了最早系统研究自然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史密斯明确主张抵制“对自然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自20世纪90年代初便在环保运动和绿色资本主义运动中很普遍。 史密斯的观点是清晰而直接的,他对资本主义自然的批评可以从“生产”的角度进行,但又避免陷入“白板论”(即资本主义不管愿不愿意都会生产自然),同时也可以诉诸于外在于自然生产过程的那些方面来进行。那种认为史密斯是一个既不赋予“自然”以能动性又不承认其道德价值的“超级建构主义者”是一种误读。 三、资本主义、自然与人类纪的激进政治 1.背景分析 21世纪初事端频发。之前对全球环境巨大变化的警告终于以更大的声音加以重复,从而使得环境政治在种类上急剧增加,加之2008~2009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重新引发了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从而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去思考一个更人性化和更具环境友好色彩的资本主义。尽管2012年召开了“里约+20”全球峰会,但环境问题已经被大多数大国置于议事日程之外,而且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一切生产都要服从于经济增长,加之某些资本家仍然决定再造自然,而不是去适应自然,因此有批评家指出,一些大国已经放弃或完全忽视了激进思维。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存在明显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在大学校园之外并没有被广泛地意识到,甚至在校园内部也是如此。在这种背景下,史密斯关于自然生产的观点可能会出于错误的理由而被认为“很刺耳”且“不切实际”。因为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所以我们对史密斯命题的价值评价也应该作出改变。 2.一种再自然化的马克思主义? 目前,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学家的著作备受关注,其中最重要的要属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及其助手。他们提出资本主义与生物物理世界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概念被理论界广泛认可,在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圈颇有影响。他们指出,资本主义正在使地球生物物理系统超出其运转能力,提出了“严重的行星生态危机”的观点,我们认为这是恰当的。它有助于纠正某些批评家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学中所发现的那种“普罗米修斯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甚至一些资本家实际上也意识到“第二个矛盾”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虚构。 那么史密斯对新康德主义的批评仍然站得住脚吗?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政治必须最大程度上预料到自然的能动性吗?史密斯本人曾对这些问题作出过回答。他在研究了资本家精英、环保主义者及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动员“自然”的新方式之后,得出了两条引入注目的论点:第一,他把“清洗自然”看做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的社会转化得到了很好的承认,但是由社会改变了的自然变成了我们社会命运的一个新的超越性决定因素”。第二,尽管人们普遍承认自然需要得到更好的照料,但史密斯却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更完整而彻底地吞并了自然。虽然资本主义在寻求可以变成商品的有用之物方面变得比以前更加贪婪,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种新的制度下,生产有用的自然这一任务开始从外部自然走向社会化的自然。 四、结论 本文考察了一些宏大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考察都很简要。可能我忽略了很多相关文献,不过通过联系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来集中讨论史密斯自然的“生产”概念,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关照了这些文献所关注的分析性问题和规范性问题。针对自然是内在于、还是外在于、抑或是既内在于又外在于资本主义的,自然是一种约束、还是机会、亦或是二者兼是,资本主义是否是“自然的敌人”、如果是,又是什么样的敌人,在资本批判中,“自然的政治”应该是什么样的等问题,我认为史密斯的观点具有分析上的优点,而且其包含的政治信息也是很有希望的——在他看来,我们可以并且应该改变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但不是因为任何源自生物物理世界的“客观”命令。 那么又如何落实到政治行动上去呢?马克思主义以试图改变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而著称。但史密斯的论证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在校园之外的现实政治中没有多少用武之地。要组织一种从生态学角度来反对资本主义的话语,“生产”这个概念似乎很怪异,甚至只是一种比喻用法。与很多论述自然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著作一样,史密斯几乎对现实政治只字未提。针对如何改善与自然的社会关系,史密斯坚持认为需要激进政治话语的新术语。可以预见的是,生物物理学问题,包括冰川问题、海平面问题、大气问题、气温问题、基因问题等,将在21世纪成为绝对举足轻重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决定我们未来的生活。资本主义当前在很多方面名声很坏,前景并不是很有希望,而马克思主义者能为我们提供一套非常具有吸引力且又不诉诸“自然”这样的常识性术语的解决方案吗? *原文标题为“Capitalism and the Marx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logy”,载于Routledge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的《政治生态学指南》(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logy)一书。标签:政治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论文; 地理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