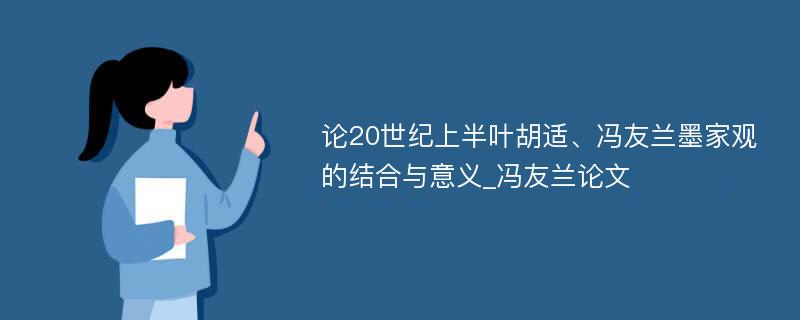
略论20世纪上半叶胡适和冯友兰墨学观的契合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意义论文,世纪论文,冯友兰论文,墨学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墨学为先秦显学,至秦汉以后几近中绝。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却出现了一股研究墨学的热潮,如胡适、冯友兰等人都有大量的墨学研究论著发表。如所周知,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冯友兰则是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二人的文化立场可谓“大异而小同”,但就他们对墨家学派的态度和看法而言,却是“大同而小异”。那么,为什么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会出现墨学热?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为什么对墨学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这是一些饶有兴味的话题,它们对于我们深入把握胡适和冯友兰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上述现象也表明,在20世纪上半叶西学盛行的历史背景下,即使分属不同文化立场的代表人物,也有着与时代精神密切相连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方法,那就是他们对西学的共同认肯,对民主、科学和现代化的拥护。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正是墨学最能与现代科学、逻辑产生共鸣,因而激发了他们对墨学的研究兴趣,并表现出“大同而小异”的墨学观。
一、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
胡适和冯友兰墨学观的第一个契合点,是其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方法并非历史唯物论所独有,早在先秦孟子就提出过“知人论世”的主张(《孟子·万章下》),强调对往古人物和思想研究要作历史情境的分析。胡适和冯友兰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分析传统,而且更注意用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考察思想产生的背景、原因并对其作出客观合理的评价。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说:“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定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胡适学术文集》,第101页)胡适指出,墨子出生在孔门正盛的鲁国,所以墨学与儒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方面墨子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另一方面他又针对儒家提出了诸多反对意见,比如:针对儒家轻视鬼神提出“明鬼”;针对儒家的厚葬久丧提出“节葬”;针对儒家重礼乐提出“非乐”;针对儒家信天命提出“非命”,等等。(参见同上,第103-104页)墨子的其他主张如“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也与当时的时代息息相关。胡适对墨学衰微也进行了历史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儒家的反对,二是政客的猜忌,三是诡辞泛滥。(同上,第172-173页)
冯友兰在《清华学报》第10卷第2期发表的《原儒墨》中,也重点解析了墨家的起源,指出贵族政治衰败之后,在失业大军中有一种专门帮别人打仗的职业,从事这一职业的可以称作“武专家”或“侠士”,“此等人自有其团体,自有其纪律。墨家即自此等人中出;墨子所领导之团体,即是此等团体”。(冯友兰,1984年,第321页)冯友兰认为墨家来源于侠士群体,其主张反映了这一群体的基本道德和主张。如墨家兼爱的目的是使天下人皆视人如己、互相帮助,这反映了侠士群体“有福同享,有马同骑”的道德;墨家的“尚同”则体现出侠士群体绝对服从团队领导的道德,等等。(参见同上,第327-328页)但墨子和墨家与普通的侠士又有区别:第一,侠士是帮人打仗的专家,而墨家是有主义的帮人打仗的专家,墨子的“非攻”就是专门替受侵略的弱小国家打仗;第二,墨子不仅是有主义的帮人打仗的专家,而且是宣传治国之道的专家;第三,侠士群体自有其道德,而墨子不但实行其道德,还把这些道德系统化、理论化、普遍化,使其成为社会的公共道德。(同上,第325页)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专门设了一节谈“墨家的社会背景”,用直白生动的语言重申了《原儒墨》中“墨子及其门徒出身于侠”、“墨学”是对侠士职业道德的发挥、侠士“更多地是出身于下层阶级”等观点。(同上,1985年,第62-63页)
胡适和冯友兰在分析墨学时所坚持的这种“知人论世”的思想理路,与历史唯物论所讲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方法有相通之处,而这与他们各自的学说以及受唯物史观的影响有着内在关联。
胡适称自己的历史观是不带色彩帽子的“秃头历史观”,也就是一种多元历史观。他说:“历史事实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虽然极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胡适文存》第2集,第160页)胡适虽然不承认经济是唯一的因,但不否认它是一种因,甚至认为它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同上)胡适还进而提出了他的“历史的态度”的主张,即要研究事情的发生、发展及其原因(同上,第1集,第276页),并把这种“历史的态度”具体运用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当中,认为哲学史的研究有三个目的:第一,“明变”;第二,“求因”;第三,“评判”。(《胡适学术文集》,第10页)可见,这样一种哲学史方法论本质上是历史主义的。这也是胡适能在墨学研究中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的重要原因。
20世纪上半叶的冯友兰虽然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从20、30年代开始他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兴趣。1927年在燕京大学时期,冯友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他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历史工作中,唯物史观也流传开来……唯物史观的一般原则,对于我也发生了一点影响。”(冯友兰,2000年,第186页)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坚持了哲学史的研究要与时代背景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认为哲学家的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盖人之思想,皆受其物质的精神的环境之限制”(同上,1961年,第16页),“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时代精神,一时代之哲学即其时代精神之结晶也”(同上),因此,“对于一人之哲学,作历史的研究时,须注意于其时代之情势及各方面之思想状况”(同上)。1934年,冯友兰从欧洲回来后作过两次演讲,其中一次的题目叫“秦汉历史哲学”,这是借题发挥,所要发挥的是他在当时所了解的唯物史观。他说:“唯物史观的看法,以为社会政治等制度,都是建筑在经济制度上的,实在是一点不错……一种经济制度之成立,要靠一种生产工具之发明”(同上,2000年,第201页);“有某种经济制度,就要有某种社会制度。换句话说,有某种所谓物质文明,就要有某种所谓精神文明”(同上,第202页)。可以说,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用历史主义的态度研究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一贯坚持的立场,其对墨学的研究也坚持了这种立场。
二、以西方哲学为参照进行中外比较研究
20世纪上半叶胡适和冯友兰墨学观的第二个契合点,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进行中外比较研究。胡适主要是以实用主义为参照,在比较中侧重于“求异”,冯友兰则主要从功利主义视角切入,比较中侧重于“求同”。两人的侧重点虽不同,但都是以各自接触和熟悉的西方思想来研究分析中国固有学术,并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因为,不论是实用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强调的都是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这在胡适和冯友兰对待墨学以及他们对中西学术共同点的分析中都有所体现。
胡适认为,儒墨两家的哲学方法不同,也就是“逻辑”不同。儒家讲“什么”,墨家讲“怎样”或“为什么”。(《胡适学术文集》,第107-108页)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换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处,知道了用处,才能知道事事物物的善恶是非。(同上,第108页)“为什么呢?因为事事物物既是为应用的,若不解应用,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应该改良了……能应‘用’的便是‘善’的;‘善’的便是能应‘用’的……这便是墨子的‘应用主义’。”(同上)墨子的“应用主义”也可称作“实利主义”,这个“利”和“用”不是指“财利”、“财用”,而是指人生的行为。在墨子看来,值得推崇的理论、学说是那些能够改良人生行为的理论、学说,否则就不值得提倡。仅知道几个好听的名词,或几句空洞的解说,都算不上真知识,真知识“在于能把这些观念来应用”。(同上,第110-111页)胡适还分析了墨子应用主义的具体应用,如“三表法”的第三表、“兼爱”、“尚贤”、“尚同”、“非攻”、“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等。(同上,第116页)所以,“墨子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只在于他的‘应用主义’。”(同上,第121-122页)
胡适用应用主义去解析墨学,与他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理念密切相关。在胡适所宣传的美国实用主义思想中,“用”、“效果”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这样一种理念去反观墨学,可以说胡适找到了两千多年前的“知音”。胡适在评价墨家名学时,认为它“在世界的名学史上,应该站上一个重要的位置”(同上,第154页),并通过中、西、印的比较论证了这一看法。胡适指出,在法式(Formal)方面,墨家名学远不如印度的因明和欧洲的逻辑,因为印度和欧洲的“法式的逻辑”经过了千年的演进,所以有“完密繁复”的法式,而墨家名学的前后历史最多不过二百年,以后两千多年就成了绝学,所以没有形成发达的法式。平心而论,墨家名学法式上的缺陷很可能正是它的长处。(同上)第一,“墨家的名学虽然不重法式,却能把推论的一切根本观念,如‘故’的观念、‘法’的观念、‘类’的观念、‘辩’的方法,都说得很明白透切。有学理的基本,却没有法式的累赘。”(同上,第154-155页)而印度的因明学,自陈那以后,改古代的五分法为三支,法式上似乎更完备了,但却丢失了归纳的精神,因为古代的五分法含有归纳,而三支差不多全是演绎法了。古代的“九句因”很有道理,后来法式越来越繁琐,宗有九千二百余过,因有百十七过,喻有八十四过,名为精密,实为大退步。欧洲中古的学者没有创造的本领,只能把古希腊逻辑的法式演为种种样式,其实法式越繁,离亚里士多德的本意越远。(同上,第154页)第二,“印度希腊的名学多偏重演绎,墨家的名学却把演绎归纳一样看重。”(同上,第155页)墨家因深知归纳法的用处,故有“同异之辩”,故能成一科学的学派。(同上)可见,胡适是从反思印度因明学、欧洲逻辑学、墨家名学三者不同点的基础上,为墨家名学法式的不健全辩护的,在揭示前二者弊端的基础上肯定了墨家名学的价值。从胡适对墨家名学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归纳法的偏爱。
与胡适以实用主义解释墨子相一致,冯友兰则以功利主义看待墨学。他在“墨子及前期墨家”一章中的第四个标题就是“墨子哲学为功利主义”,认为“兼爱”、“非攻”、“尚俭”、“节用”等都是当时人们原有的主张,墨子不但躬身实行,而且经营出一套理论系统,这是墨子对于中国哲学的贡献。(冯友兰,1961年,第115页)这套系统与儒学根本观念的差异就在于其注重“功”、“利”,是一种功利主义学说。比如,墨子三表法中的第三表即“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乃墨子估定一切价值之标准。凡事物必有所用,言论必可以行,然后为有价值。”(同上,第117页)这个“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指人民的“富”与“庶”:“凡能使人民富庶之事物,皆为有用,否则皆为无益或有害……可见功利主义之注重算账。”(冯友兰,1961年,第119页)但认为墨子的功利主义具有狭隘性,如过度尚俭、过度非乐,等等。后期墨家发展了墨子的功利主义,“与功利主义以心理的依据”。(同上,第310页)冯友兰还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参照,寻找墨学与边沁学说的共同点,确认墨学的主旨是功利主义的。他说:“边沁以为道德及法律之目的,在于求‘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墨子亦然”(同上,第128页),并指出后期墨家的功利主义思想与边沁的学说如出一辙。《墨经》认为,“吾人所喜者为利,吾人所恶者为害。故趋利避害,乃人性之自然,故功利主义,为吾人行为之正当标准也”。(同上,第310页)边沁说:“‘天然’使人类为二种最上威权所统治。此二威权,即是快乐与苦痛。只此二威权,能指出人应该做什么,决定人将做什么。功利哲学,即承认人类服从此二威权之事实,而以之为哲学之基础。此哲学之目的,在以理性法律,维持幸福。”(同上)冯友兰的结论是:“边沁所谓快乐苦痛,《墨经》谓之利害,即可以致快乐苦痛者也。边沁所谓理性,《墨经》谓之智。欲是盲目的必须智之指导,方可趋将来之利而避将来之害。”(同上,第310-311页)显然,冯友兰是通过探寻墨学与近代西方某种学说之间的共同性来确认墨学的主旨,进一步深化人们对墨学的认识。
胡适和冯友兰选择以西方学说为参照来解读墨学,从根本上说是基于他们对用西方哲学诠释中国思想合理性的肯认。他们在研究中之所以注重运用中外比较法,与他们的知识背景以及对中外哲学共同性的认可有直接关系。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说,后期墨家的著作长期没有人研究,但“到了近几年之中,有些人懂得几何算学了,方才知道那几篇里有几何算学的道理。后来有些人懂得光学力学了,方才知道那几篇里又有光学力学的道理。后来有些人懂得印度的名学心理学,方才知道那几篇里又有不少知识论的道理。”(《胡适学术文集》,第28页)就是说,只有具备了科学、逻辑学、知识论的视域,才有可能发现墨经中的科学、逻辑学和知识论的思想。胡适接着说:“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同上),明确宣称他编撰中国哲学史的参照是西方哲学;而且这种参照是有价值的:“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同上,第767页)冯友兰也是这样,他说:“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哲学名之者。”(冯友兰,1961年,第1页)就哲学一词和近代哲学起于西方而言,中国的哲学史应当以西方哲学为参照。以西方哲学为参照,不仅是胡适和冯友兰两人的选择,而且是那一时代的思想潮流。如蔡元培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所作的“序”中说:“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胡适学术文集》,第1页)张岱年也认为,“如此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张岱年,第17-18页)
胡适和冯友兰少年时代接受的都是传统文化教育,后来又有长期留美经历,对国学和西学都有深切的理解和把握,这就为他们能够运用中外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包括墨学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深厚的背景。在他们看来,中外哲学虽有差异,但也有共同的问题和方法。胡适指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胡适学术文集》,第8页)其具体包括“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胡适学术文集》,第310页),这些哲学的门类以及所涉及的问题在中国古代都是存在的。冯友兰也指出,尽管西方哲学家对哲学的界定不同,但从主要方面看不外乎三大部分:第一是宇宙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世界之道理”(A Theory of World);第二是人生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人生之道理”(A Theory of Life);第三是知识论,目的在求一“对于知识之道理”(A Theory of Knowledge)。在冯友兰看来,以西方哲学的三大部分为参照,中国的魏晋玄学、宋明道学、清代的义理之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接近于西方哲学。中国古代的学说当中,“研究天道之部分,即约略相当于西洋哲学中之宇宙论。其研究性命之部分,即约略相当于西洋哲学中之人生论。惟西洋哲学方法论之部分,在中国思想史之子学时代,尚讨论及之,宋明而后,无研究之者。自另一方面言之,此后义理之学,亦有其方法论,即所谓为学之方是也。不过此方法论所讲,非求知识之方法,乃修养之方法,非所以求真,乃所以求善也”(冯友兰,1961年,第7页)。这段话明确指出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与西方哲学的共同之处。
三、逻辑和科学的视域
20世纪上半叶胡适和冯友兰墨学观的第三个契合点,是逻辑和科学的视域。在对逻辑和科学的重视上,胡适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冯友兰也同样观点明确。他们都以此为视域,解读了墨学尤其是后期墨家的逻辑学说和科学思想。
胡适把前期墨家称作“宗教的墨学”,把后期墨家称作“别墨”、“科学的墨学”。他还称后期墨家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为《墨辩》,认为“《墨辩》乃是中国古代名学最重要的书”(《胡适学术文集》,第127-128页),并对《墨辩》的知识论、逻辑和科学思想做了细密的解析。胡适认为《墨辩》的“知”有三层含义:一是“所以知”的官能;二是由外物发生的感觉;三是“心”的作用。三者合才有“知觉”。(同上,第133-134页)《墨辩》把知识的种类分为“闻”、“说”、“亲”,胡适认为第一种和第三种知识是有限的,而“说”即“推论”的知识则是《墨辩》的一大发明,“有了推论,便可坐在屋里,推知屋外的事;坐在北京,推知世界的事;坐在天文台上,推知太阳系种种星球的事”。(同上,第136页)胡适专设“论辩”一章,阐释了《墨辩》中“辩的界说”、“辩的用处”、“辩的方法”等。尤其对“辩”的七种方法即“或”、“假”、“效”、“辟”、“侔”、“援”、“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这七种方法当中“推”最为重要。胡适指出,“推”就是“归纳法”,也称“内籀法”,认为《墨辩》的归纳法只包含三种:求同、求异、同异交得。(同上,第138-152页)胡适还关注到了《墨辩》中的科学材料,涉及算学、几何、光学、力学等多个领域,同时还包含诸如心理学、经济学、人生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材料。(同上,第153-154页)胡适总结说:“墨家名学的方法,不但可为论辩之用,实有科学的精神,可算得‘科学的方法’。试看《墨辩》所记各种科学的议论,可以想见这种科学的方法应用……墨家论知识,注重经验,注重推论。看《墨辩》中论光学和力学的诸条,可见墨家学者真能作许多实地试验。这是真正科学的精神……总而言之,古代哲学的方法论,莫如墨家的完密,墨子的实用主义和三表法,已是极重要的方法论。后来的墨者论‘辩’的各法,比墨子更为精密,更为完全。从此以后,无论哪一派的哲学,都受这种方法论的影响。”(同上,第155-156页)
冯友兰与胡适一样,也从逻辑和科学的视角解析了墨家的知识论、逻辑学等思想,他的《中国哲学史》涉及《墨经》中关于知识的性质、知识的起源、知识的分类、概念的分类、辩的功用、辩的方法等内容,同时还探讨了《墨经》的“同异之辩”、“坚白之辩”,《墨经》与其他辩者和同时代诸家的辩论等。(参见冯友兰,1961年,第307-348页)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在某些方面对《墨经》的逻辑学思想作了更深入的研究,比如在谈到《墨经》的“故”时,他指出,墨经所谓的“小故”显然就是现代逻辑学所谓的“必要原因”;墨经所谓的“大故”显然是现代逻辑学所谓的“必要而充足原因”。(冯友兰,1985年,第146页)在谈到《墨经》的“效”时,冯友兰指出,在现代的逻辑推理中,若要知道某个一般命题是真是假,就用事实或用实验来检验它,这是演绎推理,也就是墨经中所谓的“效”的方法。(同上,第146-147页)冯友兰也指出了《墨经》的某些不足,如认为现代逻辑学还区别出另一种原因,即充足原因,可以说是“有之必然,无之或然或不然”,墨家没有看出这一种原因。(同上,第146页)再比如,后期墨家在批评道家的时候揭示出了一些在西方哲学中出现过的逻辑悖论,只有在现代建立了新的逻辑学后这些悖论才得到解决,因此在当代逻辑学中,后期墨家所作的批评不再有效了。(同上,第154-155页)这是以现代逻辑为视域对《墨经》逻辑思想的深入解读。然而,冯友兰并没有否认《墨经》的价值,他说:“我们看到后期墨家如此富于逻辑头脑,实在令人赞叹。他们试图创造一个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纯系统,这是中国古代其他各家所不及的。”(同上,第155页)这段话肯定了后期墨家对中国哲学史的独特贡献。
胡适和冯友兰以逻辑和科学视域研究墨学,基于他们对逻辑和科学的自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就是科学和民主的拥护者和宣传者,也是后来“科玄论战”中坚定的科学派的代表。他把实验主义方法与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结合起来,注重用证明的方式筛选史料、辨别真伪,蔡元培称其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第一个特长,它“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见胡适学术文集》,第1页)。冯友兰也主张用科学的、理智的、逻辑的方法建构哲学体系、研究哲学史。他虽然反对维也纳学派取消形上学的哲学主旨,但却吸收和运用了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建构了“新理学”的形上学。他认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冯友兰,1985年,第378-379页)当时有人认为,“研究哲学所用之方法,与研究科学所用之方法不同。科学的方法是逻辑的、理智的;哲学的方法是直觉的、反理智的”。(同上,1961年,第4页)冯友兰反对这种观点,指出:“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凡著书立说之人,无不如此”(同上),“一个道理,是一个判断,判断必合逻辑。各种学说之目的,皆不在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其方法必为逻辑的、科学的”(同上,第5页),“科学方法即是哲学方法”(同上)。冯友兰进一步指出,逻辑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对道理的论证和证明,借荀子的话说,叫“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论证和证明只存在使用逻辑的水平的高低,不存在使不使用逻辑的问题。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胡适和冯友兰的墨学观由于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自觉的反思意识相联系,表现出了超越思想史的方法论意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代,科学、民主无疑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时代精神。在胡适、冯友兰等人看来,在中国固有的学说思想中,只有墨学的科学、逻辑思想最能与之产生共鸣,所以他们不仅对墨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还表现出了相同的墨学观。胡适、冯友兰在墨学研究上所表现出的这些共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哲学史研究依然具有启发意义:第一,在历史、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中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仍具重要性。因为哲学史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哲学史本身,而必须阐明某种哲学之所以产生、发展并形成影响的社会历史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对哲学史做出深度透视。第二,以西学为参照进行中西比较研究仍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在今天看来,胡适、冯友兰等人直接以西方哲学解读中国哲学不免有牵强附会、湮灭中国哲学主体性等一系列问题,但在20世纪上半叶这是大势所趋、潮流所致: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努力,就不会有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出现,也不会有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中国的学术就可能还会在经史子集的框架内、在经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下原地打转。因此,胡适和冯友兰及同时代的思想家选择以西方哲学为参照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从而创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是符合中国学术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趋势的,也是我们今天进行学术研究仍需借鉴的。当代世界是一个文化交流、融合的时代,从20世纪开始的世界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世界化的双向运动一直在持续展开,故恰当地运用中外哲学的比较方法,不论是对于深入理解外国哲学还是中国哲学,进而促进双方的发展,都是必要的。第三,胡适和冯友兰对逻辑和科学方法的自觉和重视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固有的思维中不缺形象思维和辩证思维,缺乏的就是严密系统的分析、实证思维,它们是近代以来科学方法的核心所在。今天的理论研究如果离开了逻辑和分析方法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标签:冯友兰论文; 胡适论文; 功利主义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墨子论文; 读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逻辑学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哲学史论文; 哲学家论文; 科学论文; 墨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