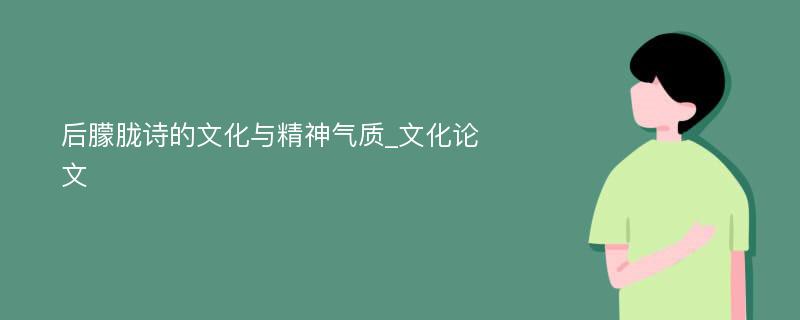
论后朦胧诗的文化与精神气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朦胧诗论文,文化与论文,气质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于坚在《赠小丁》里别有用心地写道:“至于诗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嘿嘿冷笑”,时代的尴尬造成了诗人的尴尬。后朦胧诗自从确立其身份和姿态以来,就一直面对着政治、技术理性、商品经济结盟的意识形态压力,尤其是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使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转换,人的生存变得日趋表层化、平面化,对内在精神的渴求愈来愈被肤浅的欲望所取代,作为民族触角的诗人所营造的语言幻觉显得越来越轻飘。诗歌事实上正逐渐遭到社会大众的遗弃。王寅对“大家冬天仍然爱一个诗人的感谢”(《朗诵》),俞心焦对诗人末日的《悼念》,伊沙的《饿死诗人》和“在冬天”“给诗人收尸”的宣告(《悲愤的收尸者》),以及刘漫流向“未来的读者们”“郑重托付”“这些”“主人已逝”的诗篇的举措(《致未来的读者们》),还有廖亦武在《死城》、《黄城》中对“无出路”状态的展示等,都表明我们已进入了思想贫困时代。后朦胧诗的语境完整地经历了尼采的“上帝之死”、德里达和福柯的“人之死”、利奥塔德的“知识分子之死”而抵达了“悲剧之死”的境地。在这过程中,后朦胧诗歌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流向,诗人们要么随着时代一起破碎、瓦解、变动,要么转向关注精神超越性和价值追问性的永恒命题,即从拆解与重构的不同角度给当下的诗歌本体命名。前者倾向于书写当下的生存状态,包括对琐屑生活细节的迷恋、排斥,对个人感受的呈现等等,总体上表现出对生命领域的全面暴露;后者则以社会良知、历史或文化代言人的身份主动承担价值重构的责任。与“史诗”、“回返传统”的诗歌不同,后朦胧诗歌中的相当一部分更注重以一种人类大文化作为思考的背景,专注地将精神因素导入与上帝体系有关的一切,顺承并超越了朦胧诗的广义性,从而成为精神贫困时代体现“终极关怀”的神圣标本。海子、骆一禾、西川、戈麦、欧阳江河、陈东东、张真、臧棣等诗人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这一追求。
海德格尔认为,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夜中追问终极价值之责任的诗人,都称不上这个贫困时代的真正诗人,贫困时代真正诗人的本质在于:诗的活动在他身上成为对丧失了绝对价值的诗的追问。为此,诗人必须把自己诗化为诗的本质。面对价值观念行将毁灭的时代,要么提出与传统信念完全不同的新的观点,要么处在这种危机意识中,对历史上的传统信念再反思、再审察,以帮助了解我们的境况,寻找世界意义存在的基础。在海子、骆一禾等诗人看来,诗负有对人类的精神归宿、对人的灵魂道路的抉择和确立的崇高责任,负有克服主观和客观、人和自然、意识和无意识、自我和世界分裂的责任(《倾向》1998年第一期《前记》)。不管这种叩问和建构“精神乌托邦”的努力在当代显得多么虚幻和软弱(海子、骆一禾、戈麦的相继弃世是有力的注脚),它毕竟给这个贫困时代注入了“灵魂”因素,而把人类引向深度生存的形而上问题,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失的。
后朦胧诗首先揭示了理性文明和欲望对精神世界的扼杀,展现现代人灵魂的漂泊状态,丧失家园的疼痛感、焦灼感与重建家园的深层渴望交织在一起。“土地”的丧失,使“现代人 一只焦黄的老虎”所能找到“替代土地的 是一种短暂而抽搐的欲望/肤浅的积木 玩具般的欲望”(海子《土地》),大地即精神家园本身恢宏的生命力只剩下欲望,可见我们丧失之多:“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海子《秋》)。不少诗作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整体语境从政治逐渐转向经济,文革对人性的摧残以及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这两种混合力量的陈述,曾经构成了80年代一段短暂的文化复兴运动,其总体特征仍然源于对政治问题的关注。也就是说,文化没有回到自身,精神的不安来自政治化社会的缺陷。但商品经济确立起主流话语地位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文明受到工业文明日益强大的挑战,转型期的所有矛盾暴露无遗,金钱、权力和技术成为压制一直享受崇高地位的文化精神的决定性要素。俞心焦看到了“被诗歌滋养的土地正大片大片地丧失”(《才能》),不禁嘲讽地问道:“在深夜,在举着灯笼的地方/那些摸惯金币的手还能摸到什么”(《子夜》);雪迪则用象征手法描述黑夜的来临:“乌鸦从脚下/贴着我的血管向上飞来……在虚弱的‘艺术’外面,什么东西/能有效地摧毁人类亵渎灵魂的罪恶”(《乌鸦笼罩麦田》);孟浪的描述更为有力:“这一阵乌鸦刮过来/像一片足够用力的种子/在我身边的土地上撒遍”(《这一阵乌鸦刮过来》);还有郑单衣在《夏天的翅膀》里对“黑夜统治着世界”的宣告,王家新《赞美》“秋天来了”、《预感》“这时房子在漂流,你的灵魂/开始漂流”等等,众多诗歌都注意到了文化精神濒临沦丧或正在沦丧的事实,人们愈来愈远离内心,远离情感和玄思。价值体系的松散悬浮状态让人们处于普遍的放逐之中,乌鸦、石头、秋天、黑夜、村庄等众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表明了世界存在的荒芜,对人的灵魂真切的威胁来得那么迅猛和彻底。“家乡的红果园/心灵的创伤连成一片/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家乡,火红的云端/一团烈焰将光滑的兽皮洗染”(戈麦《红果园》)。诗人担当着寻求信念、确立价值的使命,萨特说“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广义的真正诗人就是为人的灵魂立法者、精神牧师,连同精神本身使人区别于动物。诗人关心的是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世界的命运以及我的命运、整个人类的命运究竟怎样。但是现实的变动,日趋强化的物质化、商品化的世俗观念,无情地摧毁着精神层面的东西,旧的价值核心已然消解,新的文化体系尚未明朗,连诗人自己也感到梦想和沉思缺少依托:“写诗如同活着,只是为了/责任,或灵魂的高贵而美丽/……然而,一次又一次,我这样说了/也试图这样去做,但有什么意义/当面对着心灵的荒漠/和时间巨大的废墟”(张曙光《责任》)。可以说,在后朦胧诗人那里,写作的责任和有效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裂,原因在于整个文化话语的边缘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明悠久浑厚的优越感第一次在文人(诗人)身上如此失落,但传统文化的力量在知识分子的血液里又是如此浓厚。然而,“写作乃是使命与拯救的问题……是一个终人一生一刻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注:〔法〕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32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真正的诗人一如雅典娜神庙的猫头鹰,只在夜色中飞叫。虽然中国的后朦胧诗人没有经历过人本精神的历史性蒙难,如西方的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荒原”;甚至也没有朦胧诗人对“文革”摧残人性的切身体会,并且又是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他们对神圣价值缺席的不安未免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但这种精神因素的出现,正是诗歌摆脱琐屑走向“大气”的预兆,也是人的生存境界趋于升华的转机。精神世界的内蕴与外部世界的文明表现是成正比的。
因此,诗人笔下的无家可归感才会如此深切。“母亲如门,对我轻轻开着”(海子《思念前生》)这句诗中,家被影射为母体,诞生就是离家,就是永劫不返的放逐,家园依旧存在,但难以返回,也难以远离。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在这里被隐喻为肉体与灵魂的对视。杨炼《房间里的风景》也把家看作回不去的灵魂深处的异地:“那座我回不去的老房子/你也回不去了”。在长诗《幽居》里,杨炼更将家园与水连在一起,使之成为水上居所,这意味着幽寂的家园乃是建立在漂流、流逝这样的借喻基点上的,与通常意义上掩饰、稳定、安全的家含义相悖,实际上从本体角度否定了家园,荡荡游魂就成了当下直至以后生存的现实。王家新笔下的精神家园是“存在”的,但没有生命进入,没有生气灌注:“没有人。这条独自伸展的峡谷/只有风/只有满地生长的石头”(《空谷》),暗示了现代人精神的耗空状态,是人自己背弃了家园。这种倾向即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天空中已响起死亡的脚步/几万只死亡的脚步踩在我头上/多么辉煌!城市远离我们,岸远离我们,鸟群在风中/寻找它最后的家……我负债累累/我已无路可走……”(《终曲或开端》)。西川也流露出很浓重的悲观情绪:“就像上帝需要肉体的爱情/我想人类需要永恒的休息”(《海边的玉米地》),因为他对人类自己的罪愆感到绝望:“请把羊群赶下大海,牧羊人,/请把世界留给石头”(《把羊群赶下大海》)。极度的反讽暗示了灵魂救赎的可能性的渺茫。
诚然,任何文学的文本都是一种“语境的作用和表达”,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现实的产物。后朦胧诗中出现的关于精神因素的陈述,也是一种现实态度,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中国历来缺乏形而上学传统,“实践理性”是其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人们大多关注当下的生存境况,即使道家所追求的精神张扬也是为了更大限度地全身入世,很少像屈原那样对天发出七十二问,并写出倾心关注人的生存的终极问题和具有终极意义的诗歌。后朦胧诗派中的少数诗人注意到了灵魂、精神受到压迫、排挤的事实。经济迅速成为社会时代的中心,原有价值体系趋于崩溃,道德良知逐渐衰退,都在客观上造成了人的精神资源的流失。更重要的是,精神家园的放弃是现代人的一次主动选择,或许这是走向现代工业社会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如黑格尔《美学》中预言的那样“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已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维持它从前的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地位。”“因为诗的原则一般是精神生活的原则”(注: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第5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所以诗的困境就是精神的困境。后朦胧诗中的无家可归感、对救赎的绝望感等,既是诗歌本身的生存现实,又是现实生活中人的精神状态的真实裸露。这部分诗歌的背景尽管着眼于世界、人类、时空之外的广阔领域,其实正是源于现实和对现实所进行的超越性思考。“而我们世世代代的家园/一天天从脚下飘去/此生匆匆走不出异乡/骨肉沉痛,如最后的晚餐”(欧阳江河《空中花园》),远离神性,背弃家园,都使人处于孤独无力之中,人们一面遗弃,一面寻找,自伤自悼,充满悲凉:“风吹麦地,风在道路上久久怀念着可爱的家乡”(骆一禾《久唱》);“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海子《答复》);“在刈后的麦田里谁是那/孤独的麦子”(西川《拾穗》)……“麦子”作为一种经常出现的意象,与“麦地”、“家园”、“土地”等意象联系在一起,代表着人的生命源头和精神背景,强烈的“家园感”和“还乡意识”正是通过一种诗意化的实体——麦子而渗入内心世界的。麦子蕴含天地人三者之气,是我们这个农耕民族共同的生命要素,又在象征的层面上成为完美自足的精神实体,诗人常常选择它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情绪,甚至诗坛曾涌现“麦子”潮,表明了每个个体生命都面临着生存价值的危机,面临着物化、远离精神家园的危险,诗人呼唤的正是仅存的麦子所代表的人类精神。对没有意义、充满价值虚无主义的人生,诗人满怀忧虑:“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海子《九月》),“那九月山峦背后的又是什么?使生命与远方相联,使这些/卑微的事物梦见远方的马匹/我们正被秋天的阴影所覆盖”(西川《眺望》)。
这样,天地人的世界最终显现为无情无爱无信仰的世界,人将蜕变为“石头”,与动物的生存无所差异,这是作为精神实体性的诗歌所坚决拒斥的。从古至今诗人不断地反抗历史的规定,以自己存在的尖锐性突进到某种价值形态中去,从而确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克尔凯戈尔曾说,“要是一个人想使自己的生活多少有点意思,而不是像动物那样,……那么,就必得要有某种更高的东西存在,通过它,人们可以走向高处。”(注:转引自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241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正如于坚在《避雨之树》中所写的,人们需要一种内在的支持:“它像房顶一样自然地敞开 让人们进来/……在这棵树下我们逃避它稳若高山/……但我不惊慌 我知道它不会倒下 这是来自母亲怀中的经验/……它是那种使我们永远感激信赖而无以报答的事物/……那时候全世界都逃向这棵树……”。这棵“树”便是某种精神力量的象征,给人以庇护、鼓舞和生存的安全感、充实感。它使人在现实中摆脱了失重心理,满怀着对神性的向往和崇敬:“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青草向着群星疯狂地生长/鸟群忘记了飞翔/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我成为某个人,某间/点着油灯的陋室/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这种近乎宗教的精神力量,超越了广阔的时空,超越了有限的自然和有限的人类,个人在它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和简陋,不由不对它表示虔诚和敬畏,所有世俗的观念于此一扫而空,只有这股神性的力量弥漫着宇宙。成为引导人们“走向高处”的“某种更高的存在”,即这种神性精神,正是横亘古今的对人的精神的有效拯救。精神家园的存在是生命本身的必然要求,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不仅仅靠欲望活着。
后朦胧诗中出现的“新浪漫主义态度”,对精神沦丧、终极价值和意义诉诸悲痛关怀的宗教般的情怀,对生存、死亡、困境、超越的深入表达,都以一种极端个人化的语型即“准元语言”形式完成了对自身的精神建构。不少诗人通过诗歌建构或尝试着建构“精神乌托邦”,把人对现实的需要落实到大地上。海子“用幸福也用痛苦/来重建家乡的屋顶”(《重建家园》)的愿望,王家新“把一尊石头推向峰顶/然后看着它滚下来/然后再走向它/伸出双手”(《西西弗的神话》)的执著,骆一禾“灯光啊/看见你的时候/我便停止了呼吸”(《屋宇》)的献身真理的决心……一方面向着现实对话,一方面在诗歌内部进行精神元素的结构。
海子认为“伟大的诗歌”“作为一些精神的内容(而不是材料)”必然高出于它们的艺术成就,“作为一批宗教和精神的高峰”必然超于审美的艺术之上,是“人类的集体回忆或造型”(注:海子:《诗学:一份提纲》,《海子、骆一禾作品集》第162页,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骆一禾“所热爱的诗歌语言是精神直接的出现和打动”,“关注的是语言环境中精神的丰富和深度”,他认为“在诗歌中,获得精神大势和在世界诗歌领域中考虑写作是最重要的”(注:《东方金字塔——中国青年诗人十三家》第10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西川也认为“一首优秀的诗作会具有宗教般的净化力量”,希望大智者的“金链”“不会在我们身上中断”(注:分别见于《中国当代实验诗选》第21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磁场与魔方》第314页。)! 三位诗人对诗歌的理解直接导致了他们诗歌的特殊话语方式,诗中出现的诸如太阳、神、马、豹子、但丁、王、羔羊、狮子等大量充满象征意蕴的元素,使他们的诗歌尤其是长诗非常切近“表现一个民族的朴素意识”的“正式史诗”(注: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第109页。),诗中民族和个人没有分裂,意志、情感、原始生命合二为一,含有世纪末的衰败与世纪初的创世的双重特征,无疑表明了诗人追求某种“精神母本”、重建精神乌托邦的浪漫情怀。
由于长诗更能完整地揭示出它自成一个世界的独立本性,更能综合地体现精神的深度、复杂性、广袤性。因此,后朦胧诗中的精神因素于此格外鲜明。
西川的《远游》展示了远游者在北极星照耀下的天国旅程,也就是人的精神的超越飞升。“在我灵魂的深处,/攀登者所攀登的是鸟类的阶梯;/在我灵魂的深处,/泅渡者所泅渡的是星光的海域”,这些远游者——俄底修斯、三藏、马可·波罗、但丁、乔叟、诗人自己等,为追求某种真理而开始了他们的精神之旅,尽管“有限的是一个远游者,/无限的是他的必由之路”,个体生命总是处于死亡和时间的永恒之下,但强大的精神辐射力使得有限的生命最终超越了死亡。“当我能够从这歌声中分辨出/大海的音乐,一座精神的大海,/便有如解放的太阳胜利地上升!”远游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凋谢的大地使我忧伤”,“二十八个巡逻兵/在星空迷路,一个反抗生活的少妇/提灯问路,风尘仆仆”,唯有北极星“依然放射出压倒一切的光明”,“那些恒常的事物”“使我们得以超越尘埃的阻碍,/领悟伟大和公正”。西川在诗中用“在永恒的高度放射金辉的事物”即永恒的精神实体洞穿了生命的黑暗和盲目,既是对当下社会文化境遇的反抗或重建,又从本体上确立了人类精神自身的优势。
骆一禾也有一首类似的《修远》,“想起方向的诞生/血就砍在了地上”。他更注重的是血与火、精神与罪恶的搏斗,在《世界的血》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这部长诗以血为核心,以人的孤独与恐惧为两翼,展开生命的主题。面对苦难、死亡和黑暗,生命开始了超越。“黑暗是永恒的,而光明/必须运行”,诗人的目的就是要建筑一座真理的屋宇,一座精神大厦:“我所创立的屋宇和艺术/头顶有朝霞穿过狮子 过海而来:不惧死亡者/必为生命所战胜”。对死亡的抗拒,对生命底蕴的窥探,对超越困境的信念的执著,对永恒与世俗、肉体与灵魂互搏的“生存之地”的刻画,一起完成了对某种人类精神的检阅与重塑,对宿命的冲刺和对神性的张扬。
西川是从求索真理的角度,骆一禾是从生命入手来展现精神的因素。相比之下,海子诉诸终极关怀的诗篇格外深痛。他把自己看作负有重整乾坤责任的诗人,“我的事业 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祖国,或以梦为马》)。他的长诗遍布着象征性的精神因子,不管是借用西方经典文学的,还是独创的,都被以一种“先知”或“圣徒”的口吻陈述着。诗中个体生命的悲怆、激愤与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怀紧紧相联,现实场景与幻象场景相互交叉,在总体上属于“原始的图腾与冲动”。他的长诗《太阳·七部书》(未完成)就是一个庞大的精神象征体系。《传说》、《太阳》、《土地》等诗中,诗人反复提到人类的末世情调,提到生存的苦难和艰难:“土地。句子。遍地的生命/和苦难”,“没有一支解脱的歌”(《传说》),“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因为“上帝本人开始流浪/众神死去。上帝浪迹天涯”(《太阳》)。这种局面使诗人的救世理想屡屡陷入怀疑绝望之中,虽然企图“为自己和未来的昆虫寻找文字/寻找另一种可以飞翔的食物”(《传说》),但“我孤独一人/没有先行者没有后来人”,“被生存的真实刺瞎了双眼”(《太阳》)。诗人的无力、绝望是相当明显的,诗歌营造的幻象实在不堪一击。
但海子更多地呈现了原始粗糙的生命和表情,那是以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为代表的原始力量的互搏,海子极度赞美“人类的集体回忆或造型”的“精神大势”。“鼓!节奏!打击!死亡!快慰!欲望!”富有爆炸力的句式,形式上的急骤显示了生命的狂躁不安。《土地》四季循环的结构设置,也象征着内心的冲突、对话、和解,那就是代表生命力的“火在土中生存、呼吸、血液循环、生殖作为灰烬和再生的节奏”,就是显示生命黑暗底蕴的原始力量:“我假装挣扎 其实要带回暴力和斧子/投入你的怀抱”(《土地》)。海子诗歌即他内心的巨大空间之间的落差最终导致了他的陨落。
说到底,“诗是一种精神”(注:E·M·福斯特:《天国之乐》。),后朦胧诗中的精神乌托邦因素尽管在当时有如空谷足音,但诗歌绝对不能放弃对人类的信仰、价值、生命、民族和超越精神的关注。作为最具反叛性特征的诗歌,应该在商业文化的媚俗倾向中确立自己的形象。海子的自杀并不是某种悲剧精神的结束,相反它在文化上代表了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的精神的源头。
标签:文化论文; 朦胧诗论文; 诗歌论文; 读书论文; 骆一禾论文; 美学论文; 海子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现代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