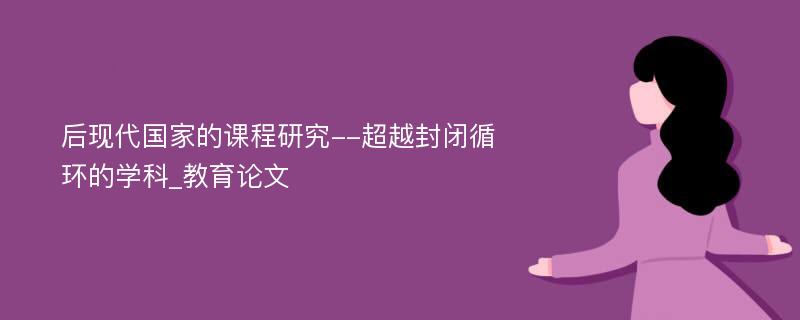
后现代状态的课程研究——超越封闭式循环的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闭式论文,后现代论文,课题论文,状态论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设定:情境与话语
不管你如何界定“后现代”,学校教育的危机在亦可称为“后现代状况”的问题情境中生成、彷徨,是谁都不能不承认的事实。在利奥塔(J.F.Lyotarod)的《后现代状况》(1979年)出版的同时,日本的学校实现了大约一个世纪的制度上与数量上的扩充,迎来了“现代化的终结”,科学技术信仰、产业主义神话、“启蒙的主体”的神话也统统丧失了,乃至“进步”与“发展”之价值也沧为衰退的情境。事实上,象征性地表现“现代”的“教育”、“教学”、“学校”之类的概念,丧失了锁定其涵义的“宏大叙事”而游移不定,不能不重新加以界定了。1980年代,“后现代的话语”华丽地登场,可以说,刺激、挑拨教育的论争乃是当然的归结。不立足于“后现代状况”的教育话语与言说,只能是对于“现代化”这一术语闪亮时代的教育的一种怀旧。
然而,在教育变革的实践中,“后现代话语”果真发挥了其华丽的语言与理论所体现的威力么?确实,“后现代的话语”在巧妙的隐喻与讽刺中,成功地揭示了现代教育话语的相对化,暴露了学校日常经验的潜在涵义,提供了跨领域的描述、论评教育经验的修辞。但另一方面,“后现代话语”反反覆覆的相对化,诱发了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在反映具体事物表层的无限的差异化的同时,助长了深层的均质化,终究招致了大量的异质话语象拼贴画那样拼贴起来的扩散式批评的倾向。进而引发了若干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作为应用这种话语的人们所特有的文化不过是停留于难解的隐语与话语的局部化与沙龙化,在华丽地批判学校与教师权力的同时,扩大了同教育实践的隔阂;或是通过教育概念的解构,丧失了教育的话语。本文就来揭示产生这种啼笑皆非现象的“后现代话语”的“封闭式循环系统”,探索克服这种弊端的方略。
二、范式的转换
在“后现代语状况”下,课程领域的话语发生了巨大的转换。正统化的“宏大叙事”的丧失,使人们对“进步”、“发展”、“启蒙”产生不信任,对“科学”与“理性”产生疑虑。其结果,导致了基于心理学与技术学的“课程领域”的“中立教学论”(neutral pedagogy)与“课程开发”(curriculum development)的概念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这是“课程领域”中的技术学隐喻与建筑学隐喻的终结。
可以说,这种范式转换的端绪是1970年前后对抗“课程领域”危机的一连串研究中所准备的。杰克逊(P.Jackson)揭穿课堂日常生活功能的“隐蔽课程”的问世、施瓦布(J.Schwab)所警告的行为科学支配下的“课程领域”的“濒死”状态、派纳(W.Pinar)从课程语源的个人自传性质作出的重建“课程”概念的论文、许布纳(D.Huebner)着眼于教育经验的多样性论述“课程话语”的复杂性的论文、梅汉(H.Mehan)借助课堂对话的分析探讨教学的社会性建构过程的民族学方法论的研究,可以说,为这种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准备。
范式的转换表现为从心理学与技术学过渡到政治学与社会学。影响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如:奥尔苏塞尔(L.Althusser)的《国家与意识形态装置》(1970)、弗莱雷(P.Freire)的《受压迫者的教育学》(1970)、伊利奇(I.Illich)的《非学校的社会》(1970)、布迪厄(P.Bourdieu)与帕斯郎的《文化再生产》(1970)、福柯(M.Foucault)的《监狱的诞生》(1975)、鲍尔斯(S.Bowles)与金蒂斯(H.Gintis)的《美国资本主义与学校教育》(1976)等等。
自那时以来,描述课程的话语,既摆脱了学科内容的话语,也摆脱了心理学与技术学的话语,转向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的话语。伯恩斯坦(B.Bermstein)的论述知识的分配与整合的论文(1973年)、阿普尔(M.W.Apple)的课程政治学(1979年)、吉尔(H.A.Giroux)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1983)等等,可以说是这种转换的典型表现。课程研究的性质从教育内容的构成这一“开发”与“技术”的修辞,转向学校现场发挥作用的权力关系的“批判”与“解释”的修辞。
“后现代话语”——利奥塔(J.F.Lyotarod)、鲍德里亚(Baudurillard)、德里达(J.Derrida)、詹明信(F.Jameson)等人——的话语与思考的样式之所以渗透了课程研究的领域,就是由于上述的范式转换的语脉。这种渗透正如建筑中的后现代的发展那样,展开了一连串的运动:从功能主义教育批判的角度揭示教育价值的“复杂性”与“对立性”,再从教育经验的“意义”赋权及其规范出发谋求相对化,“解构”(deconstruct)现代教育的话语,开拓复杂的、多层的话语空间与政治空间,并着眼于教育现象的文化意义的差异,重建“教育”的概念。1980年代,课程研究的基本概念从“功能”、“结构”、“构成”、“开发”等建筑隐喻的术语转向“权力”、“意识化”、“再生产”、“自我认同”、“共同体”等政治学与社会学的术语,进而转向“权威”、“场所”、“叙事”、“话语”、“语脉”、“文本”、“声音”、“身份”、“关系”等的跨领域的术语。这双重的转换意义巨大。它导致了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教育概念的重新探讨,从多元的、多层的语脉重新解释了日常教育经验的的复杂性与重层性。“课程领域”从伴随着“宏大叙事”的丧失的“濒死”状态摆脱出来,获得了崭新的天地。
三、封闭式循环系统
不过,“后现代话语”在课程的实践层面是否发挥了同“话语”层面的威力相匹敌的现实的力量呢?许多“后现代话语”在“暴露权力与权威”方面,激烈地抨击现代合理主义的普遍性,但自身并没有带来提出合理的、系统的替代方案的方法。这样,只能导致基于教育的差异化带来的解体的结局;或是陷入以“暴露与揭发”的自相矛盾而告终的倾向。倘若同意这种认识,那么,我们就得探讨从这种“封闭循环”“解构”“后现代话语”本身的方略。
“后现代话语”的“封闭循环”还可以指出若干。例如,“后现代话语”最得意的学校与教师的“权威”与“权力”的“暴露与揭发”这一现象,就是适例。以潜在课程为主题的一连串研究,暴露、揭发了“中立教学论”的课程深层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功能,开拓了课程研究的新领域。然而,倘若这种“权力与权威”的“暴露与揭发”仅仅局限于“中立教学论”的虚伪性与虚构性的批判,而且仅仅局限于把这种“权力与权威”还原、解释为同社会构成体结构的对应关系,或是还原、解释为社会再生产与文化再生产的结构,那么,这些话语不过是向实践者提供“绝望的话语”罢了,导致了在“封闭循环”中自身的解体。
实际上,“中立教学论”与“暴露与揭发”就象合镜一般同时形成的。一面是拼命地隐蔽暴露了的“权威与权力”,另一面是暴露、揭发所隐蔽的“权威与权力”。而且,在梦想抽空“权威与权力”的教育这一点上,两者是一致的。无论“中立教学论”还是“暴露与揭发”在一方以他方为前提才得以成立这一点上,构成了“封闭循环”。两者是循环往复地运动的。这种现象是一种基于表层理解的悲(喜)剧。杰克逊的“潜在课程”并不属于“暴露与揭发”的谱系,而是旨在重新界定教育经验与教育实践而提出的概念。德里达(J.Derrida)的“解构”也是在立足于一面批判课堂的权力、一面继续维护教师权力的矛盾之中而提出的概念。我们必须寻求的,不是学校与课堂的权力关系的“暴露与揭发”,而是“重组关系”。
“封闭循环”在抵抗“整体性”与“普遍性”而提出的“个性化=差异化”的话语中也可以发现。在它的背后,可以看到信息化社会中基于技术科学的“现实的模拟化=含义的游移”,与基于消费社会的市场经济的“商品差异化=事物符号化”的现象,这是重要的。教育的修辞从“生产”转向“消费”,描述教育经验的话语转向符号论话语。作为模拟的现实,误导人们走向事件意义之丧失这一黑洞,也误导人们走向诱惑大众的“历史的终结”。教育工作者的活动统统是一种“复制”,一种“消费”。在这里,“个性化=差异化”与“均质化”在同犯关系中齐头并进。这样,“后现代话语”包含了强烈的虚无主义,同时又提供了激进地批判教育这一文化现象的武器。
但是,在这种“个性化=差异化”中,必须留意的一点是,“后现代话语”本身是技术科学的网络与大众消费社会的自由市场这一“现代主义”的虚构为前提而成立的。”后现代话语”唯有立足于“现代主义”,才可能对“现代主义”作出尖锐的批判。倘若不认识这种关系,把“后现代话语”仅仅理解为“现代”的“否定”,那么,只能陷入“封闭循环”了。实际上,抵抗“现代”的普遍性规范,强调“多样性”与“差异化”的教育话语,不能不陷入令人啼笑皆非的状态:被信息网络与市场原理所束缚的“个性化=差异化”运动所吸收。无休止的教育的“个性化=差异化”运动,与其说是公共教育的“解构”(deconstruction),不如说是“解体”(destruction)。
“后现代话语”中的“他者性”的概念也可以指出同样的问题。抵抗“启蒙的自律的主体”这一现代个人规范的“后现代话语”,关注微分的权力中所构成的“主体化”,同时,另一方面,摸索在他者关系的网络中建构“主体”的方略。对于“声音”的“对话性”与“多声性”的关注,也许可以评价为从关系论角度重新界定“主体”的努力。象这些主张那样,我们必须在“他者性”、“关系性”、“共同性”中重新加以界定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范畴下的具体的个人。
不过,“后现代话语”中对于“他者性”的关注,在教育话语中很难说成功地析取了“主体”的概念。在这些话语中成功的一点仅仅在于,“解体”“现代自我”,在他者关系上微分并解释“主体”。但很难说由此提出了重建强韧的学习主体的实践方略。“主体”(subject)被还原为大量的他者关系,被“隶属化”(subjugation)了,由此也可以读出“封闭循环”。
“主体”的“录属化”这一事件表现在“课程领域”的种种问题上。例如,在“主体”“声音”的“复数性”要求“亲和”基础的理论(R.Roty),为教育与学习回归“共同性”提供了珍贵的启示。这种“主体”是从具体的权力关系之中抽象化的,阶级、民族和性别的认同,统统被剥夺了。现实的学习中的“亲和”是在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充满激烈的矛盾与解体的“主体的斗争”中形成的,这种原动力也在“主体”的“隶属化”中被忽略了。
“后现代话语”往往陷入的“封闭循环”,除了上述现象之外,还可以举出一些。“场所”、“文本”、“符号”、“他者性”等概念的非历史性,认识论、哲学语言学和文学评论的还原,文学评论中文学和电影文本的超语脉的运用,由于过剩的空论与势利导致的脱离教育实践,意义论解释与社会实践的隔绝,抨击“语言游戏”却又耍弄“辞藻花招”的悖论等等,可以说都是“后现代话语”的特征性的循环现象。
四、问题与课题
“后现代话语”带来的“课程领域”多彩的问题群与丰硕的修辞,为“课程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作出了莫大的贡献,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今天已经是探索“后后现代话语”的时代了。从课程研究的现状看,至今对于“后现代的语脉”的认识仍然不足,对于“宏大叙事”的怀旧仍然支配着学术界的底流。
这样说来,奔走于“后现代”的表层,在这里所说的“封闭循环”中唠叨相对化与差异化,只能助长对于教育的虚无主义与愤世嫉俗。这也是教育的自杀行为。我们需要的是丧失“宏大叙事”之后解构游移的教育经验之涵义的实践,在学校与课堂的“场所”里建构不断生成的“微型叙事”的语脉及其空间,并且以此为据点,持续地实现批评与创造的斗争。通过这种斗争,“多样性”与“复数性”的“后现代话语”的概念摆脱现代科学的“一般化”与“特殊化”的束缚,并且解构“个性化=差异化”的话语,在“个性化=特异化=普遍化”的坐标中获得锁定教育话语之正统性的方略。
基于上述论述,最后我们必须谈及根源性的问题。“后现代话语”介入之后,“课程领域”的话语焕然一新了么?经过“后现代话语”的洗礼,“课程”的话语已经从心理学与技术学的语言转换为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语言了。但是,这能够说,已经使“课程领域”从“濒死”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了么?“后现代话语”提供了丰富的跨领域的话语,但借助这些话语,并不是“学校”、“教育”、“学习”概念的“解构”(deconstruction),而不过是带来了它们的“解体”(destruction)。
确实可以说,在过去20年间,学究主义的课程研究引进文化再生产的社会学与批判理论的政治学,从“濒死”的状态中得以再生与活跃;通过同“后现代话语”的沟通,获得了丰硕的论评修辞。但是,在教育实践领域里,尽管“后现代状况”进展下的教师和儿童依然在痛苦地呻吟,但“课程领域”销声匿迹了。“课程”这一术语本身在教师的经验世界中,经历“濒死”的状态而陷入了“死语”的境地。那么,如何才能填补这个鸿沟呢?
要使“课程领域”的话语回归为参与教育的人们的话语,不是以“后现代话语”去“解体”“学校”、“教育”、“学习”之类的概念,也不是还原为其他学术领域的话语,而是必须开始综合的新的逼近:求得“学校”、“教育”、“学习”这些概念本身的“解构”与“重建”。为此,必须在教育过程中求得“后现代话语”本身的持续的“解构”;探索能够扬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对立的“学校”、“教育”、“学习”的概念。
“后现代”教育,可以作如下立场的体现——超越形而上学的“思辨”(speculation),指向教育实践的不断的“样式转换”(post mode)这一“未来完成”(post mode)的“投机”(speculation)——来加以重建。
我们同“后现代话语”沟通的课题,既不是否定“现代”,也不是“超越”。毋宁说,我们的课题在于持续的批评与创造:介入“现代”的解构,重新认识“现代”的多层性与重层性,挖掘埋藏于其古层与深层的教育实践的可能性,同时,摸索在所有场所编织“微型叙事”的亲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