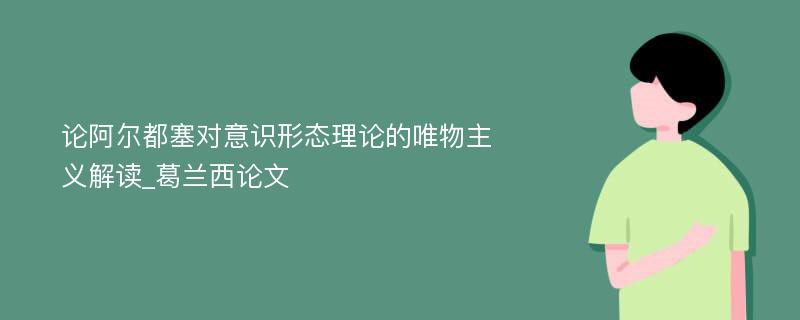
论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唯物化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论文,意识形态论文,阿尔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尔都塞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复兴的关键人物。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导论》中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区分为前阿尔都塞与阿尔都塞及其发展两个阶段。德国著名学者弗里兹·霍格认为,意识形态理论(theory of ideology)就是受到阿尔都塞的启发并在其影响下形成的。①霍格认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既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还原论分析和对意识形态与科学二元论的认识论解释,也不同于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政治统治工具的合法化理论。意识形态问题在阿尔都塞那里,已经上升到社会秩序的构成条件和统治的一般技术的问题。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不论是卢卡奇,还是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都是在意识及其异化的论域中阐述意识形态问题,从阿尔都塞开始,该问题的哲学论域从个人的意识转向社会结构,从观念和思想转向实践话语。詹姆逊在《列宁与哲学和其它论文》一书导言中指出,在阿尔都塞那里,哲学不是知识的特殊领域,而是一切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形式;哲学不是知识,而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这意味着书中的每个观念只能作为某个人的观念,作为从一个可识别的(政治的)立场出发的观念的意识形态投射:如果不首先否决意识形态的对手并揭露其意识形态的特征,阿尔都塞就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其观念的正确版本”。②这一论断可以运用于阿尔都塞的所有著作。
从《保卫马克思》到晚年的遗稿《相遇的唯物主义》,阿尔都塞的思想有一个复杂的流变过程,虽然他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立场没有改变,但理论的重心和具体观点仍然发生了重大改变。以至于学术界产生了一个阿尔都塞还是两个阿尔都塞的疑问。本文不是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全面探讨,而是主要讨论他晚年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晚年,阿尔都塞既拒绝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作为其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原型,也反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他通过社会再生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质询概念,从全新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做了系统的阐发。
一、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两种理论取向影响最大。以卢卡奇和阿多诺等人为代表的异化论传统,以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为基础,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意识的物化和异化。在著名的《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指出: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都从分析商品开始,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③在卢卡奇看来,商品交换的结构性特征不仅影响到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样也影响到人们对社会世界和自己主观世界的认识。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商品交换产生的普遍的物化意识。这种理解方式既是哲学的,也是社会学的。就前一方面而言,卢卡奇把黑格尔—马克思传统对实践的理解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人类的存在是以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实践活动定义的,就后一方面而言,“商品拜物教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④但是,这种意识形态概念总体仍然属于恩格斯所说的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理论范畴。阿多诺对所谓同一性的元意识形态的批判也是建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的。许多人认为,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代表着批判理论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向纯粹哲学批判倒退的顶峰,是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化的典型版本。然而,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仍然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价值规律——至少是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动力和它的发展与历史趋势——总是被阿多诺解释为先决条件”。⑤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明确表示:“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性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⑥虽然在阿多诺那里,同一性原则与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之间不能完全等同,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两者是相互重叠的。
但是,在阿尔都塞看来,商品拜物教理论的盛行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误入了歧途。他认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弱项,马克思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理论,因此,人们往往把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误认为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实际上,意识形态问题远比拜物教要复杂得多。从理论的反人道主义立场出发,阿尔都塞不仅拒绝承认拜物教理论对意识形态理论建构的核心意义,而且认为过于沉迷这个理论是危险的。“这些马克思主义毫不惧怕这样的事实,拜物教理论也提供了对马克思著作的人道主义和‘宗教’理解的跳板。”⑦然而,他认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并非科学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它本身就是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玷污的结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法权意识形态,从这种意识形态出发,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私有财产的交换关系。马克思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拜物教这一伪自然化的幻想特征,但本人也没有完全摆脱这一幻想。阿尔都塞明确地说道:“位于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的)意识形态核心地带的法律和司法意识形态,无疑也与‘劳动万能’的‘幻想’摆脱不了干系,而它又构成了名为马克思的哲学家的‘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幻想’的基础。”⑧总的来说,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虽然很早就触及到意识形态问题,并且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这个概念。但是,在他的体系中意识形态理论仍然是缺失的,后来马克思主义以商品拜物教理论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没有填补这个空白,反而把问题进一步引向了错误的方向。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最大问题是他始终没有超越意识哲学的论阈。“马克思,他从意识形态家(the ideologues)那里借用了‘意识形态’一词,虽然对其原有含义做了较大的改变,但基本上仍然把它视为与意识形式相关的事物,视为意识的‘客体’。”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不仅拾起经典意识哲学的主题,而且把自我的有意识行动视为主体行动的顶峰。虽然马克思承认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中的功能,但是,“可以保险地说,马克思基本上没有抛弃这样的观念:意识形态是由观念组成的”。虽然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抛弃了资产阶级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幻想,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感到有必要离开他从中获得意识和观念的哲学领域……虽然他明显相信意识形态负载着与实践的关系,或者与群体或阶级利益之间的关系,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跨越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的‘绝对界限’(the absolute limit),以及在阶级斗争物质性中的它们的物质存在”。⑨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还处在意识一边,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和它自身的物质性。
一般认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和霸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因为它不仅把意识形态从意识哲学带入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化领域,而且把意识形态作为霸权斗争的核心,从而使意识形态问题与政治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不论是威廉斯、斯图尔特·霍尔等人的文化研究,还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都把葛兰西的理论奉为经典。在他们看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决定论,为理解意识形态与统治和反抗等问题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理论框架。但是,阿尔都塞认为,从商品拜物教理论退回到文化霸权理论,同样不能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找到正确的道路。
在阿尔都塞看来,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中,霸权被还原为国家中的非强制因素,被等同于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就被理解为非强制的说服和共识,这样,霸权概念就唯心主义化和非政治化了。阿尔都塞毫不隐瞒地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推理引向它的结果,我们将得到结论:在霸权层面上可以玩任何游戏。第一,工人阶级、政党和它的联盟的霸权;第二,以国家为手段的统治阶级的霸权;最后,从国家的强力和霸权同一体中产生的霸权—效果。”阿尔都塞认为,霸权理论把革命阶级和政党的霸权与统治阶级的霸权合而为一,将使这个概念失去阶级意义,成为任何阶级都可以运用的中立工具。在他看来,脱离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来谈论霸权问题,“其高昂的代价是对经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现实奇怪地保持沉默,代价是一个缺少物质基础的霸权的绝对唯心主义,它没有解释强制机器(the Coercive Apparatuses)仍然在产生霸权效果中起主动的作用”。⑩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掩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物质再生产和阶级斗争在国家中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理论的最大问题是,它从来没有修正关于经济基础和国家的中立性假设,把霸权视为是在独立于强制国家的市民社会领域中起作用的非强制力量,也就是把霸权问题理解为社会整合机制问题。当我们把这样的霸权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其结果只能是把“意识形态还原为文化”,把一个具有理论价值的概念完全稀释为空洞的“文化”概念的同义语。
阿尔都塞从一开始就反对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与意识和意义相关的问题。在《保卫马克思》中,他已经阐述了这样的思想:意识形态既不是胡言乱语,也不是历史的寄生物,“它是社会的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但这一时期他主要强调意识形态的“无意识性”:意识形态是无意识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与意识无关的,“它们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是通过人们的‘意识’。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为人们所不知道的过程而作用于人”。(11)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主要运用拉康的想象界理论,把意识形态界定为人类与其生存条件之间关系的无意识想象形式,但他还没有明确提出意识形态本身的物质性问题。在《自我批评文集》(1967年)之后,阿尔都塞已经不再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无意识的文化幻象,而是明确提出,“意识形态不是纯粹的幻想(错误),而是存在于制度和实践中的表象体系:它们出现于上层建筑,根在阶级斗争”(12),并强调,如果不联系到社会再生条件,不联系到阶级斗争,不在社会制度和实践中找到意识形态的物质表现形式,一般意识形态概念是空洞和抽象的,由此阿尔都塞提出了著名的意识形态概念唯物主义化的新进路。
关于这一新的理论取向的意义,詹姆逊在《列宁与哲学和其它论文》一书的导言中解释道:“我们通常认为的意识形态立场——如思想、观点、世界观以及它们的政治意义和影响等等——从来不是存在于人们的头脑或个人的经验和意识形态之中;它们总是被制度和工具所支持、强化和复制的,不论这些制度和机器是军队或法律的因素,还是像家庭和学校这样的私人性东西,艺术博物馆、媒体机构、教会和小的基层法庭。意识形态首要和最主要的是制度,随后才是它对意识的影响。”(13)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阐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物质化的理论纲领。
二、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物质存在
阿尔都塞晚年在一般意识形态(ideology in general)和特殊意识形态(ideology in particular)概念之间做了区分,前者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后者只存在于特定的阶级社会。就对“一般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来说,阿尔都塞的思想与其说来自马克思,不如说来自拉康。在“弗洛伊德与拉康”一文中,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精神分析采取轻视和敌视态度是令人遗憾的。在思想方向上,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因为它们在理论上都反对人道主义,都认为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对阿尔都塞来说,意识形态不仅是永恒的,而且是普遍的。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它就像人呼吸的空气一样,是人的生存条件的一部分。按照拉康的理论,现实不是意识形态的基础,相反,现实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即使未来社会消除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般的意识形态仍然会存在下来。在这里,他对意识形态的理论依赖的是拉康的反认识论立场,即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人们以符号把握现实的先验框架。在拉康那里,人们总是生活在围绕着大他者建立的象征秩序之中,只有非常罕见的时刻,实在界才会现身,我们通常把握到的现实仅仅是象征秩序中介了的现实,而不是实在界本身。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不能超出意识形态。在其早期著作,特别是《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已经对一般意识形态概念做了系统的解释。在这里,他提出:“意识形态是一种对现实的必要曲解的表象”、“意识形态是一种人用来构成其生存条件的想象性表象”、“意识形态是作用于人的意识的统一的观念系统”、“意识形态起着社会融合功能”以及“意识形态没有历史”等一系列命题,以解释一般意识形态的特征。但是,这种意识形态概念总体上没有超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概念。对我们来说,阿尔都塞的真正贡献是对特殊意识形态的解释。在这里,他不仅把意识形态解释为制度和实践表象系统,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直接的唯物主义含义,而且把它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和阶级统治理论结合起来,解释了意识形态是如何在社会再生产及统治秩序的建构中起作用的。
1.社会再生产、统治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有三个方面:再生产条件理论、国家机器理论和质询理论,三者呈现出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进关系。社会形态再生产问题的核心是社会再生产条件的生产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的核心是劳动主体的生产问题。正如马克思在劳动力的商品化中找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突破口一样,意识形态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来解释。劳动力的再生产条件依赖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劳动力的生存所依赖的物质条件的再生产,二是劳动者技能和角色意识的再生产。阿尔都塞指出,有用的劳动力必须是有用的,而有用的劳动力不是天生的,他需要掌握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联合生产所需要的技能,而这种技能是由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种因素生产出来的。“用更科学的方式来表达,我要说的是,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的不仅是它的技能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对既有秩序的规则的顺从,即众人对统治的意识形态的顺从的再生产,以及为适合剥削和压迫者操纵统治意识形态,以使他们也为统治阶级的统治‘言说’(in words)的能力的再生产。”(14)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不是传统意义上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相反,它本身就深入到生产方式本身,构成社会再生产的始终在场的现实维度。
对意识形态在社会再生产中构成意义的论述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模式,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模式,也防止了意识形态概念向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的倒退。一方面,意识形态不是葛兰西霸权概念那样的社会秩序的中立因素,而是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直接地结合在一起的。另一方面,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拓扑学(topography)的关系。上层建筑并不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消极因素,它本身就是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二者关系不是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而是作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多元决定关系。
在阿尔都塞看来,对特定社会形态来说,意识形态与生产方式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意识形态不是人的思想和观念,而是由各种各样社会制度构成的国家机器。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中,国家机器概念不是阿尔都塞独创,霍布斯的“利维坦”就蕴含着这一概念,而马克思和列宁则直接催生了这一概念。阿尔都塞承认,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但它对国家功能和作用的解释仍然是不全面的,需要用新的理论要素来补充。“为了推动国家理论,不仅必须考虑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器的区别,还必须考虑明显处在(压制性)国家机器的同一面然而又不能与此相混淆的另一现实。根据其概念,我将这一现实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5)具体来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与直接的强制性国家机器相区别的多种私人和公共机构,包括教会、公私教育系统、家庭、法庭、工会、媒体等等。强制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就共同点来说,它们都属于国家,但二者的形态和起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1)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形态中,强制性国家机器总是唯一的,因而只能有一个强制性国家机器。这一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对暴力和强制手段的排他性垄断基础上。但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不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多种类型,是多元的。因此,强制性国家机器可简称为单数的SA,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须以复数的ISAs来表示。(2)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整个地属于公共机构,如军队、警察等等,而大部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属于私人机构,如教会、学校、家庭等等。(3)“将ISAs与(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区别开来的是以下差别:强制性国家机器‘通过暴力’起作用,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意识形态’起作用。”(16)
从形式上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似乎是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简单改造,实际上,二者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首先,葛兰西把社会理解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综合体,但阿尔都塞认为,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属于国家机器范畴,它与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样是强制性的,两者的区别只在于,狭义的国家机器是直接强制,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间接强制。其次,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强调,意识形态通过说服、教育、潜移默化的形式起作用,而阿尔都塞强调,在任何阶级社会中,主导意识形态的实现总是以国家力量为中介实现的,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国家影响之外的意识形态霸权。第三,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与生产方式没有直接的关系,它的主要领域是文化,主体是知识分子和大众,而阿尔都塞明确地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变化与社会再生产的要求联系在一起。最后,葛兰西霸权概念的核心是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它通过社会共识把不同群体联合起来起作用,而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场所和空间。在这里,“意识形态不仅是赌注(stake),而且也是阶级斗争,往往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形态的场所(site)。”(17)虽然一些人把阿尔都塞思想理解为葛兰西主义的发展,实际上,他们的观点存在着重要的差别,简单地说,葛兰西主义是文化主义的研究方法,而阿尔都塞的理论是统治技术论的研究方法,这明确体现在他的意识形态质询理论之中。
2.关于意识形态质询与主体的形成问题
阿尔都塞晚年意识形态理论的第三个核心内容是关于意识形态质询与主体的形成问题。正如他早期的意识形态概念脱胎于拉康的想象界概念一样,质询理论也脱胎于拉康的象征界理论。在拉康那里,法律和社会秩序是以父之名,即大他者代表的,任何个体都生活在大他者的凝视下,接受他的质询并努力获得他的认可,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不是人与世界的认知关系问题,而是实践关系,即主体与他者的主体间关系问题。
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就意识到,意识形态核心的意义不是认识问题,而是主体问题。意识形态不是无意义的个人幻想,而是人类的实践需要,“正是在想象对真实和真实对想象的这种多元决定中,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它在想象的关系中加强或改变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由此,这种能动作用永远不可能单纯地起工具的作用。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行为手段或一种工具使用的人们,在其使用过程中,陷进了意识形态之中并被它所包围,而人们还自以为是意识形态的无条件的主人”。(18)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质询概念中,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关系仍然是核心问题,但他不再在一般意义讨论意识形态是主体形成的襁褓,而是讨论阶级社会的特定秩序与个体之间的对抗关系。
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类型,齐泽克按照黑格尔对宗教要素的区分,区分了“作为观念复合体(理论、信念、信仰和论证过程)的意识形态;客观形式的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最后是最难以捉摸的领域,在社会‘现实’之心脏作用的‘自发的’意识形态”。(19)阿尔都塞晚期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建立在后两种概念之上的。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的唯物主义化不仅意味着它总是通过物质性的国家机器来体现,而且也意味着主体是通过反复重复的意识形态物质实践所产生的。
在个体中,意识形态不是观念和思想,而是一种内化到行为中的实践态度,这种态度是在参与意识形态实践中形成的。在这里,巴斯卡(Pascal)关于信仰本质的论述提供了理解意识形态的奇妙公式:“你必须如此这般地行动,如同你相信一祈祷、下跪,信仰就会自动地产生。”巴斯卡的公式提供了一种解释意识形态如何作用于主体的逆向自我创生(autopeotic)机制,即意识形态是在宗教仪式的“外在”践行中,在主体身上产生了“内在的”信仰效果。阿尔都塞相信,巴斯卡对信仰的论述是可以直接插入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之中的。“就单个的主体(某某个体)而言,其信仰的观念之存在之所以是物质性的,在于他的观念是被插入到物质实践中的物质行动,这些物质受制于物质的仪式,而这些仪式活动本身又是由特定主体从中获得其观念的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所界定的。”(20)
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质询是复杂的系统,它同时涉及四种物质性活动:个体的物质性活动、社会的物质性仪式、物质性意识形态机器以及由物质性意识形态机器的物质性仪式产生的物质性惯例。意识形态不是思想和观念的流通和循环,而是各种物质性力量的相互循环作用的网络,只有通过它们的共同作用,才能生产出意识形态所需要的主体。阿尔都塞的质询理论可以理解为对意识形态起作用的微观机制的解释,在这里,意识形态不再被理解为观念与现实的颠倒、思想的自我神秘化,而是被理解为从述行性(performative)的物质实践中回溯地产生的个人自主性幻想。
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的行为结构和过程理解为质询(interpellation)。在质询中,意识形态机器从自身的需要出发对个人发出召唤、提出责问和要求等等,个人通过对它的应答和回应来建立与它的关系,赢得它的承认。如果说,阿尔都塞的一般意识形态概念受拉康的想象界理论启发,质询理论则受到拉康象征界理论的影响。在想象界中,主体是与完满的母亲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个体从中获得欲望的幻想满足,在象征界中,主体则从父之名和法的世界中获得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一旦这个过程完成,人们就不再把自己与社会秩序的大他者的关系理解为强制关系,而是理解为自我的主动选择关系。
理解阿尔都塞的质询理论需要重视其核心命题:意识形态把个体作为主体来质询。这一命题在理论上预设着人的两个存在形式,即个体和主体的区分。从逻辑上说,个体先于主体,意识形态必须从具体的个体中招募成员,并把他改造成主体,但在现实中,个体总是已经被作为主体被召唤了。把一个具体的个体作为主体来质询和招呼,就是按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需要来质询,意识形态机器本质上就是质询的机器。质询过程是通过一个绝对的大主体进行的,这里的大主体就是拉康所说的主人(Master),类似于宗教的上帝。在宗教中,无数的信徒面对同一个大他者,个体通过对上帝的臣服和效忠获得臣民身份。阿尔都塞把质询理解为双重反射结构。它包括四个步骤:意识形态作为大主体(Subject)把个体作为小主体们(subjects)来质询;小主体们对大主体的臣服;小主体与大主体之间相互承认,小主体借助大主体的能指相互承认,最后完成小主体对自己的承认。一旦这一过程完成,小主体们通过大主体的质询识别出自己的身份,并在现实生活中作出正确的应对方式。至此,则万事大吉:“阿门——就这样吧!”
从上述对质询概念的解释中我们不难发现,阿尔都塞不是把社会秩序与主体之间理解为对抗和相互否定的关系,而是理解为互为条件的生产过程,主体的形成过程也是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社会秩序的建构不能脱离塑造主体的意识形态实践得到理解,同样,主体的形成也不能离开意识形态机器对个体的质询得到理解。
葛兰西把霸权理解为非强制的道德领导权,阿尔都塞拒绝这种解释路向。在他看来,质询并不是葛兰西所说的说服和教育,而是命令和强制,质询是大他者向个体发出的命令,是上帝对子民威严无比的训诫。由此可以理解,意识形态的质询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不是道德性的,它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说服和赢得被质询者的同意,而是把大他者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个体,是要生产社会秩序要求的好臣民。阿尔都塞认为,阶级社会的统治秩序是由暴力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共同维持的:“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独立地工作,除了极少数‘坏臣民’偶尔会引发(压制性的)国家机器派出的队伍干预外。绝大多数‘好臣民’都是会‘各就其位’。”(21)简单地说,对待坏臣民,统治阶级诉诸国家强制,对待好臣民则诉诸意识形态机器的物质性惯例。
阿尔都塞哲学的核心主张是“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这一主张他始终未变,只是早期他强调人道主义是具有实践功能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历史的客观科学。后期他放弃了早期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的二元论,但并未放弃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立场。在意识形态质询理论中,他强调主体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自主性是虚假的,它们不过是意识形态的效果,是对大他者要求在主体身上产生的“得心应手”的自动反应模式的误解。他明确强调,主体化不是自主的过程:“个体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被质询,以便他能自由地信奉大主体的命令,即,以便他能自由地接受他的屈从地位。……除非被迫并为了屈从,就根本不会有主体。”(22)
阿尔都塞的质询理论意义何在?它无疑是想通过对质询过程的复杂关系的分析,为意识形态理论提供微观基础,但更重要的是想表明,在阶级社会根本不存在强制性国家与非强制市民社会的二元体制,也不存在强制的主体间关系与对话的主体间关系的区分。就社会统治来说,只存在直接强制的国家机器和间接强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区别。按照阿尔都塞的逻辑,相信意识形态的非强制性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它不过是个体的主体化的意识形态效果的表现。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越是陷入意识形态,就越是否定自己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这一悖论完全可以用质询理论来解释。“意识形态是男男女女被塑造成参与一个他们自己不是创造者的过程,意识形态通过赋予他们以幻想履行了这一功能,让他们相信历史是他们创造的。”(23)任何意识形态都否定自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效果之一就是,借助意识形态来面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特征:意识形态从来不说‘我是意识形态的’。”(24)而这种自我否认构成了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幻想的社会根源。
三、暧昧的遗产
晚年阿尔都塞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一理论的唯物主义特征不是根据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解释的,而是根据意识形态参与物质再生产条件的生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性形态和意识形态质询实践的物质性来解释的。通过对意识形态的上述方面的解释,阿尔都塞恢复了这一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地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这一理论并非没有问题。篇幅所限,在这里我们只想把其中涉及的两个核心问题提出来讨论。
首先,我们能否区分一般意识形态与特殊意识形态?朗西埃明确指出,一个与社会融合的实践要求相联系的一般意识形态是从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继承来的问题,把这个概念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秩序的条件的概念是不相容的。“意识形态的两种功能(维持一般社会融合的功能与实施阶级统治的功能)的叠加(superimpositition)也许向我们表明两种异质的概念系统:历史唯物主义的与杜克海姆类型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共存,阿尔都塞的特殊伎俩是把这种共存变成了联结,它意味着双重的颠倒。”在朗西埃看来,“一般意识形态”概念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它只能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概念,把它嫁接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之上,必然损害马克思主义对统治秩序和意识形态的理解。朗西埃承认,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受制于双重决定,“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必然是扭曲和神秘化的,因为它既被结构对社会的决定的非透明性所扭曲,也被阶级分裂的存在所扭曲”。但是,我们不能把社会结构与阶级斗争作为两个不同的层面。对马克思来说,社会的总体性在结构上是被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而生产关系不过是生产资源的占有关系,因此,社会关系本质上就是阶级关系。“所以结构的表现/掩饰并不意味着一种‘一般社会结构’的非透明性:它是生产关系的效应,是一般的‘劳动者/非劳动者’的阶级对立的效应。一旦越出了阶级社会的范围,这一结构效应就完全是非确定的概念——换言之,它不过是被形而上学的传统隐喻支配的:恶魔或理性的狡计。”朗西埃的批判正中了问题的要害。在这里,阿尔都塞所犯的错误类似于资产阶级思想家所犯的错误。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研究国家问题时是先考察国家一般,再考察特定阶级社会的国家,“阿尔都塞赋予意识形态类似于经典形而上学思想赋予国家同样的地位”。(25)一般意识形态概念是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概念,它与历史唯物主义无关,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无关。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并没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
其次,阿尔都塞晚期的理论虽然解释了意识形态的政治性,但是,这种政治性更多的是单向的,即个体总是被意识形态驯服为“好臣民”,在其理论框架中,很难理解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和斗争是如何可能的。阿尔都塞的质询理论被认为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对社会阶级关系的整合能力,忽视了质询的内在复杂性和矛盾性。虽然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加了一个附录,承认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无冲突地实现其统治阶级利益。但是,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结构和框架本身使我们很难识别出意识形态领域中可能的矛盾和对抗。
阿尔都塞陷入困难的重要原因在于,他直接把拉康的象征界理论引入到自己的理论,把质询理解为大他者对作为臣民的自上而下的斥责,或上帝对子民的威严召唤,这些形象无不暗示着主导意识形态是法力无边的,人只是意识形态的奴隶,永远不能真正地对质询进行反抗,或进行反质询。在阿尔都塞学派中,米歇尔·佩舒(Michel Pecheux)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他指出,“为了在意识形态理论中更好地接纳阿尔都塞的‘无产阶级抵抗’的论述,他建议把再生产的立场加以扩展,包括再生产和转变。”佩舒认为,如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召唤的是“自律的主体”,把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作为自己意识形态的核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召唤的则是“战斗的主体”,把反对一切等级、不平等和压迫作为自己的根本要求。佩舒在自己的理论中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解—认同化”(de-identification),把意识形态的反质询要素放入到认同理论之中。这并不是说个体的主体化不存在着臣服和强制因素,而是说主体形式本身永远处在再造和争夺的过程之中。佩舒把这称为“反意识形态的反击”。(26)以民主为例,资产阶级的民主把阶级斗争保持在代议制形式之中,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应该采取“意识形态的解领域化”(ideological de-regionalisation)战略,把政治推出议会制度界限之外,创造一种越界的政治学,提出更激进的民主理想。
对任何一个理论都存在着检验的方法,这就是根据它自己的意图来观察其理论的实际内容和效果。就意识形态理论来说,阿尔都塞的理论意图首先是使马克思主义超越意识形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其次是证明意识形态领域不是纯粹的观念和思想的领域,而是阶级斗争的领域。然而,上述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缺陷的分析表明,上述意图并没有成功地达到。在这个意义上说,阿尔都塞的理论遗产是暧昧和成问题的。正是这种暧昧性使得曾经显赫一时的阿尔都塞学派在他去世后很快解体了。弗雷兹·霍格认为,阿尔都塞的理论存在着两个不相容的因素,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出发,它强调意识形态的多元决定并认为经济基础最终起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又从拉康的心理学出发,它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个体对他所处的世界的想象性再现,这两种不相容因素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阿尔都塞学派的解体。
历史地看,阿尔都塞学派的解体产生出三个不同的方向:以米歇尔·佩舒为代表,在共产主义阶级方案的语境下形成了唯物主义的话语理论,它是后阿尔都塞学派的左翼;中间派是新葛兰西主义,代表人物是拉克劳和斯图亚特·霍尔,他们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在社会各个领域起作用的话语策略,以此来批判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第三种思潮是后结构主义的阿尔都塞主义,它不仅完全抛弃阶级斗争概念,也完全抛弃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问题完全被非政治的文化和身份认同问题所取代,阶级斗争被认同和承认斗争所取代,在这个意义上,后阿尔都塞主义更多的是福柯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了。(27)因此,阿尔都塞遗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是模棱两可的。
注释:
①Fritz Haug,"Ideology The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15)2007.
②Louis Altrusser,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1,p.viii.
③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6页。
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47页。
⑤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0页。
⑥Theode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New York:Continuum,1990,p.143.
⑦Louis Altrusser,Philosophy of Encounter:Later Writings,1978-87,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6,p.127.
⑧Louis Altrusser,Philosophy of Encounter:Later Writings,1978-87,p.133.
⑨Louis Altrusser,Philosophy of Encounter:Later Writings,1978-87,pp.135,137,138.
⑩Louis Altrusser,Philosophy of Encounter:Later Writings,1978-87,p.144.
(11)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29页。
(12)Louis Altrusser,Essays in Self-Criticism,London:New Left,1972,p.155.
(13)Louis Altrusser,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p.xii.
(14)Louis Altrusser,Essays on Ideology,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71,pp.6-7.
(15)Louis Altrusser,Essays on Ideology,p.16.
(16)Louis Altrusser,Essays on Ideology,p.19.
(17)Louis Altrusser,Essays on Ideology,p.30.
(18)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30-231页。
(19)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诺等:《图绘意识形态》,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20)Louis Altrusser,Essays on Ideology,p.43.
(21)Louis Altrusser,Essays on Ideology,p.55.
(22)Louis Altrusser,Essays on Ideology,p.56.
(23)Alex Callinicos,Altrusser's Marxism,London:Pluto,1976,p.70.
(24)Louis Altrusser,Essays on Ideology,p.49.
(25)Jaques Ranciere,"On the Theory of Ideology:Altrusser's Politics," Terry Eagleton,Ideology,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Group UK Limited,1994,pp.144-145.
(26)Fritz Haug,"Ideology The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15)2007.
(27)Louis Altrusser,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p.xi.
标签:葛兰西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物质与意识论文; 政治论文; 保卫马克思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