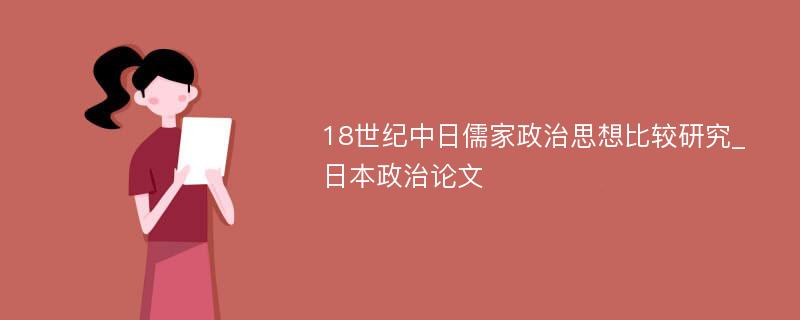
17~18世纪中日儒学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中日论文,政治思想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7~18世纪的中国,正处于明末到清中期的历史时期,即明朝万历中期至清朝嘉庆初期。在这一时期的前几十年里,中国思想界的儒学士大夫们写了一些违反传统的书,讲了一些惊人心魄的话。在这一时期的后百年里,这样的书和这样的话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原来色彩灿烂的思想潮流,也变得单调无色了。中国学者对于上述的书和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梁启超认为,明末清初的绚烂思潮,可以与欧洲的启蒙思想相比美(注:梁启超:《清代术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第45页)。胡适也说过,这个时期,“可算是中国的文艺复兴(Ren Ai San CE)时代。”(注:余英时著:《中国哲学思想论集——清代篇》,第229页。)余英时提出,这些思想的出现,“我们可以称它作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侯外庐以及更年轻一代的学者,大多数都主张,明末清初的中国思想界,不比同时期的欧洲思想界逊色多少(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已故的日本著名学者丸山真男曾说过,为什么中国的近代化失败而沦为半殖民地?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而成为东亚第一个近代国家?这是思想史应该解释的问题(注: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年3版,第7页。)。
一、17~18世纪中国儒学的困惑
17~18世纪,中国的思想界主流仍然是儒学。但是,相比明朝中后期,思想学术领域由理学主宰的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一,在前几十年间,贬抑君权,成了一种趋势。黄宗羲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明夷待访录·原君》;《明夷待访录·原臣》。),历史上的君主为“天下之大害”(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明夷待访录·原君》;《明夷待访录·原臣》。)。王船山指出,君主专制是“以一人疑天下,以天下私一人”(注:王船山:《黄书——宰制》;《四书训义·卷二十六》。)。唐甄怒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注:唐甄:《潜书——室语》。)。束缚人们近两千年的君臣伦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第二,“经世致用”,开辟了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凡“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本溯源,讨论其所以然”(注:潘耒:《日知录——序》。),而且“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反之实”(注:王敔:《姜斋公行述》。)。顾炎武总结和批评了明朝中后期士风的颓败,认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洲荡复,宗社丘墟。”(注: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为了写《天下郡国利病书》,他“足迹半天下”,“所至扼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注:全祖望:《亭林先生道碑》。)。时人评价他“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注:潘耒:《日知录——序》。)方以智编写著作,更是“采摭所言,或无征,或试之不验。此贵质测,征其确然者耳。……适以泰西为剡子,足以证明大禹、周公之法。而更精求其故,积变以考之”(注:方中通:《物理小识——编录缘起》。)。作为新学风的杰出代表,“实学”开创者之一的徐光启“平生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不愧是一位“学务可施用于世者”(注:《徐氏家谱》,《文定公传》。)。这一新学风,是对宋明理学的抗拒。第三,重新张扬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抨击宋明理学所提倡的禁欲主义。“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的王船山认为,“我者,大公之理所凝也。”并且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私欲之中,天理所寓”(注:王船山:《黄书——宰制》;《四书训义·卷二十六》。)的命题。这一思想的光辉,为后来的颜元和戴震所承继。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戴震,其思想的最高价值代表了18世纪中国的思想高峰,其杰出的思想著作《孟子字义疏证》,被胡适誉之为“近世哲学的中兴”,其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宋明理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第四,风行思想学术界百余年的“朴学”,就是发端于这一历史时期的初期。不论从中国思想发展史来看,还是从“西学”传入中国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来讲,“朴学”兴起之迅猛和浩荡,“朴学”衰落之漫长和残喘,都十分值得中国思想学术研究者求索其历史缘由。
17~18世纪的中国思想界,虽然发生了上述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思想界的主力军——儒学士大夫们,不论从思想发展的外在历史条件来看,还是从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来讲,都无法摆脱其先辈的困惑。这些困惑是:第一,儒学的三个组成部分,都已失去了鲜活的生机。其一,圣人之道,也就是伦理纲常。“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在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之中。”(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台湾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儒学的伦常旧调,既唱不出新意,也谱不出新曲。其二,道体之用,也就是经世济民。“到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事功的意味转淡,大规模的经世致用是谈不上了。”(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台湾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专制集权制度已趋成熟,满腹经纶的儒学士大夫已没有广阔的领域施展其才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儒学传统的道体之学窒息了儒学士大夫的思想。其三,经学文献,宋明理学发展到明朝后期,空谈“心性”不仅令人厌烦,也解决不了争论的问题。儒学的发展引导和逼迫着儒学士大夫们,从经学文献之中,寻找符合自己思想和观念的圣哲之言论,来证明儒学真谛为己所据,同时反证为人所误。由此竟蔚成清代的思想学术主流,“朴学”,即考据之学。余英时指出,“下逮乾、嘉之世,由于儒家的智识主义逐渐流为文献主义,不少考证学家的确已迷失了早期的方向感。”(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台湾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就像段玉裁这样的考证大师都要忏悔自己太过于追求“道问学”(注:余英时著:《中国哲学思想论集——清代篇》,第45页。)。这就足以说明,儒家从“尊德性”转向“道问学”,不仅没有摆脱士大夫们的困惑,反而徒增心智尚存者因误入歧途和荒废时光而生的忏悔。第二,儒学的政治和社会伦理作为思想基础的中国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已经丧失了促进思想文化、生产经济和社会制度进步的功能。明朝万历年间开始的“西学东渐”,虽然一度为中央朝廷感兴趣,也出现了徐光启这样的热心学习者。但是,很快中央朝廷就封闭了国门,儒学士大夫们也拒绝了“西学”。等到百年以后,落后挨打的惨痛才逼迫儒学士大夫开始张开了眼睛。这一人们熟悉的历史,足以说明,当时儒学士大夫陷入的困惑是多么的深重。
这种功能的丧失和困惑的深重,早在17~18世纪,就通过来中国进行传教的传教士们撰写的描述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的著作,传递到欧洲大陆,引起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中国“贬抑派”的批评:“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之马哥孛罗的报告,殪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哥孛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注: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等译,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85页。)后来的黑格尔分析,“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58页。)虽然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的观点并不全面和精确,但是以当时的欧洲为参照,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观点还是有其正确的方面。第三,由于历史地理的限制,又由于中国古代文明先于和高于周边国家的发展,还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缺少像环地中海诸古老文明之间的密切交往和彼此影响和渗透,除了东汉以后传入的佛教文化,中国古代文明的萌发和成熟,就不可能不具有封闭和独尊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又孕育了儒学士大夫的文化心理。例如,儒学士大夫们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观念。所以他们不具备多种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心理。又由于他们以中国文明为普天之下文明存在的唯一核心和最高形态,所以具有一种强烈而顽固的文化优越心理。(注:石介:《中国论》。)上述文化心理,使得他们只能文化输出,不能接受文化输入。孟子曾经说过,“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注:《孟子——藤文公上》。),就是他们文化心理定势的渊源。总之,上述的困惑就像梦魇一样缠绕着儒学士大夫们,使他们难以迈出前进的步伐。
二、17~18世纪日本思想界的儒学
反观17~18世纪的日本思想界,那种活泼和前进的状况,禁不住让人感慨万千。这里我们主要考察17~18世纪日本思想界的儒学演变状况。儒学传入日本,早在应神天皇16年(注: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年3版,第7页。)。宋学,也称理学,或叫朱子学,13世纪开始传入日本。但是比较广泛的传播,还是17世纪以后。儒学传入日本以后,直到17~18世纪,才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这时的日本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排斥宋学复兴原始儒教的古学派发展过程,表面上与中国的朱子学、阳明学和考据学成立过程类似,实际的思想内容却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朱子学成熟以后,就成为儒学的主流并且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不同于中国,在日本朱子学开始比较广泛地传播,日本的儒学界就呈现新颖异质的流派(注:渡边浩:《东亚细亚王权与思想》,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第71页。)。虽然朱子学派的学者在德川初期几乎是朱子的精神奴隶,不敢越雷池一步。井上哲次郎的《先达遗事》中,记述了山崎暗斋的学生佐藤直方描述拜访老师家的心情,进去时如入地狱而惴惴不安,出来时如脱虎口而轻松愉快(注: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年3版,第14页。)。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上述的看法。但是,几乎同时,日本儒学界就流派纷呈了。17世纪以前,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日本的官僚制就是常备军的体制(注:渡边浩:《东亚细亚王权与思想》,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第95页。)。这和隋唐以后,以科举为基础的文官制为主要的官僚制度的中国完全不同。进入17世纪以后,日本社会开始了长久的和平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思想和学术都开始兴起。墨守中国传统的日本儒学和儒士虽然一度拥有权威和自信,但是很快就因为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成为落伍者且被人冷落(注:渡边浩:《东亚细亚王权与思想》,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第97页。)。当时的朱子学,宣传和主张的“理”、“道”和“性”,不能适应不同阶层的利益需要和社会的发展趋势。所以,日本朱子学虽然在“道”、“利”和“义”等概念的用语和部分内容上,与“武士道”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前者被后者有意无意地篡改了意义。日本社会各阶层都从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将朱子学进行一番改造之后,再予以接受。所以日本的朱子学者开始对通过个人修养来达到对“理”的觉悟提出疑问,不相信人的“性”可以分割为“气质的性”和“本质的性”,怀疑“气”和“理”的学说可以解释整个宇宙,最后导致对朱子学的批判和超越,出现了日本儒学体系(注:渡边浩:《东亚细亚王权与思想》,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第102页。)。17世纪日本的儒学先驱,藤原惺窝和他杰出的学生林罗山,恰逢历史赋予的时机。当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德川家康为江户幕府的正统性寻找理论根据而倡导儒学,实际上是倡导朱子学的伦理纲常学说(注: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年3版,第13页。)。藤原惺窝和林罗山没有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丧失思想的独立,他们在进行儒学研究和儒学宣传时,对当时在日本流行泛滥的佛教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1)佛教玄学妙理空洞无物;(2)佛教无视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3)佛教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精神形态(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他们还认为,“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和孟子的‘性本善’学说是正确的,‘礼’则是社会差别、尊卑、贵贱和贫富问题的规范而已。“他们构成合理主义的近世儒学。”(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由于当时“诵习儒学的人自己常把它当成文化上的一种修养,用日文说是‘稽古事’或‘游艺’,它和花道、茶道、能剧歌谣、俳句等没有什么不同;而这些与日常的己为人行几乎毫无关系,更不用说和政治有什么关系了。”也由于日本朱子学认为书本知识优越于经验,把圣贤之书看作权威,主张单靠圣贤之书就能求得“物理”和“道理”,否定根据实证方法的研究,反对移植和研究西方近代科学文化。还由于日本朱子学派的早期人物藤原惺窝、林罗山、山鹿素行等主张一元政治,即国家集权。因此,日本的朱子学作为合理主义的近世儒学,可以在日本生存,但是却影响不了官僚阶层,妨碍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移植和研究,解决不了实际上存在的二元政治结构的矛盾。所以,日本的朱子学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正统的统治阶级的学术思想(注:丸山真男:《Studies in the Intel Lectual History of Tokugawa Japan》,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P.xxxiv.)。
日本的朱子学者,如果依据中国儒学的本质,“把它用来作为伦理、社会以及政治的典范和哲学,他将发现在儒学的信条和其周遭的环境,或甚至和他自己的道德信念之间实在存在着极严重的矛盾。”(注:渡边浩:中国台湾,《史学评论》,第五期,1984年1月,第194页。)自17世纪以后,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社会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诸多矛盾。日本的朱子学在克服这些新型的社会矛盾上一筹莫展,毫无能力。正是在这样的外部历史环境之下,日本的朱子学内部发生了蜕变,兴起了各种新儒学的思潮。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前期盛行一时的古学派,就是其代表。从日本儒学的政治理论来讲,古学派不同于前人的地方,或者说创新之处,就是打破朱子学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古学派提倡社会实践和经验知识,强调从古文字学进行客观科学地研究经典,期望获得经典中先贤圣人的真义。古学派认为,儒学的本质就是“先王之道”,实际上就是经典记载的礼乐制度。它是圣人——古代先王为“治天下”而制定的,并不是“天地自然之道”。因此,古学派将儒学限定于政治学的范畴,获得了两个巨大的进步。一是政治学必须随历史进步而发展;二是把不属于政治学的自然科学从传统的儒学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日本社会的近代化发展清除了思想上的障碍,开辟了道路。日本儒学的发展,最终经由古学派大师荻生徂徕影响兰学创始人杉田玄白,将其儒学与医学结合的传统,引导到有系统地移植和研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道路。
三、17~18世纪中日儒学政治思想的比较
如果说17~18世纪中日儒学流派的简单比较,已经可以看出中日知识界历史发展的差异;那么,再将17~18世纪中日儒学政治思想进行比较,就可以认识到,日本儒学政治思想不仅丰富多彩,而且直面日本社会实际,注重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同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终日沉湎于经典,陶醉于“微言大义”的考据相比较,日本社会在以后的里程中,具有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发展途径和速度,其历史缘由就十分清楚了。
17~18世纪的中国儒学界,出现了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样杰出的学者。但是,他们对专制君权的猛烈批判,对民本主义的大力宣扬,对经世致用的极力提倡,都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思想没有本质的区别和没有显示出时代的进步,只是力度上的加重和角度上的转换,不论是黄宗羲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明夷待访录·原君》;《明夷待访录·原臣》。),还是顾炎武的“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应该结合,还有王无之的反对豪强大地主,概莫能外。他们之所以跳不出儒学的传统窠臼,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欧洲在15~16世纪,日本在17~18世纪已经达到的思想水准,即“将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划分清楚”(注: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2年,第190页。)。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远远没有出现日本那样的经济和社会的急剧演变,更不用说与欧洲相提并论了。“儒学如何突破人文的领域而进入自然的世界的确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课题,而且其中直接牵涉到价值系统的基本改变。”(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台湾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同样,儒学如何突破传统政治伦理的束缚,直面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需求,也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后者更需要风云激荡的时代和汹涌奔腾的历史潮流。缺乏新兴的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经济力量的冲击,中国儒学政治思想界除了弹唱老调之外,能够期望它谱出新曲吗?
同一时期的日本儒学,其政治思想却发生了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剧烈变化。第一,反对空谈清议,反对因循守旧,提倡研究现实,研究日本。贝原益杆临终前发表了《大疑录》,表明自己对朱子学的怀疑,他指出:“朱子说,知道是为了究理达事,为什么朱子只重视究?!”(注: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年3版,第63页。)伊藤仁斋认为,如果圣人再世,一定会依据当世之状况,制定和使用新的法律(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山鹿素行经过自己的实证研究,认为历史百年大变,50年中变。除了自然和道德法则不变之外,历史是进步发展的。因此,他被称为日本近代历史进步发展论的首倡者。(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同时,他还认为儒学研究中国问题,日本学者应该转向于日本研究。平田笃胤和熊泽番山都持这一观点。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和《谪居童问》,熊泽番山的《集义外书》和《三轮物语》,就是专门研究日本文化、政治和社会的著作。在他们的带领下,当时日本的日本史研究也繁荣起来了。(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江户时期中期以后,思想界的主要特征就是以日本的特殊性为基本点的新思想和新观点的提倡及流行(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第二,反对儒学传统,反对义利分离,提出自由平等,追求实际利益。中江藤树一反传统,强调“义利”都是社会道德的一般原则,没有高低轻重之分。(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林罗山主张“义利”相容说,他进一步指出,利包括民众之利。(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山鹿素行是第一个倡导古学,反对朱子学的日本学者。他认为,人性的本质是自然的,不可分为善和恶;人类社会是有“礼”的,不可反对人的欲求。(注: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年3版,第45页。)他还对孔子的“利”予以最广义的解释,认为“利”与“义”是不可分离的。(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在肯定了“利”和肯定了“利”的追求之后,山鹿素行和中江藤树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对自由的认识。《山鹿语类——卷的第十一,治谈》中,山鹿素行就专门讨论了物质享受的自由与放纵;《改正翁问答——上》中,中江藤树特别强调了精神自由。(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伊藤仁斋提出了自己的人道概念,他的名言“人之外无道,道之外无人”(注: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年3版,第55页。)产生了巨大影响,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宝鸠巢在此前已经提出了日本的君民契约说(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井原西鹤甚至提出了经济自由的主张(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他们在日本走出中世纪的艰难历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在主张自由平等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中,石田梅岩代表町人阶层的平等论,更是独树一帜,格外醒目。(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第三,反对重农主义,反对轻视经济,力倡发展工商,重视町人阶层。藤原惺窝,山鹿素行和井原西鹤都主张反对重农主义,肯定町人阶层。(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荻生徂徕虽然主张重农主义,但是他同样重视经济。例如武士阶层贫困问题的解决方法,他提出主要的一条途径就是铸造钱币的通货膨胀政策(注: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年3版,第134页。)。佐藤信渊甚至宣扬以富国主义为中心来改定儒学(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当时的许多学者,不仅主张重商主义,而且提出了许多反对封建主义的经济思想和经济主张。山鹿素行提出贫富天命说,井原西鹤则认为人的富贵与人的努力有关(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本居宣长还提出了关于民族实力的评判标准,即领土的大小不决定民族的实力,而民族的人口数、生产力、军事力等强弱才能测定民族的强弱。据此而言,日本比其他诸民族强盛,所以日本民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此外熊泽番山和称为日本马尔萨斯的本多利明,很早就提出了人口增加和物质局限矛盾的警告(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到了德川时代的中后期,重视现实性和社会性的自由主义思想盛行,重视町人阶层和重视经济发展的自由主义主张泛滥(注:内田繁隆:《日本社会政治思想史》,日文版,东京岩松堂书店,昭和8年4月再版,第125、160、155、333、339、151、149、149、385、374、390、401、186、295、186、347、350、392页)。基于这一系列的嬗变,近代日本和日本社会比中国更早和更容易走出中世纪,迅速完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就成为一种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