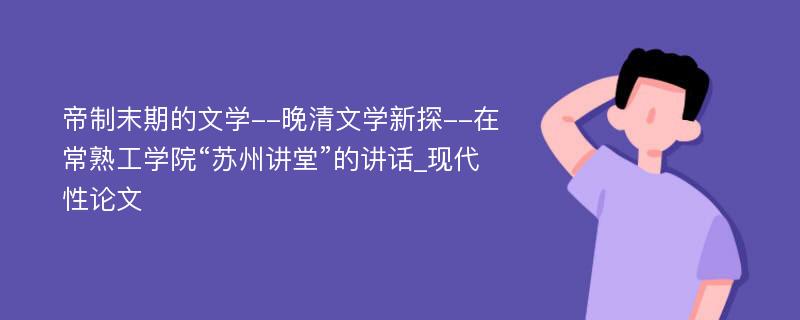
帝制末的文学:重探晚清文学——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吴论文,常熟论文,帝制论文,晚清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吴讲堂 主持人 傅大友/丁晓原
周宏(常熟理工学院教授):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东吴讲堂很荣幸地迎来了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特聘教授李欧梵先生。有人说,李老师是香港文化圈里的另类,他治的是学术,玩的是潮流,过的是生活。他不仅研究文学,也研究电影、建筑,尤其是西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为深厚,这可能就是他所欣赏的狐狸型学者的特点。这些年,李老师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文化批评上,对香港文化、人文关怀、公共空间、私人空间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很尖锐也很有意义的批评,产生了很大反响。当然,在我看来,李老师最主要的身份还是一位成果卓著、影响深远的国际知名学者,所以今天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纯学术的讲演——《帝制末的文学:重探晚清文学》。下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给我们作精彩讲演。
一
今天承蒙邀请作一个学术报告,不胜荣幸,但今天讲的只能算是一个泛论,因为我的晚清研究计划,一直没有定下心来研究,今天能够谈的也只是一些初步的想法,所以连题目也是临时拼凑出来的,当然源自王德威的一本巨著——英文名叫Fin-de-Siecle Splender: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中文名叫《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我的讲题本来叫做《世纪末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文化的再反思》(Fin-de-Siecle and Repressed Modernity:A Reconsideration of Late Qing Culture),顾名思义,完全从王德威的论述框架衍化而来,后来又觉不妥,怕有抄袭之嫌,所以改用现在的名称,但还是借用了他的另一本中文书名:《众声喧哗》。改来改去还是摆脱不了他的“魔掌”,所以在此也借机向他致敬。
那么就先从王德威的这本书说起。
德威这本书,中英对照之下,不难发现英文书名中的“世纪末的华丽”不见了,这原是朱天文一篇小说的名字,小说中描写和影射的是二十世纪台北的世纪末,德威把它挪用在一个世纪前的晚清,映照出另一种“世纪末”的颓废感——朱天文小说的背后主题,我认为极有启发性。然而“世纪末”这个名词不是源自中土,而是来自西方,特别是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大家都知道萧斯基(Carl E.Schorske)的那本名著,而且也有黄煜文的中文译本,中国没有这个名词,因为中国没有“世纪”(century)这个概念,直到晚清才由梁启超介绍进来,由此带动了“现代性”(modernity)的进步时间概念,影响到五四。我曾在其他相关文章中多次提过。
Matei Calinescu曾经在他那本讨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Five Faces of Modernity)的名著中,仔细诠释过“颓废”(decadence),它其实是“现代性”的另一面,“进步”概念的反照或逆反。表现在艺术上,就是《世纪末的维也纳》书中大画特画的画家Gustave Klimt和他那一代的文人雅士,如小说家施尼志勒(Arthur Schnitzler),作曲家马勒(Gustav Mahler)、荀贝格(Arnold Schoenberg),剧作家霍夫曼斯陶(Hugo Hofmannsthal)等人,在文化上显然呈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华丽。然而在同一时期的晚清并非如此,在一般史家的眼中,晚清最后十年(一九○○-一九一○)的文化,只能算是颓败(depredation)或衰落(decline),而不是“颓废”(decadence),换言之,它似乎缺少了一份艺术性的美感。
然而晚清最后那十年的文化是否真的那么衰败,甚至乏善可陈?我们用什么方式或理论框架来诠释晚清的文本和文化?在王德威的大著中,我似乎看到现代理论的影子,但没有浮出表面,我猜他所用的“颓废”观念有点像另一位学者Ackbar Abbas对于香港世纪末(一九九七)的研究,故意把decadent这个字拆开,变成了de-cadent,像是音乐旋律中的“不协调”。如果“主旋律”是严复和梁启超等人揭开的西方进步观念和功利式的现代性,那么文化中不协调的和弦,就表现于某些晚清文学文本中。表面看来,类似复古,甚至迂腐,但有时又饱含社会讽刺甚至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转到另一个“liminal space”,但这个新路向似乎被主旋律“压抑”了。
这当然是我对于德威的理论的误读或曲解。然而我十分赞成此书背后的用心,也就是为晚清文学请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他在全书第一章用了四个吊诡的方式来引论:(一)启蒙与颓废;(二)革命与回转(revolution and involution);(三)理智/理性与滥情;(四)模仿与谑仿(mimesis and mimicry)。然后在其他章节中逐步检视各种晚清文本,但大致都放在这四个框架之中去讨论,可谓琳琅满目,充满了洞见和创建。中文译本中尤其详尽。
然而德威的分析方法还是基于文本的解读。我原是学历史的,所以禁不住还要从文本之中和文本之外找寻历史和文化的“脉络”(context)和根据,并互相印证,然而说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我有幸在哈佛任教期间时常向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请益,并在我退休前两年(二○○二-二○○四),特别请他参加我的晚清翻译研讨班(seminar),刚好韩南教授的几篇有关晚清学术论文刚刚发表不久,后来结集出版,由哥伦比亚大学印行,中文名叫《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看来薄薄的一本,但内容实在精彩。韩南教授的文风一向言简意赅,他写下的每一句话背后都有扎扎实实的研究与考证功夫,但并不做过多的诠释,和王德威的这本书放在一起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可谓相得益彰。德威的书中理论和洞见极多,读来内容华丽,而韩南却是一点一滴地挖掘资料,沙里淘金,淘出来的更不乏惊人的发现。比如他发现中国最早翻译的英国小说是《昕夕闲谈》,他花了极大心血去找原著,原来是Bulwer Lytton的一本言情伦理小说Night and Morning的上半部。他又发现在中国最早提升小说地位并提倡其社会功用的不是梁启超,而是比他的《新小说》出版还早八年的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此人于一八九五年公开征文,以“三弊”为题:分别是鸦片、缠足和时文的弊病,据资料显示,投稿者甚众。这些资料已经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分校图书馆被发现,并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出版。有此先例,才有其他这种类型的小说作品。总而言之,晚清小说的兴起,是来自社会和文化风气的转变,并由此激发出晚清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大变动。然而内容和形式之间是否也有“吊诡”和“紧张”(tension)?社会风气又如何进入文本和文风?这反而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所在。我甚至认为,五四作家自鲁迅以来都没有仔细审视过晚清文学形式,连鲁迅和阿英也不乏偏见和盲点。所幸王德威和韩南将之纠正了。
二
晚清最后这十年(一九○○-一九一○),在政治上似乎乱成一团,无法起死回生,但晚清的出版业却异常蓬勃,发展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据樽本照雄教授多年来的研究,80%以上的小说都是在这十年中出版的,而在一九○七年达到高峰,在此之前,三分之二是翻译,之后创作的数量超过翻译,两者合计有16011种之多。所以我一向把翻译作品——包括意译和改写——放在晚清文学之中。当时的文人没有什么翻译理论,也不见得遵守严复的“信、达、雅”的原则。不管素质如何,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文化遗产,值得深入研究。从这批大量的译文中,我仍不难发现许多来自西方的新观念和新名词。
所以我又想到“世纪末”这个名词和概念——明明知道连“世纪”的观念也是在十九世纪末才介绍到中国来的。我曾在其他文章中谈到梁启超在他游夏威夷时所写的日记中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必须开始用西历,因为全世界都在用。这则日记,刚好是一八九九年十二月的圣诞节前后记下来的,也就是西历的“世纪末”——十九世纪末最后的几天。梁启超一意要走向一个“新纪元”,还写了一本未完成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登高一呼,但初时应者并不多,最多不过是把中西历并置而已,《申报》早已采用这种计法。
然而两种时间观念的重叠,也构成晚清小说的主轴架构,它的情节不是用直线进行的叙事法推动,但故事还是向前发展;它有数线叙事同时进行,有时也有点迂回,“话分两头”的情况甚多。然而,众所周知,有些晚清小说家如吴趼人——也学到一点西方小说的倒叙手法(如《九命奇冤》),更逐渐偏重叙述上的“现在”和“现实”,而不是从古说起。换言之,晚清小说在形式上已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已经和以前的章回小说不同了。用Franco Moretti的说法,就是小说形式的演变(evolution)往往从微不足道的小节开始,逐渐牵动全局,这个过渡时期的小说家也不像乔哀思一样开创一个语言的新世界,而大多是“泥砖匠”(bricoleur),这里堆堆,那里砌砌,却在不知不觉中引起小说形式的演变和发展。我认为晚清小说就是如此。这必然是新旧之间的一种文体过渡,换言之,晚清文学挣扎在“世纪末”和“世纪初”之间,既顾后,又瞻前,但在表面上却看不出形式上的创新,而是用一种乱七八糟的拼凑方式进行的,小说中的各种细节和人物——有的新、有的旧——愈来愈多,几乎在几十回的叙述构架中容纳不下。晚清小说本来就依附于各种小说杂志的连载,各章节有时自成一体,此起彼落,连接得很勉强,随时遭到腰斩,结构不可能完整。这一切都构成了晚清小说的局限性。然而,吊诡的是,这种局限并不一定是限制,有时反而构成一种“解放”,甚至可以把传统小说的结构推到极限。
然而从政治的“主旋律”来看,这一片蠢蠢欲动、甚至欣欣向荣的文学现象,却被“帝制末”的阴影所笼罩或压抑,“repressed”一词也许可以从另一方面来审视:我们回头看,非但五四启蒙的现代性压抑了晚清,而且更重要的是,晚清文学和文化中不少新的事物也被压抑在根深蒂固却已摇摇欲坠的传统之中。无论你怎么看,我认为应该正视这个“帝制末”的问题,晚清的“世纪末”就是两千年帝制传统的文化余晖,依然有其灿烂的一面,但已是近黄昏了。没有人把大清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帝制末做个比较,但两者不乏对称之处,虽然清朝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奥匈帝国(一八六七-一九一八)不到一百年,但王朝思想日渐落伍的情况很相似:慈禧左右政局不下三十年,奥国的Franz Josef皇帝也是一个昏君。只不过世纪末的维也纳人才荟萃,而中国的新文化还须等到五四时代才出现,然而晚清的文人作家也不能等闲视之。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帝国,在世纪之交都产生了文化上的极大危机,在十九世纪末的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中产阶级早已兴起,但在政治上极不稳定,有民主制度,却开始排斥犹太人,这一切在萧斯基书中皆有详细的分析。他指出维也纳的大部分艺术家都是犹太人,心理上的危机也已涌现,当然城市生活的压力也造成另一种心理压抑,这在施尼志勒的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相较之下,晚清的小说家并不从心理压抑着手,却放眼周围的社会,但魑魅魍魉的“怪现状”何尝不是心理和文化危机的外在表现?问题是如何从文学中探讨这种危机感。
我也讲过不少晚清小说和翻译作品,但至今尚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不过我发现了一个文体上的“怪现象”:晚清这十年中,非但出版蓬勃,而且文类也多不胜数,非但小说有各种分类,如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等等,其他文类如弹词、竹枝词、笔记等也应有尽有,同样展现了不少新事物,例如竹枝词中就有电车和火车的描写!而晚清小说的“叙事者”更是千变万化,花样百出,仿佛原作者必须采用各种掩饰手法,制造出各种替身,非但用以表现作者看到的各种怪现象,而且更用这种迂回手法展现作者的主观看法,更不必许多化名的象征意涵,如“东亚病夫”和“九死一生”。似乎把这种危机感也展现在层层叙事结构之中,例如吴趼人在一篇小说的开头,说他——作者——如何在路上看到一个鸦片鬼,交给他一卷手稿,求他发表。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韩南教授曾为此写过一篇名文,收在他的书中。我在课堂上问他:“晚清小说中叙事者的变化,是否与晚清社会的危机感有关?两者可否直接拉上关系?”他说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另一个现象就是晚清杂志和报纸的副刊愈来愈活泼,栏目多用“笑”字,文章算是“游戏”,政局愈危,社会愈乱,笑声似乎愈多!这是另一种“众声喧哗”,不见得和巴赫丁(Bakhtin)的理论完全合得上(晚清作家也不像Rabelais)。然而我认为它也代表了一种解放心态,不但在插科打诨之余针砭时事,开创言论的自由空间(我也曾为文从这个Habermas的角度探讨),而且借此把小说的视野扩大了。晚清小说的“嘉年华会”式的戏剧景观,在结构上有点Moretti所说的类似“现代史诗”(Modern Epic),也是一种移动景观(panorama),五花八门,但文本并不完整。最近德威引申了普实克(J.Prusek)教授的“史诗”和“抒情”两种模式的互动和互替来重塑中国的抒情传统,一直拉到二十世纪新文学,我觉得这两个模式也刚好在我最喜欢的两部晚清小说之中同时存在:一是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二是刘鹗的《老残游记》。前者是一部节缩的史诗,后者则是一部用小说手法写出来的持续的抒情散文,请容我以这两部作品为例,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
三
我认为这两部小说有互文关系。樽本照雄教授曾经仔细求证过,为什么《老残游记》先在《绣像小说》杂志连载,但在一九○五年突然停了,几个月后又在《天津日报》连载中牵涉到《老残游记》第十一章中的“北拳南革”的政治隐喻问题。杂志编者本是李伯元,但突然于此年逝世,另一位编者将小说中的第十一回删除,又修改原稿的第十回和第十二回,刘鹗的友人不满,所以才把它移到《天津日报》。樽本又考证出来,《老残游记》中有关月球绕地球是对的,《文明小史》却错了。暂且不论这个抄袭问题,我反而从这段考证得到灵感,把这两本书放在同一个时间的平台上来看:两书所描写的是同一时期(一九○五年左右)的历史现实,但表现方式完全不同,一个是抒情式的游记,一个是杂事铺陈的“小史”。用鉴赏的眼光来看,我们当然喜欢《老残游记》,因为它创出一个侠客式的主人公,他的经历几乎贯穿全书,只有内中第八到十一章换了主人公,从“申子平登山遇虎”(第八章)开始,故事更抒情,带我们进入一个超越尘世的意境,这个申子平是作者胸襟的另一种写法,值得大书特书。我最喜欢的一段是两位仙人——屿姑和黄龙子与两个侍女用古乐器弹出一场即兴的四重奏,真是美到绝顶,也不可形容。所以,作者用字也不多,和第二回的黑妞白妞说书段落恰成对比:后者我们几乎可以听出来或“看”出来是怎么唱的,而前者的演奏只有申子平才听得到,它与世隔绝,是无声之乐!这种美得出奇的音画为什么放在这里?像是一场梦,或者说只有作者本人才体会得出来。无论如何,我觉得它刚好“反照”了背后的历史危机,愈是自我抒情,背后的社会危机愈大。妙的是刘鹗自己是泰州学派的人,主张“三教合一”,他做的事都和当时的新政有关,他写这本《老残游记》,自谦是游戏文章,暇时自娱之作,即便如此,我认为这本小说中的抒情已经代表了他的内心一面,这种意境是当时社会的混乱和危机促成的:作为一个“儒侠”,他要入世,但他的道家的一面却要出世,在小说中营造自己的桃花源。
《老残游记》开头就谈哭,中间有黄河冰冻的场面,老残看了不自觉地泪流满面而成冰,这些都是常引的经典片段。在其他晚清小说中,哭的场面也不少,我认为这不见得是滥情,而是一种感情仪式,像是在祭奠即将变色的山河。这当然也是一种抒情方式,作者用诗意的语言来捕捉这几个“美景良辰”,就像日本樱花快要谢了的伤感;弥足珍贵,这是中国式的“怀旧”,但却置于“今朝”和“现时”的境遇之中,因此也和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所说的“现代性”——短暂的、临时的、瞬息即变的,它是艺术的一半,而另一半则在追求永恒——异曲同工,也互相映照,但文化的渊源截然不同。刘鹗在小说中要抓住这几个抒情时辰,甚至让时间静止,制造诗意的散文,而不全是叙述。
《文明小史》则完全相反,密密麻麻的全是叙述,人物和事物更是包罗万有,作者自己说这是一个晚清新政的万花筒,毫无抒情气氛可言,然而同样印证了那个时代,甚至同一年(一九○五)在中国发生的事。《文明小史》顾名思义,是描写一种新生的“文明”——这个字眼儿是从日本来的,指的主要是从西方传来的新的物质文明,也就是现代性的物质表象,进入了中国的生活习惯之中,特别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种物质文明,晚清时称之为“声光化电”,它逐渐侵入城市人生活的风俗习惯之中,当然怪态百出,李伯元着实将之讽刺一番。但讽刺的背后并非守旧,小说中有不少段落都有抑旧扬新的意图,譬如说书中有一个任务要到城里去拜师,先找一位教旧学的,但不满意,再去找一位教新学的老师,求新学秘笈,王德威说得好,连这秘笈也是一个文本,也成了讽刺对象。这一段直接反映了一九○五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大家莫衷一是,急求新书的狂热现象,商务印书馆趁机出版一套套教科书和字典,后又编辑数百册的《东方文库》,这些新书再现于《文明小史》的小说世界,就成了“秘笈”,成了现代性的文明表征,真是妙不可言。
《文明小史》创造出一个新人物——劳航芥,可谓史无前例。王德威也特别提出来讨论。劳航芥是一个文化买办,也是一个不得志的边缘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翻译“专家”,他在美国一间野鸡大学拿了个文凭,又在香港做过挂牌律师,最后到了武汉,在黄抚台(影射张之洞)的门下做个幕僚;他懂得英文,竟然为长官写了一封冠冕堂皇的英文信给英国领事,拒绝英国人来采矿。这段英文,不知作者从哪里抄来的,但学得惟妙惟肖,令我大吃一惊,因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双语——中文和英文,而且还有德文和俄文名称的中文音译,使得《文明小史》变成真正的多声体,不知当年的读者如何接受。似乎还没有人仔细研究过,这即使在后来五四时期的小说中也很罕见。这种外语的插入也丰富了《文明小史》这个文本。据我所知,即使在《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也没有这么多外文和洋人(当然后来的《孽海花》中更多,但出现在小说中的外国,而非直接进入小说的中土)。
“外力”文明的进入,早已颠覆了小说的结构。《文明小史》已经失去《儒林外史》中的文化稳定性,后者的故事表面上也是备极嘲讽,但它背后有一个真正的儒家支柱,所以在最后的祭奠仪式也备极隆重。但在《文明小史》中这些儒家都不见了,整个小说的各种奇怪人物都是新冒出来的,就是在这十年间才出现于晚清社会,和一个世纪前的《儒林外史》的世界差别太大了!《文明小史》也算是“外史”,但它的历史至少一半是外来的,包括意大利的工程师、英国传教士(影射里提摩太)、德国的军事教练……作者谦称“小史”,但内中新事物繁多,早已超过了正史的记述。
在小说的楔子里,说书人也和《老残游记》开始的梦一样,说道长日当空,忽来一片乌云,大雨要来了,寓意甚明——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即将降临,但小说结尾却草草了事,只说书中这一大堆新人物都被即将出洋考察的新政大臣收编了,用的是《水浒传》的模式。但将来又如何呢?这些人物似乎昙花一现就无影无踪了!这非但是一个不稳定的结局,而且还暗示前途的未知数:在一九○五年,谁知道大清王朝的气数如何?现在看来,这种结尾显然暗示着帝制的末日即将到来,《文明小史》描写的是一种“世纪末”的喧哗。是否如莎翁名句所言:“充满声音和愤怒,但意义全无”(full of sound and fury,signifying nothing)?我认为不然,帝国没落愈近在眼前,喧哗的声音也愈多愈响,单看那个时期的立宪运动,就知道政坛是如何喧嚣了,终于时不我予,帝制被共和革命所推翻。
小说如何表现这个帝制末的喧哗?最佳的例子就是《文明小史》。我认为这本小说不尽是戏谑或嘲讽,而是相当严肃的,否则不会把那么多历史的怪现象——也是新气象——塞进小说有限的篇幅之中,终于挤爆了,似乎连作者也不知如何收场。
四
因为时间的关系,而且我的能力有限,今天带的资料也不全,只能到此为止。我想在下面剩下的少许时间略谈一下晚清的科幻小说。
晚清的科幻小说和中国传统中的《桃花源》的模式不同,因为说的是幻想中的未来,而不是过去,这很明显是由新的时间观念所造成的,然而我所读过的晚清科幻小说,没有一篇是写完整的,似乎对于未来的想象有点匮乏。比较完整的可能是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但即使这本小说在下半部所展示的未来中国蓝图也不尽完善,不像Thomas More的Utopia或俄国小说家Chernyshevsky的革命幻想小说What is to be Done。中国的乌托邦只是个幻想,也存留在幻想的层次,没有实现的可能。在晚清小说中更是如此。这似乎暗含着一个历史的吊诡:在新的时间和进步观念影响下,未来变得很必要,但在晚清那个过渡时期,这种时空转换在心理上又不能完全接受;换言之,身处的现实情境逼使晚清文人作家和知识分子憧憬未来,作为一种出路,但他们又不知如何想象未来,只能用过去的模子注入新血,把经典再转化一次。《新石头记》就是一例,作者要把贾宝玉请出来,让他到未来世界去坐潜水艇(可见王德威以此为题的名文),但骨子里还是在模仿过去的模式,《新石头记》下半部的“乌托邦田园”表现的完全是小国寡民的道家理想。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所谓独特性并不那么重要,“大家抄来抄去,引来引去”是一种“继承式”的写法,所以晚清小说也模仿得厉害,有的名书还有个“后”字,如《后石头记》和《后水浒》。一个新的科幻世界需要一种新的文体来展现,但晚清的小说家似乎无此能力,加之这些人都是传统训练出来的,对于科学新知识所知有限,也不知道西方有Fourier的社会理想国或Robert Owen的理想农村,只知道Jules Verne的《月界旅行》和《地底世界》(两者皆是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还有包天笑从日文转译的《法螺先生谈》(又立即被改写出《新法螺先生谈》),原典是德国童话Baron Munchhausen。还有其他一些来自荷兰和英美的科幻小说。这些资源被晚清文人移花接木,展示了一种不三不四的未来世界版图:书中的冒险家一下子跑到南极见巨鲸,一下子又跑到地心遇到异人,最后又回到中土,不按理出牌式地胡拼乱凑。我认为这种想象骨子里还是十分保守,似乎书中的科幻旅游者不知道何去何从,甚至还有几篇描写世界末日!最特别的一篇,就是梁启超改译的《世界末日记》,原作者是法国作家佛琳玛利安(Caralle Flimarian),刊于《新小说》创刊号。为什么梁启超会译这篇他自称“悲惨风景”之文,特别是在他开创以小说鼓荡民心、“以新新民”的时候?他在译后记中借用佛家典故,说自己“译此文,以语菩萨,非以语凡夫”,似乎是一种尼采超人式的说法,又说“一切皆死,独有不死者存”云云,到底用意何在?这又和他在《汗漫录》(夏威夷日记)中首创改用西方的进步论调背道而驰。在这个关键时刻却回归佛学,似乎以东方的哲理来回应时间性的吊诡:历史的将来发展,说不定会引向世界末日和人类的灭亡;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不过是代表时间面向的两个极端。在洞悉一个“玄机”的同时,是否也隐藏了一种深层的焦虑和不安?也许,这又可解释为一种“世纪末”而非“世纪初”的心态和文化情况。至于它是否表现了另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对我而言并不重要。
以上所说,只能算是粗略地浏览,如果要仔细研究下去,我认为只能从晚清大量的文本和史料中逐步摸索,再找出各文本的连接点和细节的互文性——我认为晚清文本的互文性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然后才能展现这个整体。我同意王德威的看法:晚清绝对是承先启后的,只是这个演变过程是迂回的,而不是直线前进的,然而在迂回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展现新意,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我们研究晚清,不能理论先行或硬套,或纯做文本分析(因为它的历史因素甚多),也不能从任何制高点——如五四,去回头俯视。也许我们只能做个学术上的“泥砖匠”,一点一滴地去堆砌建造,庶几或可造成一幢大楼。
今天就讲到这里,乱七八糟,零乱不堪,好像晚清小说一样,务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教。
(此文为二○○九年十月八日讲演稿,二○一○年五月五日根据录音资料整理改写,刊于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所通讯,第二十卷第二期,二○一○年六月。二○一一年四月十一、十二日于苏州大学和常熟理工学院讲演,并在内容上做少许修正和补充。)
注释:
此次讲演所引用的主要资料如下:
① 于润琦主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②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
③ 卡尔·萧斯克(Carl E.Schorske):《世纪末的维也纳》,黄煜文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④ 李宝嘉(伯元):《文明小史》,台北:世界书局,1974。
⑤ 樽本照雄:《〈老残游记〉和〈文明小史〉的关系》,《清末小说研究集稿》,第42-63页,济南:齐鲁书社,2006。
⑥ 韩南(Patrick Hanan):《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上海教育学出版社,2004。
⑦ Moretti,Franco.The Modern Epic:The world-system from Goethe to Garcia Marquez.New York:Verso,1996.
⑧ Schorske,Carl E.Fin-de-siecle Vienna:Politics and Culture.New York:Vintage Books,1981.
⑨ Wang,David.Fin-de-siecle Splender: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标签:现代性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化论文; 晚清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王德威论文; 文明小史论文; 小说论文; 老残游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