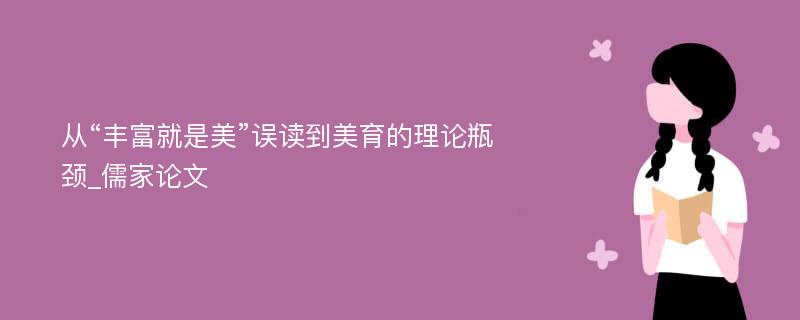
从误读“充实之谓美”到美育的理论瓶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育论文,误读论文,瓶颈论文,之谓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充实之谓美”本是孟子关于“性善”的一个命题。兴许是由于其中一个“美”字作怪,20世纪以来,海内外学者理所当然地把“充实之谓美”称为“儒家美论”的不在少数。有的美学家把孟子关于“六善”的命题拦腰砍断,把“美、大、圣、神”都解为“美”的层次;有人说“德美不分”是中国文化和“儒家美学思想”的传统,“充实之谓美”是其代表;有人称“孟子比孔子更为深刻地把握到了美与善的联系和美育与德育的关系,提出了关于人格美的论断:‘充实之谓美’”;有的海外学人干脆称“孟子的‘充实之谓美’是儒家美学强调人格之美的”代表言论。……
在美学圈子里,还有不少学者以“美”的今义比附古义,不加论证地把“充实之谓美”的“充实”讲为“道德品质”或“道德修养”,再把“之谓美”解释为“就是美”,再把这些文字相加,得出“充实之谓美”等于“道德品质就是美”(注:参阅张文勋《以“政教”为中心的先秦儒家文艺思想》,《文史哲》1986年第4期;王定金:《美育教程》,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 的答案……这类六经注我,望文生训的胆大妄为,早已不是“个别现象”。类似的误读,不但严重扰乱了审美文化的研究和导向,而且使美育长期不能实现其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始终不能真正得到实施。
朱光潜说:“不准确的理解和翻译就会歪曲原文,以讹传讹,害人不浅。”(注:朱光潜:《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91页。) 这本来是针对中外文化沟通的,但“‘充实之谓美’是‘儒家美学代表’”论的泛滥成灾,说明古今语义的沟通也存在“以讹传讹”的危害。
一、推究“美”本义与《孟子》用“美”的习惯,“充实之谓美”并非论美
“充实之谓美”是不是“儒家论美的代表言论”,把“充实之谓美”当成“公理”,是否符合“充实之谓美”的原意?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美感的“美”,和“充实之谓美”的“美”是不是同一概念。前文说过,如果“充实之谓美”没有“美”这个符号,多半没有人拿这段论述当儒家美学的经典。但持这种主张的人兴许忽视了,在孔孟言论中,“充实之谓美”的“美”和唤起美感的“美”,是差异极大的两个概念。
从字源上看,许慎《说文》有:“美,甘也。从羊大。”段玉裁注美字云:“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引伸之,凡好皆谓之美。”也就是说,“美”的本义是指美味。“好”是“美”的引伸义。而“善”的本意是“吉”,也就是好:“善,吉也,此与义、美同意。”也就是说,“善”在讲为“吉”的情况下,与“美、义”同意,都是“好”的意思。既然“美”和“好”的含义等同于“善”,而且“美与善同意”(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影印版,第154页。),那么,只要“美”在论述“善”的语境下出现,可以讲为“好”,那就应该而且只能讲为“善”即“好”,不可随心所欲地讲为别的义项,譬如讲为“美”。
“美”字在孔孟言论中,指“好吃”的相当多。如《孔子家语》有“食之,大美。”“夫好谏者思其君,食美者思其亲”。《孟子·尽心下》有“脍炙,与羊枣孰美”,这些“美”都是“好吃”的意思。至少在孔孟的言论中,说美字“从羊人”,缺乏语用学材料的支持。所以“美”“从羊大”一说,似更贴切。它的引申义也更多是“好”和“善”。
重要的是,美感教育的“美”,即与美感相联系的“美”,要旨在于充实和稳定了“美”的直观感受的一面。它的主要标志是:必有激起身心愉悦的美感的特质。如果不能使人产生身心愉悦的美感,不能称为美感教育的“美”——这一点,当为区别美感教育之“美”和“与善同意”的“美”的基本尺度。
第二个问题是,孟子“充实之谓美”的“美”究竟怎样讲,除了看“美”在先秦的一般用法,还取决于孟子本人使用“美”字的习惯。道理很简单,因为“美”这个汉字,是个表述多概念的符号,义项不少。先秦时代的用法与现当代“美”字表述的概念又有不少微妙的区别。因此,在澄清“充实之谓美”的旨趣之前,先要考察《孟子》关于“美”的习惯用法。根据我们的统计,在《孟子》全文中,除去完全重复的用法外,只有14处“美”,如“今王畋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仪仗)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主庶几无疾病矣”,“棺椁衣衾之美也”,“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等等。
在《孟子》那里,“美”字大多是“与善同意”,或“与甘同意”;有的则可以讲为“盛”;只有极少数明确地与情感和感觉上联系,如“好看”时,才和美感教育的“美”内涵相同。而“六善”第三层次的“美”,显然不是与审美情感相联系的,所以,“充实之谓美”的“美”,不可能与美感教育的“美”相当。
杨伯峻统计《孟子》17个“美”字,把其余16个“美”均归入“美好、美丽”一类,惟独把“充实之谓美”单列为“孟子所用术语”(注: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07、99页。)。我们不同意杨伯峻这样笼统地归“美”为“美好、美丽”的观点。但不管杨先生这样归纳的理由何在,至少说明他看到“充实之谓美”中“美”的用法,决不与“美好,美丽”的含义相同。即不与美感的“美”相同。
二、论述语境和历代注家注疏说明:“充实之谓美”旨在论“善”而非论“美”
在《孟子》中,有的话题似乎涉及到音乐等与美感有关的事物,其旨趣也并非讨论美感。如《梁惠王下》第一章:“庄暴见孟子”,好像在讨论“乐”,但稍作考察,可见这段文字只是以“乐”为例,说明“王天下”的主张,与论美的旨趣无涉。在《尽心下》中,孟子与高子的对话更像在讨论音乐。这段话大略是:高子说:“禹的音乐比文王的音乐高妙”,孟子问他何以见得,高子说:“因为禹传下来的钟钮都快断了”。孟子告诉高子这不能证明什么,只不过是乐器旧了便会坏罢了……很明显,这段话表面上是拿音乐说事,但孟子把论题转到了东西用久了就会旧、就会坏的自然规律。相信也没有人硬要把这段对话当成有关艺术的言论。这两个事例仍然告诫我们:断定孟子的“论美言论”要小心谨慎。即使出现了“美”,甚至出现了儒家美学核心概念“乐”,以及与艺术有关的内容,也还不好轻易断定为“论美”的文字。对“充实之谓美”的旨趣,也不能轻率地望文生训。
而且,在《孟子·尽心下》全文中,总共只有两个“美”字。前文说过,“脍炙,与羊枣孰美?”的“美”,是用的本义“甘”,意为“好吃”,与“充实之谓美”中“美”的内涵,完全不相干,可视为无;在“充实之谓美”的前后,也没有“美”和与美相关的概念。这样以一个孤立的“美”字断定“充实之谓美”为“论美”之作,等于是以“孤证”立论,这就犯了学术讨论的大忌。
从《尽心下》的主旨看,我们统计《孟子·尽心下》总共出现过36次“孟子曰”。这些表述文本要旨的论述,始终在阐述“仁”、“义”、“善”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全文的论述中心,自始至终都紧紧围绕着孟子的思想核心:“性善论”。如果说“充实之谓美”是孟子关于“美的论断”,无异于说孟子在以“仁、义、善”为主旨的著述中,偏离了主旨而去论“美”,之后又不明不白地回到了“仁、义、善”的主题。照此推论,就该得出《孟子·尽心下》的论述中心不止一个,或者论述中心发生了混乱的结论了,岂不荒唐?
反过来说,如果注意到《孟子》“性善”的主旨和“充实之谓美”的语境,对“充实之谓美”即便有“美”字,也只能是论“善”的需要有所警醒,坚信它不可能是另辟了关于“美”的论题,就很容易看到,“充实之谓美”只能讲为“性善论”的一个环节。这样,有关“六善”的一大串纷纭芜杂的文字就可以讲解得很顺溜,不至于把“六善”砍为两截了。
如果说以上论述仍然限于外围的、感悟的认识,那么,我们不妨深入到“充实之谓美”的语境和历代考据学家的文本,看他们认为这里的“美”,究竟是不是美感和美感教育的“美”。东汉赵歧《孟子注》和北宋孙奭的《孟子音义》,是关于《孟子》公认的权威注释。两位经注家的两种讲“充实之谓美”的文字,在详细考证的基础上,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充实之谓美”那个“美”的内涵,分明是“善”而不是“美”。我们先看赵歧的注解:“可欲,己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为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有之于己,乃谓人有之,是为信;人不亿,不信也。充实善信,使之不虚,是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实信善而宣扬之,使有光辉,是为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为圣人。有圣知之明,其道不可得之,是为神。人人有是六等,乐正子有善有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注: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07、99页。) 在赵歧这里,人格六层次的基础是善。以上五层,依次由小善而大善。“信”是“有之于己,乃谓人有之,是为信”。“美”的内容,是“充实善信,使之不虚”。到这里为止,“美”的内涵完全是以“善”为中心的,根本不具备与美感相联系的、可以唤起美感的“美”的特征。
八百多年后,为了补充陆德明《经典释文》惟独缺了《孟子》释文的不足,孙奭“奉敕校定”赵歧《孟子注》,孙奭以“推究本文,参考旧注,采诸儒之善,削异端之烦”为原则,在《孟子音义》中,直接把孟子“善、信、美、大、圣、神”归纳成了“六善”。并对“六善”的具体内容,作了更为详尽的阐释。在孙奭的研究里,“善”被明确地讲为“仁义礼智”;“有诸己之谓信”的“信”,则是“有是善于己,谓人亦有之”的善;所谓“美”,则是“充实其善,使其不虚”的更高层次的善;自身充实“善”,而且能以身作则,把“善”宣扬于外,就是“大”;使“善”的光芒辉映四方,影响广大,可以称为“圣”;一个人“善”的光辉达到“经以万方,使人莫知其故”的境界,就可以称为“神”了。到这里,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充实之谓美”的美,确实就是“美与善同意”的“善”。
由此可见,“充实之谓美”的核心概念“美”的内涵和外延,从未脱出“性善论”的范畴,也没有涉及儒家美学观和美育思想。而以“善”为基础的人格六层次都是层层递进,紧密相连的“善”的层次。
三、先秦“美”和儒家美学的距离及曲解儒家美学的后果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的孔子论美的文字,有不少美丽的传说,但其中并没有涉及到“美”字。这就是说,司马迁很清楚:美,并不是儒家美学的术语,不能乱用。学术界一般认为,先秦儒家最重要的论美典籍,有《礼记·乐记》和荀子的《乐论》。但我们遍查《乐记》,没有一个“美”;遍查《乐论》,没有一个“美”——公认为专门阐释儒家美学美育思想的专著、典籍,反而从来没有使用“美”来表述美学概念,不是从反面证明“充实之谓美”未必是论美之作吗?即便是所谓可靠性有疑问,年代也不算晚的《孔子家语·辨乐》和有关孔子教育思想的《六艺》也没有使用“美”的符号。在儒家美学和美育的专门论述及权威史家的记述中,都没有使用“美”字。还不能说明先秦时期,“美”这个符号与儒家美学的核心概念难以挂钩吗?
先秦儒家是怎样论述德育和美育的呢?主要是以“礼”和“乐”为术语,阐述礼教和乐教,或曰论述德育和美育的。这一点,从儒家之所以被称为儒家的缘由里就能找到些许答案。“儒家”之所以称为儒家,是因为儒家创始人孔子曾经是专为奴隶主贵族祭祀一类事情帮忙的“儒”。“儒”的前身擅长搞巫、史、祝、卜。而巫、史、祝、卜的内容,一是众多的、烦琐的礼节、规矩,一是吹吹打打的音乐。备受孔子推崇的“周公制礼作乐”,实际上就是把礼、乐从巫、史、祝、卜等原始巫术、礼仪中分化出来,形成系统化的教育思想而已。
出身于儒,又对周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孔子,坚定不移地通过“礼”和“乐”对后人进行教育,施行礼教和乐教,是顺理成章的。在儒家的教育体系中,礼教灌输行为规范的教育,相当于今天的德育;乐教是关于音乐、舞蹈等艺术素养的教育,相当于现代的审美教育。对这一点,近现代美学家并没有异议。蔡元培说:“礼为德育,而乐为美育。”(注:高平叔编《蔡元培美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叶朗说:“中国古代思想家讲得很清楚。德育是‘礼’的教育,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美育是‘乐’的教育,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注:叶朗:《应该把美育正式列入我国的教育方针》,《新华文摘》1999年第9期。) 由此可见,先秦儒家对德育、美育的不同教育功能,本就有很深刻的认识。只是他们使用的术语分别是礼、乐,而不是德、美。孟子的“充实之谓美”的“美”也不可能突然用来论美。
总之,“充实之谓美”只是阐释“性善”六层次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关于美的论断,根本谈不上儒家的“德美观”。以“充实之谓美”为“德美不分家”的理论支柱,是一种严重的谬误。只是在后人的多重曲解中,“充实之谓美”终于变成了“儒家美学代表言论”。这既是孟子和先秦儒家的悲哀,也是现代审美文化的悲剧。它实际上成了当今社会上以善代美,以善为美,美善不分的主要理论根源之一。
由于美学家纷纷称“充实之谓美”为儒家美学的代表言论,教育学家作为只是运用(而不是研究)美学成果的群体,难免以“充实之谓美”来证明美育是德育的工具。事实上,教育家和德育工作者经常使用的“人格美”概念,其中的“美”,早已同“充实之谓美”的“美”——事实上的人格“善”完全等同。然而,这个“人格美”与美感教育意义上的人格美,或者说与先秦儒家的人格美,又是有相当距离的(注:在大多数情况下,德育和教育心理学家笔下的“美”,是在用“美”字修饰有关“善”的说教,但儒家人格美的内涵绝不只限于单纯的“品德高尚”。儒家的人格美,涉及到丰富多彩的“美”的方方面面。孔子关于人格美的论述就有:“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而这里的人格美,明显包括了智育的“诗”,德育的“礼”和美育的“乐”;“文质彬彬”也包含了审美情趣和内在品质两方面。所以,先秦儒家推崇的是全面发展的完美人格,而不仅仅是“人格善”。大多数当代教育家眼中的“人格美”,既不同于儒家的“人格美”,也不符合全面发展的完美人格的标准。)。如果大家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这仅仅是一种语用现象,至少无可厚非。问题是,如果我们根本不明白这个变异,不知不觉地把“美”和“善”等同起来,就难免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和意想不到的恶劣后果。
澄清“充实之谓美”究竟论善还是论美,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还涉及到能否净化健康的学术环境,能否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能否得到实施等重大的社会问题。因此,从辨析“充实之谓美”之类重要命题的本意入手,使美育和德育各归其位,既关系到社会文化的净化,又关系到教育方针的成败,值得学术界和有关部门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