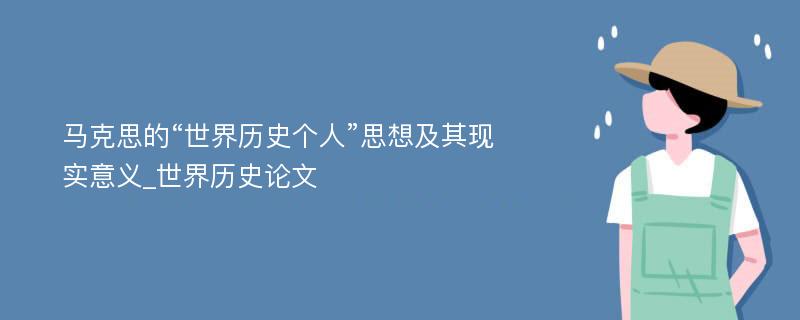
马克思“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历史性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思想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思想,内涵着对“个人”的科学把握,即把个人看作是由“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马恩选集》第1卷,第40 页)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环节,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视角考察“个人”,既避免了旧唯物主义将个人只看作是生物学的个体的毛病,也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将个人看作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的范畴的化身。从哲学的角度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包含着这种见解。
一、理论视角的转换
18世纪是产生“个人”的世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冲破了原有的封建等级制度下个人依附于家族、等级等共同体的旧模式,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体意识”姗姗而来。个人走向独立。从所有制上看,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淹没于利己主义之中。个人又走向孤立。个人出现了,有关个人的理论观点也就相伴而生。但是,在马克思以前,无论是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还是德国古典哲学,都是从抽象的意义上考察个人,前者视个人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纯粹客体,后者从纯主体的角度将个人概括为“无人身的理性”的化身,“绝对观念”的“工具”。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把个人看成是“社会原子”,社会就是由各个“原子”组合而成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本意是推崇个人、维护个人的个性和尊严,不是从社会历史因素造成的社会关系中观察人的个性,而是从人的生物本性中引伸出个人的本质。结果,本意是要讴歌个人却在理论上将“个人”放逐了。
德国古典哲学从抽象的主体性角度考察个人,成就辉煌而结果暗淡。
康德对个人的看法浓缩在他的“非社会的社会性”的人性论中。康德之所谓“社会性”是指个人先验地具有结合在一起的倾向;“非社会性”是指个体先验拥有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本性,即康德之所谓人性之“恶”。康德这里提出的其实就是个体与类的矛盾问题。康德是轻视人类的个体的,而把“自然的意图”、人的“至善”境界放置于人类的全体之中,个人只是人类走向“至善”的手段。不过康德也明确承认,整体的“至善”必须通过个人之间的私利斗争这一“恶”的途径来达到。
黑格尔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考察个人。黑格尔并不单从个体与类的矛盾中展开其个人的观点,在他看来,无论人类的整体还是个体,都不过是“世界精神”的工具。在“工具”视角下,黑格尔谈起个人,既显示了抑制不住的明快与赞赏之情,又贬低了个人的作用,理论上是矛盾的。比如,他视拿破仑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表明了其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认同,同时又将其归结为“绝对理念”的代言人、工具。
费尔巴哈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在个人的观点上前进了一大步。同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相比,费尔巴哈避免了仅从自然的生物个体自身引伸出个体的本性,而是将个体放在个人之间的相互需要的类存在中考察,显行更辩证;同康德和黑格尔相比,费尔巴哈避免了将个人仅视为“无人身的理性”的工具和化身的唯心论,提倡人本主义,从而显得更唯物。费尔巴哈的著名命题是: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前一个“人”是指个人之间结合的“类”,是超越法国唯物主义的,后一个“人”是指活生生个体,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论。但是,费尔巴哈关于“个人”的思想也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他虽然主张从群体、类中考察个体的本质,但他所理解的“类”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结合,个人之间的相互需要只是自然需要。他虽然主张从生命的个人出发,但仅把个人理解为感性的直观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实践的主体。
马克思在考察“个人”的问题上,进行了根本性的视角转换,这就是“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思想。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个人的产生,建立在两个普遍发展的基础上:一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二是交往的普遍发展。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使得原有的民族的、地方性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从而使“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
正如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而形成的那样,世界历史性个人也是如此。世界历史性是个人的基本属性,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个人只有在世界历史出现的前提下才能出现,才是一种“经验的存在”。即这种意义上的个人只能在人的生命本质之外的社会本质中得到实现。
马克思把社会意义上的个人的形成分为人类发展过程的三大阶段,“人的依赖关系”为最初阶段,包括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这时不存在社会意义上的个人,因为生产力极端低下,人只能以族群为主体,通过血缘或地域的自然纽带结合在自然的共同体之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这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资本主义时代。这时期在大机器工业和世界市场的普遍发展的前提下,出现了具有自主性的独立个人,即不同于依附在“血缘共同体”之中的自然个人的“世界历史性个人”。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个人是一种生成,也有自身的发展。“世界历史性个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一种“自发的存在”,因为个人所释放的生产力汇成一种巨大的、脱离个人的异化力量统治个人,所以这种个人只能为“自由个性”的个人作准备。
“世界历史性个人”是系统性存在的个人。系统性存在的个人是指:世界历史形成后,原有的以某一特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积淀而成的个人越出了民族、地域性的界限,而以相互交往的各民族的文化之间的渗透、冲撞与融合作为规定个人的历史背景。原因是,世界历史产生以前,各民族的历史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独立进行,以民族的个体显示人类历史之一般;世界历史形成后,各民族相互交往与渗透,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某一具体民族的关系转变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民族特色只能作为整体的一个有机部分而得到说明。马克思认为民族的特殊性逐步消失,各民族的地方文学转变为“世界文学”,其精神实质并不在于世界历史条件下民族特性不存在了,而是说民族特性已不能单独起作用了,汇入到各民族相互关系的整体之中。对个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是个体发展的历史。所以,处于世界历史中的个人,面对世界市场,他的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2 页)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并不意味着个人之间“依赖关系”的消除,而是“使这种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同上,第145页)。 越是有世界性就越有民族性。从个人角度说,越是自觉融入世界交往的个人就越具有个人性,这里,生物个体性和民族独特性只是世界历史性的载体、承担者,个人表现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即一种系统性的存在。
二、“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历史作用
“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出现,使人类历史发展的速度与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世界历史性个人”促成了人类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效应。世界历史产生以前,个人的生产活动具有种族性、区域性,个中原因在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发展水平处于发展的低层次。而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页)。 处于低层次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使得各民族的生产力相互隔绝,新的生产力在各民族那里都是“单独进行”,“从头开始”,这样,各个个人的生产力必然体现为一种低水平的循环与重复。世界历史出现以后,各个民族的历史运动越出了“狭隘的”范围,表现为在相互影响过程中的生产力与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即各个民族的生产力在普遍交往中以自己的优势部分换取不足部分,每个民族不必一切“从头开始”,而是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去创造新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跳跃式”的加速度效应。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狭隘的个人向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转变是同步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有可能突破特定文化背景所积淀的知识储存,广泛吸取人类文化的已有知识成果,使个人生产力出现放大效应。
个人生产力之所以产生放大效应,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世界历史性个人冲破了以往依附于血缘、地域以及政治共同体的个人,走向个人的独立性。马克思将中世纪的个人称之为“人类动物学”时期,意在指明受等级支配的身份性个人的非独立性,压抑着个人生产力潜能的发挥。相反,在世界历史时代,个人的等级身份变成了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包括个人之间自由地交换、让渡各自的产品,地域之间的流动,个人所属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渗透与整合。马克思曾将人化的自然看作是人的身体的延长,是人的“无机自然”,同样,独立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世界历史性个人,也将各个不同的文明成果做为自身潜能的“无机自然”。一个民族应当善于向其它民族学习,一个被强力拖入世界历史的民族,蕴育于“母体文化”的个人,应当自觉面对世界文明主潮流,将自身的原有文化背景融进各个民族文明成果整合而成的系统质之中,从而放大自身的创造力。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这里, 民族特殊性融进世界文明的整体之中,地方性个人融进世界历史性的整体之中。“特殊性”、“地方性”不是消失了,而是原有的“独自进行”的机制消失了。
“世界历史性个人”的产生不仅导致了人类生产力的加速发展,而且也是个人的更高程度的发展。“世界历史性个人”有自己的“产生史”,也有自己的“发展史”。资本主义首创了世界历史,使个人从原有的狭隘依附状态走向独立,推动了“个人”的解放,但同时,又使个人的世界历史性处于一个较底层次。个人生产力的极大释放,在资本主义时代成为支配个人的物质力量,个人处于个体与类的矛盾冲突之中。
马克思将“世界历史性个人”的低级阶段看作是向更高阶段过渡的必经环节。他认为:“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Ⅱ,第125页)。 个体与类的这种矛盾,终将会以其自身的“自我否定”而走向和谐式发展,“‘人’类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同上)。这个阶段,就是马克思称之为个人从“自发的”独立阶段走向“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做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
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看来,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应当站在已经存在的世界历史高度,面对早发的“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自发性局限,积极地建构“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新模式。正如世界历史形成后,各民族可以根据已有的发展高度来把握自身发展的起点,而不必“从头做起”,“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建构也是如此。如果说,马克思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的思想,不是作为发展模式的范导,即A变为B的过程,而是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发展中减轻“分娩痛苦”的价值参照的话,那么,“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形成也没有固定的模式。
马克思曾在早期的著作中设想落后的德国经济状况不必重复英法等国的老路,而是径直完成经济发达国家所趋向但尚未出现的真正的“人”的革命。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在当时的表达方式还存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但问题所触及的实质却是科学的、深刻的。
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呼唤有特色的“世界历史性个人”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建设,是资源配置的手段,目的是达到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从哲学的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是一场“人”的革命,即将现实的中国人塑造成有特色的“世界历史性个人”。
现实的中国人处于历史、现代、未来状态之中。面对历史,国人需要摆脱历史因袭的重负,从血缘依附、政治依附的传统个人走向独立人格的现代人。面对现代,国人处于世界历史的整体之中,有可能借助于已有的发展模式缩短独立人格的成长过程,中国人不仅应当同其它民族的人民生活在同一世纪里,更应当同其它民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人民生活于同一时代之中。面对未来,国人不应重复发达国家个人形成的旧模式,而是寻求积极的“世界历史性个人”发展的新途径。西方国家以个人本位为取向的个人发展模式,在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效应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负效应,中国的个人发展构想,应当形成自身的特色。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关个人塑造的理论源头,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其一,自主原则。马克思将摆脱血缘和政治的人身依附看作是“世界历史性个人”形成的前提,即个人走向独立的自主原则。市场经济内在地包含着平等独立的自主原则,但中国几千年的纲常伦理的等级传统,阻碍影响着独立个人的形成,这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培育与发展,反过来又影响到个人的塑造与形成。所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是一个产值问题、增长问题,也包含“人”的问题。“个人”的解放必然带来创造潜能的发挥,最终引发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当然,这个原则决非主张“个人本位”、“唯利是图”,而是内在地结合于集体主义之中。
其二,系统原则。“世界历史性”的中国人,应以整体的人类文明成果作为支撑个人的文化内涵,这意味着,不能以传统的“母体”文化作为塑造个人的根基,当然也不是要将中国人变成“西方人”。世界历史形成后,民族特色融进了整体的人类文明之中,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值”、“整合值”,“特色”只有在整体之中显现,愈有世界性就愈有民族性。这一世界大趋势下,主张通过所谓“传统的现代转换”来塑造个人,是一种幻想。这与“西化论”、“中西结合论”一样,都是忽视了各种文化冲撞与融合所形成的系统值对个人塑造的意义,而把某一局部文化作为前提,或者象“结合论”那样将两种异质文化作简单的“叠加”。所以,国人走向世界,就是中国的“母体”文化融进各民族文化的整体之中的过程。
其三,超越原则。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意味着“个人”塑造工程应面对个人的未来发展趋向上,不是跟在西方发达国家“个人”发展的现有“经验”背后亦步亦趋,而是借鉴已有的教训迎头赶上,走同步发展、“超前”发展的新路。事实上,先行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模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状态的批判,其用意就在于此。法兰克福学派有关“单面人”、“文化工业”的概括也在某种程度上击中了要害。“文化工业”说旨在表明,那种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纯感官刺激文化无法满足人们多方面的审美需求,把人的非物质的精神活动降格为一种单一的物质活动,因而是对“个人”完整性的扼杀。我国有人提出“文化市场化”的思路,尽管体现了“全球性”的眼光和与世界全面接轨的雄心,但却缺乏批判的意识。应当说,这样的战略对“个人”的塑造是不利的,是一处短视的“构想”。因此,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从塑造“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角度说,也有一个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