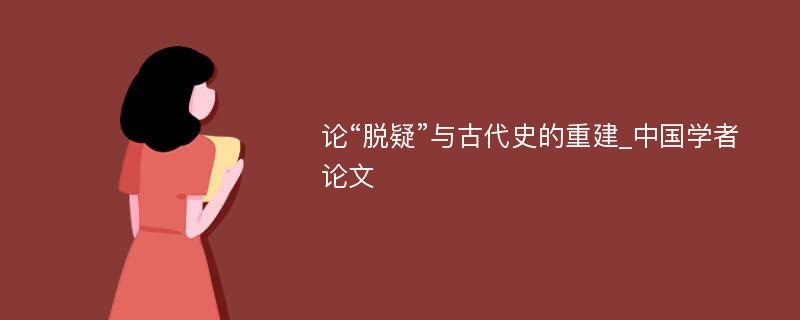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7)06-0051-07
1992年李学勤先生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作了题为《走出疑古时代》的发言,后发表在《中国文化》第7期。1995年,李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的论文集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论文集》出版修订版,增加了《谈“信古、疑古、释古”》和《对〈走出疑古时代〉的几个说明》两文。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李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理论从提出到形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论点体系,在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的同时,也不断受到学术界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这说明,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尚存在较大的分歧。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理论进行一番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以期将该问题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一、极端疑古的不良影响与“走出疑古”论点体系的形成
李学勤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的理论是在特定的学术背景下提出的。众所周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学者,否定了战国以来经书所载的古史系统,并以考证的方式辨析了旧的古史系统的形成过程,尤其是顾先生“层累造成的古史”学说,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大论战,从而颠覆了传统的历史。《古史辨》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曾得到史学界的充分肯定。如郭沫若先生即曾评价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有先见之明”[1]。当代史学家称《古史辨》的古史辨伪工作,“对于推翻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绩。”[2]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以上对《古史辨》的评价是公允的,是合乎历史实际的。然而,随着考古学的蓬勃发展与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共同发现,极端疑古派学者错疑所不应疑的偏向,的确给古史研究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即曾认为,古代“口耳相传”的史料大都有其历史的核心,也都有其历史的渊源。它是未经后人加工整理的零散资料,应比经过加工的系统化的“正经”或“正史”中史料更为质朴……古书中如《尚书》、《史记·五帝本纪》诸篇中或有靠不住的传说资料,那是因为古人在整理时的方法不够精确,并非古人有意作伪或造谣[3]。徐先生这一认识,有助于矫正极端疑古派学者错疑所不应疑的偏向,“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体系。”[3]王树民先生也曾指出,“《古史辨》几乎把古代一切有关史实的记载都看成虚实不分的传说,而不注意其中隐藏的史实,实际上是将传说与神话混同起来,结果不免将治丝而愈棼。”[4]如《古史辨》即曾将古代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传说全部视为后人编造的,而今天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五帝时代就颇应值得重视,至少包含不少史影。对古史文献的记载,要加以甄别和整理,正确的态度是不可轻信,也不要轻易全盘否定。要科学和理性地对待五帝本身和五帝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虽然是后代学者的追述,但很多是非常有价值的,从不同角度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5]。总之,由于时代的局限,《古史辨》未能结合考古学材料来考辨古史,加上有的地方怀疑过头①,他们在对中国古史系统彻底打破的同时,也将古史传说中所包含的大量有价值的素材几乎全盘否定,从而使数千年的传说时代的历史呈现出一片空白。不惟如此,有的学者还批评《古史辨》在研究方法方面存在诸多不当之处。如过分地使用默证[6];对于史料不能做到审慎地处理,抹杀不利于自己的证据等。综上所述,史学界在充分肯定《古史辨》对中国学术的重大贡献的同时,也不断认识到极端疑古思潮给中国古史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开始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理论局限,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发展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和考古学研究日臻走向深入,学术界对晚清以来的学术史不断获得新的认识。李学勤先生在对《古史辨》的学术贡献和进步作用进行充分肯定的同时,明确指出,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也有副作用,……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7]”与此同时,李先生还指出,“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了。”[7]李先生所说的“走出疑古”的必要性,正是其同时讲到的“在学术、文化上要有所发展,就一定要扬弃前人那个时代的局限”[7];而其所说的可能性,则是“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7]至此,李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的理论观点初步形成。1994年,李先生又继续阐述其大胆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原因:“最近这些年,学术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大量发现的这种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古书辨伪的成果进行客观的检验。事实证明,辨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有必要予以平反。更重要的是,通过整理、研究出土佚籍,能够进一步了解古书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还体会到,汉晋时期的学者整理、传流先秦古书,会碰到怎样复杂的问题,作出多么艰辛的努力,后人所不满意的种种缺点和失误又是如何造成。”[8]李先生在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之前,即曾提出:“疑古思潮是对古书的一次大反思,今天我们应该摆脱疑古的若干局限,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大反思。”[9]李先生在提出“重新评价古代文明”和“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大反思”的基础上,最后得出结论即“重写学术史”。李先生指出:“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这不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学术史一定要重新写,其实不只是先秦的、汉代的,后来的也要重新写”[7]。“由于简帛所涉及的晚周、秦、汉是学术史上的关键时期,这项研究工作的影响自然不限于这样的历史段落,而是关系到对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探讨和估价。”[10]P226以上“重新估价古代文明”、“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大反思”及“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11]。以上论点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李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的理论已逐渐成熟。
二、“走出疑古”理论的学术取向及其理论上的疑难
李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的观点,一经提出即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颇为强烈的影响,聚讼纷纭,褒贬不一,其中值得注意的,2006年10月21日—22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举办“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众多学科领域的五十余位学者会议期间同台论辩,就“疑古”学说的认识和评价、出土文献的意义和价值、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等一系列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有的学者称这是“‘疑古’与‘走出疑古’的第一次正面交锋”[12],李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理论自然也成为会议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事实上,早在此会召开之前,“疑古”与“走出疑古”的激辩烽烟已经点燃。如林甘泉先生指出,不能将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13]。另有学者指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表明,作为工程的指导理念,“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以及“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14]。最近,林沄先生也发表文章指出,从古史辨开创了疑古时代之后,中国的古典学,实际上就进入了疑古和释古并重的古史重建时期。这种重建是以对史料的严格审查为基础,把古文献和考古资料融会贯通而进行的。因此,无需另立一个释古时代,或另称考古时代。由于这个古史重建时期永远要保持对文献史料严格审查的精神,所以提“走出疑古时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代表信古回潮的错误导向[15]。以上各家对“走出疑古时代”学术论点由质疑、批判乃至全盘否定,代表了当今古史学界的一种学术倾向。在我们今天看来,当今古史学界对“走出疑古”理论的质疑、批判乃至否定,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李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的学术论点的确在内容和逻辑方面都存在若干重大的理论方面的缺陷,给学术界留下诸多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其次,李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体系形成过程中,一些表述,委婉含蓄,甚或是含糊其辞,使得一些学者对李先生所表达的内容在理解上产生诸多不小的分歧。既然如此,我们应对李先生“走出疑古”论点的学术取向进行一番深入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
1、“走出疑古”是对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扬弃,其真正的意图是“超越疑古”
在“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体系形成过程中,李先生不只一次地强调,“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的,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部都踢翻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7]“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确实把信古打倒了。凡细读过七册《古史辨》的人,都会看到这一思潮的成绩。疑古的学者不仅总结了宋、清以来这方面的成果,而且完善了辨伪的方法和理论。这一思潮的基本学说,如顾颉刚先生在1922年建立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至今仍影响着海内外的学术界。”[8]有的学者称,李先生所肯定的“疑古”的进步意义,“只局限于‘反封建’、‘解放思想’的思想史意义”[11],这种说法是颇为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在强调晚清以来“疑古”的“反封建”、“解放思想”的思想史意义的同时,李先生也充分肯定了晚清以来“疑古”的学术价值。如文前提到的,李先生指出,“疑古的学者不仅总结了宋、清以来这方面的成果,而且完善了辨伪的方法和理论。”李先生不仅强调“顾颉刚先生在1922年建立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至今仍影响着海内外的学术界”,而且他在古史研究中对待史料的态度与这一基本学说,并不完全矛盾。兹可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如李先生对诸子书的记载并非采取完全相信的态度,他曾指出:“翻阅战国诸子的作品,不难看到很多古史记载都受到作者的观点的影响,甚或是为了适应一定的观点而加以改造的”[16]。又如对待先秦时期的史料,李先生同样注重进行科学的审查,不可全信。如《古本竹书纪年》所载启在位年数,分歧很大。李先生称:“《纪年》所载夏王在位年数的可信性,没有可资核校的证据”,它“只是出现较古的一种说法,我们也不可完全拘泥。”[16]又如他指出,有很多书籍,记有黄帝以来,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年数。这些记载,大别之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史记》以前的文献,有的是传世古书,如《尚书·无逸》说商武丁在位59年等;也有的是古时出土的材料,如西晋时发现的《竹书纪年》。第二类虽成于《史记》之后,但可能有更早的渊源,如纬书《春秋命历序》云夏“凡十有四世,治四百七十三年。”第三类则出于学者的推算编排,如见于《汉书·律历志》的刘歆《世经》。这种编排,到宋代的邵雍《皇极经世》以下更加系统详细,但总是含有许多不足为据的主观成分,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近代学者的怀疑和否定[17]。他强调:“对传世文献材料,作严格的整理分析,首先确定材料的形成时代以及真伪。”[18]从以上可以看出,李先生在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同时,对于杳远的上古史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称得上“当信则信,当疑则疑,一切取决于对片甲碎金、断简残帛的破译与缀合。”[19]因此,尽管李先生在提出“二次反思”和“走出疑古”期间,学术界出现过一些全盘否定“疑古”和走回“信古”、“复古”的倾向②,但总的来看,李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并非意味着与“疑古”彻底决裂,或者说是与“疑古”已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11],而是试图在对古史辨派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过程中,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
2、“走出疑古”理论的局限与逻辑上的疑难
还应该强调的,李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的理论的确在逻辑上存在一些无法自圆的疑难,这一点,当代不少史学家也曾提出过有说服力的批评。顾颉刚先生晚年曾提出“疑古不能自成一派”的著名论断:“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20]历史事实也的确如顾先生所言。众所周知,顾先生的弟子有些意见跟他一致,有些并不一致,方法上也未必完全一样,只能说疑古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思潮。“古史辨”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论,刘掞藜、胡董人、柳诒征等人都极力反对。文前还列举王国维《古史新证》中亦曾批判《古史辨》疑古过甚,张荫麟直接批判《古史辨》过多使用默证。此外,实证学派中不少学者如钱穆、吕思勉等也同样批评顾先生疑古过头。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中,胡绳曾批评《古史辨》没有把历史学和史料学区分开来。吕振羽、郭沫若也极力反对《古史辨》疑古过头的学术倾向。正是基于以上客观存在的事实,林甘泉先生明确指出,《古史辨》出来以后,中国史学界根本不存在一个疑古时代,只存在对《古史辨》评价不同而已。林先生还指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不是三个阶段的问题。不能笼统地说《古史辨》以前是信古,《古史辨》是疑古,我们现在应该“走出疑古时代”。[13]林先生以上对中国20世纪学术史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其所作结论自然也是言之成理的。
当代中国古史学界普遍关注的另一重大问题,则是“走出疑古时代”之后,中国的古典学将走向何处的问题。这一问题,李先生虽然屡屡言及冯友兰先生的“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说,并不只一次地强调王国维先生将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的现代方法论意义,但由于在更多的表述中,语句委婉含蓄,甚至模糊不清,给当代古史学界留下了更多的疑问和深深的思考。如林沄先生强调指出,冯先生所说“疑古”和“释古”是分工合作的关系,“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其间无所谓孰轻孰重。”现代史学不可能有一个将史料完全审查结束而进入一个“释古”的时代,冯先生丝毫没有设想在疑古时代之后再有一个释古时代的意思。[15]此外,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李先生所谓“走出疑古”的真正学术意图即在于“超越疑古”,重建古史。这一点,在李先生的论著中有不少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李先生不只一次地强调,“我们每一代人,在学术、文化上要有所发展,就一定要扬弃前人那个时代的局限,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这样做,就不能发展。”[7]1996年5月16日,宋健先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座谈会上发表《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讲话。由李先生任首席科学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九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试图对夏商周年代学进行系统的探讨,为将来的古代文明研究在方法论上开辟新的道路。宋先生特别提到《走出疑古时代》这本书,这实际上是整个讲话,也是整个工程的基调[21]。在李先生看来,“走出疑古”、“超越疑古”就存在一个古史重建的问题。他主张“走出疑古时代”之后,下一步就是要“进入释古时代”[7]。李先生颇为推崇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古史“二重证据法”。的确“二重证据法”的运用,成功地开辟了古史研究的新途径,其在客观上对于其后建立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先秦史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二重证据法”迄今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学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王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都可以称得上是这一研究方法的积极实践者,尤其徐中舒先生及其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将“二重证据法”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他们对古史多重证法的倡导和娴熟运用,是古史研究方法论的重大突破,进一步提高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从王国维到徐中舒、唐嘉弘先生,三代学人,薪火相传,并不断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发扬光大,从而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22],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因此,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讲,李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超越疑古”及古史重建工作,事实上并非一个新的学术命题,其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
综上所述,李学勤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体系是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并不断获得重大突破的学术背景下提出的。他的本意是试图采用文献记载和考古学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古史、古书重新进行检讨,克服《古史辨》疑古过甚的错误倾向及方法、理论方面的时代局限性,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地位重新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走出疑古”并非意味着与《古史辨》彻底决裂,而是在批判继承中对传统学术的合理的扬弃,最终达到“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目的。“走出疑古”是李先生对中国当代古史理论的一次新的理论探索,其学术价值值得充分的肯定和重视。“走出疑古时代”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其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理论上的缺陷和逻辑上的疑难,它是一有待于李先生和当代古史学界共同努力、不断完善的学术命题。对这一论点体系不加分析地盲目信从或是主观武断地全盘否定,都不利于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
三、“超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古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尤其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与科学的古文字学的建立及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新兴学科的兴起,中国的古史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都大大超出了前人。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在于前人尤其是顾炎武、钱大昕等学者以渊博深邃的学术功底和较为科学的方法为20世纪的古史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可靠的学术基础,与此同时,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徐中舒、唐嘉弘、李学勤等学者更以渊深的国学功底,充分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借鉴前人和当代国内外学术界的方法理论,融通中西,不断擘划着中国古史研究的新领域,开创多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从《古史辨》到“走出疑古时代”,从“二重证据法”的积极倡导和实践到古史多重证法的自觉运用,从新资料的整理、研究到新的方法理论的探索,不断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水准推进至新的高度。正是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勇于探索和辛勤耕耘,才有了中国古史研究的迅猛发展与古典学的空前繁荣。对于前贤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理论我们应该在科学的批判继承过程中,兼收并蓄,进行科学的汲取和发展,从而不断推动中国学术的进步与创新。
前面已经分析,“超出疑古”是“走出疑古”的真正学术意图,重建古史则是“走出疑古”的学术目标。为达到这一预期的目标,笔者以为,中国的古史学界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继续重视古史理论的探索。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要对古代进行科学的研究,仅仅有文献和考古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理论……只有把理论和材料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加深对古代的认识。”[23]他反复强调,“对一个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人来说,理论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把理论、材料、眼界三方面的修养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有所进步。”[24]“先秦史的工作,必须将理论和材料结合起来,才能对距离我们如此遥远的历史文化有较全面的认识。”[25]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在前人基础上,不断进行古史理论的探索。如谢维扬先生应用酋邦概念对中国古史之系统考察[26],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国国家产生典型道路的三历程、国家形态发展阶段的三步曲和国家形成模式的三类型“庞大理论体系”的构建[27]、晁福林先生“氏族封建制”新说的提出和有中国特色社会形态理论的探讨[28],周书灿关于共主制政体下的原始联盟制国家——封建制政体下早期复合制国家——郡县制政体下的早期单一制国家的中国早期国家发展道路的概括[29]等。不管以上理论能否为学术界普遍接受,或者是否与中国古代历史实际完全相符,但这些理论探索的基础上,中国古史研究必将向着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则是毫无疑义的。
第二,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为古史研究奠定合格的古史史料学基础。真实可靠的史料是进行古史研究的基础。梁启超先生曾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又说,“时代愈远,则遗失史料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30]P40-41徐中舒先生亦有类似的表述:“史之良寙率以史料为准,史家不能无史料而为史,犹巧妇不能无米而为炊。”[31]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曾将古史材料区分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32],并强调“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33]P65。今天,现代学者在王先生“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把地下出土的无字器物和和古遗址中所包含的文化遗存并皆视为古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将古史史料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和纸上文献的继续审查则是建立合格的古史史料学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34]。合格的现代古史史料学的建立,是古史学界“超越疑古”和重建古史的前提和基础。
第三,加强科际整合,进一步提高古史研究的科学性。自王国维先生积极倡导和大胆实践古史“二重证据法”以来,古史研究深度与广度大大超过了“汉学”、“宋学”与“乾嘉之学”。王国维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35]、徐中舒先生《耒耜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36]、《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37]、胡厚宣先生《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38]、王玉哲先生《鬼方考》[39]等皆为传世之作,以上论著均将历史学科的边缘学科与交叉学科进行科际整合,成为诸有关学科的综合性典范之作。徐中舒及其弟子唐嘉弘先生开创并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资料和民族学资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更是对“二重证据法”的进一步发展。苏秉琦先生指出,“自考古学和民族学已分化成独立学科后,把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结合起来的工作,在欧洲,至迟19世纪末已经开始;在我国,自本世纪(按:指20世纪)20年代以来,也不断有人进行。但三者的全面结合程度,至今仍有相当的距离。”“实现考古、历史与民族三学科的结合,定将大大提高认识过去和预见未来的能力。这无疑是三个学科的共同责任。”[40]随着古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宽,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地理学、文学、文字学乃至自然科学多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必将成为未来学术发展的大势。古史学家应主动与各边缘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专家,相互合作,形成古史研究独具特色的多学科性综合型风貌,以进一步提高古史研究的科学性。
第四,进一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在疑古思潮笼罩下,中国古书、古史普遍受到怀疑,尤其在“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支配下,封建史学家所编排的古史系统被彻底推翻,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呈现一片空白。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与研究深入,被《古史辨》一笔勾销的东周以上的历史逐渐清晰。首先是殷墟的发掘及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证实了商朝的存在及司马迁《殷本纪》所载商代先公先王世系的完全可靠,由此人们推测司马迁《夏本纪》所载夏代世系同样应该是可信的。二里头遗址大型宫殿基址的发现与二里头青铜文化的内涵,极具说服力地印证了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的客观存在。然而,由于考古学家对二里头文化的族属及考古学上的夏文化的概念,争讼不止,长期以来,夏代历史的研究仅停留在依靠晚出的几条文献记载的推测阶段,《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拥有470年历史的夏代变成了事实上的“传说时代”。至于夏代以前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历史,则由于“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57],历史学家则很少问津。自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58]一书问世,这段漫长的传说时代的历史的研究才真正起步。建国后尤其是近年来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无论是考古工作涉及的地域之广,还是获得考古资料之丰富,都是空前的,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虞、夏之际历史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在“走出疑古”理论的影响下,2002年国家“十五”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正式启动,该工程涉及的内容广泛覆盖了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学、古环境(含古动物和古植物)、冶金史、科学分析与冶金技术等近十个学科。该项目设置有古文献有关尧舜禹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成果的整理、中国天文学起源研究、礼制的起源与研究成果的整理、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分期等十一个课题,目前,各分课题已不同程度地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而新近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以许顺湛先生的《五帝时代研究》[59]、王晖先生《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新证》[60]等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发表,标志着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将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超越疑古”和古史重建的新阶段。
注释:
①早在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曾批判“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他积极倡导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杨向奎先生曾批判古史辨派学者怀疑《左传》全是伪作,“给当时的古史研究者添加了许多麻烦,以致有人用了很大力气证明《左传》不伪。”参见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杨向奎:《论“古史辨派”》,《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
②裘锡圭先生说,疑古派以及其他做过古书辨伪工作的古今学者,确实“对古书搞了不少冤假错案”。不过他们也确实在古书辨伪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有不少正确的、有价值的见解。真正的冤案当然要平反,然而决不能借平反之风,把判对的案子也一概否定。对古书辨伪的已有成果,我们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决不能置之不理或轻易加以否定。可是现在有一些学者所采取的,却正是后一种态度。虽然他们多数只是对古书辨伪的一部分成果采取这种态度,在学术上的危害性也还是相当大的……我们走出疑古时代,是为了在学术的道路上更好地前进,千万不能走回到轻率信古的老路上去。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包括古书辨伪在内的古典学各方面的已有成果,从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继续前进。只有这样做,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才能正常地顺利地进行下去。参见《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2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