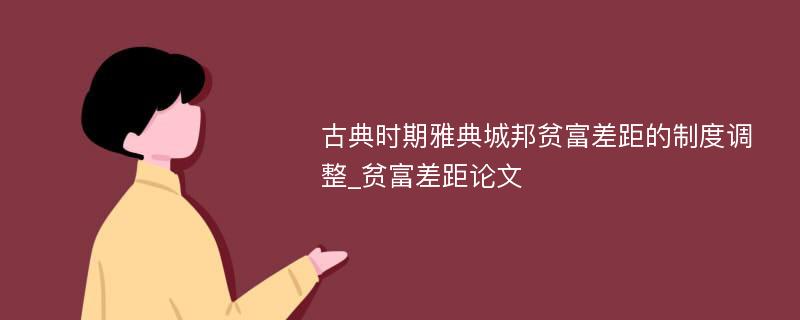
古典时期雅典城邦对贫富差距的制度调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典论文,城邦论文,贫富差距论文,时期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6)03-0014-06
贫富差距的存在是阶级社会的必然现象。贫富差距的增大,往往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危害国家长治久安。古典时期,雅典从一个蕞尔小邦,独步发展为整个希腊世界的强国,社会局面相对稳定,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究其原因,与其十分注重对社会成员贫富差距的制度调适不无关系。雅典城邦施行的解负令(disburdenment,seisatcheia)、公民兵制、公职津贴制、征收非常财产税(direct property tax,eisphora)和公益捐制(liturgies,leitourgia)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最富有阶层,扶持最贫困阶层,强化中等阶层的历史作用,从而缓解了因贫富差距增大而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保证了古典时期雅典城邦的社会稳定与繁荣。
穷人与富户:雅典公民的贫富差距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雅典城邦逐渐形成富有的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贫富差距逐渐凸显。古典时期,“富人”(α ενπορα,the rich)和“穷人”(α πενητεs,the poor)都是构成雅典城邦各阶层的重要部分①,但由于缺乏相关的人口、财产等详细的统计文献,穷人和富人只能是大致的划分,其标准也不尽一致。例如,关于有产阶层的划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二人的观点就不一样。前者主张:卫国之士的军人和军官,不应有财产,而农民则可各有其田亩。农民必须按时缴纳收获物的赋课,以供养卫国之士。后者之见则正好相反:土地应该属于公民,军政人员都是“有产阶层” (ενπορα)②。当然,有产阶层不一定就是富裕阶层。古希腊乡村的穷人可有一头耕牛,但非富裕阶层③。那么,如何判定古典时期雅典公民的贫穷和富足呢?也许,梭伦是具体标定雅典公民财产等级的第一人。
众所周知,梭伦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把公民按其土地的年收成分成四个等级,每个等级的财产标准分别是第一等级五百麦斗(medimnos),曰“五百斗者”(πεντακοσιομεδιμνονs,Pentakosiomedinmoi);第二等级三百麦斗,曰“骑士”(ιππαδα τελουνταs,Hippada Telountes);第三等级二百麦斗,曰“双牛者”(ξευγται,Zeugitai);最低等级的年收成在二百麦斗以下,曰“日佣”(θητεs, Thetes)④。可以推想,梭伦所给出的财产数额,都是每个等级的最基本收入,事实上,年收入高于五百麦斗或低于二百麦斗的公民一定存在。因此,以财产判定贫富的等级标准难以非常具体而恒定不变。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公民登籍的财产资格应订适当数额,但是,“要想制订一个适用于一切城邦的财产数额是不可能的。必须考察各邦的实际情况,然后分别定订一个最高数额,这个数额应该不多不少而符合于这样的原则:一邦大多数的人户都尽够合乎这一资格而可以取得政治权利,被这项资格所限制而摈弃于公民团体以外者则仅属少数。”⑤这就是说,城邦的贫富标准底线,必须是使大多数的公民按财产资格尽可以取得政治权利为准。公民应当是有产阶层。公民的贫富之别,则是指有产阶层中财产多寡之差,财产多者为富,反之为贫。所以,在希腊语中,“穷人”(οι πενητεs)也可称作“平民阶层”,可以拥有少量的财产。只是在乡村和城市,穷人的财产指向是不同的。如前所言,乡村的穷人可有一条耕牛作为其财产,并非一贫如洗。至于市区穷人的财产如何,因囿于资料,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城乡一致的:“极穷的人”(赤贫)是指完全没有资产的人⑥。如此看来,梭伦时代(640-561BC.)雅典富有公民的财产,想必是指年收入五百麦斗以上者,二百麦斗以上至五百麦斗者为中等阶层,二百麦斗以下者则为贫民。贫、富公民的年收入之差至少为三百麦斗,富者的年收入为穷者的1.5倍以上。
雅典富有公民的人数也是不断变化的。公元前480年左右,德米斯托克利将劳里昂矿开采所得的100塔兰特借给雅典最富有的100个公民,每人1塔兰特,令其建造三列桨战船⑦。据此推算,公元前5世纪左右,雅典最富有的公民约100人左右。如果以公元前5世纪雅典公民人口的总数为10万人计算⑧,富有公民数约占公民总人口的1‰。也就是说,在雅典城邦鼎盛发展的公元前5世纪时,富有公民所占的比例并不高。这可能与抑止富室的政策有关。受战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元前4世纪,雅典公民人数大约减至4万人,绝大部分公民的财产为2000德拉克马以下。财产价值达2000德拉克马以上的公民约9000人,占公民总人数的35%。其中,约300人为雅典最富有的公民,拥有财产价值均超过21000德拉克马。贫穷的公民(thetes)约5000人,占公民总人口的20%⑨。由此可见,这时雅典公民中的穷人和富人间的财产之差至少为1900德拉克马,富人的财产价值大约是穷人的10倍以上,贫富差距极大。而公元前4世纪,恰是雅典城邦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尽管雅典城邦衰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极富极贫差距的形成,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危机,加速了城邦公民集体的分离和瓦解⑩。
抑止富室:古典思想家的构想
对于贫富差距之变与城邦兴衰的关系,古典立法家、思想家等皆有洞察。年龄稍长于柏拉图的加尔基顿人法勒亚(Phaleas,Φαλεαs ο Χαλκηδονιοs,加尔基顿立法家)最先提出用节制财产的方法来消弭内乱的主张(11)。柏拉图(427-347BC.)、色诺芬(430-355BC.)、亚里士多德(384-322BC.)等人,一直将抑止富室,保障公民的整体利益,建立“良好”或“正义”的城邦,视为企求的社会理想。如柏拉图所言:“建立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特别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可能的幸福。”(12)为此,柏拉图建议:“任何公民增益他财产的初期是不必加以抑止的,等到他的增益已达最低业户产额的5倍左右时,须予以限制。”(13)色诺芬则十分重视和平环境与城邦繁荣的关系,认为:必须和平才能保持和增加收入,“如果没有和平的环境,城邦是不可能获得丰裕的收入。……那些享用和平环境最长久的城邦也是最幸福的城邦,而在一切的城邦中,雅典与生俱来最适宜在和平的环境中日趋繁荣。”(14)亚里士多德从历史的感悟中更为深刻地注意到调适贫富差距对邦国安危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15)贫富两方常相仇视,“两者每为一城邦内的正相反对的两个部分”(16)。“人间的争端以致酿成内乱常起因于贫富的不均,所以适当的节制财产是当务之急。”(17)“对贫富有所协调,或设法加强中产(中间)阶层,可以遏止由那个特别兴盛的不平衡部分发动变革的危机。”(18)“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19)“立法家应该慎重注意各政体所以保全和倾覆的种种原因,应该尽心创制一个足以持久的基础。应该对于一切破坏因素及早为之预防。”(20)“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而言,惟有以中产阶层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21)
诚然,防止极贫极富,扶持中等阶层,使富有的自由民和贫苦的自由民都不致各走极端,是古典思想家们的政治信条。因此,他们对“贫富有所协调”的理论构想,并非为了最终消灭穷人或富户,而是寻求社会力量的平衡。中等阶层即被视作这样一种平衡力量。亚里士多德本人也坦言:如果不兼容富户和穷人,不存在贫富两个阶层,那么,平民(贫民)主政的政体即平民政体和富人主政的政体即寡头政体也就“都不能存在或不能继续存在”。所以,实施平均财产的制度,企图消灭富户或排除平民群众的做法是“过激的法律”(22)。
需要指出的是,古典思想家在主张抑止富室,调适贫富差距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对富室的保全。“不仅他们(富室)的产业不应当被瓜分,还应保障他们从产业所获得的受益。”减少不必要的捐输,“阻止富室被强迫或处于自愿的无益于公众而十分豪奢的捐献,例如设置不必要的剧团、合唱队、火炬竞走以及类似的义务等。”(23)“豁免他们各种无补于实际的公益捐款”(24)。
如果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抑止富室的主张,更多的是一种理想,那么,雅典城邦的历史演进中究竟有无具体的调适贫富差距的立法和制度呢?
制度调适:防止极贫极富的实践
古典时期,雅典城邦所施行的解负令(disburdenment,seisatcheia)、公民兵制、公职津贴制、征收非常财产税(eisphora)和公益捐制(liturgies)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最富有阶层,扶持最贫困阶层,强化中等阶层的历史作用,从而缓解了因贫富差距增大而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保证了古典时期雅典城邦的社会稳定与繁荣。
解负令是梭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其推行其它法令的前提和基础。梭伦改革前夕,雅典的许多平民处境窘困,被称为“六一汉”(Hectemodoi)(25)和“贫民”(Thetes),也即是贫穷的农民。他们被迫以人身作抵押还债。有些在国内沦为奴隶,有些则被卖往国外。许多人被迫出卖自己的孩子(因为当时并无法律禁止这样做)或流浪他乡(26)。“贫民本身及其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了。”(27)雅典城邦贫富差距悬殊,阶级矛盾激化,平贵斗争异常,“以至于城邦在各方面都走到了革命的边缘,看起来结束这种混乱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僭主政治。”(28)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梭伦“采取最优良的立法,拯救了雅典国家”(29)。那么,梭伦立法的“优良性”何在呢?其实就是通过防止大富极贫或防止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来求得当时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稳固。兹以梭伦的诗歌为证:“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双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30);“我使这样的事情普遍流行,调整公理和强权,协和共处”;“如果我有时让敌对的两党之一得意,而有时又令另一党欢欣,这个城市就会有许多人遭受损失”;“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在他们的武装对垒群中,立起了一根分离两方的柱子。”(31)尽管解负令的详细内容学界尚未能完全确定,但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解负令取消了一切债务(32)。欠债为奴的贫民不仅因此获得了人身自由,而且收回了因债务而丧失的土地(33),有效遏止了富室财产的极度扩张。因此,解负令可谓是雅典历史上第一次以立法形式消除公民集体内部债务奴役的法令。解负令的施行,确立了雅典公民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巩固了雅典城邦的土地私有制,实现了公元前7-6世纪雅典公民贫富差距的基本平衡,使富有的贵族和一般的公民之间一度形成比较和谐的关系。以此为基础,加之梭伦所推行的其它奖励生产的立法,雅典独立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阶层逐步形成。
继梭伦之后的庇西特拉图,同样注意改善贫穷公民的经济地位。学者们认为,庇西特拉图进行了土地分配。他将被放逐的政敌之闲置土地分成小块,分配给最需要的人,使之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者只须交纳大约产品的1/10,甚至1/20的土地税,小农的经济负担大为减轻(34)。庇西特拉图还“拨款借贷给贫民,以供他们产业之需,使他们能够依靠农耕,以自赡养。”(35)
在此后雅典城邦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基于梭伦和庇西特拉图所推行的扶持贫穷公民的经济政策始终未变,抑止富室与扶持穷人之举,齐头并进。如雅典城邦通过向其依附城邦派驻公民的制度,使公民占有份地(tenant farmer,κληροιχια)。公元前504年,4000名雅典公民在卡尔息斯每人分得一块“马匹饲养者”(horse- breeder,ιπποβοται)的土地(36)。伯里克利曾派发1000名雅典公民定居凯尔索涅索斯(Chersonesus),1000名定居色雷斯,500名定居那克索斯(Naxos),250名定居安德罗斯(Andros)(37)。此后,雅典城邦又分别将其公民派居卡尔息斯、勒斯泊斯(Lesbos)、勒姆诺斯(Lemnos)、伊莫布罗斯(Imbros)和斯居罗斯(Scyros)。而移居他邦或在外邦分得土地的公民往往是贫穷的雅典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阿提卡没有土地(38)。
此外,雅典还通过征收非常财产税和公益捐制等经济手段,调适贫富差距。非常财产税“伊斯富纳” (eisphora)是在战争等非常时期向外邦人和公民征收的直接财产税(direct property tax)。公元前378-377年对非常财产税进行改革,固定税率向所有人(除了最贫穷的公民阶层以外)征收。如此征税时断时续的一直延续到希腊化时期。富有公民在平时和战争时期还需要向城邦自愿交纳另一种税“伊匹多斯”(epidosis),作为城邦的备用金。这是富有公民的职责。公元前4世纪后,“伊匹多斯”由先前的富有公民自愿交纳变为强制性的捐税(39)。
公益捐(liturgies/public burdens,leitourgia),是根据收入或资产向富有公民征收的不定额税(no regular tax)。可以捐献财产,也可以为公益活动牺牲时间等。一个人一生中可能有一到两次的公益捐义务。研究者认为,捐助制度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初(40)。公益捐项目众多,尤其是与各种节日相关的重大宗教活动以及戏剧比赛、合唱队和歌舞培训等的费用,都由富人以公益捐形式承担(41)。主要包括戏剧节合唱队的费用 (khoregi),战马的保养费(hippotrophia),节日联欢费 (arkhitheoria),三层桨战舰费(trirarchia)和公餐费(hestiasis)(42)。雅典执政官上任后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任命三个雅典最富有的人为悲剧合唱队队长(43)。对合唱队的资助在公元前502年已成为制度(44)。最早有关资助合唱队的记载是在公元前480年。戴维斯对雅典富有家庭的研究证明,德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西门等均在捐助者之列,他们都拥有较大规模的田产,捐助过戏剧比赛等公益活动(45)。例如,德米斯托克利曾资助公元前477年城市狄奥尼索斯戏剧节上演的、悲剧家佛里尼科斯(Phrynichos)的剧作《腓尼基妇女》,伯里克利曾资助公元前473年的城市狄奥尼索斯节上演的、悲剧家埃斯库卢斯的名剧《波斯人》。公益捐起初是荣誉性的和自愿的。公元前4世纪初起,公益捐变为强制性的义务。
为保证公益捐制的顺利实行,雅典还制订“交换法”(αντιδοδιs)。如果被指定捐助的富有公民不愿意提供捐助,并能提出没有被指定为捐助者的更为富有的公民,往往会诉诸法庭,双方分别将财产列出清单,呈交法庭。被告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承认自己比原告更为富有,并自愿承担原告的捐助;要么否认自己更为富有,并因此拒绝承担捐助。如果他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便可以免于捐助的负担(46)。因此,“交换法”使公益捐更为制度化。公益捐的实质则是富人财产的公益化——既调控富室财产,又使更多的公民从公益活动中直接受益。
在军事方面,雅典城邦实行的是公民兵制。“在古希腊,继君主政体之后发生的政体的早期形式中,公民团体实际上完全由战士组成。”(47)所有的公民都是保卫城邦及个人利益的战士。服军役既是公民的权力也是公民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城邦的武力,不论是骑兵 (cavalry)、重装步兵(heavy infantry)、轻装步兵(light infantry,包括弓箭手和狙击兵)和海军(marines),其武器装备等必须由公民自备。因此,有些装备花费较多的兵种,自然会落到富人的头上。如骑兵和重装步兵因乘骑和甲胄非贫民所能置办,全赖富室。古代的战马皆畜于富饶的著名家族(48),只有富室才有能力畜养战马和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49)。雅典的重装步兵基本以富裕公民为主体。一个重装步兵维持其地位所需要的财产价值约为2000德拉克马(50)。雅典三层桨司令官 (trierarch)也基本选自富有的公民。他们必须自己负责三层桨的军备,这是义务也是职责(51)。最早有关负担三层桨战舰费用的记载是在公元前480年。这一年,雅典舰队的180艘三层桨战舰参加了决定希波战争胜负的萨拉米海战。负担三层桨战舰费用的捐助者均是雅典的富有公民,一般拥有较大规模的田产(52)。贫穷公民只能充任轻装步兵中的弓箭手、桡手和狙击手等(53)。因此,在公民兵制下,城邦的富有公民,意味着更多的军事义务和军役负担。
为尽可能减少因贫富差距而造成的公民在参与政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不平等,雅典城邦主要依靠公职津贴、出席津贴和观剧津贴等进行调适。
约自伯里克利时代(Periclean Age,440s-430s BC.)开始,雅典实行公职给薪制。一开始,出席公民大会者每次给薪1个奥波尔,至公元前327年,每次给薪 6个奥波尔,参加重要会议者(主要议程为对那些认为办事好的在职长官进行投票表决,并讨论粮食供应和国防问题)每次给薪9个奥波尔。公元前5世纪,出席会议者常达5000多人。陪审员每日2奥波尔(约等于一人一天的生活费,公元前425年左右,增至每天3奥波尔);九执政官每日4奥波尔,并备有一个传令官和一个吹笛者;议事会议员每日5奥波尔,担任主席者,另加1奥波尔(54)。人民出席民众会常会,领取1德拉克马(55)。萨拉密斯执政官则一天得1德拉克马。竞技裁判官在阿提卡的第一月即7-8月中,自泛雅典娜节日所在月份的第4日以后,在普律塔涅嗡就餐。驻提洛的近邻同盟代表人每天由提洛得1德拉克马。所有派往萨摩斯、斯居罗斯、勒姆诺斯、或伊莫布罗斯的官吏也领款以为膳费(56)。对于雅典的公职津贴制,芬利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没有哪一个希腊城邦象雅典这样,带薪的公职是如此之多。”(57)
雅典观剧津贴始于伯里克利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观剧津贴一度取消,旋又恢复。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记述: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民主政治渐趋混乱,粗悍之辈争相取媚群众,以自植势力。克里奥丰 (Cleophon)为平民派领袖,始立观剧津贴,凡公民入场观剧,可得2奥波尔;数年后,加里克拉底(Callicrates)又增加为3奥波尔。后来,二人都因浪费公帑被处以死刑(58)。
公职津贴、出席津贴和观剧津贴,赋予公民实实在在的政治与文化生活权利。如果没有这些津贴,许多乡居的公民,尤其是贫穷的公民,城邦所提供的诸多参政议政机会及丰富多彩的戏剧艺术等文化生活,也终究是形式而已。因为机会多多,并不等于公民实际所享有的权利和实惠多多。对于散居阿提卡各村落的远郊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为按时与会而不顾农事或手艺,实属不易。过多的时间消耗以及经济上的压力,往往会使下层民众力不从心,很难热心城邦政事。有些无薪的公职更使一般平民不敢问津。“除非有薪,否则,许多公民将被排除在民主政治之外,因为他们无法承受时光流逝而日无所获。”(59)即便是在任的议事会议员也常常因私事耽搁而不能出席每天的例会。所以,即使城邦推行了津贴制,在雅典政坛,“富人于议事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60)。公元前336年的一份议员名单显示,所记录的248名议员中,绝大多数为三列桨船长或其家庭成员(61)。至于出席公民大会的情况,格劳茨认为,公民大会的人数从来没有多于应参加的人数。在Pnyx的公民几乎没有多于2000或3000人,这些人中的多数是城居的市民(townsmen)(62)。亚里士多德也承认:手艺人(artisans),店主(shopkeeper)和雇佣者(hirelings),几乎成为单一的有选举权的人(constituent)。由于这些人经常交易和驻守(the exchange and the citadel)城市,“他们容易地参加公众大会(public assembly)”(63)。至此,也就不难理解掌控雅典商业的异邦人,因其长期居于城市而比其他临时来城里的人拥有更多的“特权”(64)。这也许是古代雅典城邦永远都无法调适的城乡差距。
小结
财产私有制是阶级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往往会导致个人财富的不断增长和社会成员贫富两极分化。抑止富室与扶持贫民是雅典城邦调适贫富差距的联动措施。其目的主要在于追求社会的平等、公正与和谐发展。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最为公正的政体,应该不偏于少数,不偏于多数,而以全邦公民利益为依归。”平等的公正,就是要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65)。“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自当注意到勿使一邦的群众陷入赤贫的困境。”(66)古典时期的雅典城邦正是依靠立法和制度来调适贫富差距,防止极贫极富,从而有效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实现政治民主,文化繁荣,形成古典盛世的历史局面。
从另一角度看,调适贫富差距,也是对雅典城邦乡村区域的重视,因为雅典城邦的“穷人”绝大多数是乡居的农民。农民和乡村是构成城邦整体的必要部分和基础。因此,雅典城邦对贫富差距的制度调适说明,对城邦的历史考察,不可只重视城市的地位和作用,阿提卡的乡村同样有着许多未知领域值得去探究和发现。西方古典盛世的历史遗产,对于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Aristotle,Politics,Ⅶ.Ⅷ.1328b10,22.The Loeb Classicsl Libra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文中引用古典文献未注明出处者,皆据劳易伯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希腊文和英文对照本。下同。
②Plato,The Republic,Ⅳ.419-421; Ⅲ.464C; Aris totle,Politics,Ⅱ.Ⅴ.1264a32.
③Aristotle,Politics,Ⅰ.Ⅱ.1252b12.
④Plutarch,Solon,Ⅹ Ⅷ.2; 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Ⅶ.3-4.
⑤Aristotle,Politics,Ⅳ.Ⅹ Ⅲ.1279b1-5.
⑥Aristotle,Politics,Ⅰ.Ⅱ.1252b12; Ⅵ .Ⅴ.1320b32; Ⅲ.Ⅷ.1279b9; Ⅱ.Ⅹ.1271a30.
⑦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Ⅹ Ⅹ Ⅱ.7; Plutarch, Themistocles,Ⅳ.2.
⑧N.G.L.Hammond and H.H.Scullard,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second edition,1987,P862.
⑨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154-156页。
⑩M.M.Austin and P.Vidal-Naquet,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An Introduction,English text,translated and revised by M.M.Austin,Berkeley,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P151 -152.
(11)Aristotle,Politics,Ⅱ.Ⅵ.1266a38-40.
(12)Plato,The Republic,Ⅳ.419C.
(13)Plato,Laws,Ⅴ.744E.法勒亚和柏拉图都主张限制财产过多,但他们所指的财产并不一样。法勒亚所主张平均分配的财产,专指土地,而柏拉图所容许增益的财产则包括对各家的一切财物和收益。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9页注释③。
(14)Xenophon,Ways and Means,Ⅴ.1-4.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5)Aristotle,Politics Ⅳ.Ⅹ Ⅰ.1295b,1-5.
(16)Aristotle,Politics,Ⅳ.Ⅳ.1291b9.
(17)Aristotle,Politics,Ⅱ.Ⅶ.1266a36-37.
(18)Aristotle,Politics,Ⅴ.Ⅷ.1308b28-30.
(19)Aristotle,Politics,Ⅳ.Ⅹ Ⅰ.1295b,40.
(20)Aristotle,Politics,Ⅵ.Ⅴ.1319b35-1320a1.
(21)Aristotle,Politics,Ⅵ.Ⅹ Ⅰ.1295b28-30.
(22)Aristotle,Politics,Ⅴ.Ⅸ.1309a38-1310a2.
(23)Aristotle,Politics,Ⅴ.Ⅷ.1309a15-20..
(24)Aristotle,Politics,Ⅵ.Ⅴ.1320b5.
(25)“六一汉”,Hectemori,εκτημοριοι,学者多主张为交租六分之五,自余六分之一的佃户。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对“穷人”的表述有所不同。前者把所有的穷人都看成是“六一汉”和“附庸”(πενητεs),而普鲁塔克则把穷人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人为富人耕作,被迫交纳六分之一的收成,因而被称作“六一汉”和“贫民”(θητεs);另一部分人则陷入债务,因而失去自由,他们或在国内沦为奴隶,或被卖到国外。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Ⅱ,2; Plutarch,Solon,Ⅹ Ⅲ.3-4;同时参见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
(26)Plutarch,Solon,Ⅹ Ⅲ.3.
(27)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Ⅱ,2.
(28)Plutarch,Solon,Ⅹ Ⅲ.4.
(29)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Ⅹ Ⅰ.7.
(30)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Ⅶ.1.
(31)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Ⅶ.4.
(32)Plutarch,Solon,Ⅹ Ⅴ.5.
(33)J.B,Bury,Russell Meiggs,The History of Greece, 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8,P123.
(34)布瑞认为,1/10的财产税可能非庇西特拉图首创。这个古制可能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因为土地得以充分耕耘而又继续施行。后来,尽管因劳里昂矿发掘等,收入有所增加,但税额反而降为1/ 20。J.B,Bury,Russell Meiggs,the History of Greece, 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8,P129; 1/20的税额参见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Ⅵ.LⅣ.5.
(35)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Ⅹ Ⅵ.4.
(36)Herodotus,The Persian Wars,Ⅴ,77.
(37)Plutarch,Pericles,Ⅹ Ⅰ.5.
(38)详见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第124页。
(39)Lesley Adkins and Roy A.Adkins,Handboolk to life in ancient Greece,New york:Facts on File,Inc.,P188.
(40)J.K.Davies,Weath and the Power of Weath in Classical Athens,Salem:the Ayer Company,1981.P25.转引自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第126页。
(41)J.B,Bury,Russell Meiggs,the History of Greece,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8,P217.
(42)Lesley Adkins and Roy A.Adkins,Handboolk to life in ancient Greece,New York:Facts on File,Inc.,P188.
(43)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L Ⅵ.3.
(44)J.K.Davies,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600- 300B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25.转引自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第126页。
(45)J.K.Davies,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600- 300B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7826Ⅲ; 6669,8429.转引自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第127-128页。
(46)交换法可能由梭伦订立。参见Demosthenes,Private Orations,Ⅴ.Ⅹ L Ⅱ:An Unknown Pleader against Phaenippus in the Matter of an Exchange of Properties. 1.
(47)Aristotle,Politics,Ⅳ.Ⅹ Ⅲ.1279b15; Ⅳ.Ⅱ.1289b36; Ⅵ.Ⅶ.1321a8.
(48)Aristotle,Politics,Ⅵ.Ⅲ.1289b36.
(49)Aristotle,Politics,Ⅴ.Ⅳ.1304a28; 1321a5.
(50)参见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5页表一。
(51)J.B,Bury,Russell Meiggs,The history of Greece,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8,P217.
(52)Herodotus,The Persian Wars,Ⅷ.44; J.K.Davies,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600-300B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25.转引自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第127页。
(53)Aristotle,Politics,Ⅶ.Ⅵ.1327b8-12.
(54)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LⅦ,2.
(55)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Ⅹ LⅢ.4.
(56)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L Ⅹ Ⅱ.2.
(57)M.I.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P58.
(58)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Ⅹ Ⅹ Ⅷ.3;同时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3页注释②。
(59)John Salmon: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Greek City,见 Greece and Rome,Vol.Ⅹ L Ⅵ,No.2,October 1999. P151.
(60)J.A.O.Larsen: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5,P11.
(61)P.J.Rhodes:Athenian Bolue,P5-6.
(62)参见G.Glotz:The Greek City and its Institutions,P153 -154.
(63)参见G.Glotz:The Greek City and its Institutions,P154.
(64)Geoge Willis Botsford; Charles Alexander Robinson,JR.: Hellenic History,forth edition,P158.
(65)Aristotle,Politics,Ⅲ.Ⅹ Ⅲ.1283b35-40.
(66)Aristotle,Politics,Ⅵ.Ⅴ.1320a2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