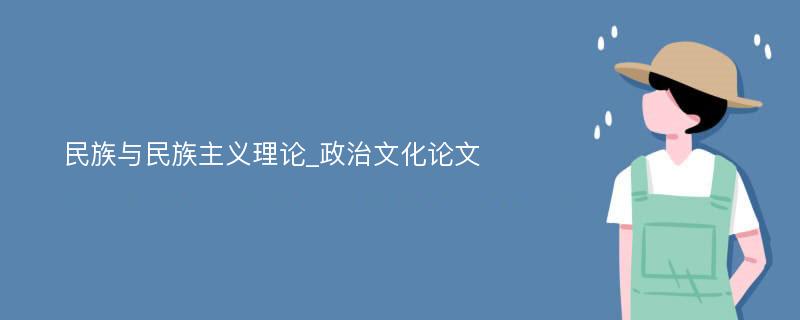
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主义是当前突出的国际政治现象之一。1989年东欧剧变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力地证明,我们正处在国际关系的新时期。从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到南斯拉夫的内战;从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斯里兰卡的战火,到魁北克试图脱离加拿大的全民公决;从欧盟内部的疯牛病问题、美国和欧洲的农产品之争,到举世谴责的美国赫尔姆斯-伯顿法;从西欧根深蒂固的排外主义势力、印度的寺庙之争,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总之,冷战后的世界并不像西方国家早先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人类和平、和谐的世界;更不是福山先生(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匆忙告诉人们的:“我们不仅看到了冷战,或是战后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结束,而且我们还在见证历史的终结,那就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束,以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世化,从而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注: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1989,p.4.)相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国家政治力量的扩张、民族经济利益的矛盾、各国间宗教和文化的相互渗透与抑制。难怪有人说,民族主义“这个在两极霸权时代一度被认为是已经或趋于消失的现象,现在不仅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而且显然已成为国际政治画屏的最重大的焦点之一”。(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然而,在诸多讨论民族主义之具体表现的文章中,却有不少关于民族主义概念本身的似是而非的定义。本文不打算加入针对冷战后民族主义之具体表现的讨论行列,而是想从理论上对我们正在讨论的民族主义概念本身作一梳理,并试图阐明,民族是有高度政治性的,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产物;民族主义不仅存在于单一民族国家中,而且存在于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主义与民族的概念一样,也有着不同的层次之分,但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都可以被认为是以政治性较强的“民族”这一概念为中心的一套思想、理念、纲领和行动。
一、英文nation(民族)的由来
毫无疑问,讨论民族主义,离不开对民族概念的理论争论。民族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人们共同体形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归属。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是自有民族以来在世界历史上为人们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它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什么是民族,如何给民族下一个科学的、较全面的定义,却是困难的。古今中外的学者和政治家们从他们生活的年代和所从事的学科性质、政策应用等不同角度和目的出发,分别给民族下了许多不同的定义,其中当数斯大林的定义在政界和学术界影响最大。1913年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94页。)这一著名定义于1929年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中又被加以重申。(注:《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86~305页。该文是斯大林于1929年3月18日为答复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等人而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在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直到1949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斯大林全集》第11卷时,才第一次刊登出来。(参见杨堃:《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24页)我国的辞书至今仍然沿用这一定义。围绕此定义,同时也围绕着关于民族的其他定义,主要在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争论。这些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学科、不同立场之间的交锋;反映了人们对于近、现代民族形成问题的不同理解。这是我们在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时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
尽管早在西方的民族概念传到中国之前,就有众多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中华大地上,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这一概念实实在在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民”和“族”均有所阐述。(注:如以“民”泛指被统治的人(《诗·大雅·假乐》:“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以“族”泛指危难与共、同抗外患的一群人(《说文》:“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从族,从矢”);或泛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左传》曾提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我族也”)。(参见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有时这两个字同时出现在同一句话中,如《左传·僖公十年》中的“民不祀非族”;《礼记·坊记》中的“民犹淫佚而乱于族”等。但在西方的民族概念传入中国之前汉语中从未将这两个字并列在一起,以表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注:虽然汉人郑玄在注释先秦典籍《礼记·祭法》时就曾将“民”、“族”二字并列用在一起(“大夫以下,谓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但这里的“民族”二字还不是一个名词。(参见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2页)据考证,汉语中的“民族”一词是从日文中借用过来的。1899年,梁启超在他的《东籍月旦》一文中最早使用“民族”一词。在这篇文章中,出现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和“民族竞争”等新名词。(参见金天明、王庆仁:《“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转引自《中央民族学院研究论丛》编委会编:《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文选(1951~1983)》,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63~64页。)因此我们在讨论民族定义、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时,不能不首先弄清英文nation(民族)一词的内涵。
英文nation一词最初是从拉丁字nasci的过去分词演化而来的,意为出生物(to be born)。后又进一步衍生为natio,(注:参见WalkerConnor,A nation is a nation,is astate,is an ethnicgroup,is a...,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1,No.4,October 1978,p.381;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199页。)指具有同一出生地的居民团体,亦即拥有某一特定地理区域的人类集团。(注:参见Mostafa Rejai,Political Ideologies,A Comparative Ap-proach,Londen,M.E.Sharpe,Armonk,1995,p.24。)中世纪初期,natiovillae被用来表示村里的亲属集团。如牛津的贵族们在1258年用natio regni Angliae表示英格兰王国的亲属集团,以反对亨利三世的外国追随者。也有人认为,大约在1400年时,natio就有了“领土”的含义。(注:参见Philip L.White,What Is a Nationality?CanadianReview of Studies in Nationalism,XII,1,1985,p.7。)在1500年到法国大革命这段时间,natio开始以nation(nacion,nazione)的面目出现在当地的语言中,且具有了政治的含义。(注:如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荷兰人雨果·格劳秀斯在他所著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的英文版中,就多处将Nations和Rulers或Kings并列使用,而这部书的1738年伦敦英文版标题更是明确写成:"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in ThreeBooks wherein Are Explained the Law of Nature and Nations and thePrinciplal Points Relating to Government"。(参见Philip L.White,WhatIs a Nationality?Canadian Review of Studies in Nationalism,XII,1,1985,pp.7-8)16和17世纪,nation一词便开始被用来描述一国之内的人民而不管其种族特征如何。波兰被瓜分和法国大革命时,nation开始成为country(国家)的同义语,(注:参见Louis L.Snyder,The Meaning of Nationalism,op.cit.p.29。)并且开始具有与“人民”(people或peuple)相对立的意义。(注:在当时的词汇中,peuple常含有贬损的意思,这才有了用nation取代peuple的“时髦”说法。(参见Guido Z-ernatto,Nation:The History of a Word,TheReview of Politics,op.cit.pp.364-366)总的来说,nation“意味着全部的政治组织或国家(state)”。(注:Hans Kohn,The Idea of Nationalism,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6.p.580.)法国大革命后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就明确宣布:“所有主权的来源,本质上属于国家(nation)。”(注:Walker Connor,A n-ation is a nation,is a state,is an ethnic group,is a...,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1,No.4,October 1978,p.382.)此后出版的词典也开始采纳nation早先已经具备的政治含义:“民族意味着流着相同的血液、出生在相同的国家,而且生活在同一个政府之下的众多家庭。”(注:Philip L.White,What Is a Nationality?Canadian Reviewof Studies in Nationalism,XII,1,1985,p.8.)而这个nation实际上是指某个社会群体,“集体”或“国家”的概念在这个nation中显然占有主要的地位。因此马克斯·韦伯说:“在明显的、模棱两可的‘民族’一词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它清晰地植根于政治领域。”“人们可以通过下列途径来界定‘民族’这一概念,即:民族是一个可以用它自己的方式充分显示它自己的感情共同体;而且一个民族是通常趋向于产生它自己的国家的共同体。”(注:Max Weber,The Nation,in FromMax Weber:Essays,in Sociology,trans.and ed.by H.H.Gerth and C.Wright-Mill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48,p.179.)美国著名学者卡尔·多伊奇说得更明白:“一个民族(nation)就是一个拥有国家的人民(people)。”(注:Peter Alter,Nationalism,London,EdwardArnold,1994,p.6.原文为"A nation is a people in possession of astate"。)
这就是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到的nation(民族)一词的来源。它有助于我们认清nation一词最终演化成了一个与国家相关的名词,以至在后来的很多场合下,它都被明确地用来表示“国家”,如联合国及其前身——国际联盟中的“国”,在英文中用的就是nation一词。明确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它清楚地告诉我们,nation(民族)是有高度政治性的。(注:阎学通博士也认为“nation是全民性的政治概念”。(参见其近著《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页))
民族之所以与政治或国家、政治组织有关,是有它的现实政治背景的。我们已经从“民族”一词的发展演变过程看到,“民族”经过数世纪的演化,到法国大革命时最终成为有关政治的词汇。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工具和斗争武器,民族主义对建立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维护资产阶级的民族利益、打倒封建王权、推翻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民族主义促进并巩固了民族国家的观念。民族、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民主等口号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而这些口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要求个人自己管理自己,本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在这中间,民族与民主和公民个人的关系相当密切,是由当时欧洲的政治现实决定的。因此,斯大林明确指出:“民族不是普遍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00页。)“世界上有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资产阶级民族,例如法兰西、英吉利、北美利坚及其他类似的民族”。(注:《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88页。)明确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所谓民族主义的中心概念——民族,正是指现代民族这种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民族。
二、关于民族的不同层次问题
理清nation的来源有助于我们严格区分nation和其他表示部分“民族”含义的英文单词翻译成中文后显示不出来的差别,因为nation不同于ethnic group,(注:ethnic group,暂时还没有适当的和公认的中文译名,本文暂且称它为“族体”。在本世纪30年代前,ethnic,ethn-icity等词的出现频率还不高。只是从那时候起,ethnic group才被广泛地用于特指一个依靠种族、民族的根源或文化凝聚在一起的集团,而这个集团相对于在社会上占主体地位的集团来说,又保持着它在社会中所占的少数地位的特性(参见Philip L.White,What Is a Nationality?Canadian Review of Studies in Nationalism,XII,1,1985,pp.14-15)。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解释说,作为形容词,ethnic有如下含义:(1)种族的,种族上的,人种学的;(2)异教徒的,非基督徒的;(3)源自(或属于)某民族(或国家)文化传统的,原始种族的,等等。可见,在ethnic group中有中文的“种族”的因素,但它所表达的主要是由于人们在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人类集团,这种集团当然不能说是nation(民族)。在美国,学者们常用ethnic group来称谓某些属性易引起争议的共同体,如美国的黑人、加拿大的魁北克人、前南斯拉夫境内的穆斯林、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等,而这些人显然都不能称为nation(民族),但又都有某些民族特征。这是令中文苦恼的地方,因为找不出合适的词与英文中的不同民族或族体一一对应。这也使我们在讨论民族(nation,ethnic group,people,race,tribe,等等)问题时,又增添了一个新问题。(参见下文的讨论))nation所指范围更大,更具有政治意义;ethnic group则是指次于nation的族体,如我国的汉族、回族、藏族等都是ethnic group,而“中华民族”则是nation。(注:费孝通先生提出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来表述我国族际关系的现状。1988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Tanner讲演时指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在这里,费先生所说的民族单位就是本文所说的ethnic group,而中华民族就是nation。在另一篇文章中,费先生谈到了中文“民族”一词和英文“民族”一词的区别。他说:“我们所用‘民族’一词历来不仅适用于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集团,而且适用
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集团。这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名词。这一点和欧洲各国的传统是不同的。在欧洲各国,‘民族’这个概念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是欧洲近代史的特点……由于我国和欧洲各国历史不同,民族一词的传统涵义也有区别。”〔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一九七八年九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的发言)》,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斯大林说:“现今的意大利民族(nation)是由罗马人、日耳曼人、伊特剌斯坎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等组成的。”(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1页。)这句话中的“××人”就是ethnic group,而不是nation。之所以产生这种问题,是由于英文和中文(其他语言也一样)之间存在一个翻译的问题。英文中有不少词可以表示中文里的“民族”,比如:nation,nationality,people,tribe,ethnic,group,race,等等。而中文里与之相对应的只有“民族”一词,显然它不能表达那么多英文单词的含义。(注:参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89~90页。因此,除非特别说明,下文中的“民族”一词均指英文中的nation。)两种语言间的不一致由于翻译时受到词汇的局限而导致一些英文同义词在中文里被错误地相互借用。如梁启超最初使用“民族”一词时,就将“民族”与“种族”概念相混淆。他于1903年发表的《新民说》在概述地球上所存在的“种族”时说,“民族”包括“一、黑色民族,二、红色民族,三、棕色民族,四、黄色民族,五、白色民族……”。章太炎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在1903年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把种族和民族看作是同一个概念的两个不同的名词。他写道:“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注:金天明、王庆仁:《“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第66页。)因此本来就很复杂的西方的民族概念传到我国后,又增添了一层麻烦。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能是还英文nation以本来面目,用nation对应中文的“民族”一词,而用e-thnic group等词对应中文的其他相关概念。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一个明显的优点就在于它将“民族”与“种族”作出了严格的区分,排除了以往只用某个单一的标准来界定民族的做法,从而使得“民族”的概念更加清晰可辨。
与上述概念有关的还有“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注:参见王缉思:《民族和民族主义》,载《欧洲》,1993年第5期。在这篇文章中,王缉思先生认为是美国学者Karl Deustch将民族划分为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的。但Peter Alter认为,将民族区分为cultural nation(文化民族,德文为Kulturnation)和political nation(政治民族,德文为 Staatsnation),应归功于德国历史学家Friedrich Meinecke。(Peter Alter,Nationalism,London,Edward Arnold,1994,p.8.))所谓“政治民族”实际上就是指本文所讨论的nation;而“文化民族”实际上是指本文提到的ethnic group。明确区分“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或明确区分nation和ethnic group,对深入开展国际问题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是民族国家,所以我们除了要研究国家关系以外,还应该研究一个国家内部的族体关系。国家内部的族体关系的演变,正是民族和国家发生变化的原因。正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层次之分,所以民族主义也有不同的层次之分,既有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也有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
三、在“民族”定义争论的背后
从英文nation一词的发展、演化来看,“民族”(nation)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生物学、人种学到社会学、政治学演变的历史过程。随着nation(民族)概念本身的不断演变,人们的看法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人们总在试图发现生活中的民族到底是怎样的,于是在衡量、判断什么是民族时,便有了众多不同的见解。当人们具体考察“民族”的内涵时,出于不同的目的、角度甚或偏见,便有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和纷繁复杂的解释。例如,地理学家认为自然环境对民族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意义;历史学家则把民族看作是生活在特定领土内的、在共同的历史中因共同的愿望而拥有共同的思想和感情的、主权政治国家的全体居民;政治学家认为民族是一类人的正式组织;哲学家认为民族是文化与共同的历史、语言、文学、传统、英雄和忠诚的统一体;社会学家则把民族看成是最大的和最重要的人类集合体之一,他们强调,构成民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是一致的或同一的感情;心理学家把对民族的观察点定在个体的行为上,以寻找所谓的民族心理特征;精神病学家则把民族描绘成个人直接显示他的忠诚的最大社会聚合体,以及超我的外在的代表。(注:参见Louis L.Snyder,The Meaning of National sm,NewRrun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4,pp.14-55。)总之,有人强调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对民族形成的作用;有人用传统、语言、宗教来界定民族;有人用所谓感情、一致性等来区别不同的人类集合体;也有人从国家、政治组织等角度来给民族下定义;还有的学科更看重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试图从中指出什么是民族形成的主要因素。面对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关于民族的定义,王缉思教授采取了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来区分的办法。他认为:“尽管民族的定义千差万别,但归纳起来不外是从社会群体的主观归属感和划分群体的客观标准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区别民族与非民族。”(注:王缉思:《民族和民族主义》。在他看来,主观派的代表人物有法国人厄内斯特·勒南(ErnestRenan,1823-1892年)及英国人休·塞顿-沃特森(HughSeton-Watson)。勒南的观点是:“一个民族是一个灵魂,一种精神原则。”“共同受苦,共同欢乐和共同希望,这些就是构成民族的东西。”(参见Ernest Re-nan:What Is a Nation?in John Hutchinson & Anthony D.Smith ed.,Nation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7-18)。休·塞顿-沃特森的观点是:“当一个共同体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构成一个民族,或他们的行为如同他们自己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时,该民族就诞生了。”(参见Hugh Seton-Watson,Nations and States,an Enq-uiry into Originsof N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L-ondon,Methuen & Co.Ltd.,1977,p.5)而客观派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人朱塞普·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年),虽然马志尼也注意精神的基础,但其断言:“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规定了意大利民族的界限。凡是说意大利语的地方,就是意大利人民的家园。”(参见〔美〕爱·麦·伯恩斯著、曾炳钧译、柴经如校:《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26页)此外,斯大林的著名定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代表了客观派的看法。)用归属感和客观标准来区分民族与非民族,其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可以简单明了地将形形色色的民族定义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在民族构成问题上的争论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有人要以主观标准来确定民族,而有些人要以客观因素来判断一个社会群体是否为一个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以客观标准来界定民族,是想强调既有的社会群体的合法性基础;而以主观标准来衡量民族,则是想通过这个标准来加强某个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客观派的观点还在于,在确认自身的民族身份的同时,否认其他特定群体的民族身份;而主观派的观点则赋予了想建立“民族”的社会群体(或未被公众承认为民族的群体)以更大的活动空间,以便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树立起这个社会群体内部的认同感。争论的背后恐怕都有一个利益的因素在起作用。主、客观两派的争论大多发生在19和20世纪。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某个社会群体是否被承认为“民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当时,某个社会群体是否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首先必须被承认为一个“民族”;因为依据对民族自决权(注:所谓民族自决权,最初源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人的权利”说,是他最早提出自决(self-determination)一词。〔参见Elie Kedourie,Nationalism,London,Hutchinson & Co.(Publi-shers)Ltd.,1961,pp.20-31.〕在当时,自决原则适应了欧洲的政治现实。伴随着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自决成为当时民族主义运动的最高要求,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随着欧洲的向外扩张而传播到全世界。本世纪民族自决的浪潮几度兴起,自决原则也在1945年被写进《联合国宪章》,逐渐从一项政治原则演变为一项国际法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和列
宁等革命领袖都对民族自决的原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支持,并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民族自决权原则。他们的相关论述是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民族自决权,以及观察、分析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有关民族自决的论述除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外,还可参考下列文献:梁守德:《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自决权原则》,载《民族研究》,1980年第6期;庞森:《关于民族自决权的一些思考》,载《国际问题研究》,1997年第2期;任东来:《自决原则在历史上的实践及其含义的演变》,载《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3期;〔日〕长江守男:《民族问题与自决》,载《现代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11期;Alfred Cobban,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7;Benyamin Neuberger,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Dilemmas of a Concept,Nations and National-ism,1(3),1995,pp.297-325;Omar Dahbour,Self-determination in P-hilosophy and International Law,History ofEuropean Idea,Vol.16,No.4-6,pp.879-884;Yael Tamir,The Right to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Social Research,Vol.58,No.3,1991,pp.565-590。)的字面解释,各个民族有权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这样建立起来的国家更具有合法性,所以当初围绕民族概念的争论并不仅仅反映了学术界面临的困境,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是概念的提出者出于服务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所有有关民族定义的争论都是在所争论的人类共同体本身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出现的。(注:例如,厄内斯特·勒南最早提出“什么是民族”时,时间已是1882年。显然,我们所讨论的现代民族早在此前一百多年就已经存在了。)可以说,无论是以主观因素来划定民族,还是用客观标准来界定民族,都是为了试图有利于下定义者心中所要建立或维护的国家,都是出于定义者要维护他本人所属的那个民族的利益。比如主观派的代表人物——法国人勒南以高度理想化的形式构成他的民族概念,在他的民族定义中没有任何经济的、地理的因素,有的只是所谓的“灵魂、精神原则”、“丰富的传统”、“尽量发挥共同传统的愿望”,等等。(注:参见Ernest Renan,What Is a Nation?见John Hutchinson & Anthony D.Smith ed.Nation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7-18。)在这样的民族定义下,讲德语的阿尔萨斯人由于主观的归属感而成了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注:参见Peter Alter,Nationalism,London,Edward Arnold,1994,p.10。)再如客观派的代表人物——意大利人马志尼,他用客观的地理(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语言(意大利语)等因素来强调民族的构成,其目的也在于将科西嘉、撒丁尼亚和西西里划入意大利的版图。(注:参见〔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425~427页。)因此,针对斯大林的著名定义,属于主观派的休·塞顿-沃特森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斯大林并不是从社会政治分析的角度来论述民族问题,而是一场政治论战,目的在于否定犹太人是一个民族……(注:参见Hugh Seton-Watson,Nations and States,An Enquiry into Originsof N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London,Methuen & Co.Ltd.,1977,p.4。)从这些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民族定义争论的背后所反映出的社会、政治问题。因此,真正客观、公允地给民族下定义是不可能的。有关民族定义的争论实质上与民族主义的内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把握民族及民族主义的真实含义,从而在认识相对一致的基础上讨论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
总之,民族主义就是以上述具有高度政治性的nation为中心的主义。讨论民族主义,必须以对民族(nation)的认识与理解为基础。因为nat-ion形成于近代,所以民族主义也是一种近代的历史现象。它产生于近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经过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互影响与作用,在已有的民族感情的基础上,强烈地显示出对整个民族及其国家的热爱与忠诚。这是本文立论的基础。离开了民族(nation)这一中心,民族主义无从谈起。因此在学术界,“伊斯兰教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都被看作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注:参见张建华、李凤飞:《作为一种世界性潮流的民族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1期。)
四、民族主义的含义
如同“民族”没有一个公认的、普遍适用的定义一样,关于“民族主义”也存在着概念上的争论。这不仅是因为下定义者的立场、观点和角度不同,而且是因为民族主义有着一个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正如久负盛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汉斯·科恩所言:“民族主义在所有国家和整个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且取决于它所植根的不同地区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结构。”(注:Hans Khon,Nationalism,Its Meaning and History,'preface',Priceton,New Jersey,D.Van Nost-rand Company,Inc.,1955。)正因为如此,人们对“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个在1774年就开始出现在德国哲学家赫德尔的著作中、(注:参见Peter Alter,Nationalism,London,Edward Arnold,1994,p.3。但也有人认为,nation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409年的莱比锡大学。(参见A-nthony D.Smith,Nationalism,A Trend Report and Bibliography,Cu-rrent Sociology,Volume XII,(1973),No.3,p.21;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5页)还有人认为,nationalism一词最早在1836年被界定为“民族感情”的一种形式。(参见G.de Bertier de Sauvigny,Liberalism,Nationalism,Socilism:The Birth of ThreeWords,Reviewof Politics,Vol.32,April,1970,pp.147-166)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被普遍使用的词,至今仍然争论不休。很多学者得出结论:给民族主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注:参见Louis L.Snyder,The Meaning of Nationalism,Part II,New Brun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Press,1954。给民族主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之所以比较难,还在于民族主义和民族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还是有很多人对此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他们努力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民族主义的真正内涵。尽管70多年前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卡尔顿·海斯曾经断言“对爱国主义、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属性和历史的完整且系统的研究,在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注:Carlton J.H.Hayes,Essays on Nationalism,NewYork,TheMacmillan Company,1928,p.2.)但今天我们欣慰地看到,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研究汗牛充栋,而对民族主义含义的理解更是众说纷纭。
其一,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在他于30年代主编的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或一个民族内部的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注:The Royal 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 Affairs,Nationalism,A Report by A Study Groupof Members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Lo-ndon,Frank Cass and Co.Ltd.,1963,p.xviii.)汉斯·科恩则给民族主义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他在有名的《民族主义的观念》一书中指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应被认为是一种思想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体现了个人对民族国家的高度的忠诚。”(注:Hans Khon,The I-dea of Nationalism:A Study of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6,pp.10-11.)后来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与科恩的观点相似,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状态,每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至高无上的世俗的忠诚”。(注: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15th edition,1993,Vol.8,p.522;Vol.27,p.419.)
其二,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学说或原则。埃力·凯多力认为:“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在欧洲被发明的一种学说”;“简单地讲,这种学说坚持认为人类被自然地划分为民族,而这些民族又通过特定的可确认的特征为人们所熟知,而且政府唯一的合法形态是民族自我统治的政府。”(注:Elie Kedourie,Nationalism,London,Hutchinson & Co.(Publi-shers)Ltd.,1960,p.9.)厄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原则,它坚持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注: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England,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1983,p.1.)
其三,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运动。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美国人路易斯·斯奈德认为:“民族主义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占据了大多数人的行动和政治思想行为的一种强劲的感情。它不是自然的,而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出现是对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式的回应。”(注:L-ouis L.Snyder(ed.),The Dynamics of Nationalism,Readings inIts Meaning and Development,New York,D.Van Nostrand Company,Inc.,1964,p.23.)英国人约翰·布热奥利也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形态,指的是寻求和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运动,并用民族主义为理由去证明这种行动的正当性。”(注:John Breuilly,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 Press,1985,p.3.)当代著名的民族主义问题专家、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的安东尼·史密斯教授持同样的看法。他在总结前人已有的各种定义之后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目的在于为一个社会群体谋取和维持自治及个性,他们中的某些成员期望民族主义能够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注:Anthony D.Smith,Nationalism,A Trend Report and Bibliograp-hy,Current Sociology,Vol.21,No.3,1973,p.26.)
其四,认为民族主义不只具有上述某一方面的内容,它的含义应是多方面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上述观点的综合,也就是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广义的和狭义的民族主义概念。马克斯H·玻赫姆认为:“从广义上说,民族主义指的是在整个价值系统中将民族的个性放置于一个很高的位置(类似于爱国主义)的态度”;而“从狭义上讲,民族主义意味着在损害其他价值的情况下的一种特别过分、夸张和排外的,强调民族价值的倾向,结果导致自负地过高评价自己的民族而贬损其他民族”。(注:Max Hildebert Boeham,Nationalism:Political,Encyclopedia of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1937,XI,pp.231-232,转引自Louis L.Snyder(ed.),The Dynamics ofNationalism,Readings in Its Meaningand Development,New York,D.Van Nostrand Company,Inc.,1964,p.25.)赫伯特·吉本斯的看法与玻赫姆相类似。他认为民族主义有具体和抽象之分:“具体来说,民族主义可以被看作是显示民族精神(如历史、传统和语言)的特定的方式;而抽象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制约一个民族的生活和行动的观念。”(注:Herbert Adams Gibbons,Nationalism andInternationalism,NewYork,1930,p.2,转引自LouisL.Snyder(ed.),TheDynamics of Nationalism,Readings in Its Meaning and Development,New York,D.VanNostrarid Company,Inc.,1964,p.25。)
其五,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在我国出版的不少辞书中都这样记述有关民族主义的定义,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就这样写道:民族主义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他们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30页。)《现代汉语词典》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运动中,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运动中,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注:《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85页。)
综观上述有关民族主义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如同卡尔顿·海斯早先所指出的几点:(1)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建设民族国家;(2)“民族主义”一词意味着包含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原则或信念;(3)民族主义是某种将历史进程和政治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的政治行动;(4)民族主义意味着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忠诚超越于其他任何对象。(注:参见Carlton J.H.Hayes,Essays on Nationalism,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28,pp.5-6。)
虽然海斯的观点并非无可挑剔,但总的讲,上述这四点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民族主义的含义,后来的学者对民族主义所下的定义再也没有超过海斯的上述定义。
五、民族主义的起源、发展和演变
关于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问题,学术界的看法较为一致。一般认为,近代世界的民族主义产生于欧洲,尤以法国大革命为其形成的最主要标志。如安东尼·史密斯教授认为,18世纪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开端,其中尤以波兰被瓜分、美国和法国革命为主要标志。(注:参见Antho-ny D.Smith,The Resurgence of Nationalism,Myth and Memory in t-he Renewal of Naions,Note 1,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egy,Vol.47,No.4,December 1996。)乔治·古奇也认为,现代民族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注:原义为:a child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参见George P.Gooch,Studies inModern,History,London,1931,p.217,转引自Louis L.Snyder(ed.),The Dynamics ofNationalism,Readingsin Its Meaning and Development,Princeton,New Jersey,D.Van Nos-trand Company,Inc.,1964,p.26〕)在英、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观念传遍欧洲,并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而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区,现代民族主义由此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具备了全球性的意义。民族主义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民族主义在西欧的兴起和发展。伴随着新教运动的展开和王权势力的扩张,民族主义在此阶段彻底瓦解了教会势力,建立了各自的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经历了从宗教信徒到王朝臣民到祖国公民的角色转换;经历了从盲从教皇利益到效忠王朝利益到追求国家利益(也即民族利益)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从迷信宗教神权到建立王朝、王权到确立人民主权的斗争过程,最终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这是一个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其间反封建的积极意义毋需赘言。
2.民族主义扩展到欧洲的其他地区。法国大革命后的一系列对外侵略和扩张不仅反映了民族主义功能的另一面,即“争取民族的伟大,争取使每个民族有权把自己的统治扩张到相似的民族或有关的民族中去,而不管后者是否同意”,(注:〔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424页。)而且自然而然地唤起了欧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一大批民族国家在欧洲应运而生。从此,欧洲的民族主义更多地带有对外侵略扩张的性质。也正是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指导下,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殖民扩张。
以上两个阶段主要发生在19世纪,民族主义还没有明显地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3.民族主义传遍全球,成为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有力武器。这是发生在20世纪的重大历史现象。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20世纪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通过作用于各种超民族的意识形态而对世界格局进行重构的历史。”(注:陈林:《论民族主义对20世纪历史的重构》,载《欧洲》,1995年第5期。)在这一阶段,一方面民族主义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重新确立了它的建立民族国家和反抗外来侵略、捍卫民族独立的积极形象,推动着整个世界朝着民主、平等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对外扩张、排外的民族主义以及狂热地崇拜、依附本国的所谓“爱国主义”,仇恨和猜疑外部世界的情绪所引发的冲突与战争,也使得整个世界动荡不已,因而民族主义所遭到的谴责和批判远远超出了它确立和巩固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所产生的积极意义。进入90年代以后,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为主要标志,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在全球兴起。这是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兴起的民族主义,它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有人称之为新民族主义。
鉴于民族主义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所呈现出的不同表现形态,卡尔顿·海斯曾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分类,这就是所谓的“人道主义的民族主义”、“雅各宾民族主义”、“传统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整合的民族主义”,以及“经济民族主义”。(注:参见Carlton J.H.Hayes,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New York,Richard R.Smith,Inc.,1931。)海斯的这一分类法实际上将有史以来民族主义的类型作了一次梳理,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民族主义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以致经济因素最终成了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汉斯·科恩专以地理界线为标准,将民族主义划分为两种类型,即: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包括英格兰、法国、荷兰、瑞士以及美国、英国自治领的民族主义;非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包括中欧、东欧以及亚洲等地的民族主义。(注:参见Hans Khon,The Idea of Nationalism,New York,TheMacmillan Company,1946,pp.18-20,329-331。)也有的学者跨越时空的限制,综合历史上已有的民族主义类型,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划分为“压迫型的民族主义”、“领土收复型的民族主义”、“预防型的民族主义”以及“威望型的民族主义”。(注:参见Max Sylvius Han-dman,'The Sentiment of Nationalism',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36,No.1,1921,pp.104-121。)
总之,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运动,它包含了对民族的理性认知,也蕴含着巨大的非理性的情感表达,两百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也一直影响着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在研究和讨论民族主义时,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力求以科学、冷静的态度全面分析和对待民族主义,尤其是冷战后的民族主义。
本文在分析、归纳已有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概念的基础上认为,所谓民族主义应该是指以具有政治性的民族(实际上等同于国家)为中心,以该民族及其国家为最终效忠对象的一套既定的思想、信念和行动。在它的影响下,一些尚未建立国家的民族寻求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英文nationalism就其字面意义而言,指的是以nation为中心的主义。由于中文“民族”一词具有不同的层次之分,这个nation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中文的“民族”,而应把它放到当时的欧洲大环境中去理解。这个nation只能被理解为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的民族,这个“民族”实际上也就是近代的国家。这是民族主义与国家关系的理论源头,应该还民族主义以本来的面目!
毫无疑问,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构成了民族国家。但是由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因而并非所有的民族与民族国家都发展成单一民族的国家。(注:有人统计后认为,当今世界的所谓单一民族国家只占全球约190个国家的10%。(参见王缉思:《民族与民族主义》)此外,石毛直道在他的《趋于多民族和多文化的日本》一文中也写道:“在联合国的180个国家中,单一民族集团占总人口9成以上的国家为23.3%;超过总人口一半的国家为49.7%;哪个民族都不满总人口一半的国家为27%。世界上70%的国家,10个人中就有1个以上的人生活在多民族以外的民族集团。”(原文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3期))因此不仅是单一民族国家中有民族主义,在多民族(族体)国家中亦存在民族主义。它所引发的问题往往与国际政治形势紧密相关,冷战后出现的民族主义就是这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正是因为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具有的主体地位,这种民族主义反过来又加强了民族国家体系以及国家在这一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一句话,民族主义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其内涵和外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复杂,需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国家与地区进行具体分析,对冷战后的民族主义尤应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