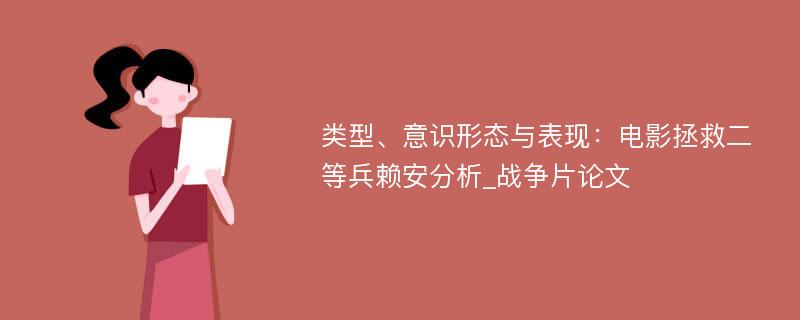
类型意识形态与呈现方式——析影片《拯救大兵瑞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大兵论文,瑞恩论文,影片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
编剧:罗伯特·罗达特
摄影指导:詹纽兹·卡明斯基
美工:汤姆·桑德斯
主演:汤姆·汉克斯
麦特·戴蒙(又译:马特·达蒙)
汤姆·塞兹摩尔
出品:派拉蒙影片公司梦工厂影片公司
叙事的裂隙与整体性
这部影片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詹森·瑞恩的三个哥哥在诺曼底登陆战中不幸先后阵亡,将军(马歇尔)为了不让瑞恩的母亲再次伤心,决定派出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把瑞恩从战场上找回来,并准许其回家。影片以老年瑞恩带着一家人来到墓园悼念约翰·米勒拉开序幕。在这个序幕段落的最后,镜头切为瑞恩若有所思的近景,又切为两只眼睛的大特写,喧嚣的战场效果声也同时跟了进来。接着,登陆奥马夏滩的战斗便打响了。表面上看这是老年瑞恩的回忆,但看完全片我们才知道他并没有参加过这场战斗,因此便不能说这是他的回忆。从老年瑞恩正在回忆的镜头切到一场他并没有参加过的战斗,这多多少少增加了观众对角色认同的困难。以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处理是与类型片的叙事策略背道而驰的。
而从剧作的角度来看,奥马夏滩之战这一段落与影片主体故事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说瑞恩的三个哥哥中有两个阵亡于此,但这一长达二十多分钟的段落始终不能让观众看清两人的面目。直到战斗结束,才在一个俯拍镜头的降落中(全景→近景)让我们看了一个军包上的名字:“瑞恩”。因此,这么长的一个段落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在完成提供一个初始情境的功能,并且也不能说是在提供后边“拯救”行动的动因。这些功能都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段落中完成的:女文书发现三个瑞恩是同一个母亲的儿子,便告知了一军官,于是将军下达拯救的命令,约翰·米勒接受任务、组成特别行动小组。这样,“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才算真正开始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叙事上的裂隙是怎样产生的呢?
应该说,战争或大或小都是降临在人类头上的灾难。作为制造梦幻,讲述神话的好莱坞类型片,一方面对这类便于提供影像奇观和视听冲击力的题材趋之若鹜,另一方面又总在影片中把灾难给予巧妙地放逐,以达到抚慰观众的目的。把灾难设置于一个过去时空中就是好莱坞的惯用手法之一,刚刚轰动全球的《泰坦尼克》即是一例,而这部《拯救大兵瑞恩》也不例外。在这部影片中,编导为了商业利益在把战争奇观尽情展示的同时,又要将其置于影片人物的回忆之中。但问题是回忆者瑞恩并不是拯救动作的主体,他作为整个拯救故事的叙述者是没有足够的资格的。于是在这里、普通的类型片叙事套路对具体的一个电影文本产生了带有惯性的影响,叙事上的裂隙也就产生了。
“真正的”二战片与电影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据说,斯皮尔伯格拍这部影片是不准备赚钱的。作为商业片的大导演,《辛德勒的名单》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他关注二战期间犹太人命运的那份苦心,看到了他的另一侧面。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所说的拍一部不准备赚钱的真正的二战片的话。
如果我们借助于格雷马斯的动素模型,也许可以更为清楚地理解这部影片在故事层面上与之前的战争片的异同。在找寻瑞恩的故事中,主体的扮者是以米勒为首的特别行动小组,发送者则是由马歇尔所代表的美国军方/政府所担任,那些盟军特别是曾与瑞恩同在一个部队的士兵担任了帮手。敌手则是历史文本中最易辨认的邪恶势力德国纳粹军队——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与人类和平的破坏者,而客体就是被寻找的大兵瑞恩。如果说以上动素与一般战争片毫无二致,那么在受惠者一项上则有了一些区别:米勒等人作为行动的主体并没有成为最后的受惠者,而得到他们在一般影片中应该得到的自由、和平与安全返乡。寻找客体的动作虽然完成了,但主体却(大多)先后死去;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最终的受惠者却没有了他们。也许,这就是斯皮尔伯格眼中的战争:死亡无处不在,但士兵们不计回报地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在这种意义上,《拯救大兵瑞恩》并不是在讲述一个一般类型片中的美国英雄神话,而是为二战中牺牲的将士唱了一曲最为悲壮的赞歌。
但是,正如托马斯·沙兹所说:“战争片是以两种基本的对立势力为主导的、一种是让一个令人同情的文化集体和一个带威胁性的敌对势力形成外部的冲突;另一种是把形形色色的个人总合纳入战斗集体的内在的冲突中,从而有利于解决那外部冲突。”(注:(美)托马斯·沙兹《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周传基、周欢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P87。)在这种意义上, 影片在动素分配上对类型片套路的那点突破实在微不足道。同一般战争片一样,以约翰·米勒为首的8人小组恰恰构成了一个战斗集体, 他们与敌对势力德国纳粹的冲突则构成了影片的外部冲突。而8 个人在对这次行动的意义、对德国俘虏的态度等问题上的分歧,则成为集体的内在冲突。除了基本矛盾冲突延续了传统的战争片,基本主题也没有什么突破。斯皮尔伯格的二战片依然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复制地与良载体。
正如笔者在第一部分所指出的,登陆奥马夏滩的段落实际上是分离于影片故事主体的。应该说,对战争场面的残酷、血腥极尽渲染之能事,这才是本片与之前的战争类型片最大的一个区别。编导之所以如此,是与下面的一个三段论不无关系的。这个三段论的大前提是:战斗越激烈、越残酷,士兵付出的牺牲越大,换来的胜利越有意义;小前提则是:奥马夏滩一战(乃至整个二战)是极其激烈、残酷的,牺牲也是无比巨大的。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参加二战的将士功勋卓著,取得的胜利意义非凡。美国陆军部长以(影片)“使美国人重新记起军人们为了保护祖国而作出的牺牲”(注:参见《戏剧电影报》1998年9 月24日第10版。)为由,而授予斯皮尔伯格“杰出人士勋章”,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如果说一部影片“讲”故事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论证’过程”,那么《拯救大兵瑞恩》需要论证的首要问题就是:用8 个人冒险去拯救一个人,其价值和意义到底何在?影片在“论证”这一问题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复制。
还是让我们先看一下瑞恩太太的一场戏。这是影片过去时空故事中最令人神往的一个场景。大片大片的麦田,一座小屋安详地矗立在远处,一条小路蜿蜒地把它与远方联系在一起。这时,一辆黑色的军车以右后方入画,打破了田园的宁静。接下来,镜头切到屋内的瑞恩太太,一位纯朴的美国妇女。她为了祖国的和平,把四个儿子送到了大洋彼岸的欧洲战场。家里的门上还贴着象征着四个军人儿子的整整四颗五角星,门旁的墙上则挂着四个儿子身着军装的合影。但这种和谐已因军车的到来永远不会再度复现,瑞恩太太一下子瘫软在门口的地上。在这个段落里,影片把和平的美好与家的温暖和盘托出。而瑞恩家中与国旗上的五星完全相同的四颗五角星,无疑是对家庭与国家关系的一种暗示:正是许许多多这样的家庭才构成了美利坚合众国,也正是这些家庭在保卫着美国,国家/政府当然也应该保护这些家庭的完整与幸福。在紧接着的下一个段落中,美军最高统帅下令寻找詹森·瑞恩——瑞恩太太最后一个可能幸存的儿子,便成为故事发展的必然。
但是,瑞恩有理由退出战场并不等于米勒等8 人的生命就应该接受死神的考验,他们也是人,也都有各自的母亲。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影片首先在人物设置上适当地弱化了观众对这八人的认同(这也是与类型片的叙事策略相左的)。从8个人组队去寻找瑞恩到最终找到,只有 70分钟左右的片长,不及影片长度的一半。并且在这一部分中,影片把叙事重心放在了他们克服一个个困难上。除了队长约翰·米勒,其它人都没有给予过多的刻画,更没有过多地涉及每个人的“前史”。人物形象的简单、平面多多少少减少了观众对其命运的关注。在影片进行到三分之二时,8个人中幸存的6个人找到了瑞恩,并与之一起在后边的战斗中冲锋陷阵。到这时,实际上已没有必要追究“拯救瑞恩”这一任务的意义了。
其次,影片通过寻找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情境,对这一问题给予了侧面的回答。
特别行动小组出发不久就遇到一家法国人,一个队员因为鲁莽的善良葬身枪下。从米勒愤怒的表情与其对不应抱那个小女孩的强调中,我们知道这8个人并不是无知的敢死队员, 也不是不珍惜自己及战友的生命。他们之所以用8个人去寻找一个人, 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被寻找者是一个不同于法国小女孩的生命。
在一个为了讨好观众的俗套:找到一个假“瑞恩”的小噱头中,影片通过对渴望回家、惧怕战争的假“瑞恩”的温和嘲弄,在为后来真瑞恩的英勇抗敌唱着赞歌,也在为约翰·米勒等人的行动作着肯定意义的注解。一如瑞恩的主演麦特·戴蒙所说:“瑞恩变成米勒和他的士兵们的一种象征,因为他的安全归乡就代表着他们全体安全返家。”正因为瑞恩及他的三个兄长为了美国的和平而英勇抗敌甚至付出了生命,将军才会特许瑞恩离开战场回到母亲身边。约翰·米勒等人既然同瑞恩一样英勇(当然,翻译除外),他们便也有理由相信自己也能得到政府的关心,也能安全回家。在这种意义上,将军让8 个人去寻找一个人的命令,不仅仅是对瑞恩及其母亲的一种关怀,同时也是对米勒等人的一种精神抚慰,同样可看作是对全体美军将士的一种精神抚慰。就这样,“拯救大兵瑞恩”的命令在树立起美国军方/政府体恤民情、爱护将士的光辉形象的同时,也为瑞恩、米勒等美军战士在二战中的表现下了一条最好的评语。到此,上面那个悖论式的难题也就彻底解决了。
但无论如何,米勒等人在完成了任务的同时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果说他们的阵亡除了换来了那一场战斗的胜利还别有收获的话,那就是促成了“作为米勒等人的一种象征”的瑞恩安全返乡。在影片的序幕段落中,伴随着舒缓、沉郁的音乐,一面美国国旗的满幕镜头呈现于银幕之上(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巴顿将军》)。接着,镜头从老年瑞恩缓慢且略带跟踪蹒跚的脚步上摇为瑞恩背面近景。镜头反打,是一个瑞恩的妻子与三个女儿的中近景。然后镜头又切为瑞恩的儿子,他正举起相机为父亲拍照。仅仅是四个镜头,影片已把瑞恩一家呈现给观众,并象征性地暗示了他们与国家的关系。维护核心家庭的完整与幸福始终是好莱坞影片支持的一个价值系统。这样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形象,正是约翰·米勒等人用生命保护着;高高飘扬的美国国旗也是他们用生命来捍卫的。
最后需要论及的是影片对战争的态度。战争从来就是一个充满了悖论的人类活动现象。正如影片人物约翰·米勒所说:“(虽然)我手下死了94人,但我救过的人超过这十多倍,或许二十倍还多。”不同于越战片中对战争与人性关系的反思,《拯救大兵瑞恩》对战争是不存在什么批判态度的。坚持释放德国俘虏的文弱、仁慈但也胆小的翻译,在影片快要结束时也举起了枪,打死了自己曾放走的那个俘虏。在这里,编导似乎更相信善恶的二元论,并且拒绝考虑二者之间的转化。善就是善,恶就是恶,翻译举起的枪正是善对恶的一种裁决。很显然,影片与美国的其它历史文本一样,讲述的是一个美国站在和平主义立场上打败纳粹集团、保卫祖国、解放全人类的神话。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可以看清影片编织了怎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网络。一个寻找大兵瑞恩的过程就是一个树立美国国家形象(包括政府/军方及人民/战士)的过程,瑞恩的被拯救与安全返乡正象征着一种英勇、团结、爱国的美国精神的被拯救与在影片中的巧妙安置。在这种意义上,《拯救大兵瑞恩》同所有的美国战争片一样,充当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
战争作为奇观与纪录片风格
正如笔者前面的论述,把战争作为奇观来展示,一方面能够突出战争的残酷、血腥、激烈,并在上面“三段论”的作用下,实现影片的意识形态功能,另一方面也能借此满足从没有参加过战争的普通大众的精神需要,实现影片的商业价值。
但是,制造奇观与电影的纪实本性并不像它们表面上那样是矛盾对立的,恰恰相反,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只有让观众信其为真的奇观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拯救大兵瑞恩》就是立足于电影的纪实本性并进而来用纪录片的风格而营造了史无前例的战争奇观效果。影片的主创人员在观看了大量二战纪录片的基础上,模仿其手提摄影的方式,通过大量不稳定的移动镜头去表现战场上特殊的气氛。在美工、烟火、化装等每一个部门上,影片力求每一件衣服、每一个道具、每一张面孔与当时的气氛相一致。胶片、洗印等制作工艺上也做了许多特殊处理,在真实性的追求上可谓精益求精。
另外,战争奇观被展示得成功还得益于细节表现上极其真实、丰富。“电影的全新表现方法所描绘的不再是海上的飓风或火山的爆发,而可能是从人的眼角里慢慢流出的一滴寂寞的眼泪。”细节表现是电影媒介区别于其它艺术媒介的一个重要特征。仅以登陆奥马夏滩的战斗为例,以约翰·米勒抖动的右手到水中的战士喷出的血柱,以水面上横飞的子弹到被炮弹炸断的左腿,从浑身燃烧的战士到被正面击中的脑门,以随处可见的弹片、伤口、鲜血到战士们一张张不惧死的面孔,等等。细节如此丰富以致于每一个镜头都是那么地令人震撼、令人惊叹。这个段落放映时间接近23分钟,大致150个左右的镜头, 但能明确地指认为全景的镜头只有16个,其余都是一直处于运动中的中、近景镜头,甚至特写。历史中的奥马夏滩一战盟军阵亡2500余人,战斗不可谓不大。但影片为了保持纪录风格的完整而完全摒弃了可以展示战斗气势之大的大全景、大远景以及航拍镜头,而是仅仅依靠中近景镜头和丰富的细节呈现出了一场银幕上以未有过的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我们可以指责这部影片气势不够宏大,节奏不够丰富、多变,但我们不能不为能看到这样“纯正”战争场面而赞叹不已。
在视听呈现上,与纪录风格相一致的是影片力求视点上的单一。在奥马夏滩一战的段落中,只有三、四个是以德军枪械为前景的敌方视点镜头,其余都是美军的视点。而在越过德军狙击手阵地的一个段落中,这种风格化的追求达到了一种极致,全部战斗只用了文弱、胆小的翻译一个人的视点。但《拯救大兵瑞恩》毕竟是虚构的故事片,编导还是适当地设置了一些敌方视点,以调节影片的视觉节奏,丰富影像的内容。在保护法国小女孩的段落中,正因为有了敌方视点镜头,我们才能更加倍地关心起伤兵的生命,更加庆幸于“神射手”的机智。
不难看出,仅仅就视听呈现而言,影片在遵循普通的类型片法则(制造奇观)与追求独特的影像风格上做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而这一切又都是为表情达意服务的,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树立勇敢的美国精神。
对影片《拯救大兵瑞恩》的分析,从类型片的角度切入是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上理解斯皮尔伯格的这部新片。当然,“类型片”的概念并不等于美学标准。影片虽然在叙事的整体性、观众对角色的认同及动作主体的生或死等方面与一般战争类型片不完全相同,但正如笔者上面的分析,这种突破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传播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不管斯皮尔伯格在形式上(比如对战争的呈现方式)作了多少创新,其宣传一种美国精神的核心决不会改变。近年来,随着分帐大片的进入中国,好莱坞影片日益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精神食粮。对于好莱坞影片,我们无意苟同于那种高呼“狼来了”的态度,但更反对不加反思地一味吹捧。本文对《拯救大兵瑞恩》的分析就是想提倡一种客观研究、批判到拿为我用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