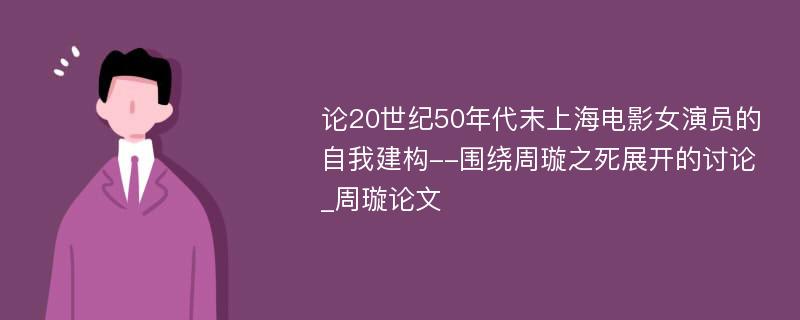
论1950年代晚期上海电影女演员的自我建构——围绕“周璇之死”展开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期论文,女演员论文,上海论文,之死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3)18-0152-03
《闺塾师》是著名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探讨明清江南才女文化的名作,在“‘五四’解放妇女话语”几乎主导妇女史学研究之时,这部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著作,却对这一论调提出了颠覆性的批评。在《闺塾师》的导论中,高彦颐指出,为了服务于现代国家民族话语,“五四”男性文化精英将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建构成为牺牲品和可怜虫。[1]2如果说,将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形象构建成为“传统社会的牺牲品”是“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的一种创造,而非历史真实;那么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话语则将这一创造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一方面,它选择性的完全忽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文化的传统和发展,仅仅截取中国女性生活的断面而大肆宣扬,将新中国成立前的女性生活描述得水深火热;另一方面,却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共和国的妇女形象建构成彻底解放、重获新生的新女性形象。这种将解放前后妇女的处境选择性的进行强烈对比,过分渲染对她们来说犹如“冰火两重天”的境遇,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电影女演员的出现不仅仅是时代推进和商业发展的产物,同时,在“五四”妇女解放话语的背景下,这类女性职业群体的诞生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青春靓丽的她们首先出现在商业化大都市上海,这一职业群体的诞生,其本身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体现。从1920年代初诞生之日起,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止,观影大众、文化精英及电影女演员自身对电影女明星的身份认知,经历了一个从接近娼妓身份的娱乐从业者向趋向文化精英的文艺工作者转变的过程。当然,处于身份光谱两端的娼妓及文艺工作者的身份,经常纠缠在一起,从没清晰地区分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形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政权赋予了电影女演员教育大众的文艺工作者的职业身份。然而,不管其身份如何,在民国时期,电影女明星在上海都市文化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推动民国上海都市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力量。[2]74-82然而,从民国上海走进新政权的电影女演员,在经历了1950年代的几场政治运动以后,已经不能“真实地回忆”自己的过去,而是逐渐认同了新政权关于旧时代的女性是牺牲品的叙述,并将自己的经历作为构筑官方叙述的组成部分。本文就将考察著名女演员周璇去世之后,围绕着她的一生所展开的各种言论是如何将与周璇同时代的并以她为代表的电影女演员逐步的建构成“旧社会的牺牲品”的;同还将时探讨那些与周璇同时代的女演员们,又是如何配合国家权力话语,最终完成了对新旧两个时代的典型女性特征和境遇的建构。
周璇于1920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在她四岁的时候被舅舅拐卖,此后生活辗转,几经周折最终到上海给一位过气的粤剧演员当了养女。1932年,她加入了上海联华歌舞团,并在1935年开始了她不寻常的命运轨迹。这一年由她主演的电影《马路天使》一炮而红,并且这部轰动一时的电影片中的主题曲《四季歌》也正是由周璇演唱,她出色的表演和动人的歌喉使得她一举成名,赢得“金嗓子”的美誉。解放前夕,周璇前往香港继续她的演艺生涯拍片,1950年秋,她接受电影《和平鸽》的邀请由香港返回上海。然而在这部电影拍摄的尾声,因受片中验血镜头的刺激,周璇的情绪受到了极大的波动,这部电影也不得不停拍,此后周璇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在银幕上露过面。1952年10月,周璇以治疗“精神分裂”为名被送往上海精神病疗养院。1957年春,周璇病情好转,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然而同年7月19日,她突然发病高烧不退,并于1957年9月22日在上海去世。
周璇去世的消息发布之后,相关方面也非常积极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周璇的主治医师上海精神病疗养院苏复院长作了“周璇生前病情和治疗过程”的汇报,详细叙述了在周璇生病期间,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她的治疗情况。[3]22周璇的治丧委员会由上海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组织,包括当时上海电影界几位主要领导,周璇生前的众多好友赵丹、王人美、王丹凤等也包含在内[3]21。在1957年的9月24日,上海万国殡仪馆在上海电影人的参与下为周璇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当时的著名导演郑君里在追悼会上作了题为《一个优秀女演员的一生》的报告,报告详述了周璇的出身背景以及后来从艺并成名的过程,对周璇的代表作品做出了评价,这份报告花了十分浓重的笔墨对她在旧社会里饱受折磨甚至导致精神分裂的往事进行了叙述,而落脚于其在新社会下如何接受了党和政府关心而进行积极治疗的情况。
郑君里在报告中这样描述了周璇的婚姻生活:周璇于1937年结婚,然而她在婚后却常受到丈夫虐待,不仅如此,她的丈夫在经济方面也对她多方欺诈,她的婚姻也因此被迫走到了尽头,但这远远还不是她悲剧的结束,她的丈夫唆使国民党特务流氓出面来威胁她,这时的周璇悲痛万分,准备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但为熟人碰见从而捡回一命,但这一段悲惨的经历给她的精神上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严重创伤。
1942年,日寇侵入上海租界,这个时期的周璇生活境地仍然是十分悲惨的,一直受到汉奸恶棍张善琨的欺压,这对于她的精神又产生了极大的伤害。然而在这篇报告的叙述中,周璇的悲剧仍然没有结束,即使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各种落后的势力又怂恿着她到香港拍摄《清官秘史》等片,香港拍片期间,她在精神上又受到重大摧残。1950年秋天,周璇从香港回到上海,在电影《和平鸽》的拍摄过程中,精神病发作使她不得不暂时告别了银幕。从1951年夏天到1957年之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周璇先后在四个知名的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直到她去世的前夕,她的病情已然有了重大的好转,在她的意识里已经开始逐渐的认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然处在了一个以前难以梦想的、崭新的新中国里了。[4]75-78
郑君里的这篇报告几乎代表了1950年代官方对女演员周璇一生的标准叙述,此后出现在报端的几个不同的版本皆以此篇报告为蓝本。1957年9月25日的《文汇报》将这篇报告进行部分删节,并以《周璇在新旧社会的两种遭遇》为题,予以登载,再度强调周璇在新旧社会受到的不同的遭遇,突出着周璇在新社会的关心下获得新生。[5]1957年10月版的《上影画报》,对公祭周璇的现场进行了多达两个整版的图片报道,然而其编者按上的叙述同一个月以前的《文汇报》如出一辙。翻看1950年代的相关史料,笔者发现其对周璇一生的描述和重点惊人的一致,周璇作为处于大众凝视下的女性,其角色的构建陷入了一种完全刻板的状态一:她是旧时代的牺牲品和可怜虫。[3]22
不久后,周璇为她写的题为《旧社会的牺牲品》的悼文呈现出一些不同的角度,然而这种改变,只不过是从新的层面强调了上述官方叙述的可信性。与郑君里报告突出叙述周璇在旧社会遭受伤害而在新社会受到关怀不同,黄宗英的文章虽题为《旧社会的牺牲品》,却是重在讲述周璇在新社会受到的党和政府的关心以及已经逐渐开始发生的变化。黄宗英在文章中描述了一件非常具体的往事:那时周璇刚从香港返回上海,未婚先孕的她对自己的境况多有担心;在和黄宗英、赵丹初次见面的时候,周璇丝毫没有掩饰这种担心,她眼含着泪水害怕因此而名誉受损。黄宗英认为,周璇的这种担心是完全出自于旧社会对女性尤其是女演员的偏见,她安慰周璇,在新的社会里,人们不会嘲笑她,只会更加的同情她。[6]79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黄宗英更是发自内心地为周璇错过了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而惋惜。
郑君里的报告节选周璇人生的几个片段进行了详细描述,这篇报告以及之后各类出版物对周璇之死的相关报道,在大众媒体上将周璇建构成了“旧中国的制度社会下遭受层层恶势力压榨的女艺人”的典型代表。可以说,不仅是在女艺人这一特定的职业群体中,周璇的形象和遭遇甚至成为旧中国妇女苦难形象的缩影之一。在这种描述下,电影女演员成为富人和权力阶层的玩物,是任人宰割的牺牲品和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卑微的可怜虫,她们的境况只有在新的政权和社会制度下才能够得到改善。且不论这样整齐划一的话语对从民国时代进入共和国早期的电影女演员的标准建构,是否具有特定时期迎合政治需要的某种历史合理性。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表达不仅完全无视女演员在民国上海都市文化空间的构建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把她们作为一个个努力生活的个体,为同自己的命运所作的种种抗争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性一并抹杀了。黄宗英的文章看似换了一个角度,实则换汤不换药,不仅没有超越时代的局限,而且还恰恰以这种现身说法的姿态,使关于女演员是旧社会的牺牲品的建构,显得愈发生动真实。
从民国上海走进社会主义新政权的电影女演员们,在经历了195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其后的几场政治运动之后,已经相当熟悉和适应,或者说懂得运用新政权所创造的措辞,也深知如何在公众领域进行言说,才能更好地满足新政权对她们的期许。至大跃进时期,她们已经逐渐地适应了国家权力话语对她们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积极迎合它。在许多场合,电影女演员们首先更愿意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演员,努力淡化其作为女演员的性别身份。[8]黄宗英是为数不多的仍然坚持用“女演员”来界定自己身份的人,虽然无从得知她这样的坚持,是出于怎样的思想挣扎,显而易见的是她的种种言论和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顺应了当时的国家权力话语,更好地完成了对新旧社会妇女生活“冰火两重天”的建构,在她的笔下,旧社会的电影女演员的形象烙上了更加鲜明的等待共产党解放的可怜虫的印记。
20世纪50年代后期,女演员们努力配合国家权力话语的要求,将自己的过去建构成等待解放的“旧时代的牺牲品”。看上去她们自己也几乎完全相信了这种建构。与其说是女演员被动地接受这一切,不如说是为了完全融入新社会而做出的一种积极的“选择”,令女演员欣慰的是,她们的愿望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满足了,她们确实因此而顺利地融入了新社会,不仅获得了文艺工作者的清晰身份定位为,有佼佼者还跻身于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之列,电影演艺界的发展似乎也空前的高涨起来。
许多女演员还被鼓励积极参与到文艺创作的各个方面,写剧本、当导演在当时成为部分电影女演员的副业,她们中的一些甚至成功地迎来了事业上的另一个新的高峰。然而,这些正风风火火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电影女演员们却并没有意识到,她们作为女性的性别主体身份已经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依从国家权力话语,在大跃进的年代,“妇女已经获得彻底解放”宣传不绝于耳,任何反对这一认识的思想都会被斥为异端。[11]在这一前提下,“妇女已然解放”是一个不能被讨论不能被质疑的事实,基于这样的认识,任何关于“妇女存在的问题”的讨论都变成了荒谬的笑话。女演员们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活跃,为她们贴上新时代知识女性的标签,她们的“被解放”更无需过多证明。这一切的发生或许有利于女演员获得令人尊重的职业身份,却也实实在在地模糊了她们对其主体身份的认知,使得她们甚至没有任何官方话语以外的词汇来表达自己在新社会和生活中的体验与困惑。虽然女演员演艺事业上的成功似乎表明了她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贡献,甚至我们还惊异地发现少数跻身政治文化精英阶层的女演员在某些场景下分享了男性的话语权。但是,即便是处于职业序列顶端的电影女演员,也只是在历史的洪流中被裹挟着走上了一个虚高的顶峰,她们对于自身女性身份的主体意识的认知已荡然无存,她们在共和国早期的生活反而更像是一场永不落幕的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