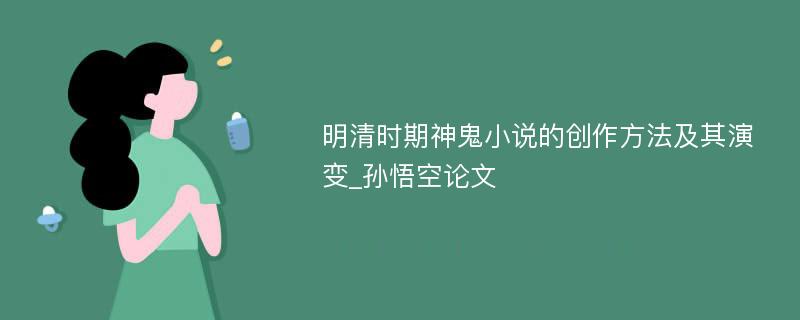
明清神魔小说编创方式及其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神魔论文,方式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6-0142-06
神魔小说是明清通俗小说的主要类型之一。该类小说多以神佛魔怪的出身修行、斗法飞升等为题材内容,故事情节奇谲诡异、真幻相间,变相地表现了现实社会中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神魔小说是在明代中后期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文化背景下,在《西游记》的示范和影响下,迅速崛起并蔚为大观的,至清末作品数量达80余种。如此繁夥的神魔小说是采用什么方式编创出来的?又有哪些因素制约了神魔小说的编创方式及其演化?本文试从神魔小说的编创者、出版者、评点者和接受者的互动关系入手,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西游记》与神魔小说编创方式的确立
《西游记》是怎么写成的?以往学者在探讨其成书过程时多指出它是采用“滚雪球”的方式累积而成的。因为早在《西游记》成书以前,“西游”故事就曾以宗教传说、戏曲、说唱等多种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从《西游记》中通俗唱词的大量穿插与故事情节的程式化等现象,也可以看出它脱胎于俗文学的痕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其编创者只需对民间流传的西游故事进行一番整理、编辑和修订,就可以使之成为一部伟大的名著。事实上,只要将小说《西游记》与此前的西游故事略作比较,就不难看出无论是从题材内容的拓展、故事情节的建构,还是艺术手法的运用,《西游记》都不只是简单的继承和吸纳,而是进行了脱胎换骨的艺术再创造。
其一,编创者对西游故事的题材内容作了进一步的丰富与拓展,使唐僧师徒遇到的磨难猛增至“九九八十一难”;仅经过的人间国度就有宝象国、乌鸡国、车迟国、西梁国、祭赛国、朱紫国、狮陀国、比丘国、凤仙郡、玉华县、天竺国、铜台府等;而妖魔数量也空前增多,除《西游记平活》所列之外,又有尸魔、黄袍怪、金角与银角大王、鼍龙怪、虎力羊力与鹿力三仙、金鱼精、青牛精、蝎子精、六耳猕猴、九头虫、黄眉怪、金毛犰、白鹿怪、豹魔王、九头狮、犀牛怪,等等,真可谓无怪不有。
其二,与“八十一难”相联系的是“降魔伏怪”叙事模式的重新建构。本来,这一模式在杂剧、平话中已初步成形,《西游记》对之所作的改造,就是把以往的“唐三藏西游记”转变成了“孙悟空传”;这样,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就被提到了卷首,孙悟空的经历遂成为贯穿全部情节的主线,小说也随之变成了孙悟空改邪归正后“降魔伏怪”的战斗史,全书旨趣发生了很大转变。
其三,编创者还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借幻写真,“寓庄于谐”。本来,以往的西游故事已不同程度地带有谐谑色彩;不过,与《西游记》相比,《诗话》也好,杂剧、平话也罢,都明显缺少深刻的现实内涵,艺术品位不高。《西游记》的编创者也颇善谐谑,爱“以戏言寓诸幻笔”,[1](P1382,任蛟:《西游记叙言》)甚至“任意大开顽笑”,[2](P542)但他又很善于借神魔世界来观照人间社会,往往在风趣、戏谑、幽默中针砭世态人情,寄托他对世事人心的感慨。故鲁迅说《西游记》所写的“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3](P111)并说它“揶揄讽刺,皆取当时世态”。[3](P114)
其四,编创者在改造和加工传统的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的故事时,还有意以幻寓理,用“心猿”来指称“孙悟空”,借孙悟空的传奇经历,隐寓“修心炼性”的人生哲理。例如,孙悟空上天入地大闹乾坤,作者就在回目上说他是“心何足”、“意未宁”;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作者则说这是“定心猿”;以后孙悟空去西天取经,作者又说这是“心猿归正”、“炼魔”、“魔灭尽”与“道归根”;还说:“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等等。
总之,《西游记》的编创者在利用以往的西游故事进行再创造时,既拓展了西游故事的题材内容,确立了以孙悟空传奇为叙事重心的结构方式,又赋予了它丰富的现实内涵与哲理意蕴,这使《西游记》不仅取得了卓荦不凡的艺术成就,而且在开拓新题材、建构故事情节、借幻写真、以幻寓理等方面,均对后继者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后来的神魔小说创作基本上就是沿袭《西游记》开辟的路子前进的。
二、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的联手炮制
万历二十年,《西游记》世德堂本问世,由于题材新颖、故事热闹、风格谐谑,很快受到读者追捧,并激发了神魔小说的编创热潮,仅万历后期至天启末,就涌现了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余象斗《华光天王南游志传》(又名《南游记》)、《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又名《北游记》),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又名《东游记》),邓志谟《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朱星祚《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朱鼎臣《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朱开泰《达摩出身传灯传》,杨尔曾《韩湘子全传》、许仲琳《封神演义》等20余部小说。这些神魔小说是怎么编写成的呢?
首先,从编创者情况来看,他们多为书坊主或由书坊主聘请的下层文人。如余象斗自万历十九年起放弃儒业,专事刻书编书。杨尔曾也是在“颠毛种种,仕路犹赊”的情况下从事编书、刻书的。罗懋登则游食四方、卖文为生,万历后期受雇于金陵书坊唐氏富春堂,编创《西洋记》。邓志谟则“阻于时,扼于困”,[4]不得已“糊口书林”,替建阳余氏萃庆堂编写小说或杂书。吴元泰也是受雇于三台馆主人余象斗,编写《东游记》的。李云翔则受书坊主舒冲甫所托,续补、修订了《封神演义》。这些人并不是为了“发愤著书”,而是受利益驱动,把迎合读者的文化心里与阅读口味,力求“利多售速”作为其编书的主要准则。所以,他们有意选取那些为俗众喜闻乐见的神佛(诸如观音、天妃、华光、真武、八仙、萨真人等)作为主人公,以其出身修行、斩妖除魔为主要内容。这些神佛本来在民间就广有市场,其灵异事迹既见诸载籍,又传诵于众口,因此为这些神佛编造较为系统、连贯的神奇故事,无疑可以动人观感,收到很好的传播与接受效果。鲁迅就说:“凡所敷叙,又非宋以来道士造作之谈,但为人民间巷间意,芜杂浅陋,率无可观。然其力之及于人心者甚大……”[3](P104)
其次,这些编写者的文化素养和创作能力本来有限,却又急于求成,所以只好从民间传说、话本戏曲、宗教典籍中杂取素材,以抄袭、杂凑、编缀为主,如《南游记》、《北游记》,题“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编”;《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题“竹溪散人邓氏编”;《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题“抚临朱星祚编”;《天妃济世出身传》,也题“南州散人吴还初编”。他们编的这些小说,篇幅多在二三十回左右,字数一般不到五万,明显为草率编成的急就章。例如,《东游记》既汲取了民间的八仙传说,又抄袭了《列仙全传》记载的八仙事迹,只不过编者在八仙的相互关系上,下了一番撮合功夫。至于其第三十二至四十四则所写的辽宋大战天门阵的故事,则是删节、改写了《杨家府演义》中的天门阵故事,再添加到《东游记》各仙成道的事迹当中。又如,《北游记》主要是杂取《道藏》中《玄天上帝启不录》、《元洞玉历记》与民间传说拼凑而成。至于邓志谟编写《铁树记》,也是“考寻遗迹,搜检残编,汇成此书”;[5](P2446,邓志谟:《铁树记》篇末语)后来,他又“暇日考《搜神》一集,慕萨君之油然仁风,摭其遗事,演以《咒枣记》”;[5](P1856,邓志谟:《咒枣记引》)“搜其遗事,为一部《飞剑记》”。[5](P2235,邓志谟:《飞剑记》篇末语)这三部书都是在摭拾旧闻的基础上略加演绎编成的。其实,就连《西洋记》,也是罗懋登“集俚俗传闻”,编演而成。钱曾《读书敏求记》曾说:“盖三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戏剧,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6](P66)另外,该书对西洋诸国的描绘,则抄自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而抄袭话本、笔记之处也屡见不鲜,如第九十一回《阎罗王寄书国师》,就整篇引述了《剪灯余话》卷二《田沫遇薛涛联句记》;第九十二回又引述了《古今小说》里玉通禅师私红莲,月明和尚度柳翠的前半段;第九十四回插入了《百家公案》第四十四回金鲤鱼迷刘秀才一案;第九十五回又照抄《百家公案》中的包公判五鼠闹东京故事。可见,罗懋登是很惯于东抄西借来编书的。
再次,编写者在编造故事、建构情节乃至人物塑造等方面,还刻意效仿、抄袭《西游记》。例如,《西洋记》叙碧峰禅师和张天师为郑和护航,走西洋水路去找传国玉玺,一路上降魔斩妖,历经无数磨难,征服了三十九国;这与《西游记》写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捉怪,历经八十一难的叙事结构方式,如出一辙。不仅如此,罗懋登还频繁偷袭《西游记》的情节片段,赵景深通过详细比较,就指出他“总爱偷袭,同时也爱改头换面来标新立异”。[7](P289)《南游记》在结构上也是有意仿照孙悟空的传奇来写华光的故事。华光原是如来法堂前的一盏油灯,变为人身,因有罪贬去投胎为马耳山娘娘的遗腹子灵光,又转世为灵耀,自号华光天王,也和孙悟空一样,大闹天宫。他还曾变作齐天大圣去偷仙桃,与孙悟空打得不可开交,后来火炎王光佛出面说和,两人才尽释前嫌,结为兄弟。其他像“华光与铁扇公主成亲”,“华光占清凉山”假变观音等情节,也明显脱胎自《西游记》。《东游记》不仅模仿《西游记》,依八仙的游历来安排情节,而且还写八仙大闹龙宫,与天兵交战,齐天大圣也仗义出面援助八仙。《咒枣记》也以主要人物的行踪来连缀故事,其第六回还大段抄袭了《西游记》第四十七回“大闹通天河”。《铁树记》描写许真君与蛟龙斗法,也借鉴了《西游记》中二郎神与孙悟空打斗的情节。 《韩湘子全传》第十六回“入阴司查勘生死”、第二十回“美女庄渔樵点化”,则分别袭自《西游记》第三回、第九回和第七十六回。就连《天妃娘妈传》中的猴精也会放瞌睡虫。可见,编写者在人物、故事和结构方面对《西游记》的刻意效颦。
最后,编写者还借鉴了《西游记》“寓庄于谐”、借幻写真的写法,有意将神佛世俗化,使神佛的传奇皆带上戏说甚或恶搞的成分,以此媚俗娱众。如《东游记》中的吕洞宾,即贪酒好色,嫖恋白牡丹,还说“嗜欲之心,人皆有之,而遇美色,犹为难禁”。其师汉钟离出言相讥,他竟私自下凡,怂恿椿精一起协助辽国入侵宋国,与宋兵争锋。《南游记》中孙悟空则娶妻生子,儿孙满堂,其女儿月孛星不仅“目大腰宽,口阔手粗,脚长头歪,喊声似打雷”,而且以骷髅头作兵器,只要敲打骷髅头,对手立即头痛眼昏,栽倒在地;华光则娶了铁扇公主为妻。《北游记》中玉皇大帝看到刘天君家有宝树,贪羡不已,竟然慨叹:“如何能得到他家做个子孙,得享此物,孤心足矣。”总之,这些小说给人的感觉就是敢于胡编乱造,神佛或妖魔都没有什么明确的界线,彼此之间可以通过投胎、转世的方式相互转化,而且轮回转世既不要什么合理的原因,也可以不受任何的限制。小说中的角色,神佛也好,妖怪也罢,往往都不守信用、心胸狭窄、喜怒无常,一下子弄恼了,就翻脸不认人,为了一点贪欲或琐事,就可以大动干戈。但这些小说的长处,恰恰就在于率意杜撰,将一切清规戒律都视同儿戏,将天上地下的秩序搅得乱七八糟,从而起到了为市井细民娱心的作用。
既然书坊主和下层文人是采用上述方式来编写神魔小说的,这就难怪其作品多半“芜杂浅陋,率无可观”了。但是,如果从通俗小说的创作历程尤其是神魔小说流派的形成来看,那么也正是它们追随《西游记》,才壮大了神魔小说的声势,打破了历史演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丰富了通俗小说的题材、种类与编创方法,扩大了通俗小说的社会影响,并使此后一些素质较高的文人陆续介入到神魔小说的编创与评点之中来,因此它们在小说史上的价值还是应该予以公允的肯定。
三、文人评点对神魔小说编创方式的引导
以《西游记》为代表的神魔小说的兴起,不仅激发了人们阅读该类小说的热情,而且还引起了人们评点神魔小说的兴趣。诸如神魔小说编创的意义、编创特点和经验等理论探讨,无疑会对神魔小说的编创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
早在世德堂本《西游记》刊行时,陈元之就在该书序中提出用写作史书、子书的要求来衡量该小说是不合理的,认为作者之所以采用“其言参差而俶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涯涘”的方式来写作,只因“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这样,他就把作者所描绘的神魔故事与“浊世”联系起来了,并断言“其书直寓言者哉!”他还认为,“旧序”所谓悟空、白马、八戒、沙僧、三藏等,分别隐喻“心之神”、“意之驰”、“肝气之木”、“肾气之水”和“乳郭之主”,魔怪则隐喻“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魔以心生,亦以心摄”等,即其所寓之理。[8](P555-556)
陈氏的“寓言”说以及“以心摄魔”之论,由于部分地反映了《西游记》的创作实际,并且与明中后期流行的心学思潮鼓桴相应,因而很快得到了评论者的广泛认同。多数论者都喜欢从心学的角度来阐析《西游记》的修心寓言。例如,谢肇涮就指出:“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并明确地说:“《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他还指出:“《华光》小说则皆五行生克之理,火之炽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扑灭,而真武以水制之,始归正道。其他诸传记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这就具体地阐释了神魔小说“以幻寓理”的寓言性质。并且,他还认为:“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9](P313)这又从艺术上对神魔小说的编创方法进行了肯定。与谢氏相呼应,张誉也对神魔小说的真幻、虚实关系作了较透彻的阐发,指出:“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小说创作应该“兼真幻之长”。[1](P1347)此后,袁于令又在《西游记题辞》中大赞《西游》之妙,认为:“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1](P1358)睡乡居士在《二刻拍案惊奇序》中也说:“即如《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8](P534-535)
上述言论或有偏颇之处,但对“以幻寓理”、“幻中有真”、“言真不如言幻”的肯定,则揭橥了神魔小说的创作特点及其价值所在,并对神魔小说的再编创起到了有效的导向作用。明末清初,由文人创作的神魔小说就是自觉地朝着“幻中有真”、“幻中有理”的方向拓展的,特别是“修心摄魔”几乎成了创作的主要旨趣。例如,潘镜若编创《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就继承了《西游记》幻中寓理的写法。该小说中所写的叹贫迷、做官迷、豪气迷、狂妄迷、风月迷、嫉妒迷……名虽为妖,实为各种邪欲之化身,“三教开迷”,用意即在于“见性明心,驱邪荡秽,引善化恶,以助政教”。[10](P6-7)清溪道人编创《东度记》,也旨在“假圣僧东游,而发明人伦”,该书序谓“昔人撰《西游》,借金公木母、意马心猿之义;而此记,借酒色财气、逞邪弄怪之谈。一魅恣,则以一伦扫,扫魅还伦,尽归实理。”[1](P1416,世裕堂主人:《扫魅郭伦东度记序》)作者以寓言手法,把酒色财气拟化为四个邪魔,诱人作恶,还捏造出一群七情六欲的邪魔,以此图解“魔以心生,亦以心摄”之理。《续西游记》则围绕人的机变心大做文章,阐说种种妖魔鬼怪都由机变心产生,进一步演绎了《西游记》所说的“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禅机妙悟。《后西游记》又把“心即是佛”的命题和儒家的“求其放心”结合起来,更注重于破心中魔,并且破魔之法主要靠修心炼性。《西游补》则补写孙悟空闯情关的故事。作者董说在《西游补答问》中说:“《西游补》者,情妖也;情妖者,蜻鱼精也。”又说:“情之魔入,无形无声……若一入而决不可出。知情是魔,便是出头地步。[1](P1393)诸如此类,皆与《西游记》中祛除“六贼”、摒弃“二心”等隐喻手法异曲同工。
与此同时,这些神魔小说亦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西游记》“揶揄讽刺,皆取当时世态”的手法。例如《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对晚明社会的诸种弊病以及风俗人情的浇漓,即时寓针砭,对恶人、小人,也常作词曲予以讥嘲,正如作者自序所言:“传中浪游三吴齐鲁之地,见履人情物理之事,真实不妄;而慷慨以发宏议,实开布讽之私。”《西游补》也在荒诞的故事中寓含了强烈的讽世之意。如小说第二回,作者借宫人之口嘲讽道:“皇帝也眠,宰相也眠,绿玉殿如今变成‘眠仙阁’哩”;第四回又揭批科举制造就的秀才,一个个“无耳无目、无舌无鼻、无手无脚、无心无肺、无筋无骨、无血无气”;第九回写行者审秦桧,秦桧道:“爷爷,后边做秦桧的也多,现今做秦桧的也不少,只管叫秦桧独受苦怎的?”《后西游记》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书中对佛教轮回报应之说,歪嘴和尚念经骗财之风,文人舞文弄墨之习等,颇多奚落和嘲讽。
总之,由于文人评点的有效引导,加上明末心学思潮的濡染,以及人欲横流、世风日下的刺激,神魔小说逐渐从侈谈神魔以媚俗娱众,朝着寓言讽世以救正风俗的创作路子上转变,使其思想、艺术品位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四、读者接受对神魔小说编创方式的影响
神魔小说起初主要描写神佛与妖魔之间的斗法、争胜,其所述神仙鬼怪,变幻奇诡,光怪陆离,虽然幻妄无当,但却幻中有真、幻中有趣、幻中有理,并且由于多取材于民间传说,编演的是民众熟悉、喜爱的神魔故事,糅合了民间的宗教信仰、鬼神观念及世俗欲望,因而深受读者喜爱,得以风行一时。
不过,读者的接受心理与审美趣味,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比如,当神魔小说盛行时,以“描摹世态,见其炎凉”为主的世情小说开始兴起,该类小说因为贴近市井细民的现实生活,时代气息浓厚,甚受读者欢迎,并逐渐改变了人们对神魔小说的看法。如凌濛初就说:“今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1](P785,凌濛初:《拍案惊奇序》)笑花主人也说:“《西游》、《西洋》逞臆于画鬼。无关风化,奚取连篇……夫蜃楼海市,焰山火井,观非不奇,然非耳目经见之事,未免为疑冰之虫。故夫天下之真奇,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1](P793,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当时,就连著名的思想家李贽也这样说过:“世人厌平常而喜新奇,不知言天下之至新奇,莫过于平常也。……是新奇正在于平常,世人不察,反于平常之外觅新奇,是岂得谓之新奇乎?” [11](P60)这种“奇”出于“常”之论,无疑是不利于神魔小说的创作与接受的。
与此同时,不少历史演义的接受者也纷纷贬斥神魔小说诞谬不经。如明末戏笔主人就讥讽《西游记》“专工虚妄”;[8](P535,戏笔主人:《忠烈全传序》)金圣叹也嘲笑《西游记》“太无脚地”;[8](P537,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清初李渔则说:“《西游》辞句虽达,第凿空捏造,人皆知其诞而不经,诡怪幻妄,是奇而灭没圣贤为治之心者也。”[1](P902,李渔:《三国志演义序》,毛宗岗也说:“读《三国》胜读《西游记》。《西游》捏造妖魔之事,诞而不经,不若《三国》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1](P932,毛宗岗:《读三国志法》)
另外,明末清初时局的动荡不宁,社会的急剧变迁,也使民众的注意力逐渐从“曼衍虚诞”的神魔小说转移到了反映现实社会与时事政治的世情小说、时事小说上面,而书坊主的出版热点也随之发生了转移,时事小说、拟话本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出版盛极一时,而神魔小说则陷入了低谷。
在这种情况下,神魔小说若想继续招徕读者,就势必要改变一味谈魔说怪的创作老路,或另辟蹊径向荒诞寓意的创作路子上走,或朝着文体兼容化的方向发展。明末清初,一些文人就有意本着“灭心中魔”的理念,以寓言之法创作神魔小说,并力求“幻中有趣”,以吸引读者。如潘镜若即说他之所以要在小说中“杂以诙谐谑浪,非故怪诞支离,以伤雅道”,而是怕“执经义示人,召其盹睡”。[10](P6-7)方汝浩作《东度记》也是考虑“世多好奇信诞,故于深言处,设为浅诞”。[12]清初,刘璋作《斩鬼传》,“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3](P156)并“用夸张手法逞其诙谐”,[13](P59)可谓别开生面。在其影响下,清中叶产生了《平鬼传》、《何典》、《常言道》、《精神降鬼传》和《回头传》等一批寓意类小说,这些小说“盖寒士不得志者所作,故托以鬼语,骂尽世人”,[14](P159)其编创特点是假托殊方鬼域故事,讽世寓理,可是作法雷同,又“词意浅露,已如漫骂”,[3](P156)爱用方言,故它们虽可得到部分文人的欣赏,却不易为读者大众所接受。
于是,有些编创者遂改走文体兼容化的创作道路,或附会历史,杂糅战争,或涉笔世情,影射现实。本来,神魔小说与讲史就有较密切的渊源关系;神魔小说在将神魔之争世俗化时,也必然会涉笔世态人情,因此神魔小说融汇历史演义与世情小说的创作因子,丰富自身的审美内涵,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如《走马春秋》和《锋剑春秋》,即以战国纷争为背景,或演乐毅伐齐,或写孙膑与秦军斗法破阵,虽侈谈神怪,荒诞无稽,但主要人物孙膑、乐毅等则实有其人,乐毅伐齐亦于史有征。又如《希夷梦》,通篇演述梦境,抒写感慨,人物和情节多为任意编撰,但作品首尾又点染赵匡胤陈桥兵变、陆秀夫背负幼君投海等史实,以櫽栝宋代三百年之兴亡。《平鬼传》还有意仿效历史演义中的战阵、攻城等写法,来演绎神魔之争。《绿野仙踪》叙写冷于冰求仙访道、除恶济弱的经历,也是既涉笔明嘉靖年间的忠奸斗争,又时常摹绘世态人情,诸如官场之窳败、吏役之凶残、纨绔之纵欲、妓女之矫情、腐儒之迂鄙、帮闲之鬼蜮、市井细民之困窘等,都写得活灵活现,故鲁迅称此书“盖神怪小说而点缀以历史者也。其叙神仙之变化飞升,多未经人道语;而以大盗、市侩、浪子、猿狐为道器,其愤尤深也”。[15](P121)
总而言之,神魔小说是在《西游记》确立的编创方式的影响下,经由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的模仿、炮制,迅速走向繁荣的;接着,又是在小说评点者的引导下,在心学思潮的濡染下,继承和发展了《西游记》寓言讽世的创作手法;此后,又由于其他类型小说的勃兴、时势的变迁、读者阅读需求和审美口味的转移,促使神魔小说或向荒诞寓意的创作路子上拓进,或朝着与世情小说、历史演义合流的方向蜕变。可见,经典作品的示范、书坊主的运作、评点者的引导、读者的制约等,的确从不同方面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因此,只有把这些影响因子都纳入到对神魔小说编创方式的考察之中,才能对神魔小说的编创方式及其演变作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