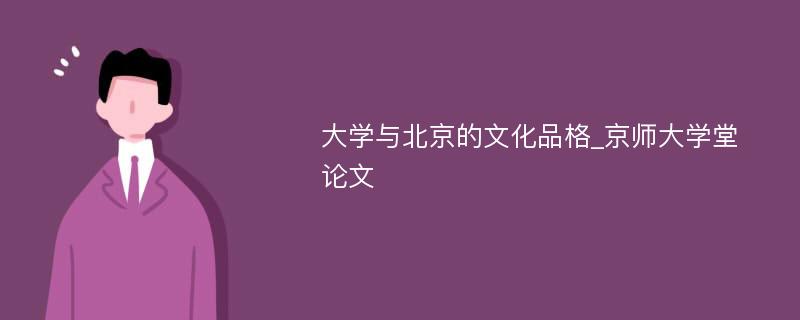
大学与北京的文化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格论文,北京论文,文化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7)06-0099-08
城市的文化品格,是指城市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凝结而成的,反映其理想目标、精神信念、文化底蕴、审美情趣、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的价值观念体系和群体意识。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在其漫长的城市文化发展史中,有两个“三分之一”尤其值得关注。其一,北京近三千年的建城史中,有近三分之一即近九百年时间是作为中国的“首善之区”存在的。从世界文化的发展规律来看,“首善之区的文化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需要的影响,但首都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却是以文化为根基的” [1]。其二,中国自太学创立以来两千余年的高等教育史中,亦有三分之一即约七百年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而从教育文化的发展规律来看,“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2](P3118-3119),“首善之区”至高无上的文化地位,恰恰是以其在教育方面的先导性和辐射性为前提的。可见,“首善之区”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以先进的“首善文化”为基础;而先进的“首善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又必须以先进的教育,尤其是居于教育链顶端的高等教育的进步为前提。
因此,所谓北京的文化品格,就是一种以发达的高等教育为首要标志的“首善文化”的品格。那么,何谓“首善文化”?“首善”一词最早出自《史记·儒林列传》:“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2](P3118-3119)意谓实施教化自京师开始,京师为教化的起点和先导。大约从宋朝起,“首善”一词被用来专指国都,意思是国都文化水平最高,是全国的楷模[3]。而今,“首善之区”的功能定位早已不可与古代同日而语。党中央已经提出,要求北京努力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各个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前不久在北京市第十次党代会上,刘淇书记也在会议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力办好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开创首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新局面,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繁荣、文明、和谐、宜居的首善之区。”①可见,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对“首善文化”的含义起码应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作为与“首善政治”、“首善经济”、“首善社会”相平行的一个方面,对首都其他几个方面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和支撑作用;二是作为文化发展的排头兵,对全国文化发展的示范和辐射作用更胜以往。
北京的“首善文化”品格,具体表现出以下特征:其一,经世性。北京文化被赋予了一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从国家民族利益着眼,不拘眼前小利,雍容大度,志向高远,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为特征的经世性格,这也正是北京文化显著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之处。其二,先导性。就梁启超所提出的文化三层次,即器物——制度——伦理三者而言,相对于上海、广州等另外一些以“开风气之先”而闻名的城市,北京在衣食住行等“器物”的层面上,算不上是一个“时髦”的城市;它对文化的引领,更多地表现为在制度和伦理等更深层面上的思考和变革。其三,包容性。北京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的、多元文化荟萃的中心,近代以来,更成为中外文化对话、融合的重要平台。
近几年来,随着北京市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成功,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开始,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各项工作的全面展开,以及“国家首都、历史名城、世界城市、宜居城市”发展定位的确立,学界对于北京“首善文化”的讨论日趋热烈②。但迄今为止,关于大学与北京文化品格的关系,尚未见有专文论述。而这方面的讨论显然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因为,在北京文化“首善”品格的形成过程中,大学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是促使其内涵不断变化、丰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主导性因素。
一、古代大学与北京“首善文化”品格的形成
其实“首善之区”高等教育的重要作用,很早即为统治者所高度关注。西汉元狩元年(前124),汉武帝在董仲舒及丞相公孙弘的建议下,建太学于京师,并创立博士弟子员(太学学生)制度,是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开端。而就在太学创立的同时,董仲舒便在《对贤良策》中提出:“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4](P140)也就是说,太学是封建王朝培养“贤士”的最高教育机构,而“贤士”的培养,又关系国家教化的本原。其后至隋代炀帝时期,改设太学为国子监,名称虽有变化,其培养士人、教化天下之宗旨则一脉相承。
元大德十年(1306),北京于安定门内成贤街(后改名国子监街)建成国子监,这是北京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它的建立,奠定了北京文化“首善”地位的基础。之后,历元、明、清三代,国子监的教化意义被封建统治者一再强调,北京“首善文化”的至尊地位也从而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康熙八年,敕谕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官曰:“朕惟圣人之道高明广大昭垂万世,所以兴道致治敦伦善俗莫能外也。朕缵承丕业文治诞敷景仰先哲至德,今行辟雍释奠之典,将以鼓舞人才,宣布教化。”[5](P255)康熙四十一年,上谕礼部:“训饬士子文,若令各府州县学宫一体勒石,恐有不产石州县地方,或致借端扰派,应俟国子监勒石后,以撰本典颁各省转发所属学官,一体遵行。”[6](P261)同治元年年底,清政府再次下诏敦促国子监祭酒、各省学政切实讲明正学,端正士风:“太学为自古培植人材之地,我朝振兴庠序,加意教习,世宗宪皇帝赏给库银,增置黉舍,首善之区,四方观瞻所系,必得如唐之韩愈、宋之胡瑗,躬行实践,讲明正学,以为表率,人材自能蒸蒸日上。” [7](P147)上述一系列煌煌上谕,一方面突出了国子监“兴道致治敦伦善俗”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四方观瞻所系”的特殊地位。而从传统教育的宗旨和传统士大夫的价值取向来看,北京作为“首善之区”的教化功能的不断强化,无疑对其基本文化品格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其一,古之“贤士”,素以“经世济国”为己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8](P527)“齐家、治国、平天下”,“致天下于大治”,“厝天下于衽席之上”正是传统士人的最高理想。北京“经世”品格的形成,显然与此不无关系。以嘉道年间存在于京师宣南、以汉族士大夫文人集团为主体的“宣南诗社”为例,其中便不乏太学出身的成员。他们初以“消夏”为名聚集在一起,“或春秋佳日,或长夏无事,亦相与命俦啸侣,陶咏终夕,不独消寒也。尊酒流连,谈剧间作,时复商榷古今,上下其议论,足以启神智而扩见闻,并不独诗也。”[9](P53)其明为以诗会友,实则以经世济国之论相交流,正是北京经世品格的体现。惟其如此,在嘉道之际,“宣南诗社”成员广受重用③。
其二,“京师为首善之地,太学为育才之所”[10](P8563),为师者“必得如唐之韩愈、宋之胡瑗”之才[7](P147),就学者必以“兴道致治敦伦善俗”为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上也力求完备、先进,而不像其他学校参差不齐。因此,太学或国子监本身即是“首善之区”文化“先导性”的重要保证。
其三,太学学生的招收范围至为广泛,并不局限于北京一地,甚至不局限于繁华地区,而是及于居处偏远的“荒裔殊族”。据载,“世祖定鼎之初,即仿古太学之遗意设立国子监,俾八旗子弟与直省贡监生得从容肄业,其中而以祭酒司业等统率之。当是时,郁郁者文,彬彬者士。甚至荒裔殊族亦向风慕义,率其子弟来读我太学书者。呜呼!岂不盛与?”[10](P8555)太学学生来源的广泛,不仅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更从文化层面上提升了北京的“包容”品格。
二、近现代大学与北京“首善文化”品格的升华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奇变”,国子监作为国家教育管理最高行政机构和国家最高学府的地位,被作为近代高等教育源头的京师大学堂所取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清政府诏定国是,谕:“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奋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势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行省倡,尤应首先举办。”[11](P922)从而拉开了“戊戌维新”的序幕。尽管这场维新昙花一现,维新期间推出的一系列变革措施也未及实行便化为泡影,但值得庆幸的是,京师大学堂得以硕果仅存。而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恰恰昭示了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就其象征意义而言,京师大学堂的出现,体现了清政府以学术风气的转移和教育制度的革新为主导的变革思路,这不仅适用于北京,且适用于全国;既凸显了文化本身的使命感,又强化了北京“首善文化”的中心地位。其二,就其实际意义而言,京师大学堂不仅“为行省倡”,而且“以建首善而观万国”[12](P307),这意味着,北京的大学及其引领的北京文化不仅应该走在全国的前列,而且应走在世界的前列。而突破“华夷之辨”,“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宽阔文化视野使北京的“首善文化”品格得到了空前升华。
进而至“五四”以后,随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精神的逐步形成,北京的“首善文化”品格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所谓现代“大学精神”,是“一种非实体性的精神文化”[13](P8)。它通常被放在两个层面上加以讨论:一是宏观的层面,如有人认为大学精神“应该是大学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和文明成果”,“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14];二是微观的层面,即“大学精神是在某种大学理念的支配下,经过所有大学人的努力,长期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14],它以个体作为讨论对象,如“北大精神”、“清华精神”、“辅仁精神”、“联大精神”等。本文所着重探讨的,则是由北京地区诸大学率先倡导,并对中国现代大学的整体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精神和理念。
正如有的论者指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15](P4)由于中国近现代大学是以对传统教育制度的批判和破坏为出发点,在移植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它在形式与教学内容、方法、手段上与古之太学已截然不同,精神核心也迥然相异。从这一意义来讲,近现代大学的建立对北京的“首善文化”具有“涤荡”的意义。然而,正如近现代以来对中西文化、“新”“旧”文化持续不断的讨论一样,现代大学的文化精神亦不可能与传统决然断裂,而是隐然渗透了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这种“西化”趋势下隐而不彰的中西会通,集中表现为现代大学精神对北京“首善文化”品格的进一步升华。
第一,作为古代大学向近代大学过渡的内在动力,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忧天下的社会关怀被现代的大学知识分子演绎成了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北京文化之“经世性”由此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
作为发轫于首善之区的中国第一所国立现代大学,京师大学堂以“发奋为雄”、“通达济变”[16](P700)为宗旨,不仅继承了古代士人“经世济国”的传统,更承戊戌维新“救国在学”之余绪,加以发扬光大。
此后,随着现代大学在全国各地纷纷涌现,延续传统士人人格理想、重塑社会文化中坚成为现代教育家群体的共识。诚如杨东平先生指出,“当封建正统文化崩解、新的民族文化尚待建立之时,他们(现代教育家群体)的一个共同追求,是继承儒家文化中培养君子、士的人格理想,使之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养成衔接。”[17](P4)在此追求的观照下,北京的大学教育与政治之间,似乎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一方面,强调大学为研究学问之机关,应以服务社会为职志,避免成为政治的附庸。如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之后,不仅以“自此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历千百年之大计”[18](P28)自勉,而且在就职演说中,明确主张学生进大学不当“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有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同时“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18](P50);北高师校长陈宝泉先生则提出,“夫学校用以改良社会者,是学校为社会设,非学校为学校设也”[19](P48),“学校为社会而设置者也,学生则社会服务者之预备员也”[19](P38)。另一方面,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大学又屡屡在爱国救亡运动中冲锋陷阵,成为时局的焦点。1919年5月4日,北大、北京高师等13所大学师生参与到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中,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1935年12月9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北平爱国学生群情激昂,清华、燕京等学校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组织下,冲破国民党政府沿街设置的封锁线,聚集新华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1947年,在清华大学带动下,北平学生分赴市区向各界群众宣传反饥饿、反内战,并组织了北平、天津等地大、中学校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万人大游行。
事实上,从“经世济国”的角度来看,二者非但不相矛盾,而且高度统一。因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救国图存恰恰是知识分子社会责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怪乎清华大学校长潘光旦先生在1944年撰文写道:“一个人有做人的身份,就是他有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的权责。一个人也有国民的身份,就是他对他的政治团体也有一些不可分离的权责。一个人有他专业的身份,就是他有学术家、教育家、店员、匠人……一类的权责。任何人有做人、做国民、做一种专业的身份与权责,而做人与做国民的比起做专业的来更要先决,更要基本。没有做一个完整的人的意识的专家,无论他的专业如何精深,他终究是一个匠人,学术家也罢,泥水匠也罢。没有政治意识的专门人才,可以加入伪北京大学,可以到沦陷区做顺民,而无害其为专门人才,学术家也罢,泥水匠也罢。”[18](P125)
第二,作为文化的引领者,北京的现代大学不仅从西方引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内容,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为保持北京文化的先导性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
如: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仅倡导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机关,而且要求师生在研究中运用科学方法,获得创新成果。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是以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者也,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虽曰……苟吾人不以此自馁,利用此简单之设备,短少之时间,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许之新意,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18](P3)此外,他还首先提出了教授治校的原则。清华校长梅贻琦则是通才教育的力倡者。他借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语,详细阐释了“通才教育”的内涵。他认为,大学的各种课程乃至课程之外的学校生活、课外活动,均与明明德、新民密切相关:“大学课程之设备,即属于教务范围之种种,下至基本学术之传授,上至专门科目之研究,故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课程以外之学校生活,即属于训导范围之种种,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至若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程之设置,学生课外之团体活动,以及师长以公民之资格对一般社会所有之努力,或为一种知识之准备,或为一种实地工作之预习,或为一种风声之树立,青年一旦学成离校,而于社会有所贡献,要亦不能不资此数者为一部分之挹注。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18](P47)正是在这样一些理念的指导下,北大、清华先后对学科、课程设置等进行调整,其他大学也纷纷效仿,一时间,学术自由的风气弥漫于北京各个大学。而上述先进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基础,并预示着其基本走向,直至今天,依然对北京乃至全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宝贵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第三,北京的现代大学既体现了海纳百川的人文胸怀,又反映出学贯中西的文化视野,由此使北京文化的包容性放射出前所未有的光彩。
一方面,从北京各大学的机制来看,“包容”无处不在: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各大学教师的背景和来源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以北大为例,蔡元培任校长时期,先后聘请来校任教的大师,既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也有实用主义的拥护者胡适;既有主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钱玄同、刘半农,也有宣扬国故、反对革新的复古主义者刘师培、辜鸿铭;还有来自美国的著名学者杜威等。以听众而论,各校上课无论是否本校注册之正式生,愿听即入。此风不仅传为美谈,也演为传统。另外,在社会进步舆论和蔡元培的支持下,从1920年新学期开始,王兰、邓春兰等九名女生进入北京大学旁听。1920年寒假后,北京大学正式招收女学生。是为男女同校的开始。
另一方面,北京的大学在文化视野上无疑是开阔的。这种开阔,主要与以下原因有关:第一,近代大学是中西文化会通的产物。甲午一役,创巨痛深。正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20](P113)而梦醒之后,先进的知识分子不仅认识到学习西方文化的迫切:“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21](P479)而且将强国强种的首要之务,确定为开办学堂,引进西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他指出:“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日后分科设教,及推广各省,一切均应抱定此意,千变万化,语不离宗。”[22](P426)其后在朝廷下令正式开办京师大学堂的上谕中,也强调了“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势者,实力讲求”的宗旨。相对于京师大学堂的开办,清华有着另外一种中西文化会通的背景。作为美国用中国庚子赔款建立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清华早期的学生一方面感受的是切身的民族耻辱,体会到中国之不如人,“知耻而后勇”;另一方面又更多地接触西方文化,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第二,近代首都的大学首批校长及教师大多有着融贯中西的文化背景。如 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曾以翰林编修的背景前往德法两国留学;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文学院长的陈独秀,不仅在清代获得举人地位,而且后来留学日本及法国,由之揭帜的新文化运动宣扬“德先生”和“赛先生”,与这一背景不无关系;在北京各高校兼课的鲁迅,早年留学日本学医,受到落后挨打的触动,转而回国并成为批判传统文化的斗士;马克思主义的首位推介者李大钊,早年留学早稻田大学,并对“集合中外思想予以裁剪选择,构成他自己的一种系统”[23](P275);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健将胡适,留美回国执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第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坚信,中西文化的汇通交融,必能促进文化的进步和更新。蔡元培在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演说《东西文化结合》时即指出:历史上,例如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受了阿拉伯与中国文化的影响,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而近代,西方的著名思想家,“几乎没有不受东方哲学的影响的”[24](P51);东方诸民族也都在努力地学习借鉴西方文化。胡适也不止一次地说道中国因吸收印度佛教文化而促成宋代理学的昌盛,他坚信,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结果,也必然促成中国新文化的诞生。第四,北京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将其置于推动中西文化汇通的前沿。北京是“首善之区”,是“文化之都”,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首当其冲承担着展示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与世界各种先进文化对话的神圣使命,而作为文化的代言者,坐落在这里的大学,必须具备宽阔的、国际化的视野。
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才资源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的形势下,作为教育链的顶点、新知识的提供者和新技术的传播者,大学对北京文化品格的影响也将更为重要。
三、大学在21世纪北京“首善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洛韦尔说过:“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受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④大学是“立学、立人、立国”的根基,“首善之区”的大学又是“首善文化”的本原(“太学者,教化之本原也”)和主流(现代大学精神),因此,在21世纪,北京的大学必然继续在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别是“首善文化”品格的塑造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一,塑造城市人文品格,既是北京当下构建“文化名城”的题中首要之义,又凸显了“首善文化”经世性的时代内涵。而大学在21世纪北京人文品格的塑造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正式将“文化名城”列为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之一。作为一座历史名城特别是古代名都,北京显然无愧于这一称号。而作为一座现代化的文化名城,其核心的要件就是城市独具的人文品格。故此,在21世纪,大学对北京“首善文化”之“经世性”内涵的提升,首先就表现在对其人文品格的提升。
所谓城市的人文品格,是一个城市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积淀下来的文化精髓,它展现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是城市深层内涵的集中体现。大学作为北京人文品格的重要载体和塑造者,对后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
一是通过对城市人文价值与人文内涵的探讨。如美国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认为:“一所大学如果不能在各个重要的学科领域都竭尽全力,包括对于探究人文价值,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等多种社会形态以及人类传统、文化和世界观起核心作用的人文学科领域,它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所杰出的大学”⑤。
二是通过对每个人人格的完善。人文教育以完善人格为目的,“大学教育的杰出性是无法用美元和人民币来衡量的。最好的教育不仅使我们在自己的专业中提高生产力,而是(且)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25](P20)
第二,创新是推进城市文化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更是保持“首善文化”先导性的必要条件。在 21世纪,大学将成为北京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决策。与之相适应,北京颁布了《“十一五”时期科技发展与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制定了到2010年将北京初步建成创新型城市的发展目标。“创新型城市”着眼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培养城市的创新品格。这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创新要素发挥核心作用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际化大都市城市功能与定位的必然趋向。
“创新”是21世纪保持“首善文化”先导性的首要条件,而要建设创新型城市和培养城市的创新品格,人才是关键因素。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大学教育又是核心和关键环节。因此,要保持城市文化的先导性,首先需要发挥大学的先导性。发挥大学的先导性与北京创新型城市的建设之间,是高度一致、彼此促进、互为条件的。
一方面现代大学的根本使命,乃在于研究学问、发展知识、追求真理,培养不仅具有责任心,更具有创新精神和开拓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大学的不断创新本身就是北京创新型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以知识为主要增长要素的创新型城市的构建,不可能离开大学的不断创新。反过来,大学的创新又必然会带动科技、文化等多领域的创新,从而提高北京的综合创新指数,进而凸显北京“首善文化”的先导性。
另一方面,从北京的示范和辐射效应来看,北京地区的大学创新将有力地带动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大学创新,大大加速全国范围内知识存量转化为创新优势、创新优势进而转化为竞争优势的步伐;与之同步,保持首都作为全国创新中心和先导性创新城市的地位,也将对全国的城市创新起到更强大的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从而使我国的大学和城市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面前,居于更具竞争力的位置。
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不断加强,“首善文化”的“包容性”将在首都“世界城市”的建设中体现得更加突出。而首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将成为“世界城市”的重要窗口和“首善文化”包容性的生动缩影。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在文化上的成就,相对于经济和政治而言,往往具有更持久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随着世界日益变小,各国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已变得越来越方便。这使得世界上的各所大学能够彼此共享资源、相互学习和相互帮助。在空前的竞争和合作面前,对不同文化的包容不仅能赢得对手和合作伙伴的尊重,更能使自身占尽先机。
“走向世界”是全球化时代大学的必然发展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网络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新一轮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浪潮。广泛开展大学之间的国际合作,是21世纪大学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大学应该更加自觉地面向世界,具有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在推动不同文化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融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北京各大学正致力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在新颁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也明确提出了“世界城市”的发展定位。无论是北京的大学,还是北京这个城市本身,都面临着国际化、世界化的机遇和挑战。大学作为北京国际化的前沿和窗口,担负的使命尤为艰巨;同时作为北京“首善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大学也将对“首善文化”的包容性品格作出更加令人信服的诠释。
[收稿日期]2007-08-16
注释:
①参见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06news/china/c/20070517/ula2838029.html。
②如许嘉璐:《首善之区需要首善文化》、郑师渠:《首善之区与北京文化建设》二文对此皆有专论,均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③据有关学者统计,嘉道时期“宣南诗社”成员中受重用者,全国共有总督八人,巡抚十三至十五人。督、抚之下,全国还设布政使二十人,按察使十八人,各省道员的名额,共有守道二十人,巡道七十二人,另有津海关道一人。此外,全国还设学政二十人,漕运总督一人,河道总督三人。参见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④转引自张文斌:《大学的世界品格与大学生人格塑造》,《思想教育研究》2006年第11期。
⑤转引自汪银生:《论一流大学的文化品格》,《科学时报》2006年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