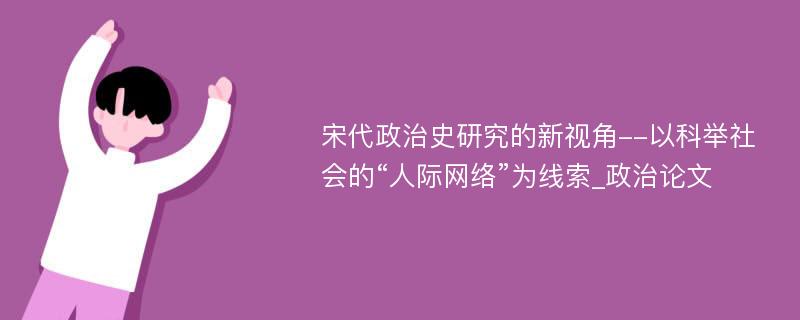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以科举社会的“人际网络”为线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宋代论文,线索论文,人际论文,新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潮流 在现今的宋代政治史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股潮流。第一股潮流是“新史料”的发掘与史料的活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明版《名公书判清明集》的发现,以法制史、社会史为中心,大量的新知识、新见解层出不穷。而至近年《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发现,也预示着宋代官僚制度的相关研究将出现更新的可能性。然而,这样的新史料发掘就宋代史研究而言是十分稀有的事例。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努力的方向应该是,重新审视以往的政治史研究中未能充分利用的史料,关注如何对之进行解读以及灵活运用的课题。第二股潮流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开拓。如今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对象超越了至今为止以政治制度史、政治事件史为中心的范畴,并不断地扩大,包含了如以国际秩序和外交等作为对象的国际政治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史、地方政治史、政治文化史、政治集团史(或称人际网络)、思想·美术·医学·文学等与政治史相关联的讨论方向、由政治地理的观念展开的研究等等。这种现象本身应该是值得认可的,但同时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开拓也必须成为重要的课题。近年,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优秀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并被视为宋代政治史研究新趋向的先兆。然而,政治文化是什么?要怎样研究政治文化?这样的根本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方向,结果导致“政治文化”一词在研究中的滥用。而且,政治文化史研究本身的研究对象是相当广泛的,如象征、仪礼、政治传统、日常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生活等,我们有必要从更加广阔的视野中考察政治文化问题。对于政治文化史的概念,阿河雄二郎在《イメ一ヅと心性の政治文化史》一文中指出:“政治文化论考察的对象不是政治制度或政治思想等硬件方面,而是面向人们日常就在经历的政治生活以及作为其背景隐藏的无意识的信条、象征、价值观等软件方面的内容,并且通过与其他地域进行的比较研究,从总体上探讨‘政治指向’的问题,进而摸索对更为深奥的文化内涵的理解。”(竹冈敬温、川北稔编:《社会史ヘの途》,东京:有斐阁1995年版)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具体地实践第一、第二两个方向的课题研究呢?以下将围绕“宋代科举社会的‘人际网络’”问题,谈一谈我的观点与做法。 二 宋代科举社会史研究的视角 作为把握宋代社会的指标,许多学者使用了“科举社会”一词。如近年出版了《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研究》的作者近藤一成关注科举所具有的“社会流动性”和“社会再生产机能”,指出“科举被列入传统社会体制的再生产系统之中,故称之为科举社会”(近藤一成:《宋代中国科举社会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9年版,第4页)。我也认为在把握宋代以降的社会时,“科举社会”这个概念是极为有效的。不过,必须注意“科举社会”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在把握这一社会时,什么样的研究视角才是有效的。 在把握科举社会时,我想先对两种看法进行一番整理。其一是科举促进“社会流动性”的看法。宋代的科举考试和现代的考试一样,以客观性和公平性为宗旨,通过书面考试来决定合格与否。禁止唐代“行卷”、“公卷”等考试前的私下准备活动,施行“糊名”、“誊录”等严格的考试体制,除此之外,基本上向全民开放考试资格,中式之后即可获得官员身份(荒木敏一:《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69年版)。一般说来,成为官员之后,在户籍上被编入“官户”,不同于一般庶民的“编户”,获得税役和刑法上的优免特权。但是,这种特权只能延续三代,如果其间未能产生后续的官员,其家族则会遭遇没落的危机。另一方面,即使是庶民阶层,只要科举合格的话,就可以上升为被称为士大夫的上层阶层,科举具有产生身份阶层的社会流动性功能。何炳棣是这种学说的代表性学者[参见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他通过调查大量的明清时代的登科录,论证了明清时代因科举而产生的社会流动性极高。社会的流动性不单是指上述地位、阶层之类的流动性,还有由科举带来的空间的流动性。魏峰的《宋代迁徙官僚家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说明了科举作为一种媒介,促成了人群向科举考试相对容易合格的地域流动。但是,也存在着与此不同的看法。其二是高度评价科举所具有的“再生产体系”的功能。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具备几种条件。在没有义务教育的时代,受教育本身要比今天来得困难,为此要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而且还有如何筹措参加考试的旅费、住宿费等问题。此外,家庭教育环境左右科举合格与否的可能性也很高。虽然和科举不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运用“文化资本”、“语言资本”、“社会关系资本”等新概念,对现代法国的社会阶层再生产结构进行了阐释(参见布尔迪厄和让——克劳德·巴塞朗合著的《再生产:教育、社会、文化》,东京:藤原书店1991年版)。本杰明·A·艾尔曼(Benjamin A.Elman)把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巧妙地运用于科举之中,主张科举是“再生产忠于皇帝的官僚的政治性再生产装置”,是“再生产士大夫阶层的社会性再生产装置”,是“再生产士大夫文化的文化性再生产装置”,作为“再生产体系”而发挥功能[本杰明·A·艾尔曼著,秦玲子译:《再生产装置としての明清期の科举》,《思想》第810号,1991年。不过,这种看法是不是艾尔曼的独创性看法,稍微有些问题。类似的看法已经在宫崎市定的《科举》(东京:秋田屋1946年版)中得到说明。此外,对于艾尔曼后来出版的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平田昌司在2002年撰写的书评(《东洋史研究》卷61第2期)中指出,该书在以官话为线索论述语言资本的再生产等方面存在着错误]。究竟能否将科举视为这样的“再生产装置”,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讨论[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刘祥光在《宋代的时文刊本与考试文化》(《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5期,2011年)中予以了介绍;艾尔曼运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通过“规训(discipline)场”进行运作的权力论,试图发现科举的这种机能]。虽然尚有讨论的余地,但是被称为“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宋代明州史氏一族这样的事例,亦是不争之事实。而且,在科举合格者较多的地域,同时也是考官辈出,冈元司曾在《南宋科举の试官をめぐる地域性——浙东出身者の位置を中心に》(《宋代社会のネツトヮ一タ》,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版)中,对由此看出的考生和考官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进行了量化分析。 我觉得科举确实产生了身份阶层乃至空间的社会流动,作为“再生产装置”的科举对宋代社会也发挥了很大的功能,这也是事实。若视之为一种“系统”,那么解析“科举社会”的关键,就取决于系统背后的社会构造和网络可以获得多大程度的阐明。此外,再回到科举社会的问题,前引近藤一成的著作把宋代的解额视为揭示科举社会的重要关键,科举考试本身与当时的户籍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于是,为了有利的考点而冒充户籍的“冒籍”现象频繁出现于宋代的科举相关文献之中,显示出考试和户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绵延久远。 三 宋代科举社会的系统、网络与空间 接下来,我想简单说明一下使用“网络论”的观点分析社会结合的理由。关于前近代中国社会的社会结合问题,已经有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其中我比较关注的是中国史研究会提出的“法共同体不存在”论。简而言之,就是虽然在中国专制国家之下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结合,但是不存在具备法的主体性的共同体。中国史研究会的研究者根据二战之前“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法制史研究者的见解,展开了这样的讨论。近年出版的伊藤正彦《宋元乡村社会史论——明初里甲制体制の形成过程》(东京:汲古书院2010年版)一书,阐明了以义役为中心的宋元社会组织结构产生出明初的里甲体制,指出义役是“建立在在野读书人阶层的各种活动以及州县官参预的基础上,以农民的赞同并集结起来的形式而结成的”。总而言之,他主张在前近代中国社会,不存在西方封建社会的行会组织和城市共同体,或者绝对王政时代的社团以及日本村落社会中所能见到的自律性共同体,在结构上由读书人阶层和官府不断地重组社会。 如果中国不存在西欧和日本那样的法共同体,那么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共同关系,且如何运作社会呢? 我想用本文所运用的网络这个方法论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正如社会学所用网络概念的定义那样,是“复数的‘物’以具有一定程度持续性的某种关系为基础,形成了某种统一”(金子郁容:《ネツトヮ一キソゲヘの招待》,东京:中公新书1986年版),是不限于组织性和制度性的把握各种社会关系的用语,而作为方法概念使用的网络被认为是“决定行为者之行为的重要因素,是围绕着该行为者的网络”(安田雪:《ネツトヮ一ク分析 何が行為を決定すゐか》,东京:新曜社1997年版),摆脱了重视个体资质和能力的属性主义,认为决定行为的是围绕着行为者的关系结构。例如,一直以来,前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史屡屡被看作是朋党对立、抗争的历史。虽然这个理解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诸如“朋党究竟是什么”这样根本的问题却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考察。根据对朋党史料的分析,在批判、弹劾对手的时候,文献中经常使用“某人是某人的朋党”的表达,但是“朋党”是否实际存在?举一个例子,苏轼本人就一直否认“蜀党”的存在。还有,在概括某个政治集团的时候,受到后世见解的影响,我们较多地使用“新党”、“旧党”等名词来称呼它们,然而我们首先应该留意并且厘清的是当时的史料用语如“王安石党”、“刘挚党”等称呼的实质内情。其次要考察的是一直以来对朋党的理解。例如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の意义》“朋党性质的变化”一节,指出了以婚姻和亲戚关系为基轴构成的唐代朋党向以政治上的主义、学问上的出身关系为基轴构成的宋代朋党的转变,从重视“家世”、“婚姻”、“学问”等个别的资质与能力的属性主义立场来分析朋党的形成。但是,我在宋代朋党的实际研究中发现,与血缘、地缘关系相关的因素非常多,而相对正确的做法是,在对个案的网络进行详细、彻底的调查之上,进一步归纳该网络的特性。 运用网络论作为社会结构的分析手法,经常见于东南亚和西南亚研究之中。因为这些社会被认为相对于“组织”和“制度”而言,更重视“网络”[关本照夫:《二者関係ネツトヮ一ク論再考——東南アジアの事例》,《中国—社会と文化》第6号,东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1991年版。关于社会结合中的“组织”性问题,参见中根千枝《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単一社会の理論》(东京:讲谈社现代新书1967年版)]。关于前近代中国社会,以“社”、“结社”、“诗社”等所谓“社群”为线索进行分析,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方向。但是,在探讨宋代的科举社会时,尽管能够看到“义学”、“义塾”、“义庄”等以血缘联结的关系,或者“乡曲义田”、“贡士庄”等以地缘联结的关系,但只是一些断片式的情况,难以找到支持整个系统的明确的共同关系。因此,本文试图从网络的观点,考察当时的社会结合究竟为何物。 不过,本文并非一篇史实论证式的文章,我在这里要描画的是思考的过程。迄今为止,我与日本的宋史研究者设立过不少共同的研究计划,并有数本著作作为其成果刊行,其中之一就是《宋代社会のネツトヮ一ク》(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版)。该书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不同侧面切入,阐明了作为“软结构”的中国网络社会的各种面相。然而,该书的研究缺乏对网络背后存在的空间,或者说是令网络发挥功能的秩序的探讨,为此我们又编纂了《宋代社会の空間とコミュニヶ一ション》(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版)一书,其中对“空间”的概念进行了如下定义:人们活动的空间不单是指物理性的空间,当然它也是由人们创造出来的,在经过各种各样的联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交流过程以后,这个空间逐渐衍生出政治的、社会的秩序等所谓社会的构造。这里可以参考近年在历史研究中被大量使用的“空间论”[如日本史研究者仁木宏的《空間·公·共同体——中世都市から近世都市ヘ》(东京:青木书店1997年版)、包弼德(Peter K.Bol)的《地域史と後期帝政国家につぃて——金華の埸合——》(《中国—社会と文化》第20号,东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2005年版)等著作。后者提出“space"和“place”应该区别考虑]。要而言之,该理论所着意的空间(place),并非所谓的物理性空间(space),而是拥有区别于其他空间(space)的明确领域,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其关系孕育出来的社会秩序、文化、学问等各种各样内容的空间(place)。不过,这个阶段的认识仍有不足。近年我参加的中国近现代都市史学会的学者们提出了以下观点。都市研究的方向,是对拥有独特的地理性环境以及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关系的空间体如何通过系统和网络被构筑的过程进行了透彻分析。也就是说,都市研究采取的思路是,对系统、空间、网络等复合式要素进行分析综合,逐渐呈现出都市的实际形态(叶文心:《系统与网络:城市研究的几个思考》,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近代东亚城市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网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2年7月)。这是都市分析的指标,同样也可以作为社会分析的指标。我从中得到的启发是,社会构造自身也具有从系统、空间、网络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的可能性。 以这三个角度为指标可以对“宋代的科举社会”进行怎样的分析呢?下面要谈的是我个人的一些理解和方法。 1.宋代科举社会的系统 如前所述,科举既有促进身份阶层、空间两方面变化的“社会流动性”的一面,又有促进政治、社会、文化方面再生产的“再生产体系”的一面。其关键角色就是“解额”,也可以说是户籍和考试融合的制度。以往我在考察“宋代科举社会”的构造时,科举及其延伸出来的官界网络问题也被同时提出。当时曾得出如下结论:生活在以科举—官僚制为核心的政治世界的士大夫,为了获得晋升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荐举”,一方面在自己所处的地缘、血缘、学缘、业缘(同官、同僚等相同职业种类的连带关系)等各种关系——各种“同”缘之中,不但有“同学”、“同舍”、“同年”、“同乡”、“同姓”、“同官”,还包括“座主门生”、“师弟”、“上司、部下”等关系——的主体中进行选择,另一方面又被卷入到各种关系当中。然后,这些关系不断推动政治斗争和升迁竞争向着“朋党”那样的政治性的人的结合形式发展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宋代人事制度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除了累积一定的资格以外,在不断上升的阶梯中必须获取推荐者的“荐举”制度,它的重要性与科举是平行的。如是,一连串的“系统”就是宋代科举社会运作的齿轮,若不对这些系统进行解析,也就无法分析其网络问题。 2.宋代科举社会的网络 正如上文所论述的,我认为在宋代的科举社会或说是以科举—官僚制为核心的社会中,确实可能存在以由某种机缘联结起来的“同”作为纽带的社会网络。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个网络同时存在两种侧面。与日本这样一般从属于单一的“场”而且过分侧重“场”中的排列顺序的“纵”型社会相比,中国的情况则是对单一的“场”的从属性较低,而重视网络的“横”向关系的倾向更强。尽管如此,在科举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被称作“独特的纵向系列的序列主义”的独特的关系,与网络的横向关系相互交错。其一是以“天子门生”、“座主门生”为代表的皇帝与考生、考官与考生的关系[根据岸本美绪《風俗と時代観》(东京:研文出版2012年版)中《明清时代の身份感觉》一文,清朝基本政策倾向是严禁门生关系或“盟”关系等在明末士绅阶层中兴盛的模拟的血缘关系,强化皇帝与官僚之间一元的隶属关系。不过,从《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等描写科举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同年”、“门生”等关系仍然作为科举社会的中心关系发挥着它应有的影响力]。在应考的同时获得的身份(或地位)在彼此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序列意识。例如,清人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中的一节说道:“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做‘朋友’,称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进了学,不怕十几岁也称为‘老友’。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还称‘小友’。”童生被称为“小友”,而成为生员以后则称为“老友”,据描述,他们之间在席次和仪礼上都是差别对待的。随后若成了之上的举人、进士,那么身份的距离就会表现出天渊之别。这样因身份(或地位)的不同带来的关系性问题,不仅止于称呼,甚至延及衣服、居所等各个方面,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此处呈现出的一种序列主义型构造[高桥芳郎《宋代の士人身分につぃて》(京都《史林》第69卷3号,1986年)一文指出,在宋代,以科举考生和学校的学生为中心,在徭役和刑法上获得某种程度特权的“士人”阶层确立,并成为明清序列主义型构造的萌芽]。不过,与《儒林外史》的世界相比,洪迈《夷坚志》的世界中很难看到这种序列主义的构造,我认为原因之一是明清时代的科举在科举试之前设置了学校试,于是生员、举人的称谓分别成为取得学校试、科举试两个阶段合格资格的一种身份化的结果,而与这种多段结构的序列构造不同,宋代的科举制度规定,解试合格但接下来的省试不合格者,就只能重新接受解试,于是不存在解试合格者这一阶段的身份。尽管如此,网络分析仍然需要同时着眼于纵、横两个方向,而同一课题的研究也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其共同建构的关系。 3.宋代科举社会的空间 关于空间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考虑。地域社会与中央官界是两个不同的空间,考生以州学、县学或者书院、义塾等场所为基点共同进行科举考试的准备工作,逐渐形成了称为“同学”、“同舍”的关系网络。在官学里形成了地方士大夫参与的乡饮酒礼或建立先贤祠、乡贤祠祭祀乡里贤人等礼仪的空间。此外,在解试完毕之后,这里还举行为考试合格者送行的壮行会(鹿鸣宴、期集宴)。而且,令人更感兴趣的是,正如山口智哉的研究所指出的,并不单单是在同一场所学习或共同举行同一个礼仪而已,解试的合格者为了彰显解试中的“同年”关系,以“期集小录”、“乡饮小录”、“同舍小录”等形式进行书籍的印刷和出版,以便培养“同”的意识(山口智哉:《宋代“同年小録”考——“书かれたもの”によゐ共同意識の形成》,《中国—社会と文化》第17号,东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2002年版)。“同年录”中最有名的就是殿试结束之后由合格者出资出版的那种,而到了明清时代,乡试、会试、殿试不同阶段都会有同年录的制作。 阅读《夷坚志》我们可以看到,考生们一同乘船出发到京城、住宿在同一旅馆、考前时间一同度过等情形的记述。这种情况估计与当时考生求取连带保证的“保”的制度有关,但也可以看到考生们在考试之前确实有一同旅行、娱乐、饮食等机会。如此,邸店、旅馆等住宿场所,茶馆、酒店甚至京城里非常兴旺的欢乐街瓦市,还有作为信仰、文化、商业空间中心点的寺观、祠庙等,都成了考生之间交流的基点。在读《夷坚志》的时候,最常见的事例之一就是考生参拜寺观、祠庙等进行“乞梦”的记载。荣新江《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等2008年版)一文,曾意味深长地指出了如上所述都市空间的发达。初唐长安的“王府”空间在中晚唐时期被转用为寺观,以此为线索,可以看到中晚唐时期部分寺观的世俗化倾向得到加强。其一,公共的政治空间(安放皇帝图像,通过庆祝皇帝生日和国忌的祭祀活动等,担负起皇帝祭祀的一个部分);其二,公共的学术空间(唐初,在此举办译经和讲经活动,到了中晚唐时期,成了士人读书、集会、创作诗文和学术讨论的场所。同时作为藏经之地,承担起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其三,大众文化的场所(除了俗讲——僧侣以抑扬顿挫的声调通俗地解释佛典和历史故事之外,还成了戏剧、乐舞、歌唱等民间娱乐演艺活动的场所);其四,大众的娱乐空间(成了民众观看喜爱的花卉和景色,并向神佛祈祷的空间)。荣文认为,通过上述四个功能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业和消费阶层的增强,为宋代以后的近世社会充当了桥梁作用。这个公共空间论虽然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关于近代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公共圈”(可以进行交流的公共的言论空间)问题并不相同,然而在那个时代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介体,实现公共功能的空间确实变得发达,那么科举社会的网络似乎也可以看作是以那样的空间为中心而展开的。不过,围绕“公共空间”、“公共圈”的讨论仍需要考虑两个方向的可能性。其中一个方向的着眼点是如明清都市史研究所揭示的,地缘、业缘有关的会馆、公所和都市慈善机关的善堂等具体组织及其空间。而另一个方向的着眼点则是如日本中世史研究所揭示的,“建筑物”、“广场”、“道路”等在近世都市发展之前过渡性地象征“都市性”的都市场所。研究则就其场所的社会关系展开分析(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版;《中世都市研究17:都市的な埸》,东京:山川出版社2012年版)。围绕前者的“善堂”已有研究展开讨论,并试图从中考察地方自治的发达程度,像这样对“空间”论穷根究底,我们才能看到都市性空间以及以其为媒介的“公共圈”的渐次形成。在现阶段,我认为可以像荣新江的研究那样,把“公共空间”论作为前提,将宋代科举社会视作都市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从而考察它的网络与秩序等问题。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谈一下史料的问题。在进行科举社会的研究时,与“系统”紧密相连的是制度和机构,根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正史、实录类史料以及《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政书、会要类史料,我们可以获得相关部分的资料。关于“网络”,则“墓志铭”、“行状”、“神道碑”等传记史料,书信及“举状”等与推荐关系有关的资料也十分有用,某些情况下分析交际情况,还有必要留意到类似于“诗”之类的资料。而他们实际上是怎样活动、怎样交流的,我们需要结合小说、随笔、杂著等多种史料进行考察。 本文撰写的宗旨就是讨论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所谓新的观点并非全盘否定以往的一切研究,不过是进一步探求在研究中如何活用史料、如何分析问题。因此,希望大家仅将文中所谈思路与方法看作是思考如何推进政治史研究的一种提议。为了解读一个网络,不但要对该网络进行细心的分析,还要把目光放到推动网络运作的“空间”与“系统”之上,于是,经过总体的分析综合,宋代科举社会的实际形态就会慢慢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收稿日期 2013—11—20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新视野论文; 读书论文; 儒林外史论文; 夷坚志论文; 宋朝论文; 科举制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