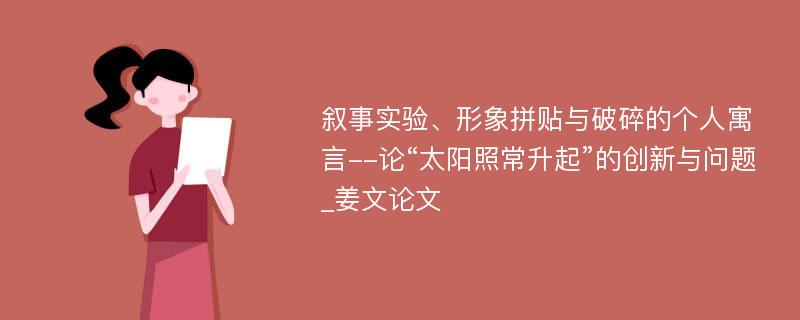
叙事实验、意象拼贴与破碎的个人化寓言——评《太阳照常升起》的创新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寓言论文,太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艺术都有一个接受或消费的问题。在严格的意义上说,缺少艺术的流通、接受、消费这一环节,艺术是不完整也是不存在的。正如萨特所言:“鞋匠可以穿上他自己刚做的鞋,如果这双鞋的尺码符合他的脚,建筑师可以住在他自己建造的房子里。然而作家却不能阅读他自己写下的东西。”具有工业生产和商品消费性质的电影何尝不是如此。因而,电影工作者创作出电影作品并不意味着艺术生产活动的完结,恰恰相反,这既是一个新的艺术创造活动的开始,也是意识、思想、价值、资本等再生产的开始。
在一定程度上看,《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偏离上述艺术常规的率性任意之作,是一次对电影生产常规的有意无意地冒犯。在我看来,对这部极为独特的电影来说,懂或不懂,或者说是否一定要把四个故事里的人物关系用一种常规的合乎世俗逻辑的方式加以勾连(甚至去猜测诸如姜文是否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以及一一破解那些琐碎密集的或有意或无意的繁琐意象之含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把这部电影置于姜文的创作,置于整个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解析,为何出现这样的电影?有什么样的个人的或集体的意识形态症候?我尤其认为,这样的电影出现在票房至上的今天,它的遭遇,它所引起的猜谜和争议的意义——可以引申出更多关于电影的艺术与工业的矛盾、作者与大众、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等电影基本问题的思考。而这样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电影本身。
一、结构与叙事:创新与局限
《太阳照常升起》最引人注目的创新在于姜文对一种他从未用过的“分段叙事”结构的运用,虽然这一结构在世界电影史上并不鲜见,但对于姜文,无疑有创新和突破意义。因为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鬼子来了》,结构都是单线的,前者是以马小军的经历和心理为核心展开故事叙事,后者更是一个完整的线性故事(整个挂甲屯的人们卷入一件突发性事件的始末)。而对《太阳照常升起》来说,是四个故事的并置。这四个故事分别是所谓的“疯”、“恋”、“枪”、“梦”,这四段都通过字幕的方式明确厘清。前三个故事发生在1976年,第四个故事则发生在1958年。
回首中外电影,不难发现,从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一种电影的“分段组合”式叙事结构蔚然成风,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电影叙事艺术新动向,经典案例包括《机遇之歌》、《薇洛尼卡的双重生活》、《情书》、《滑动门》到《低俗小说》、《暴雨将至》、《罗拉快跑》、《通天塔》等, 甚至在中国也出现了《爱情麻辣烫》、《苏州河》、《周渔的火车》、《英雄》、《孔雀》等分段叙述的“移植”或“变种”。
“叙事”是人类认识和表述世界与自身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是指在时间和因果关系上有着联系的一系列事件的叙述或者符号化再现。麦茨曾指出,电影是一种会讲故事的机器。在电影叙事形态上,分段组合叙事结构与传统的电影叙事结构有明显的差异。传统的电影叙事结构以因果律和必然律为基础,在电影叙事的形态上,具有一致性和透明性。而在分段组合的电影叙事中,结构的各个部分之间是独立的甚至是对立和互否的。所以,分段叙事结构背后的主体意识应该是以偶然、无常、悖谬、存在主义式的荒谬、荒诞,因果链条的断裂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为依托的。
《太阳照常升起》第四段既是大结局,更是大开端,显然表达了姜文对人生无常、命运偶然、存在荒谬的了悟。一边是浪漫和狂欢,一边是无法为人知的撕心的痛苦。两个女人曾在一起走过沙漠,而因不同的爱情、命运而分开,走向尽头或非尽头。火车开过狂欢的人群时, 时间空间又交织在一起。第四段也是一个在视听觉上达到狂欢化高潮的尾声。这个尾声试图把前面三段留下的种种关系在此澄清,试图把那种各自为政的分段叙事结构画上一个华丽灿烂的圆圈。无疑,如果把第四段放到第一段叙述的话,剧情会好懂得多。当然,那种悬念的效果就会差得多。
第四段的狂欢式出场,是对前三段叙述的一次大缝合。在如梦如幻的狂欢中,解释了诸如:疯妈为什么发疯,她有着怎样难为人知的哀痛,小队长从何而来,唐妻为什么出轨(从浪漫跌落到平庸),梁老师为什么忧郁为什么自杀(他在第四段中是何等的欢快俏皮浪漫!)等问题。
从姜文在这部影片中首次实验的分段叙述的结构看,姜文是力图创新并超越自己的。1994年,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与以分段叙事声名鹊起的《暴雨将至》同时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前者获金狮大奖,《阳光》只有夏雨获得演员奖。影片的分段式圆形叙事结构也许因此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但在这种结构已经很普遍,已经成为“公器”的今天,姜文的结构探索并没有太多的实验性意义和创新价值,相反内涵和表意可能更为重要。
其实,如果把第四段放在第一段之前,如果我们不要被第一段中过多的神秘意象所迷惑,从叙事结构来说,《太阳照常升起》的线性时间逻辑还是非常清晰的。故事的结构与总体叙述并不复杂也不是太难懂。令人遗憾的是,这四段叙述风格似乎并不统一协调,连配乐的风格都大相径庭,像是不和谐的变奏,拼贴感很强,每一段都像是独立的即兴小品。不用说,姜文的前两部作品无论风格还是叙事都是基本统一的,但是《太阳照常升起》却有点率性自由,信马由缰,因为方向太多太杂而没有了方向。很明显,影片有意无意地设置过多的偏于私人化的意象,是这部电影让人费解的最根本的原因,结构倒在其次。
二、寓言与个人化意识形态
我们说,理解《英雄》、《十面埋伏》可以“离开”张艺谋,但要理解这部电影,离开姜文本人是不可能的。这也许就是这部票房不佳很小众的“作者电影”与大众电影的区别。毫无疑问,对这样一部具有明显的“作者电影”特征的电影的解读,不能脱离开导演姜文,正如他在导演自述中说的,“每一部电影,都是创作者生命中的一部分。”
不妨说,整部电影就像姜文做的几个梦,就是姜文私人梦幻和个体童年的影像化呈现。影片中有大量的姜文个体记忆的留影,而这些梦或记忆并不都具有能够引发普遍共鸣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太阳照常升起》比之于《阳光》、《鬼子》,是大踏步地往个人化的迷宫里深陷。
《太阳照常升起》无论在姜文创作的出发点和某种刻意追求的“匠心”而言,还是在影像的表现风格形态上都非常接近梦。众所周知,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现实的、具象的材料而营造出非现实、非逻辑的情境,就像以表现梦境著称的画家达利把各种在世俗生活中完全不可能并置的东西并置在一起。姜文正是以他非常私人化的个人生活经验创造了这部影片,因此从某种角度说,对这部影片的读解也是对姜文成长的心灵史的揭秘。电影中很多意象(人、事、物),显然都是姜文成长历程中亲见亲历过,或者说是以做“白日梦”的方式幻想出来的。姜文自己也说,“在拍之前,我就已经在脑子里看到了这部电影。这个电影似乎本来就存在着,只是我把它找了出来。那种感觉,就像梦一样,是那样的久违而又新鲜。”
最像梦的无疑是第一段和第四段。第一段中,疯妈的怪和不可理喻的行为举止乃至不凡身手,都似真似幻,还有那个是人非人、似鬼非鬼的李叔、梦幻般石头洞屋中的种种古怪情景,都在提示或营造着一种超现实的梦境气氛,但影像却是相当的清晰。
在最后一段(这一段比之于其他几段更是被导演直呼为“梦”),有一个镜头极有隐喻意味:一边是具有梦幻感效果(而非写实性效果)的众人狂欢、烈火焚烧,一边是姜文正躲在一边悄悄做美梦。这真是“庄生晓梦迷蝴蝶”,不知是蝴蝶梦到庄子还是庄子梦到蝴蝶了。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极富寓言性。所谓寓言性,正如弗·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指出的,“在传统的观念中,任何一个故事总是和某种思想内容相联系的。所谓寓言性就是说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希腊文的allos(allegory)就意味着‘另外’,因此故事并不是它表面所呈现的那样,其真正的意义是需要解释的。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
从某种角度说,《太阳照常升起》的让人费解猜谜,所引起的懂与不懂的争议,正是因为故事太多,每个故事的呈现又是那样的像“梦”,那样的具体而微却又怪诞而超现实,而每个故事以及每个故事中那些令人目眩神迷的意象似乎都另有寓意,你必须要“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这当然使得对影片的解读变得像猜谜了。
应该说,导致如此的原因有三:一是寓言过于个人化了,二是寓言结构稍嫌复杂,最要命的是导入寓意的障碍(意象)过多,太密集。三是想表达的寓意过多了。姜文在影片中仿佛憋了一股劲,太想把他曾梦到过、经历过、想象过的人、事、物,以及他对一些经典电影桥段的学习感悟全部容纳到影片中,跨时代(从1958到1976)、跨中国地域(东、南、西北),跨各种电影风格(现代、后现代、超现实、写实主义),更不用说那些随时可以让人联想起来的经典电影片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低俗小说》、《地下》、美国西部片等等), 总之,姜文借助电影表述自己的欲望过于强烈。
三、“二元对立”:人物与人物关系
《太阳照常升起》的人物关系颇为复杂但依然有规律可循。小队长与唐叔是否父子关系就已经见仁见智,引起很大的争议了,但我觉得更有探究价值的是影片中几对人物之间的某种隐含的关系。罗兰·巴特曾谈到过他对“二元对立”的热情,他说,“就像一个魔术师的魔杖一样,概念,尤其当它是成双成对的时候,就建立了写作的可能性。”不难发现,《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人物设置常有这种两两相对的二元对立的特点。
当然,只能以推断的方式来猜谜:小队长与唐叔是不是前世今生或者少年与成年的关系?疯妈与唐婶是不是一个人的两面(类似于“维洛尼卡的双重生活”?)唐叔与黄秋生又是一对什么关系?
在姜文的个人电影谱系中,《阳光灿烂的日子》与《太阳照常升起》有着明显的承续关系。这部影片中房祖名扮演的小队长则不无马小军的影子,但显然已经过了马小军那种“强说愁”式的青春期烦恼,带有更多的对疯妈的责任,得不到母亲对缺席的父亲的那种情感的苦恼,对父亲的神秘向往,一种“无父”的莫名痛苦,这些情感或意识因素无疑是马小军形象的极大深化。在我看来,小队长是影片中难得的一个非扁平的,有时间长度和性格变异的复杂人物,他的一脸迷茫单纯和苦恼烦躁,“一根筋”似的对“天鹅绒”的执着,都让人能感受到他的复杂和立体,这是一个来自于经验现实的,“颇食人间烟火”的形象,比之于其他人物,这一形象更能引发观众的共鸣。这个形象是对中国电影形象画廊的一次丰富。
而从小队长到唐老师,是否也代表了人的成长?如果这样说的话,姜文之枪毙房祖名,则是与自己的懵懂少年告别了。也许,房祖名与唐叔,都是姜文自己的一面,一者是经验的,所以真实动人,而另一者是想象的、欲望的,徒有潇洒之外表,实则悲凉而虚空,也缺少性格深度。
姜文这一形象从第四段到第二段和第三段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是浪漫的丧失。原先的姜文,置身于西北大漠,设置路标,朝天鸣枪,把妻子的肚皮比作天鹅绒,可谓超级浪漫(是五八年那个浪漫时代的留影或投射?)但浪漫之后则是庸常、无聊、偷情。下放之后则在山野里皮革戎装,“雄姿英发”、漫游打猎,当“草头王”,弹无虚发。这或许折射了姜文这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
黄秋生扮演梁老师颇富内涵,虽然还显得单薄平面,以至于使得他的死不明不白,留下太多悬念。也许,黄秋生和姜文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一个是清高、内敛、自持,自我压抑,一个是自傲、狂放、放任、纵情。也许,梁老师又是唐老师的另一面,梁老师内向害羞还可能性无能,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有恋母情结,他唱的歌就是表达对家乡母亲河的思念之情的。当唐老师对他的枪(枪是母亲给的)感兴趣时,他给自己留下了枪带,有人认为枪带正是脐带的隐喻,所以,黄秋生用枪带吊死了自己,带着微笑,回到母体(他的自杀是一系列的仪式性镜头)。
值得一提的是,《太阳照常升起》留下了一系列光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很可能隐秘曲折地折射了姜文少年时期对女性的不同想象——纯男性视角的想象:一种是如疯妈那样美丽而忠贞,但却敏感而神经质,充满着永远捉磨不透的神秘感,一种是陈冲演的那种似乎整天都湿漉漉、浑身透着性感和骚劲的荡妇,当然也有给黄秋生打电话的那种丑陋而可怕,会给少年留下性心理障碍的悍妇。
四、观影角度的一点反思:创新与张力
如果把《太阳照常升起》置于姜文电影的谱系中去,不难发现姜文卓异的创新能力,他的几乎每一部电影,都是多年磨剑,厚积薄发,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鬼子来了》,到今天的《太阳照常升起》,他都在一步步不断超越自己。难怪有人说,单凭姜文拍过《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两部,他就可以当之无愧地在中国电影史上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太阳照常升起》与《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关联无疑更为密切,不仅因为时代背景,不仅因为少年心理,也不仅因为某种唯美抒情和超现实的风格,里面多个镜头拍摄的运动性和仰视角度都几乎如出一辙(如算盘抛起与书包抛起,房祖名游泳与马小军在游泳池)。《太阳照常升起》所传达的时代记忆特征极为明显:苏联歌曲、《怎么办?》、军装、部队、戈壁、火车、大生产、操场电影、抓流氓、红色娘子军、最可爱的人、工分、算盘——姜文对时代显然是有着某种反思意向的,但这种反思意象因为具有唯美情调的风格化表现和让人如猜谜般费解的情节结构而退居次要地位。另外,更为超越性的哲性思考,也使得反思意向向着更为深刻的层次超升。尤其是第四段,两个女人在骑着骆驼在红色山脉和大雪纷飞的白色天地中的行走絮叨,经历并感悟着人生的偶然、无常。当然,她们是被一个更大的感悟参透者——姜文所操纵的梦幻人物。今天的姜文,比之于《阳光灿烂的日子》时期的姜文,显然是长大了,沧桑多了,人生悟道也更深刻。
姜文创新的野心、勇气和才气都是绝对超群的。与前两部影片相比,《太阳照常升起》的结构复杂了,叙事多元了、人物类型多样了,主题意蕴更是丰富复杂了。
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姜文通过复杂的叙事结构,表达了极为复杂的主题意蕴,诸如成长的苦恼、寻父的焦虑、对成熟女性的欲望投射和征服欲,英雄情结、枪或性的崇拜、对浪漫消逝的喟叹,以及理性层面上的对时代历史的思考,对世事无常、命运轮回的参透,存在主义意味的人生感悟,等等。这些复杂的、多层次的主题意蕴的细密交织,增加了影片读解的难度。这是姜文对自己的超越,也是超越过度之后几乎无法避免的问题。
毫无疑问,电影的魅力在于对观众个体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挖掘。观众与银幕的共鸣往往是因为电影中人物所披露的深层潜意识与观众发生共鸣,或是一种遥远的原始记忆、青春记忆、历史记忆的被唤醒。也正因如此,电影的接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充满着对话与潜对话。
观影过程是主动性与被动性互动的张力性过程。观众既是被动地接受,也是主动地选择,观影是在被动与主动之间发生的。借用“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型心理”理论,外部世界与人的内在世界都是力或场的结构,当这两个力或场的结构相对应时,会发生顺应与同构的心理运动,其运动的结果,两个力或场的结构就交感契合,融合一体。通俗点说,真正好的电影,既不能让观众什么都知道,太俗套太无内含个性,也不能太让观众陌生费解以至于猜谜,应该使观影过程中的顺应/同化、主动/被动达成一种饱满而恰当的张力。
而在姜文这部极为个人化的影片中,这种对话的可能性,这种可能的饱满充足的张力,被导演过于复杂求深的主题意向,复杂的结构,过多的个人化私人意象阻断了。电影的进展成为姜文的梦幻私语,观影的过程则成为紧张疲劳不堪的单向的解谜猜谜过程。观影接受过程中主动性与被动性之间的张力平衡被打破了。
从观影接受的角度看,这或许是《太阳照常升起》票房不尽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无论怎样,《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现及其创新的努力,都是为中国电影在探索中前进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标签:姜文论文; 姜文导演作品论文; 姜文电影论文; 电影叙事结构论文; 寓言论文; 阳光灿烂的日子论文; 鬼子来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