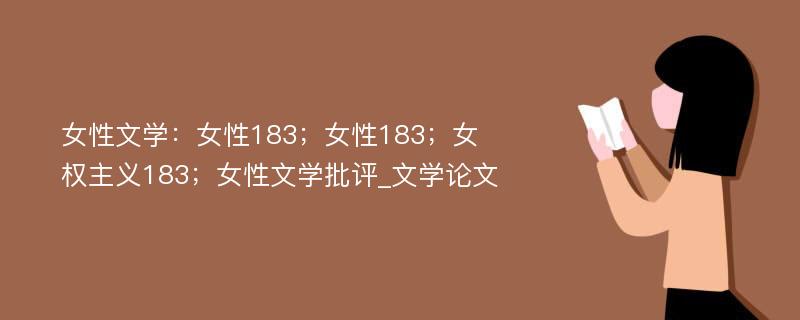
女性文学:女性#183;妇女#183;女性主义#183;女性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文学批评论文,妇女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字面上把女性文学理解为一种按性别分类的性别文学,就像青年文学按年龄分类,西部文学按地域分类,女性文学不过是特别标出作家性别的一种性别方言罢了。果真如此,女性文学不仅失去了它起码的理论意义,而且可能起到强化女人“第二性”位置的作用,使生而为女人者感觉到某种看不见也说不出的以宽容面目出现的性别歧视。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女作家拒绝认同女性文学这一命名的心理原因。而且越是自信心和独立意识强对两性不平等有深刻体验的女作家越是拒绝把自己归入女性文学命下。她们说:“我只卖文,不卖女”(丁玲),“女性是人,不是性”(张洁),“好作家不分男女”(张抗抗)。她们自信自己是凭着不逊于男作家的作品自立于文学之林,无须凭着更无须玄耀那种令人难堪的性别“优势”。
女性文学既是性别文学又不是性别文学这一悖论,可以用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理论来说明。概念符号与所指称的对象不是同一的相等的,语言相对于它所指称的对象既是照亮又是遮蔽,它的意思是某种暂时的、后延的,有待于发生发现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符号可以完善的穷尽它所指称的对象的全部涵义。因此,概念的意思(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概念)常常是包含着悖论的有待于发现、填充和更新的(注:参见《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英)特里·伊格尔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前述美国《女性独立宣言》把“人”这个词改为“男女”,中国女学生把讲义上的“他”改为“男女”,美国女性在history 之外又创造了一个 herstory, 便是女性在人的范畴里要求男女平等而在符号学上的体现。女性文学这一命名在人学体现上的不完善及其悖论,触及到了人类历史讳莫如深的幽深地带,而“女人也是人”这一觉醒的女性“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是世界范围的女性文学哲学的和女性人文主义共同的思想的和逻辑的起点。
索绪尔认为语言中的意思只是一个差异问题,每一个符号的意思只是因为它不是其他符号的意思。如果我们要相对稳定地和准确地界定一个符号的意思,便应该把与它相近的或似是而非的意思排除出去,也就是要从该符号不是什么入手。
女性文学不是什么呢?
前述关于性别文学的悖论,意思是女性文学虽然以“女性”这样的性别概念为标志但并非凡是女作家写的就是女性文学。作家的自然性别固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前述女性文学的现代性这一特质在时间上排除了五四以前的妇女古典诗词,包括以秋瑾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前后表现了鲜明的妇女解放要求的作品,应历史地看作是我国女性文学的萌芽或前躯。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应如何概括?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及我国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讨论这一概念时,一般认为应该是体现了女性意识的作品,伊丽莎白·詹威认为要看她对自己所写的生活内容的体验、理解是否是女性的。鉴于女性意识、性别意识这些概念含意的模糊性,我意应在前面加上“现代”二字加以限制。这就把那些虽为现当代女作家所写却体现了传统的男性中心意识的作品排除在外(注:女作家所写的不属于女性文学的作品在八十、九十年代如陈蕙芳在《神话的窥破》中所指出的一些回应男权复归的作品如《东方女性》(航鹰)、《飞去来》(戴晴)、《一路风尘》(王小鹰)等。)。
女性文学也不是一个题材概念。人类生活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参加和共同维系的,尽管历史对男/女、社会、家庭的角色位置进行了等级制的刻板定位,但任何生活领域都难以截然划分为纯然男性或纯然女性的题材,任何女人的问题都和男人有关,反过来说也一样。题材决定论的实质是题材等级论,即等级制的公众,个人、集体/私人等二元对立模式。前者似乎是男性领地而后者则似乎注定属于女性。庐隐萧红等均因此而受到过非议。近年来这种以题材等级论鄙薄女性文学的现象明显升温,出现了种种以“小”和“私”为中心词的命名(“小女人散文”、“私小说”、“女性小品”等)。事实上题材本身无所谓价值上的大小高低,重要的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和写得怎么样?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在这方面的区别不在题材而在女性一般来说习惯于以内视角和个人记忆个人生存体验来处理各种生活范围的题材。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中国女性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事实上出现了哪些形态类别了。女性文学和我国20世纪历史息息相关,不可能摆脱种种历史合力的牵制而只能在历史给定的不尽相同的条件下做出不尽相同的选择,从而呈现出现代性进程的丰富性。诚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语言并非是一个规定明确、界限清楚,包含着表现者和被表现者对称单位的结构。它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蛛网,网上的成份不断交换和循环,没有一个成分受到绝对的限定,每一种东西都受到其他各种东西的牵制和影响(注:参见《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英)特里·伊格尔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这个“无限展开的蛛网”上有的成份发展了,有的成份消失了又复现了,也有新的成份出现、发展或消失,也有的成份发生了变异成为不是它原来的东西。“女性”、“妇女”、“女性主义”便是女性文学发展进程这张蛛网上三个重要的“网结”。在我国女性文学之现代性进程中,恰恰可以梳理出女性文学、妇女文学、女性主义文学这三种形态。
“女性”(female)是女性文学及女性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它和“妇女”这个概念是同义的可以互换的吗?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这里基本上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女性与妇女这两个概念的混淆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女性文学批评对女性文学现代性的漠视、盲视。
据美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白露考证,我国直至清末还没有女性这一概念。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不存在一个超越社会人伦关系的女性概念,凡指称女人的词语都是指在具体的家庭人伦关系中的女人,如次于儿子的女儿、次于丈夫的妻子、次于父的母等,各人只有根据自己在亲属关系中规定的角色规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会认可的角色位置。“女性”这个词与“他、她、牠”这些人称代词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白话文学的主题之一,是一个超越了亲属人伦范畴超越于传统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人社会角色定位的一个革命性反叛性符号(注:《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第265-267页,鲍晓兰主编,三联书店1995年版。),也是一个有待发展和完成的概念。我们在20、30年代的一些论文和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女性”这一有别于恪守三纲五常的传统女人依附性身份的概念,有的文本为了与旧式的传统女人相区别,常常在“女性”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新女性”便成为“现代女性”的同义词。白露也指出了“女性”一词的负面含意如被动、柔弱、智力与生理上的低能等,这恰恰是女性概念的暖昧性不稳定性而在运用过程中被男性偏见所填加进去的意思。
白露还考察了“妇女”(Woman)这个概念内涵的变化。 在传统话语中,泛指女人时有女子、妇人、妇,也有妇女这个词,都是指的传统女人。白露所分析的是妇女这个概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被填加进去的意思。她指出早期共产党人将欧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的Woman 译作妇女,强调社会生产与妇女的关系,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的翻译奠定了“妇女”一词的政治意义,三十年代农村根据地、苏维埃政权以至毛泽东时代国家、妇联等政治机构继续沿用的“妇女”一词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注:《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第267 -268页,鲍晓兰主编, 三联书店1995年版。据收入该书的王政的文章介绍,白露认为“妇女”一词在“女性”之出现,是“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倡导下出现的,尽管与女性词义不同,但它仍来自殖民主义话语。”这是不对的。早在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妇女”一词,如蔡谈《悲愤诗》中“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等。不过白露“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妇女作为国家话语的形式”,也就是本文所肯定与吸取的“考察了妇女这一传统概念内涵的变化。”)。 “妇女能顶半边天”便是从生产劳动和政治功能意义上使用的。
可见“女性”“妇女”这两个词尽管都指称了“女人”这一性别,但二者的内涵并不一样也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之中,前者以区别于旧式女人的作为人的主体性为本质内涵,而后者则是一个被国家权力话语政治化了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日本,妇女的概念一般是指没有解放的老式女人;而女性一般是指现代社会中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解放的新式女人(注:参见王绯:《女性意识与妇女意识》,《中华读书报》1997年1月29日。)。就一般意义而言, 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也应有这样的大体上的区别。
“女性”、“妇女”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恰恰与五四到十年“文革”女性文学的历史嬗变形成同构的关系,也就是说,上述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内涵恰恰对应了相应的两种不同的女性文学类型的基本内涵。我国女性文学与女性这个词同时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二十年代后期与妇女概念内涵的政治化功能化的同时,出现了丁玲文学创作方向的“大转变”,出现了女性文学的分化,逐渐形成了一支以丁玲的《韦护》、《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之二)、《水》、《田字冲》等作品为代表的妇女文学,恰与妇女概念内涵相对应。并在四十年代出现了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在不同的话语空间的并存现象,直到新中国成立,解放区工农兵文学被规定为新中国文艺的共同方向,女性文学与五四人的文学同时被阻遏,妇女文学以顺应时代潮流和主导意识的方式与工农兵文学一起得到了长足发展,直到在“文革”十年中被极左政治推向极端而走向反面。八十年代初,随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女性与女性文学再次出现,成为当代文学中一支既有别于男性文学又有别于妇女文学的现代性的女性文学。而妇女文学则走向了衰微。在女性文学的发展中,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出现了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新类型,而更多的女性文学也在继续发展。
就这三种女性文学类型的关系而言,妇女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话语环境下女性文学所衍生出来的两个分支。应该承认即使是妇女文学,在其发生之初,也还是基于女人争取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和价值的实现的现代性进程的产物,但二者的思想资源不同。妇女文学的思想资源来自社会主义的妇女观,主张妇女应投身于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洪流之中,在社会/阶级/集团的解放中解放自己,故更多着眼于社会底层妇女,主张知识女性要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故其主人公多为各种社会/阶级/集团斗争中的女英雄。至于这种“社会解放我解放”的模式,究竟能否解放妇女和在何种程度上解放妇女,那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妇女学理论问题,本文暂不展开论述。女性主义文学的思想资源显然是80年代中期才陆续译介过来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但就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更多地吸取了弗尼吉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和贝蒂·傅瑞丹的《女性迷思》、《第二阶段》这些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女性人文主义思想,而对西方激进的和学院派的“性政治”“累斯嫔主义”以及建立在男/女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的性别对抗路线则采取了谨慎的既有所认同也有所保留的态度,有的女作家如王安忆、铁凝的一些小说则对这些理论进行了严肃的艺术探索,从而使自己与西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拉开了距离(注:这也是feminism这个词译为女性主义而不译为女权主义,在我国女性文学批评界已取得共识的原因。)。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女性主义文学从自在到自觉,对中国妇女尤其是中国知识女性、职业女性的精神成长和主体性建构进行了默默的和艰苦的探索,代表性作家如八十年代的张洁、张辛欣、残雪的一些小说,诗人陆忆敏、萨玛(崔卫平)、王小妮、伊蕾、翟永明、张烨、张真、叶梦、期妤等的一些诗和散文,九十年代铁凝、蒋子丹、方方、徐坤、徐小斌、陈染、林白等的一些小说等。这里有一些作家在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这两个类别中同时进行了探索,正如丁玲是现代文学中在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这两种文学中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一样。不同的是前者基本上出于她们的自觉选择而后者则是无奈的在时代纷纭复杂的历史潮流里跌着跟斗,而一些众所周知的女性文学文本还受到过多次批判。就此而言,现代知识女性的命运还是有所改变。时代毕竟不同了。比丁玲年轻得多的蒋子丹、徐坤们毕竟不再是别无选择而是在一定限度内赢得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有论者批评二十世纪女性文学研究对女性文学和妇女文学这两种文本存在着严重的偏科和理论上的误植,并认为这样的批评拉大了这两种文本的距离(注:王侃:《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研究批判》,《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 该文把笔者所指称的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命名为性别/政治这两种文本。至于该文作者根据笔者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前言中的一段话,所归纳出来的两点意思,已属似曾相识的“上纲”术,笔者保留反批评的权利。)。这恐怕在相当的程度上偏离了这两种文本的实际。由女性文学而出现了与主导意识形态同构的妇女文学,这本身就说明了二者的差异,加之政治作为一种强大的权力话语的控制和干预,使原本具有合理性的妇女文学走向了政治化这一文学的危途,从根本上改变了女性这一概念的现代性内涵,导致了女性、妇女同时在生活中和文学中的双重失落,在被男性化的同时也失落了自己作为精神上独立自主的人的价值。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新生,其内在的思想底蕴不能不是对政治化的妇女文学的反思。这不是哪一个女作家个人的问题,这两种文本的差异自然也不是依照哪一位批判者主观意志所能够消泯的。论者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水》、《田家冲》,五十年代菡子、茹志鹃、刘真等对战争题材的抒写归之为“政治文本”,意思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讲述”。萧红的《呼兰河传》,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不幸也被划入“政治文本”。至于是什么样的政治则语焉不详,更不提即使是这些对当时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讲述”的作品(且不论这样的概括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是不准确的),也有不少为当时的政治所不容,刘真的《英雄的乐章》、《春大姐》、茹志鹃的《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宗璞的《红豆》等都受到过左倾政治的批判,至于杨沫的《青春之歌》在政治压力下由初版本到再版本的重大变化,更是政治对妇女文学的强力扭曲和规范。妇女文学被强行纳入左倾政治权力的巨掌之中,改变了和阻遏了广大妇女求解放的现代进程,这正是女性文学发展中的深刻教训,能否吸取这一教训也是妇女文学能否更新的关键。在这里,女作家和女性文学批评者的价值立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是从妇女作为人的价值立场出发还是从泛泛而论的暖昧不明的政治立场出发?论者将庐隐、冰心、凌叔华、苏青、张爱玲及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等归之为“性别文本”即“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话语的文学书写”。这“性别文本”是指女人的“自然性别”( sex)还是“社会性别”(gender)?而“性别意识”包不包括女人作为人的意识?而“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意识”这样的界定,即使仅指上述的女性主义文学,也基本上不符合这些作品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徐坤的《女娲》、《出走》、《厨房》,蒋子丹的《桑烟为谁升起》、《绝响》、《等待黄昏》、《贞操游戏》、《从此以后》,铁凝的《玫瑰门》、《对面》、《麦秸垛》、《棉花垛》、《孕妇和牛》,陈染的《破开》、《无处告别》、《私人告别》、《私人生活》,林白的《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及近作《说吧,房间》、方方的《暗示》,萨玛的《父亲》、王小妮的《应该做一个制作者》、张烨的《鬼男》等女性主义文学名篇都是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高度探寻女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的。她们鲜明的作为人的性别意识无论是体现在对父权制男性中心意识的批判还是体现在对女人自身身体的认识对母性和爱的新的认同以及人性的审视,都立足于人性的提升完善和女性的成长与解放这一女性人文理想的价值立场,这也正是女性文学能够超越时代,超越性别,超越时效性和功利性的变幻莫测的政治而具有长久的历史和美学价值的原因。
我国女性文学批评自八十年代中期兴起如今才刚刚走过了十余年的历程,理论的建构问题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需要一种清晰的能说明我们自己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和规律性的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的理论,我选择了女性人文主义。这种理论将启蒙理性的人文主义向女人关闭的一扇大门打开,以人文理想的价值之光和无穷思爱的神性光辉朗照被压抑被遮蔽被曲解的女人生存之真女人的个人真实性,和女作家们一起以澄明的女性之思展开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无限可能性。女性人文主义不是启蒙理性人文主义的对立面,而是它的必要的丰富和发展。这种理论将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既是批判的又是建设的,女性人文理想的价值立场和“人——女人——个人”这一综合的阅读批评视角将有可能把曾经被视为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方面如同一性和差异性、个体性和相关性、个人与群体、自由和限制、物质与精神、人的恒定性与可变性、自由选择与神性自律、此岸与彼岸乃至传统的与现代的、后现代的一些合理性因素辩证的统一起来,将既是开放的多元的又不是相对主义的批评。同时,面对少数持有男性偏见的批评者对女性文学的误读、曲解乃至鄙薄,我们将不再是没有回应和对话能力的“弱者”(注:如有论者说“小女人散文”是“既非贵妇也非贱婢,既不奢望当贵妇又不屑于做贱婢的女性流行式”,“做不成大女人的女人,大多数不是因为清高,而是德才都不够格缘故”(《贵妇·贱婢·小女人》)又如有论者认为“裸露是这部小说(指铁凝的《玫瑰门》)的叙事基调”,“事实上女人要用她们‘性’的本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善’,这与其说是强调了女性的自然力,不如说这是女性别无选择的逃离了人类文明”“用女性的善性化向社会和男性发起战争”等等,见《‘女权’写作中的文化悖论》,不过此文的三位论者也正确指出了“人性的发展似乎不在女权主义尤其是极端的女权主义理论的逻辑范围之内(见《文艺争鸣》1997 年第5期)。)。
女性不应该逃离人、人性、人文主义,不应在本质上是男性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局限性面前裹足不前,不能没有自己的女性人文主义思想。
这一理想的又是可行的批评远景向我召唤,我将竭尽余生做好这一件事。
标签:文学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女性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丁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