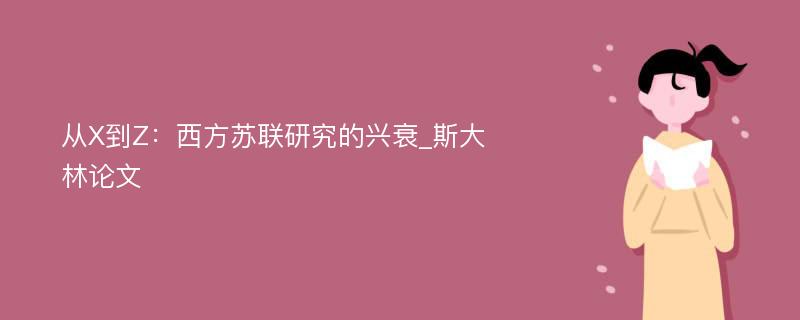
从X到Z: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1-0069-(18)
一、问题的提出
1989年,象征着传统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分野的柏林墙顷刻之间倒塌,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全盘重新洗牌。然而,“历史”并未像西方自由主义者所断定的那样就此“终结”。欧亚大陆各类民族主义滋生繁衍,其惯性和冲击力不仅继续支配欧亚大陆“后共产主义”制度/地区的政治生态,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欧洲本身的政治—经济整合、欧盟与俄国的关系以及美俄关系。在“9·11”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下,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也在亲西方的理想/自由主义和更为传统的欧亚主义(Eurasianism)之间摇摆和探索,寻求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欧亚大陆未来的政治走向前景如何?欧亚大陆最大的政治实体俄罗斯如何应对其“渴望”又不可及的西方?基本上错过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良性”运作时期的俄罗斯如何摆脱目前全球化的“厄运”期?美国主导的西方又会怎样对待一个劫后重生、欲振乏力但雄心未泯的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如何看待一个与其若即若离的俄国?什么样的俄罗斯更符合美欧的利益?俄罗斯又如何自我定位?一个在西方化与俄罗斯化之间永久徘徊的俄罗斯到底是正常还是反常?这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走向又意味着什么?西方俄罗斯研究与西方对俄政策之间有何种联系和互动?
冷战以后西方的俄罗斯/欧亚研究和对俄政策,是冷战期间“苏联学”的继承和发展。本文的任务是对西方/美国的“苏联学”研究进行梳理,并将其置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加以比较和考察,同时兼顾美国对苏政策的制订和走向,以寻找三者之间的交叉点和互动之处,以期为进一步研究冷战以后西方的俄罗斯/欧亚研究和对俄政策提供一个基础。
二、X先生与“苏联学”(Sovietology)
冷战后美国和西方的俄罗斯研究,对冷战时期的“苏联研究”有继承也有扬弃。从苏联到俄罗斯的转型剧变,对西方的苏联/俄罗斯研究和政策制定,以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都造成了强有力的震荡和冲击。
二战后西方“苏联学”研究之拐点,一般要追溯到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47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以“X”笔名发表的“苏联行为之根源”(“The Sources of the Soviet Conduct”)一文。① 该文提出的“遏制”观念,不但被杜鲁门政府立即转化为美国冷战时期的对苏政策,也影响了几代西方苏联学学者。
冷战期间,西方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学界、政策界和政府部门设立了众多的“苏联研究”项目和机构。政府的外交、国际事务高官中也多有研究苏联问题的重量级学者,如基辛格(尼克松、福特政府)、布热津斯基(卡特政府)、赖斯(小布什政府)等。② 不仅如此,战后美国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拓展,在相当程度上也借助了苏联研究的动力和资源,前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分量,更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无论是以国家实力为研究基本出发点的汉斯·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③ 还是立足于国际体系、高屋建瓴的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structural or neo-realism),④ 均与苏联在二战后崛起、成为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强国有关。而在七十年代出现风靡一时的所谓“极派”(polarity)学者,更是与中苏两个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相同的大国由结盟转向对抗、并因此产生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在以往泾渭分明的国际两极体制之外开拓了“三度”的想象和操作空间有关。⑤ 总之,前苏联的盛与衰,催生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大批理论性著作,其中包括约翰·盖迪斯(John Gaddis)的“持久和平论”(long peace),⑥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⑦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⑧ 甚至冷战结束以后开始成气候的建构主义,也是建立在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评之上的。而批评的矛头所向,就是这两个学派都未能预见到苏联的解体。⑨
建构主义对主流学派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在苏联问题上误判误导的绝不仅仅是学术界。美国情报界和决策界也未能预见强大的苏联会突然解体。中情局资深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盖茨(后任中情局局长、现任国防部长)在1986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就曾坚持认为,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政策毫无新意(“nothing new”),“在苏联只有暴政才能行得通(The Soviet Union is a despotism that works)”;全然没有察觉到戈尔巴乔夫与众不同的能力和致命的施政弱点,及其在以后的几年里给苏联政治和社会带来的巨变。拥有众多类似盖茨这样的“苏联通”的中情局,因此也只是年复一年地编织着苏联强国强军的神话,直到编不下去为止。⑩
苏联问题研究是美国外国问题研究领域中投入最多的项目,但其最终结果却远不如人意。这种投入产出完全不成比例的现象,与美国情报界10年以后未能预测到“9·11”恐怖袭击的背景完全不同。当时以小布什总统为首的美国决策界和情报界几乎完全忽视了恐怖主义的滋生蔓延。(11)“9·11”前的几个月,小布什总统的注意力实际是在俄、中两国——2001年3月驱逐50余名俄国间谍、4月1日中美军机相撞,可以证明这一点。
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有密切关系,但美国对苏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似乎有自身的逻辑和惯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和不断变化的。简单地认为美国学界和政策界之间是无数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s)——即学者与政府官员和智库人士经常转换位置,互相配合——进而认定学界与政府之间的“共生”关系,可能是过于武断的推论。
一般来说,中情局如此“钟情”甚至迷信前苏联的“长治久安”,其主要目的之一很可能是为了美国国内军工集团的利益而塑造一个强大的对手,以便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种政治化的情报当然无法客观和精确。对于中情局夸大苏联实力的做法,居然还有人匪夷所思地认为,该局在对苏分析中的“盲点”是前苏联谍报机构在中情局内部长期卧底的间谍阿尔德瑞奇·艾姆斯(Aldrich Ames)所造成的。在最高决策层面,老布什本人从内心不希望戈尔巴乔夫失败。而他的国务卿贝克及其助手对苏联事务的了解几乎是一张白纸。相比之下,其前任舒尔茨国务卿和他的副手们则精通对苏事务。贝克本人出身律师,擅长言辞和谈判,但对历史和地区事务知之甚少,对苏联的突变当然缺乏直觉。(12)
其实,决策者所需要的不一定是非常专业化的知识,而是战略眼光和对历史的把握。在这一点上,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早在1821就对俄国目后的发展有言在先:
很难设想……俄国未来的扩展仍然会一帆风顺。如果俄国不能教化那些居住在俄国统治所伸延到的天涯海角的游牧族类,这些被征服的部族就算不给俄国添乱,也不会给俄国帮忙。而教化这些部族的过程又会使俄国成为一个膨胀过度的帝国,它必然会重蹈历史上无数帝国最终分崩离析的覆辙。(13)
麦迪逊的先见之明是建立在类似“物极必反”的常识基础之上的。他虽然不可能精确预测前苏联解体的具体时间,但对苏联帝国的长远走向显然有相当的洞察力,至少避免了中情局众多“苏联问题专家”们的双重错误: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不相信他会改革,而在戈氏执政后期则低估了改革的风险。
三、Z先生的“苏联必亡论”
中情局的失误不是偶然的。苏联剧变前夕,西方和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主流沉浸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引发的亢奋和企望之中,对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1990-1991年)陆续出台的激进改革政策所遇到的阻力以及伴生的风险毫无察觉。甚至有学者在戈尔巴乔夫激进改革开始之前就宣布西方已经胜利,可以高枕无忧了。(14) 在西方政府、媒体和学界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齐唱赞歌时,美国的一家名为《代达罗斯》(Daedalus)的人文学术杂志在1990年冬季号发表了一篇署名“Z”的长文,指出苏联的极权体制必定会走向灭亡,而戈氏改革只会加剧这一进程。对“苏联问题”和国际关系学界来说,该文的署名“Z”立刻使人联想到凯南当年以“X”笔名为冷战“定调”的长文,在西方和美国造成了轰动效应。(15)
在这篇题为“通向斯大林的墓地”的文章中,Z先生严厉斥责西方苏联学界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一厢情愿的盲目乐观(第296-301页),指出了前苏联制度的“不可改革性”,原因是苏联制度不是一般的官僚体制,而是以意识形态构成的意识形态—官僚体系(ideocracy);任何背离这一体系的举动都会引起连锁反应,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苏联的问题不是如何改革其共产主义制度,而是如何使之解体(dismantling,第337页),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自掘坟墓。(16)
Z的真实身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苏联历史学教授马丁·马里亚(Martin Malia),(17) 使用匿名是为了保护为此文提供消息的前苏联人士。在西方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一片赞歌中,马里亚在苏联解体近两年前做出极为悲观的预测,似乎有“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洞察力。Z文的论述基于两点:对前苏联历史系统和细微的观察,以及对西方苏联学主流的强力批判。在马里亚看来,在苏联解体前的20余年里,西方苏联学的主流学者及其各种“理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苏联集权制度的辩护士;他们看到的只是制度表面的超稳定性(18),认为苏联体制已逐步过度到“成熟的工业社会”,甚至具有“向多元社会发展的潜力”,全然忽视了前苏联社会变迁所经历的巨大震荡和付出的沉痛代价。
据马里亚观察,六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的苏联学界对二战以后一直占据苏联研究主导地位的“集权模式”(totalitarian model)进行了数次“修正”,以加强对社会和经济等“底层问题”的研究,却忽视了对集权模式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等“高层问题”的专注,即以“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取代了“政权研究”(regime studies)。(19) 在这些被修正了的、非集权化的模式中,西方的苏联学界几乎把前苏联描述成了具有西方民主特点的政体,认为苏联模式虽然是从乌托邦开始,但经历了城市化和教育普及后,最终发展到了“现代化”。(20) 根据这种逻辑,斯大林的“暴政”不过是过眼烟云(a passing phase),或一个“非正常”现象(an aberration);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实际上恢复到了所谓“正常状态”(normalcy)。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出现了所谓“机构性多元主义”(institutional pluralism),苏联军方、企业管理阶层、或科学院学者,都可以通过多元方式表达各自的见解。(21) 最令马里亚反感的,是西方苏联学界中有人把斯大林时代描写成由一个从下至上、由“恐怖社会”经过“进步”发展,达到社会“流动”(terror,progress,and social mobility)的“民主现象”,使得勃列日涅夫一代领导人能够由底层脱颖而出,(22) 等等。他认为,西方苏联学主流未能透过表象看到前苏联极权主义的本质(第300页),过分注重前苏联集权政治的程度和数量(degree and quantity),而非本质和质量(nature and quality)。在马里亚看来,尽管戈尔巴乔夫对前苏联体制动了大手术,但该体制的基本内核(党政体系、中央计划、警察系统、党务系统等)基本上得以延续(第301页)。
作为苏联史学家,马里亚认为要真正把握现状和洞察未来,必须以史为鉴。首先,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基于乌托邦式的理念。之所以“侥幸”成功,是由于俄国在一战期间的深度危机。革命后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以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对沙俄旧军队的控制,以政治警察(或契卡)来打击布尔什维克的一切“敌人”。在1917-1920年间,有1500万到1900万俄国人死于战乱、饥荒和疾病,其中主要原因是布尔什维克的乌托邦式的奢望和执政不力(第305-310页)。三十年代的苏联经济高速发展和1929-1935年代强制性集体农庄运动,造成了600万到1100万人死亡;3000万农民迁入城市从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力因此遭受严重破坏,农村生活水平倒退至1913年以前的水平,俄国由一战前欧洲的“粮仓”沦为谷物净进口国,至今元气尚未恢复。
在工业方面,前苏联政府发布的三十年代的年经济增长率为20%;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西方经济学界估计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仅为4-6%。(23) 此外,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增长极为畸形,绝大部分是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几乎没有发展。整个苏联经济犹如一个庞大的军工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第312页)。而确保这一庞大体系运行的则是1936-1938年间斯大林的“大恐怖”(Great Terror),,以此来制止任何可能对其农业政策和“一五计划”的怀疑和批评。马里亚援引西方和前苏联学者的统计,从1936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大恐怖”的受害者可能高达1000万,而这还是比较保守的统计。(24)
在这千万人的受害者中,包括80%的苏军军官(第314页)。苏军受到如此重创,为何还能在二战中击败德军?马里亚认为是“地利”的原因:苏联幅员辽阔,斯大林有足够空间去换取时间,使希特勒自己犯错误而步步走向失败;同时苏联有时间转移大量军工企业,保存实力,并伺机反击。卫国战争的胜利,使苏共政权拥有了新的合法性;四十年代末的原子弹、五十年代末的人造卫星、七十年代与美国实现了核均势……这一切华丽的表象,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粗糙内涵。这种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经济,建立在对资源和人力大量消耗、不计成本的基础之上,在工业化和战时可以有傲人的业绩,但在高、深层次的经济发展阶段就日渐乏力。到七十年代末,苏联的发展模式达到巅峰。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同年,苏联的经济增长为零(第316-319页)。
后斯大林时代被马里亚划分为赫鲁晓夫的解冻期(thaw)、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期(stagnation)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期。对赫鲁晓夫来说,在政治上清算斯大林似乎并不难,一纸秘密报告就可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也可一挥而就。然而赫鲁晓夫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改革前苏联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在马里亚看来,恰恰是因为赫鲁晓夫在三个方面触动了苏联官僚体制的最敏感处,最终导致其下台。首先,赫鲁晓夫把经济决策权下放到新成立的“地区经济委员会”(Regional Economic Councils,Sovnarkhozes),从而削减了中央部门的权限。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又把党务系统分为主管农业和工业的两部分,引起众人反对。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赫鲁晓夫力图对重要的党内职务的任期加以规范和限制,触动了一大批党内高层人士的根本利益。赫鲁晓夫在这些国内政策上的失分,甚至超过了古巴导弹危机,最后墙倒众人推(第320页)。
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1964-1982)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被称为“停滞期”。其政策走向包括停止非斯大林化,因为过分贬低斯大林不利于政治稳定;虽然勃列日涅夫政权从未以官方名义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但停止了赫鲁晓夫时期对“个人迷信”的攻击。在经济方面,由于工业部门的反对,柯西金总理试图用以某种有限的权力下放提高生产效率的政策也裹足不前,工人对工作没有积极性,得过且过,经济效益低下;与此同时,“地下”经济却大行其道,最终导致相当的经济管理部门、党务系统、甚至执法部门“黑社会化”(Mafiaization)。到八十年代初,随着前苏联执政的老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脚下,整个苏联的体制已病入膏肓,滑向一座巨大的斯大林式的墓地。
在马里亚看来,医治这些制度上的痼疾,挽救这一垂死的机体,对经历了18年“停滞期”以后上任的戈尔巴乔夫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以悲剧(drama)收场的改革尝试。然而,戈氏还是知难而进,对已经不可救药的政治、经济体制施以“重建”(perestroika)、“透明化”(glasnost)和民主化“三板斧”。戈尔巴乔夫的重建政策始于1985年4月,目标是为举步维艰的苏联经济打一剂强心针,以加速经济发展;为此,戈尔巴乔夫问计于专家学者,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对政府经济部门进行改组和合并,撤换了一大批官员;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酗酒运动,实行质量检验制度。然而这一切均未能重振经济,反而适得其反:反酗酒运动迫使伏特加的销售转入地下,国家失去了一大笔收入;质量检查制度使大批企业完不成利润计划,收入下降;机构调整和人事变动又使各级官员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到1986年秋,戈尔巴乔夫的各项“重建”政策均遇到重重阻力。
不得已,戈尔巴乔夫发起了“透明化”运动(glasnost),力图通过知识界和舆论,营造开放、改革的气氛,对体制内的官僚体系和僵硬的思维方式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甚至亲自打电话给正被流放的萨哈罗夫(前苏联主要持不同政见者),请他“出山”并保证其言论自由,希望他能为改革推波助澜。其结果是苏联的政治生态急剧分化,自由/改革派的交锋日益白热化,来自反改革派的阻力也越来越强。保守派的领军人物利加乔夫(Ligachev)指责说,自由知识分子的批评会使苏联的体系、传统和价值观念毁于一旦(到1989年,前苏联的几乎所有政治和价值观念都受到公开指责、批判和诋毁)。对此,戈氏的改革派认为,不存在除了重建以外的任何其他选择;如果苏联经济继续停滞,苏联会很快失去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以致亡党亡国。到1989年初,由“透明化”运动引发的改革和保守派之间的辩论白热化,并在苏联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中造成强烈的危机感。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大败笔是打开了遍及苏联各地的分裂、分离运动的闸门。就在改革、保守两派争论不休、苏联经济每况愈下时,前苏联除俄罗斯以外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倾向日趋明显。从1988年初到1989年,在亚美尼亚、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克兰,来自底层的分离运动与经济保障、政治民主、个人自由的各种诉求合为一股力量,严重地动摇了各地党政机构权力的合法性;戈尔巴乔夫的“透明化”运动实际上对各地的分离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一切是改革的始作俑者始料不及的。马里亚认为,前苏联领导人之所以错判形势,是由于俄罗斯中心主义(Russocentric)的自大和天真。诚然,俄国在二十世上半叶已攫取了周边大片疆土,但俄国人在这些地区统治的合法性一直是个问题。戈氏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目的是要削弱中央官僚体制,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周边地区控制的削弱。这本来是一个常识问题(第325-326页),但戈尔巴乔夫却完全忽视了民族分离、分裂的危险。
“重建”苏联经济未果,推动政治“透明”遇阻,戈尔巴乔夫最后在1989-1990年启动激进的民主化进程,以期解开苏联政治、经济的死结。根据马里亚的观察,1989年的民主选举苏维埃人民代表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一向令人生畏的苏共一夜之间开始惧怕平民百姓了(第327页)。在1989年5-6月间,苏联电视台在两个星期里实况转播最高苏维埃代表会议,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代表实际上把大会变成了对苏共进行控诉和批判的大会。与此同时,大会并未就困难重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提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到了7月份,苏联各地开始出现各种形式的公民社团,实际上开始干预和管理地方事务。至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入死胡同。其结果是旧制度瓦解的速度远超过新体制建立的速度,或者说破旧而未立新。更确切地说,1989年苏联的问题是旧制度拒绝死亡,而新制度无力出生。到当年秋季,莫斯科已有政变的传闻(第331-332页)。至此,前苏联制度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了。
马里亚的这篇文章止笔于1989年底(Daedalus杂志1990年1月号),离莫斯科的“8·19”政变还有20个月。事态的发展从多方面验证了其逻辑和预测的准确性,正如马里亚在该文一开始引用法国作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名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开始改革之日(The most dangerous time for a bad government is when it starts to reform itself)”。而在这同时,西方苏联学的主流仍陶醉在对戈氏改革的赞歌之中,中情局也仍在编织苏军强大的神话,美国高层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寄予厚望。
四、X与Z:非主流派的沉浮
从凯南冷战宣言式的“X”长文,到苏联解体前夕马里亚的“Z”调“挽歌”,西方/美国的苏联学走过了43年轰轰烈烈的历程。在政府、军方、情报界、学界和私人的合力下,形成了美国“外国研究”(foreign studies)最庞大的“国别/地区研究”(country/area studies)体系,同时也对西方/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二者之交叉、借鉴和互补,几乎难分彼此,构成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环节。由此产生的众多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反过来又影响着苏联研究的发展。
X的身份是外交官,Z则终身执教。两篇文章发表时间相差近半个世纪,但都文笔犀利,逻辑严密;谈古论今,一气呵成;不仅有论述,也有政策建议。虽然二人侧重点不同(凯南侧重苏联的外部行为;马里亚则聚焦于苏联内政), “X”“Z”二文在西方繁缛枯燥、过分学究式的书山学海中,都有相当的可读性。在方法论上,二人都是从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虽然都因发表匿名文章而名声在外,然而二人在各自领域(政策界和学界)内却均不得志。凯南出名后,美国外交界和政策界日益强烈的意识形态化,使他倍感忧虑又无回天之力,只好自我“流放”到学界。马里亚在成名前的几十年间也难以苟同学界四平八稳的实证主义流派,于是对苏联的看法日趋极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凯南与马里亚的为学和个人境遇虽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在对前苏联体制和行为的认知方面,二人几乎是南辕北辙。
马里亚对前苏联政治史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和分析有强烈的价值观取向,对前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有刻骨仇恨。与事事考证、自我标榜价值中立的西方社会科学主流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完全不同,倒是与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更为相近。二战以后,西方苏联学一度由“集权主义”模式主导;此后社会科学的发展陆续开辟了众多的模式,比如发展理论(developmentalism)、官僚/机构模式(bureaucratic-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研究等。这些治学路径(approaches)和方法论被陆续引进苏联学,对传统的集权模式造成强烈冲击,并从六十年代起逐步取得了主导地位。在西方的苏联史学界,普林斯顿大学的斯蒂芬·科恩(Stephen F.Cohen)1980年出版的《布哈林传》(25),以及影响了西方整整一代新左派的伊萨克·戴舍尔(Isaac Deutscher)三卷本的《托洛茨基传》(26),对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本身并不完全否定,而是认为苏联有可能回到类似二十年代那种更为人道的新经济政策的政治环境。
事实上,西方苏联学在六十年代“转向”、致力于寻找和发掘一个“正常的”苏联,这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内部的政治走向息息相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深陷越战,经济不振;国内政治危机重重,暗杀成风(肯尼迪总统和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分别于1963年和1968年遇刺身亡),民权和反战运动高涨,美国制度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与此同时,作为美国制度对立面的苏联似乎蒸蒸日上,对西方左派和自由派人士有强烈的吸引力。像戴舍尔这样探求人性化共产主义的学者,在学界和战后“婴儿潮”一代人中的影响力剧增。西方/美国学界一直由中间偏左的自由派占据,乃是六、七十年代新左派运动的惯性使然。而在西方知识界向左转的大潮中,马里亚认为根本不存在人性化的共产主义。在他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过是通向集权的第一步,戈尔巴乔夫主义不过是这一制度的最后挣扎而已。(27) 这种“极端的”、非学术的观点,在西方的苏联学界无疑属于“另类”,并一直被边缘化。(28) 在此种大环境下,马里亚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学界那些他认为只注重表象的经验主义学派缠斗,而最终以Z文震动学、政界。两年后苏联解体,马里亚从伯克利退休,功成名遂。
五、苏联之命运:在必然与偶然之间
马里亚虽然相对准确地预见到了苏联的解体,但这更出于他的极端意识形态化的信念:即苏联的制度是邪恶的,而邪恶的制度是不可能持久的。事态的发展与其说验证了马里亚的预测,不如说是实现了他的企盼。在治学/研究方式方面,无论从历史或逻辑的角度,马里亚都并非无懈可击。从历史上看,前苏联的政治制度显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集权”特征多多少少是承袭了俄国传统制度的特色。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中叶的农奴制在欧洲绝无仅有,而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沙俄逐渐成为一个警察国家也是不争的事实。此外,马里亚一味淡化或贬低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历史意义,认为苏联制度本身并没有根本改变,从而断定该制度必定消亡。然而这并不能抹杀一个基本事实,即对前苏联绝大多数人来说,后斯大林时期政治运作的方式和制度的包容性,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至少,斯大林时期人人自危的恐怖感已大为降低,一般民众和官员的日常生活开始了某种“正常化”。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是通过政策而非政体的改变而实现的,社会和民众所付出的代价显然比革命性的变化要小得多。同样的道理,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政治至少在体制内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在对外政策方面,戈氏对东欧和阿富汗不仅仅是“撒手”,而且是一种在哲学上和道义上与前苏联以致俄罗斯传统的帝国理念告别。戈尔巴乔夫这样做是冒了极大的政治风险的,没有勇气和魄力的平庸之辈难有如此境界。而美国的政治精英在对周边小国和弱国的政策上,一直在实行门罗主义;不仅如此,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实际上是将门罗主义放大到全世界。
戈尔巴乔夫国内改革的最后失败是悲剧性的,但并不能因此断定其改革动机就是为了维护在马里亚看来是“邪恶”的制度。戈氏改革裹足不前,最终失败,不仅有众多必然的和结构性的因素,而且不排除偶然因素。事实上,造成改革后期急转直下的局势是有多种变量的。社会变迁与自然界的变化不同,是不大可能加以精确预测的。尤其是苏军在改革后期逐步政治化,为1989—1991年的苏联政治动荡注入了极大的不确定因素。(29) 在更深的层次,马里亚在z文中为前苏联的历次改革所设计的“要么不改革——要么打碎一切”的两个极端的结局,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主要思想流派的极端性。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力图严格按照自身的模式和逻辑改造世界,都追求各自体制的最高纯洁度和完美性,都拒绝第三条道路,都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看作是零和游戏,毫无妥协的余地。马里亚的思维方式就是此种极端宗教性的、僵硬的意识形态的表现,也是违反常理的。现实是一个是充满灰色地带、黑白皆有、善恶混杂的“混沌世界”。戈尔巴乔夫在内外政策上的改革,实际上走出了典型的西方意识形态的零和式思维。凯南的现实主义也排斥意识形态的极端性,可惜在美国难有容身之地。
其实就是在马里亚执教的美国,宪法保护下的自由也一直是有条件的。马丁·路德·金所称的“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在二战以后一直在容忍甚至纵容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30) 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精英最终放弃种族隔离,实行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上与前苏联争夺道德制高点。一个在美国看来是“邪恶帝国”(evil empire)的前苏联,客观上迫使美国向更民主、更平等的社会迈出了一大步。以此观之,戈氏改革的最大失败,是在国际体系层面造成严重失衡:侥幸获得单极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实际是在情不自禁地走向帝国。而且,它不仅在国际上为所欲为,在国内政策上也开倒车,开始逐步放弃很多对少数族裔的优惠政策。(31)
与马里亚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和“先苦后甜”的经历相反,凯南则更注重前苏联对外政策的“行为”(behavior)。他对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关注在于其与对外政策的关联,对苏联内政事务则静观其变,由此认为美国和西方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对苏联的对外扩张加以遏制。(32) 其实X文有两个版本。在1946年初凯南即将卸任美国驻苏使馆代办前发给华盛顿的5300字的“长电”中,把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定义为“俄罗斯传统的和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只是在俄国革命后,这种不安全感才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相结合。(33) 凯南的电文引起了对苏强硬派海军参谋长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Forrestal)的注意,他力促凯南将此电文公开发表,这就是后来发表在《外交季刊》1947年7月号的X文。然而X文中,只是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定位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源,完全不提俄罗斯对外部世界的“传统”的不安全感,这当然包括十九世纪初拿破仑侵俄,更不用说不久前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无独有偶,X文发表前四个月,杜鲁门总统在对国会的演说中,也借用凯南的“遏制”概念,正式推出“杜鲁门主义”。在演说中,杜鲁门强调世界已分为自由与集权两大阵营,美国必须以4亿美元经援军援土耳其和希腊,以制止苏联对这两个国家的“侵略”。在演说中,杜鲁门也只字未提俄罗斯“传统”的不安全感,仅仅把苏联描绘成意识形态的洪水猛兽。凯南事后对杜鲁门政府的“断章取义”十分不满,认为杜鲁门主义严重歪曲了他的本意,由此引发的冷战过于意识形态化、过于强调武力的作用。他认为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援毫无必要,而且会挑衅苏联。不仅如此,凯南在以后近60年的余生里,致力于反对美国历届政府对外政策中日益军事化、意识形态化和泛道德化的趋向。(34)
X和Z文及其作者的经历,仅仅是美国和西方在冷战时期苏联研究巨大冰山的一角。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代表这一领域中的“诸子百家”,然而却在不同时期以不同角度折射出这一领域中主要学派,以及这些理论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凯南和马里亚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文章发表前后的个人经历和命运。凯南以X文出名,却因美国的对苏政策日益意识形态化而逐渐远离决策中心,几乎成为“体制外”人士。但他却仍坚持现实主义的观点,直到2005年辞世。Z文的意义在于,走向斯大林墓地的不仅有苏联体制,还有伴随着这一体制的西方苏联学。美国的苏联学也由此改头换面为俄罗斯学或欧亚学(Eurasian studies)。
六、理论、常识与决策
凯南和马里亚二人的经历,还揭示了另一个问题,即美国的苏联研究与美国的对苏政策之间的“不同步”现象。美国/西方学界在六十年代以后逐步走向非意识形态化,至少主流是如此。与此同时,美国的对苏政策和整体外交政策,除了尼克松政府的短暂时期,基本上都是意识形态化的。(35) 究其原因,这既有无处不在的麦卡锡主义,也有“美国特殊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缘故。(36) 美国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霍斯泰德尔(Richard Hostadter)曾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其命运不是有没有意识形态,美国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化身”(It has been our fate as a nation not to have ideologies but to be one)。(37) 在这一基础上,北卡大学历史学家马克·亨特(Michael Hunt)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一书中,描述和分析了美国意识形态的三个组成部分:1)民族自大情结(feeling of national greatness);2)以种族和肤色来区别和看待他国人民;3)怀疑、惧怕和反对革命。(38) 总之,作为一个没有深层文化的移民国家,美国必须以意识形态作为其民族凝聚力。(39) 对于美国对外政策中非现实的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美国现实派大师基辛格在“9·11”数月前出版的《美国还需要外交吗?》一书中认为,美国六、七十年代深陷越战而不能自拔,不是因为美国过度使用武力,而是由于美国过度推行其价值观。不考虑历史条件而滥用道德标准,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到了克林顿时期,美国除了军事和经济政策以外,已无真正的外交可言了。(40)
一个拥有阵容最强大的国际关系学的国家何以“没有”了外交?拥有最庞大的苏联研究和最强大的情报系统的美国为何没有预见到苏联局势急转直下的可能?而这些失误与西方对苏联研究的投入根本不成比例。原因何在?是研究资料的问题还是判断有误?是价值观念的问题还是方法论的问题?其实美国学界和情报界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不是第一次犯类似的错误。包括对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判断,对伊朗、朝鲜、日本(1941年珍珠港事件)、甚至“9·11”恐怖袭击,都曾出现过巨大误差。在苏联学和地区研究以外,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也常常对研究对象误读、误判、误导。(41)
上述问题可以从多方解读。然而学界和政策界的“不对称性”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有效的外交并不一定依赖学术理论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外交更是一门艺术而非学术,其成败取决于领袖人物和精英团体的战略洞察力,而非简单地依靠对对方的大规模的技术性侦查;是把握战略机遇的大智大勇,而非时时处处标榜自身、贬低他人的小动作和小聪明。而这些外交的艺术和智慧在美国的对苏和对外政策中,似乎是日益短缺。2009年1/2月号的《国家利益杂志》刊登了安德鲁·克莱比奈维茨(Andrew Krepinevich)和白瑞·沃茨(Barry Watts)的题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里少了什么?”的文章,指出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部门的战略判断力和决策力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下降,这当然包括对苏联的评估、战略和政策。(42) 相对来说,20世纪前半叶,美国在国际社会以外交为主导,军事上后发制人,其业绩可圈可点。这包括1900年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不费一枪一弹就获得了进入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权利,又在名义上维持了中国的“统一”;1905年小罗斯福总统在日俄之间调停,因此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私下里又得到了日本对美国侵占菲律宾的认可;美国在一战各交战国筋疲力尽时介入欧战,1919年又以民主和民族自决的道德制高点,打开了美国介入欧洲和国际事务的大门;甚至美国在1941年以前的中立政策,都是美国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地缘战略资源,从交战各方攫取最大利益。为此,当时还是参议员的杜鲁门曾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上风,我们就应帮俄国;如果俄国占上风,就要帮德国。让他们自相残杀好了,尽管我无论如何也不希望希特勒赢。”(43)
可以说,美国大战略意识衰落的拐点是越战。历时11年(1964-1975)、耗费万亿美元的越战,除了造成数百万的伤亡以外,美国所得到的唯一的“积极”遗产,恐怕只是历久不衰的百老汇保留剧目《西贡小姐》(Miss Saigon)。孜孜寻求敌人、刻意夸大对方实力,从来就是中情局的“职业病”。这包括肆意夸大前苏联的实力,断定萨达姆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与此同时,美国庞大的情报体系居然未能感受到“9·11”恐怖袭击前山雨欲来的种种迹象。就此,英国记者乔纳森·帕维尔(Jonathan Power)在“9·11”三天过后一篇题为“世人皆知,只有美国蒙在鼓里”的文章中指出,恐怖袭击是针对美国在九十年代的一系列政策。美国在巴以冲突、全球温室效应、海外驻军、反导等一系列问题上唯我独尊的(take-it-or-leave-it attitude)处世方式,使美国处于自我毁灭(self destructive)的境地。帕维尔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傲慢与偏见,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报复。任何政治运动都可能产生诉诸暴力的少数极端分子,但这并不等于这些运动的主流是错误的,它们总是事出有因(elements of truth)。对此,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唯有美国由于其大部分政治领袖和媒体的自我封闭而蒙在鼓里,对“9·11”袭击大惑不解。(44)
其实,国与国相处的最基本的原则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老话。在美国学界中,除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以外,绝大多数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定义、假说和概念,似乎连这一基本常识都不具备。在美国的外交和对苏政策中,兼顾对方利益的想法和做法更是少见。对此,前国务卿基辛格说:“美国是对苏联对外干涉主义最严厉的批评者,但美国本身却从未接受过不干涉内政的原则。”(45) 冷战期间,前苏联的核报复能力可能是唯一使美国保持自身行动平衡的清醒剂;而美国三权分立的内部结构,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制衡作用。(46)
注释:
① George Kennan,“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Foreign Affairs,July 1947.
②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历届国家安全顾问中,从未有“中国通”。
③ 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5th edition,New York:Knopf,1978.
④ Kenneth N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
⑤ 有关“大三角”的主要著作有:Joseph L.Nogee,“Polarity:An Ambiguous Concept”,Orbis 18,Winter 1975; 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Boston:Little,Brown,1979,esp.837; Ilpyong Kim,ed.,The Strategic Triangle: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Paragon House,1987; Herbert J.Ellison,ed.,The Sino-Soviet Conflict:A Global Perspective,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2; Gerald Segal,The Great Power Triangle,London and Basingstoke:Macmillan Press,1982; Gerald Segal,ed.,The China Factor,London:Croom Helm,1982; Douglas T.Stuart and William T.Tow,eds.,Chin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West:Strateg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in the 1980s,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2; Strobe Talbott,“The Strategic Dimension of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Enemy of Our Enemy,or True Friend?”in Richard R.Solomon,ed.,The China Factor,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1; Lowell Dittmer,“The Strategic Triangle: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World Politics,Vol.33,No.4,July 198 I; Kenneth G.Lieberthal,Sino-Soviet Conflict in the 1970s:Its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ategic Triangle,Santa Monica,Calif.:Rand Corporation,1978; Steven I.Levine,“China and the Superpower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0,Winter 1975-76; Min Chen,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d Regional Conflicts:Lessons from the Indochina Wars,Boulder,Colo.:Lynne Rienner,1991; Harvey W.Nelsen,Power and Insecurity:Beijing,Moscow,and Washington,1949-1988,Boulder,Colo.:Lynne Rienner,1989.
⑥ 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 1986.
⑦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no.16,Summer 1989.
⑧ 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es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summer 1993.
⑨ Russell Bova,How the World Works,1st ed.,Longman,2010,pp.24-25.
⑩ Walter LaFeber,A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1945-2006,10th ed.,McGraw-Hill,2008,pp.344,349.
(11) 见Richard A.Clarke,Against All Enemies:Inside America's War on Terror,New York:Free Press,2004.
(12) Walter LaFeber,A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1945-2006,10th ed,pp.344,352,355.
(13) 引自麦迪逊给理查德·布什的信,1821年11月20日,in James Madison,Letters and Other Writings of James Madison,Philadelphia,1867,III,pp.235-236,cited by Walter LaFeber,A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1945-2006,10th ed.,p.349.
(14) 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是这一时期典型的乐观派,“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1988; 另见Michael Kaufman,“Martin Malia,80,Soviet-Era Skeptic,Die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4,2004,http://www.nytimes.com/2004/11/24/obituaries/24malia.html.
(15) 在前苏联存在的74年里,各种预测苏联消亡著作不计其数。其中主要的学者以及著作有:George Orwell,James Burnham 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London:Socialist Book Center,1946); Ludwig von Mises,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1); Robert Conquest,The National Killers:The Soviet Deportation of Nationalities (The Macmillan Company,1970); and Zbigniew Brzezinski,Dilemmas of Change in Soviet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Between Two Ages: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 (Greenwood Press,1970),The Grand Failure:The Birth and Decay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9).然而上述预测均未引起Z文所造成的轰动效应。
(16) Z,“To the Stalin Mausoleum”,Daedalus,vol.119,no.1,winter,1990,pp.295-344.“代达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建筑师和雕塑家,传说曾为克里特王国建造迷宫。
(17) 1993年,马里亚出版了The Soviet Tragedy:A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Russia 1917-1991(Free Press,1994)一书,基本沿用了Z文的观点。
(18) 甚至美国政治学泰斗亨廷顿在其1968年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也把前苏联的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提并论。见Samuel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19) 其代表作为:Robert Tucker,ed.,Stalinism,Essays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New York:Norton,1977.
(20) 对“现代化”问题(modernization)的研究是二战后西方社会科学所致力的重要议题之一。有关苏联“现代化”的研究,见Richard Lowenthal,“Development versu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in Chalmers Johnson,ed.,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Richard Lowenthal,“Beyond Totalitarianism?”and Michael Walzer,“Failed Totalitarianism”,in Irving Howe,ed.,1984 Revisited:Totalitarianism in Our Centur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3.
(21) 马里亚把“机构性多元主义”的代表作Jerry Hough与Merle Fainsod的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一书,与Fainsond本人1963年出版的How Russian Is Ruled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相对比,认为后者是建立在“集权主义”模式基础之上。
(22) 此种观点的主要著作有Sheila Fitzpatrick,ed.,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1928-1931,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78; Sheila Fitzpatrick,The Russian Revolu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23) 见Abram Bergson,The Real National Income of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2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24) Robert Conquest,The Great Terror,New York:Macmillan,1968; Roy Medvedev,Argumenti I Facty,September 1989,cited from Z,op.cir.,note25,p.342.
(25) Stephen F.Cohen,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A Political Biography,1888-1938,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26) 伊萨克·戴舍尔分别于1954年、1959年和1963年出版了托洛茨基的三部传记:The Prophet Armed:Trotsky,1879-1921(1954),The Prophet Unarmed:Trotsky,1921-1929(1959),The Prophet Outcast:Trotsky,1929-1940(1963),见Isaac Deutscher,The Prophet:Trotsky:1879-1940,Vol.1-3,Verso,2009.出生于波兰的戴舍尔二战时移居英国,后在西方多所著名大学讲学。其托茨斯基的传记是戴舍尔在哈佛大学多年研究的结晶。
(27) 见The Soviet Tragedy:A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Russia 1917-1991,Free Press,1994.
(28) Michael Kaufman,“Martin Malia,80,Soviet-Era Skeptic,Dies”,The New York limes,November 24,2004,http://www.nytimes.com/2004/11/24/obituaries/24malia.html.
(29) 苏军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政治化”,表现出以下若干现象:(1)1989—1990年的选举改革,首次允许苏军参与推选军人代表参加选举并进入最高苏维埃。而在改革后期的动荡时期,军人代表往往“被迫”在不同的政治派别中进行选择。(2)由此导致一些少壮军官质疑甚至公开挑战上级。(3)1990年初开始,苏军和苏内务部高级将领日益强烈要求对国内的分离主义倾向和动乱采取强硬措施,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事实上,苏军作为一个整体,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满,主要原因是从东欧撤军、与美国达成中导协议等,对苏军的利益和士气损害极大。(4)俄罗斯联邦1990年总统选举中,两位总统竞选人叶利钦和尼古拉·瑞斯科夫(Nikolai Ryshkov)的竞选搭档都是军人,苏军内部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态度已呈分裂状态;政客也竞相拉拢军中派别以壮声势。(5)苏联党、政、社会日益深化的改革与保守的分歧,也在苏军内部日益显现,最终驱使苏军保守派于1991年8月19日发动政变:但苏军本身已经严重分裂,军中改革派随即反击,使政变迅速瓦解。详见Yu Bin,“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Transition of Communism:China and Russia”,Curren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Russia,vol.4,no.3/4,New York:Nova Science,1995,pp.237-246.
(30) 见Martin Luther King,Jr.“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 [King,Jr.]”,16 April 1963,http://www.africa.upenn.edu/Articles_Gen/Letter_Birmingham.html.
(31) Yu Bin,“America's War against Racism”,Asia Times online,June 26,2003,http://www.atimes.com/atimes/Front_Page/EF26Aa01.html.
(32) Walter LaFeber,A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1945-2006,10th ed.,pp.60-72.
(33) Barton Bernstein and Allen Matusow,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 Documentary History,New York,1966,pp.198-212.,凯南的“长电”全文,见http://www.gwu.edu/~nsarchiv/coldwar/documents/episode-1/kennan.htm.
(34) 关于凯南的“失宠”经历,见Walter LaFeber,A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1945-2006,10th ed.,pp.61,66-67,69,70-71,104,134,208-209; 关于美国对外政策日益军事化、意识形态化和泛道德化的趋向,见Henry Kissinger,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NY:Touchstone Books,2001; George Kennan,American Diplomacy,expanded edi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 Walter LaFeber,The American Age,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 1750 to the Present,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nd edition,1994.
(35) 见于滨,“‘9·11’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兼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上海美国研究所,论文,2006年6月。
(36) 引自Godfrey Hodgson,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p.1.
(37) Michael Hunt,Ideology and U.S.Foreign Policy,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38) Ibid
(39) Samuel 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97.
(40) Henry Kissinger,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NY:Touchstone Books,2001,chapter 1,pp.236,258.
(41) 见于滨:“‘9·11’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兼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上海美国研究所,论文,2006年6月。
(42) Andrew Krepinevich and Barry Watts,“Lost at the NSC”,The National Interests,January 6,2009,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aspx?id=20498.
(43) 见Walter LaFeber,A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1945-2006,10th ed.,p.7.
(44) Jonathan Power,“Everyone but US could see it comi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eptember 14,2001.
(45) Henry Kissinger,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p.237.
(46) 见Steven Hook,U.S.Foreign Policy:The Paradox of World Power,3rd ed.,CQ Press,2010,第五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