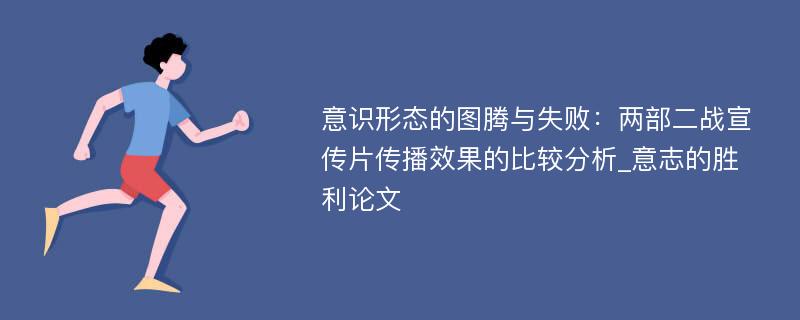
意识形态的图腾抑或失效——关于两部二战宣传电影传播效果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图腾论文,两部论文,效果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09)07-0044-05
同为二战时期著名的宣传电影,德国纳粹的《意志的胜利》和美国的《我们为何而战》却一直没有被放在同样的理论框架下予以阐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研究《意志的胜利》的主要是电影学者、美学家和哲学家,他们往往会从视听语言、美学表征、意识形态内涵等角度对这部电影做出分析,并将这部电影的传播效果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传播结合在一起,得出鲜明的纳粹批判的结论;相形之下关注《我们为何而战》的却更多的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他们着重于考察这部电影究竟传达了什么内容,进而在观众身上产生了什么样的(行为、态度的或心理的)影响。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梳理关于这两部电影研究的理论话语,力图找到这两部电影背后蕴含的一种共同的理念运作的规律——电影意识形态传播效果的规律。
《意志的胜利》:意识形态图腾崇拜的例证
探讨电影媒介与政府和政党宣传的关系,里芬·施芬塔尔无疑是无法忽略的人物。是她在电影发展早期就将这一作用推上极致,她的两部作品《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成为用电影影像宣传极权主义的典范,尤其是前者。分析这部电影,成为破解法西斯宣传蛊惑策略的重要密码。
《意志的胜利》的内容是纳粹在纽伦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这部电影被桑塔格称为是“迄今为止最成功、最地道的宣传性影片,它的构思概念本身就否定了影片的制作者具有独立于宣传之外的美学或视觉概念的任何可能性。”①从传播效果来看,《意志的胜利》是极其成功的。据当时的新闻媒体报道,这部影片在德国及西方国家放映时引起巨大轰动。狂热的巴黎影迷把里芬·施芬塔尔抬到肩上,拥抱、亲吻,甚至把裙子也撕坏了。②这部电影同样获得电影评论界的广泛认可,它获得“国家电影奖”、威尼斯影展的金奖和巴黎世博会的最佳电影奖。这部电影在欧洲各国巡回放映时,受到空前的欢迎,甚至连斯大林也给里芬·施芬塔尔写了亲笔信,对电影表示赞赏。直到今天,这部电影依旧是研究电影美学,尤其是研究电影纪实美学的经典文本,其艺术价值早已得到确认。而这种艺术价值和极其反动的纳粹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又成为该片导演最为人诟病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和“善”的冲突在《意志的胜利》这部电影中被表达到极致,施芬塔尔因此被称为“永远有罪的玫瑰”。
思考这部电影获得良好传播效果和口碑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部电影的拍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它担负着鲜明的政治任务,没有任何商业压力。这样,传播者就会形成“重视受众”却“不尊重受众”的受众观念。重视受众,因为要完成所谓的政治宣传任务,得让他们听电影的话;不尊重受众,因为只要他们听话而不需要有自己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志的胜利》的成功体现了“枪弹论”的合理性,里芬·施芬塔尔是在用电影的语言和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遥相呼应。
在拍摄过程中,施芬塔尔具有随心所欲的预算和一个由120多人组成的庞大摄制组和几十架摄影机可供调配。国家拨款的资金来源决定了这部电影的传播效果必须对政府负责而不需要对观众负责。所以后来很多电影研究者认为这部电影名义上是纪录片,其实是剧情片。关于这一点,施芬塔尔自己也承认:纽伦堡大会“不是作为一个壮观的群众集会而构思的,而是作为壮观的宣传性影片而设计的……所有的仪式,以及游行、阅兵、群众队伍,背景的礼堂和运动场的建筑设计都考虑到要为摄影机提供便利。”③在她眼里,纽伦堡大会的举办目的,并不是为了开会,而是为了拍电影。会议的实际支配者并非希特勒(政治目的),而是施芬塔尔(视觉传播的目的)——电影画面的摄制比实际情况更重要,不是为了记录,而是为了宣传。其次,《意志的胜利》的电影语言充满了感性魅惑。意识形态搭载这种魅惑容易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即在电影画面语言的感性直观的作用下下,观众的情感会产生激奋,最终认同影片所宣传的纳粹思想——意志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胜利的。电影意识形态的图腾就形成了如下的线索:电影技术——画面——激发激奋的情感——认同某一意识形态。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典型画面来分析这一命题:
在影片刚刚开头的时候,是纳粹元首希特勒的飞机在云层中穿行,然后突破云层,在太阳的辉映下降落到地面。这组画面极具象征意义,它表征着希特勒引领着德国人穿越了重重迷雾走向历史的坦途。同时,希特勒被塑造成一个类似从天而降的神灵,他到人间来拯救德国人。这完全符合当时德国人对希特勒个人形象的心理期待。影片还表现了很多个人崇拜的镜头,如画面对德国民众行纳粹礼的表现:无论是在街道、广场还是在纽伦堡大会的会场,德国人见到希特勒都笔直地伸出右手,贴在右耳边,这是用纳粹礼向希特勒致敬。施芬塔尔会用中景表现出树林枝干密布般的行礼的手臂,在展示希特勒威望的同时也展示了一种审美上的气势,对于观众来说,这种气势具有咄咄逼人的压迫感。同时,施芬塔尔也擅长用现场同期声和音乐来表现“希特勒伟大”的效果,整部作品没有解说,全部运用现场声音及配乐:人群的欢呼、党员呼口号、乐队的演奏、行进的军歌。在希特勒演说的时候,也完全用现场同期声,强化希特勒的面部表情和手势。
第三,这部电影成功地体现了法西斯美学的力量,即它是从“对情境的控制、服从行为和狂热效应的迷恋中”建构了一种“主宰/奴役”的二元维度的美学,这就是④:
成群集结的人;把人向物转换;物的增多以及人与物均围绕一个无所不能的、有催眠术的领导人或领导力量集结。法西斯舞台艺术的中心是强大的力量和它的傀儡之间的狂热交替。法西斯的舞蹈设计师无穷尽的动作和凝结的、静止的和“有男性气概的”架势之间的交替。
法西斯美学是要塑造这样两种艺术意象:一个完美、极富魅力且具有强大力量的偶像和众多的追捧、服从偶像并且随着其指令而运动的追随者。所以,法西斯的传播一定是一方面夸耀偶像的魅力和力量,另一方面歌颂追随者的屈服和愚昧,最终歌颂具有宗教献祭意义的死亡。在1930年代的德国,电影作为有组织的大众传播自然特别适合这种美学的传播,传播格局的不对等——拥有传播媒介的传播者和被动信息接受的大众极易形成“主宰/奴役”的传受格局。
总之,施芬塔尔证明了电影是展示法西斯美学的最佳载体。电影可以按照十全十美的原则直接生产幻象。在拍摄《意志的胜利》的时候,很多镜头被多次重拍,这说明她丝毫没有纪实精神,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宣传的目的,而这种目的也被证明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我们为何而战》:电影宣传的有限效果
如果仅仅凭借《意志的胜利》就判断电影具有良好的意识形态传播效果那就错了,我们可以在电影史上找到完全相反的例证。这就是《我们为何而战》这部纪录片在美国播映时候所遭遇的意识形态传播的尴尬。
1941年12月7日,日本未经任何警告就悍然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为了能够有效地进行战争动员和宣传,尤其是要成功地“将市民变为士兵”,美国军方力图用电影这种传播艺术手段进行战争知识的普及和军队士气的鼓舞。于是在1942年,时任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招募好莱坞著名电影制片人卡普拉制作了7部电影,即《我们为何而战》的系列片。这部系列片的指导思想也是以宣传为导向的,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乔伊特的考证,卡普拉当时是在施芬塔尔的强烈刺激下来制作这部系列片的,“他希望以此反击《意志的胜利》的效果”。⑤
电影播出之后,霍夫兰等社会心理学家对这一事件产生的效果进行了追踪调查,这些研究证明了卡普拉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因为这些电影并没有达到鼓舞士气、改变士兵对战争态度的作用。最终的结论有点令人沮丧,它们是:⑥
1.《我们为何而战》在增进人们关于导致战争发生事实的知识方面有明显效果。……
2.这些影片在改变人们的观点方面也有明显的效果,影片所得出的这些观点是建立在对电影内容的分析和从这些分析中得出的预期观点的基础上完成的。
3.这些影片在改变人们那些独立于电影内容以外的、自然形成的观点方面仅有微弱的效果,而电影完成导向性效果的目标正是由电影的内容完成的。
4.这些影片对于增进人们从军和战斗的动机方面没有任何效果,而这才是这个项目被赋予的最终极的目标。
我们或许可以这么来总结,这些电影在“理性”层面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传递了相应的知识和信息,并藉此灌输了一些观点给受众,但在“感性”层面收效甚微,这表现在观众在对待战争所采取事情的“动机”方面没有任何变化,这和前文所述的《意志的胜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感性传播和作为整体的大众:影像艺术宣传有效性的来源
同样是电影宣传,希特勒通过施芬塔尔可以有效地宣扬其“法西斯美学”,而美国国防部却未能成功地鼓舞士兵的士气,增强他们参战的动机,个中原因,颇能引人思考。
首先,《意志的胜利》的宣传强调的是散布一种集体性的感性魅惑,这是《我们为何而战》最为缺乏的元素。施芬塔尔所秉承的法西斯美学追求巨大的社会规模,它是一种群体性的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反个人、反启蒙的;同时,它还追求一种类似于酒神精神的审美效应,它将人的感性的力量推到极致,它是反理性的;这种美学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是一种“施虐/受虐”的美学,它是建立在偶像崇拜和群体服从的基础上的。其实,最能概括法西斯美学特性的是希特勒自己在《我的奋斗》中说到一句话:“领袖应该永远专注于启发群众,并时常处在一种驱使他们行动的歇斯底里状态之中。”⑦法西斯美学的三个关键词都包含其中——“领袖、群众和歇斯底里”。在这一格局中,人往往处于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中,这正是沃林所谓的“非理性的魅惑”的结果。一方面,视觉感性的力量被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群体性的社会结构配合并强化了这种力量的发挥。
其次,法西斯艺术追求非理性,这使它走向复古主义。在艺术领域“复古”本无可厚非,但法西斯的“回到古典”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是使得人们会丧失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从而回到人类童年时期的思维水平。用维科的话来说,这种非理性的背后其实是诗性思维运作的结果。诗性思维又被称为形象思维,它是人类在童年时期具备并普遍采用的一种思维能力,这种思维凝聚出神话、宗教等审美意识形态,它是原始人对世界不理解进而惊奇地想象的产物。维科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特宜于诗的材料是近情近理的(可信的)不可能”。朱光潜先生举例解释这句话:“例如雷神操纵雷电,是种不可能,但是原始人仍深信不疑,因为对于原始人的想象力来说,这还是近情近理的。所以原始的想象虽不夹杂理智活动,却不因此就成了没有理性的或不可信的。”⑧由雷声构想出雷神,这就是典型的诗性思维,这是原始人(人类童年时期)的理性。“诗性思维”的对象是自然以及人们想象的自然背后的人格神,它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形成了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使得人的精神有所皈依。在纳粹德国的背景下,“诗性思维”最终结果也形成了德国人对纳粹的信仰,但它的思维对象却是机械、武器、民族国家等现代性叙事话语,它处理的是(德国)人与杀人武器、领土扩张、民族地位等等之间的关系。按照诗性思维的运作逻辑,它最后会抽象出一个“人格神”。那么在30年代的德国,这个人格神必然是希特勒。
前文我们已经论述,它虽然号称“纪录片”,但这部电影从拍摄到剪辑都充满了主观的创作和意识形态的引导,被精心制作的画面同时被精心植入了意识形态的内涵。由于看画面的时候,人们动用的是“诗性思维”,故而会想象这些画面背后的人格神。在维科看来,这是“以己度人的隐喻”。在《意志的胜利》这部影片中,希特勒的形象始终是突出并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无论是在会场中的演说(希特勒演讲,众人倾听并伴以雷鸣般的掌声和如林般的敬礼的手臂),还是在广场上举行仪式(希特勒个人作为检阅者而成为中心,其他人要么是作为随从而尾随,或者作为检阅对象而排列成巨大的队伍造型以展示国家和民众的力量),希特勒都被电影塑造成这一壮观景象的力量源泉。这样的电影图像会让观众自然而然地将眼睛所看到的壮美、崇高等等意象与希特勒个人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以己度人的隐喻”。维科曾经举例解释这种隐喻的内涵:⑨
当人们对产生事物的原因还是无知的,不能根据类似事物来解释它们时,他们就把自己的本性转到事物身上去,例如普通人说,“磁铁爱铁”。
人与人之间互相喜欢进而拥抱在一起,是因为“爱”的情感。当人们看到磁铁吸铁,找不到真正的原因的时候,就凭借自己的心理经验,把磁铁想象为对铁有爱情。同样的道理,当观众被《意志的胜利》壮观的画面所震惊的时候,他们同样不知道形成这些画面的真正原因:希特勒、戈培尔等在资金人员上的巨大支持,施芬塔尔的精彩构思,还有电影拍摄的各种技巧以及这些技巧给观众的眼睛造成的错觉等等。他们看到电影中希特勒的演讲引发轰动,就认为他的演讲真的精彩并且是真理。当他们看到电影中人们纷纷伸出手臂表达对希特勒的敬意的时候,他们真的认为希特勒具有足够的魅力值得人们这么做。当观众看到纳粹军人在希特勒的指挥下言听计从的时候,他们认为希特勒真的具有这样的力量。如此,希特勒被电影赋予了一种巨大的合理力量,观众由于不理解镜头背后的逻辑而认同了这种赋予。
《我们为何而战》的拍摄思路则完全不同。如果说,《意志的胜利》的传播手段是煽情与感染,那么《我们为何而战》则是叙事与说理,即它的拍摄目的是教育,而且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教育。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被卷入战争。但军方忽然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美国人民尤其是美国士兵对战争的无知。他们知道的仅仅是:⑩
“日本人是混蛋”,因为他们鼠窃般地轰炸了珍珠港。“德国人是卑鄙的”,因为他们占领了欧洲很多国家并想统治整个世界。
而下面的这些更重要的信息他们是不知道的:(11)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治历史,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日之间谈判的内容和内涵,导致欧洲极权主义兴起的系列事件,或者这些欧洲国家试图征服世界的策略。
造成这种原因的关键是因为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基本上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仅仅关心自己本国的事情,于是他们在战争来临之际还对国际局势一无所知。美国军方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考虑到电影媒介传播直观感性的特性,它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告诉士兵们“敌人及其联盟的本质以及他们为什么要为了战争而训练”,马歇尔将军找到了卡普来拍摄这部战争系列片。(12)
由于《我们为何而战》的主旨是“教育士兵”,故而这部电影的拍摄手法是“用事实说话”,用马歇尔将军当年的话来说就是,这些电影是“展示事实的信息电影”(factual informeation films),它们的功能在于“对我们的孩子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战斗和我们为之而战斗的道义是什么”,这和《意志的胜利》以狂热、煽情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拍摄思路形成鲜明的对比。通过卡普自己的话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这一点,他是这样谈自己的拍摄构思的:(13)
这些影片风格的形成是为了明确目标和真实的记录,故而直接数据的引用、官方资源的获取、生动的表格、国内和国际的新闻简报和宣传电影的内容在这些影片中都有所体现。电影视觉表现的内容是关于战争的故事以及背景的解释。而电影的整体倾向是“让事实自己说话”,当然他们不是干巴巴的事实。
由于是要让事实自己说话,所以《我们为何而战》的系列影片从头到尾都贯穿着具体的历史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系列片更像历史纪实片:《战争序曲》介绍的是德意日三国法西斯的崛起过程;《纳粹入侵》详细介绍了德国入侵别国的历史事件;《分化和征服》详述了德国征服挪威、丹麦、比利时等国的过程;《不列颠之战》详述了希特勒是如何袭击英国并遭到英国从空中和地面上的顽强抵抗。
不一样的电影拍摄思路导致了这两部影片截然不同的风格和观众接受状态。《意志的胜利》从头到尾都在抒情,它像诗歌用一种情绪的感染力来获得观众的认可。它的画面因为设计、导演等原因,往往与真实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画面中的人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在现场也确实对着领袖欢呼了,但这一切的背后却是一个更大的谎言——一切都是被电影技术设计出来的,所有画面中的人的行为、举措都是要符合电影拍摄的要求。这正是汉娜·阿伦特所分析的希特勒宣传的本质特点:“主要是撒弥天大谎,这位领袖借此来娱乐他的客人,以博取人心。”获取了人心之后,科学就可以变成巫术,或者说是一种使群众感动的艺术。这种艺术“使画家、音乐家和诗人能够拥有一种力量,取悦和感动群众,其自信程度不亚于数学家解决一个几何难题,或化学家解释任何一种物质。”(14)艺术家的煽情手段如果获得了成功,他就能从情感上征服受众,那么它就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性。《我们为何而战》却是典型的纪录片,与《意志的胜利》从头到尾的煽情不同,这部电影一直在试图叙事,从头至尾,它介绍了一个又一个二战中的具体事件。卡普等创作者认为,是非对错、爱憎情仇等等都蕴含在叙事中了,这就是所谓的“让事实自己说话”,并且他们也相信,“事实——观点——情绪——由情绪带来的相应的动机”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这是颇为理性且尊重观众主体性的一种传播方式——把观众当成了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人。然而正是因为“理性”而非“狂热”,电影这种大众传播仅仅达到了“有限”的传播效果:电影传播的“事实”受众能够认可,与事实相关的观点大家也能接受,但这些都不足以让他们生发出相应的情感,这将直接影响到相应动机的形成。如果电影等传媒能直接将人们的情感引导出来,那么人们对相应的观点、事实的认可也就水到渠成,这就是具有欺骗性的“宣传”。
进而我们能发现,这两部电影表征了不同的“受众观念”:《意志的胜利》是把民众当成没有主动意识的乌合之众,或者是阿伦特所谓的“现代群众”——“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使群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是一种他们在其中成为组成部分的系统的一致性。”(15)《意志的胜利》精彩地展示了这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成为纳粹党一分子,成为在广场上为希特勒欢呼的群众中的一员,就融入了第三帝国的整体事业中,这一事业会给个体一种乌托邦般的承诺,群众借此乌托邦逃避现实,正是因为这种逃避,人们才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因为相信了,就得自己做判断并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是弗洛姆所谓的人的内心中“逃避自由”的本能冲动。《我们为何而战》却没有迎合人们的这种本能冲动,而是把观众当成了具有独立自我意识和判断能力的主体来对待——相信他们了解了事实之后自会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与《意志的胜利》等电影刻意营造那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导向的信息环境完全不同。正是对受众理性的信任,才导致了电影传播效果的有限。
注释:
①③④苏珊·桑塔格:“迷人的法西斯”,载罗岗等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7、110、117页。
②林贤治《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为纳粹堕落的电影女神》,载《南方周末》,引自http://www.ce.cn/kjwh/ylmb/ylysj/200711/09/t20071109_13533780_2.shtml。
⑤参阅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389页。
⑥Shearon A.Lowery & Melvin L.Defleur: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Third edition),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6页。
⑦转引自Toby Clark《艺术与宣传》,远流出版公司,2003年,第74页。
⑧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39、340页。
⑩(11)(12)Shearon A.Lowery & Melvin L.Defleur: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Third edition),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7~138页。
(13)Carl I.Hovland,Arthur A.Lumsdaine,and Fred D.Sheffield,Experiments on Mass Communic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9)22.
(14)(15)汉娜·鄂兰(即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491、496页。
标签:意志的胜利论文; 希特勒论文; 法西斯主义论文; 伟大的元首希特勒论文; 传播效果论文; 希特勒演讲论文; 我们为何而战论文; 纳粹德国论文; 纪录电影论文; 德国电影论文; 战争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