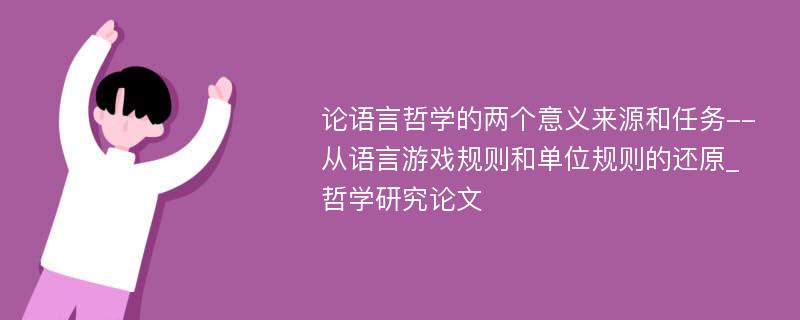
论意义的两个来源和语言哲学的任务——从语言游戏规则和单位的还原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游戏规则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1-0032-08
一、语言游戏说的核心问题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把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语言观概括为:
语言中的语词是对象的名称——句子是这样一些名称的联系。
每个词都有一个含义;含义与词语一一对应;含义即词语所代表的对象,[1] (第1节,P4)
这种语言观也是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罗素等哲学家的基本语言观,也是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1922)中图式论的基本语言观[2]。我们把从柏拉图以来的意义对应论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图式论称为意义概括论,即含义是指称或对象的概括。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词的意义即用法,并把语言比作游戏,词的用法好比游戏规则。目前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理解还有一些分歧。我的初步理解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哲学的视角讨论语言习得过程,说明意义的来源,最后得出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语言被看成是一种游戏,儿童在语言游戏中学会了游戏规则,也就学会了词的使用,词的意义即词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我们把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的观点概括为意义用法论。维特根斯坦以前也有不少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谈到过词的意义和词的用法有关系,但正是维特根斯坦全面深入地讨论了意义和用法的关系,在意义解释中给词的用法以绝对的、唯一的地位,并把这个问题纳入了语言哲学的视角,认为意义即用法是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维特根斯坦通过儿童学说话描述了语言游戏:
教孩子说话靠的不是解释或定义,而是训练。[1] (第5节,P6)
当然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用法论也包括了指称,指称被看成是用法的一种特殊情况。他的“指物识字法”就是在谈指称也是一种用法。上面提到的训练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指物识字法”:
训练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教师用手指着对象,把孩子的注意力引向这些对象,同时说出一个词;例如,指着板石性状说出“板石”一词。[1] (第6节,P6)
但指物识字法的确有助于这种理解(指含义);但它必须同一种特定的训练结合才有这种作用。如果采用的是另外一种训练,同样的指物识字法就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1] (第6节,P7)
维特根斯坦认为奥古斯丁语言观是一种特殊情况:
要有人问:“奥古斯丁那样的表述合用不合用?”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像上面这样说。这时的回答是:“是的,你的表述合用;但它只适用于这一狭窄限定的范围,而不适用于你原本声称要加以描述的整体。”[1] (第3节,P5)
我们可以说,命名以及和它联系在一起的指物定义是一种特定的语言游戏[1] (第27节,P21)
在使用“含义”一词的一大类情况下——尽管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可以这样解释“含义”: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
而一个名称的含义有时是由指向它的承担者来解释的。[1] (第43节,P33)
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指物定义本质上就是通过指称来确定含义,维特根斯坦早期的图式论也是需要依赖指称来确定含义。为什么含义有时候要由指称来承担?为什么不说一个词的含义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维特根斯坦没有从语言还原机制去论证这一点,没有把这两个问题统一起来。但有一点是可以看出的,维特根斯坦并不是否定他早期的图式论,不是否定指称定义,而是批评它不充分。维特根斯坦认为指物定义或指称定义只是语言游戏的特殊情况。
我认为有两个关键理由使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说,避开正面回答含义。第一个理由是,词的很多维妙用法是词典中无法解释的,人们误用词语在很多情况下是只知道词典中的定义而不知道词的各种用法。第二个理由,而且是最关键的理由,是定义或解释没有尽头:
我们追问到“红色”、“黑暗”、“甜”等语词,这些问题也一样没个尽头。[1] (第87节,P61)
我要对语言(词、句等等)有所说,我就必须说日常语言。[1] (第120节,P74)
维特根斯坦认为,儿童在语言游戏中通过词的用法获得规则,意义即用法,各种用法只存在家族相似,我们不可能给词的用法一个普遍规则,精确定义是不可能的。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和意义即用法解释了语言的功用以及意义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弄清词的用法,对于清楚地认识哲学命题的含义,确定哪些是有意义的命题,哪些是伪命题,也是必要的。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哲学家必须在语言游戏中通过词的用法来掌握意义,而不是通过解释或定义来掌握意义。维特根斯坦认为理解的核心是用法而不是定义:
我描述说:“植物覆盖了这整片地面”,——你会说我如果不能给“植物”下个定义我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1] (第70节,P51)
上面的分析只能代表我对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的初步理解。语言游戏说是对语言习得的一个观察角度,是深刻的。不同意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的哲学家可能会认为语言对应实在,词的意义是对指称的反映,词的意义是可以定义的,会认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种对应论立刻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很多词是没有指称的,或者指称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通过指称来定义。即使承认大部分词是有指称的,从维特根斯坦的角度看也可以退一步说语言游戏也是实在的体现,所谓对指称的概括意义也可以从语言游戏的用法中体现出来,所以目前对意义概括论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并不能证明意义用法论不合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建立在语言游戏基础上的意义用法论更严格。下面我将通过语言习得机制的初步分析进一步论证,意义用法论和意义概括论都是初始概念,语言哲学需要从两个角度展开。
二、单位和规则的还原机制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核心是语言习得问题,语言分析哲学的任务和分析方法都是由这个核心问题引申出来的。意义即用法,用法就是游戏中的规则,但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游戏中没有解释游戏规则的形成过程,更一般地说,维特根斯坦没有解释语言单位和语言规则的还原过程,因此没有解释语言的生成过程。还原论并不是各个领域中都需要的,但对语言习得来说,是必须的。儿童学习语言时,所接触到的言语片段是有限的,所接触到的言语片段的用法也是有限的,儿童必须而且也能够在接触过的有限语句和有限用法中还原出有限的单位(语符或词)和规则,并用这些语符和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回答语言习得问题首先要回答单位和规则的还原问题。
制约单位和规则还原的方式可能不止一种,但我认为还原过程最核心的方式是对比。如果我们教会儿童下面一些片段:
鸭头、鸭舌、鸡翅、鸡骨
从这些用法中,儿童可以进一步生成下面一些新用法:
鸡头、鸡舌、鸭翅、鸭骨
儿童显然把言语片段进行了对比,还原出了“鸡、鸭、头、舌、翅、骨”这样一些语符,然后把这些语符进行新的组合。这些语符有的不单说,所以儿童不是单独学会这些语符的。儿童感觉到“鸭头、鸭舌”中有共同的成分“鸭”,这个过程依赖了音义同一性对比。当儿童说出新的“鸡头”这个片段时,他认为“鸭头”中的“头”和“鸡头”中的“头”在某些方面具有同一性,尽管现实中鸭子的头和鸡的头是不完全相同的。儿童在依赖外部世界的相似来判定同一性。
把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20节讨论的内容重新排列一下,我认为从对比中提取单位已经在他的视野中:
拿给我一块石板
递给我一块石板
拿给他一块石板
拿两块石板来
维特根斯坦在讨论中暗示通过这种对比可以提取词。维特根斯坦没有回答词是什么。我们不打算在词这个问题上争论下去,下面把问题集中在单位和规则的还原。对比是结构语言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可以提取语素,但还不能有效区分规则语素组和不规则语素组。[3] (P350—336)由于语言游戏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游戏规则,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更深入的对比是要区分规则片段和不规则片段。语素在线性方向的组合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行为:有规则的活动方式和无规则的活动方式。比如:“白车”是指白颜色的车,其整个片段的意义可以通过“白”和“车”的意义加上组合关系推导出来,这是语素有规则的组合。但“白菜”却不是指白颜色的菜,整个片段的意义不可以通过“白”和“菜”的意义再加上组合关系推导出来,这是语素无规则的组合。很明显,不规则语素组是需要记忆的,在数量上应该是有限的。有效区分规则语素组和不规则语素组是语言习得和自然语言理解的基础。为了后面讨论方便,我们把规则语素组“白车”中的“白”和“车”称为语符,把不规则语素组“白菜”也称为语符。人脑储存语符的地方称为语符库,储存规则的地方称为规则库。语符库和规则库中存放的语符数量是有限的。
当我们说“白车”的意义可以通过语素和组合关系推导出来时,这里的“推导”只是一种不严格的说法,并不是严格的操作程序。“近视、远视、弱视”是否可以推导就不容易断定,因此仅仅靠“推导”还不容易确定它们是规则组合还是不规则组合。又比如“心儿、门儿”这类儿化现象,从成分和组合关系看应该可以推导出整体的意义,似乎应该是规则组合,根据后面得出的结论,容易判定“X儿”这类组合中只有理解规则,应该归入语符。
我们需要找到一种严格的方法或程序来区分规则组合和不规则组合,弄清语言游戏规则的获得机制,才能进一步回答意义和语言游戏的问题。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的单说论[4] 和陆志韦1957年提出的扩展法[5] 是目前区别词和词组的主要语言学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在运用中不能严格一致贯彻下去,不能有效区分不规则语素组和规则语素组。[3] (P350—366)乔姆斯基(Chomsky)以及他后来的论著中多处讨论规则形式和不规则形式在转换分析中的差异,但并没有给出严格判定规则形式和不规则形式的标准或原则。[6] [7] 我认为这个原则就是对比的平行与周遍,而要达到平行周遍的要求,有时候必须要考虑语义类比和语义概括。现在我们来证明这一点,下面的实例都是由自由语素构成的,不是专名:
布鞋、白鞋、跑鞋、冰鞋、凉鞋、雨鞋
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偏正关系,前项不同,后项相同。下面是前项是否可以进行平行周遍对比的情况:
“×鞋”对比表
平行周遍 平行周遍 平行不周遍 平行不周遍 不平行 不平行
布鞋 白鞋
跑鞋冰鞋 雨鞋凉鞋
皮鞋 黑鞋
跳鞋球鞋
金鞋 绿鞋
拖鞋
*雪鞋
纸鞋 红鞋
套鞋
*山鞋
铜鞋 瘦鞋 *登鞋
草鞋 新鞋 *走鞋
木鞋 旧鞋 *滑鞋
棉鞋 男鞋
银鞋 女鞋
胶鞋 [小鞋]
… [破鞋]
“布鞋、皮鞋”一栏是平行周遍的,“X鞋”平行周遍规则可以概括为:
X表示质料,鞋是用X做的。
由于是平行周遍格式,所以有生成性,我们还可以说“玻璃鞋、塑料鞋、水晶鞋、钢鞋、石鞋、铁鞋”,等等。
概括地说,平行周遍满足以下条件:
1.被替换的部分具有平行特征。
2.在被替换部分保持平行特征的前提下,组合关系平行。
3.整个组合在分布上平行。
显然,“白鞋、黑鞋”一栏也是平行周遍的,“X鞋”平行周遍规则可以概括为:
X表示性质,鞋具有X的性质。
和“布鞋”一栏不同的是,“白鞋”一栏有“小鞋、破鞋”这样一些转义的实例,不过这些转义的实例只是少数例外。一般地说,除去转义的实例,平行周遍格式仍然是平行周遍的。
“布鞋”和“白鞋”这两列的平行周遍规则可以进一步统一起来,因为“质料”和“性质”可以统一看成属性,统一的平行周遍规则是:
X表示属性,鞋具有X的属性。
“跑鞋、跳鞋、拖鞋”之间是平行的,“跑、跳、拖”这些语素表示的是运动方式,但不周遍,我们不可以说“走鞋”。“球鞋、冰鞋”之间是平行的,“球、冰”表示的是和运动项目相关的名物,也不周遍,我们不可以说“山鞋”。从两列的关系看,这两列字组的前字和“鞋”组合都是表示跟运动有关系的鞋,但滑冰的鞋要说成“冰鞋”而不说成“滑鞋”,踢球的鞋要说成“球鞋”而不说成“踢鞋”,跑步的鞋却要说成“跑鞋”而不说成“步鞋”,这都是不规则现象,在找到平行周遍条件以前,“跑鞋、跳鞋、拖鞋”都应该看成是语符。球鞋的情况有些不同,“球鞋”的后项可以找到平行周遍的实例:
球鞋、球裤、球衣、球帽、球袜……
只要一个片段至少有一个成分替换后满足平行周遍,这个片段就是规则组合,“球鞋”符合这个条件,是规则组合,可以不存放在语符库中。“冰鞋”的前项和后项被替换后都很难找到平行周遍的对比实例,“冰鞋”应该存放在语符库中。
“雨鞋”在“雨”上不能进行平行周遍对比,但在“鞋”上可以进行周遍对比:
雨衣、雨具、雨帽、雨伞、雨靴、雨披……
“凉鞋”前项不能够进行平行周遍对比,后项可以进行平行对比,但不周遍:
凉鞋、凉椅、凉席、凉帽、*凉凳、*凉衣、*凉袜
所以“凉鞋”应该存放在语符库中。
以上是在考虑单位与规则的还原,还原的基本方法是平行周遍对比,而平行周遍对比又涉及语义特征,这说明对比离不开语符的含义,因为必须先有概括的含义,才有语义特征。整个还原过程都与区别规则和不规则语素组这一根本目标有关系,如果不区别规则和不规则语素组,“布鞋”和“冰鞋”就不必加以区分,也就不必涉及“质料”这个语义特征。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不区分规则和不规则语素组,就等于没有学会语言,没有学会语言游戏规则,就不能从有限的单位生成无限的句子。因此,学会语言游戏意味着必须学会语言游戏规则,必须学会规则意味着必须考虑语义特征的提取和语义概括。我们考虑的还只是两个语素组合的情况,在更多的语素组合中,要提取规则,都要以平行周遍对比为条件,都不同程度的要依赖语义概括。
平行周遍对比是以相似为基础的,维特根斯坦已经提到了语言游戏的家族相似,但他所说的相似和我们所说的共同语义特征和语义概括不是一回事。维特根斯坦反对共同性对比,反对概括,我们说“布鞋、棉鞋、金鞋”有同一性,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是说“布鞋”和“棉鞋”有相似的地方,“棉鞋”和“金鞋”有相似的地方,但三者没有共同相似之处。维特根斯坦说:
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更好的说法来表达这些相似性的特征;因为家族成员之间的各式各样的相似性就是这样盘根错节的:身材、面相、眼睛的颜色、步态、脾性,等等。——我要说:各种“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1] (第67节,P49)
但若有人说:“所以,这些构造就有某种共同之处——即所有这些共同性的选言结合。”——那么我将回答说:现在你是在玩弄字眼。[1] (第67节,P49)
我们的认识是,我们称为“句子”、“语言”的东西不具有我前面想像的形式上的统一,而是或多或少具有亲缘的家族。[1] (第108节,P70)
我们上面的分析说明,不追问语义概括就找不全语言游戏规则。
三、语言习得的用法-对比模式
从单位和规则的还原过程看,意义不只是用法。以上判定“布鞋”是规则组合,需要“质料”这个语义特征,这个特征仅仅从用法上是提取不出来的,比如:
N+鞋:皮鞋,铜鞋,冰鞋,水鞋,*气鞋……
V+鞋:跳鞋,跑鞋,拖鞋,*走鞋,*登鞋……
D+鞋(D:区别词):金鞋,银鞋,男鞋,女鞋,童鞋,*公鞋,*母鞋……
以上每一组中的前一个语素都代表了一种分布,即一种用法,N代表名词性用法,V代表动词性用法,D代表区别词性用法,每一组都有一定的平行实例,但并不周遍。
“质料”这个语义特征也不是从“X鞋”以外的其他用法中推导出来的,下面表示质料的语符的用法并不相同:
金 银 布纸
*金是物质 *银是物质 布是物质 纸是物质
*买金 *买银 买布 买纸
*金! *银! 布! 纸!
金鞋
银鞋
布鞋 纸鞋
前面有“*”号的表示没有这样的用法。“金、银”不可以作主语和谓语,也不能单说,当然也就没有维特根斯坦提到的下达命令、请求等各种用法[1] (第23节,P18),“布、纸”可以作主语和谓语,也能单说,因此也有很多其他用法。“金、银”和“布、纸”代表了两类不同用法的语素,但它们有共同的“质料”语义特征,这种共同语义特征在于它们都能指称一类物质。只要任何一个X语符,即使我们不知道它的用法,只要具有“质料”特征,“X鞋”都是规则组合。如果没有“质料”这个语义概括条件,“布鞋、金鞋、皮鞋、银鞋”等的平行周遍规则就提取不出来。这说明母语者在区别规则字组和不规则字组时确实参考了语义因素。也就是说,在对比中,必须考虑语义特征,而语义特征是一组语符的含义所具有的共同聚合特征,所以含义在一定条件下是独立于用法而存在的,而“布、草、金”等语符的质料语义特征追问到底是和“布、草、金”指称的对象有关系。一旦我们知道某个语符的含义,知道该语符有“质料”这个特征,比如“石”,就可以知道该语符可以用在“石鞋”中,即使我们过去没有听说“石鞋”。
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个关键的结论,在一定条件下,知道“金、布”等语符的含义或语义特征也可以知道“金、布”等语符在特定语境下的用法,即知道词的含义或语义特征也可以知道词的某些用法。词的意义不仅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可以从词的用法中得出,词的有些用法也可以从含义中对比出来。
在结构语言学中,哈里斯(Harris)的分布理论可以看成是意义即用法的一种代表。哈里斯认为只要充分研究语素在话语中的分布,就可以掌握语素的分类,并通过这些分类生成新的话语,但由于哈里斯不区别周遍和不周遍两个概念,就不可能有效区别规则组合和不规则组合[8],因此哈里斯不可能发现我们前面讨论的“X鞋”中必须涉及的意义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区分规则组合和不规则组合,我们就不能解释语言的生成性[3] (P350—366),也等于不能有效掌握语言游戏规则。
语言习得至少应该有两个重要步骤。先通过语言行为和用法获得核心言语片段的意义,这只是言语习得的第一步。仅仅获得核心言语片段的用法是不够的,因为言语片段的数量是无限的。母语者也不可能记住每一个言语片段的用法。自然语言不是若干核心言语片段的用法的堆积,而是在有限言语片段用法的基础上,还原语符和规则,通过有限的规则和语符生成无限的言语片段。当儿童通过第一个过程获得若干核心言语片段的用法后,就需要通过一些方式获取有限的语符和规则,这就是单位和规则的还原过程,是语言习得的第二步。第二步需要语义的概括、对比。
我们说语符或词的有些用法可以从含义中对比出来,但不是所有的用法都可以对比出来。前面提到的“金、银、铜、铁、锡”都是金属语素,对象的类是平行的,但用法并不一样。“金、银”在组合上要受到限制,而“铜、铁、锡”不受限制,我们从这些金属语符的含义和指称上很难给出解释。可见,用法确实具有初始性,即用法不可能全部通过“含义、指称、对象”这些概念推导出来。我们给出这个实例是要说明,维特根斯坦通过语言游戏来解释语言习得过程,得出意义即用法的结论,这一观察尽管不是充分的,但却是相当深刻的。可以说,不是所有的用法都可以通过概括意义推导出来,也不是所有的概括意义都可以通过用法推导出来。意义不只是用法,意义即用法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至于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类比出新的用法,在哪些条件下不能,还需要深入的研究。
用法和概括是相对独立的。在学习顺序上,用法在先,然后是概括,通过概括预测用法。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用法-概括”学习过程。
四、语言分析与语言哲学的任务
哲学要做什么?如果把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或数学,用人工语言表述哲学命题是必要的,但这样一来哲学问题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我对哲学的理解是,哲学是一种终极解释活动,一种最基础性的思维活动,哲学的目标就是追问一切科学活动或认识活动的基础问题和方法论的合理性问题,包括自然科学活动和人文科学活动。有关存在理论本身的方法论问题也要得到追问。哲学拿什么语言来展开终极解释活动,当然不能靠人工语言,因为所有的人工语言都是通过自然语言来定义的,人工语言肯定不能充分表述哲学命题,自然语言是最初始的元语言,于是哲学的语言最终只能回到自然语言。我认为这是语言哲学必须转向日常语言的更充分的理由。即使把哲学看成是科学的先驱,这个理由也是成立的。
如果语符或词的意义不只是用法,那么语言哲学就有更多的任务,而不只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中所断言的:语言用法说清楚了,哲学问题就消失了。
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解释学的角度阐述过语言和哲学的本体关系。海德格尔认为任何人对“存在”这一重大哲学问题作出解释时都受到前结构的约束,这种前结构就是解释者的先入之见、背景知识和假设前提,它们存在于语言之中,因此对存在的解释就是对语言的解释。[9] (P196—203)在海德格尔的思考中,语言被看成哲学的本体。在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中,语言本体论的思想更为突出,哲学被说成是按照语言的方向思维,而不是用语言思维。存在就是语言的存在,当人们谈论语言的时候语言背后的实在也就消失了。[10] 无论海德格尔的说法是否正确,他所说的前结构应该是存在的,只是不同的人对前结构的依赖程度可能不一样,从解释的角度考虑语言和哲学的关系,似乎更接近我们所理解的哲学的任务,即终极解释活动。但从海德格尔前后发表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语言是指语言的文本,包括口语文本和书面语文本,而不是指语言结构系统。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把语言分析仅仅建立在文本的基础上是不够的。语言中隐藏着前意识,前意识可以分成两个关键部分,一种是隐藏在文本中的前意识,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前结构,一种是隐藏在语言结构系统中的前意识。语言哲学不仅需要研究文本中的前意识,更需要研究语言结构系统中的前意识,后者隐藏得更深。
既然语言习得必须依赖类比,必然会引出在类比基础上的概括。怎样类比,怎样概括,这正是认识论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些类比方式和概括方式会或明或暗地隐藏在语言系统中,并以观念的范畴化体现出来。观念的范畴化程度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前面多处谈到,任何一种语言最根本的核心部分是词集(或语符集)和语法规则集。词集是一套有限的单位,语法规则集是一套有限的规则,这两套由有限要素组成的集合可以生成一种语言中无限的句子。这两套集合中的要素都范畴化了。一种观念如果在某语言中没有进入词集或语法集,而只是用文本表达,说明这种观念还没有范畴化,它在该文化中只是一种临时的、浅层的观念。如果一种观念在某语言中用词组表达,像英语中elder brother和younger brother的对立,说明哥哥和弟弟的观念在该文化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但还没有范畴化,因为这种观念还没有进入词集。如果一种观念在某语言中用词来表达,像汉语中“哥哥”和“弟弟”的对立、“姐姐”和“妹妹”的对立、“伯伯”和“叔叔”的对立,这时该观念已经进入词集,所以已经范畴化了。但由于不具有普遍性,比如在祖辈中很少有这种对立,所以这种范畴化不是很深的。如果一种观念在某语言中用可省略的虚词、黏着语素表达,这种观念在该文化中也已经范畴化了,已经进入了词集,并且比用词表达的范畴更深,但由于表达该范畴的虚词、黏着语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省略,比如汉语中的“哲学家们”也可以说成“哲学家”,所以单数和复数对立这种观念的范畴化在汉语中也不是最深的。如果在某语言中某种观念用形态变化来表达,或者用不可省略的虚词、黏着语素表达,说明该观念不仅已经范畴化,而且已经语法化了。这时的范畴表达方式不可以省略,说明该观念在该文化中的范畴化程度已经相当深。[11] 语言中的范畴化深度反映了集体认识过程。还有些范畴,比如哲学层次上的认识范畴,并不一定反映集体的认识活动,可能反映的是部分热爱智慧的人的认识活动,这样的范畴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词汇和语法中,但由于这些智慧活动都是通过自然语言展开的,所以这些范畴通常会隐藏在自然语言中,往往需要更深入的语言分析才能找出来。
在语言系统中,语符或词的用法是第一个初始概念。儿童可以通过对比、归纳,得出含义,形成新的用法。对比、归纳行为可以统一到类比上来。类比会引导人们对经验进行分类,形成一些重要的范畴,包括认识论上的范畴。研究人类是怎样对经验进行分类的,这属于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词的意义不仅仅是用法,词的背后还包含了我们关于世界的分类知识,这些前意识对哲学认识论的形成有潜在的影响,哲学作为一种终极解释活动,应该对包含在语言结构系统中的前意识及其和认识论的关系作出解释。沿着这条思路,语言哲学的任务不仅是通过语言分析发现虚假的哲学命题,而且应该通过语言分析发现隐藏在自然语言背后的认识范畴,通过分析这些范畴来研究哲学中的认识论,这是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说语言哲学不仅是消解,即找出哲学命题在表达上的错误,也是建构,即找出哲学认识论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