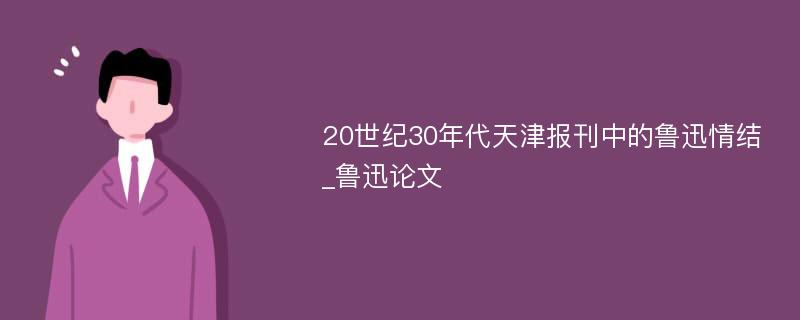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天津报刊中的鲁迅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天津论文,情结论文,报刊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4)05-0067-04
翻阅20世纪30年代的天津报刊,竟然发现有不少的报纸副刊和文艺杂志都不同程度地 发表和评介过鲁迅的作品。鲁迅逝世之后,他们又全方位报道有关的消息,高度评价鲁 迅的贡献,隆重悼念鲁迅的功绩。有的报刊还因此而夭折,但是,他们无怨无悔。可以 说,从这些报刊中,表现出了很浓很深很强烈的鲁迅情结。
一、认同鲁迅
1934年2月16日,由吴微哂主编的《天下篇》半月刊在天津创刊。该刊的创刊号上即发 表了鲁迅的《上海杂感》。这是1933年12月5日,鲁迅应约用日文写作的杂感,最初发 表在1934年元旦日本大阪《朝日新闻》。不久,吴微哂的朋友吉人便将该作品译为中文 ,发表在《天下篇》创刊号上。该刊的编者按语指出:鲁迅的这篇杂感“怕是很有些人 想看的文章。我们很愿意在这里刊出。不过血究竟也是可怕的,我们不得已在这文章中 用了一段‘……’,好在并不甚妨碍文意。谨此申明一句,以当致歉!”其中被省略的 部分出在第五自然段中,是谴责当时的“政府”无端逮捕作家的有关文字。鲁迅敢讲真 话,无所畏惧,即使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之下,也敢于直面现实,这便是其中的 一例。
《天下篇》杂志本是综合性期刊,宗旨是:“想用浅近的文字,介绍各方面的各种事 情。希望能使人们知道了自己是怎样的人物,也明白了旁人是怎样的情形。”该刊的创 刊号除刊发了翻译的鲁迅作品外,还发表了小说、随笔、讽刺诗以及马彦祥译介的匈牙 利喜剧等。
《天下篇》杂志在发表鲁迅作品之前,虽然未曾征求鲁迅的意见,但是,鲁迅收到样 刊后,仍然立即回信,对他们表示了支持。数月后,鲁迅将该文重译,以《一九三三年 上海所感》为题,重新发表在1934年9月25日创刊的左联进步刊物《文学新地》上。这 便是后来以《上海所感》为题,被收入《集外集拾遗》的那一篇作品。
接着,《天下篇》杂志又拟译载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上的鲁迅杂感《火,王道, 监狱》一文。于是,在3月上旬,他们两次致函鲁迅,商谈此事。鲁迅回信表示同意刊 发,只是“拟觅一较可凭信者翻译”自己的作品。最终,鲁迅还是自己将其译成中文, 题目为《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于3月28日寄给了《天下篇》杂志社。意想不到的是 ,在3月16日,《天下篇》杂志第3期出版后,即因种种原因而被迫停刊了。原拟刊发第 二篇鲁迅杂感的计划,也就搁浅了。
《天下篇》杂志社自创刊始即自觉地把译介和发表鲁迅的作品作为一种职责,一方面 反映出编者对鲁迅的认同,意识到自己应该与鲁迅站在同一战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编 者有意迎合读者的心理,因为他们知道读者中很有些人想看鲁迅的作品。虽然,他们也 意识到“血究竟也是可怕的”,但是,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发表鲁迅的作品,并很快为 此付出了代价:最终以《天下篇》杂志的迅速夭折而告终。
二、崇拜鲁迅
1935年6月15日,在天津《庸报·当代木刻》第4期的头条位置,刊发了鲁迅的作品《 <全国木刻联展专辑>序》,署名“何干”。从鲁迅序文的写作到发表,无一不是由青年 编辑、木刻爱好者对鲁迅的热爱与崇拜所引发的。
1934年下半年,平津两地的青年木刻爱好者金肇野、唐诃等发起筹备第一次全国木刻 联合展览会,并拟选编出版《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以下简称《专辑》)。在筹备 和巡展期间,出于对鲁迅的崇敬和爱戴,他们曾多次致函,主动争取得到了鲁迅的支持 和指导。鲁迅编印出版的《木刻纪程》、《引玉集》以及收藏的木刻作品等,也都作为 展品提供给了他们。可以说联展达到了以进步的木刻作品教育大众、鼓舞斗志的目的。
在他们热情诚挚的嘱托和恳请下,鲁迅于1935年6月4日,为他们拟出版的《专辑》写 了序文。他从木刻图画的历史和它的“大众”属性谈起,热情称赞新兴木刻“乃是作者 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 代社会的魂魄”。他还指出了新兴木刻艺术更光明、更伟大的发展前景。
鲁迅作序的次日,即将手稿寄给了唐诃。那时,唐诃与金肇野在天津《庸报》副刊编 辑、进步文人姜公伟的支持下,已于1935年5月1日主编并创办了《庸报·当代木刻》半 月刊。这是我国北方创办的第一个木刻专刊。它是借着全国木刻联展的东风应运而生的 ,却仅仅维持了两个月,出版了5期便被迫停刊了。该刊不仅刊登反映大众生活的木刻 作品,如《卖盐》和《逆水行舟》等,而且发表有关木刻作品的评介文章,如《论连续 图画<水灾>》和《苏联木刻近况》等。作者多为当时活跃在平津沪、且与鲁迅有交往的 青年木刻爱好者。该专刊的迅速终刊,原因已经不言自明了。
鲁迅的序文在天津《庸报·当代木刻》第4期发表的同时,为了与拟出版的《专辑》相 一致,他们还将鲁迅的序文手稿制成了木刻图版。并于1936年9月16日,鲁迅55周岁生 日前夕,将仅存的序文刻印稿寄赠给鲁迅,令鲁迅感激不已。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同年11月10日,由天津人黄树则主编、唐诃协编 的《文地》月刊在津创刊。该刊的创刊号就成了鲁迅追悼特辑,不仅刊发了鲁迅画像、 手迹和纪念文章,而且依据序文刻印稿,再次刊发了鲁迅的《<全国木刻联展专辑>序》 。从鲁迅的一篇序文在天津报刊的两次发表,足以显示出青年木刻爱好者对鲁迅的敬重 。
三、理解鲁迅
1931年2月23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63期,发表了鲁迅在当年2月4日写给李 秉中的信,题目为《鲁迅之手书》。该信虽然未经鲁迅同意便发表了,但是,它最先帮 助鲁迅澄清了事实,揭露了无耻文人造谣滋事的卑劣伎俩,使鲁迅被捕的谣言不攻自破 ,令关心鲁迅的人们抒怀释念,充分表现出了对鲁迅的关心和理解。
1931年1月17日,柔石、殷夫等五位革命作家被捕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就放出了要逮 捕鲁迅的风声。20日,鲁迅携眷转移到黄陆路花园庄旅馆暂时躲避。在此期间,国民党 官方报纸及各种无聊文人办的小报,就不断造谣中伤鲁迅。21日,天津《大公报》就曾 刊发了“上海专电”,报道了“鲁迅在福州路被捕,现拘押捕房”的消息,令鲁迅的亲 友为之惊忧。
当时身在日本的李秉中也听到了传言,深为鲁迅担忧,急忙发信向周建人打听虚实。 这让鲁迅着实感动,于是,他在2月4日给李秉中写了回信,感谢他的关心,同时也谈了 自己的处境和当时的心情。他说:“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事,结舌无 言,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员,而上海文坛 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哀其无聊,付之一笑 。”他说:“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 以来,几于日以发函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 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辄不知来日如何耳。东望扶桑,感怆交集。” 鲁迅的信写得何等真切、动容!
李秉中得知真相后,很快便将这封客观反映真实情况的信寄给了天津《大公报》文学 副刊编辑部,受到重视,被迅速刊发,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鲁迅被逮捕之消息,由 南而北,喧传报端。近始悉为子虚乌有之事。本刊顷得鲁迅致常为本刊撰稿之李秉中君 手书一通,亟为披露,藉以辟谣,并见上海文坛情形之复杂也。”编者挺身而出,仗义 执言,以“子虚乌有”一词,彻底否定了混淆视听、流传甚广的谣言,让上海文坛的造 谣者无地自容。鲁迅这封重要书信的发表,也为后人编辑《鲁迅全集》留下了宝贵的原 始资料。
四、支持鲁迅
1936年4月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公开发表了鲁迅在上海被国民党检查机关禁 止发表的译作,用实际行动支持鲁迅与恶势力做斗争,表现出了编者的胆识与正义感。
鲁迅一向是主张阅读俄国作家契诃夫和高尔基的作品的,“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 界更接近”[1]。为此,在1934年冬和1935年春,他陆续翻译了契诃夫早年的短篇小说8 篇,其中《坏孩子》、《暴躁人》等7篇作品均先后在《译文》月刊发表,惟有《波斯 勋章》一篇被国民党检查机关禁止刊发。鲁迅在1935年9月15日所作的《<坏孩子和别的 奇闻>译者后记》中说:“谁知道今年的刊物上,新添的一行‘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 审查证……字第……号’,就是‘防民之口’的标记呢,但我们似的译作者的译作,却 就在这机关里被删除,被禁止,被没收了,而且不许声明,像衔了麻核桃的赴法场一样 。这《波斯勋章》,也就是所谓‘中宣……审委会’暗杀账上的一笔。”他说:“《波 斯勋章》不过描写帝俄时代的官僚的无聊的一幕,在那时的作者的本国尚且可以发表, 为什么在现在的中国倒被禁止了?——我们无从推测。”鲁迅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 扼杀文艺的罪行。然而,他又坚信:“一面有残毁者,一面也有保全,补救,推进者, 世界这才不至于荒废。”因此,他照样把《波斯勋章》等8篇翻译小说结集成册,定名 为《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拟单行出版,并为此写了《前记》。至此,鲁迅这本译文集 中的作品,就只有《前记》和《波斯勋章》未曾单独发表过了。
在文网肆虐的状况下,鲁迅自己已经不肯再将文稿他投,生怕因此而损害了文社和刊 物的利益。因为他知道:国民党的“官场有不测之威,一样的事情,忽而不要紧,忽而 犯大罪。实在不值得为了一篇文字,也许贻害文社和刊物”[1]。就在此时,天津《大 公报》文艺副刊开辟了“译文特刊”,通过黄源得到了鲁迅的文稿,以头条位置,同时 发表了鲁迅的《<奇闻八则>前记》和翻译小说《波斯勋章》两篇作品。他们这一举动以 及与上海文网对着干的劲头儿,在读者中产生了不小的反响。这一次,刊物不仅没有因 发表鲁迅的作品而被剿杀,反而办得越发红火,显示出了正义终究战胜邪恶的力量。
五、评介鲁迅作品
30年代中期的天津报刊是比较注重宣传鲁迅的。这主要表现在鲁迅生前,关注并及时 评介鲁迅的作品;鲁迅逝世后,从不同角度,全方位报道有关悼念鲁迅的消息,高度评 价鲁迅的贡献和功绩。仅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例。
1936年1月,鲁迅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由上海文化生活社出版。这是鲁迅生前出 版的最后一部作品集。仅仅过了一个月,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便以头条位置,发表 了常风评介《故事新编》的文章。他认为:“鲁迅先生在他创作生活的开始就与他同时 代的作者不同。”他说:“大概是因为年纪的关系,鲁迅先生开始写小说时已是中年的 人并且投身社会已久,所以他能冷静地观察人生,注意到个人以外的世界。这正是鲁迅 先生高人一筹的原因。”他认为鲁迅的创作力量是惊人的。他已有十年不写小说了,而 重新拿起笔来一点不曾生疏。“这个集子就是他的新成绩。在这样的时代,敏感的鲁迅 先生更该体验了、观察了不少的‘现实’,然而也必更感觉得重重难以言传之苦衷吧。 像这集子借古人以立言的深意我们是十分了解的”。更有青年评论者宗珏在《故事新编 》中的小说《出关》最初发表时,便给予关注并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评论文 章,指出:鲁迅的小说《出关》“虽然是历史题材,但是运用新的观点,针对着某角落 的现象,在大众的面前揭露出一些曾经使许多人迷信的偶像的原形,还是极有意义的” 。他认为“这篇小说可说同是鲁迅先生底一贯的对历史之尖刻的观察底心得”。宗珏的 眼光让鲁迅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他是看出了作者的用意的。”
1936年9月,鲁迅的译文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由联华书局出版。这是鲁迅生前出版 的最后一本译文集。对于这部译文集,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同样予以重视,并及时 发表了评介文章,充分肯定了鲁迅译介俄国作家契诃夫作品的现实意义和良苦用心。
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对鲁迅晚年作品的评介,使那些熟悉或不熟悉鲁迅的读者都 受到了感染,使他们对鲁迅伟大的人格有了更切实的认识。
六、纪念鲁迅
鲁迅逝世后,天津人民也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鲁迅的悼念:《益世报》发表了社论《 悼鲁迅先生》,高度赞扬了鲁迅的民族气节和伟大人格;《北洋画报》刊发了鲁迅的照 片和纪念文章;《诗歌小品》、《文地》等杂志也都刊发了悼念文章;知识书店举办了 鲁迅图片及著作展览;天津的文化界还举行了鲁迅追悼大会。
在全国各地纷纷纪念鲁迅的日子里,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则独辟蹊径,推出了外 国人纪念鲁迅专刊,刊发了英国教授谢迪克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纪念文章, 还配发了鲁迅的照片,让读者从外国友人的评价中,看到了鲁迅在世界文坛上的价值。
作为一位外国学者,谢迪克对鲁迅的作品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鲁迅的写作才 力充分表现于他的杰作《阿Q正传》中。文虽短,而其深刻、完整,艺术手腕的成熟, 感人之深却不亚于长篇小说或戏剧。”“当我们读完了这故事以后,我们会感觉到中间 每一句子都是用血和泪写成的。”他称鲁迅是“人类的爱护者”、“中国的革命英雄” 。
斯诺认为鲁迅是可以与高尔基、伏尔泰、罗曼·罗兰等伟大作家比肩的,“他一向是 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导”,“鲁迅的‘坚定不移’的态度,不仅是激发和鼓励所有为着同 一的理想而奋斗的中国青年的原动力,而且增强了所有的友邦人士一向对于中国前途的 信念”。斯诺预言:“鲁迅之于中国,其历史上的重要性更甚于文学上的。……料想不 久鲁迅的名字将广为人知,并成为当代世界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我们不能不承认斯 诺是很有远见的。
在30年代的天津报刊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浓浓的鲁迅情结,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客观上看,首先是鲁迅那为国家为民族为正义为真理而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对知 识分子有着巨大的鼓舞作用。鲁迅是中国文坛的主将,他代表了新文化前进的方向。他 那穿越时空的文字魅力,博大精深的思想魅力以及蔑视权贵、同情苦弱的人格魅力,是 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会为之震撼的。天津的报刊编辑当然也不例外。正像鲁迅评价章太 炎时所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借此来评价鲁迅同样 是相宜的。在他的杂文里,反映着“中国的大众的灵魂”。通过发表和评介鲁迅的作品 ,通过广泛宣传和高度评价鲁迅的贡献,即可“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 ”[3]。这是毫无疑义的。
再者,鲁迅的思想和创作都是代表大众的,“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 ,无不相通”[4]。而报刊又是提供给大众阅读的,从迎合大众心理的角度看,刊发鲁 迅作品、培养鲁迅情结,应该说也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主观上看,那时天津报纸副刊和进步文艺杂志的编辑,大多是不带偏见的文学创作 者和研究者,他们有着明确的好恶,有着理性的思考,更有理智的判断。他们把正义和 良知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无论是从理性上,还是从感性上,他们都表现出了对鲁迅由 衷的信任、崇拜、理解和支持。鲁迅主张实干总比说空话要好一点,他们就在实际行动 中,支持并彰显鲁迅精神。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用鲁迅精神教育读者,激励斗 志,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自强而奋斗不息,实现鲁迅所期盼的:让将来的世界能够多一分 光明,少一分黑暗。
如果说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一种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尺度,高扬人性,揭示人的生存的 意义,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文化精神;那么,从30年代天津报刊中的鲁迅情结这一文 化现象,恰恰反映出了拥有600年历史的天津的人文精神的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