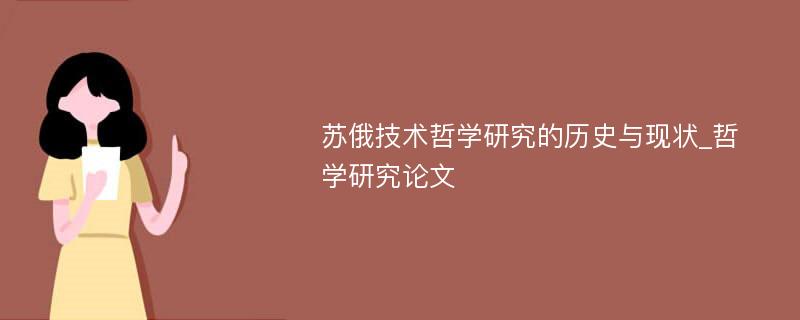
苏俄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俄论文,现状论文,哲学论文,历史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8862(2002)11-0041-05
在国内,与对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热度相比,对前苏联、俄罗斯技术哲学的关注程度则呈现出与日俱下的态势。为使学界对苏俄技术哲学研究有一个大致了解,本文就苏俄技术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一总体评价,将苏俄技术哲学近百年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事件和观点进行评述。
一 艰难起步:萌芽时期的前苏联技术哲学
有资料表明,在E.卡普逝世的19世纪最后十年中,就有俄国人开始在德国杂志上发表使用“技术哲学”一词的论文,此人就是作为工程的技术哲学(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创始人之一的п.к.恩格迈尔。他毕业于莫斯科帝国技术学院,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工程师。1911年,第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召开,恩格迈尔在“技术哲学”的标题下,对技术的本质、研究方法、学科分支以及与科学、艺术、伦理学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奠定了技术哲学在世界哲学研究中的学科地位。
十月革命,特别是192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国家需要大量的从旧政权接收过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帮助布尔什维克进行经济建设,因此,在20年代前苏联开展了一场“专家治国”运动,宗旨是依据技术原理改造和管理企业和社会。而这一宗旨恩格迈尔早在1899年的长文“技术的一般问题”中就已经阐发:“技术专家(Techniker)一般认为,当他们提供了价廉物美的产品时,他们就尽了他们的社会职责。但这仅仅是他们的专业工作的一部分。当代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专家不只是在工厂里才能找到。高速公路和水路运输,市区经济管理等已经处于工程师指导之下。我们的职业同事正在爬上更高的社会阶梯;工程师甚至偶尔正在成为一位国务活动家。而同时技术专家必定总是一位技术专家……”(注:转引自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第7页。)
另一位倡导专家治国思想的学者是п.帕尔钦斯基。帕尔钦斯基的工业规划纲领注重合理性,他认为:“制定计划的工程师不可能创造奇迹,但是,如果让他用公开的与合理的方法来处理每一个问题,他就能对经济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为了使前苏联工程师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帕尔钦斯基认为工程师的社会角色应当改变:“以前的工程师是由社会指派的一个‘被动的’角色,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他解决指定给他的技术问题;现在的工程师应该成为一个‘主动的’经济与工业规划人,提出经济在什么地方和应当用什么方式发展。”(注:转引自洛伦·R·格雷厄姆:《俄罗斯和前苏联科学简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第180-181页。)其他一些工程师,如и.А.卡林尼科夫(他是专家治国思想核心期刊《工程师通报》的主编)、н.Ф.恰尔诺夫斯基、в.и.奥奇金等人也加入了这场运动。美国学者肯德尔·贝尔斯对上一世纪20年代前苏联的“专家治国”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注:参见贝尔斯:《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技术与社会》,纽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
不难看出,帕尔钦斯基和他的同事们急切地想把工程师推向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这种想法很快成了泡影。斯大林不允许专业技术人员拥有帕尔钦斯基为工程师所要求的那种自主权,甚至不允许有这样的工程师。1929年,帕尔钦斯基被指控为阴谋推翻前苏联政府的“工业党”的领导人秘密枪决。在接下来的肃反扩大化中,有几千名工程师被扣上各种罪名遭到关押和流放(要知道,当时的前苏联仅有一万名工程师)。名噪一时的“专家治国”运动就这样夭折了。
专家治国论(Технакратия),可直译为技术统治论,是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表示建立技术专家的政治,其特点是不把某一阶段的“私利”,而是把技术专家集团为全社会利益而利用的科学技术作为基础来管理社会。作为管理社会的一种模式,专家治国论有它的合理之处,但在当时却遭到了激烈的批判。
今天看来,尽管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的“专家治国”运动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最终归于失败,但是,这场运动却促使一批职业工程师开始反思技术本身以及工程师的社会地位问题,产生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的最初萌芽。1927年,恩格迈尔组织了一个名为“一般技术问题”的讨论班,他在《工程师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技术哲学是必要的吗?”的文章中,对该讨论班的计划作了总结:“发展一项技术哲学计划,包括试图解释概念性技术(concept technology),当代技术的原理,作为一种生物学现象的技术,作为一种人类学现象的技术,技术在文化史上的作用,技术与经济,技术与艺术,技术与伦理学,以及社会其他因素。”(注:转引自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第9页。)不难看出,恩格迈尔已经为技术哲学的研究提出了最初的纲领,奠定了苏俄技术哲学在世界技术哲学中的独特位置;而有些提法,譬如“概念性技术”则比M.邦格等欧美学者早了半个多世纪。
二 独树一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技术哲学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准确地说,是斯大林式的)在前苏联解体之前一直是作为前苏联的“正统哲学”或“官方哲学”而存在的,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修正。新成长起来的前苏联技术哲学家们为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技术观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库津的《马克思与技术问题》(1968)、斯托斯科娃的《恩格斯论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1970)、梅里钦科和苏赫尔金的《列宁与科学技术进步》(1969)等都是有代表性的著作。因此,F.拉普在分析技术哲学不同的传统时,将前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技术哲学视为最为确定的一个思想流派。
20世纪中叶,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在科技革命的条件下,生产的自动化和建立人-机系统是发展生产力亟需解决的问题,反映在技术哲学上,就是对“机械和机器理论”(теория механизма и маШины)的关注。作为关于机器的普遍学说,这一理论对整个技术科学领域中的技术设计活动具有方法论的功能。阿尔托博列夫斯基院士认为:“机器理论是一门科学,它研究同工作过程与实现该过程相联系的机器的内在复杂结构。机器理论的任务是在我们已有的全部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制造机器,以便最大限度地保障生产的高效率、对能源的低消耗以及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注:阿尔托博列夫斯基:《现代机器理论的状况和它的迫切任务》,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54.第4页。)通过研究,前苏联学者基本达成以下共识:(1)技术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有机地联系着,但是,自然科学知识在技术手段中“被取消了”,它采取了“自然技术知识”的形式。该种知识是指围绕着要创造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技术手段,对自然科学的概念、规律进行补充,使其具体化。(2)技术知识可以分为设计的知识和工艺的知识,尽管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前者是指能够指导建设、制造技术设备及其组成部分的知识:后者是关于加工、制造劳动对象的方法和过程的知识,与前者相比它的特点是操作方法的知识占了很大比重。(3)技术规律是人工构成物性质、关系稳定的必然的联系。它表现为抽象方案、理想技术客体(如卡诺热机)、技术原则等形式,从而使制造能带来技术效果的机器设备成为可能。(4)技术科学能够“绕过”自然科学,在自然客体自主的状态下研究它并揭示新的技术规律(蒸汽机的发明就是如此)。如果结论是直接从自然科学知识中得出,那么,自然科学作为伴随的次要方面也能对技术规律给予指导。(5)技术科学同社会科学有机地联系着,这种联系表现为社会技术知识,即从技术-经济学的、工程-心理学的、技术-美学的以及其他社会观点来评定技术手段。(注:см.:Г.И..Шеменев.Философия и техн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
除了强调技术与科学的区别,特别是不能把技术简单地看成科学的应用以外,前苏联学者还认为在科技革命的形势下,由于基础研究和技术发明之间的距离日益缩小,还应关注技术和科学的相互作用问题。л.в.亚先科就认为:“发明的使命就是用被掌握的、在社会控制下的、在专门装置内部起作用的自然力来代替人力。这时来帮助发展者的,不仅有揭示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而且有提供已建装置、零件方案以及技术规则的技术科学……在这种形势下,越发强烈地感到并不需要绝对增加专业人员的数量,而是借助于加强科学技术合作来消除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之间的脱节现象。因此,应该建立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创造学交叉点上的边缘学科。”(注:И.Т.弗罗洛夫:《辩证世界观和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第376-377页。)
这一时期,前苏联学者研究的问题还有技术进步(提高创造性活动和劳动生产率)和新人形成(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新价值观的形成)等问题,《哲学问题》杂志1975年第8、9期连续发表了长篇社论,强调了这类问题的重要性。总的来说,前苏联学者能够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基本观点出发,对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这场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问题做出哲学反思,在欧美技术哲学的丛林中树立起具有自己特色的旗帜。特别是对技术科学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所作的分析(这种分析直接源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前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发生的重大转向,即从所谓的本体论研究转向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是比较深刻的,不仅影响了我国技术哲学的研究,而且为西方学术界所关注和引用。这种变化也表明,与萌芽时期相比,越来越多的职业哲学家而不仅仅是工程师开始关注技术哲学,出现了所谓哲学研究的“技术转向”。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时期前苏联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存在不少缺陷,比如学术空气沉闷,研究成果整齐划一,特别是缺少像恩格迈尔那样有独创性的学者。而某些提法,如“马克思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А.А.库津),则明显地曲解了马克思的思想,造成了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的混乱。
三 走向世界:日趋成熟的俄罗斯技术哲学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东欧发生了一系列巨变,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经过10多年的发展,俄罗斯技术哲学已由当初的变动不居到今天日趋成熟,表现出既与西方技术哲学趋同演化又力求保持自己特色的学科特点。
事实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就已经从过去的闭门造车开始走向世界。首先是出版了一些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著作,如《西方新的技术统治论的浪潮》(1986)、《联邦德国的技术哲学》(1989)等;其次是涌现出一批颇有见地的技术哲学家,如В.М.罗任、Ф.Н.布留赫尔、В.Н.布鲁斯等,与他们的前辈不同,这些哲学家对技术的思考多是从人文的(Humanities)而不是从工程的角度出发;其次,对西方技术哲学的许多结论由过去主要是批判转变为主要是吸收借鉴,对许多曾经是批判对象的哲学家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普遍认为西方技术哲学研究的特色是:“清晰地反映出人文科学和价值哲学的关系;把技术的本性与实质以及它对于我们文化发展的意义等问题置于首位;对其他一些与一般哲学问题相伴随的问题的思考,如对技术方案的评价与鉴定、对技术发展的预测以及工程师的教育问题等。事实上,自М.海德格尔、к.雅斯贝尔斯、л.芒福德之后,国外技术哲学家就在把我们的文化与文明危机和技术(准确地说是广义的)联系在一起了。”(注:см.Новая технократия волна на заиаде,м.,1986.)
技术是什么?这是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每个研究技术哲学的人都要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过去前苏联技术哲学界对技术的理解是统一的,前苏联《大百科全书》关于技术的条目倾向于“手段说”,认为技术是“为实现生产过程和为社会的非生产需要服务而创造的人类活动手段的总和”,“生产技术是技术手段的主要部分”,而“生产技术中的最积极部分是机器”。因此,前苏联技术哲学并没有深入探讨技术的本质问题,而是积极发展“机械和机器理论”,形成了“技术=生产技术=机器”这样一种简单化的倾向。现在则不然,俄罗斯学者对技术本质的理解表现出很大差异,主要有:(1)认为技术是一种为社会所需被某些人如工匠、技师、工程师创造的人工物(артефакт),为此,需要利用一定的构思、思想、知识和经验。但是,所有的人工物需要分成两大类:技术和符号。如果说技术遵循着自然规律和实践规律的话,那么符号就必须遵守交际学和符号学的规则。尽管在文化中需要用语言来描述技术建制,但技术本身并不是语言。(2)认为技术就是工具(инструмент),是为了满足人在诸如力量、能量、运动、自我保护等方面的某种需要而使用的工具或手段。这样一来,就把简单的工具和机械(如斧子、杠杆等)与复杂的技术中介(如现代建筑、高速公路等)统统归于技术。(3)认为技术是一个自主的世界或实在(реальность)。它独立于自然界、艺术、语言、所有生物乃至人本身。但是,人存在的一定方式却与技术相联系,当前就表现为文明的发展前途系于技术。(4)认为技术是利用自然界物质和能量的专门的工程手段(инженерныи сиосо6)。诚然,任何一项技术在历史上都是对某种自然力的应用。但是,只有在当代才开始把自然界当作物质、力量、能量的独立的、无止境的源泉来看待,才学会在科学中记述相似的自然现象并使之为人类服务。在这种意义上,技术创造无论是在古代、希腊时代还是在中世纪都被看作是一些小技巧而已,至于如何造物和制造机器是不清楚的。而今,技术创造是对自然力(过程、能量)的一种有意识的计算,是为了满足人的活动需要的有意识的装置,就是发明和工程设计。而这两种活动的前提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理性。总之,通用的、外于历史的技术概念是不存在的。(5)技术和广义的工艺(технология)是不可分的。此前,工艺仅仅是作为组织生产过程的某一方面而存在(其他方面还有组织的、资源的、技术的)。但近二三十年这种情形发生了些许变化,现代工艺是指一系列形成某种“技术圈”(техносфера)的原理的总和,而“技术圈”的状况是由当时的技术水平、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的。在某些工业发达国家,工艺正在逐渐地演变成技术超系统即“技术圈”,它决定着所有简单技术系统的形成和发展,乃至产生出新的技术科学与知识。(注:В.М.Розин.Философия техники и кулвьв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еконструкпии развития техники[J],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6(3),cc.24-26.)虽然关于什么是技术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尚无一致的看法,但俄罗斯学界目前这种争鸣的局面较过去相比更有利于技术哲学的进步。
至于技术哲学的发展方向,俄罗斯学者认为,无论是从对技术知识的结构和演变的认识论分析,还是从对技术含义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论述,都应该转向把技术当作人类文明发展的复杂的、多方面的和矛盾的因素,进行综合系统的、跨学科的分析。因此,广泛意义上的技术哲学并不是哲学,按照知识的特点和它所要完成的使命,这种对技术的反省不仅仅是哲学的,而且是方法论的、价值论的,特别是伦理学的。在分析现代技术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影响时,普遍认为潜藏着三种危机:对自然界的破坏和毁灭(生态危机);人的嬗变和灭亡(人类学危机);第二、第三自然即组织的结构和社会的基础不可控制的改变(发展危机)。所以,技术哲学目前最大的争议领域应该是关于技术进步的社会后果问题。
众所周知,前苏联解体以后,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物质条件上,俄罗斯的技术哲学研究都是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进行的。尽管这样,俄罗斯学者还是做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从一开始的全面西化,到后来逐渐结合上自己的特色,特别是把技术置于广阔的人类文化史中去把握,克服了对技术的自然主义理解。他们一方面把技术看成是复杂的智力和社会文化过程,另一方面,又把技术当作人生存的一个特殊环境。这种技术观给出了另一种技术-工程的世界图景,也标志着俄罗斯的技术哲学正在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