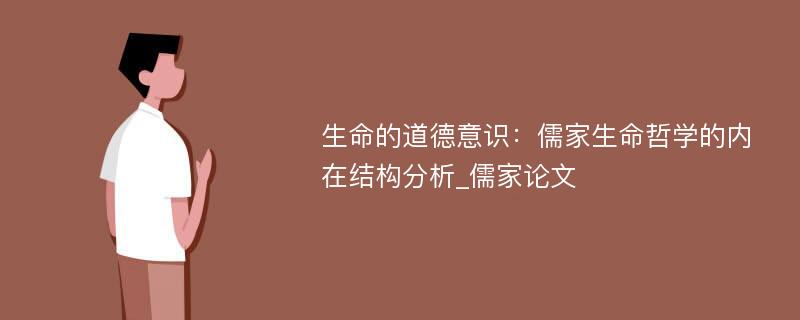
德感生活:儒家生活哲学内在构造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儒家生活理念中,道德是生活的前导和感通性力量,该生活样态可定名为“德感生活”。在思想生态的历史变迁中,“德感生活”的理论重心也经历了从“礼”向“理”的转变,生活理性的反思面也从显像层转向潜隐层。先秦儒学重“礼”,反映在生活观念上就是先秦儒学倡导礼治生活,要求对生活事象的形式化引导,德感生活表现为对外在规范的重视;宋明儒学重“理”,更相信内在道德性的力量,表现为生活的性理化、道德的内向化。“礼备德盛”、“穷理明德”是儒家“德感生活”的两种诠释类型。在现代生活情境中汲取儒家德感生活的固有精神,切入当下生活情境,是建构当代生活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德感生活:儒家生活哲学的定名
哲学离不开生活,理性地反思生活、引导与构造新的生活,构成生活哲学的内在要义。生活在此离开了它的物性含义,不再停留在物质表象层面以及日常文化语境,敞开了它的哲学维度。生活理性又要求哲学不停留在玄思阶段,而是深入到生活事件中去,把哲学理性发展为生活的实践理性,也就是说,哲学的抽象思辨和观念系统必须首先进入人类的生活实践,并在这一生活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充实。
儒学肯认“生活”的直面性,即把“生活”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本质特征和终极实践指向,“生活”在此具有本体论的优位和价值,儒家哲学是“生活本体”论的哲学。“生活本体”论的底蕴是把“整体性生活”命名为哲学存有域,而在功用层次上儒学的理论效应和价值系统也以此为依归,所谓“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五)。这透露出儒学和生活的深度关联性。儒家生活哲学强调“生活”的自我构成,生活理性、生活价值、生活意义、生活方法均直接通过生活自身加以说明、得到充分诠释,不必借助“上帝”等“非生活”概念对现实生活进行附加性注解与佐证。生活在此具有了自足与自主的属性。
儒家生活哲学可界定为“德感生活”。在古代语境中,“感”既指主体性的情绪和意念,如感情,亦有向外的感动、感触之义,如(以德)感通万物、(以德)感格人心、圣人(以德)感天下、(以德)感格于神明等等。德感生活有主体性含义——道德感情,对于情感、欲望、意念、意志,儒学把它们转化为道德词语,如道德化情感、道德欲望、道德意志、道德意念;德感生活又有客体性含义或外化的含义,它把“德”看成是中心的和不断转换的价值观念,从而导致“生活的价值学”或“宇宙的道德化”。从理论建构上看,儒家的概念术语如性、心、命、天等本体论话语,皆是德感生活的超越理性之表达;政、学、礼等制度论话语,皆是德感生活的公共生活理性术语之表达;穷理、致知、返本等修养工夫论话语,皆是德感生活的返己性和反身性之表达。这些术语都是具有道德属性的,由此展现出德感生活的内在逻辑和殊途而同的价值指归。
“德感生活”初发于殷周之际的人文转向和忧患意识的萌动,并在文化精神的流变中占据中国生活观念的主体地位。殷人尚鬼,接神而奉之,建立以“天”、“帝”为中心的宗教神性生活结构,生存建立在对“上帝”的信心基础上;周人敬德,“制礼作乐”,其思考重心放在生活制度的建立方面,构筑了以现实生活为依归的礼乐典章制度,生存建立在对人间事务的敬意之上。两者最终发生冲突,殷周之际的汤武革命的思想史效应把中国古人关注生活、反思生活的“生活的道德性”在神学话语之外浮现出来。“德”的问题的出现标志着生活理性的张扬,在精神气象上表现为以生活的道德理性精神反抗神学话语系统,在理性类型上则表现为以天帝为中心的宗教神性转换为以“德”为中心的道德理性,生活价值系统的关键语汇也由以“帝”为中心切换为以“德”为中心。“德感生活”浮出的机缘因先民特有的生活意识——“忧患意识”萌动的历史积淀而生成。对生活价值、生活意义的眷注与笃思所蕴含的生命责任意识,与对生命活动的未来性关切与深远的思虑,是忧患意识的固有内容,由此引发出精神结构中深层次的观念:“敬”;“敬”又渐次形成其道德观念——“敬德”、“明德”(徐复观,第32页)。
儒家德感生活观念是中国哲学的主流或模型,它不仅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心理潜态、文化面貌、思想结构,而且在多元文化建构中,它也直接影响了道家和佛教的生活观念。虽然佛教、道家表层上否定或降低道德意识的优位,但是它们的生活理论中充满了某种“形式的道德理性”或“合道德性”。因此,无论是儒家德感生活、道家自然生活,还是佛教灵性生活,都切中道德本体的意蕴。道德理性构成了中国传统生活哲学的轴心与本质要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生活哲学是儒家的、道德性的。
“德感生活”具有超越性、主体性、情境性的特征。(1)德感生活观念虽然冲决了殷商的鬼神观,但是并没有消弭生活的超越之维度:“德感生活”如欲扩大为普遍的生活理性,就必须对自身的超越根据进行论证。在这种理论要求下,德感生活的理论进路是“以人化天”,“天德”合于“人德”。前者指的是天道之性质及其创生力量,如《周易》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后者指的是人的道德努力。儒家对生死鬼神等问题的悬置,以生活理性和生活实践开始取代神意和神圣启示成为玄思的中心和主要内容,其出发点虽是人的当下生存状况,但又把人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的超越之维紧密联系起来,并把后者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生活与超越精神的合一,这种超越不是对外在的崇信,而是内在的超越。例如,先秦儒家把德感生活中的“礼”看成“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礼记·礼运》)。(2)真实的“生活”必然落实到主体的生存上:德感生活具有主体性特征,是主体生活世界的伦理实践方式。在该解释框架下,“道德”是业已“觉解”的个体的生存意义域和体证之境界,一切社会文化活动都统摄于自我道德意识,是自我道德意识的外化形式和分殊之表现。更为重要的是,德感生活又将主体性转化为内在的道德性,这构成了中国哲学中丰富的道德修养论内容。于是,德性的生活实践以个己生命活动的开展为对象,生命活动也就转化为道德理性的实践活动。儒家所提倡的“为己之学”、“慎独”、“躬行”和“格物”、“致知”,无不是德感生活主体性的表征。主体性还表现为理论的切己性,哲学思考主体嵌入所欲理解的对象之中,知识、学问与生活事象相互感通,玄思和生活实现双向互动。在“生活”的融摄下,形上学本体论话语、工夫论话语、知识论话语彼此渗透。(3)在儒家的生活哲学的视野中,“生活”具有主体性、即时性与当下性等诸多特质,因而“德感生活”持一种“情境主义道德观”(situational ethics)。儒者思考的起点是生活经验与先于理论建构的微观“生活事实”,并把它们内化为主体的感性的道德价值,强调以“生活经验”为介质,把“经典”和“现实”、“理性”和“感性”、“经验”和“想象”加以整合。这样,通过对生活“事物”或“事件”的详致观察和“冥游神想”般的道德体验,对当下生活场域进行道德的意义重构。
二、类型Ⅰ:礼备德盛
经过先秦儒者的努力,德感生活的理性精神取代了先周宗教神令式的教条主义,把宗教转化为“礼”教。“礼”——日常生活的具体设施——是道德生活的实现形式,儒者坚信“礼”能够唤醒人的“道德自觉”,培育“德感”生活理性。“礼”既要维护生活的秩序、对生活秩序之认同,又会加强对“礼”的重要性的认识,而“礼”的践行则导向生活中的道德自觉意识。以“礼”为枢纽,生活秩序→道德自觉→道德生活,在逻辑上构成顺次演进的序列,但它们又是共时性存在,互相之间是融洽感通的。“礼”把生活建构为德感化、逻辑数理化的象征符码体系,在完全自发的、协调而适宜的礼仪行为中,生活的道德性得到自然体现,生活即成为道德性的礼治生活。于此,“礼”成为把握原始儒学理论的一把钥匙。
进一步而言,先秦儒者坚信“德”和“礼”合一。一方面,礼的确立是基于对人之性情的认识:“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史记·礼书》),另一方面,礼是道德的“寓所”。这样,首先,礼被规定为“道德生活的秩序”,是道德生活的理念化、象征化。如《礼记·礼运》中说,礼“始诸饮食”。其次,礼还使人性的生活得以维持,并且是判定生活品质的标尺。先秦儒家甚至把“礼”提升到“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的高度。再次,礼又是德感生活之“本”,所谓“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记·礼器》),“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记·曲礼上》)。
对“礼”的解析向我们展示出“礼”的多层含义,同时也表征“德感生活”的多界面性。如:(1)将它看成超越神圣天命复于人世的法则,所谓“神道设教”(《易传》);(2)礼的产生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是对人际间相互冲突的欲望的调适(《荀子》);(3)礼是人们表达精神生活和内在情感的较为雅致的途径(《左传》);(4)礼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感的最后呈现形式(《中庸》);(5)礼是教化“中人之性”的工具(董仲舒);(6)礼是“天理”之节文(朱熹);(7)礼是主体内心生活中的“自适其宜”之“理”(陆九渊);(8)礼是因顺“良知”自然的条理(王阳明)等。上述诸种关于“礼”的界定,皆把礼还原为生活的道德理性:礼以德为体,这种本体可以是神性、情感、欲望或道德律。
礼学是生活实践之学、道德运作之学。国家政治建制、社会交往习俗、个己心性修养是礼化生活实践的几个层面。《周礼》、《王制》载有西周的典章制度;《仪礼》载有宗周春秋的仪节规范;《礼记》则多从人情、天道、心性角度说礼,这三者(礼制、礼仪和礼义)恰好构成了德感生活展开与运行的三个层面——政治生活典章制度、社会交往人际行为、精神生活。
第一,在制度方面。儒家有“周公制礼作乐”的传统说法,纤悉毕备的礼乐制度是周人维持其独特的观念——“德”的关键性思想文化设施。《左传·文公十八年》有季文子语:“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周公之言点出了“生活之则”、“生活之德”和“生活之事”之间的深度关联,国家治理的各项礼制都是道德理性的具体体现。
第二,在礼仪方面。周代号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仪、威仪是古代道德生活的仪节化产物。生活道德和日常之仪节是对应的,有何种“德”,必有特定的“礼”与之相契合:因父子之道而制为士冠之礼,因君臣之道而制为聘觐之礼,因夫妇之道而制为士婚之礼,因长幼之道而制为乡饮酒之礼,因朋友之道而制为士相见之礼。在礼仪的践履过程中,负载着抽象德性的礼仪,作为道德运作的具体形式,直接作用于行为,成就了儒家的道德行为艺术。
第三,在精神生活方面。“礼”是精神生活世界的整体符号象征系统。“礼”是“礼仪”的精神化,是蕴含在礼仪行动中的价值原则,是构建德感生活形上义理的重要内容。从精神生活角度看,“践礼”不仅是遵守外在的规范,更是遵循精神世界的道德律令,它表达出人们对外在仪范的内在认同,以及对内在道德感情的认知。例如简单的“射箭”(“乡射礼”)动作隐喻着内心世界的道德秩序:“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礼记·射义》)。至于把礼诠释为“中庸”、“诚”的天道性命思想,则纯粹属于精神世界的思辨,它说明:“践礼”将导向道德形而上学,而后者则赋予“礼行”形上之根据。
三、类型Ⅱ:穷理明德
不同于先秦儒学以“礼”来说明道德生活的思考方式,理学生活哲学的核心是“理”。在先秦儒学的观念系统里,已经产生了“礼是万物之条理”的观念。如果把“万物之条理”归纳、抽离,绝对化为“天理”或“心中之理”,用以反观生活,则走向了理学“穷理明德”的生活观。把生活理性训为“理”(而非“礼”),儒家的“生活之道”就发生诠释学转向,即不再以传统的“礼”来论说生活之道德合理性,解释路径转向了“性理之学”。
在理学“体用不二”思维方式下,德感生活凸显出精微细致的内部构造。首先,“明德”即等于“穷理”。“理”是宋明儒学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它表征着生活世界一切事象的普遍法则,也是事物的本性和道德的根源。(“理”不仅是程朱理学的最高范畴,也是心学的最高范畴,不同的是心学把“理”看作心中之理。)通过“穷理明德”,塑造生活主体的道德自觉,培育其道德实践理性,是宋明儒学的根本旨归。朱熹曾说,“明德”就是“具众理”:“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大学章句》)。王阳明认为“穷理即是明明德”:“格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传习录》上),这是心学意义上的格物明德论。
理学生活观的内在构造,首先表现为生活的二值化,即:未经审视的自然生命或情欲生命,称为原生态意义上的消极生活;天理下贯之理化生活,称为道德化了的积极生活,也就是“德感生活”。它们是理学的两种生活样态,我们分别用生活(-)和生活(+)来指称。理学范畴如理气、道器、性习、人心与道心都同它对生活的二值界划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在生活(-)中,“气”化流行不可避免地导致人性的迷失和道德堕落,这在理学家看来是“欲”和“邪”,这是生活的负面、阴暗面。在生活(+)之中,经过“理”的澄清与转换,一切原生形态的生活世界的骚动、情感焦虑和念想执着都被过滤掉了,它是对生活(-)的否定之否定。在这种生活样态中,由于“理”性的全幅朗现,生活世界的一切事象均转生为德性之光照耀下的道德事象,每一个生活个体都获得了对自身道德属性的明确体认与觉醒,并把对天理的认识划归、落实为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事上的道德践履。
“穷理明德”的内在逻辑构架可表示为:生活(-)→理→生活(+)。
生活(-)→理的过程即是理学讲的“即用见体”。“天理”是生活实践的终极价值引导,它范导着生活,使生活不断得以提升与超越。“生活之事”通往“生活之理”不仅是一种价值跃迁,而且更重要的是生活的层次与境界的塑造与提升。从“生活之事”通往“生活之理”,有三种模式或路径:(1)“明理”。即程朱理学所说的“即物穷理”。明理要求研究渗透入生活事象的自在规律,发掘其道德属性。程颐曾说:“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二程遗书》卷二十五)朱熹也认为,要“随事观理,极深研几,无不各得其所止之地”。明理也蕴含着对主体道德意识的改造,因为我们生活在“彼此关联”、“物我一体”的世界中,“观物察物”与“见物反求诸身”、“随事观理”和“随处提撕此心”的巧妙结合构成“明理”行为的一体两面。穷理不是追逐与我们生活无关的客观知识或概念,而是竭力寻求内在于实践主体自身的生活理性,这体现了知识、道德、生活三者的合一。(2)“逆觉”。牟宗三探讨了心学中的两种体证工夫。一种是“超越的体证”,如禅修之静坐,虽不必隔绝现实生活,却要在静中闭关以修之;一种是“内在的体证”,即内在的“逆觉体证”,它要求对于本心而言反而觉识之、体证之。“内在的体证”(逆觉),是“就现实生活中良心发现处直下体证而肯认之,以为体之谓也,此所谓‘当下即是’是也”(牟宗三,第394页)。心学强调体认“心中之理”,“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工夫论上有“复其本心”、“致良知”或“逆觉体证”诸种异名,它们都是要发见我们本来业已完全具备生活理性、生命价值和道德经验。所谓体证无非是“全体发见”此生活理性,从而促使生活的圆满。(3)“践形”,即在客体化的“事物”、“形体”、“人力”上面进行道德实践的生活理性,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颜元、戴震为其代表。
理→生活(+)的过程即是理学讲的“由体发用”。生活理性决不是静态的玄念,而是必须在生活事象中得到自我确证和意义充盈,于是,“理”便呈现为“百姓日用”,也就是说,生活的超越维度——理体(心、性、知)——必以生活事象为终极指向。生活之“理”不是悬诸云霄的设准,而是以转化为生活现实层面运转的力量为鹄的。理学思想中最值得称道的“百姓日用之学”就体现了这种精神——超越的形上“理”体赋予了生活事象的道德性,从而使生活演化为道德生活,这是生活的道德形上学。理学的此类话语很多,如“道理只在日用常行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百姓日用莫非天命之流行”(《明儒学案·泰州学案》)等等。朱熹认为,“理”要从虚悬转归活用,即要由生活之道(理体)发为生活之用(百姓日用):“道之体用……能虚心静虑,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实。”(《朱子全书》卷一)程颐持相同观点,王阳明也非常强调生活中的道德实践,认为“致良知”即是“实实落落”去做,戴震则坚持道和日用的合一。三者的思维进路虽有差异,但都坚持生活超越之理要贯彻到具体的日用、器物中去。惟有如此,生活理性才能与生活样态、生活实践保持始终应然的张力,从而使生活获得内在的引导与规范,生成德感生活。
概言之,“由一本而万殊,而所谓体者,常呈露于用之中。合万殊而一本,而所谓用者,未尝离乎体之内”(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九),这是理学的体用生活逻辑构造集中而简约的表达。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体”和“用”、“本”与“殊”之间的运行不是直接现实性的生活运动,而是精神领域内的意念运作,或者说是在意念领域中完成的。“理”的体认和下渗完全系于主体的道德修养,“穷理明德”的生活哲学导致“生活”的理念化、境界化,同时也表明理学生活观念是私己化和精英化的。
四、余论:“德感生活”的现代开展
现代性表现为“生活世界的非传统化”(哈贝马斯语),“现代性生活形态”“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吉登斯语)。现代“生活世界”已经历了陌生化、合理化过程,被贯注了公共性、理性化生活程序。在中国,现代性生活观念冲击的直接后果是儒家“德感生活”的渐次解体,这是由儒家德感生活的固有弊端决定的。在德感生活的解释框架下,道德成为古代文化的核心价值系统和社会生活中的渗透性力量,道德化言说方式变成支配性话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德感生活”的排他主义思考方式容易造成“道德至上主义”、“道德绝对主义”以及“泛道德主义”。然而,只有在现代情境中,我们才能较为明晰地辨识这种弊端。“五四运动”前后,梁启超、李大钊等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两种生活观念的冲突,这就是“静”的生活与“动”的生活的对峙。他们认为,古典生活观念导致“闭关自守”和“静”的生活,道德、圣道、王法、纲常名教也应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郭湛波,第120页)。“五四运动”对“吃人的礼教”和“理学杀人”的批评有其合理之处。
然而,在这种理论气候下,仍然有学者在努力使“德感生活”进入现代社会。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的,道德生活是中国传统生活界域的主体和渗透性力量。在现代的人心政俗之变之过程中,要接续儒家生活哲学的理性精神。(梁漱溟,第133页)儒家生活哲学的现代开展问题一直是冯友兰思考的重点,《新原人》提出的“人生四境界”也可以说是生活的四境界。他还把《新世训》定名为“生活方法新论”,力图构造古老儒家生活哲学的新样式,用崭新的现代生活经验去诠释、接引、落实儒学德感生活观念,使之在变化了的世界里重新获得话语能力。《新世训》的突破点是:生活方法必须以“眼前之事”为证,而不必遵循古代的教条;生活方法是依据每个个体所皈依的生活理性而不必如宋明理学家那样以“圣人”标准为遵循,也就是说,要“为生活而生活”,而不是为了达到“圣人”的目标而生活;生活的目标不必像理学家那样崇尚静止的“境界”或“气象”,而是要在现实生活的运动中来把握。(冯友兰,第375-381页)《新世训》强调遵循生活的道德理性和理智理性精神,并把“尊理性”集中在日常道德生活视野内,消解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生活实态之内在紧张关系,从而力图达到接续传统道德观念进入崭新生活世界的目的。唐君毅则认为,“当下生活之理性化”是儒家传统“尽性立命”的补充义、延伸义,必须以当下的情境为起始点,亦即人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必须面对此当下情境而开朗。在此之境,“性命之德”与“天德”同时流行,这是儒家生活理性、生活哲学切入现代生活情境的另外一种方式。(《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第760页)唐君毅认为儒家生活哲学应因时而变,其理论旨趣比起遵循绝对“天理”律令的宋明儒学无疑鲜活了许多。方东美从哲学人类学视野界划了德感生活,他把生活境界界划为物质境界、生命境界、心灵境界、艺术境界、道德境界。“道德生活”归属于道德境界,是生命地位、生命成就、生命价值之最高地位的体现,道德生活可以旁通一切人类、一切万物。(《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方东美卷》,第467页)这些见解显示了当代儒家较为开放性的视野。
在现代社会中,儒家“德感生活”的具体设施、度数、仪则或许已过时,运作机制也需要改迁。在维护“德感生活”的理性精神和超越原则之外,追寻生活的道德理性的实现形式,应该是儒家进入当下生活的可能方式。建构当代中国生活哲学,“德感生活”的缺位将使我们错失中国文化的核心与精髓。这一文化认知同时也为中国哲学的自我更新敞开了一条隐秘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