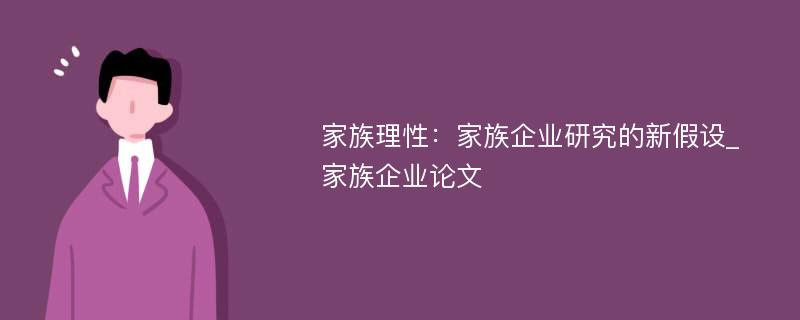
家族理性——家族企业研究的新假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族企业论文,理性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家族企业作为企业的主要类型之一,普遍存在于现实社会中,对家族企业的研究目前也成为一个热点。但家族企业优其是中国的家族企业)的许多问题却难以运用西方企业的理论去解释。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西方企业理论本身的假设与方法之误。将“家族理性”作为研究家族企业的前提假设,则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合理的逻辑基础。
一、家族企业及研究中的难题
1.产权与治理机制问题
对中国家族企业的产权问题,基本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家族企业产权关系简单,产权主体明确。因为家族企业产权拥有人数较少,企业资产的归属、支配、处理和收益关系比较明晰(甘德安2002)。另一种观点认为,家族企业产权高度集中,原始主体界定不清。产权主体界定模糊有两个表现:一个是家族成员内部之间产权界定不清;二是家族企业与外界产权关系不清(姚贤涛 王连娟2002)。而家族企业产权的模糊性是与“家”概念本身的模糊性联系在一起的(李欲晓2003)。
比照西方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以及西方社会的现实,中国的家族企业的确存在产权模糊不清的问题。产权模糊不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笼统地说受中国传统文化家族观念的影响是不够的。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甚至没有“个人产权”的观念,以及社会本身没有保护个人私有权利的法制传统和法律制度。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也大量存在家族企业却不存在产权不清问题的现象。
根据西方企业理论,现代企业的治理机制应当是建立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相分离的基础上。目前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则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实际分离,企业与家族合一,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主要控制在有血缘、亲缘和姻缘为纽带组成的家族成员手中,企业决策程序按家族程序进行。
如何解决治理机制的问题呢?企业的产权与治理结构是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家族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否分开并不重要,而且一定要分吗?这里面显然存在着很深的理论问题需要研究。现实中的确存在大量的家族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不分离也管理得很好的案例,但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并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理论解释。
2.信任机制问题
目前,中国社会的“信任缺失”问题很严重,已经对社会的全面进步产生了阻碍。对家族企业来说,信任问题更成为制约其健康发展的障碍。
西方学者对中国人的信任问题早就有过研究,而且普遍认为:华人之间的信任度很低或是有限的,是与西方式的“普遍信任”相对的“个人信任”。(马克斯·韦伯1995,雷丁1993,福山1998)目前海内外的华人学者似乎已经接受了西方学者对中国人信任特点的评价,而且根据西方学者的理论提出了自己对中国人信任的解释。其主要观点是:中国人的信任是基于家族主义的家族信任。家族信任本质上就是一种私人信任。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是随血缘关系的不同而区别开来的,并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此外,经过历史的变迁,中国社会的信任已经超越了狭隘的家族信任的屏障,形成了一整套既含有亲情的信任,又含有算计性的工具信任的“泛家族”的信任原则。(李新春2002,卢福财、刘满芝2002年,姚贤涛、王连娟2002,储小平2003)
信任问题和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二起的。有学者把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的关系问题归结为职业经理人本身的职业道德,并认为,职业道德的根源在于制度。(张维迎2001)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不仅缺乏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职业经理,事实上也缺乏具有良好企业家道德的企业主。(储小平2002)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家族企业在雇用职业经理人问题上的特殊障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担心企业重要的商业“隐私”信息的流失;二是家族担心可能失去对企业的实际控制,而蜕变成经理人控制的企业。中国的家族企业未必具有国外企业所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职业经理人本身也有着强烈的家族主义价值取向,既他会将作为经理人看成是为别人作企业并把这一过程看成是自己学习创业和获取社会资源的平台,一旦有机会,他就会去开创自己的企业。在这种双方的信任博弈过程中,家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加剧了双方的互相不信任。(李新春 2003)
3.封闭与开放问题
中国的家族企业已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挑战,是继续维持传统的以家族为核心的封闭式经营局面,还是勇敢地打破家族血缘关系网络所构成的樊篱,走向公众化的道路?
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关键。如果这种社会资本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就可能成为家族企业发展的障碍。(曹祥涛、郭熙保,2003)问题是,向哪个方向积累和提高?是沿着原来的以“家族”和“血缘”为起点的方向继续提高?还是向着以“个人理性”为基础的方向转移与提高?不能忘记的是:社会资本深深的根植于一个社会的宗教和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时要看到,即使在现代西方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企业依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见2004年1月2日《新闻晚报》;维里尔,1999)家族企业接班人的选择问题事关家族企业的健康存续与发展,任何一个家族企业的所有者们莫不对此极为重视。家族企业产权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家族企业接班人的选择更多的是采取“血缘继承”、“代际传承”的方式,以确保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
有学者认为,家族企业的血缘继承模式有着天然的缺陷。(潘晨光 方虹,2003)但为什么大多数家族企业仍愿意采取“血缘继承”、“代际传承”的模式?无论是中国的家族企业还是外国的家族企业,寻找和培养继承人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选择封闭式的家族化管理模式还是开放式的非家族化管理模式的问题,是要把企业引向哪种发展方向的问题。
4.研究中的理论难题
由上不难看出,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面临着一些理论上的难题:一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如何理解“产权”、“所有权”等观念?二是如何理解“血缘”、“缘分”等等因素在人的经济理性中的作用?三是如何将中国社会“家”文化的传统纳入经济理论的体系之中?
这些问题涉及对一些基本的西方企业理论概念,尤其是其前提假设——“个人理性”的理解与认识。“个人理性”是被西方社会奉为圭皋的理性原则。在这背后是西方社会传统文化的大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下,最突出的是“个人”的观念。产权、所有权、经营控制权等等,都是建立在“个人”观念基础之上的。对所有经济问题的理解都是依照“个人理性”,强调“个人”的权利。这正是与中国社会截然不同的地方。
对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说,如何突破中国“家”文化的传统,特别是血缘关系的负面因素的束缚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然而,这种突破是否意味着应从根本上抛弃中国“家”文化的传统?是否意味着像西方社会那样(事实上,在西方也未能完全做到)将人们彼此从“血缘”的纽带上彻底剪断,使人变成纯粹的只知道经济利益、只会计算个人经济利益的“经济人”?那样,是否中国人也就完全变成了与西方人一样的“个人”呢?显然,这都是做不到的。
许多学者在研究家族企业的问题时,往往不加批判地借助于西方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可在中国家族企业的实际问题面前,却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个现象说明,一方面西方企业理论存在着缺陷,另一方面尚未能建立起合理解释家族企业问题的经济学企业理论。那么,西方企业理论的缺陷在哪里?
二、企业理论的假设与方法之误
西方主流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团队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对于打开被新古典经济学处理成“黑箱”的企业,的确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所创造和使用的概念,如交易费用、契约、有限理性、团队生产、资产专用性、可剥削性准租等,在解释现实中企业的特征和性质时确有其科学与合理性。
但是,在现实世界里,企业的组织形式是复杂而又多样的。尤其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说,上述企业理论的解释力显然不足。原因何在?
1.前提假设之误
科斯认为其写作《企业的性质》的目的,“就是要在经济理论的一个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这个鸿沟出现在这样两个假设之间:一个假设(为了某些目的而作出的)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为了其他一些目的作出的)是,资源的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我们必须说明在实践中影响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基础。”(科斯1937)在科斯看来,“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而交易费用的存在为这种选择替代提供了的基础。在科斯所说的假设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假设?既然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企业被假定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那么,是选择市场还是选择企业进行经济活动,就取决于企业家(权威)的个人选择(个人选择理性)。进一步考虑到科斯所处的社会制度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科斯的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假设——个人理性之上。
团队理论并没有直接说明其理论所依据的假设,但其理论所阐述的内容是,团队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独立个人之间的协作是团队生产的本质特征,由于团队中个人行为的不可精确测量,会导致机会主义的产生。我们不紧要问:个人为什么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呢?这里面。显然隐含着一个前提性的假设:个人的自利理性。
威廉森的观点是:“交易成本经济学据以运作的认知假设和自利性假设分别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有限理性被定义为‘在意图上是理性的,但仅在有限程度上如此’的行为;机会主义则被定义为用诡计来追求自我利益。”(威廉森2001)
在詹森和麦克林(1976)看来,代理关系的本质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所签订的一份合同。“如果双方都是效用最大化者,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代理人不会总为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行动。”可见,委托——代理理论的假设是:委托人和代理人根本利益的对立,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者。很明显,这里同样隐含着一个更深层的假设:个人的自利理性。
如此,很容易得出结论:所有现代西方主流企业理论,无不是建立在“个人理性”的前提假设基础之上。“个人理性”是西方经济学及其企业理论最基础的前提假设。
“个人理性”这个假设的设立有其深刻的传统文化背景,是依据西方社会的思维传统所作出的“合乎逻辑”的假定。这种思维传统就是自古希腊、古罗马以降,尤其是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所极力倡导和推行的“个人”的权力、平等、自由、民主传统。在古希腊的文化传统里,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原子式的,每个人都只是社会中的一个独立的“原子”,它构成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社会的秩序要靠“原子式”的“个人”之间的契约以及由契约构成的法律来维持。而家庭、家族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在文化和宗教的意义上被消解、被抛弃了,“血缘”关系也被强化了的“个人权利”所遮蔽。在经济上,只有从利己出发的、为自己的利益精心算计的“个人”才是“理性的个人”。“个人理性”成为一切个人的经济行为的出发点。
西方企业理论的“个人理性”的假设显然过于抽象。“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自利性,或极大化原则的强调,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汪丁丁,1998;徐华,2003)西方经济学家也意识到了“个人理性”假设的缺陷,并做出了种种修正,如用“个人的有限理性”代替“个人的完全理性”,用“效用最大化”代替“利益极大化”等等,但由于始终不放弃“个人理性”这一理论假设,因而,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也无法解决由于个人追求单纯的经济利益所产生的经济伦理与道德问题。同时,更无法解释家族企业优其是中国的家族企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个人理性”假设的缺陷,还体现在其逻辑基点是个人“利己”与“利他”动机的二元分离。这导致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理论逻辑不能兼容个人的“利己”与“利他”两种理性,更无法解释“血缘”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
在研究家族企业的问题时,简单的套用西方企业理论,就等于不加分析地接受了其理论得以建立的基础假设。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愈加远离对家族企业本质的认识。
2.方法之误
西方社会是典型的强调“个人”的社会。个人与社会即等同又对立,个人之间的竞争被视为社会的常态。家族的观念则被有意识地消解于争取个人权利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1998)因此,个人主义成为西方社会文化传统的核心。个人主义方法亦成为西方学术领域研究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本方法。
这种方法论最主要的缺陷是“它把个体与社会等同起来,把社会当作个体的简单加总,从而无法对社会有机体做出科学的解释。”(林岗 张宇,2002)社会或企业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但它们并不等于是众多个人的机械的简单加总,而是有着特殊的规则和特定的结构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一旦形成,就具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单个的个人所不具有的特殊属性。”(同上)
家族企业本身是社会有机体。家族企业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社会上独立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尤其在家族文化根深蒂固、家族伦理观念极强的中国社会,血缘联系使得家族及家族企业中的“个人”与整个家族融为一体。在家族的经济理性诉求中,家族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家族整体利益的稳定发展往往是第一位的。家族中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也与西方式的“个人主义”所倡导的不同。研究家族企业中的“血缘关系”问题时,显然不能把家族与个人对立起来。因此,当以个人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时其局限性就显而易见。
三、家族企业研究的新假设——家族理性
近年来,许多社会学和管理学的学者也对家族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限于这些研究的角度与方法得不到合理统一的符合家族企业特点的经济学方法论支撑,加之现有西方企业理论的假设与方法之误,使得目前的家族企业研究尚无法形成逻辑基础坚固和统一的理论。
目前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在套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来分析中国的家族企业的问题。但是,当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观念发生碰撞的时候,就会遇到对这些假设和概念的不同“理解”的问题,进一步就会影响到对存在于不同社会文化传统背景下的家族企业本质的认识。
这里不妨将东西方的经济观念及概念作一简单的对比(见表1)。
表1 东西方不同观念及概念体系的差异
西方主流企业理论东方家族企业观念
前提假设 个人理性?
方法论 个人主义 整体主义(家族主义)
产权问题 私人所有 家族所有
利益取向 个人利益 家族利益
行为方式 竞争 中庸和谐
信任机制 契约法律(高文本)血缘关系(低文本)
企业传承 市场选择 代际传承
通过上表,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在研究家族企业时,前提假设的缺失是难以形成逻辑统一的理论的根本。因此,我们提出“家族理性”的概念作为研究家族企业的前提假设。
什么是家族理性?家族理性是以家族或“缘份共同体”及其事业的整体荣誉、整体利益和稳定发展为最高价值取向而支配人去思考、推理、判断、行事的心理认知结构。(李东,2004)
相对于“个人理性”,我们认为“家族理性”包含三层涵义:(1)“利己”与“利他”相对均衡的原则,至少在家族、缘分共同体内是如此。延续几千年的中国社会里,在家庭、“家族”乃至在“泛家族”和“缘分共同体”中,利他主义也即人性中的“利他性”根深蒂固。在这个思维传统中,“理性”的最大特点是超越了单纯的“利己”而融合了“利他”,为“己”就是为“他”,为“他”也就是为“己”。(2)安全、稳定发展原则(中庸原则)。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理性”原则,既“中庸”。中国人做事讲究“度”,讲究“适宜”。把这些原则运用到经济活动中,就是追求财富、财产的安全及家族产业的稳定发展。恰到好处就能保证安全,安全有了保证,稳定发展就有了牢固的基础。(3)和睦、和谐一致的原则。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和为贵”。不仅家族内部讲究和睦、和谐,而且整个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也是天下和睦、和谐、天下一家。“和谐”的意识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时的思维传统中。其中,家族的和谐是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和谐。和睦、和谐自然是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要的“理性”原则。
按照“家族理性”及其原则,相信家族企业及中国社会现实中的许多经济问题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标签:家族企业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产权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