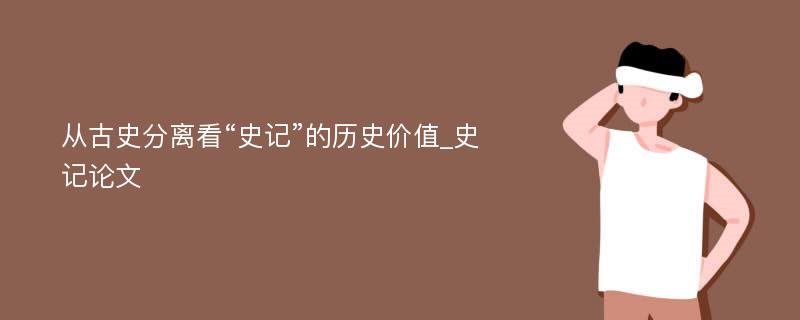
从经史分离看《史记》的史学价值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史学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5-0138-07
一、略说经史的合与分
“经”之名称出现,大抵在孔子没后。当其时,七十子之徒始尊孔子所删定的“六艺”为“经”[1](P1254)。《礼记·经解》即把《春秋》作为六经之一,《春秋》称“经”,此大概为最早。然而,《春秋》是经还是史,从《春秋》出现以至汉代被正式尊为经的这一期间就已存在着不同的阐述。据《史记》所载:“是以孔子明王道……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贬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2](P509-510) 可见,在孔子没后七十子之徒口授《春秋》之“传指”,就已出现“退而异言”[3](P1715),甚至“人人异端”的情形。而左氏则惧失其真,于是“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这也正是班固所言:“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3](P1715) 显然,七十子之徒以“空言”(即褒贬大义)说经,而左氏则“论本事而作传”,而此两者已有侧重义法(包括空言)与注重人事之不同。这里隐然已显示出《春秋》不但蕴涵着两方面内容(即义法与人事),而且这两方面已有分途发展的趋向。正如雷家骥先生所言,如果重视义法为经学,重视人事为史学,那么经史分途在此时已出现。显然,“义法”与“人事”是区分经史的标准之一。
此后,孟子论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4](P192) 《庄子·天下篇》则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5](P288) 由此可见,孟子虽承认《春秋》含有“事”与“文”,但其所强调的则是《春秋》之“义”;而庄子通过比较《春秋》与《诗》、《书》、《礼》、《乐》、《易》,得出《春秋》之主旨在乎“名分”。然而,不论孟子之“义”还是庄子之“名分”,两者显然都属于“义法”的范畴。按照上述的标准,这显然认为《春秋》是经学。
《礼记·经解》认为“春秋之教”在于“属辞比事”。它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乱……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1](P1254-1255) 关于“属辞比事”的含义,一般都认为是“连缀文辞、排比史事”之意。而雷家骥先生则训“比”为“密及”,故而释“属辞比事”为“连缀文字而使之与事相密及”,亦即“如实书事”、“文如其事”;同时,他又把“属辞比事”与周朝史官所谨守的法守与传统即“记事简略而有法”相结合,故而认为春秋之教就是“用文辞以记事,而所用之文辞不违周礼义法,所记之事理有条理而不紊乱”。因此,雷先生认为“属辞比事”实是基本的史学方法论,而《春秋》也就是史学。
其实,《春秋》本身就兼具义、事、文三者,它既含有经学的成分,又具有史学的特质。《春秋》自产生以至于汉代,其著述宗旨就是循守“义法”以“道名分”,但此“周礼义法”又是寓于事中、蕴于文中的,亦即孔子所言“我欲载之空言,不若纪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P3297)。可见,在这一阶段《春秋》虽已称“经”,实际上则兼具经与史的双重特质。
汉初,《春秋》被正式尊为经典且立于学官。《公羊》、《穀梁》秉承《春秋》义理,专研微言大义,走上离史以尊经(即正式形成经学学科)的道路。大约同时,司马迁扬弃《春秋》义理,形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P2735) 的著史宗旨,并在著述体例、著述路数上也显示出独有的特色,这就标志着史学也初具离经而独尊(即正式形成史学学科)的发展趋向。然而,这种分途发展的趋向实际虽已形成,但反映在目录学上却是直到曹魏时期的荀勖《中经簿》,才正式把“史”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与“经”、“子”、“集”相并列[6](P214)。
总之,《春秋》被修之初即蕴涵着史学与经学的双重成分,这可以说是经史合一的状态;同时,也出现了经史分途发展的趋向,而直至汉初《春秋》立于学官与司马迁著《史记》才标志着经史分离在实质上正式形成。当然,分离并非意味着经史之间没有了联系,而是指形成了彼此独立的学科而言。这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说,汉代经学和史学在统一中分离着,也就是说汉代经史在思想上具有统一性,而学科上则朝着分离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一直都贯彻着经学之“例”与“名”的指导思想[6](P214)。
二、著述宗旨:从“微言大义”到“成一家之言”
汉初经学独尊的局面出现之后,治《春秋》之学者尤其是《春秋》今文学日益活跃。大较言之,《公羊》、《穀梁》偏重义例,兼重文辞与史事,循着微言大义的宗旨向前发展。而古文《左传》则偏重名物训诂,但后来亦言义例,沿着以事解经的方法传承《春秋》。其实,不论今文还是古文对《春秋》宗旨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宗旨,也就是《史记》所言:“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2](P3297)
关于孔子修《春秋》以“达于王事”的阐述,孟子早就论及。《孟子·滕文公下》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4](P155) 今文家对此深信不疑、大加阐发,《公羊》曰:“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7](P2354) 后来,董仲舒竟尊孔子为素王,以《春秋》当一王之法。此时,古文家虽不注重阐发《春秋》大义,但从未否定《春秋》义例的存在。据《史记》所载,左氏虽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而“论本事而作传”,但其目的仍在于“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3](P1715)。可见,孔子修《春秋》的宗旨即以“周礼”为准绳而行褒贬,以达于“王道”。这是汉代今古文经所共同的看法。司马迁对《春秋》的论述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汉初学者对《春秋》的认识。他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2](P3297-3298)
可见,自《春秋》之修以至汉初,人们对《春秋》宗旨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即作为“礼义之大宗”的《春秋》,其宗旨在于“辨人事、达王道”。显然,《公羊》、《穀梁》就是尊奉这一宗旨而阐发大义。这种情况在《公》、《穀》之中俯拾即是,如《公羊》阐发“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者正月?大一统也。”[7](P2196) 仅从“元年春,王正月”六字就阐发出如此之多的义例法则,可见《公羊》治经之“微言大义”的宗旨。同样,《穀梁》在宗旨上与《公羊》大致相同,而其重视的则是“谨始”。它阐发“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则是:“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王也。”[7](P2365)
在这种治经宗旨的影响下,《春秋》公羊学经过董仲舒等人的阐发,到何休时最终形成了所谓的公羊家“义例系统”。何休《文谥例》总结说:“《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以矫枉拨乱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纪也。”[7](P2195) 在此期间,《春秋》还出现了经学谶纬化、神学化的情形,还产生了很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这也在一个侧面显示其“微言大义”的治经特点。对此,清代康有为总结说:“自伪《左》出,后人乃以事说经,于是周、鲁、隐、桓、定、哀、邾、滕皆用考据求之。痴人说梦,转增疑惑……盖《春秋》之作,在义不在事,故一切皆托,不独鲁为托,即夏商周之三统,亦皆托也。”[8](P27-28) 虽然,康氏非议《左传》以事说经乃偏颇之见,但他认为《春秋》“在义不在事”不能“以考据求之”,则准确说出了《春秋》之宗旨在“微言大义”[9]。
司马迁崇拜孔子,继《春秋》而作《史记》。这在《史记》中屡有记载,《孔子世家》曰:“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2](P1947) 《伯夷列传》曰:“犹考信于六艺。”[2](P2121) 再者,司马迁曾从公羊学大师董仲舒问学。可见,孔子与“六艺”尤其是《春秋》对司马迁著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司马谈因病留滞周南,不得从事汉家之封而发愤将卒之时,司马迁就答应其父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2](P3295) 后来,他在《报任安书》中又一次申述其继《春秋》而著史的志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2](P3296)
从司马迁继《春秋》的志向,可知他著史受《春秋》宗旨的影响是无疑的。然而,司马迁答壶遂问时却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2](P3299-3300) 这一回答与上述他立志继《春秋》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不然。司马迁在此申述其“述故事”而不可“比之于春秋”,要表明的就是《史记》与《春秋》在宗旨上的区别,这正是史学与经学的区别。
由上述分析可知,一方面司马迁深受《春秋》以及公羊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说其著史不可比之于《春秋》,只是“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那么,“述故事,整齐其世传”显然是关乎《史记》之著史宗旨的。为此,把司马迁“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与《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所言之著史宗旨相比较,可以看出他著史宗旨的本质。《太史公自序》曰:“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作十表……作八书……作三十世家……作七十列传……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2](P3319-3320) 在此,司马迁首先阐述《史记》的整体架构,即“五体”所记述的内容大要,这显然就是“述故事,整齐其世传”的纲要性概括,在此基础上道出其著史宗旨即“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显然,他的著史宗旨就是通过“述故事”而成“一家之言”。对此,《报任安书》阐述的更为清楚。他说:“此人(指西伯、仲尼等)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P2735) 在此,司马迁阐述的更为明确,他著史就是通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以“述故事,整齐其世传”,由此“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最后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
综上分析,当汉代尊《春秋》为经之时,司马迁著史也深受《春秋》的影响,但他对《春秋》的继承则异于汉代经学家对《春秋》的继承。司马迁继承的只是《春秋》“述往事,思来者”之经世致用的精神,以及“我欲载之空言,不若纪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P3297) 的著史方法。也就是说,他扬弃了《春秋》“微言大义”的宗旨以著《史记》。其实,司马迁所遵循的是《左传》“本其事而作传”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从而由“述故事,整齐其世传”达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最后自然而然地达到其著史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P2735)。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言:“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在写史而不是在评史中陈述出来的。”[6](P272)
总之,孔子修《春秋》以后,治《春秋》者多从“微言大义”的宗旨出发。《春秋》被立于学官之后,《公羊》、《穀梁》甚至《左传》显然都以“义例”治《春秋》,借“史事”以阐发“大义”,甚至是“在义不在事,一切皆托”而阐发义理。而司马迁则通过“述故事,整齐其世传”的方式记述历史的发展变化,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自然地凸显出时代精神与历史发展脉搏的“一家之言”[6](P272)。汉初多以“微言大义”的宗旨治《春秋》,这显然属于经学;而司马迁继《春秋》则是通过“述故事”而成“一家之言”,这显然属于史学。可见,“微言大义”与“成一家之言”正是经与史在著述宗旨上的分水岭,而此也注定了经史分途发展的必然。《史记》“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显然奠定了史学在著述宗旨上的独立地位。
三、著述路数:从“春秋笔法”到“实录史学”
记事之“书法”起源甚早。据《周礼》所载,周朝史官即掌礼法并准此礼法以记事,这在《左传》以及杜预所见《竹书纪年》中都有所反映。至孔子修《春秋》又有“笔削”之说,而后逐渐形成所谓的“春秋笔法”。其实,“春秋笔法”也就是使用特定的语言文字记述历史事件,借以表达褒贬之义。
从表面上看,“春秋笔法”只是重视文字的差异,实质上文字背后则“展示出一系列道德规范和判断是非的标准”[6](P262)。更为重要的是,“春秋书法”还反映出当时人们认识历史的途径是“以同概异,以一般绳特殊”[6](P264),即把道德礼义作为一般的原则去认识、评判具体的史实。因此,他们所重视的也就是一般原则,而非具体的史事了。《春秋》显然是从一般法则出发的,即按照“以一般绳特殊”的方法记述历史并表达对历史的看法。
同样,《公羊》、《穀梁》正是沿着“以一般绳特殊”的著述路数出发,也就是从“礼义”之一般原则而非从具体的史实以治《春秋》。这在《公羊》、《穀梁》中非常普遍,例如《春秋》隐公十一年载曰:“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羊》则曰:“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7](P2210) 《穀梁》同样说:“公薨不地,故也。隐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罪下也。”[7](P2371) 而《左传》则详述隐公被弑的原委曰:“冬十月……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僭公于桓公而请弑之……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7](P1737) 前后相较,可见《公》、《穀》对于隐公被弑的原因及其过程不甚在意。它们仅从《春秋》的文字入手揭示其书法,所重视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史实中所蕴涵的一般原则即君臣之间的道德准则。其实,《公》、《穀》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方式解经,这反映出它们的著述路数显然是“以一般绳特殊”。
而《左传》“本其事而作传”,被后人认为是“以事解经”。比如对于“天王狩于河阳”、“赵盾弑其君”等史事,《左传》都是首尾完具、详其本末,以此补充《春秋》之书法隐讳及过于简略的内容,使很多历史真相得以显明。正如桓谭所言:“《左传》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10](P546) 从今天《左传》的文本来看,它的大部分内容是“论本事而作传”,但中间也夹杂着义例的阐述,比如宣公四年曰:“夏,弑灵公,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7](P1869) 这显然是从一般的礼法来认识历史。对此,赵光贤认为《左传》阐发微言大义,乃刘歆所为[11](P155)。即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向发明”之后,《左传》于是“章句义理备焉”[3](P1967)。可见,《左传》在著述路数上虽有“以一般绳特殊”的义例,但更多的则是从具体事实出发,详述史事的原委本末与发展变化。
此后,《史记》不但继承了《左传》记事首尾完具的特点,而且“由特殊而体现一般”② 地记述历史。这突破了“春秋书法”之记事的局限,从而达到全面如实地记述历史的发展变化。因此,《史记》被称之为“实录史学”。
其一,比较《史记》与《春秋》的记事以及《公羊》、《穀梁》的解经义例,我们以为《春秋》、《公羊》、《穀梁》的记事与解经虽注意史事的真实性,但这些记事多是作为阐发一般原则与道德褒贬的凭借,有时忽略甚至损害了史事的真实性(如“天王狩于河阳”等);而《史记》记事则是真实地“实录”历史的发展变化,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道德褒贬的羁绊。因为,《史记》没有直接继承“春秋书法”以定褒贬,而是采取“述故事”的方式全面记述历史的发展变化,以真实地再现历史,并在写史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看法(如“寓论断于叙事”)。这也就是从特殊的历史事件出发“实录”历史的发展变化,从而突破了“春秋书法”之记事的局限,基本上解决了一般原则即道德义理与特殊事实之间的矛盾,缓解了《春秋》在“史实”与“大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情形在《史记》的记事中有很多,比如《六国年表序》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2](P685-686) 秦之德义虽不如鲁卫之暴戾,但司马迁依然正视历史事实。说秦“世异变,成功大”,而对“牵于所闻、不察其终始”的学者不以为然。可见,司马迁记事以事实为准绳不以道德为原则,而是“对史事作全面深入的考核得其真,并加以如实地记述以传其真”[12]。
其二,司马迁认识历史的方法是“由特殊而体现一般”,就是通过实录特殊的历史事实而体现历史之“常”。即,司马迁把历史发展中的“一般”自然地蕴涵于具体史事的发展变化之中,这个“一般”就不再是义例原则,而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由“变”而“通”所体现出的“常”。比如,司马迁指出历代王朝兴起的主因在于道德背后的人心向背。他说:“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2](P759) 显然,这里是从“一般”的角度来论述的,这个“一般”就是历史发展中所包含的“常”,在这里就是指“德”。自三代以至于始皇,历代王朝的兴起,无不是积善累德“数十年”乃至“十余世”,可谓艰难异常。然而《秦楚之际月表》又载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2](P759)
然而,在秦汉之际却出现了一个特殊,即“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的局面。对于这种与历代情形迥异的特殊局面,司马迁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进行剖析,揭示其“特殊”的表面背后依然存在着“一般”,即历史发展变化的恒常因素。他说:“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钮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2](P760) 在此,《史记》首先记述“坏名城,销锋镝”的情况,明确阐明这是“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也就是说秦国为维持“万世之安”所实施的措施,却为闾巷中的“贤者”刘邦提供了迅速成功的历史机遇。我们再进一步比较秦末的暴政与刘邦“约法三章”的仁政,可知这里的“天”并不神秘,它依然是道德与人事激烈冲突与互动的结果。透过这个“特殊”的历史局面,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变化中依然隐藏着“一般”,即“道德”与“人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发展演变,只不过秦楚之际的历史局势变动得激烈一些而已。由此可见,《史记》记述历史的发展演变,不但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方方面面,更进一步从“特殊”的史事中体现出历史发展演变之所蕴涵着的“一般”。正是基于此,《史记》不但全面而通变地展现出“历史之变”,而且还于动态之中深入地揭示出“历史之常”[13](P80)。因此,“由特殊体现一般”正是司马迁记述历史由“变”而“通”、由“通”入“常”地认识历史的路数,并由此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
综上,我们以为《史记》认识历史突破了“春秋书法”。首先,它以历史的真实性为目的,全面而变通地记述了历史的发展变化,突破了由“一般绳特殊”而导致的道德原则与史实的矛盾;其次,《史记》记述历史渗透着“由特殊体现一般”的著述路数,这种著述路数不仅全面地记述了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且还蕴涵着历史的“变”、“通”以及“常”的关系,即通过“通古今之变”以达于历史之“常”。同时,《史记》没有拘于“一般”的原则,致使“一般”损害历史的“真实”,相反,它是由“变”而“通”地展现了变动中的历史真实,由“通”而入“常”地揭示了历史进程中的真理。总之,在著述路数上《史记》突破了“以一般绳特殊”的“春秋书法”,发展成为“由特殊体现一般”的“实录史学”。
四、著述体例:从“春秋义例”到“五体架构”
一般的说法,在体例上《春秋》是编年体,《史记》是纪传体。实质上,《春秋》以及三传所蕴涵着的“义例”应是“体例”更本质的内涵;而《史记》既含编年又有纪传,其实是一种综合体[14](P11-12),其“五体架构”则更能体现其体例的本质。从经学的“春秋义例”到史学的“五体架构”,正是经史分途发展在各自内容与结构上的体现。
在著述体例上,《春秋》显然是编年体,所谓编年就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15](P27),即按照时间的顺序记录史事,其实这仅是史书编纂的表面形式。而古史之“体”指史书的构成内容及其次第联结;“例”则是著史遵循的规则[16]。其实,孔子修《春秋》是“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这已表明《春秋》包含着史书构成内容(辞文)与义例(义法)两方面。而对《春秋》“体例”,唐儒赵匡的解释确为恰当该要。他说:“故褒贬之指在乎例(诸凡是例),缀述之意在乎体。所以体者,其大概有三,而区分有十。所谓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会,此常典,所当载也,故悉书之,随其邪正而加褒贬,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赋税、军旅、蒐狩,皆国之大事,亦所当载也。其合礼者,夫子修经之时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书,是也。其非者及合于变之正者,乃取书之,而增损其文,以寄褒贬之意,此其二也。庆瑞灾异,及君被杀被执,及奔放逃叛,归入纳立,如此非常之事,亦史策所当载,夫子则因之而加褒贬焉,此其三者也。此述作大凡也。”③ 刘家和先生认为,这里所说的“体”,就是孔子修《春秋》时所用以选材和立意的一般标准;“例”则是指对各类问题分别使用不同的书法的具体标准[6](P265)。赵匡所述的“例”与“体”正是《春秋》内容的选材、立意与书法的具体准则,而所谓的“大概有三,而区分有十”就是《春秋》内容与准则的“述作之大凡”。这可谓是《春秋》之“体例”更为本质的内涵。
明乎“体例”的本质,我们可知《公羊》之五始、三科、九旨等,《穀梁》之“正名尽辞”等,以及刘歆所阐发《左传》之“章句义理”与杜预所总结《左传》之三体五例、五十凡等,其实既包含着《春秋》之“体”即选材内容,又包含着《春秋》之“例”即准则义例。从这个意义上看,“春秋义例”实际上包含着“体”与“例”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显然比表面上的编年体形式更能反映出其“体例”的内容及其主旨。
然而,对于《左传》的解经“义例”历来有很多争议④,但多数学者认为《左传》记事首尾完具,是“以事解经”。对此,我们不作专门的探讨。但是,在这种解经方式中,《左传》体现出了“寓纪传于编年”的发展趋向,这对《史记》的体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胡宝国就通过比较《春秋》、《左传》与《史记》,发现编年与纪传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详载史事的《左传》就于编年之中蕴涵着纪传,这种共性的存在就为两者的转换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可能性[17](P27)。可见,《左传》不仅在记事上而且在“体例”上都可以说是从《春秋》到《史记》的一个过渡。
关于《史记》五体的来源历来争论颇多,但对司马迁综合各体创为“五体”则大都认同。程金造说:“凡此五体,均非太史公所自创,而乃仿自前人……其勒此五体以为一书,使之虚实相资、详略互见,彼此裨补、各尽其用。既具史事之文,又见治乱盛衰成败之机者则太史公固为首创,正史中不祧之宗也。”[18](P31-32) 这种“五体架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详细的阐述,他大致规范了各“体”的内容与宗旨,并以此来进行选择、批判史料。进而建构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历史进程。最后,综此“五体”共同以达其著史宗旨,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P3319-3320)。
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并没有严格按照所谓的“五体架构”来规范变动不居的历史,相反,而是灵活地突破“体例”以适应历史的发展变化。张大可把这种现象归纳为“五体破例义例”,他说:“所谓破例是与立例相对而言……无例,述史无规范,必将流于泛滥。死守成例,不能典尽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势将流于呆板。因此立例而又破例,是客观情势使然。司马迁恰好是最善于把握情势的历史家,故所创五体能容纳大量的历史素材,有无限的蕴藏力。”[19](P139) 张先生的总结可谓切中肯綮。可见,司马迁综合各“体”创为“五体”,并没因此而拘缚复杂而变动的历史。相反,则是忠于史实,灵活应变。例如《周本纪》、《秦本纪》等都追溯周、秦之起源与发展以“察其终始”,而非严格拘守一帝一纪;再如为协调名实关系立吕后、项羽为本纪,立陈涉为世家等,都反映出尊重历史事实的实录精神。显然,司马迁没有拘“例”以自限,因“名”而害“实”。这些都说明司马迁非常清楚“体例”只是工具,而著史宗旨才是目的,工具只能为目的服务,而决不可颠倒。
综上,《春秋》以及三传表面形式上是编年体,实际上则是《公羊》、《穀梁》都有自己的“义例”,而这些“义例”既是其内容纲要,又是其义例准则;《左传》亦有“义例”,而其“寓纪传于编年”的著述体例则是向《史记》纪传体的一个过渡。而《史记》没有从《春秋》的“义例”出发记述历史,而是综合各“体”创为“五体架构”,并灵活运用“五体”来实录变动不居的历史进程。
由上述内容可知,自《春秋》之修以至于汉初,经学与史学在学科上先合而后分。孔子修《春秋》之后七十子之徒即尊其为经,《春秋》于是蕴涵着史学与经学的双重成分,当其时经史处于合一的状态。其间,《公羊》、《穀梁》多以“微言大义”阐发其义理,已经走上了所谓经学研究的路子;而《左传》“本其事而作传”则沿着“以事解经”的趋向向前发展。汉初,《春秋》被尊为经,大约同时,司马迁扬弃《春秋》而著《史记》,这标志着经史在本质上的分离已经形成。
在著述宗旨上,《公羊》、《穀梁》皆把“义理”作为治《春秋》之要义,所以借“史事”以阐发“大义”,甚至以“在义不在事,一切皆托”的方式治《春秋》。显然,它们都是以经学的路数,阐发“春秋大义”。在著述路数上,《春秋》及三传都在不同程度上注重“春秋书法”,多按照“以一般绳特殊”的方法记述历史与表达对历史的看法。最后,在著述体例上,《春秋》及三传所体现出来的“春秋义例”,表面形式上是编年体,实际上它们都有自己的“义例”,而这些“义例”就是其主要选材内容与义例准则。而《左传》记事“寓纪传于编年”,对纪传体的《史记》产生了重要影响。
司马迁著《史记》则首先通过“述故事”表现出历史的发展变化,揭示历史进程中的“成败兴坏之理”,以凸显时代精神与历史发展的脉搏,以达到其“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其次,司马迁记述历史渗透着“由特殊体现一般”的著述路数,这种著述路数不仅全面地记述了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且还蕴涵着历史的“变”、“通”、“常”,并“通”古今之“变”以达于历史之“常”,亦即由“变”而“通”地展现变动中的历史真实,由“通”而入“常”地揭示历史进程中的真理。这就突破了“以一般绳特殊”的“春秋笔法”,从而发展成为“由特殊体现一般”的“实录史学”。最后,《史记》综合各“体”创为“五体架构”,并灵活运用“五体”来展现变动不居的历史。显然,《史记》没有按照“春秋义例”来记述史事,而是融合各“体”创为“五体架构”的史书新体例。
总之,比较《春秋》及其三传与《史记》,我们以为它们于著述宗旨、著述路数以及著述体例上存在着显著的区别,这些区别正是经学与史学的区别,也正因为这些区别决定了经与史分离的必然性。很明显,《史记》正处于经史分离的关节点,而此关节点正凸显了《史记》在中国古典史学上的地位与价值。正如赵翼所言:“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20](P3) 显然,赵翼是仅从“五体”来推尊《史记》为史学之鼻祖的地位。我们以为从经史分离的角度来看,《史记》不仅在“五体架构”,而且还在著述宗旨、著述路数上都扬弃了《春秋》,从而成为“史家之极则”,这也就更全面地说明了《史记》在中国古典史学上的地位与价值。
收稿日期:2008-04-12
注释:
① 本文所探讨的经与史,主要集中于《春秋》、《公羊》、《穀梁》与《史记》,兼及古文《左传》,重点阐述今文经与《史记》在著述宗旨、著述路数和著述体例上的区别,以展现《史记》之发凡起例的史学地位与价值。
② 在此,我们使用的“由特殊体现一般”,与刘泽华先生在《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一文中所说的“由特殊而见一般”略有不同,参见刘泽华:《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此处的“一般”指历史之“常”。
③ 参见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本文引用部分转引自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④ 关于《左传》之解经的内容,至今还有不少争议。一般认为今本《左传》的内容大体是《左传》原本,但也有学者如赵光贤就以为其解经部分是后来流传过程中加上去的。其实,除去《左传》文本本身的争议外,这种争议本质上是《左传》“以事解经”与“以义例传经”的两种路数的纠缠与矛盾。就今天的《左传》文本而言,有许多内容是首尾完具地记述历史史实,而其中所含有的“义例”也与《公》、《穀》之微言大义的义例有所不同;再者,刘歆尤其是杜预所阐发的义例是后来归纳出来的,并非全部都是《左传》原本所含有。我们以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左传》在“体例”上兼含“以事解经”与“以义例传经”,是从经学的“春秋义例”向史学的“五体架构”的一种过渡。
标签:史记论文; 司马迁论文; 儒家论文; 太史公自序论文; 春秋论文; 国学论文; 报任安书论文; 孔子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左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