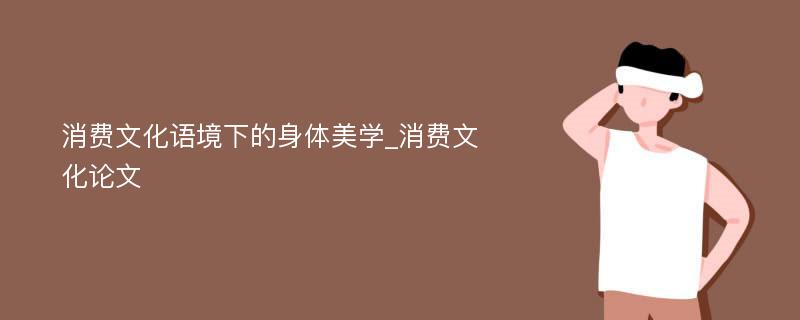
消费文化语境中的身体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美学论文,身体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身体研究在当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兴起
消费社会中的文化是身体文化,消费文化中的经济是身体经济,而消费社会中的美学是身体美学。这样来概括我们今天这个消费社会及其文化,虽然有点夸张,但还不算太离谱。《身体与社会理论》(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的作者克里斯·西林(Chris Shilling)指出,身体问题在西方社会文化理论中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学者一致认为,在当代消费社会,身体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核心,即一个人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感觉,而不是出身门第、政治立场、信仰归属、职业等,来确立自我意识与自我身份。① 随着对于身体的学术兴趣的空前高涨,出现了“身体社会学”、“身体美学”、“身体文化学”等等所谓的新兴学科。美国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Bryan S.Turner)提出了“身体化的社会”(somatic society)这个概念,以示身体在现代社会系统中已经成为“政治与文化活动的首要领域”②。
消费社会中的大众传媒对于身体的兴趣更是强烈得无以复加。各种各样的时尚报纸、杂志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身体意象,花费大量的篇幅推销化妆、减肥、健身、整容外科技术,介绍如何使身体显得年轻、美丽、性感。女孩子们为身上“多余的”脂肪而愁眉不展,茶饭不思。她们提出了“全世界姐妹们联合起来,为了苗条而奋斗”的口号。减肥与健身工业于是勃然兴起。
当然,对于身体的兴趣并不是新鲜事物。但是在当代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语境中,身体的外形、身体的消费价值已然成为人们关心的中心。这才是十分值得关注的新文化现象。
二、身体翻身的社会文化语境
身体地位的突出是具有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原因的。特纳认为:“我的一个假设是,我们近来对于身体的兴趣与理解是西方工业社会深刻的、持久的转型的结果,特别是身体的意象在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中的突出与渗透,是身体(特别是它的再生产能力)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分离的结果。对于快感、欲望、差异、好玩的强调——这些都是当代消费主义的特征——是下述文化环境的组成部分,这个文化环境产生了大量的相关过程:后工业主义、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资产阶级工业资本主义的道德机构及其相关的关于性的宗教与伦理律令随着基督教伦理的消蚀以及大众消费主义的兴起而消失了。晚期工业社会中道德与法律的这种变化反过来又与经济结构的变化相联系,特别是与世界经济秩序中重工业生产的衰落有极大的关系。后工业环境中服务工业的不断增加的重要性与传统城市工业阶级的衰落相联系,与生活方式的变化、早龄退休、休闲的增加等联系在一起,劳动的躯体正在变成欲望的躯体。”③ 这表明,无论是大众还是学者,对于身体的兴趣的高涨是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转型的产物。
1.现代性与祛魅
从文化语境上看,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宗教与意识形态教条在界定、规训、控制身体方面的权威性的削弱,身体正变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不受宗教或政治的控制。这是现代化、世俗化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是一种所谓“盛期现代性”(high modernity)现象。现代性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身体的命运极为重要。一个反面的例子是,在当今世界宗教传统依然深厚的一些国家(比如阿拉伯国家),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依然受到严格的控制。④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对身体实施严格的控制,男男女女都穿没有性别特色的服装,上上下下齐动员清除所谓“奇装异服”。
随着现代性的进一步展开,社会文化的祛魅(去神圣化)步骤也进一步加剧,但是现代化过程摧毁了宗教信仰以后却没有建立另外的稳固信仰,陷入“上帝死了以后怎么都行”的信仰无政府主义,以及“众神纷争”的价值多元化状态。消费社会的文化没有能够提供指导我们生活的核心价值。这样,对于那些丧失了宗教信仰、丧失了对于宏大政治话语的兴趣的人,至少身体好象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在现代世界中重建可以依赖的自我感觉的基础。我们什么也没有了,但是至少我们还拥有我们的身体。在一个把至关重要的价值置于“年轻”、“性感”核心语汇的时代,身体的外在显现(外表)成为自我的象征。特纳说:“现代自我的出现是与消费主义的发展紧密联系的,现代的自我意识与无限制的对于快乐之物(食物、符号以及消费品)的个人消费观念紧密联系。”⑤ “我消费故我在”(I consume therefore I am)而不是“我思故我在”,成为今天的大众的自我确证、自我认同的核心。这种自我观念与西方笛卡尔以降的哲学与社会思想传统迥异,后者在心灵/肉体的二元对立基础上,认为人之为人、使人成为“社会性动物”的恰恰是心灵,而身体是不能体现人之为人的本质的,身体是自然性的、生物性的、乃至动物性的,而不是社会性、文化性的。
2.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变化
同时,古典哲学与社会学偏爱对身体的二元研究方法,它没有彻底忽视身体,但是身体在古典社会学中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古典社会学没有把身体当作具有自身存在价值的领域予以重视。就此而言,身体在古典社会学中是缺席的。比如古典社会学很少谈论这样的事实:我们有一个肉体化的身体,它使我们能够尝、闻、触、摸,等等。但是当代社会学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在解释人类行为以及社会的建构与功能时,不可避免地要解释身体化方面。古典社会学对于身体的关注是隐在的而不是显在的,而且常常只是有选择地关注身体化的一些方面。比如,它研究语言与意识,但却不承认这些能力是一种身体化的能力。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所说,我们的语言与意识能力是内在地身体化的,是身体的一部分,是受到身体限制的。同时,古典社会学也忽视了人的能动性的身体维度和身体基础。近来的社会学理论则认为:事实上,是身体使我们能够作出行动,卷入并改变日常生活之流。不解释身体就不可能有适当的能动性理论。在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行动的人就是行动的身体。
3.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比文化的变迁或许更加重要的是经济形态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消费社会中,身体的保养、维护逐渐成为核心的产业之一。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特别是现代化的大城市中,不但文化,而且经济,都是围绕身体这个中心旋转,开发身体、管理身体、美化身体、保养身体、展示身体、出卖身体,成为经济的命脉。无论是各种各样的公司、企业还是个体,都在为身体而忙碌着。
看看现代的城市中遍布的洗浴中心、健身中心、美容院以及休闲胜地等所谓“服务业”,就知道了身体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所谓“服务业”,其中一大部分是为身体服务的。2003年在上海召开的“国际科技美容专家高峰论坛”传来的消息称:美容整容已经成为继购房、买车、旅游之后的第四个消费热潮。国家工商联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08年底,中国大陆有美容院3154万家,年产值568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GDP的3.2%。同时推动相关的化妆品行业消费4600亿元人民币,并以25%的速度增长。保养和管理身体甚至可以说是现代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他们(特别是女性)的主要开支。现在正在西方与中国兴起的所谓“美的工业”(beauty industry)实际上就是身体工业。化妆品工业当然是最最重要的身体工业。美的工业的最杰出作品,就是现代城市中各种男女明星光彩照人的玉照,它们已经成为视觉文化的主题。化妆品工业实际上是“美丽产业/工业”的一个部分,这个“美丽工业”的核心就是打造美丽的身体,而依据的标准就是那些明星。⑥
三、从手段到目的
消费文化中的身体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成为人们追求的目的本身,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也就是非身体的目的的)手段。
在消费社会以前的人类历史上,身体的命运总的来说不怎么好。传统社会——包括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西方古希腊、斯巴达社会,以及现代初期的工业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禁欲主义传统,即压制身体以及身体欲望。在这样的禁欲传统中,身体及其欲望被看做是威胁性的、危险的、肮脏的,是不守规矩的非理性欲望与激情的载体,是堕落的根源。它必须受到理性、灵魂以及文化规范的控制。人们制定了严格乃至残酷的抑制身体、控制身体的措施,各种各样的禁忌常常都是针对身体的,比如非洲部落的割礼,阿拉伯国家的服饰,中国古代的裹脚。还可以包括中国“文革”时期对所谓“奇装异服”的严格禁止。
在传统社会中,在最好的情况下身体也只是被当做工具而不是目的,身体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有军事价值、生产价值、繁殖价值等等。传统文化总体而言倡导为一个比身体更高的理想而“献身”(“献身”就是把身体献出去),这是一种献身(身体)伦理。在古希腊的斯巴达,为了提高人们的战斗能力而重视身体锻炼;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初期,身体的生产价值(包括生殖价值)得到突出和重视。鲁迅先生说:“贾府中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原因何在?恐怕在于林妹妹的身体虽然合乎消费社会中的“苗条”标准,却没有生殖与生产能力,所以不合乎焦大的身体理想。“文革”时期的那些熊腰虎背的男子与英姿飒爽的女子,也是生产性身体理想的体现,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知识分子的“小白脸”形象。总而言之,拥有一个健壮身体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他目的,通常是精神性、宗教性的目的:如上帝、共产主义理想、革命(所谓“练好身体干革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但是到了消费社会,身体翻身作了主人,身体的享受成为生活、人生的目的本身。消费性、享受性的身体突出出来。消费社会极力塑造一个能够消费同时又能够被消费的身体,因此,身体的外观(与生产能力与生殖能力无关),亦即身体的审美价值,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身体从手段变成了目的,不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而是“革命是身体的本钱”。身体不是“革命”的手段而是“革命”的目的——“革命”在这里只是一个比喻,它的含义在今天已经转变为为了享受而进行的各种操劳。“革命”成为工具。
身体地位的变化也导致身体与服饰之关系的变化。禁欲传统(包括毛泽东式的现代“革命”时代)中的服饰是用以遮盖、隐藏身体的;而消费社会的服饰是设计来展示、凸显躯体的(遮的目的是为了露)。这使得人们对于身体的外观极度敏感,身体而不是精神成为现代人的快乐与痛苦的根源。(因为发胖而忧心忡忡,因为苗条而信心十足。)所谓“生活的艺术”差不多就是身体的艺术(美化身体、开发身体、管理身体,当然更要享受身体)。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迷恋青春、健康以及身体之美的时代,电视与电影这两个统治性的媒体反复地暗示:柔软优雅的身体、极具魅力的脸上带酒窝的笑是通向幸福的钥匙,也是幸福的本质。
四、身体的审美化:看与被看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身体观念的变化与整个社会转型都存在密切的关系。这里我想补充的是:在消费社会中,原先被赋予身体的各种职责、使命与功能现在大多消失了,特别是,身体与生产/生殖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分离(现在的劳力主要转移到了“脑力”上)。这使得身体被解实用化、去功利化。对于快感、欲望、差异、好玩、风格、外表这些非实用—功利因素的强调变得越来越突出。
有人把身体的这个变化命名为社会脱位(social deslocation),它意味着身体已经更加面向消费文化的游戏性—审美性使用,这种对于身体的游戏性—审美性使用,已经成为消费主义欲望的主要载体。
身体的审美化于是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文化思潮。这里,“审美化”指的是实用功能淡出之后对于身体的外观、身体的视觉效果、观赏价值以及消费价值的突出强调。由于身体的实用功能衰退而审美功能凸显,所以消费社会中的人们对于身体之美、身体的外观与年轻特别关注,对于身体“老化”采取了空前坚决的拒绝态度(同时伴随对于老化的极度恐惧),对于运动、美容等的美体实践之重要性的空前重视。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美丽工业”(beauty industry)、身体工业(body industry),各种各样的现代女性成为这个“美丽工业”或“身体工业”的劳动力、消费者以及材料来源(如各种各样的模特儿)。但必须指出,“身体工业”正确地说是身体外观工业或身体形象工业,它注重的不是身体的内在品质,甚至也不是身体的健康(许多减肥行为实际上是非常有害于身体健康的),而是身体外在显观。我们今天整天听到人们讲“呵护身体”、“关爱身体”,但是“身体的呵护”显然不止是(或者主要不是)为了健康,它还关系到使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外形显现(既显现给自己,也显现给别人)感到满意。而且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健康”已经变得越来越与外观呈现相关,尤其是在女性那里,健康几乎就等于苗条,而这种“苗条的身体”实际上已经不再合乎医学的标准。或者说,在消费文化中,苗条已经与健康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健康教育的要旨——过度肥胖有害健康——已经融合进了常识性的智能。但是,实际上人们追求苗条主要是出于“好看”的目的。那些节食的妇女其实很清楚:节食的主要动机是使身体更具魅力,即好看。而“好看”不仅是获得社会接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通向更加令人激动的生活方式的钥匙。一个减肥杂志展示了苗条的好处:苗条不仅可以获得更多崇拜的眼光,而且使人感到更加自信地走出去,更加有吸引力。苗条可以增加人的身体资本,这个身体的资本还可以转化为别的资本,提高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竞争力,对于妇女而言首先是提高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对于身体的这些关切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其普及性的读物——不计其数的健康手册、自我保养手册、化妆指南等等——更是成为图书大厦中的亮丽风景,占据了最显眼的位置。
由于注重身体的外形或身体的观赏价值,而不是实用价值/生产价值,视觉文化与身体文化就成为现代消费文化的两翼:在视觉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身体(特别是各种女性的玉照),而身体文化则是视觉化、图像化的。人体彩绘堪称为身体审美化、身体美学的杰作。彩绘没有任何的实用意义,与身体的生产价值、生殖价值以及健康价值都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社会的身体图象消费中,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现象。广告中的性别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经常是极度模式化的,其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随处可见。这种权力关系常常体现为看与被看的关系模式。
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分析视觉与其他感觉器官之区别时,曾经对于看这种知觉行为情有独钟。西美尔认为,看是相互的,而其他的感觉行为(比如听)则常常是单向的。我看别人,别人也看我。这种互动性使得观者不至于沦为被审视或监视的对象。但是在消费文化中,看的情形有所不同。我们看电影、电视、广告画面或模特表演,常常只是我们在看,而对象并不在真实地看我们。因此有人指出,被纪录并被展示的对象往往和看者处于一种不平等状态,看者更多地像一个“窥视者”而处于优势地位。
在那些关于女性化妆品之类的广告中,这种不平等常常特别明显地体现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女性主义的理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在电影之类的媒体中,女人总是作为被展示的对象出现,而男人则总是处于观看主体的地位,就如同猎物与猎人的关系一样,其中隐蔽着某种男性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如当代著名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所指出的:
在一个性别不平衡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已被分裂成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决定性的男性注视将其幻想投射到女性形象身上,她们因此而被展示出来。女性在其传统的暴露角色中,同时是被看的对象和被展示的对象,她们的形象带有强烈的视觉性和色情意味,以至于暗示了某种“被看性”。作为性对象来展示的女性乃是色情景观的基本主题。⑦
这就是说,在看的行为中,实际上包含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内容,这些意识形态因素由于文化的遮蔽和常识的掩盖,一方面变得难以察觉了,另一方面又使得种种视觉行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朱迪丝·威廉森(Judith Williamson)在她的著作《解码广告:广告中的意识形态及意义》中对于一种叫Dry Sack的酒的广告进行了分析,广告中的那个女子穿着没系纽扣的睡衣,眼睛挑逗性地看着前方。作者认为,这个广告中有一个虽然不显在却隐在的男性,“他不但‘无所不在’,而且‘使一切得以存在’,他是一种‘创造性的不在场’(creative absence)”⑧。其实,五花八门的女性化妆品广告、减肥广告、“丰乳肥臀”外科整容广告中,都有一双或明或暗的男性眼睛。
如果这类广告中的性别不平等可能还是比较隐蔽的,那幺“华伊美粉刺一搽净”的广告就十分赤裸裸了,这个广告告诉我们:女子的幸福就是被男人喜欢。广告画面中右边那个衣冠楚楚的男子一看就是一个“成功人士”。他拿着放大镜,仔细地审视身边(居于广告画面的左侧)那位女子的脸部,并念念有词:“乖乖,华伊美真厉害,不但将满脸的粉刺消除得一干二净,连粉刺斑也没有了,放大镜也失去了作用。”而这位女子则歪着头甜甜地、“自信”地笑着:“不久前,我脸上长满了痘痘,他经常嘲笑我,一气之下,十几天不见他,就悄悄地用起了华伊美粉刺一搽净,效果非常好。你看现在的我不是很靓吗?”这则广告告诉我们:对于女性而言,幸福就是得到男子的宠爱,而得到男子宠爱的前提则是自己的青春资本。因而靓丽可人就是幸福的同义词。这种幸福与社会取向的事业成功无关,而只与外表相关。美丽(面部的洁白无暇)是女性获得幸福的根本。又因为女性的幸福在于得到男性的宠爱,因而这种美丽实际上是给男人看并由男人来鉴定的。男性处于欣赏者与评判官的角色;女性则是取悦于人者,只有被欣赏与被评定的份儿。
这方面另外一则典型的广告是浪莎袜业广告:画面右上角是一位具有模特儿般身材的魅力四射的女子,只见她穿着背带裙,两手叉腰,头微微向左盈盈远视,作出一副非常标准的模特儿姿态,特别突出自己的修长玉腿以及玉腿上一双透明的袜子。这位女子是为了谁而展示自己的性感之驱?原来画面的左下角站着一位身着熨得十分妥帖整洁的高档服装的男子,他右手高举额头,头向右侧仰望右上角的那位女子,完全是一副看风景的样子。
在这种非常典型的看与被看的关系背后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绝大多数的女性用品(化妆品、首饰、减肥产品等)广告都有一个显在的或隐在的男性主体,一双男性的眼睛。广告上的女子就是对着这个主体或这双眼睛频抛媚眼,翘首弄姿。比如夏士莲洗发水广告。镜头之一:一个中国姑娘穿着非常暴露的上衣,展示给边上一个欧洲男性看,这个男性只是瞟了一眼,继续看他的报纸,女性声音:“他说这样没关系”(男性主体许可了);镜头之二:还是这个中国姑娘穿着长裙,裙子的中缝开得很高,露出性感的大腿,展示给同样一个男性看,这个男性还是不动声色,女性声音:“他说这也没关系”(又许可了);镜头之三:该女子原先的长发变成了又短又乱的短发,这次这位男子看到以后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绝对不行”;镜头之四:女子恢复了原先的长发,经过处理以后油光发亮(画面上出现“夏士莲”的广告语)。这同样是一则十分典型的体现性别歧视的广告:女性的外表装束与身体管理必须得到男性的认可,因为这种“管理”的目的就是取悦于男性,化妆品的力量就在于增强女性吸引男性的青春资本。有些广告甚至利用汉语的特点,大量使用露骨的性隐语,比如“一戴天娇”、“丰胸化吉”、“从小到大的关怀”、“做女人‘挺’好”、“不要让男人一手掌握”等等。
无独有偶,“太太口服液”广告几乎在重复着这种男女性别模式:一对情侣坐在一起吃荔枝,女孩秀气水灵,男孩帅气英俊。女孩一边剥荔枝一边撒娇地问男的:“现在的我漂亮还是从前的我漂亮?”男的回答:“以前的你就像……这个”,边说边拿起一枚果肉枯黄的荔枝:“干瘪枯黄。”女孩一脸不高兴。男孩话锋一转:“不过现在的你呢……”,他又拿起一枚饱满鲜亮的荔枝,望着洁白晶莹的果肉说:“就像这个,又大又滑,怎么看也看不够。”女孩于是转怒为喜,甜甜地笑着说:“这都是‘太太口服液’的功劳。”俩人相拥而笑,做无比幸福状。这位女性的悲喜、她的自信建立在男性的认同上,只有男性的认同才具有权威性与可信性。更有甚者,用荔枝来比拟女性,其深层含义是:女性就像是荔枝,是满足男性生理需要的。她的价值或许比荔枝高一些,但是本质上相同,都可以通过金钱得到。
五、可塑的身体与“身体规划”
现在人们的身体观念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认为身体是目的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变化就是:身体不是自然生成的、固定的,而是可以改造的、可塑的。过去我们常常认为:身体是固定的、先天的,是父母给的,但是消费文化中的趋势却认为,躯体的特征是可塑的而不是固定的,人们通过努力以及“躯体制作”(body work),可以达到特定的、自己想要的外形。正如克里斯·西林(Chris Shilling)在《身体与社会理论》的导言中指出的:“现在,我们有了一套程度空前的控制身体的工具……随着生物学知识、外科整容、生物工程、运动科学的发展,身体越来越成为可以选择、塑造的东西。这些发展促进了人们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也促进了身体被别人控制的能力。”⑨ 也就是说,身体成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规划与工程。这就是所谓“不确定的身体”。身体不再臣服于从前曾经规范肉体存在的那些限制。
这种情形在提供人们控制自己身体的潜力的同时,也刺激了一种对于“身体是什么”的高度的怀疑。换言之,在高科技促进我们更高程度地卷入身体塑造的同时,也动摇了“身体是什么”的知识,使之变得捉摸不定。(比如我们的身体观念总是与性别观念、父母观念、肤色观念等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这一切似乎都变得捉摸不定了。在挑战肤色与种族身份方面,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而在挑战身体的性别身份方面,韩国的变性人河莉秀则是一个著名的范例。)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我们关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允许科学重构身体”的道德判断,总是落后于科学的发展。
我们越是能够控制与改变我们的身体,我们就越不知道是什么构成了我们的身体,什么是身体的“本质”,什么对它来说是“自然的”。实际上现在身体已经变成了一种“规划”。情形似乎是:在这个缺乏稳定性的后现代消费社会,我们对于自己身体的意识也不可能稳定。我们目睹了正在出现把身体看做是处于不断生成过程中的倾向。身体成了一个应该进行加工、完成、完善的规划。这与传统社会中如何打扮自己的身体(主要集中于身体的外在装饰)是不同的,因为它更具有反思性与规划性,不仅范围更广,而且更触及身体的深层本质,与继承下来的、被社会广泛接受的身体模式与观念(这个模式常常是通过共同体的仪式塑造的,传统的身体装饰常常只是强化这种被文化规范认可的身体观念而不是颠覆它)更少联系。而在消费社会中,承认身体是一个“规划”意味着接受这样的观念:不仅身体的外观装饰物是完全自由选择的,而且其大小、高低、性别、肤色等都是可以依据身体拥有者的意志改变的。在这样的语境中,身体变成了可以锤炼的实体,这个实体可以通过警惕、看护身体以及艰苦的“造体”努力得以实现。这里我们应该感谢现代的科学(生物学、外科整容手术等),现代医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别、身高与骨架,现代外科技术使得人体的再造不再是神话。
同时,以改变性别与整容手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也以特别敏感的形式提出了“什么是身体”的问题。身体塑造(bodybuilding)活动是身体规划的一个极好例子,这是因为身体的塑造者所达到的肌肉质量与大小挑战了传统的关于什么样的女性身体、什么样的男性身体是“自然的”观念。在一个男人在工厂进行的体力劳动被机械取代的时代,在女性挑战家庭妇女角色的时代,传统的身体观念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改造自己的身体:除了减肥以外,还有更加激动人心的:改变性别、增加高度、丰乳肥臀、人工制作处女膜(这样一来,似乎“贞节”的定义也要重新界定了。一个处女的标志还是是否拥有处女膜吗?一个妓女经过重新安装处女膜,是否还是处女?报纸上常常有这样的报道:某某妓女声称:等自己赚够了钱以后就重新装一个处女膜嫁人,然后永远忠实于丈夫)。“造人”(正确地说,是造躯体)的时代正在到来。
最后,这种身体规划的观念还涉及一个道德问题:广告以及其他各种媒体要求个体对于自己的外形负责,而不是把它推诿给“老天爷”或“爹娘”。如果一个人的身体不合乎“标准”,那不是爹娘的责任,而是因为自己的懒惰。这不仅对于青年人是重要的,而且对于中老年人也如此。消费文化语境中的健康与医学话语主张:面对自然衰老,人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应该通过有效的躯体维护,在化妆品工业、美的工业、健身工业、休闲工业等的帮助下,来与皱纹、肌肉松弛、脱发等伴随老年化出现的现象进行斗争。人定胜天。这样的广告有助于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个体被迫在情绪上变得脆弱,持续地监视自己身体的不完美性,这种不完美性不再被认为是自然的。
六、身体与身份认同
消费社会学认为,消费文化把身体与自我认同联系起来,个体常常通过塑造身体来建构良好的自我感觉,更加好看、更加年轻、更加有吸引力已经成为人的一个基本需要,因为好看的人就会感觉良好。
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在《自恋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中所展示的一种新的人格类型,即自恋的人格,已经在20世纪出现,它的特点被描述为“过分的自我意识”、“对于健康的持久的不安”、“恐惧老化”、“对于老化征兆的极度敏感”、“沉浸于永远年轻与充满活力的幻想”。自恋的文化形成于20年代,成熟于战后,现在则广泛传播。自恋的人格与培养这种人格的自恋文化指向一种新的躯体与自我的关系,在与自恋的文化最接近的消费文化中,出现了新的“自我”概念,即表演性自我(the performing self)——极度强调外表、展示、印象设计的那种自我。⑩
西方的社会学家认为,最能够体现这种新的人格的是一些所谓的“自助手册”(self- help manual)(相当于中国的各种“生活指南”)。可以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自助手册上看到表演性自我的逐渐呈现。19世纪的自助手册强调的是新教伦理:工业、节制、节俭、公民资格、民主、责任、工作、荣誉、道德;而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自助手册强调对声音的控制、公开场合的亮相与演说、锻炼、悦耳的声音、外表的修饰等。它对于道德没有兴趣。这种新的人格文化所要求的社会角色就是表演者(performers)的角色,它强调真正的快乐可以通过取悦于他人(make oneself pleasant to others)而获得。个人应该发展他的演员技巧——20年代的自助手册以及其他的大众媒体都这么强调;而好莱坞的明星则提供了榜样,即所谓的“个性化明星”(personality star)。有些明星还亲自写自助类的书。也有人认为,20世纪后半期百货商店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举足轻重。百货商店通过越来越精细的广告技术出售新近批量生产的便宜服装。原先标志着特定社会地位的服装逐渐被回避,而个体的穿着越来越被看做是其个性的表现。他既要译解别人的外表,又要努力设计自己(留给别人的)的印象。这就鼓励了更加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在公共场合的自我审查。
在消费文化中,个体被要求成为角色扮演者,有意识地监督自己的身体呈现。一个人的自我感觉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身体感觉而不是其他(长相美比心灵美更加重要)。身体、外表、姿态与行为举止成为自我的指示器。对于躯体的忽视会在日常的人际互动中受到惩罚。这就鼓励个体仔细关注与寻找自己衰老的迹象。如同拉什所说:“我们这些人就如演员与观众,生活在镜子的包围中。我们在这些镜子中寻找我们迷惑别人或给别人深刻印象的能力的保证,我们焦急地寻找可能会损毁我们有意设计的外表的瑕疵。广告工业有意识地鼓励这种对于外表的优先关注。”(11)
这样,向自恋的与表演性的自我发展的趋势,在职业的管理中产阶级中表现得最明显。这些阶级既有时间也有钱从事生活方式的活动并培植自己的角色形象。消费文化的意象与广告不能仅仅被贬低为“娱乐”,即人们并不认真对待的东西;消费文化也反对这样的观点:个体被操纵去追逐错误的欲望与需要。消费文化在两个广泛的层次上运作:(1)它提供各种用以刺激欲望与需要的意象;(2)它建立在改变社会空间的物质安排以及社会互动的本质的基础上,并有助于这种改变。日常生活的物质组织的变化包含了对于社会空间的重构,比如新的购物中心、新的现代化旅店等,而这种重构则鼓励、促进了躯体的演示。
七、身体与图像文化和广告
我们已经说过,消费文化注重的是身体的观赏价值、审美价值而不是生产价值、实用价值。所以,身体的图像在其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打造合意的身体外形,消费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理想的身体意象(特别是女性的身体意象)以供大众模仿。以身体为核心的视觉图像工业开始兴起。
一系列通过电子摄影技术、电影与电视技术生产的图像使得我们置身于一个图像组成的镜城中,也使得我们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身体——特别是其外形——的存在(不管是美的身体还是丑的身体)。图像使得个体对于身体外表的呈现、对于自己的“外观”具有更加强烈的意识。外国的学者研究指出,电影、电视等影像工业通过把人从词语引向运动与姿态而改变了20世纪人的情绪生活。一种受词语支配的文化倾向于内向性、抽象性与不可触摸性、想象性(比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罗敷》对于美女罗敷的描写),把人的身体还原为一些看不见的文字,而对于视觉形象的强调则把注意力引向躯体的外形、穿着以及姿态。
这样,处于由身体图像组成的镜城中的当代人常常陷入对于自己身体的严格自我监督中。百货商店就是这样的一个镜子之城。商店中的商品展示越来越精致讲究,许多人到这里进行窥视性的消费(voyeuristic consumption)。到这里来的人不仅仅是来买东西,同时也来进行审美:他们在看别人的时候知道自己也被人看。所以在这里,特定的穿着标准与外观标准是非常重要的。随着个体穿越于被展示的商品场域,他自己也处于被展示的位置。我们对于自己外表的日常意识大大加强,通过与自己过去照片的比较,与广告与大众传媒中宣扬的理想美女俊男的“标准”身体的比较,使得我们对于外表的敏感程度、挑剔程度以及不满程度变得更加强烈。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说说广告。在消费社会中,广告信息是使我们的整个文化迷恋身体的主要教唆者。在这里,各种模特以及影视明星常常充当了“形象大使”、“形象楷模”的角色。电影、电视、各种各样的广告图片是消费文化中标准的身体图像的生产者与供应者,许多青年男女就是这样准备来监管、打造自己的身体。这些明星为了保证具有完全符合完美标准的形体,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化妆技术、整容技术以及假发等以消除不完美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常常遵循严格的饮食、训练以及化妆。据说美国的化妆工业就是从这种做法发展出来的。
消费社会无处不在的身体图像与广告不断吸引人进行比较,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看上去是什么样的?通过努力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不是要开拓身体产业的市场吗?怎么开拓?必须制造对身体极为挑剔的消费者,而广告就是有效地制造这样的消费者的工具。大量广告使得个体对于自己身体采取一种“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态度。现代广告与世界大战前的广告的不同在于:“它越来越集中于使接受者情绪不稳定,它通过这样的‘事实’——体面的人都不是像他那样生活的——来对他进行当头棒喝。当代广告让一个家庭主妇焦虑地瞧瞧镜子中的自己是否像广告中那位35岁的太太一样,因为不用Leisure Hour电子洗衣机、洗碗机而憔悴不堪。”(12) 广告总是要制造一个使你感到自卑的“理想”身体图像,使你感到自卑与焦虑,然后又不失时机地给你希望:只要用了我的产品,你也能够有一种理想的身材。据说在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年,化妆、时装以及广告工业的主要冲击对象是女性,而对于男性的冲击则出现于60、70年代。但是,20年代的男性明星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在塑造男性躯体偶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还改变了皮肤以白为美的观念,导致棕色皮肤以及阳光浴的流行。
因此,广告有助于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个体被迫在情绪上变得脆弱,持续地监视自己身体的不完美性,这种不完美性不再被认为是自然的。是啊,如果是自然的、不可改变的,谁还会用化妆品?
总之,消费文化中的人们一方面以身体的享乐为最高的生活目的,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自己的身体,这样,他们对于身体的态度是矛盾或者说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的时代是空前放纵身体的时代,另一方面,它也是对于身体的控制空前严厉乃至残酷的时代。在消费文化中,广告、流行出版物、电视、电影文化等,提供了大量理想化的身体形象。此外,大众传媒持续不断地强调化妆品对于身体保养的好处。对于严加约束的身体的奖赏,不再是灵魂的拯救,甚至也不是改进了的健康状况,而是强化了的外表(enhanced appearance)与更加适合于销售的身体。如果说在宗教的语境框架中节食被理解为对于肉体诱惑的抵制,那么,在今天,节食与身体保养(body maintenance)已经越来越被视做释放肉体诱惑的载体。控制身体与享受身体已经不再被看做是不相融的。事实上,通过身体保养的严格程序来对身体实施控制,才能够造就被大家接收的外表。消费文化并不意味着彻底地用快乐主义来取代禁欲主义,他倡导的实际上是“精心计划的快乐主义”(calculating hedonism)。
注释:
① Chris Shilling,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London;Thousand Oaks,Calif.:Sage Publications,2003,Introduction.
②③ Bryan S. Turner,The Body and Society,second edition,London :Sage publication,1996.
④ 《北京晚报》2003年11月9日在题目为《只因穿比基尼选美,“阿富汗小姐”面临指控》的文章中,报道了就读于美国的阿富汗女大学生维达·萨玛德因为参加2003年度“地球小姐”而面临在阿富汗被起诉的危险,原因是检察院认为这位参加选美的阿富汗姑娘违反了阿富汗文化传统。
⑤ Bryan S.Turner,The Body and Society,second edition,London :Sage publication,1996.
⑥ 参见《北京“美丽产业”加速度》,载《新京报》2003年11月25日。
⑦ Laura Mulvey:“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in Charles Harrison and Paul Wood(ed) :Art in Theory:1990-1999,Oxford,Bleckwell ,1992,p.967.
⑧ Judith Williamson,Decoding Advertisement :Ideology and Meaning in Advertising,London,Marion Boyars,1978,p.80.
⑨ Chris Shilling,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London; Thousand Oaks,Calif.:Sage Publications,2003,Introduction.
⑩(11) Christopher Lasch,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New York :Warner Books,1979.
(12) Stuart Ewen,Captain of Consciousness,New York:McGraw-Hill,1976,p.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