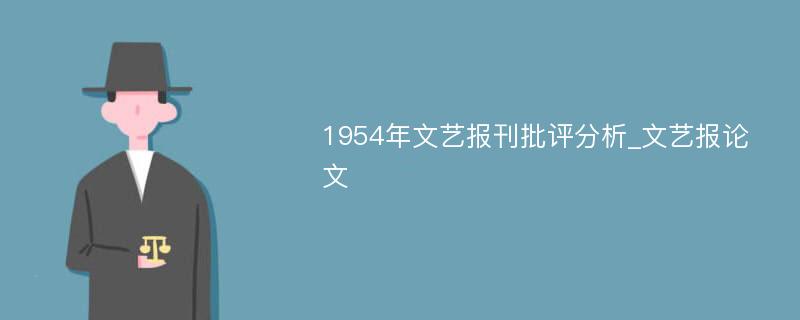
一场批判 三种声音——试析1954年对《文艺报》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报论文,三种论文,批评论文,声音论文,试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动了对红学家俞平伯的批判。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形成了党外批判俞平伯、党内批评《文艺报》的紧张形势。对于批判俞平伯,党内外众口一辞,而对《文艺报》的批判,则有不同的声音。对《文艺报》的批评,时间不长,声势很大,影响深远。重新认识当年批评《文艺报》时的不同思想倾向,对于理解新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曲折历程,是有意义的。
一、批评《文艺报》的三种声音
对《文艺报》的批评,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然而,这一运动的特定背景和文艺界的复杂情况,却使其间充斥着一些很不相同的声音。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批示、批语、信件,《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文章,《文艺报》刊载了“青年宫会议”(注:1954年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扩大的联席会议,先后开了8次大会。会议在北京青年剧院楼上的青年宫召开,故称“青年宫会议”。)的主要发言摘要,《文艺报》召开的外省市在京作家座谈会发言摘要,该刊编发的大量读者来信摘要,等等,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场批判运动中,至少有三种声音。
第一种声音,当然是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对《文艺报》的批评,有着非常集中、非常明确的指向,这就是批评《文艺报》容忍和保护资产阶级思想,以“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打击“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他在10月16日致刘少奇等28人的党内信件中,批评《文艺报》“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压制‘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向资产阶级作家“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投降(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575页。)。这封信当时没有发表。公开地、完整地转达毛泽东上述观点的,是由江青授意、袁水拍执笔、经毛泽东阅改并指令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这篇文章批评《文艺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屈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注:《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8日。)。毛泽东阅改这篇文章时,在原文批评《文艺报》粗暴否定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的一段文字后面加写了:“《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589页。)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文艺报》的两大错误,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既然容忍和保护资产阶级思想,就必然打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也就是说,《文艺报》犯的是“右”的错误。
第二种声音,是胡风的声音。他的矛头所向是党对整个文艺的领导工作。在“青年宫会议”上,胡风作了两次长篇发言。他以《文艺报》第一、二卷发表的评论文章为依据,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文艺报》犯错误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他认为,《文艺报》创刊之初即向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投降;《文艺报》很早就“对于进步的作家、对于小人物”采取了打击的态度,1950年对阿垅的批评可为例证;在《文艺报》批评工作中,“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占着支配的地位”。胡风不但批评了《文艺报》,而且批评了《人民日报》;不但批评了冯雪峰、蔡仪、黄药眠、陈涌等人,也点名批评了周扬、袁水拍。他认为《文艺报》和冯雪峰的“失败”,是“我们战线的失败”。
第三种声音,是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声音。许多作家、艺人、《文艺报》读者,猛烈地抨击了《文艺报》宣传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艺理论,坚持“粗暴的骂倒一切、横扫一切”的文艺批评,因而严重阻碍文艺事业发展的错误。作家刘大海说:“很多读者都认为《文艺报》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好像它永远是正确的,所以有人就把《文艺报》叫做‘一生正确’。要是周围同志中谁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别人就把他叫做《文艺报》。”(注:《文艺报》1954年第22号第9页。)类似的批评言论非常之多,言辞激烈、尖锐。
显然,这三种声音是十分不同的。毛泽东批评的是《文艺报》向“资产阶级唯心论”投降并因而打击新生力量的“右”的错误。文艺工作者批评的是《文艺报》以错误的文艺理论和审判官式的粗暴批评压制创作自由、批评自由的“左”的错误。胡风批评的则是党的整个文艺领导工作。以往对批评《文艺报》事件的研究,显然忽视了文艺工作者一方面的声音,对胡风的观点也缺乏完全正确的理解。
二、为什么会有三种声音
在批评《文艺报》的过程中,之所以会有三种声音,而不是一种声音,从主观方面来说,是因为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观察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想通过批评《文艺报》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从客观上来说,《文艺报》的表现的确为这三种声音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依据,也就是说,它们都不是空穴来风。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领袖,极端重视意识形态的改造。建国后,他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文艺整风运动,支持对陶行知等教育界著名人物的批判,都是为了改造旧的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绝对领导地位。然而,这些运动都没有有力地触及旧的意识形态的深层和核心——由胡适思想长期统治着的学术领域(不仅仅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1952年夏季以后,鉴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对文学艺术和教育事业造成的严重影响,党不得不有限度地调整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使意识形态领域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毛泽东从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战略高度观察问题,不能容忍这种状况。他需要找到一个契机和缺口,打破“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一统天下,于是找到了《文艺报》和红学研究。尽管冯雪峰对批判《文艺报》始料不及,事后也想不通,说是“有苦说不出,低头挨闷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注:史索、万家骥:《冯雪峰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17页。)。但是,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说冯雪峰主编时期的《文艺报》放弃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大概是不冤枉的。
1952年2月,冯雪峰接任《文艺报》主编。同年5月25日,《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发表社论,引人注目地提出要开展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资产阶级倾向与反对“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重点是强调后一个方面。这是有限度调整文艺政策的信号。冯雪峰立即行动起来,迅速而显著地调整《文艺报》的编辑方针。先是在稍前即已发起的“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中公开批判公式化、概念化。文艺整风结束后,又开辟了“对概念化、公式化倾向的批评”专栏,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抨击。1953年夏天,他在一些讲话和为第二次全国文代会起草的工作报告草稿(未被采用)中,尖锐地批评了党的文艺工作,认为建国后“违反毛主席思想的主观主义思想支配了我们创作的领导”(注:《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496页。),亦即“左”的错误占据了党的文艺工作的主导地位。1953年9、10月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把反对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粗暴批评作为主要的倾向来讨论。这样,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作用,在1952年秋季至1954年10月的两年间,《文艺报》的面貌有了相当的改变,粗暴批评大为减少,对“资产阶级思想”所谓批判则几乎绝了迹。这在1954年群众对《文艺报》的批评中可以得到反映。当时许多人认为,近两年来,特别是第二次文代会以后,《文艺报》的评论文章越来越少,“战斗性”不强,变得“消极”了。毛泽东对《文艺报》的批评,是借题发挥,但不是无中生有。
文艺工作者批评《文艺报》的目的是反对教条主义束缚,争取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争取作家与批评家的平等地位。他们的不满,主要是针对《文艺报》由丁玲、陈企霞、萧殷主编时期和冯雪峰接手初期。《文艺报》1954年22号和23、24号合刊发表的批评《文艺报》的材料约10万字,其中批评者列举的作为《文艺报》粗暴批评例证的文章有30多篇,绝大多数是1952年秋季以前发表的。《文艺报》第22期刊发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学员陈亦洁的文章《论批评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举了4篇文章,其中3篇刊于1951年以前,1篇刊于1952年3月。的确,早期《文艺报》的形象是“凶凶狠狠”、令人生畏的。建国不久,文艺界出现了一股教条主义的思想潮流,报刊上的粗暴批评泛滥成灾。冯雪峰接手时,正值“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艺整风运动的高潮。由于政治空气和惯性作用,更由于文艺界领导人和《文艺报》并未深刻认识过去的偏差和错误,因此,1952年秋季特别是第二次文代会后,粗暴批评少了,但并未绝迹,1954年初还发生过若干不恰当地批评李准小说一类的问题。这样,群众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对“左”的倾向和不满,借毛泽东批评《文艺报》之机倾泻而出。
胡风在“青年宫会议上”上发起“进攻”,是许多人没有料到的。胡风是一位有独立思想的文艺理论家。他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有显著的差别,加上文艺界长期的宗派纷争,建国前屡遭批评,建国后倍受冷落,动辄得咎。1952年下半年,中宣部召开4次座谈会,批评他的文艺思想。《文艺报》1953年第2号、第3号,发表了中宣部指定何其芳、林默涵撰写的批胡文章。胡风不接受批评,1954年7月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直陈对建国后文艺工作的看法。他的意见当然不被接受。《文艺报》问题发生后,胡风显然认为,《文艺报》的问题和文艺工作者对“左”的倾向的强烈不满,验证了他对建国以来文艺状况的判断,为他的文艺思想提供了实践的佐证,因此才非常“激动”地发表了无所顾忌的“攻击性”言论,企图否定建国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用自己的文艺理论影响整个文艺工作。
一场批判、三种声音这种情形的出现,除了人们的地位、意图和观察《文艺报》问题的视角不同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将毛泽东指出的《文艺报》相互联系的两大“错误”分割开来,避开《文艺报》“容忍和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错误,而借“压制新生力量”问题大加发挥。二是袁水拍的文章把“否定”李准小说作为《文艺报》打击“新生力量”的例证,对批评《文艺报》的舆论方向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误导作用,因为文艺工作者认为那是粗暴批评的典型。
三、为什么转向批判胡风
对《文艺报》的批评,自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文章开始,到12月8日周扬在“青年宫会议”上发表毛泽东审阅的《我们必须战斗》的总结报告结束,只持续了40天,次年1月便草草收场。骤然而起的,是对胡风的批判。形势的发展,似乎偏离了毛泽东原定的主题与方向,因为当初并无立即批判胡风的打算,而且无论如何,胡风的思想是很难归入胡适一派的。
按照传统的说法,斗争指向的急剧改变,直接起因是胡风的“进攻”。这有道理,但不全面。应该说,批评《文艺报》期间文艺工作者对“左”的文艺理论、文艺政策的激烈批评,也是导致运动转向的客观原因之一,因为批评《文艺报》期间,文艺工作者对“左”的倾向的批评,具有十分严重的性质。
第一,《文艺报》是“以指导文艺思想为主要任务”的刊物,是“文艺思想战线的司令部”,名义上隶属全国文联,由作协主席团代为指导,实际上领导它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另一方面,按照党的文艺理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通过文艺批评实现的。严重地批评《文艺报》和批评家,无异于批评党的领导。
第二,人们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公式化、概念化和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人们已经认识到,粗暴批评是现象,其要害在于宣传“无冲突论”等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以前,文艺界的领导人总把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责任归罪于作家。如周扬说,作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不是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是是主观地按照预先设定的公式来描写生活”,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最普遍最主要的原因”(注:周扬:《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53年第19号第9页。)。现在作家们说:“公式化、概念化的主要原因在批评!”周扬说,粗暴批评之所以发生,一是批评的态度不对,二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一些教条、公式出发。现在作家们说:“不是态度和方法不对,他们根本就在自觉地宣传和提倡错误的文艺理论!”这就实际上提出了系统清理教条主义文艺理论的要求。
第三,人们公开要求文艺界领导对《文艺报》的错误承担责任。刘白羽说,从《文艺报》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也不能不谈到领导的责任和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作为全国文联的机关刊物,全国文联有没有领导呢?作为研究、批评文学问题的刊物,作家协会主席团有没有领导呢?……我觉得这不是简单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整个文艺界汲取教训,改变作风的问题。”(注:《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合刊第16页。)他们明明知道文联、作协领导不了《文艺报》,但除了胡风,没人敢公开批评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所以,批评文联、作协的真正用意是批评周扬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就在文艺工作者把本来对《文艺报》“右”的错误的批评变成对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讨伐的时候,胡风加入了“进攻”的行列。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直接导致了运动的转向。
胡风的武器和策略是批评庸俗社会学。他的批评显得非常有力,因为他把群众对粗暴批评和公式化、概念化的一般批评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他认为,统治着文艺批评的,是庸俗社会学。庸俗社会学的基本特征,“是不从实际出发,不是凭着原则的引导去理解实际,而是用原则代替了实际,从固定的观念出发,甚至是从零乱的观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或者政策的词句去审判作品”。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或者叫做公式化概念化,或者叫做‘无冲突论’(虚伪的所谓‘乐观主义’),或者叫做教条主义,或者叫做反历史主义,或者是仅仅从表面现象看‘社会意义’的客观主义,等等”。庸俗社会学是粗暴批评的根源。“五年来,我们文艺上的有生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压制,我们的文学事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我们的青年作者,一切有进步倾向、有革命要求、忠实地拥护革命政权的爱国的作家们,包括绝对大多数的年纪大的作家在内,都是愿意写出好的作品来,都是愿意从实际出发,一步一步向前走,一面劳动一面改造自己的。但我们文艺战线反而消沉了。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这种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和批评,以及以它为武器的一套做法从内部把文艺实践拖得不死不活,使我们感到苦恼,更使青年作者们感到苦恼的。”(注:《文艺报》1953年第19号第10页。)
胡风的发言有片面、过激甚至错误之处,但是,不能不承认,他对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的批评,较之其他批评者,是更为深刻、有力的。尽管这时的胡风已被视为文艺界的“异端”,许多青年并不很了解他,他的言论对饱受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批评之苦的青年人,还是极有影响的。党看到了这一点。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中说:“他的许多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根本的分歧的,不管是在对《红楼梦》的评价上,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上或是在对《文艺报》的批评上。胡风先生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有些人也是这样地看他。”(注:《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合刊第16页。)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为了避免文艺工作者为胡风所“误导”、为他所“利用”,避免这两种力量合二为一形成对党的文艺方针的威胁,彻底割除胡风这个文艺界的“毒瘤”,才迅速结束了对《文艺报》和俞平伯的批判,立即转向对胡风的讨伐。
1954年,广大文艺工作者和胡风对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的批评,本来可以成为纠正错误偏向,使新中国的文艺事业顺利发展的契机。由于不能正视现实,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的批评,不能容忍文艺理论的多样化,以及“宁左毋右”心理的影响,失去这个机会,使得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在批判胡风运动中更加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