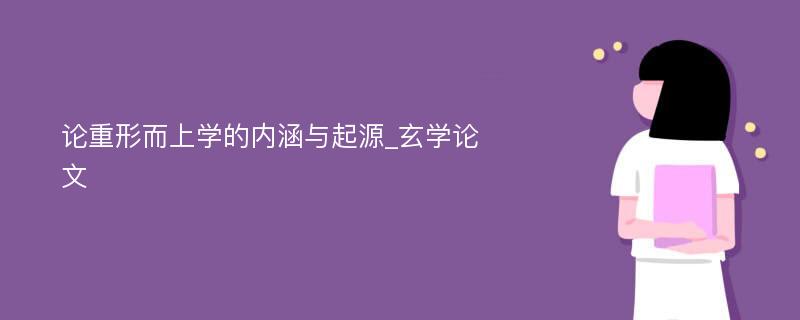
试论重玄学的内涵与源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玄学论文,源流论文,试论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2)03-0069-05
“重玄”一词来自于对《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一语的简括,但作为一种哲学术语与学派,则有着丰富的内涵,古人谓之“重玄之道”。两晋隋唐乃至宋元时期,道徒、释子、儒士常常在其言谈及著作中讲论这种“重玄之道”,显示出它是中国中古时期重要的哲学思潮。弄清其内涵与来龙去脉,对于研究中古时期的道家、道教、佛教的思想理论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道家、道教与老学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先后发表有关论文与专著20多种,其中仅专论初唐道教学者成玄英重玄思想的论文即达10篇以上。但仔细分析其中内容,感觉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与辩正。
一
20世纪40年代,蒙文通先生校理唐代成玄英、李荣等人的《道德经》注疏,开重玄学研究的先河。他引罗什注《老子》“损之又损”文曰:“损之者无粗而不遣,遣之至乎忘恶;然后无细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恶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损其非,又损其是,故曰损之又损。是非俱忘,情欲既断,德与道合,至于无为。已虽无为,任万物之自为,故无不为也。”指出:“重玄之妙,虽肇乎孙登,而三翻之式,实始乎罗什,言老之别开一面,究源乎此也。”[1](p343)意谓老学重玄思想的阐扬虽然肇端于孙登,但“三翻”模式即三重否定的典型表述则伊始于罗什。东晋玄学之士孙登的生平,史书语焉不详,但据其父孙统、叔孙绰及堂叔孙盛等人传记推断,可知其生活于4世纪下半叶,至迟不会超过4世纪末年,佛教三论宗中国初祖鸠摩罗什则始于公元401年来华译经。汤一介、卢国龙等当代学者据成玄英《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晋世孙登云托重玄以寄宗”一语推定老学重玄思想的源头当追溯到东晋孙登及其堂叔孙盛和佛教徒僧肇、支道林等。其中,卢国龙进一步将“道教重玄学”之始推衍到南朝宋末年顾欢的《老子义疏》(注:参见汤一介《论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载《非实非虚集》,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卢国龙《中国重玄学》第1章,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赵宗诚《试论成玄英的重玄之道》,载《中国哲学》第11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孙盛《老聃非大圣论》云:“伯阳(老子)欲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裴頠)欲执今之有,以绝古之风。吾故以为彼二子者,不达圆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在其《老子疑问反讯》中有言:“《道经》云‘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故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何以复须有欲得其终乎?宜有欲俱出妙门,同谓之玄,若然以往,复何独贵于无欲乎?”[2](卷五)僧肇在其《涅槃无名论》中说:“……况乎虚无之数,重玄之域,其道无涯,欲之顿尽耶?书不云乎,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为道者,为于无为者也。为于无为而曰日损,此岂顿得之谓?要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损耳。”[3](p1858)李大华则将“重玄”归属于道教,认定道教“重玄”哲学的源头,就“时间次序来说,孙登为先”(注:参见李大华《道教重玄哲学论》,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9期。)。何建明在对上述各家之说作了比较与评价之后,又将“重玄”界定为“道家重玄学”,并指出:道家重玄学宗源于庄子(注:参见何建明《道家思想的历史转折》第1章第1节,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呢?笔者发现是由下述两方面的模糊认识引起的:其一,多数有关论著都将“重玄”等同于佛教“空论”的“四句”、“百非”、“双非”、“中道”等概念,或将“重玄”思想的“双遣”仅仅理解为“遣有遣无”、“非有非无”,从而把重玄思想的源头追溯到佛教三论宗那里;其二,不注重区分“重玄学”的属性与外延,对于“重玄”究竟指的是一种方法、一种境界,还是一个学术流派?莫衷一是,故而在“老学重玄”、“道家重玄”、“道教重玄”之间互相否定。因此,要探索重玄思潮的源流问题,首先必须弄清重玄学的内涵与属性。
众所周知,唐初道教学者成玄英是公认的重玄学集大成者,其《道德经义疏》(注:本文所用版本为《蒙文通文集》第6卷,巴蜀书社2001年8月版。)第1章中对老子“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段话的疏解,则是关于重玄思想的典型表述:
玄者,深远之义,亦是不滞之名。有无二心,徼妙两观,源乎一道,同出异名。异名一道,谓之深远。深远之玄,理归无滞。既不滞有,亦不滞无,二俱不滞,故谓之玄。
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
在第37章、79章疏中,成玄英对上述思想又有所补充:
前以无遣有,此则以有遣无,有无双离,一中道也。……前以无名遣有,次以不欲遣无,有无既遣,不欲还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泯。此则遣之又遣,玄之又玄。
行人虽舍有无,得非有非无,和二边为中一,而犹是前玄,未体于重玄理也。……虽遣二边,未忘中一,故何可尽善也。
此外,成玄英还对“重玄”境界作过如下描述:
虽复三绝,未穷其妙,而三绝之外,道之根本,所谓重玄之域,众妙之门。意亦难得而差言之也。[4](《大宗师》疏)
仔细分析上述引文,不难看出:其一,成玄英的理解思路是将“重玄”解释为“双遣”。这里所说的“双遣”是指遣“有无双执”或称“有无二偏”、遣“非有非无”或称“遣其遣”。这种“双遣”实际上表达的是三重否定,亦即三重遣除:第一否定(遣)有,第二否定(遣)无,达到非有非无的“一玄”境界,也就是“一中道”;第三否定(遣)非有非无,达到非非有非无的“重玄”境界,即遣其遣,以至于无所遣,这就是“重玄之道”。成玄英在《庄子·大宗师疏》中所说的“三绝”就是这种三重否定的另一表述方式:“一者绝有,二者绝无,三者(绝)非有非无,故谓之三绝也。夫玄冥之境,虽妙未极,故至乎三绝,方造重玄也。”这就是两晋隋唐重玄学思想的基本内涵,显然其“双遣”、“三绝”是达到“重玄”境界的一种方法论。其二,所谓“重玄”是为解释道体而言的,即“至道”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更不是“非有非无”,而是“非非有非无”,也就是“自然”状态,亦即“重玄之域”、“重玄之理”、“重玄之道”。可见,“重玄”又具有本体论意义,它所谋求解释的是一种世界本体意义的境界。其三,佛教三论宗所谓“非有非无”的中道观,对于重玄学来说,只是“一玄”、“一中道”而已,并未体现出“重玄理”,故不是尽善尽美之道。所以,“重玄”思想有两个特征:一是以“双遣”导出“重玄”,以“重玄”界定“双遣”,“双遣”是其内容,“重玄”是其名称;二是三重否定法,从而使“重玄之道”与佛学“有无双遣”的“一中道”区别开来。比现代哲学所谓“否定之否定”的双重否定也要更深一层。其实质是无所谓是与非,无所谓滞与不滞,一切听任自然而无所为!因而,重玄之道的最终归属是“自然”境界。
而佛教所谓“四句”即“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所谓“百非”即一切皆非,所谓“双非”即“非有、非无”,罗什,僧肇的所谓“双遣”即遣有、遣无,中道观的基础则是所谓“八不”: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在重玄思想看来,佛教的这些观点都还停留在道家所谓“一玄”、“一中道”的范畴,这些认识仍然执滞于“空”、“非”与“不滞”。只是在隋唐之际三论宗名僧吉藏吸收道家老庄学重玄思想,将“二谛”进一步解释为四重境界后,才使上述代表佛教三论宗“空论”基本观点的思想臻于道家、道教所谓“重玄”境界。那么,如何看待本文开头已列举的罗什、僧肇注《老子》“损之又损”章文字呢?笔者以为这恰恰是罗什、僧肇接受玄学影响的表现,道理很简单:第一,其注文没有使用任何佛学术语;第二,一个佛教徒解注中国道家著作的文字,依据一般逻辑推断只能表明其接受了道家思想,怎么能够反过来作为道家学说受佛教思想影响的证据呢?更何况罗什的文章并没有“重玄”、“三翻”的表述,充其量只是“非有非无”的“一中道”思想的中国化文字,而僧肇的文章明引“重玄”概念,则既表明其接受了中国玄学家的“重玄”思想,也昭示出“重玄”思想在此之前已经产生。与僧肇同时的佛学名士支道林有诗云:“中路高韵溢,窈冥钦重玄,重玄在何许?采真游理间”,“涉老怡双玄,披庄玩太初”,“总角敦大道,弱冠弄双玄。”[2](卷三十)“总角”、“弱冠”云云,说明早在支道林青少年时代便已产生“重玄”思想,且支道林对老子之道和重玄学说十分心悦诚服;而“涉老怡双玄”则显示支道林的重玄思想来自于《老子》或注老之作,也意味着“重玄”思想在支道林之前便已产生。所以,将重玄思想简单地理解为佛教三论宗的“空论”与中道观,恐怕是一种历史的误解,而将“重玄”简单地理解为“遣有遣无”的“双遣”更不确切。
那么,这种“自然”境界与“道”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成玄英指出:
次须法自然之妙理,所谓重玄之域也。道是迹,自然是本。以本收之迹,故义言法也。[5](第25章)
自然者,重玄之极道也。[5](第23章)
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成玄英在《庄子·则阳》疏中曾明确作过区分:
虚道妙理,本自无名,据其功用,强名为道,名于理未足也。……因其功用,已有道名,不得将此有名比于无名之理。……今以有名之道比无名之理者,非直粗妙不同,亦深浅斯异,故不及远也。
又在《庄子·德充符》疏中说:
虚通之道,为之相貌,自然之理,遗其形质。且形之将貌,盖亦不殊,道与自然,互其文耳。
正因为“道”尚不足以名“虚通妙理”,才进一步有了“重玄”的体道方法,才有了“重玄之道”,这个“重玄之道”方能体现“自然之妙理”。可见,“虚通之道”与“自然之理”是有区别的,虚通之道是有名之“迹”,自然之理是无名之“本”。“本能生迹,迹能生物也。大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从道生,物即是末。”[5](第52章)“自然生道”的思想其实并非成玄英的发明,而是他继承南北朝道教义理的结果,在他之前,《西升经·虚无章》曾总结出一套:“虚无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成玄英在其《道德经义疏》中引用《西升经》最为频繁,这说明他对《西升经》的教义是相当熟悉和信服的,所以他的思想中有“自然生道”的观念不足为奇。
一种理论的产生必然有其产生的需要,没有需要就没有创新。结合老学与玄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重玄学的思路实际上是这样形成的:魏晋玄学家何晏、王弼等崇“无”,将老子之道理解为“无”,认为“无能生有”;稍后,玄学家裴頠、郭象等又将老子之道理解为“有”,认为“无不能生有”,“万物独生而无所资借”;传入中国后的佛学三论宗的中道观则崇信“非有非无”,将老子之道解释为“有无双遣”。这样一来,老学、道家、道教理论如果不再向前发展,就明显地落后于佛学。东晋直至隋唐时期的佛道论争,也一再地反映出佛学在理论上屡次嘲讽道教理论贫乏,特别是抨击老子之“道”肤浅无内涵。于是,一方面产生了“老子化胡说”之类荒诞传说,以便将佛学精华据为己有;一方面“以庄为老”,在魏晋玄学的基础上发展出重玄思想,将“有”、“无”、“非有非无”统统视为“执滞”,主张一切无所滞、无所执,“有”也好,“无”也好,“执滞”也罢,“不执滞”也罢,一切任凭自然,自然该怎样便怎样,不要有意去遣除,也不要有意不去遣除。这种“重玄之理”,实质就是“自然而然”。
因此,“重玄学”既是一种方法论,又是一种本体论。它可以为各学派、各教派所利用,但它本身不能成为一个学派,因为它不能自成为一个学术体系。因此,前述所谓“老学重玄”、“道教重玄”、“道家重玄”实际存在外延上的区别:“老学重玄”是指《老子》一书及历代注解此书而形成的注疏体系所包含的重玄思想与重玄思维方法,“道教重玄”是指道教教理体系与义理阐释中的重玄思想与重玄思维方法,“道家重玄”是指道家学派理论体系中的重玄思想与重玄思维方法。蒙文通、汤一介、卢国龙等学者所论乃“老学重玄”的源头,李大华所论乃“道教重玄”的源头,何建明所论乃“道家重玄”的源头。在同一属性界定范围内,除了李大华与卢国龙在“道教重玄”的源头问题上认识显然不同外,其余见解并不存在矛盾。“老学重玄”、“道教重玄”、“道家重玄”三者义蕴虽相互有所涵盖,但不可视为一体,混为一谈,应该说,作为“重玄之道”的不同外延,都有其存在的根据。
二
明确了“重玄学”的内涵、属性与外延,我们便不难判断上述几种有关“重玄”思想源头的见解,究竟孰是孰非。首先,在未发现新的反证材料以前,我们只能相信成玄英、杜光庭等人对孙登《老子注》的判断,无法怀疑孙登《老子注》作为“老学重玄”思想的源头的结论。因为,据成玄英、杜光庭所说,上面所提到的成玄英有关“重玄”思想的典型表述来自孙登,孙登是第一个在解注《老子》一书时“托重玄以寄宗”的,即运用重玄思维方法作为解注《老子》一书的纲领。而李大华将“道教重玄学”的源头也追溯到东晋孙登那里,就显得比较牵强了。因为,他既不是道教徒(有的学者将孙登说成道士,这是错误的,蒙文通先生早在40年代便驳正了这种误解),也不是为了道教的教理需要而注老,所以,道教教理运用重玄思维的历史不宜追溯到孙登那里。如果一定要寻找“道教重玄学”的源头,那么,卢国龙所论顾欢《老子义疏》为南朝道教重玄学之始的见解大约是言之有据的。
其次,对于何建明将“道家重玄学”的源头追溯到庄子的见解,笔者以为既有其独到之处,也有可商榷之点。作为重玄思想的源头,应该有两个条件:一是具备重玄思想的主要内涵,二是具备重玄思想的典型表述。按照这样的理解,尽管我们可以从《庄子》一书中,感受到齐同万事万物、玄通不滞的思想倾向,但按照重玄思维来看,这仍然是执滞于“不滞”、“齐同”。更何况《庄子》一书除了其中的《齐物论》等少数几篇提出过无是无非、“道通为一”的见解外,找不到类似于“双遣”、“重玄”的表述方式。只有郭象的《庄子注》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这种表述方式:
《庄子·齐物论》: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郭象注:今以言无是非,则不知其与言有者类乎?不类乎?欲谓之类,则我以无为是,而彼以无为非,斯不类矣。然此虽是非不同,亦固未免于有是非也,则与彼类矣。故曰类与不类,又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也。然则将大不类。莫若无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于无遣,然后无遣无不遣,而是非自去矣。成玄英疏:类者,辈徒相似之类也。但群生愚迷,滞是滞非,今论乃欲反彼世情,破兹迷执,故假且说无是无非,则用为真道,是故复言相与为类,此则遣于无是无非也。既而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
《庄子·大宗师》:仲尼蹵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郭注: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
这里,郭象在解释庄子原文“类与不类,相与为类”的大意时并没有直接导出“双遣”思想,而是在随后的发挥中提出“双遣”概念的;成玄英在进一步疏解“类与不类,相与为类”时也只是导出了“遣于无是无非”的结论,在随后解释郭象的“双遣”概念时才导出“遣之又遣,方至重玄”的思想。显然,郭象在注解庄子的这种齐同有无、是非的思想时,无法直接将之解释为“双遣”与“重玄”,而是就庄子的“言外之意”向前发展了一大步,提出了“既遣是非,又遣其遣”,“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的“双遣”思想。成玄英“重玄”思想的核心正是这种“双遣”思维。实际上,何建明已经注意到了郭象的这一贡献,指出:“在孙登以前,西晋道家玄学者郭象已明确地阐述过成玄英等人所极力标榜的‘双遣’重玄思想。”成玄英的重玄思想“正是在隋唐佛教思想与郭象、孙登以来的中国重玄思想相契合而共生的产物。也正因为有了较高思辨水平的佛学思想方法的引入,才使得他的重玄学理论达到了比郭象、孙登等人高得多的水平。”“与其说是郭象注《庄子》,不如说是《庄子》注郭象。”[6](p31)这种见解应该说是非常恰当的。但令人费解的是:既然认为是郭象首先阐述了重玄思维方法,而《庄子》只是郭象借以阐发思想的注脚与支点而已,那么,道家重玄学之宗就应当是郭象,为什么反倒归到为郭象作注脚的庄子身上去了呢?此外,我们不妨将上述成玄英关于“重玄”思想的典型表述再作些分析:成玄英的“重玄”思想的主要内涵是“双遣”,而成玄英明确说过,其重玄思想以孙登为宗(注:说见成玄英《道德经义疏》“开题”。)。由此可以推想,孙登的“重玄”思想也一定是以“双遣”为基本内涵的,而孙登在注老时不可能突然产生这种“双遣”思维方式,必然是有所启发与宗承的。上引僧肇的文章与支道林的诗句都说明其前已产生“重玄”思想,那么再往前推,这个先驱是谁呢?在当时“晋人以庄为老”、郭象的《庄子注》如日中天的时代大背景下,这个先驱只有可能来自玄学名家郭象及其《庄子注》。因此,笔者以为,“道家重玄学”的源头只能追溯到郭象那里。并且,可以由此进一步推论,郭象提出了“双遣”思维方法以后,孙登等人将其运用到注解《老子》的工作中,因此产生了“老学重玄”思想与思维方法,然后便是道教学者吸取郭象道家“双遣”思维方法与孙登老学“重玄”思想,从而产生了道教的“重玄”学理论。随后,佛教三论宗中国初祖鸠摩罗什及其高徒僧肇等人在不同于正始玄学的重玄之学方兴未艾的历史背景下,意识到要使佛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就必须借助中国固有的哲学理论,于是纷纷注《老》解《庄》,接受郭象与孙登的重玄思想,从老庄的哲学思想中吸取养分,最后隋唐时代的高僧吉藏运用“重玄”思想重新解释佛教的“二谛”论,将之发展为四重境界,指出:原来以有为世谛,空为真谛;以若有、若空为世谛,非有、非空为真谛;如今则要以“空、有为二,非空、非有为不二,皆是世谛,非二、非不二,名为真谛”。这就是说要在原来否定空、有的基础上再否定非空、非有。这就达到了“重玄”、“双遣”的思想境界。
理清重玄思想的上述来龙去脉并不需要非常复杂的论证和旁征博引,但时贤为什么既看到了郭象《庄子注》的深远影响,又囿于孙登与佛学的光圈而顾左右呢?笔者以为个中原因可能在于:一则如上文已经提到的,没有将“老学重玄”、“道家重玄”、“道教重玄”的外延性略加区别;二则由于“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定论深入人心,似乎隋唐时期只要与佛学相近的理论大约都是佛学影响所致。殊不知,中国先秦及秦汉道家的许多思想本来与佛学有相通之处(如道家的虚无观与佛学的空论),而且佛学传入中国后也逐渐吸收了道家的许多理念,导致其与道家思想更加接近,正因为存在这样的互通与互补关系作为土壤,才导致了所谓“老子化胡说”的产生。
总之,笔者以为两晋隋唐的“重玄”思想孕育于先秦老庄道家思想,由西晋末年的玄学家郭象在其《庄子注》中第一次提出这种思想的“双遣”、“三翻”的典型表述,从而形成以“双遣”、“三翻”为特征的重玄理论,并非受佛教影响而形成,而是为佛学理论所吸收,同时也为道教义理所摄取,因而不能谋求把它归属于某一家某一派。
收稿日期:2001-11-09
标签:玄学论文; 老子化胡论文; 化胡为佛论文; 庄子注论文; 老子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孙登论文; 玄英论文; 道家论文; 佛学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