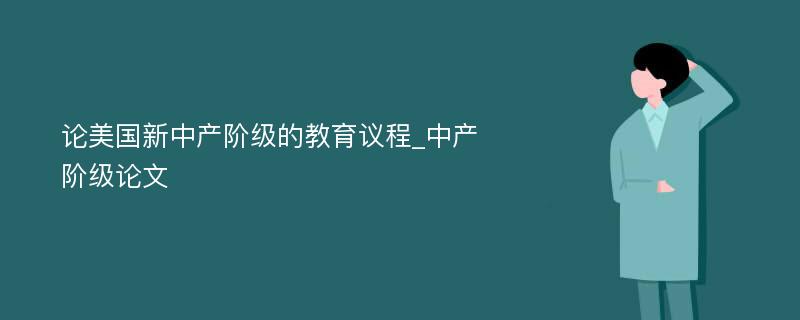
论美国新中产阶级的教育议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程论文,中产阶级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4)05-0013-10 20世纪是美国新中产阶级崛起和飞速发展的时代。有学者将其称为“白领薪给集团”,也有学者称之为“白领雇员集团”,他们作为社会存在,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并影响了社会的文化。关于新中产阶级与教育的关系问题,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还是教育学、管理学都已有诸多论述,此处便不一一赘述。已有研究大多从教育与社会分层、教育与社会流动、中产阶级与教育消费等方面讨论美国的新中产阶级与教育的关系问题,进而形成了许多关键词,比如“文凭社会”、“趣味区隔”、“文化资本”等。而本文将从梳理美国新中产阶级的阶级特征出发,来论述在其影响下美国新中产阶级的教育诉求,以及在实践教育政策文本中的体现。 一、新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①是一个比较流行的概念,但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在学界是存在争论的。最早提出“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的是马克思,马克思从社会群体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出发,指出“中产阶级”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富农、律师、医生、牧师、学者等,中产阶级的主要社会职能是维护社会稳定,而一旦失去中产阶级,或者说大批中产阶级落入社会下层就会激化社会矛盾,进而引发社会革命。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必然趋势之一就是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和中产阶级群体的缩小,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② 在马克思之后,许多学者围绕着“中产阶级”的概念进行研究,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派学者的观点:一派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将所有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群或者所有通过工作获取工资和薪水的人群都归结为无产阶级,即他们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不断消亡的社会阶层,由于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因此他们在本质上等同于“无产阶级”,他们将会成为社会的主体,也就是整体社会的“无产阶级化”。③另一派被称为“修正派”,以伯恩斯坦为代表,他们赞同德国经济学家、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古斯达夫·施穆勒的观点,首次将包括公务员、技术雇员、管理者、办公室人员和销售人员在内的整个“薪金雇员”阶层称之为“新中产阶级”,并认为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弥补了马克思所说的“老中产阶级”衰落而带来的问题,“新中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化和“新中产阶级”的日益扩大化,实际上代表了工人阶级内在的分化与经济条件的改善,因而资本主义并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剧烈对抗,相反“新中产阶级”成了社会对抗缓冲带,并随着这一群体的不断扩大,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也日益稳定。④由此可见,机会主义与修正派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薪金雇员”阶层的归属问题,即他们是否是无产阶级的一员。 而首次全面研究中产阶级问题的是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他在《现代薪金雇员问题》与《新中产阶级》接受了施穆勒的“新中产阶级”观,将“薪金雇员”阶层排除出无产阶级,认为“薪金雇员”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并且这一阶层随着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推进而不断扩大。在莱德勒之后,“中产阶级”的话题就成了社会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诸如此类的著作包括《中产阶级的神话》、《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地位诉求和政治取向》,其中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成了研究“新中产阶级”最为重要的著作。而米尔斯所定义的“新中产阶级”的概念——新中产阶级即以领薪水为生的白领——也是本文所使用的概念。 在米尔斯的研究中,他区分了美国的“老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认为在美国并不存在欧洲式的、严格的、以“血缘”为根本的“秩序”、“身份”与“权力”的区隔,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与“农民”。在美国,富饶的耕地以及充分的耕耘机会孕育了美国式的“中产阶级”,也就是私人小企业主。他们占有小土地,信奉个人主义,强调经济自由,是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与杰斐逊政治理想的最佳结合。⑤19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的推进,资本的大量集中与垄断的出现,大公司制的盛行,洛威尔制⑥的推广;标准化、专门化的生产线模式,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一方面降低了对工人多样化技能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强化了对标准化管理的要求,私人农庄逐渐整合成了商务管理的实体,“管理社会”⑦开始出现,这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由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化浪潮,小土地不断被兼并,这把原有的私人小企业主推入了劳动力市场,他们不再以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为生,而以靠出卖知识、技术、服务来谋生活;或者说“操‘家伙’的人越来越少,而与人和符号打交道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他们所不沾手的一件事就是制造东西来谋生;他们依赖那架对制造东西的人进行组织和协调的社会机器谋生……协助某些人制造出来的东西转化为另一部分人的利润……监督着实际的制造工作并记录完成了的事情……他们提供技术和个人服务,同时教授其他人他们自己已经掌握的技能,以及其他所有通过教学传授的技能”⑧。因此,与其说美国新旧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不如说新中产阶级区别于旧中产阶级的最大特点是“职业”的转变——从靠操“家伙”到操纵“符号”和“人”,从靠“资本”和“土地”到靠“智力”、“组织”、“协调”社会机器的职业来获得直接的收入。并且,这一群体在整个20世纪的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从1870年到1940年,美国中产阶级雇员从75万上升到1250万;也正是在这一个时期,老中产阶级增长了135%,雇佣劳动者增长了255%,而新中产阶级增长了1600%。⑨到了20世纪80年代,全美的最富有阶层约占社会总人口的6.7%,社会下层约占6.2%,其余的87.1%都处于“中产阶级”的地位。⑩ 新中产阶级的快速发展,标志着拥有“专业”和“技术”知识的各级管理人员群体占据了社会的主流,“知识”、“文凭”、“效率”、“标准”、“客观”、“消费”开始在社会意识形态中普及,而这些也必将成为社会改革与政策制定的源头,教育政策也难逃其中(11)。 二、“科层机器”及其对教育的浸润 “科层制”是新中产阶级依存并信仰的组织模式,是新中产阶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既是美国新中产阶级崛起的重要因素,也是其延续发展的典型特征。正如前文所述,美国新中产阶级崛起的标志是“管理社会”的出现,也就是随着大工业的飞速发展,资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开始分离;在这一过程中,拥有资本的资本家被管理人员所挣来的利润养肥,而技术管理人员虽然不占有生产资料,却在实际上控制着生产资料,形成新的社会“权威”,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专业技术管理人群。 专业技术人群发号施令依赖的不是基于“身份”或“财产”而形成的权威,而是依赖技术理性,即一种运作于明确的规章和程序基础之上的等级权威结构。这便是“科层制”。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理想中的“科层制”是一种完美高效的运行模式(12):它将全体员工分成较小的单元,权威和责任明显分离,人员聘用主要根据其技术和专业资格来确定,详细的规章制度对员工的工作方式进行了严格规定,确立科层晋级制度。建立在技术理性之上的科层制,不依赖于个人及其人格特征,而是完全依赖于常规化、非人性化的规章制度与集权化的权威等级,这在极大减少了个人对工作和组织运作效率的干扰,增加了工作的专门化、专业性、连续性和中央监督机制的力度。为此可以说,所有的管理人员都致力于建构各种由智力技能组成的灵巧的科层制度。 但在现实中,科层制却是僵化的,它将窒息组织体制内雇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由少数人统辖整个组织会使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高度集中于那些位居高职的人手中;还可能会使雇员产生过分谨慎的态度,极力希望维持现状而无意革新。也就是说,科层制的本质与主旨本身,既有可能保障组织效率,也有可能降低组织效率。作为工薪雇员的新中产阶级,他们的“许多专业工作互不搭界,他们经过标准化并被纳入到经过培训的技能和服务的新等级组织之中;深而窄的专业化已经取代了自我培育和广博的学识;助理们和其他辅助性专业人士承担了日常琐碎的尽管也常常是错综复杂的工作,而成功的专业人士则越来越精于管理。在某些领域,这种转变如此重要,以致理性化本身都似乎被从个人手中褫夺过来,作为一种新型的脑力被植入睿智的科层制度当中”(13)。 新中产阶级对科层制的迷恋,实际上也浸润着教育实践与相关政策。这首先体现在新中产阶级造就的教育系统中的“资格证”等级与“专业化”的禁脔。在新中产阶级的庞大群体中,学校教师作为一类学术雇员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在美国所有的技术管理人士中大约有31%是某类学校的教师(14);而学校教师又通过教育系统“再生产”着符合既有新中产阶级范式的白领薪金雇员。以美国教师职业准入制度和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形成为例,其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科层制的植入。理想中的教师专业化,意味着教师的专业自主、专业自治和专业自觉。所谓专业自主,是指教师能自主决定日常教育教学行为,能在专业领域内自主制定决策,而不受学校中其他控制机制的干扰;所谓专业自治,是指教师专业团体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不受“外行人”的控制,主要是让教师在人事聘用、任命、资源分配、监管、纪律、奖励等方面享有自治权;所谓专业自觉,是指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的专业性有清晰的认识,明确教师专业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形成坚定的教师专业信念和崇高的专业理想,主动维护教师专业的声誉等。而在现实中,在倡导教师资格证和职业进阶制度的表面,是代表专业控制权力的教师委员会和各级教师协会,而在背后支撑这类制度“合法性”的却是等级森严的科层制程序。它以僵化的、静态的、“标准化的”、“专业化的”的政策文本,打断了动态的、“无法标准化”(15)的个体教师自身职业的发展过程;它以“规章化”的形式取代了个体教师自身能力不断充实完善的过程。“……他必须专业化,或者说他受到鼓励对此深信不疑……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科层体系的一员,这个体系几乎完全被其中产阶级的环境和知识的隔离状态封闭起来,脱离了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科层体系中,平庸制定了自己的规则,并塑造了自己的成功意象。而上升之路本身也可能会像创造性工作一样成为行政俗务。”(16) 其次,新中产阶级的科层制组织模式还造成了学校组织系统与知识筛选过程的“垂直分裂”。同其他所有大大小小科层制组织一样,学校也是依靠层级化、劳动分工、专业化、正式规范等方式来协调控制其成员,以达到共同的目标,这也是其行动的必要途径。(17)从美国学校的管理、监督部门上来看,在学校一级,有校董事会和校长;在学区一级,有学区的督学与教育委员会;在州一级,有“州立学校首席官员”或者称之为州督学和州教育委员会;在联邦一级,还有教育部和教育部部长。这在实际上,就已经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层级化组织结构。美国学校的知识选择同样存在着科层制模式。以美国的“全国课程”改革为例,在1991-1992年间,美国联邦教育部曾与其他联邦机构,例如全国人文基金会、全国科学基金合作,资助、奖励那些致力于开发七门全国课程标准的学者和教师。这七门课程包括科学、历史、地理、美术、公民课、外语和英语。(18)其目的是,通过确立“主要的”学科课程的标准,来构建一个“逻辑严密的”、“严格的”“学术要求”,并将其用于指导教师教育、教科书的制定,以及考试内容的设计,并尝试通过控制联邦政府的经费的划拨,来确保这种“学科的”、“事实性的”核心知识逐级往下在各个州、各个学区、各个学校推进。这实际上体现的便是知识筛选过程中科层制。它通过形成从“联邦政府—州政府—学区”以及各级学科专业委员会的权威等级秩序,通过“让全州、全国能够广泛采用的目标”的设定,通过课程评价的“标准化”与“中立化”的伪装,使得科层制介入实现“公共利益”的全过程中,并通过严格的层级化权威等级制度让全州、全国的个体公民都对“真正的知识”达成统一的意见与理解。这样便形成了等级化的知识和公共学校机制,形成了“领导者和追随者的概念——带领我们又回到了分等级的智力和启蒙的概念”(19)。 对教师的塑造、对学校组织的构建,以及对知识内容的选择仅仅是故事的一小部分,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新中产阶级价值观对教育的渗透:专业化的、标准化的、批量式生产的教师、课程与教学方式,浸蚀着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与其说是一个独立自治的系统,不如说是一个适应性的机构,适应着新中产阶级的诉求,进而再造着一个更为庞大的新中产阶级人群。 三、“数字意识”与“测量”、“客观” 与科层制这一特征直接相关的,是新中产阶级的“数字意识”。“数字是中性的。没有哪一个数字比另一个数字‘好’。”(20)在数字的世界中,没有阶级、性别、财产、血缘的偏好,每个人在这个数字的超级市场中都是孑然一身,一切都成了客观的百分比。这恰巧迎合科层制所依赖的技术理性的要求。新中产阶级可以据此建立起一套非人格化的、客观的标准与程序,进行“科学”的管理,而在这其中“科学”的“统计”、“计算”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洛威尔制所带来的生产流水线,也要求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尺寸、每一件产品都必须进行标准化,而这些都使得根源于“技术理性”的“数字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并千方百计地将这种数字技术或者说统计技术应用到一切“可说的”与“不可说”(21)的方方面面,出现了日常生活中我们非常熟悉基于人体测量学的“衣着民主”、“统计质量管理”、“现金出纳机”(22)等形式。当然,我们必须廓清的是,“数字意识”并不是20世纪的新生物。在英语世界中,“统计”或者“统计的”这两词最早出现于1790年前后,它来源于德语,与民族主义、科学革命的完成有着直接联系,但“数字意识”在美国的普及却是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尤其是以1878年《美国统计摘要》的出版为标志,不能不说这与新中产阶级的崛起有着直接联系,是新中产阶级的另一个典型特征。而这一特征在教育中的体现就是对“更多、更高频率的测验”的依赖,以及相随而生的对“客观知识”的偏好。 首先,最能生动体现新中产阶级“数字意识”的便是测量技术在教育中的推行。20世纪最初20年,测量运动如日中天。测量运动最初是和儿童研究紧密联系,被认为是一种确定儿童之间个体差异的科学方法,可以通过它来制定课程。其领袖人物是G.斯坦利·霍尔。后来随着将“科学”的法则运用到儿童研究之中、并获得更大的效率的推崇,教育测量思维便开始出现。当时已经开始使用的智力和能力测试包括: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和西奥多·西蒙开发的比奈—西蒙智力量表,试图以统一的标准比较个体的智力差异;以及斯坦福大学路易斯·特曼对比奈—西蒙量表的修订版本,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把比奈测验推广到普通学生和天才学生之中,直到今天,它依然是美国使用范围最广的个人智力测验。 如果说霍尔是将测量思维运用于儿童研究的话,那么桑代克则将测量的思维运用于高等教育。他首次在大学中开设了教育测量课程,并撰写了第一本关于使用社会测量的教科书——《智力和社会测量理论导论》。同时,桑代克为智力和学业测试的标准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撰写并讲授了测验设计,他还和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一起开发了一些领域的学业测试。桑代克认为:“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有数量的。想彻底了解它就要知道它的数量及质量。教育与人类的变化密切相关;一个变化是两种条件之间的差异;这些条件中的每一个条件只有通过它生产的产品才能为我们所知——做的事,说的话,表现的行为,等等。测量这些产品中的任一个都意味着以某种方式确定其数量,以便胜任者将知道它有多么大,比它们没有测量要好。”(23) 而由《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发起的“高风险测验”(high-stakes testing),即采用标准化考试来决定学生的升留级和毕业;同时随着1994年对《初等与中等教育法》的重新核准,《改革美国学校法》的出台,高风险测验进一步获得了联邦政府的资助,规定州政府应根据本州的标准来评价本州内学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然后根据评价结果判定处境不利学生是否在实现这些标准的过程中完成了年度进步目标,并据此对学校进行奖惩;甚至当下所谓教育测量与统计的“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这一切的一切都与新中产阶级的“数字”诉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次,便是对“客观知识”的认同。“知识”是中立的,是价值无涉的。“即使是那些强烈主张课程应由地方来控制的专家也会承认,在课程中存在着‘公共序列’——至少是在诸如数学、科学以及历史和地理的基本事实方面,它们与性教育是不同的,是不会也不应该引起争论的。”(24)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的语言学家赫什就开始探索公共学校应传授的基本要素与内容,并于1987年结集出版了《文化素养:美国人须知》。赫什认为,“核心知识”应成为美国公共学校中教授的基本内容。所谓“核心知识”,即西方文明和美利坚民族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的“事实”、“概念”、“日期”和“称谓”。他从艺术、宗教、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细化出5000个“核心知识”,他认为这是每个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应该掌握的基本“知识”(25)。“它囊括了一切内容;打破了世代、社会团体和阶级的鸿沟;它也许不是所有人的第一位文化,但由于它跨越了家庭、社区和地域的限制,因此它必然是所有人的第二位的、存在于每个人现实生活中的文化知识”(26)。而1981年,科尔曼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调查给“客观知识”的论点带来了“统计学”上的有力支持。科尔曼发现,在私立学校,特别是在天主教学校中,各类学生的学业成就普遍好于公立学校。这是因为在私立学校中,无论学生的家庭背景如何,教师都严格地按照学术标准来要求每一个学生,课堂讲授的也是“共同”的学术类课程,这就大大减少了来自家庭的“智力资本”对学生学业的影响,也就使得处于劣势地位的儿童与处于优势地位的儿童站在同样的学业起跑线上。这便是“客观知识”的价值(27)。 可以说,新中产阶级对“人”与“符号”的操纵已是炉火纯青,它在“科学”的名义下,要求所有的“人”与“物”都必须走向严格的“定量化”;将人看成是一个“纯客观”的现象加以剖析与肢解,极大地忽视了对人的内心活动、人的情感、人的需求的研究,忽视了将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研究;它把人看成“社会机器”的一个机械的组成部分,造成了人性的缺失、人的能动性的缺失,以及人的自我的缺失,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学校教育中,学生的所有能力是否都可以被测量,语言能力、理解能力、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合作乐观的学习态度,这些对于学习而言至关重要的能力是否能够被真实地测量;以分数为指针的学业成绩反映的究竟是学生的认知能力还是精英权力,它与学生的社会背景、家庭经济条件与文化宗教团体又有何种联系;显然,奥卡姆的“剃刀律”在这纷繁复杂的教育现实面前是惨白的。新中产阶级的崛起所进一步推动的技术至上主义的自负,将学校教育系统推向了“一无所有的经验主义”和“没有头脑的计算器”的深渊。(28) 四、“消费前卫”与教育的市场化改革 又一个与新中产阶级科层制的组织行为相联系的特征,便是其“前卫”的消费态度。当一个社会群体的一切都依赖于权威体系内地位的时候,便会使其更为疯狂地寻求在这一等级体系之内的地位,而这些地位则需要依靠个人在经济上的支付能力来认定。正如米尔斯所言,“在白领的等级体系中,个人往往因琐碎的等级划分而四分五裂……科层制打碎了声望的等级基础……在向上爬的过程中,他们常常会期待着与上一级形成认同”,“除非你能够不停地显示自己的支付能力,否则你就是‘不怎么起眼’的”。消费成了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花钱买高位”给了新中产阶级自我满足的虚幻感,“在昂贵的度假胜地——那里你谁也不认识;在豪华的旅馆——哪怕只住上三昼夜;在游船的一等舱——只包一个星期。大多数度假地都和这种地位周期相配合;职员和顾客像戏班一样共同做戏,似乎大家相互同意这种虚幻的成功的一部分”(29),它通过暂时满足消费上的愿望补偿他们与社会上层相形产生了经济上的自卑感。同时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新中产阶级的日益富裕,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日趋普及——“它假装尊敬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使其溶解并庸俗化”(30)——“消费者就是上帝”,“消费,消费,再消费”;这实际上是用一种“经济”上的民主概念消解、麻痹着现实存在着的意识形态与阶级上的区隔。 而这种“消费”诉求在教育中的表现,便是对教育市场化的赞同与拥护,附和着自由主义经济对“看不见的手”的推崇。教育是可交换的商品,家长与学生是教育商品的消费者,学校是教育商品的供给者,并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方面满足消费者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保证教育商品的高效生产,从而实现学校的“市场控制”。他们深信,“源于市场普遍法则进行的社会重组而引起的加剧竞争,不但会使质量得到改善,而且还能向有‘选择自由’的消费者提供种类丰富多样的服务”(31),并提出了几种市场化改革模式:第一种模式,“选择公立学校”,它是在一个学区或者一个州的范围内为学生提供入学的机会;第二种模式,既可以选择公立学校,也可以选择私立学校,并通过“学费退税”或者补助等形式鼓励家长选择私立学校,从而促进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的竞争,来实现“优效学校”;第三种模式是“政府资助下的私有化改革”,即由政府资助父母,让父母为孩子选择任何一所学校,并用质量监控、教师资格认证等形式来保留政府的宏观控制权;第四种模式是“完全私有化”,即要取消所有的公立学校和政府对教育的补贴。(32) 而学校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满足“顾客”,即“消费者”的需求,而市场机制能够更好地保证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满足:第一,在市场环境中,教育商品的生产者有很强的内驱力去做出决策取悦学生和家长。(33)第二,市场机制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自由的选择”。人们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利益与需求作出决定。如果家长和学生对某所学校提供的教育不满意,他们可以选择退学,寻找更能满足自己需求的学校。(34)第三,在市场机制运营下,那些不能满足一定数量的教育消费者需求的学校将被淘汰出教育市场。对于那些幸存下来的学校来说,它们满足了教育消费者的需求,会渐渐繁荣壮大起来,但是他们也时时面临着新进入市场的学校带来的压力,这些新生力量以更好的方式提供类似的教育服务,或者满足了特定教育消费者的需求。在学生、家长需求的推动下能适应教育消费者需求的学校数量将越来越多。(35) 教育“市场化”逻辑中的核心命题是“消费者的选择是民主的担保人”。在新中产阶级的“市场化”主张中,“消费者”是至关重要的,是整个学校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生产的起点;而“民主”也被重新界定为“在无拘无束的市场中保证选择”(36)。世界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超级市场,教育被简单地视作像面包、汽车和电视一样的商品。公民的观念就是消费者的观念,民主就是消费的实践。(37)这使得民主不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变成了一个完全的经济概念。因此,市场将成为社会价值的最终仲裁者,效率和成本效益分析将成为社会和教育变革的“发动机”(38)。这些政策潜台词中关键的关键又与“数字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中“独立的个体——作为消费者——是没有种族、没有阶级和没有性别的”(39),而这一切都进一步诠释着新中产阶级“消费者就是上帝”的理念。但是,在一个现实的充斥着阶级、种族和性别冲突的社会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五、“后卫政治”与教育改革的“钟摆” 与美国新中产阶级前卫的消费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相对保守的政治姿态,米尔斯将其称为“后卫政治”,即所谓政治上的“无根性”。对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属性的判断,学界是存在争论的,要么是沿着马克思所创设的经典路径——中产阶级最终将走向无产化,与无产阶级融为一体,成为革命的一员;要么是沿着修正派的路径——中产阶级的总量不断扩大,使其成为大资本家与劳工阶层的缓冲器,作为一支稳定社会的力量,它的存在将使自由资本主义得以延续,甚至有可能在将来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下一个时代是属于他们的”;要么认为新中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保守的,是资本家的帮凶和走狗。而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意图行事政治权力都需依赖三方面的因素:意愿、机会与组织——意愿有赖于该群体对自身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机会受限于该群体的社会地位;而组织则与意愿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因此,理解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属性,首先要理解的是它的政治意愿。 一方面,与政治意愿密切联系的是某一社会群体的“政治敏感度”。早在20世纪初期传播学的研究就已经尖锐地批判了现实中的“政治敏感度”的虚幻性。也就是说,在信息传播的世界中,一方是个人,另一方是政治事件与权力,这两者之间的鸿沟依托于大众(中产阶级)媒体的联系,“现代政治一如戏剧,有导演、舞台、一群演员,还有最重要的幕布,用以分隔舞台上所演的行为——对此观众可以从后台进入,那才是‘价值观分配’之所在”(40)。大众媒体将饱含着实体政治利益的信息压缩简化形成许多朗朗上口的标语式的口号,并由此缔造了一个由刻板印象所形成的“假环境”。在这出戏剧的幕后,是观众看不见的政治世界;而观众仅仅通过一些耳熟能详的“口号”、“象征”、“常识”来对这个“假环境”进行判断与反应,这种判断也必然是不真实的。也就是说,在现实社会中,大众媒体(中产阶级)通过预设大众(中产阶级)的政治情感,消解了真实的“政治敏感度”,带来的结果便是冷漠的政治态度,形成了新中产阶级政治上的“疏离”现象。另一方面,新中产阶级的“前卫消费”也进一步减少了他们发起政治运动的可能性。“他们拥有较为干净、声望较高的工作,并且意识到他们底下还有蓝领大众,这使得他们感到投身到激进的但却可能失败的运动中去得不偿失”,“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没有任何持续的不满,也不会因其进行任何有责任感的斗争”(41)。因此,新中产阶级面对的政治问题是,他们是一块“平衡木”,是一个“跷跷板”,他们拥护与跟随的是“最有可能取胜的集团与运动”。 新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态度或者“后卫政治”的姿态很好地解释了20世纪以来美国公共教育改革中的“钟摆”现象——在“进步”与“保守”之间不断游移。20世纪初由进步主义运动所引发的进步主义教育改革,推崇“儿童中心”、“社会改造”、“社会效率”,这一方面暗合了新中产阶级对社会上层充分关注个体儿童的兴趣、探寻个体的发展以及反思的迎合,对新中产阶级眼中“雅文化”的附庸;而另一方面,“科学”的测量、“有效”的课程方案、“标准化”的教学过程又契合了新中产阶级的“数字意识”;新中产阶级成了进步主义教育改革的主力军(42),这本应该是一项美好的事业。但来自威斯康星的“红色恐慌”颠覆了这一切——进步主义对“共同认知”、“合作主义”、“社区主义”、“民主生活”的强调,与自由政治、教科书的改造联系起来促进国际理解,讨论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些都使得它们被有意无意地、暗示地将其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43)因此,为了转移和避开批评,当时的许多教育家开始有意识地“淡化进步主义的特征,以免他们被视为颠覆分子,他们大力强调'3R's',‘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对美国传统的忠诚”。(44)也就是说,在进步主义教育改革的后期,参与改革的新中产阶级实际上对麦卡锡主义采取的是默认与隐忍的态度,以免“惹祸上身”。因此,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斯普特尼克一号的成功能够在一夜之间使得美国教育在一夜之间从“生活”、“经验”、“活动”、“民主”、“合作”转向了“科学”、“数学”、“学术”、“高质量”与“高标准”。(45)新中产阶级无情地抛弃了进步主义教育改革,美国教育改革的“钟摆”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走向“保守”的一端。 而1964年随着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一声“向贫困宣战”的呐喊,公共学校改革成了整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议程。约翰逊总统信誓旦旦地宣扬,“解决美国所有社会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教育”(46),教育者就是“‘向贫困宣战’的斗士”(47)。轰轰烈烈的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了,学校成了这场“伟大”的社会运动的重要阵地,教育改革的“钟摆”再次随着新中产阶级投入自由民主社会主义的怀抱而发生了摆动。补偿性教育、促进种族融合、扩大职业与技术培训,在强势的自由主义政治力量的驱动下,新中产阶级怀着对社会下层的同情,以及对社会上层“慈善”与“施舍”的蹩脚模仿,开始大面积地参与到这场教育改革之中——大批的白人教师参与到黑人社区的教学改革、人本主义知识分子振臂高呼社会机器对人性的异化、要求“去学校化”。 但好景不长,当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那些试图通过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来解决贫困问题、种族问题和失业问题的努力,最终沦为街头巷尾的打架斗殴时;当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反主流文化、反越战、支持民权运动的校园反叛者,最终沉溺在奇装异服、毒品和无节制的声色犬马之中时;当为争取平等的社会权利而奔走呼告、疲惫不堪的美国白人教师与非裔知识分子成为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黑人激进主义运动最终的受害者时,保守主义就成了另一条出路。也就是说,面对注定要失败的社会教育改革,新中产阶级的向心力再次发挥了作用,“新左派孕育了新右派。”(48)迈克尔·哈灵顿说得好:当“伟大社会”的最后一线希望淹没在自由主义的群氓运动中时,保守主义的“伟大”复兴就开始了。(49) 在20世纪美国教育改革的“钟摆”现象中,我们看到了新中产阶级的“摇摆不定”,“他们思想上犹豫、迷惘、彷徨,行动上漫无目的、缺乏持久性。他们忧虑、怀疑,但是和很多人一样,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忧虑和怀疑什么。他们在政治上也许容易激动,但却缺乏政治热情;他们是合唱队,因为胆怯而不敢开口,遇到掌声又会歇斯底里。他们是一群后卫”,“在美国社会的政治市场上,新中产阶级正在高声叫卖自己;任何看上去足够体面、足够强大的人都可能占有他们”(50)。而正是这种“摇摆不定”,使其发挥了巨大的“向心力”作用,使得教育改革乃至整体的社会改革如同“钟摆”一样,永远不会偏离社会主流价值太远。 最后,笔者还想对本文的立场做进一步的说明,本文并不是阶级决定论者,分析新中产阶级的阶级特征及其在教育议程中的体现,只是为了说明阶级这一维度在教育政策与实践中所扮演的作用,并不是说阶级决定一切。恰恰相反,在教育这个庞大的社会系统之中,阶级、性别、族群、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往往是复杂交织在一起的;其他的维度还有待后续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①“中产阶级”与“中等阶级”、“中间阶层”基本上是同一个概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使用了这个概念,当时德文版的表述是"Mittel Klasse",英文版的表述是"Middle Class",中文版的表述则有“中等阶级”、“中间阶级”等。周晓虹.再论中产阶级:理论、历史与类型学:兼及一种全球化的视野[J].社会,2005,(4):3。 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剩余价值理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③Karl Kautsky,The Class Struggle(New York:W.W.Norton,1971)。 ④Eduard Bernstein,Evolutionary Socialism(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1)。 ⑤朱世达.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演变与思考[J].美国研究,1994,(4):41。 ⑥洛威尔制,麻省梅里曼克河沿岸洛威尔的工厂体制,其主要特点是大量投资,在统一的管理模式下,将素有的工序集中到一个工厂内完成,工序专门化,以减少对工人技能的要求。朱世达.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演变与思考[J].美国研究,1994,(4):42。 ⑦James Burnham,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41)。 ⑧⑨(13)(14)(16)(29)(41)(50)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周晓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51,49,87,100,101,201-202,252,280。 ⑩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18。 (11)Michael Apple,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New York:Teacher College Press,1996),52-53。 (12)参见:Max Web,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New York:Free Press,1947);John E.Chubb,Terry M.Moe,Politics,Markets,and America's School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0);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92-202。 (15)(19)迈克尔·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4,86。 (17)John E.Chubb,Terry M.Moe,Politics,Markets,and America's School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0),26。 (18)Diane Ravitch,Left Back:A Century of Battles over School Reform(New York:Simon & Schuster,Inc.,2000),432。 (20)(22)参见: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的历程[M].谢廷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9.204,231。 (21)Michael W.Apple,Kristen L.Buras,The Subaltern Speak:Curriculum,Power,and Educational Struggles(New York:Routledge,2006),272-273。 (23)E.L.Thorndike,"The Nature,Purpose,and General Methods of Measurement of Educational Products",The Measurement of Educational Products,Part Ⅱ,Seventeenth Year —Book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Bloomington,IL:Public School Publishing,1918,7。 (24)E.D.Hirsch,The School We Need and Why We Don't Have Them(New York:Doubleday,1996),37。 (25)E.D.Hirsch,Jr."What Literate Americans Know",Cultural Literacy: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7),152-215。 (26)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7),19-20。 (27)Diane Ravitch,"The Coleman Reports and American Education",Aage B.Sorensen & Seymour Spilerman(ed.),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Policy:Essays in Honor of James S.Coleman,(Westport,Conn.:Praeger,1993),129-141。 (28)阎光才.教育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数据:兼议当前的大数据热潮[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4)。 (30)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91。 (31)Geoff Whitty,"Consumer Rights versus Citize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Policy",Unpublished Paper,University of London,Institute of Education,1994,1-2.转引自:Michael Apple,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New York:Teacher College Press,1996),92。 (32)埃尔查南·科恩.教育券与学校选择[M].刘笑飞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33)Milton and Rose Friedman,Free to Choose:A Personal Statement(New York:Avon Books,1981),140-178。 (34)Janet A.Weiss,"Control in School Organizations:Theoretical Perspectives",in Choice and Control in American Education Volume 1:The Theory of Choice and Control in Education,eds.William H.Clune & John F.Witte,113(New York:The Falmer Press,1990)。 (35)John E.Chubb,Terry M.Moe,Politics,Markets,and America's School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0),33。 (36)(38)(39)Michael Apple,Educating the "Right" Way:Markets,Standards,God,and Inequality(New York:Routledge,2006),39,36,32。 (37)迈克尔·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迈克尔·扬.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M].谢维和,朱旭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1。 (40)Mary Lee Smith,Political Spectacl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n Schools(New York:Routledge,2004),11。 (42)李颜伟.知识分子与改革: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43)S.Mondale,S.Patten(eds),School,the Story of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Boston:Beacon Press,2001),183-213。 (44)S.Foster,Red Alert:Educators Confront the Red Scare in American Public Schools,1947-1954(New York:Peter Land,2000),184。 (45)Dwight D.Eisenhower,"Our Future Security",in US Congress,Senate Committee on Labor and Public Welfare,Science and Education for National Defense: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Labor and Public Welfare,85th Cong.,2[nd] sess.(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8),1357-1359。 (46)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6),19。 (47)Hugh Davis Graham,The Uncertain Triumph:Federal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Kennedy and Johnson Year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4),53-57。 (48)Kristen Buras,Michael W.Apple,"Radical Disenchantments: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Disciplining of Desire in an Anti-utopian Era",Comparative Education,Aug.2008,(Vol.22,No.3):292。 (49)Michael Harrington,"The New Class and the Left",in The New Class? B.Bruce-Biggs,137(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Books,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