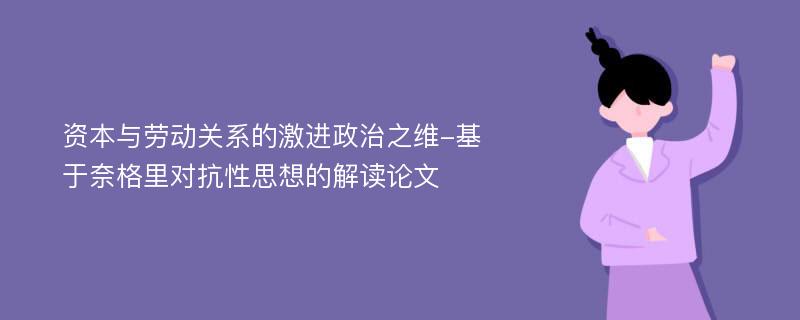
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激进政治之维
——基于奈格里对抗性思想的解读
李 胤
(哈尔滨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在当代激进左翼思想中,奈格里以对抗性重塑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资本作为主体”与“劳动作为主体”构成了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双重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只把资本主体当作研究的前提,而缺少对劳动的主体性的关注,从而忽略了斗争的实践本性以及无产阶级作为主体的实践潜能。劳动作为主体表达了一种与资本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对抗性是一种多元的、断裂的、非决定的、开放的社会关系的体系结构,它打破了资本主义矛盾辩证统一的总体性逻辑规律。只有澄清作为对抗性前提的生命政治语境及其生成的逻辑,这一思想的合理性才能被合乎现实的理解。
关键词: 资本;劳动;对抗性;主体性
十月革命失败之后,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呈消退趋势,革命问题似乎不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最关心的话题。虽然兴起于20世纪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探索早期革命失败的原因,并力图寻找新的革命可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探讨和争论的焦点逐渐从革命问题转到社会问题,从如何唤醒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等政治问题,转到了通过文化批判、交往手段等去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等问题。与此同时,资本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发展几乎使全人类都沉浸在资本的冰水中,而全然没有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已经从生产领域进入生活领域,实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全方位占有。正是在这种资本统治不断深入,而反抗资本的革命趋势不断弱化的境遇中,后马克思主义激进左翼学者奈格里提出了革命主体性的问题,意图从主体的潜能出发,以主体的对抗性原则重塑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为反抗当代资本的统治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论路径,这对重启并推进当代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双重逻辑
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对西欧革命失败原因的探索,从卢卡奇意图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到葛兰西的追求文化领导权的革命,再到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进入到了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的革命历程,这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待革命的问题意识的转向,它开辟了批判资本主义的新视域,在某种程度上解答了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然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理论家的批判意识所指向的目标并不相同。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人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切实地推进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但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普遍偏离了这一路径,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将其对意识和文化等不同视角的批判与无产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而只是从各自的观点出发去揭示他们所发现的社会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社会改革方案。对此,佩里·安德森总结道,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1]。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实践,转而去用哲学或社会学的话语去谈论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现在的斗争形式只是一种基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斗争,这种斗争形式注定了它只能在资本主义本身的范围内进行。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造成了何种形式的人类困境,思想家们就针对这种困境予以批判,但结果只能是对资本逻辑的揭示和改良,却无法超越资本逻辑本身。由此,致力于消灭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斗争从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解放运动发展成为一种纯粹的学理性的批判活动,从而忽略了斗争的实践本性以及无产阶级作为主体的实践潜能。
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强调资本对人的统治为出发点,即把资本主体当作前提来进行批判研究。奈格里在批判这种“假设资本作为主体的前提”过程中指出,“通过这些假说,生命、社会和自然都受到了资本生产力的影响,从根本上被剥夺了潜力。异化概念跨越整个理论领域:换句话说,整个行为现象学和存在的历史性被认为完全被吸收到资本主义剥削计划和资本主义生命权力生产中。科技被妖魔化了,启蒙的辩证法就这样完成了”[2]。从这样的前提出发,人只能处于资本的对象性的客体状态,结果是,“对于革命者来说,唯一的选择是坐下来等待重开历史的事件;对于那些不是革命者的人来说,唯一的选择是泰然处之——安静的顺应天命”[2]。可见,革命在这种视域中只能是被动的,只能从资本出发,在资本内部反对资本,却无法超越资本的界限。
奈格里认为,这种资本的界限依赖于资本统治的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的“反抗是依附并从属于其所反抗的权力的。或许有人会向其提议使用具有马克思主义内涵的‘反权力’,但这个术语意味着次级权力,与其所反对的权力并无本质区别”[3]36。也就是说,如果依附于权力先在性的前提,反抗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越权力的范围。然而,事实是,“不应该将权力视为第一性,将反抗视为后起现象;相反,这听起来也许有些自相矛盾,但反抗是先于权力的”[3]58。这是因为,权力只能作用于那些本来是自由的主体,如果主体先天不享有自由,就像那些刚出生就成为奴隶的人一样,那么他们也就无法去反抗权力的统治;相反,只有主体是先天自由的,那么当权力作用于主体之上时才会引起主体反抗。由此,逻辑上先在的主体性及其反抗的动力,才构成了超越资本的革命的可行性基础。
那么,如何能够扭转把资本作为主体来批判的视角,从而超越资本的界限去推动革命的发展呢?其关键就在于找到包括资本在内的,真实的社会发展和革命倾向的动力来源,从而破除以资本自身发展为前提的假说。奈格里指出,从近几十年的发展来看,新自由主义重新确立了市场规范,否定了劳动的自主性权力,否认了劳动能够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观念。从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社会权力越来越导向由资本的私有财产控制的权力,而劳动的主观权力被褫夺。这样来看,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资本而不是劳动本身的发展。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尽管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掩盖了社会生产的领域,以至于危机虽然是由上而下去治理,却总是由下而上产生的,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对立、抵抗和要求所造成的”[4]。在这个意义上,首先要确认的是人的劳动的主体性而非资本的主体性,只有劳动的主体性才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可见,奈格里将社会的发展归因于生产层面,这与马克思从生产层面也就是从经济基础入手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一致的。马克思作为一位革命家,他的理论和实践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以认识世界为前提。马克思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的过程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来达成。然而,当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解主要集中于对资本逻辑及其运动规律的揭示,却忽略了对批判之后的问题的关注。也就是说,忽略了在认识世界之后对改变世界何以可能问题的继续追问。事实上,认识资本的逻辑不是变革资本的逻辑,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只提供了一个认识论前提,而不提供变革资本的行动方式。对于变革资本来说,这种变革只能由行使变革的人来完成。人本身之所以能够实现变革是因为人的劳动具有创造性的能力,劳动才是有生命的、给予形式的火,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劳动的肯定就是对生命本身的肯定。
此外,从绿色环保的角度来看,光伏发电与风力、水能发电一样,作为可再生能源,对保护资源、环境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
可见,在机器体系中,作为个体的工人已经不能决定自己的实际劳动,而只能存在于机器支配下的抽象劳动的生产之中。因此,“从劳动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而囊括生产过程这种意义来说,生产过程已不再是这种意义上的劳动过程了”[9]91。相反,劳动仅仅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成了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总之,“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9]91-92。这时,劳动以与之前不同的形式完全内在于资本的控制之中,奈格里指出,“当资本创造出不再属于非资本主义形式而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劳动过程时,这种吸纳就变为实质的。对马克思来说,在工厂内部生产出来的工业劳动形式是实质吸纳的典型”[3]164。因此,机器体系实现了资本对劳动之间关系的从“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的转变,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资本全面地控制了整个生产过程。
Pierro 'Little Touch of Christmas' Cabernet Sauvignon Merlot L.T.Cf 2014
二、劳动作为主体的对抗性逻辑
但是到了“机械论片断”,马克思指出的这种“形式吸纳”的关系结构发生了改变。活劳动被嵌入到了机器体系当中,这种机器体系“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9]90。在自动的机器体系运转内部,与之前相比,重要的转变发生了——工人与机器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在以往的生产过程中,工人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工具以灵魂,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而机器只是作为活劳动的劳动对象,是劳动改变物质形态的工具和手段,是劳动与自然之间的中介。但是在机器体系的生产过程中,一切都发生了颠倒,原本作为对象化资料和工具存在的机器,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机器的特征决不是像[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那样,在工人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方面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工人的活动表现为:它只是在机器的运转,机器作用于原材料方面起中介作用”[9]90-91。而相比之前工人掌控机器的情况,现在则是机器代替工人具有技能和力量,机器通过运转和调节,使工人活动变为那种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的工人活动。在这一过程中,“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9]91。
事实上,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中蕴含着最深层次的对抗性,这种剥削关系以资本对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为核心。可以说,只有在这种对抗性的初步定义中,作为资本增殖秘密的剩余价值理论才能够被正确地理解并得以发展。关于剩余价值与对抗性的关系,奈格里认为,以往关于社会的、抽象的一般劳动所生产出的剩余价值的整个分析,都是在对剩余价值进行量化的定义。实际上,剩余价值规律是通过对主体反抗的极端强调而形成。“劳动的创造性力量(如果它是自由的话),都不会倾向于定义资本:只有当剥削作为一个支配和压缩的政治过程,作为对社会的普遍控制的时候,才能直接决定价值和剩余价值。最初的反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只有剥削、限制和力量才能成功地解决它。”[6]101可见,剩余价值作为一种对劳动主体创造力量的占有,只有在剥削和对抗性的双重视域下才能正确理解。而以往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只把视角集中在单一剥削形式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转化和计算等问题上,而没有详细涉及剩余价值产生过程中同时蕴含着的主体的对抗性方面。事实上,对于工人来说,这是一种绝对的对抗性,这表现为,“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7]。
奈格里以对抗性构建起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如何能够破除当前以资本为主体的牢笼进而指向革命?事实上,以资本为主体出发去寻求革命的道路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资本逻辑始终以一种意图达到动态平衡的统一性来解释社会运动的真实规律。奈格里指出,对于资本逻辑内在的矛盾形式来说,它在“表面上有着不可超越的障碍,这种障碍在对资本‘不断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大。这个过程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平衡发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6]200。可见,资本逻辑的对立统一的总体性并不能真正解决矛盾。所以,单凭这种抽象的逻辑并不能在理论与历史之间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因此,以资本为主体施行的资本逻辑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把真正的现实神秘化为资本的现实,以至于无法在其内部指向超越资本的革命。
而在奈格里看来,对抗性就是这种反对现实的、历史的斗争形式。对于对抗性本身来说,它代表的是一种否定性。从否定性的概念来讲,这种对抗性的否定性是一种绝对的否定性。这种绝对的否定与黑格尔辩证法当中的否定是不同的,黑格尔辩证法中否定的最终目的是达到肯定,其预设的是绝对精神的演进,即通过否定与肯定之间的辩证逻辑及其层次的跃迁最终通往绝对精神。可以说,黑格尔否定的逻辑归根到底是一种基于绝对精神的总体性发展的逻辑。然而,这种对绝对精神的预设导致的结果就是否定性是无法超越绝对精神之外的,否定性只能在绝对精神内部进行逻辑的运演。而现实的历史发展并不指向某种确定的预设,它是从当下出发,通过对当下的否定而指向某种被构建出的新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对抗性的目的是不断地超出当前的体系结构。奈格里指出:“对抗中的两股力量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不是封闭的系统关系;或者说,当每一方在建构自己的认同时,由于否定性力量的存在,所以,所建构的同一性是脆弱的、暂时性的,非完整的。”[8]也就是说,对抗所具有的否定性力量具有打破传统同一性体系结构的能力。在奈格里看来,发展两股力量之间的对抗性关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进而跃迁到一个新的层次,而不是为了达到矛盾之间的和解。如果只是矛盾的和解,那么矛盾的双方仍然不会超出他们当前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对抗性不同于寻求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以及以和解的方式处理矛盾问题的总体性方法,因为这种对立统一的总体性只表达了一种客观的矛盾规律,而不是主观的矛盾的变革运动。客观的矛盾运动并不直接带来资本主义的灾难,灾难是人的主体的对抗性活动的结果。奈格里不仅没有否认过资本主义中存在的客观矛盾,相反,他是在承认资本主义客观矛盾的基础上,从主体的对抗性角度出发指向矛盾的解决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对抗性是通过不断地否定并激化造成矛盾的对立从而达到彻底的变革。
一时间,苞米、葵花盘长了翅膀似的飞向徐进步,徐进步顾上顾不了下,狼狈地蹿到了几个箩筐后面。无辜挨打的男知青们也跟着东躲西藏。
可以说,一方面,对抗性发展了矛盾的多元性而不是趋向于矛盾的同一化。依照对抗性去解决矛盾的对立,并不是使对立达到一种同一的维度。对抗性寻求的是矛盾的共同发展,是为了达到矛盾对象多元化的差异共存。而差异的共存必定不是一种最终的矛盾形态,它只表现为一种暂时性的状态,需要不断地进行更新。这一状态由上一个阶段的否定所确定,它指向了当前的存在形式;而且由于其暂时性,因而也表达了一种通向未来的趋向。可见,在这种对抗性的理解中,它总是作为当前阶段斗争的结果以及接下来新阶段的前提而存在。另一方面,对抗性表现为一种层次的跳跃。也就是说,对抗性并不是在原本的矛盾层次上达到对立的和解,不是依照原本的逻辑规律发展矛盾,而是意图突破原本矛盾对立的维度,在新的维度上实现多元化的存在形式。因而在奈格里看来,在对抗性中“没有线性的连续性,只有观点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不断寻求对抗中的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有节奏的研究中不断寻求叙述中的每一个跳跃,总是寻求新的叙述”[6]31。这种对抗性的本质使矛盾的对立发展面向了开放的空间。在这一开放的空间中,对抗性以断裂和分离的方式打破了矛盾对立统一的总体性形式,从而以承认总体内部差异和多元的开放性打破了资本“封闭的经济学理论”。对这一封闭体系的破除表现为对以“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运行的总体性逻辑规律的超越,实现的是对人的劳动为主体的活动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对抗性才具有指向革命实践道路的可能。正是基于这种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奈格里从主体性视角出发,揭示出了革命主体与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的关系。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一直到“机械论片断”之前,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总是表现为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组成的有机关系。然而在这种有机的结构内部,这两者的关系却始终是“外在的”。之所以是“外在的”,是因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总是吸纳外在于资本创造出的劳动行为,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劳动行为只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具体来说,生产过程一方面表现为活劳动利用资本提供的材料和工具去创造价值,另一方面表现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无偿占有。资本虽然可以在组织形式上宏观地控制整个劳动过程并占有劳动成果,好像劳动是在资本的控制之内进行的,但事实上,它却不能决定具体的劳动行为,这种创造性的行为在内容上只能来源于个体劳动者自身,因此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只能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奈格里指出,这种“同时处于资本内部和外部的现象”[3]164就构成了马克思所谓的资本对劳动关系的“形式吸纳”。
三、对抗性的生成逻辑
奈格里之所以提出主体的对抗性逻辑,这是资本发展的现实与理论思想相结合的成果。一方面,资本的现实发展需求催生了对劳动的主体性层面的关注。在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过程中,生产以工厂的机械化大生产为主。这时,资本逻辑追寻的是同一性的价值规律,资本与劳动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有机的关系,在这种有机关系中劳动主要以抽象劳动的形式存在。而到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合作化、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的社会化和网络化直接决定了社会的财富,这使得资本逻辑转而去寻求多样性的创造和发展,为了保障其自身价值的持续增殖。这时,资本不仅仅需要抽象的劳动力,更需要那种活劳动的创造潜能。这种资本需求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对劳动的关注从无生命的抽象劳动转移到了活劳动本身,即转移到了劳动的主体性层面。
另一方面,意大利革命的理论需要使得奈格里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寻找理论支撑。在奈格里对革命思想和道路的探寻过程中,马克思的《1857-1858经济学手稿》(简称《大纲》)是具有奠基性作用的文本,奈格里评价《大纲》“是马克思的理论和政治思想发展的核心”[6]3、“是马克思思想中具有能动性的中心”[6]17。而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文本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著名的、被学界称为“机械论片断”的章节则被奈格里誉为“我们在《大纲》中,也可能是在马克思所有著作中所能找到的运用矛盾而且建构辩证法的最高级例子”[6]178,它处于《大纲》中马克思理论张力的最高点。在奈格里的阐释中,这一片断蕴含着资本与劳动在生产关系上的分离从而导致他对抗性思想形成的秘密。因此,反思对抗性问题首先就是要揭示这一思想形成的秘密与资本现实发展关系的内在逻辑。
正是因为对劳动概念的重视,对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奈格里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有着两种主体的社会体制。其中,一个主体(资本)通过强迫劳动和强迫剩余劳动支配另一个主体(工人阶级)”[6]中译本导言6。在这种双主体的划分中,社会发展的力量需要诉诸工人而非资本的主体性。奈格里指出,资本在增殖过程中实现的财富创造和社会控制只是表面上的,“工人阶级是独一无二的财富的唯一源泉。因此,我们位于关于动态的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定义的核心,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本质是价值的创造者,这一本质包含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这些斗争一方面造成了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造成了阶级构成的增强”[6]100。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才是社会发展动力的源泉,虽然资本通过剥削工人创造的价值实现了自身财富增殖的幻象,但是在本质上,它却不生产财富。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是基于那种资本发展先于工人创造的思想,把社会的发展误认为是资本自身的功劳而非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结果,这实际上构成了对真实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的颠倒。因此,只有从劳动而非资本的主体性出发,才能确证社会和革命发展的动力源泉,并切中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真实本质。
然而,为了不至于使这种对抗性的政治行为沦为一种主观的革命乌托邦,必须在当下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中赋予其真正的现实基础。正如奈格里所说:“我们感兴趣的是形式上的机械论、差异性是如何以及通过什么转变成对抗性的。好,这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只有将客观前提转变为独立假设,或者说给它以活力特征的资本主义方面,才会不断回到它并且定义它。”[6]79因此,有必要深入到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去对这种对抗性何以可能的内在前提进行反思,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之处去论证对抗性的合理性。
奈格里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重新确认了劳动的主体性特征,那么从这种劳动的主体性出发,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表现为何种形式?它在何种意义上变革了以往以资本为主体的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的关系?奈格里强调,主体性视角为超越资本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必须澄清这种作为现实中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动力的主体性究竟如何运动,从而避免陷入抽象。针对这一问题,奈格里指出,“我们必须要遵循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主体的对抗性”[6]195。
在奈格里看来,劳动的概念应该在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去寻求。一方面,劳动概念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中被理解。劳动实践的定义即不能被给予,其本身也不固定,它由社会历史及其内在斗争所决定。因此,对劳动的定义本身应该到历史和社会的关系中去寻求。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劳动也是历史发展的前提,它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劳动概念主要指我们在使用中存在的价值,这种价值由劳动所创造。在这种劳动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不仅表达了主体对知识和能力的运用,而且可以看到社会和使社会活跃起来的各种活动的产生,这实际上就是生产本身的产生。然而,在由资本逻辑定义的劳动概念中,劳动只是抽象的劳动,是价值量的创造工具。但事实上,劳动不应该简单地定义为一种活动,任何一种活动,都应该是有价值的生产性活动。“劳动力的概念被认为是生产中相对独立于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运作的一种稳定价值的要素。这就意味着价值的统一性主要是指价值的统一性与‘必要劳动’的关系,‘必要劳动’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必要劳动在历史上是由工人阶级在改造劳动本身的过程中反对劳动的斗争所决定的。”[5]8在劳动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层面上,奈格里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指向一种基本的、激进的选择,这种选择使得对劳动的分析不仅成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破坏性力量,而且成为对另一个社会的一种主张或肯定”[5]7。
枣树叶片的光和速率以及枣树的蒸腾作用是影响枣树果实形成的两个重要生理特性,光和速率影响枣树植株营养的输送和吸收、蒸腾作用直接影响枣树的产量,因此研究施肥和覆盖对枣树光和生理特性的影响有一定的必要性。试验结果表明,经过覆膜处理的枣树叶片的光和速率优于未经覆盖处理的枣树,原因主要是覆盖处理改良了枣树的土壤质量,降低了土壤的水分蒸发量,改善了土壤盐碱化情况,减轻了缺水对于枣树造成的伤害。
这一机器体系之所以能够为资本立下汗马功劳,其产生和发展之所以是可能的,在于它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在优势,那就是它们能够创造出比以往更高的生产力,拥有着巨大的生产效率。马克思认为,这种巨大的效率“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9]100,而科技的进步又源于知识或一般智力的积累发展。因此,先进的科技在机器体系中的运用就把作为创造性来源的知识与作为掌控者的资本联系了起来。针对这样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9]92-93,从而被裹挟到了资本的生产之中。由此,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知识或一般智力就成了使资本朝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新的内在因素。而这种发展因为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向更高层次的变革,因而是社会运动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综上可见,马克思的“机械论片断”揭示了知识或一般智力被纳入到资本之后形成的资本完全统治劳动过程的逻辑。但奈格里认为,在其所在的时代,这种资本把知识纳为己用的逻辑不可能完全实现。他基于与马克思“一般智力”及其在生产中地位的不同理解,提出了在“生命政治”视域下“一般智力”脱离固定资本的限制而进行自主生产的新生产劳动过程。奈格里认为,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的理解“有着重要性和局限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点上,马克思只瞥见为未来而运动的种种力量充满了科学、交流和语言的力量”[10]350,这种理解只是把“一般智力”看作内在于资本统治的一种形式上的知识。但事实上,“一般智力”是由积累起来的知识、技能和技巧所创造出的一种集体、社会的智力。是通过生产与再生产,同样也在(劳动、情感与语言的)流动当中表现其自身的方式”[10]350-351。在帝国时代,这种集体的生产形式通过“图像、信息、知识、情感和符码以及社会关系”[3]99的联合而形成了一种非物质生产的霸权,从而具有了脱离资本统治的可能性。
在奈格里那里,他用“生命政治”这一更贴近当下主体生产形象的概念来代替非物质生产概念。之所以是“生命政治”,一方面是因为非物质生产劳动“不仅生产产品即客体,同时也再生产生产者之间的协作关系和社会关系即主体,在其生产能力和行为直接就具有政治性的意义上,这种生产是政治性的”[3]5;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劳动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力量,这实现了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的交叉,因而完全渗透到人的整个生命活动之中。这样,“生命政治”表征的就是社会中新主体性的创造和再生产,是主体生产的自主性的体现,它以一种整全性的意义代表了劳动主体在当下所处的生产关系的现实境遇。
奈格里的对抗性思想正是在这种生命政治的视域下产生的。“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看待世界,我们如何与他人互动都是通过社会和生命政治的产物创造出来的。”[11]生命政治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资本生产座架的新的生产语境,为我们认知新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从而脱离在传统生产过程层面上的资本统治,并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对抗资本权力对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规训,提供了“反抗并寻求主体性生产的另类模式”[3]36。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再仅仅表现为以资本为主体的批判逻辑,社会运动也不再仅仅表现为基于资本逻辑批判的改良。在生命政治视域下,劳动的内在的主体性表达了其与资本关系的对抗性本质,这表征着超越批判性,走向对抗性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激进政治维度。
结语
奈格里以“机械论片断”入手,从“一般智力”的发展出发,提出了一种生命政治语境下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新模式,为对抗性思想奠定了生产的现实基础。这种对抗性转变了自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来以资本为主体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阐释路径,打破了资本逻辑在社会运动中力图实现的矛盾的对立统一的总体性趋势,对透析当代资本逻辑的生命权力统治,对我们重新制定“驯服”甚至“超越”资本逻辑的方案具有巨大的理论贡献,对促进当代激进理论向革命政治行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不可否认,奈格里提出的对抗性的革命与真正的革命实践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群体能够真正成为这种对抗性的主体承担者。虽然奈格里提出了“诸众”的概念,但他只是提出了作为这一概念群体存在的“可能性”,并没有在“确定性”的意义上给出这一群体如何能够结合在一起以及共同行动的解答,因此对抗性的革命实践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这不仅是奈格里,甚至也是整个激进左翼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每年汛期洪水发生期,水体浑浊度高,含沙量大。农药、化肥、垃圾等各种杂物被洪水带入水体,易滋生细菌,造成有机污染与化学污染。而且雨季一般气温较高,杂物极易变质污染水体。目前水体净化完全依靠自来水厂,每到上游入洪时,自来水厂水处理便出现困难,不能满足用水需求。
随着计算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多媒体、互联网、云技术等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完全可以让学生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进行实践操作,将信息技术与实训教学相融合。信息技术将需要通过理论讲解而无法直接进行实训操作的这部分知识和技能用虚拟实训、微课学习等信息手段,让学生能直观地进行学习。学生可在反复的解剖拆装搭建编程以及观看微课过程中学习自动化生产线设备的拆装、系统搭建、编程、调试与维护等内容,昂贵的精密设备可任意拆装,操作失误不会造成设备损坏或人身危害。
参考文献:
[1]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高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44.
[2]Antonio Negri.Marx And Foucault:Essays[M].Cambridge:Polity,2017:19.
[3]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M].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4]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Assembl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200-201.
[5]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Labor of Dionysu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6]安东尼奥·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张梧, 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9.
[8]孔明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569.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0]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M].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1]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M].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 2004:66.
The Radical Political Dimen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Capital and Labor :Based on Negri 's Antagonistic Interpretation
LI Yi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radical leftist thought, Negri resharped the adversar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pital and the labor in capitalist society with antagonism. “Capital as subject” and “labor as subject” constitute the dual dimens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The social critical theory of western Marxism only takes the subject of capital as the premise of the study, but lacks the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ivity of labor, thus ignoring the practical nature of struggle and the practical potential of the proletariat as the subject. Labor as the subject expresses an antagonistic relationship with capital. Antagonism is a pluralistic, fractured, undecided and open structure of social relationship, which breaks the overall logic rule of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capitalist contradictions. Only by clarifying the biopolitics as the premise of antagonism and the logic of its formation can the rationality of this thought be properly understood.
Key words :capital; labor; antagonism; subjectivity
DOI :10.16614/j.gznuj.skb.2019.04.003
收稿日期: 2019-04-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70年代美国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18BZX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胤(1988-),男,黑龙江佳木斯人,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哲学基础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3X(2019)04-0020-08
责任编辑 李兰敏 英文审校 孟俊一
标签:资本论文; 劳动论文; 对抗性论文; 主体性论文; 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