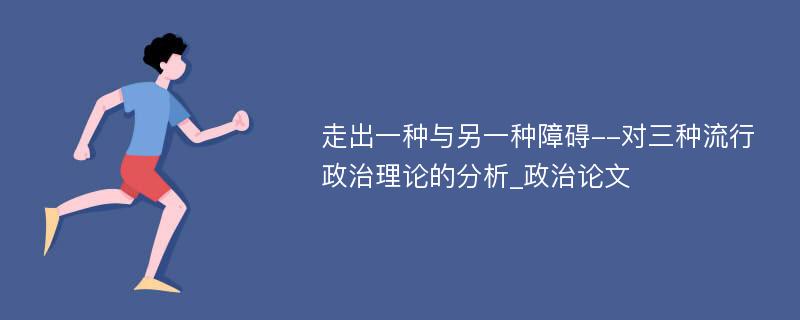
走出非此即彼的樊篱——三种流行的政治理论观点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樊篱论文,非此即彼论文,政治理论论文,三种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来,理论界深深浸淫着某些流行的政治理论观点。如强调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国家权威和秩序优先,社会民主可以暂缓,将国家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目标置于压倒一切的位置,忽视社会基本价值等。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些思想观点颇为各方认同。某种思想观点的流行自有其原因,但是知识界缺乏深人的理性分析,丧失其独立的批判意识,其后果难免造成盲目“跟进”,误入非此即彼的樊篱。这正是中国知识界和社会容易走极端的原因之一。
观点之一:国家行政力量对经济的推动
这一观点最初来自于国外某种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了赶超发达国家,不能走经济社会自然成长的老路,而应强化国家力量的推动。一些学者对所谓“东亚模式”和“亚洲经验”的考察,也得出了这一结论。1993年后,这一观点继续得以延伸,即由强调国家推动转而突出中央政府的推动,强调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和中央政府的集权,甚至主张中止分权式改革,以防国家的四分五裂。出于对失控的担心和动乱的恐惧,“集权说”流行一时。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国家行政力量对经济的推动和对市场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在于不能笼统提国家推动和行政干预,并夸大其作用。
我们知道,国家是一种来自社会又高于社会的公共权力机构。如果从权力资源配置看,在国家外部,存在着国家与社会的分权,在国家内部,存在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西方的现代化基本上走的是分权式道路。而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其表现是国家对社会的全面干预和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充分利用了西方国家所没有的巨大的国家行政组织这一传统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迅速积聚社会资源、广泛动员民众、建立权威秩序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由此笼统得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家的推动,并要强化中央集权的结论,就有些过于轻率了。如果根据这一逻辑推理,在高度集权的古代中国,在1949年后的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下,岂不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代吗?
事实恰恰相反。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关键因素是对国家统摄一切的传统集权体制的突破。对此,中国领导人的认识是相当清楚的。邓小平在1987年6 月发表的《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一文中指出:“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中国,权力下放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将统摄一切的国家权力下放一部分给社会民众,一是将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下放一部分给地方。由此形成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格局。正是这一格局调动了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才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并突破了延续数千年的传统的“大一统”结构框架。
由于中国正处于历史大转变时期,社会市场的发育,地方能动性的增长,难免呈一定的无序状态。正如长期关闭的闸门一旦开启而难以控制一样。面对这一情况,应以宽阔的视野加以理性分析。笼统强调国家行政力量推动和加强中央权力,势必压抑刚刚发育尚十分脆弱的市场的成长,扼制刚刚具有尚不太强的地方的自主能动活力。
根据世界现代化和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和趋势,我认为,在发展战略上,应明确和强化国家与社会分权,中央和地方分权,调动两方面积极性的意识;在策略上,则可根据情况作适当调整。切莫为了一时需要而将战略目标置之一旁,盲目推崇国家行政的推动。
观点之二:国家权威和秩序优先,社会民主缓行
这一观点的产生背景是,由于复杂的原因,80年代伴随经济改革出现的民主化进程屡屡受挫。有人根据东亚,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认为中国的首要目标是发展经济,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必须借助国家的强大权威,建立稳定的秩序,而民众参与的社会民主则可缓行。换言之,只有经济发展了,才可搞民主。这一观点颇为流行。不少人因此断言,只有20年后,才可谈民主!
民主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民主并非只是自然生长和仅供观赏的花果,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以社会参与国家,以社会制约国家。因此,社会民主和国家权威这一相生相克的对立物,都是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不可或缺的。离开了哪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都会失衡。不错,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通过国家权威和秩序优先,社会民主缓行的政治策略实现了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但人们在眩目于非凡的经济成就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衰败紧相伴随,“金权政治”已成为社会毒瘤,上至国家领袖,下至公务人员腐败成风。其深层原因便是社会沉浸在经济成长中,民众沦为单一的“经济动物”而失去“政治头脑”。当国家权力缺乏来自社会的参与和制约时,政治衰败在所难免。
与东亚国家和地区不同,中国通过革命,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权威。这种权威能量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和秩序,构建了基本的工业体系,但也曾导致过重大失误,乃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性后果。其重要原因在于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的约制。正是基于此,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由于人们对刚刚来临的民主的不熟悉,甚至将其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之物,忽视了“民主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邓小平语。)致使民主化进程屡屡受挫。但不能因此否定民主的独立价值,将国家权威与社会民主绝对对立起来,仅仅强调国家权威的功能。特别是进入市场化过程后,国家权力被侵蚀而造成政治衰败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君不见,因腐败而被解职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曾经是国家权威和秩序的最坚定捍卫者之一。国内外人士普遍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官员腐败高速增长的“两个高速增长”而困惑,其实这正是国家权力缺乏社会民主有效约制的重要表现。公共权力变质和官员腐败必然导致国家权威能量的迅速流失,将出现的是既无民主、亦无秩序的景象。
“民主不是万能的,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在中国现代化中,切莫将国家权威和秩序与社会民主简单对立起来,过分突出国家权威而忽视、乃至放弃对民主的追求。对所谓的“东亚模式”和“亚洲经验”,应批判性视之。
观点之三: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发展经济、满足社会大众生存要求,其他社会价值暂可搁置一边。
产生这一论点的背景是,80年后期以来西方国家一些人士屡屡以“人权”、“自由”、“民主”等社会价值观念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在对西方责难的抗争中,有人认为中国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发展经济,满足社会大众最紧迫的生存需求。至于诸如人权、自由和民主则因为是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口号而避之不及或搁置一边,似乎中国并不需要这些社会价值。
20世纪可以说是中国人为生存抗争的世纪。而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抗争,必然需要国家力量的组织,需要统一的国家目标整合分散的社会大众。对于个体来说,国家的目标成为至高无上,压倒一切,乃至唯一的指向。20世纪上半期是求亡图存,20世纪下半期是赶超富强。在这一背景下,个人本位的“人权、自由、民主”等社会价值很容易被忽视,一切由国家作主,国家全知全能。民众只需获得生存,一切皆足。
在20世纪这一各民族国家凭借实力而角逐竞争的时代里,将国家某一特定时期的目标置于优先地位,以其为中心,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将国家整体与社会个体,国家目标与社会价值绝对对立起来。离开了单个的社会个体,国家整体不过是“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语)。而作为社会个体的人,不仅需要温饱,还需要自由表达意愿,人身不受侵害,人格得到尊重,免于恐惧和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等。人的嘴巴除了吃饭外,还会说话。只有这样,人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人;民众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现代公民而存在。
在现代社会,国家之所以要制定宪法,重要目的之一是确立人民的主权地位和公民多方面的政治社会权利。只有如此,才能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实现国家整体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成功,除了提出“打土豪、分田地”这一满足民众生存需要的口号外,还与提出人民大众享有广泛权利的人民民主的口号有关。1957年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屡屡受挫,直至出现亿万人食不果腹的危机,不正是仅仅赋予人口以吃饭的功能而钳制人口的言论功能所导致的恶果吗?
所以,我认为,不能因为国家目标优先,而将社会价值搁置一旁;不能因为西方人士利用“人权”、“自由”和“民主”责难中国,而对这些社会价值避之不及。不论什么时候,富强、民主和文明都应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成为中国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
